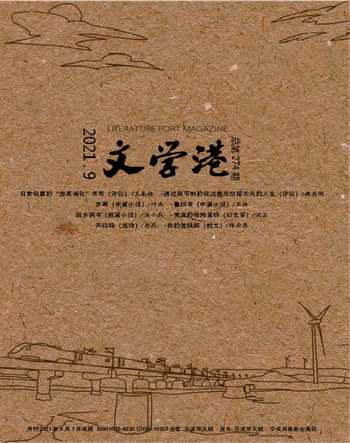杜湖旧事(散文)
沈银华
人,总是喜欢叙旧的。旧,久也。能被拿出来常说的事物,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旧事,旧物,旧人。记下几件有关杜湖的事,那么此文就题为杜湖旧事了。胡适先生说过,写短篇的文章,要用最经济的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部分。
(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去了观海卫的韩家、方家、庙桥、花桥,又从方家浦到徐家浦十塘海边,是旧地重游。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又再次踏上这块生长劳动的土地,特别是方家浦的六塘凉亭。当年小小年纪的我,为看护大队蜂场的蜜蜂,在凉亭里住了一个多月,到了夜里,别人都回家了,只剩我一人,真有点恐惧,虽近有水利处六塘闸看闸人,和东山红旗大队漁业队。如今,三间平顶的老凉亭没了,围边一沟沟的地没了,本该蒹葭苍苍、长满茅草和芦苇的小洋河没了,六塘闸依旧在,那看闸人,还有那渔民呢?不知还在不?在十塘徐家浦的海边,不错,是十塘,我向四周张望。当年,六塘的外边是海涂,里边是农田,海皇山是海中的小岛,而今日,已是陆上的小山。
中午受阿涛战友的邀请,在郑家浦吃了午饭。回来的路上,经过了阿章当年知青插队的村旁。在车上,他讲起了一件事。一九七○年某月吃完夜饭后,浒山黄金道地西边的一个门头里,阿章妈刚洗刷完在桌边坐下,灰黄的煤油灯闪着光。这时,和阿章一起在东海公社插队的同学,气喘吁吁地进来,说:“阿章妈,阿章妈,我给你话,你家阿章他……你心勿急,心勿急哦。”老人:“你说呀,我家阿章到底怎么啦?”同学:“你勿急,你勿急。”老人:“侬话吧。”同学:“造水库黄泥塌下来压死人啦,阿章他没事。”咳,阿章的这同学,可把老人吓得……原来阿章那日正休息,他的生产队开釆黄泥的山塘工地,发生了山体塌方,四位农民工遇难。有一年我在图书馆的慈溪烈士册里见到过,有记载。
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掘井人。吴作镆,造湖塘,人们记着他。上世纪的那代人,在党的领导下,做丁坝,围海造地。建水库,兴修水利。用汗水,用青春,用鲜血,用生命,用血肉之躯,创造了奇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为家乡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人们更应记着他们。
(二)
五十年前,建造杜湖水库。杜湖是由外湖和里湖组成,在现杜湖水库大坝的位置,原有一条低矮的湖塘,把湖隔开,塘南为里湖,塘北称外湖。塘靠西头有一桥,一闸,一减水坝,坝下方有一深潭,名为“白太子潭”,又称“白龙潭”。白太子即为东海龙王之子,据传,白龙居此潭。此潭深有数丈,即外湖干涸时,用最长的毛竹探测,也不到底。后来,有一日,来了一条黑龙,与白龙争抢此潭,发生恶斗,白龙战败,逃亡到白洋湖,这潭被黑龙占据。然而人们仍称白太子潭,是何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一九六六年大旱,我去六岙、蛇蛋岙砍刺柴,常从潭边经过。韩家人砍刺柴是有传统的,因没有山,只能砍些人家不要的带刺的灌木。
建杜湖水库时,我去参加了两次劳动,每次一个月,一次是西埠头村新址平地基,另一次就是在坝基挑黄泥。造水库大坝,我们叫造湖塘,生產队的壮劳力,自带钱粮,轮流参加,为时一个月。当然,工分还是记的。这是每个农民需承担的社务工。政府当时没有钱,是一种征集民工办社会事业的人力征用,这种社务工,是按地亩多少来核定的,每年根据水利工程量核定每年应分担的社务工,以工票拿到生产队换算成工分,计入下半年决算。
大坝筑基时,没用水泥,不像现今用水泥桩和钢管桩,只是用黄泥,一层层地碾压。那时也没有压路机,只是两辆不知是从哪里借来的“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开来开去,把我们排着队从山坡上挑来的黄泥,反反复复地碾压,一层一层地压,这就是当年的生产力,当年的水平。工地上,那些开拖拉机的,拿着三角架水平测量仪的,拿着图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几位领导,因为他们有文化知识,是最让我们一根扁担挑着两畚箕黄泥的农民敬佩和羡慕的。
五十年前,我一个农民工,只记得有王新红、阮祥尧、翁章根。
(三)
昨日,住在西埠头的友人发消息说,今秋冬,少雨水,水库水位下降了很多,被水淹五十年的西埠头村址露出了水面。
他回忆说,五十年前,里杜湖造水库大坝,水位提高,将淹没整个西埠头古村,于是决定整村搬迁到村后西边的山坡上,新村屋基的平整工程他是参与了的。其实我也参与了平坟挑土劳动。嘿嘿,今日想来,记忆犹新。当年,我们常在西埠头村后砍柴,这里有些许大坟,也有碗窑址,在平屋基时常有坟里的骷髅、骸骨出现,还有青色的破碗、破壶、破罐出现,要是现今,知道这是千年越窑的东西,我就会捡几样,留着玩。唉,可惜当年无知啊。
他还说,信风水的认为,西埠头村这个地方,是块风水宝地,两边是小山一直伸到湖中央,后面是高山挡住了西北风,东南面太阳一来出照射到整个村庄。曾有诗:“鸟鸣山更幽,清泉石上流,汇入杜湖中,润泽众生灵。”所以,先民就居住在这里,许多大坟也建在后面。村的东北面是栗子岙越窑遗址,千年前这里烧制的青瓷器,通过水路运到外地。这里有码头,其实埠头应该是码头,西埠头也即是西码头了。这里有瓷器,有茶叶,都可以装船运出去。如果讲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也应算一个。
(四)
巍巍五磊山,高高的马鞍岗,汇集了一股清澈的溪流,在大樟树下流入杜湖。山溪两边,石塔耸立,青松蔽日。云水相伴,树石相依,流水潺潺,山风阵阵。站在千年古樟下,仰头看浮云,低头看流水,好一个可神游之地也。
大樟树边,我们公社民工的宿营地,就在这里。临溪的一排草舍,是食堂,里边就是各大队民工宿舍。食堂里,有乾官伯、新富伯两位,有一位大胖子,不知哪位是,我记不得了。两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其实也不老,五十来岁吧。他们管做菜蒸饭,我们把米放在写有自己名字的铝制饭盒里,交给他们,下工回来就买盆菜和一碗汤就是了。最难忘的是食堂里用冬瓜酱油做成的红烧肉,一听是肉,吃起来就有肉的味道了,现今想来,有点不可思议。那时,我一顿能吃八两米饭。阿富伯说,你们这年纪,吃石头都能化掉。唉,现今只能吃二两了。岁月流逝,生死幻灭,你说怎能让人不感慨。
水库大坝筑成工程结束后,这块地方建了一个大砖厂,是慈溪最大的砖厂,全称“地方国营慈溪砖厂”,由慈溪县内好几个窑厂撤并组成的,观城卫前砖瓦厂也被并到这里。新建的窑叫“轮窑”,是一种新式的窑,烧出来的砖头是红的。以前我家旁的罗潭庙卫前砖瓦厂,在观城一带是比较大的,厂部和工人的宿舍设在罗潭庙內,有食堂,有厂长办公室,有会计间,有活动室,我们常去打乒乓球。烧砖瓦的窑是连体的,即两只窑并在一起,建在大塘河边上。这窑烧的是青砖、青瓦。青是什么颜色?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说法,应比蓝深些,比深蓝还深。又有黛瓦粉墙之说,看来黛与青近义了。烧红砖产量大,红砖比青砖坚硬。
人类社会在进步,青胜于蓝,红胜于青,人们择优而取,这也是一种必然。
(五)
我们宿营地的东北面,就是石湫頭,在杜湖的东边。石湫头,应是一个景点,湫,水潭的意思,温州的雁荡山,有大龙湫、小龙湫风景点,我们杜湖有石湫这个风景点。几年前,到五磊寺下院做佛事,专门去探寻这个石湫,如今在五磊寺下院内,以前在石湫头庙内。
宓家埭有个童家,我小时候就知道,因我老家的邻舍隔壁太婆娘家在童家。前年清明,去马鞍岗墩祖父坟头,扫墓回来碰到的、送我一支黄泥笋的阿伟,也是童家人。但我不知道哪个村是童家。从书上见过,七百多年前的元朝,童家有位当官的,叫童金,为纪念祖父童居易,办了一所学校“杜洲书院”。以前书院就是学校,“杜洲书院”直到明朝洪武年办了将近五十年。位置就在石湫头庙的位置,最大可能是这个庙就建在“杜洲书院”的旧址上。石湫头庙,现今只剩下一点点了。据老人们说,信释教的人都把这里当成阴间一个机构,它管辖山北一带的阴间事务。解放了,新的文化来了,寺庙曾被取缔,石湫头庙的房屋办了杜湖中学。我朋友家祥,他中学就在这里读的,他说,边上还有一小庙,叫“杜白将军庙”,是学校的教师住的。再后来,造杜湖水库的工程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一块上书仿宋体的“杜湖水库工程指挥部”字样的木匾挂在门旁,路边有松枝搭成的彩牌楼,上面插着红旗,写着“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电线杆上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这是指挥部留给我的印象。在大坝的工地上,人流滚滚,红旗猎猎,大喇叭里的歌声、人声和拖拉机声交结在一起,这是大坝工地留给我的印象。
(六)
杜湖岭,在哪里?在杜岙的最南端,也就是杜湖水库最南边,翻过岭就是山南了。那边的人,我们称山南人,山南人称我们为山北人。山北人名气大,如在上海、宁波、杭州,一说山北,都是晓得的。
杜湖岭,岭不高而挺秀,泉不急而飞翥,松柏参天,修竹满坡,古有一亭傲于岭顶,有“苍烟郁幽霭”之称。明人叶金胪,访友登上杜湖岭,作了五言诗一首,其中有几句:“一径入深碧,丛篁森涧陲。通以羊肠路,累以鹿眼篱。苍烟郁幽霭,斜阳漏曦微。群雀噪其中,与过皆惊飞。逶迤陟步顶,孤亭踞崔巍。岩树翠低蔚,野花馨暗滋。”
我笫一次过杜湖岭,如今只记得,山路小小似羊肠,路边的柴草没过人的膝盖,山上的树木也不甚高大。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隔壁的新桥叔带我去玩。翻过岭,右边有一小山村,叫罗家畔,在他亲戚家住了一夜。过了许多年,我去了一次岭下王家。这杜岙从西埠头往南走,有好几个山村,有解家、洪家、王家,据说以前还有张家。我有一战友慕宗兄,家在岭下王家,他家祖上也许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也许与阳明先生有交集。一九七几年回乡探亲,他让我带几本书给他兄长,再从兄长处带几本书回部队。他兄长叫阿明,东山中学毕业,复旦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后在宁大当教授。我在他家第一次看到了一套《资治通鉴》。我是和阿裕兄一起去的,他骑一辆重磅“永久”牌自行车,我骑一辆轻便“永久”牌,我们一同飞奔在水库东岸的山间公路上,他夸我车技好,我心里还美滋滋的。阿裕兄是我战友的兄长,很可惜,多年前因病走了,他和阿明兄,都是东山中学出来的,当年都在公社当干部。
东山中学是人材辈出的学校,能上这学校的人,真让人羡慕。作为山北人,没能上故乡这么好的学校,真是遗撼,也许是宿命吧。
前些年,又去过杜湖岭,岭已夷平,咳!
(七)
藏云溪,五磊山下,里湖东岸的老鼠老猫山边的黄泥岙中的一条溪坑。古人有诗“五磊润名寺,山暇藏云溪,身处仙境中,不觉三四里”。全长1.5公里,是以幽谷、清溪、怪石、奇树为特色的风景点。我曾作有一幅水墨《五磊藏云图》。
五十年前造水库时发生在这的几件事,是今天遇见的一友人与我说的。其一,就发生在黄泥岙。当时二十几人抬一块巨石,从山上下来。忽然,不远处响起了短促的哨声,随后传来“放炮了”的喊声,和“嘭嘭”的两声炸药爆炸声。石片纷纷飞来,幸亏大家放下巨石,就地扑倒得快。过了一会,大家以为爆破结束,慢慢起身。正在这时,又是“嘭”一声,一石片飞来,击中了一人头部。他应声倒下,当即死亡。其二,在打南隧洞时,石片“呼”的一声,从他的耳边呼啸而过,好险,好险啊,差一点点,就一点点,命要呜呼了。还有一次,打北隧洞,北面的洞口石质较松,是阿石,洞口随打随加固。有一天,他们吃完午饭回来,洞口已被塌方的泥石封住,好险,又好险。如若他们正在洞里,后果怎样?无法想象了。
他说起建杜湖水库时的这事,异常兴奋,手舞足蹈。他是亲历者,讲得很生动,使人身临其境,然而文字总是蹩脚的,再加上我的笔拙,只能这样记述了。胡适先生说,文要有物,文有物才能载道。
(八)
杜岙有一棵古柏,朋友,你见过吗?我在不同时日,见过三次。20世纪六十年代,去山南,途经杜岙,在溪坑边,远远向东望去,有一棵大树。阿桥叔告诉我,这是一棵千年古柏树,虽遭多次雷击,仍然昂首挺立,枝繁叶茂。这初见,当年里湖水库大坝未造,到山南的路在一条大溪坑两边,在两边的小桥、流水、人家之间。本世纪初,公路已通,我骑车去杜岙写生,古柏正好在路边,似一耄耋老人,主干依然,枝杈无几,我用笔记下,回家作了一幅《杜岙古柏图》。越三年又路过杜岙,见古柏已静静地躺在农家的屋后。杜甫有描写柏树的诗,我也想写诗,树龄长的柏树叫古柏,是承载着当地历史文化的,但我不知这棵古柏,有什么故事。思及宇宙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何为生命?生死幻灭。千年生命也只一瞬。那我们人呢?才百年啊……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寓意着一种精神,一种激励人的力量。水库建成五十年了,当年参加建造水库的那一代人,一部分也似这棵杜岙古柏,已逝去。他们已化为溪水,流入湖中,化为白云,飘在天空。我们祭奠一下他们吧!用水库里的青鱼,山间的杨梅,林中毛笋,湖外万顷良田里刚打下的金黄的稻谷和白白的米饭,还有一杯湖水泡的雨前新茶。
(九)
朋友海金说,藏云溪在蛇蛋岙,不在黄泥岙。他是宓家埭人,他说的应该是对的。那么蛇蛋岙应在黄泥岙的附近,南边,同在里湖的东岸。那里有很多圆圆的巨石,远看酷似蛇蛋,故而名为蛇蛋岙。岙里有青蓬蓬樹木,岙里有潺潺溪水,巨石下边有黝黑的水潭,溪边的石蛋路一档档地铺向山上,直通五磊古寺。据说,三国时孙权的母亲,到五磊寺烧香拜佛,是从这里上山的。这么多年前的事,不知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太久远的事,探究太多,实在也无多大意义了。还是记叙近代、当代和即将老去的这代人所经历的改天换地的事吧。建杜湖水库这么大工程就是最应记叙的。
朋友,你到过杜湖吗?你见过雄伟的水库大坝吗?你知道大坝里面是什么吗?你以为是钢筋水泥吗?建造水库大坝用的是大量的黄泥,都是从附近的山里挖的,然后用肩挑,用手拉车装,运到工地上,再用人力,一点一点,一层一层,一米一米地堆起来的。你相信吗?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把周边山都挖去厚厚一层皮,就连巨石缝间的黄泥也挖来了。山里的黄泥,压实后是很牢固的,叫三合土,坚如水泥。山脚的黄泥最多,山顶上就没有黄泥,黄泥是哪里来的?科普一下,是经日晒雨淋,岩石风化变成砂粒,砂粒风化再变成泥土,这是岩石在雨水日光和漫长时间的作用下形成的。
海金给我说,有一年,十七岁的他,在蛇蛋岙砍了一担柴,重一百八十斤,挑回家。当时柴担又重,肚皮又饿,一路靠喝溪坑水坚持把柴挑到家,此情此景永不会忘。人说,当一个人饿了,喝饱了水,只能走三里路,后再喝水,只能走二里了,再喝水,就没用了,人会晕到,昏过去,进入饿乡。记得清代有人写过一篇《饿乡记》的文章,讲人在饿昏之后的情景,讲到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在饿乡为主人。今又找到此文,把头里一段记下:“醉乡,睡乡之境稍进焉,则有饿乡,王,苏二子之所未曾游也。其土其俗其人,与二乡大同而小异。但其节尚介,行尚高,气尚清,磨励圣贤,排斥庸俗,则又醉乡,睡乡之所未能逮也。”《饿乡记》作者是清雍正年间福建人,蓝鼎元,王绩写有《醉乡记》,苏轼写有《睡乡记》;王苏二子就是指这俩人。刘伶写有《酒德颂》。古人真有意思,什么题材拿来都可作文。
有人说,成年人写的文章,都应该有思想,其实,并不其然,有些文章就是给人取乐解闷消遣的。况且,文章有无思想,不在于作者,而在读者,他能否读到,能读到多少。
(十)
从千年古镇鸣鹤场的西溪闸,到石湫头,这条湖塘从西向东蜿蜒十数里。百年前,乡贤吴作镆建水闸修湖塘,一定花了他不少的银子,这么多的石料不知哪里买来的,大概是山南的大隐,这些材料就要不少钱了。大隐产石料,当年应属慈溪;以前河姆渡、二六市、三七市都属慈溪管辖。
十里长堤,是十里湖塘,开始是砂石路,现今是柏油路,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湖边已种上了垂柳和桃花,还装上了石柱和带铁链的栏杆,有点杭州西湖的味道。我想,如果把公路改道,湖塘改为湖畔公园,湖里种些荷花,再弄几条游船,供人们休闲、游玩,欣赏杜湖的湖光山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现今的杜湖,也是一游山玩水、欣赏浙东温山柔水的好去处。当你从古镇里出来,到陡塘桥,向南是西溪闸、五步岭、古村瓦窑头,这里也是风光无限的地方。向东是半湖塘、洪凉亭、石湫头、水库大坝。水库大坝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景点,不只是山水风光的优美,雄伟大坝的壮美,还因为有太多的文化积淀,有太多的人文故事。
你若站在半湖塘凉亭,或洪凉亭处,或此段的任一处,隔着湖面,极目南望,东西两座对峙的山峰间,一条高耸的大坝挡住了你的视线。里湖,杜岙,还有杜岙里的几个小山村,你一点也看不见的。但大坝的雄姿足以让你震撼,包括大坝朝北面硕大的“杜湖水库”四个大字。大坝的东端亭子,是作为减水坝和放水闸的;西端,还有发电站的厂房,大坝底部的一片水杉林。
你若到任一处山顶,站在山头俯瞰,大坝似两边青山伸出的臂膀,形成一个怀抱,把五磊山、栲栳山、大霖山的所有北向的溪流揽入怀中。大坝南的里湖,像一块翡翠,镶嵌在青山之中。大坝北的外湖,是一块湖蓝色的绿松石。
用文字来表述,总是蹩脚的,总不能尽意,尽管写散文可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手段,可用多种修辞手法。况且欣赏美是一种感性的心理活动,都得凭你的直觉,无论是欣赏自然美,还是艺术美,有时像佛,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
朋友,有闲,还是亲临其境,来看看这湖水,看看这群山,看看这水库,更要登上水库大坝。这里有自然的美,有艺术的美,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