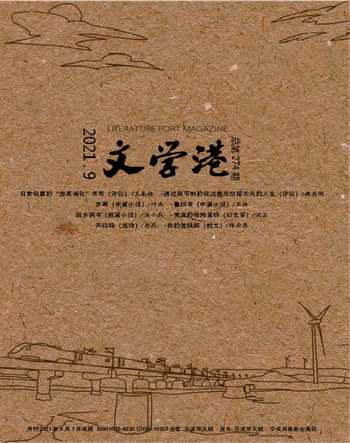红色之旅
在四明山论幸福观(外一首)
胡 弦
不要让溪涧太深,
不要让竹根太深,
黑暗中的,要让它们能听见我们说话,
听见我们的脚步声。
哪有什么天花乱坠,
只是这山里春酣。
世间事浅浅的,因风而起。
一个早晨,外在于你思考的深刻性。
刚才群峰如黛,现在,
却起了大雾。
雾中,破译过的秘密仍是秘密。
树头,桐子花像雪,
树下,石头却没什么变化,
像稳定的观众,
在一堆绚烂旧闻中。
在河姆渡遗址
我们日日进食的新米,
其实是种古老的纪念品。
稻壳、木屑、陶片,都是纪念品。
木桩穿过泥层,又悬浮在
黑暗深处,拒绝成为纪念品。
有人磨制出石斧,
后来,又烧出了黑陶。
但那个手拿骨针的人,
并没有把时间缝合在一起。
残月,带着有点褪色的象牙白,
像一件饰品被遗忘在天顶。
在河姆渡口
龚学敏
稻谷还在,用来成熟稻谷的时间
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
风一样的我,空虚,徒有姓名的壳
解说员一说,便碎了
渡口渡来渡去
过往最多的还是河水自己,我只是一个
斑鸠身边的配角
炭化在考古的镊子上
风来长一年
雨去消一岁,直到头发苍白
那人手中的稻谷,还在对岸
我只是一棵把很远的水路站直的秧子
每天都是渡口新的封面
对岸即封底
书中所有的字,稻米一样真实的字
从来,不敢成熟
每一粒谷壳里都是一个盛满白色的
夜晚。风一直刮着
稻米是我们从未离开过的
摆渡人
河姆渡博物馆
刘向东
光荣属于你,长江
口岸,神土,福地
沉埋于泥里一丈二的稻谷
离地悬空三尺以上的目光
陶器,木器,骨器
大器不竭的渴望
插进七千年深处的船桨
听鸟儿叫遍
周围的山冈
耕读与知行因为有你
超出汉诗最大的想象
比神农更早的神农
谷粒上史诗的断章
太阳两旁相守的鸟儿
是不是凤凰
我赶到的时候
孩子摘食杨梅去了
老人在阴凉里打磨石斧
鱼钩和鱼叉
树枝上还挂着湿漉漉的网
瓷片也蘸水相互打磨
借助风儿打水漂儿
力求在今晚成为星光
河水依然让预言流淌
听鸟儿叫遍
周围的山冈
至于陶釜所呈现的人吃人
的证据,不看也罢
看猪,看狗,着牛马羊
看它们与如今有什么差异
看守仁之花,此花
与汝同归于寂
或颜色一时明白明亮
太阳两旁相守的鸟儿
是不是凤凰
回首,再看,老宅基上
房架子依然是人字结构
立柱如脊骨立地顶天
椽子是肋骨分享阴阳
听鸟儿叫遍
周围的山冈
让我深为可惜,可叹
作为回到过去的过去
作为面向未来的未来
馆舍太小了,本该大的啊
大到上林湖四周的风中,以及
所有江南沃土,故园
家园,温暖之乡
与梦乡之中
骨耜(外一首)
李 云
呦呦、哞哞之声
从这宽厚的骨缝里汨汩渗出
木柄上先人汗渍的咸
沿木纹的弯曲路经飘荡而至
一場场农事:拓士、整墒
浚水、扬场
禾苗茁壮
谷子金黄
面对这朴素的骨制工具
我暗谢捐骨与人的动物们
也暗谢最先以骨制器的先人
一个向死而生
一个智慧聪灵
黑陶
我看见了先人的指纹
在稻穗花纹下面
在陶璧之上和底足之下
我感受到先人的体温
在陶的腹部和沿口
在我目光里暖着
盛过水和酸枣、橡子、薏米仁
盛过五谷和酒
更盛下幸福的阳光和爱情
此时它空空如野
空谷一样空着
侧耳过去
聆听一首谁在吟唱远古的山歌
临空蹈步由远而近
黑陶如铁
铁的黑在黑陶的骨头上开着黑夜的黑色花朵
那不是铁锈
黑陶哪怕碎了,也不会生锈
鹿 亭
孙 思
四月的风,似一位故人
对着我徐徐吹
那个身着长衫的孔祐,还坐在
他当年坐过的地方,恬淡的样子
似乎从来没有改变
那只受伤的鹿,正躺在他的脚前
微闭着眼,在它的一生中
有一次这样的相遇
它不知道,是谁给了恩赐
后来,鹿亭来过很多人
很多人来过,又走了
他们中一定有人
也想遇到一只受伤的鹿
让自己成为,另一个孔祐
这骨哨之音依旧在深情倒叙
安海茵
有金灿灿的稻谷层层叠炭
昭示时光之手在果腹前的喑哑
有鲨鱼的骨头仿若天空之翅
在昔日的沙滩蔚蓝上燃烧
又在橱窗之中埋下雨滴
橡子,菱角,粉红色的果实
河姆渡人的黑陶是荒野赋予的象形
我的时钟永远都追不上——
他吹散白雾的骨哨
羽毛状修饰着女子的耳垂
鱼藻纹遂以敛眉祈望和顺
葫芦和酒在干阑式
寂寥的墙壁上互为伙伴
将思辨色彩的星空逐一唤醒
总有人以薏米粥复制那时的光景
有人还是愿意在
车轮的咆哮中反复烤火
我其实并未觉察冷意
相信你也以杯盏一并 遥遥祝我
谁都不会长久地关闭自己
新石器的砍斫密如年轮 永无休止
你听这骨哨之音依旧在深情倒叙
那未可知的晨曦仍在河流之上铺陈
春雨霹雳 大地桃花
河姆渡:双鸟朝阳徽纹
江 离
他们追随日出的第一缕金线
直到东海之滨——
这最靠近神祇的地方
繁星灿烂,时时喻示
海浪不息的节奏,枕在耳畔
河姆渡,把双鸟朝阳刻入木牌
把野猪烧制在陶罐上时
也拥有了神力
护佑着逐渐可靠的生存
他们打磨石器,收获黍稷,渔猎煮食
他们佩戴玉饰,让美的光泽
开始流动
在我们仍然神秘的开端
它是在怎样的序列中?
当它幸运地保存下来,让我们体察
自身的历史,犹如今天高速公路上的
路灯,无限的绵延
告诉我们,已经走得多远
当飞机升空,穿过云层,它正来
那种恒久的渴望——鸟即摆脱重力后的飞翔
余姚四明山
麦 豆
时隔多日
四明山下的流水声
仍然响在耳畔
那里,太安静了
石头和树的数量
远超到访的人类
想起一个人,指着树上的石斛
说,石斛
可我什么也看不见
一种草,尚待命名
想起晚饭后
沿着山路
独自往山顶又走了一会
因鬼怪出没
而中途折返
四明山,至今仍是一个谜
陶 器
陈巨飞
如何在陶器里找到火?如同
在姚江的横截面,
找到向下的渡口——
夜间,四明山飞出两只凤凰。
它们在烈焰中,
完成对传说的烧制。
在河姆渡遗址,现实的榫头
对应历史的卯口。
时间是最纯净的胎泥,
捕捉了黑色的灵感。
流星,从人字坡屋顶滚落。
它将在黑陶中孕育成珍珠。
瓦缶盛着稻米,星空下,
井口发出微光。
这个景象,喂养了我们几千年。
作为吃饭长大的人,我继承了
祖先们的饥饿感。
但星空的教育,我只领悟一半。
弹 壳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
许天伦
我在注视着一枚弹壳
一枚被纷飞战火洗礼过的
子弹壳
弹壳,曾将无情的弹头射向敌人
当子弹在敌人胸膛炸開的瞬息
一种诤诤的永恒
嵌入了天空
在这陈列柜里
金属质地的弹壳爬满锈蚀
却亦如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
就算满身伤疤累累
已失去了
那震慑天地的怒吼
可战场上最后一刻的淬火
没有让它化成灰烬
如今,弹壳依旧屹立不倒
而成一座丰碑
河姆渡博物馆离赠
北 鱼
所有陶器都在假寐,稻谷的
呼吸穿透七千年土层。身为游客
我唯有从考古笔记的裂缝中
窥见河姆渡人种地、生火、喂养子嗣
这已经足够,我得知了
祖先应该完成的全部事情。在后面的旅程
我忽然醒来。这是适合浇水的午后,不算太迟
在河姆渡遗址
双 木
沿着陶器、稻谷、石斧、动物头骨
指向的脉络,向前是七千年的星辰
往后,古渡口的人潮和姚江的波涛,
永不停歇。
勤劳的祖先,更近似一场梦境
挖井、生火,甚至打猎和迁徙
正在发生,又在顷刻破灭。
在河姆渡,一切都是活的
历史从未真的消失。
一种隐秘的勾联
成为我们之间的图腾。
织 衣
——河姆渡遗址剪影
陶 火
这就是房子、裁衣刀,和其他相似的命运
一个女子。博物馆一角的织布机
昨晚外婆来电,问我的毛衣织什么样式
我想起那些幼小的夜晚,幼小住在我的发梢上
外婆点燃线头:
“闻一闻,什么味道?”
火光里黑烟伸展四肢,秘密地膨胀
那些日子,金属毛衣针的撞击声拍打被褥
仿佛一只干燥的大手。拍了许久
阳光好的下午,女子捏起稻壳在指尖细捻
男人们用石块的抽象打猎、耕地
模仿凶器,事物就会变得危险
衣角猎猎作响。捧出羞怯和情愫的娇红
一处磨损是一则故事
她编织着,仿佛每一个过路人的母亲
痛苦和洞穴是否同样古老?
我叩响的断层残留着走姿,
连带坐卧和一次递送。
展厅的布料未定型,她在编织哪里的纤维?
不远处,一个古铜色孩子静静辨别
游人的轨迹是另一种编织,
打捞更迭和移换。
一定有人读出谜语:
经纬里的张弛。如果母亲要说一句话
你一定早已把它摩擦得发热
祖先序曲
陈起起
1.
一切开始于一个灵光乍现的虚构
故事,挣脱蛛网,张开新鲜的双翼
飞行在,每一个未被命名的黑夜里
人们点燃篝火,在干栏里沉思
所有刚萌芽的概念在体内游走
“需要有一双手,巨大的手。”
于是,空中展现神的奇迹,故事的
发明者垂钓信仰,在一种宏大的
想象中安睡:明天,依旧是与野狼
讨论生命交换的一天,如何用长矛
多换得一些猎物,这些不必着急,
他们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故事,关于
如何将野狼改名为家犬。这个故事
强壮有力,教他们握住野狼的手
说,“坐下,小黑。”
2.
在篝火和干栏之间,他们沉醉地
描摹海洋的遐想。也许下一次
他们就能去南边更南,较量
双门齿兽和地懒。亦或者去
阿拉斯加,穿越比雪更厚的雪
把象牙珠子挂在手上,摇晃着
一个比夜晚更深的黑影。他们
起舞,火焰为他们烘干泪珠
水稻在脚下吱吱叫,如一条条
弯曲的缰绳勒紧土地粗糙的
手掌,每一个屏息挺立的陶罐
都有一肚子关于四季的低语
3.
在无人苏醒的夜里,野狼也有
它的幽默和深情。飞起来或者
不,那些善于拣择的鸟类,啄
醒了一个春天的寂静。睡梦中
他们被召回,绢云母质的黏土
渗入植物的茎叶、谷壳,熔成
一个内部中空的谜,谜底在溪水
与耳朵的相互厮磨中,孵化了
一尾无鳞的鱼,它循着河流
游至我的掌心。我听到陶胎质软
胎厚量轻,听到釜、罐、盆、钵
挺立着。远处,一匹羊嚼着五月
河姆渡博物馆
赵 俊
真实的历史就是那变形的床,
场景简单的复原就是全部。
时间的真相:不断的核衰变,
历史糖分的代谢再缓慢,
仍无法阻止虚空的到访。
博物馆是一个被豁免的人,
可以借助通史还原场景。
有时它甚至站立在原址之上,
任凭你脚尖的力在无限践踏,
它仍要卖力讲述事件的每一帧。
哪怕有人在它的阴阳脸上涂抹浓妆,
它的唾沫仍飞溅在你的眼窝。
当追光灯的尾翼在渐变中折翅,
繁华的洒落,在每一个人脸上逗留,
这次坠机又是一场必要的偶然。
你又回到未被修补的故居,
在名人的素描中剥开油画的釉面。
瘫坐着你被主义和定论戕害的观感,
在无数经验和现实构成的夹角中,
永恒不变的,是悲悯加持的、默诵的番号。
仍有火焰的声音
颜九念
烧掉泥土的坚固,
它会变成另一种坚固。
这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陶器,
黑暗中发光的摇篮,
在更深处,在更深的细流之上,
那只鸟站在时间里——
一团炽烈的焰火,
一束耀眼的荣光,
时光扇动起她的羽翼。
我拿起放大镜,
追随她线条的流速,
只为抓住萬物言说的深意。
但停留在此空间的,仅仅是我。
每次篝火结束,那只鸟依旧,
婉转,翩翻,朝向金色的渴望。
干栏式木屋
远 心
在这里,余姚县上姚江畔
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遗址,6000年前
我们就是母女,凌空的干栏高出地面两三米
带榫卯的木构件:
柱头柱脚榫、梁头榫、带销钉孔的榫、燕尾榫
平身柱卯眼、转角柱卯眼、直棂栏杆卯眼
连接木屋。尖顶上铺满稻草
像少女的长发纷纷披下
阳光洒在木屋前的黄土上
你是妈妈,我是女儿
我坐在木栏边,双腿荡在空中
你在部落场院上织竹席
对面上姚江,水流渊深
6000年后的春日,我又回到这里
这一世:我是妈妈,你是女儿
遇见一座河姆渡干栏式建筑
你坐在木廊上,荡着双腿,看我
我放下手中的竹席转身,看你
稻草如长发披上木屋
对面,上姚江水滔滔而过
那些榫和卯把我们连在一起
鹿亭时光记
雷元胜
在中村喝茶
我们邀请白云桥一起
喝一杯叫做中年的茶
有三人在玩纸牌
另外一桌人一边闲聊
一边嗑瓜子
大多时候,我在思考
该用什么样的手法揉搓生活
才能挤出一点时间的甜?
学晓鹿大溪里那几只麻鸭吧
把余生的光阴做一下甄别
差的、好的,不好不差的
呱——呱——呱——
东岗山的杜鹃花开啦
这些被孤独打败的杜鹃花啊
还有几分野心
立夏将至,我愿意与杜鹃花交换一下身份
夕阳像遥控的无人机准点降落
无数条金光大道在水里竖起来
照在我眼睛上
也照在望柱的狮子眼睛上
夜卧鹿亭
黑 多
夜卧山中,我枕着雨声
或松竹,或青冈或麻栎
协奏非凡的复调,草木
早低过我的意念,它们的
呼吸与交谈,时有时无
如同被虚构
我羞愧,说出这些秘密
关于山中的一切,我或许
知道一些,又或许什么
也不知,我所见皆是虚妄
一个藏身山中的人
正蓄养起慈悲,识无相之相
等待清晨叮当鸟的鸣叫
破窗而入的第一声
第二声、第三声……
太阳的光芒,串起晶莹的
雨珠,谷底的雾岚
接引亘古的长空
去鹿亭镇
郑 委
听说要去鹿亭
鹿亭在哪里,有什么,漂亮吗
我一概不清楚
很快又迷迷糊糊睡去
昨夜的醉,我并未完全醒来
车过了一个又一个山弯
鹿亭还是没有到
朋友说,鹿亭可能是个亭
也许很早以前
有人在那里看到一只鹿
后来便在那里
搭了一个亭子,让鹿避雨,让鹿
躲大雪
那只鹿有樹枝一样的角
有梅花一样的蹄印……
他们还在讲述
我睡了醒,醒了又睡。梦里,我去了
一趟又一趟鹿亭
鹿 亭
宗 昊
对白云幻想,隐约看到鸟的双翼
白云搭建的桥,已进入隐喻中
藏匿于深山老林,竹林环绕
“鼋鼍”栖居于此,露出了水面
看向天空,阳光饱满,滋养着万物
风轻轻吹,露出古老的面目
鹿亭,这是中国的两个汉字,也是一个村
进入历代诗人的词语中,进入了教科书中
我常常喜欢在水边坐着,这些水
越来越让我着迷,让我思考乡村
乡村这个词,乍一看就已有古老的迹象
逗留半日,恍若看了一部文明史
谭启龙
方其军
四明山的风,与井冈山的风
都是被草木滤净的
深呼吸一口,再深呼吸一口
整理书刊、文墨
码齐一句句惜别的乡情
把四年的枪声打包
捆绑的绳子一勒
一颗心,直喊疼
这里有一道数学题:
从几百人到一万五千余人
花名册像一片薄田变得肥沃
这里留有一道哲学题: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几多热血男儿青山埋忠骨
只解了一半的题,留待回来再解
“我们一定回来。”
夜色里,风将山林染得斑斓
野果子缀满枝头,汁液暴涨
夜色里,响起婴儿饿醒的啼哭
井
筮 维
一场雨后
有巢氏抬头
琢磨起储云的法子
人可否
把水稻种在云上
风吹过骨头
就有神替人间插秧
人可否
把一汪隔宿的水搭出井字
二十四根木榫头
明月是卯眼
有巢氏在云上挖了一个孔
从此天开了口
他不知道七千年后
神的咳嗽会落到地上
一场雨后
稻粒纷纷而下
我们低着头
面朝云的窟窿认祖归宗
时间的窗口
方启华
时间也有恍惚的一面吗?
河姆渡似另一个世界的出入口
确信会有人和我一样短暂迷失过
我们坐着虚无的铁船,穿越7000年的光阴
元宝山上,布谷鸟叫出了胎动的频率
余姚江畔,鱼尾轻轻挑逗玩水的猪崽
你想要在干栏中栽花
骨耜凿出花园
你想跳一支自创的舞蹈
我来做陶埙和骨哨
我用榫卯为你建造一座阁楼
你用石器在陶碗画上麦穗
你还用针织给我做了一顶王冠
然后我问神仙住在天空的第几层?
在河姆渡,时间可以被无限缩小
世界也许只有一个部落那么大
星空洒下智慧的种子
四层土壤孕育出文明的花火
遥想某个春日
——致敬会画鸟和太阳的先人
柳 柳
厚重冰冷的雪一层层消散了,草屋轻盈起来
15岁的先人一身肌肉,两眼放光
他蹦蹦跳跳地离开草
把所剩不多的稻米拿出去晒
分量不能比邻居家多
四月的阳光在鼓励他,沿着湖泊跑得再远一点
与水鹿再比一比奔跑的速度
大喊一声,高大的树木纷纷冒出绿叶
他又感觉自己能活一万年
谁也不能否认
7000年前的春天比现在还要神秘
没必要发明文字去记录过去的事
洪水还没有泛滥,他的心中也没有菩萨
劳动从来不苦,集体的意志和大笑诞生于此
临水而居,打下一根根木桩
草屋离地一米,院落里养起犬猪
炼泥制陶,在陶器上画上
植物安静的纹路,长嘴的猪
水稻在抽穗中释放着克服自然的伟力
只是,忽然想起去年和他一起追野猪的妹妹
他越跑越慢,春天一点点亮起来,妹妹暗下去
一样的是闪烁在高处的飞鸟,更高处的太阳
和上一个春天一样温暖着他
妹妹再也吃不上今年的新稻了
其实他比水稻还要渺小吧
谈不上哀愁的迷惘困住了豪迈的他
人类的文明似乎往前挪了一小步
他想去追寻更长久的事物了
坐到树下,集中身体里的洪荒之力
汇聚成一双巧手,刻下太阳和飞鸟
它们会比他存在更久吧
在四明山下
邹胜念
第一次碰触这里的土壤
我极度想踏平春意
把那些盎然青色,碾碎
揉进裙子每条褶皱
带回。
我早知道
某些空间里的木地板,对步伐失去渴望
终日吸收消毒水,维持光亮平滑
代表有活人的自律与清爽
但我此番要带回的
是它们一生无法谋面的闲逸
远处,大樟树梢漏下的薄薄金光
袒护了没有戴帽子的人
我們极速奔跑,模仿闪电和雷鸣
赐予竹林一阵风
山顶的事无从知晓
清泉挂在岩石,浸润苔藓
野猪背着灌木林里最隐秘的过往
奔至山脚的一块菜园地
在四明山下,一个人,来回走
恍然是一群人在走
头顶二三,心中藏二三
深爱的,远去的,等我的
人影,如惊醒的凌晨与失眠的夜
互相交织,并在一捧清泉里
清晰地沉浮。我要走了,四明山。
领着叠嶂的人影走了。再会。
聆 听
毛小景
水井架在第二层,井水
无边
一千年向西,一千年向东
井水流淌在村庄和田野
向上逆流,再向上
井水静静流淌在
河姆渡的一边
我们来了,我们经过
我们静静聆听
井水清洗这四万平方的先民
遗 址
马修诚
深坑——在睡眠中——缺席
而苏醒
来源于——一只面包虫的死去
丛林,永远——移送一块
透明的铁锹
而风暴的闪电——在墓穴中
到达——秧苗的尸骨
自言自语,总是
被文明之胴体——包裹的昨日
播种
遗址——被藏埋自身的事件
挖出自己
如流苏式的悲哀
携来机械眸色的一丝绿光
(流血的人,站在草木门口
山野和麦田——分泌,一次次
那不被理解的,时代的胰岛素)
安置死亡的——山雀之眼
该如何
目送被握紧的枝桠
撑起——众多
迟来的——脸的博物馆
同谋者,芦苇之上
比铁石器——更快抵达
白色制服融汇的——摇篮的深渊中
语言开始龟裂出的一瞥
通过
如此多——简单的祭品
作为:在场的救世主
于所在之地——停顿,是史页真实的燃烧
如我们存在并永远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