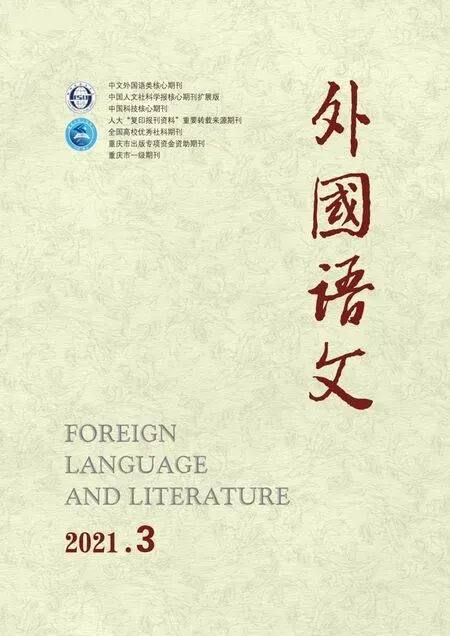想象与抵牾:生态视角中的文学荒野及现代启示
纪秀明
(大连外国语大学 科研处,辽宁 大连 116044)
0 引言
“荒野”(wilderness)指原生自然和原野,“是人类尚未涉足的原始大自然,人工的痕迹几乎不明显,而只显现出自然力量的影响”(Allin,1982)。基于古希腊哲学的“被独立”与“二元化”思维,荒野被注定了其在漫长思想史里的与人类主体的“隔离性质”。尽管我们认为荒野常以隐喻的方式植根于科学和文学的想象,但是这种隐喻与想象依然还是主体想象的附庸,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以他物之名名此物”(Garrard ,2004)。作为生态批评的重要渊源,浪漫主义经常赋予荒野以隐喻功能与意义,传达哲学与文化反思,或以隐喻的方式进入政治与民族国家构建的想象。但是,就本体意义而言,荒野承载了个体与自然、社会及宇宙怎样丰富的隐喻关联?现代化进程中荒野自然的意义与功能发生怎样的微妙转换?文学与批评中的荒野如何跨越隐喻诸种,实现从荒野美学到实践美学之转型?
1 另一种隐喻?通识的工业、异化与自然应许之地
浪漫主义对荒野极度推崇。在某种意义上,荒野是人心灵与自我实现的家园隐喻。蓝仁哲(2003:5)指出,“在库柏看来,荒野保持了原始的幽美,……这种自然与文明间的冲突和渴望回归自然的迫切性在福克纳的小说《熊》中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对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来说,荒野的边疆充满希望,它是承诺自由的福地。”不少作家把荒野理想化,将其描写成摆脱社会限制、享受充分自由的最好去处。库柏《拓荒》中的猎手班波沉醉于淳朴的自然之美,森林就是艺术走廊和圣洁的教堂,雷蒙德湖是他的第二天堂,是“令人欢欣鼓舞之地”,是“天马行空的逐猎之地”。在福克纳的《熊》中,万事万物急不可待回归荒野,遵循生命与自然的规律。荒野是生物回到平等对峙的场域,而万物之灵的人只有脱开现代物象的束缚,才能把自己融入荒野。事实上,恰恰是自然以及自然里的一切生物,成就了人的生存与内心的平衡,完成了猎人的自我实现。马克·吐温也借荒原实现哈克贝利·芬的自我成熟与完善。诗人笔下的自然是心灵回归的殿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写道:“听凭大自然的引导:与其说像一个在追求着所爱,倒莫如说正是在躲避着所惧。因为那时的自然(如今,童年时代粗鄙的乐趣,和动物般的嬉戏已经消逝)在我是一切的一切。”(卞之琳,1983:67)正如缪尔所说的“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爱默生也再三申说“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和信仰”,在自然界永恒的宁静中人,又发现了自我。
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文本已然将荒野与自然的复兴作为主体对抗异化的方式与手段。随着现代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整个社会对自然资源进行无以复加的掠夺,人们逐渐远离了往日纯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以自然为精神自由的幻梦逐渐被破坏,“自然界永恒的宁静”越来越难奢求,上帝的荒野纯粹性越来越被质疑。荒野从精神自在的想象,沦为主体不得不的抵抗。库柏《拓荒》的猎人坚决拒绝,并抵制与其他拓荒者合作开垦自然资源。在他看来,不断扩大的聚居地和西部荒野开发都会加剧践踏环境。他控诉同伴们不择手段地推进西部开发。认为他们已经剥夺了上帝所造万物的生之愉悦,在制造麻烦并最终铸成罪恶。然而西部移民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纳蒂对移民进程的阻挠必然式微。绝望落寞的猎人最终决定逃离斧头砍伐声、树木折腰声,走入荒野深处去寻求自然的真善美,找寻心灵的宁静。猎人独自走向落日余晖,表明了他对自然的刻意回归和对西进移民的抗拒。
马尔库塞关于技术合理性与统治逻辑的辩证性乃至悖论性的论述,对理解浪漫主义自然对抗工业理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他肯定了工业逻辑与社会科学秩序的合理性:“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并基于相同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式,它甚至为该事业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与开拓。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道,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马尔库塞,2016:125)同时,马尔库塞还强调:“我们还懂得,生意必须做下去,替代性选择是乌托邦。这种意识形态属于既定的社会结构,它是该机构继续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其合理性的组成部分。”(马尔库塞,2016:125)
马尔库塞还批判了机构对“人化自然”目的的破坏,“然而该机构击败了它自己的目的,如果它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以人化的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话”(马尔库塞,2016:125)。他既看到了肯定与否定的复杂性,又指出了价值判断的难度。这种状态不是心灵的状态,“从一开始,否定性就寓于肯定性之中,野蛮寓于人性之中,奴役寓于自由之中,而是现实的状态,在这种现实中,科学头脑对于联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起决定性作用”(马尔库塞,2016:125)。马尔库塞对工业文明和科技理性提出了批判,也对工业技术中的道德与正义功能由谁监督的问题提出质疑,但难免陷入正反思辨的悖论。“如果善和美、和平和正义既不能从本体论的条件中推导出来,又不能够从具有科学理性的条件中推导出来,那么它们在逻辑上,就无权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普遍的实现” (马尔库塞,2016:125)。也就是说,观念受科学理性的排斥,它们变成了单纯的理想,而它们具体的、批判的内容则消散到特定的伦理和形而上学氛围里。
也许,对单向度的批判,恰恰说出了答案的多维性与制约性以及形而上学无限递进性。尽管我们一直以笛卡尔的二维思维看待科学性与理性的决然与独立,甚至过度“概念化”,或者违反逻辑地攻讦,或以政治、道德、历史取代科学,但是其科学价值与功能实践本身亦受制于价值体系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看浪漫主义乃至之后所有文学现象里的对荒野与自然的遁世处理,更能看出其脱离实践的空想性与唯心性。
2 超验与神性
晚近生态批评的崛起,提醒我们再次回到理论原点。我们有必要对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重新进行探讨。柏拉图认为,人的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有天壤之别。知识和真理属于先验的秩序,属于纯粹永恒的理念国度。笛卡尔的二元论发展了柏拉图的观念,奠定了现代理性与哲学的基调,也促成了现代逻辑里的自然与人、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等的对峙。这是一种对中世纪神学的釜底抽薪的决裂。也促成了现代逻辑对工业文明等问题的单向度思考,甚至是文学思维的制约,比如系列荒原与城市对峙的意象与原型,比如逃离与回归主题。
受基督教教义与科学理性二元观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自然放在人类的对立面做理性客观的分析和推理。然而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笛卡尔的二元论是靠不住的。其思维着的自我实体将类似于广延实体,并预言出现一种能够定量观察和测量的科学主体。笛卡尔的二元论已经暗含着它的否定。它将打通而不是阻挡建立单向度科学领域的道路。在这个领域中,自然客观上是关于心灵的,也是关于主体的。”(马尔库塞,2016 :132)由此,我们更便于理解为什么爱默生所引领的超验主义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解放运动,被后世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同样,撇开纯粹到令人质疑的二元论对峙,现代自然观因神性反思而富有弹性,欧金尼奥·加林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中诗化描述“在现实的陈旧观念逐渐消失的基础上,萌发出‘人文学科’和‘新的科学’艺术家们发现了神话的古老使命,恢复了它的含义,同时成熟的意识把‘神的’形象置于美丽的幻想中,把它们处于天空辽阔的空间里,并使向人发出的歌声充满着寂静宇宙,这样人就不再害怕”(欧金尼奥·加林,2016:89)。浪漫主义自然观脱离了对二元论的信赖,或者更为准确地说,以自己的情绪与感性,参与对自然经验世界的崭新体验。
“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一种与世界的全新关系呢?我们的诗歌和哲学为什么总是遵循传统,却没有洞察力呢?”(爱默生,2010:1)爱默生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反思是自发自觉的。“在树林里,我们回归理智和信仰”,“他在天空和树林永恒的宁静里,重新找回了自我”(爱默生,2010:4,8)。他突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峙的边界,思考人与自然的主客融合,歌颂荒野与生命的力量,歌颂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如果说,加林强调与憧憬的依然是人的先导,强调“恢复”“使”“置于”“把”,爱默生则以神性和上帝为先导。人、荒野和上帝精神具有内在关联性。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指出: “自然只是智慧的影子或模仿物,是灵魂中次要的东西。自然只是一个无形的实在。”“每个自然物,如果观察得当,都展示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爱默生,2010:18 )爱默生认为,上帝是万能的,是理性与道德的精神集合体,主宰着世间万物,人要信仰上帝。他将超验看作为人向上帝不断靠近、回归以及重拾神性的进化过程。爱默生将上帝与大自然相联系,自然是爱默生思想体系中作为本体的“超灵”与作为人理性能力“直觉”的中间环节。
在实现主客观、信仰与道德统一的方法上,自然的神秘性与神性已然成为至高标准与手法。倡导自然、人神统一,“超灵”与直觉的神秘主义恰恰富含对抗性与同一性。“(神秘主义)那种奇特的关于普遍对象的非实在性的感受,即与日常事务的联系的丧失;在这种丧失中,外部世界失去了其稳固性,而心灵则似乎在完全的孤寂中从自身深处产生了奇异幻象的疯狂舞动。这些幻象迄今是作为不受约束的真实而有生气的东西出现的。” (罗素,2017:18)这是神秘主义对抗性的一面:“怀疑普遍知识,并为接纳一种看似更高级的智慧的东西扫除障碍。”(罗素,2017:18)神秘主义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同一性。“它相信同一性,并拒绝承认任何地方的对立与分割。”万物统一,“宇宙是一个不可分的全体,而且似乎是其部分的东西,假如被看作实质性的及自存的,就只是一种幻觉”(罗素,2017:19);“神秘主义哲学相信洞见,而反对零散的分析的知识:它们相信一种智慧的、突然的、穿透性的及强制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一种完全依赖感官的科学对外部现象所做的缓慢而易错的研究形成了对照”(罗素,2017:20)。
更为重要的是,爱默生和浪漫主义诗人强调人、荒野和上帝三位一体的道德美学体系,这弥补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对神性与善的某种忽略。爱默生将美学问题与信仰问题结合,将美学复归于对宇宙本体的真与善的把握上。自然与荒原的道德指向是真善美。“大自然是一片贮存着形式的大海,这些形式极其近似,甚至是一致的。一片树叶、一束阳光、一幅风景、一片海洋,它们在人的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几乎是类似的。所有这些东西的共同之处——那种完满与和谐——就是美。” “宇宙的激流在我的身心间流淌;我成了上帝创造的微粒的一部分。……在树林里面,我们重新找到了理智与信仰,在那里,我会感到我的一生永远不会有任何遭遇——没有耻辱,没有灾难。”(爱默生,2015:21)华兹华斯《丁登寺》同样强调自然的神性力量,以及神性所指向的生命和谐之美:“我凭借它们还得到另一种能力,具有更崇高的形态,一种满足的惬意,这整个神秘的重负,那不可理解的世界令人厌倦的压力,顿然间减轻;一种恬静而幸福的心绪,听从着柔情引导我们前进。……和谐的力量,欣悦而深沉的力量,让我们的眼睛逐渐变得安宁,我们能够看清事物内在的生命。”(卞之琳,1983:67)
3 心灵实践与本体自然
就浪漫主义的一般内涵而言,梭罗没有逃离爱默生式的浪漫主义哲学思想:对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理性的反抗、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对个体与自然的照拂、以及对消逝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对自然回归的向往都在预设之内。但是梭罗之所以在生态批评史学上得到更多重读与价值重估,在于他对爱默生式“神秘超验”的凌逾。爱默生认为自然是精神的象征,自然被理解为中介与对象。梭罗早期的思想和创作如出一辙。比如他说:“我热爱野性,同样也热爱德行。”认为自己有“一种本能的对神秘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但也有另外一种对原始的野蛮生活的渴望。”“荒野是一个安置我们的最好环境”(梭罗,1997:198)。浪漫主义思潮本身就负荷对工业世界的精神与个人栖息的反思。因此,田野与荒原的书写,就有了遁世与逃离的自我解救意味。
心灵实践与“深林”试验,让梭罗越来越具有当代生态主义意蕴。他自己避世瓦尔登湖,栖息深林逃离现代生活,通过“回归荒野”更新自我。荒野是野性的贮存库,人可以享有物质社会绝对不能提供的独处和精神自由,从而找回自我,洞悉自然本真。“遁入某个荒野里。在那里,我能有更好的机会让生命发生作用”,梭罗认为自然是实实在在的本真存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这种自然本体伦理观使其成为生态主义的先驱,被誉为美国生态文学的源头和奠基人。
瓦尔登湖的旅居事实上是梭罗的实验,是为了验证自己对社会改革的一些想法。他曾说道:“我从自己的实验中了解到,如果一个人能自信地在他所梦想的方向上前进,争取去过他想象的生活,他就可以获得想不到的成功。他将把一些事抛在后面,超越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新的、普遍的,而且更自由的法规将在他周围和内心自行建立起来;或者旧的法律得到扩大,以更自由的意义做出对他有利的解释,他可以在生命的更高级的秩序中生活。(罗伯特·塞尔,1996:652)但是正如布伊尔所指出的,这种实验依然是乌托邦式的,因为“至于封闭的问题,当我们研究一个作家对‘自然写作应聚焦于一个远离社会的空间’这种假定抵制时,(就如同)瑞秋·卡逊的事业就是有力的证明,因为有这样的发现:地球上没有一个空间能够脱逃人为的毒害”(布伊尔,2010:47)。这也是浪漫主义被现实主义者们所诟病的原因,比如查尔斯·霍依德在《马拉德与新浪漫主义》中批判梭罗式“浪漫主义对客观现实的拒绝”,认为浪漫派实质上是逍遥派,不敢或不愿面对现实,仅仅局限于“心灵”的实践。
为什么浪漫主义自然观与荒野观成为我们迟迟无法转移的话题?因为当代英美生态批评经常将生态哲学的反思追溯到18至19世纪浪漫主义。这其中,可以看到其对后来生态批评滥觞的种种“前”迹象与隐脉。事实上,爱默生并没有给予自然主体认同,“自然总是呈现心灵的色彩”(爱默生,2010:5)“自然只是智慧的影子或模仿物,是灵魂中次要的东西。自然只是一个无形的实在”,“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精神存在的象征,每一个自然现象都对应一种思想状态”(爱默生,2010:13)。荒原与自然问题始终以神性与道德为形而上取向,并将最终的希望寄托于资本理性与自然理性的结合。梭罗承继爱默生的观点,又以荒野中的“心灵”实践形态,进行远离社会的乌托邦式实验。而约翰·缪尔的逃亡则更有书生理想主义的意气。1907—1913年的赫奇荒野大辩论(官方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和以缪尔为首的民间自然保护主义[Preservation]),终究以缪尔派的失败而告终。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现代科学已经从理性上使浪漫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的神圣信念与道德神庙构想成为不可能。“科学已证实大自然是破坏性的,极端凶恶残忍的。在他们眼里,人类是物质的人,处于监狱般的环境里,像是盲目的囚犯,没有意志也无选择。在这样的世界,浪漫主义者不过是稚气的空想家,他们的自然美景只是幻象,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纯粹是空话。”(周思钊,2020:81-88)
直到当代生态批评的崛起,利奥波德大地伦理观、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以及奈斯深层生态学的三维解读,让作为本体意识的自然再次跌跌撞撞闯入理论漩涡的中心地带,开始了一场正式规模的对自然重新审视的浪潮。很明显,此次对荒原野性的呼唤,既有基于浪漫主义同样的理论权宜,比如以荒原为手段的反现代性,一如以荒原为手段的反理性、反工业的路数。更有基于伦理与现实的、基于地方与全球的、世界自然与政治景观格局变动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崭新思考——谁为中心?如何组织与运行?实现怎样的栖息?因此,这一次的逃离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并非简单地回归,而是一种新意识的变革与升华。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界限打开,直接从伦理层面进行了共同体设想与论断。共同体就体现了“非鸟瞰”“非俯视”的整体性与平等性。自然作为中间位物,不再是上帝与人之中间,而是在其间,是天、人、荒野合一。自然亦非泛神性的,而是与伦理共建的,一方面以此去魅了神秘与唯心性,一方面,又以人伦与社会关系拓展了人、天、自然维度。这种观点不同于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观点。
同样,深层生态学家奈斯的观点也具有重要转折性意义。作为一种生态中心论的世界观,奈斯凸显了人的民主与自然的民主,他在“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大写”的自我实现原则。奈斯理论之所以有这么深的影响力,就是他兼顾了荒野大地与“人”关系的独立性。奈斯将自我的成熟理解为三个层次:“本我”“社会自我”及“形而上自我”。“‘形而上的自我’又可以称为‘生态自我’,它不仅包括我,一个个体的人,而且包括全人类,包括所有的动植物、甚至还包括热带雨林、山川、河流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它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雷毅,2001:24-56)同时,强调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感与实现过程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超越整个人类而达到一种包括非人类世界的整体认识的过程” (雷毅,2001:24-56)。可以说,对象范围与非人类世界促成了“生态自我”的成熟与完善。个体自我实现的水平越高,就需要越多的其他生命存在物达到自我实现,即‘共生’——‘自己活着,也让他人活着’”,“当人达到生态自我,就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也能在自我中看到所有存在物”(Naess,2005 :137)。这里吸取了存在主义的关于“本质”的定义方法,也与曾繁仁的“生生美学”对现象与存在的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大有“物我合一”的哲学思辨。
谈荒野的哲学思辨,不能不关注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与 《自然界的价值》。奈斯认可自然基于平等的整体内在价值“对我们而言,整个星球、生物圈、盖亚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其中的每个生命存在物都有平等的内在价值”(Naess,2005 : 18 ),而罗尔斯顿在强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强调荒野自然非工具主义的内在价值。“荒野首先是价值之源,其次才是资源”,“自然物身上存在着某些自在的价值”(罗尔斯顿,2000:131),这种价值主体性是客观的、至上的、绝对与此在的。自然与荒野因其母体的“创生性”而被霍尔斯顿推演出割裂历时的本体静态价值。这也是其理论后来被第二浪潮公平正义批评一直所诟病的。“荒野”作为本体,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想象与抵牾的逻辑矛盾:为了论证荒野的至上性与绝对性,环境伦理学极力张扬荒野的先在性、系统性与自组织性特征,其结果却反而说明了荒野的非自在性和非原始性。无视自然的实践中介性与社会中介性,导致“荒野自然观困境”。荒野自然观不过是“客观自然主义”自然观, “客观自然主义”是“毫无血肉精神的”,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上的虚无主义(孙道进,2006:15-18)。
认识到荒野回归实践、回归社会之必然,当下的西方生态学者对生态批评做了重大理论调整——自然观与环境公正、社会正义相结合。布伊尔(2010:14)指出:“文学研究的环境转向一直是更多地受问题而非范式驱动”。显然,由于问题导向,“那些实践中的所谓生态批评家们的‘生态’就更倾向于美学、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而不仅仅是环境自然与科学。这种倾向自运动的开端就存在,而且还不断发展”(布伊尔,2010:14)。“生态批评从自然环境发展到把城市环境、‘人为’与‘自然’维度相交织的所有地方以及全球化造成的各个本土的相互渗透都囊括在内。”(布伊尔,2010:14;2015)在现实与行动主义等理论的推动下,生态批评将进入美学、伦理学与社会政治学理论“回旋”,其从文学想象、经田野实践到社会实践已成必然。
4 结语
生态批评以开明、公正而可持续性视野对过往和当前世界提供了独特见解,将自然与人的问题放在一个更整体、更系统的语境下思考。利奥波德不局限于对“共同体伦理”的观念性想象,一再重申“实践、教育、公共策略”的协同意义;布伊尔对城市生态、地方性、濒危世界写作的思考不断深入;生态女性主义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化行动与介入等。生态批评时刻以理论内部不息的对撞与自新、自反,昭示着不可阻挡的日趋社会化与世俗化的荒野美学到实践美学之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