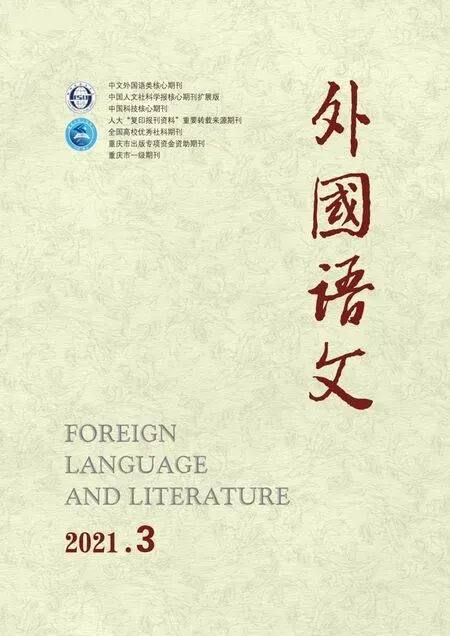莎士比亚《捕风捉影》中的饮食叙事
胡鹏
(四川外国语大学 莎士比亚研究所, 重庆 400031)
0 引言
在近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食物被研究者们视为身份与差异的符码,折射出性别、年龄、阶级和伦理等诸多社会学上的变化(Caplan, 1997:9)。而食品生产加工及消费的模式同样如此,阿兰·博德斯沃斯与特丽萨·凯尔就指出:“饮食行为是根植于作为整体的一系列生理的、精神的、生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交叉发展进程中的。”(Beardsworth et al., 2000:5-6)那么作为高度凝练生活的符码,文学无疑也涉及饮食行为。在乔戈波罗看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食物指涉不单定义了角色的身份,触及其年龄、性别、阶级、宗教、国族、文化背景等因素,更是涉及角色特殊的性格特点(Georgopoulou, 2017:67)。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中《捕风捉影》的导论中写道,某些食物的甜与美味是建立在苦的基础之上的,苦味自身是味道差、惹人厌的,而单独的甜腻味道也会让人厌烦。一切都依靠味道的编织调和,自然界如此,受过训练的厨师也是如此。《捕风捉影》首次出版于1600年,可能写于1598年,就是如此一道珍贵的食物。戏剧将两个故事串联起来:欢喜冤家贝特丽丝与班尼迪从争吵到爱慕以及克劳第误解其未婚妻喜萝不贞(Greenblatt, 2016:1395)。进一步说,正是食物与宴会在剧中穿插从而推动着整个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剧中一直持续不断的宴会模式:比如彼得罗请班尼迪到廖那托那儿走一趟,替他向廖那托致意,“对他说晚餐(supper)的时候我准到——他为了铺排酒席,当真很费了一番工夫呢”(27)。卜拉丘谈到廖那托的宴席:“那边正在大摆酒席呢(great supper),我才从那儿来。”(33)唐·约翰接话道:“咱们也到宴会上去吧。”(34)廖那托招呼彼得罗:“殿下,请移步吧;晚饭已经准备好啦(dinner is ready),”(67)贝特丽丝去请班尼迪:“真没法儿想,他们硬是要我来请你进去吃饭”(68)等等。本文以《捕风捉影》为例,从文本中的食物叙事出发,探讨不同的食物及饮食习惯乃至宴会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中的关键作用。
1 橘子的异国性与功效
我们可以发现剧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特别显眼的水果——橘子。莎士比亚在《捕风捉影》中两次提到橘子。第一次的情景是贝特丽丝说起害相思病的克劳第是“一位庄严的伯爵,庄严得像是一只橘子,并且脸上带着一点那种嫉妒的颜色(a civil count-civil as an orange)”(49)。此处的橘子是塞尔维亚橘子(Seville orange)的双关语,一种稍苦涩进口自西班牙用于制作柑橘酱的原材料,她嘲笑的基础是观众都知道以酸橙闻名的西班牙城市塞尔维亚。克劳第嫉妒而愤怒,就像塞尔维亚橘子一样,但同样可解释为像橘子般来自西班牙的人惹人不快。也可以阐释为贝特丽丝的评论是一种更加巧妙的批评,即“庄严的伯爵”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位“塞尔维亚”伯爵,英国的新盟友之一。
第二次提到橘子是克劳第错误地认为喜萝不忠贞从而进行公开指责的时候:
这里就是,廖那托,把她拿回去吧;可别把这个烂橘子塞给自己人!她只是给自己挂了个“贞洁”的幌子——瞧,她脸儿都红了,多像个闺女!啊,狡猾的“罪恶”,它真会把自己装扮得冠冕堂皇、一派正经!那两片羞答答的红晕不是正好给她的纯朴作证?你们瞧着她这一副表情,不是都愿意发誓说,她是个黄花闺女?那可大错特错啦;她早已领略了火热的枕席上的风情。她脸红,不为了害羞,是为了罪恶!(102)
克劳第再次确认爱人的“背叛”,于是在婚礼圣坛前将未婚妻塞回其父亲那里:“别把这个烂橘子塞给自己人!”(102)除本剧之外,莎士比亚仅仅在《科利奥兰纳斯》第二幕第一场与《冬天的故事》第四幕第四场中各提到橘子一次。因此本剧中两次出现的橙子一词引人注目。从苦橘子到烂橘子,在彼得·卡内罗斯看来提供了有关爱的两极,更为重要的是开启了剧中有关食物、爱与政治的话语模式(Kanelos, 2016:57)。
首先,我们发现剧中的橘子和异国性相关的,因为当时橘子还是一种进口的奢侈水果。早在1568年,就记载了装有4000个橘子的单个船只从西班牙抵达伦敦。随后贵族开始尝试在英国本土种植栽培这种奢侈水果:“一份宫廷记事年表就表明了1600年左右对此的极大关注,开始在冬天用玻璃屏、盖以及可加热升温的墙体来保护这种外来水果树。实际上当时富人们对果树栽培种植抱有极大的雄心。”(Thirsk, 1999:21)而橘子园及养橘温室在英格兰的流行始于16世纪晚期,已知最初的橘园是1580年左右由弗朗西斯·卡鲁爵士(Sir Francis Carew)在其萨里郡的地产上投资兴建的,到了1587年,正如威廉·哈里森所记载那样,富人种植了品种繁多的非本土植物:“因此我们储藏了很多奇怪的水果,如杏子、杏仁、桃子、无花果、玉米秆都能在贵族的果园里找到。我还看到过马槟榔、柑橘和柠檬,听说野生的橄榄树也在此生长,还有很多其他奇怪的树木植物,它们来自遥远的异国,我都叫不出名字。”(Harrison, 1577)到1631年,杰维斯·马卡姆(Gervase Markham)劝告保护一些脆弱的水果树,有“柑橘树、柠檬树、石榴树、肉桂树、橄榄树、杏树”,将它们放置在“紧邻花园的一些低矮拱形走廊”边(Thirsk, 1999:21)。正如“柑橘暖房”(orangery)这一术语所表达的那样,柑橘是贵族特别偏好的水果,也是当时最时髦的外国进口水果,因此能否培育柑橘也是此人政治身份的一种象征符号。农史学家就写道:“当1604年詹姆士一世和他的王后在白厅举行宴会庆祝英格兰与西班牙缔结和约时,詹姆士一世递给自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重要客人一截绿枝,上面有一个柠檬和六个橘子。他说这是西班牙的水果,但现在已经移植到了英格兰。”(Thirsk, 1999:21)“西班牙的水果”显然是来自弗朗西斯·卡鲁爵士的果园,他为国王在这一场合提供新鲜的柑橘是希望能够得到国王的赏识从而增强其在宫廷中的影响力(早先时候,伊丽莎白女王也曾拜访过卡鲁所拥有和管理的位于贝丁顿的庄园,通过小心地延迟水果的成熟期,他为女王提供了新鲜的樱桃)。詹姆士一世所庆祝的英西和约的缔结,标志着长达19年英西战争的终结,而战争是由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国开始的,同样此举也在表明西班牙的水果现在已经生长在英国的土地上拥有了英语名称(Kanelos, 2016:63)。
进一步而言,橘子之所以受到追捧还因为其食用价值高,具备医学疗效。一方面,与其他水果不同的是,橘子被那些食谱作家所认可,他们认为橘子能刺激食欲,即便直接生吃也毫无问题。饮食作家安德鲁·博德就是那些认为橘子“让人有好胃口”的典型代表之一,橘子皮以糖腌制“能让胃部舒缓”,而橘子汁“是一种很好的调味汁并能刺激食欲”(Boorde, 1547: H1v, D1v)。他的观点得到了托马斯·艾略特的回应:“少许橘子皮在消化时能舒缓肠胃,特别是以糖腌制处理后小块空腹食用。将一块烤面包蘸橘子汁食用,此果汁中加入少许薄荷、糖、肉桂混合而成,是非常好的刺激食欲的调味汁。在发烧时喝加糖橘子汁是不应反对的。”(Elyot,1595:F1r)托马斯·柯甘同样也推荐这种水果:“由橘子汁制成的糖浆对发烧有效,特别是对那些胃部发热病人。同样橘子汁放入少许薄荷、糖、肉桂制成的果汁对胃部虚弱者有效,能刺激肠胃。橘皮以糖腌制保存,橘子花同样如此。两者任意取少许服用对肠胃虚弱无力者甚佳。”(Cogan, 1636:118)但是柯甘也记录下了某位权威(意大利医学家马修欧鲁斯)的不同意见:“橘子的主要吃法是直接食用果肉,或作为果汁,然而马修欧鲁斯并不赞同此吃法,而古拉夫人不但赞成将橘子与肉一起食用,同时也发明了用切成薄片的橘子撒上糖而做成的宴会料理。”(Cogan,1636:118)托马斯·墨菲特特别推荐了塞尔维亚橘子,他将此写作了“Civil-orenges”并认为其“果汁和果肉能促进食欲、压制胆汁(愤怒)、解渴”,对那些“胃部不能消化肉类”的人很好。但是他抵制那些他认为“难吃的”橘子,指出它们“既不营养也没其他用处,只会在胃部坠胀,在腹部产生气体并妨碍消化”(Moffett,1655, Ee1r)。另一方面,很多食谱作者也认为橘子会唤起性欲,我们毫不奇怪像橘子这类被认为可以刺激食欲、对肠胃有特殊作用的食物,会与性欲刺激乃至怀孕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联系也是暂时出现的:班纳特注意到在帕斯顿家族(1422—1509)的信件中提到“橘子……是妇女分娩时所极度渴望的;约翰·帕斯顿(John Paston)认为有必要获取一些送给伊丽莎白·卡尔索普(Elizabeth Calthorpe),因为她 ‘虽然没怀小孩但渴望橘子’”(Bennett,1922:58)。早期现代英国人认为某些食物有益健康,而另一些则有害。琼·菲茨帕特里克指出:“一些奇怪的观念出现,特别是要小心选择蔬菜和水果,而动物的肉则对身体很好。”(Fitzpatrick, 2007:4)在莎士比亚之前的时代,“绿色蔬菜和水果被认为只适合穷人或那些选择修道院生活的人”,直到莎士比亚的时代,蔬果流行而且“新的、多品种的蔬果被进口到英格兰”(Thirsk,1999:16)。其中如桃子、柠檬、柑橘、樱桃等水果则只有贵族才能全部享用(Olsen, 2002:291)。水果可生吃、可做成馅饼,亦可用糖腌制。“水果的食用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一些作家认为过多食用会导致疾病。这种观念到16世纪末期逐渐没落:“在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的推动下,水果逐渐在英格兰得以推广”,因为他们能够进口外国品种、引领饮食习惯(Thirsk,1999:19)。
但是,实际上人们对待食物存在着偏见,尤其是英国人对待柑橘类水果的态度值得怀疑,因为绝大部分柑橘都是进口货物。橘子大量而广泛地进口到英格兰,但是由于售卖时已经超出最佳时期,很多时候人们无法通过外表来判断是否变质,很可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正因为柑橘和柠檬一类水果是从地中海地区进口,因此在英国人看来柑橘的品质与产地的人们是一致的,因此橘子就和放纵与轻浮、无节制和欲望的阴暗面联系在一起,正如阿登版莎士比亚中所讲到:“柑橘与卖淫者相关(或许是因为性病所带来皮肤上的痘疮);它们同时也象征着欺骗和诡计,因为没人能够根据表皮判断里面是什么味道。”因此一方面柑橘是少部分人所享用的时髦奢侈品,另一方面也是大众所共享的知识和疾病认知中相关的物品。从历史上看,这种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买柑橘的人和卖淫者的关联在后来得以巩固和加强,实际上剧中克劳第的“烂橘子”就“被认为令人非常讨厌”(McEachern, 2016:296)。我们看到莎士比亚和他的观众很可能将橘子与西班牙的、时髦的、异国的、激情的、稀罕的、想拥有的、易损坏的、骗人的等形容和概念相联系,因为我们知道吃是基于欲望与基本需求的联合,这也正是橘子在《捕风捉影》中能够为爱情这一浪漫关系提供完美转喻的原因。
2 宴会与食人、捕手与猎物
食物从来就不是中性之物,正如菲茨帕特里克指出那样:“早期现代的食谱书明确指出了食物与饮料并不仅仅是某人的必需之物,同样也暗示着某人在有关阶级、国族、灵性等复杂观念中的位置;有分寸的消费能够修正道德上和肉体上的缺陷。”(Fitzpatrick, 2007:3) 进一步而言,莎士比亚在戏剧中以食物塑造人物身份,甚至食物是“一位剧作家描述角色最简单有效的方法”(Fitzpatrick, 2007:10)。因此首先我们可以发现食物与人物性格特点的联系。根据盖伦(Galen)的描述,如唐·约翰这类忧郁症患者:“贪婪、自私、怯懦……恐惧、谨小慎微、孤独……顽固、有野心、善妒”,由于他们不完善的消化能力,他们会避免过量的吃喝(Fitzpatrick, 2007:2-3)。所以我们看到唐·约翰只会在饿了的时候才吃东西,他说:“我胸中有了气恼,谁也别想逗引我笑一笑;肚子饿了,我就吃我的,别人有没有功夫我管不着。”(32)他宣称克劳第对喜萝的兴趣是他的机会,“出一口气的机会也许来到了”(33)。他假设自己战场上的对手依旧在和平时期对其敌对:“咱们也到宴会上去吧。他们看见我低头服小,更可以开怀畅饮了。”(34)因此他不是要和他人一起用餐,而是想以他们为食,正如基特里奇(George Lyman Kittredge)注意那样,暗示着“欢宴——特别意味着有好东西可以吃”(Kanelos, 2010:53)。随即唐·约翰恨不得把宴会上的宾主都毒死,险恶地加了一句:“要是那厨子的心思跟我一个样,该有多好。”(34)其下毒的欲望将喜剧的欢宴转向了悲剧的氛围,突出了食人的意图,因为他不但想将欢饮的宴会变成复仇的场所,同样也是实现复仇的手段。而且在剧中,爱的推动是跟随着宴会这一交流符号同时进行的。当贝特丽丝到达邀请班尼迪赴宴时说:“真没法儿想,他们硬是要我来请你进去吃饭。”(68)班尼迪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甚至可以说欣喜若狂,因为这是由他的爱人所传达的。与其说食用女性,倒不如说是与特定的女性共同赴宴,他也说:“真没法儿想,他们硬是要我来请你进去吃饭。”(69)这句话里包含着双关的意义,在他看来,贝特丽丝的话中有话,代表着两种乃至多重意义。即便班尼迪愿意向贝特丽丝妥协,但贝特丽丝还没有准备好(Kanelos, 2016:68)。
更进一步而言,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中,人与人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因此剧中的人物既是食客也是食物,换句话说既是猎物也是猎手。首先,我们可以发现的是男性将女性视为物品和食物。一方面,克劳第将喜萝完全具体化为物:“全世界的财富能买得到这样一颗珍珠吗?”而班尼迪则回应:“当然啰,还可以奉送一只安放珍珠的锦盒呢。可是你说这样的话,是心里亮堂堂的呢,还只是满口胡言,把盲目的小爱神说成猎兔的好手,把打铁的佛尔干说成是出色的木匠呢?”(22-23)他把丘比特和捕猎联系起来,让猎物落入陷阱并被杀死。另一方面,克劳第将喜萝视为可口的甜品,他坚持认为喜萝是“是我从没见过的、最可爱的姑娘了”(23)。此后这一克劳第反复坚持的概念后来又被班尼迪在阐释食物时所证实。当克劳第认为自己失去喜萝时,情绪失控,从而被班尼迪取笑:“小孩儿偷了那瞎子的肉,他却去打一根柱子。”(45)卡内罗斯指出,肉是基础的食物之一,在这一句中,小孩儿偷了肉似乎指的是偷了糖果蜜饯果脯。然而从物质性和肉欲上都暗示着女性是肥肉,只适合短暂的食用,同时也镶嵌了班尼迪的评论(Kanelos, 2016:67)。剧中另一女性角色贝特丽丝后来出场时,班尼迪宣告:“殿下,这道菜我可不爱吃!——我吃不消咱们这位尖嘴姑娘”。(48)而在描述克劳第对喜萝难以自拔的爱时,班尼迪嘲弄他“满嘴儿都是些稀奇古怪的词儿,好像是一桌摆满了山珍海味的酒席”(58)。随后班尼迪上了克劳第的当,将他们编造的贝特丽丝对他疯狂的爱信以为真,也以食物摄入作比形容自己的变化:“可是人的口味儿难道不会改变的吗?年轻的时候爱吃的是肉,到老来,也许一看见肉就厌了。”(68)“肉”代表着他现在所拒绝的以前固执的习惯和看法,即以往他对女性的捕猎和食用。我们看到喜萝和贝特丽丝女性都是被当作肉和菜肴,在父权制社会形态下,毫不奇怪剧中出现更多的是与女性相关的食物指涉。而且食物会腐烂变质,于是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特别使用水果来比喻出轨、不忠的女性和未婚妻,例如烂橘子,洗不掉腐烂之处,只能扔掉。
其次,不单单剧中的男性这样看待女性,同时女性中间也是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贝特丽丝身上。喜萝与欧秀拉采用了钓鱼的比喻来描述她们的计划:“钓鱼,最有趣不过的就是看着鱼儿用它那金划子拨开了银浪,贪馋地吞下了那引它上钩的香饵。现在,这条鱼儿就是贝特丽丝”(71),因此她们要让贝特丽丝“吞下那引诱她的香饵”(72)。这一意象从钓鱼的角度进行暗示,意味着作为猎手捕捉香饵的鱼也会成为钓者的猎物。喜萝的目的就在于让贝特丽丝相信班尼迪表面讨厌实则爱慕,甚至“害了相思”,从而“用一串谎话铸成一支爱神的利箭”,趁机射进她的心房,正如后来对欧秀拉所说:“谈爱情全靠碰巧——有的中了爱神的箭,有的中圈套。”(7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萝自己随后也中了自以为是爱人(克劳第)所设置的圈套,在婚礼上颜面扫地。
再次,剧中的男性也毫不例外地成为食物和猎物。对班尼迪而言,爱情把一位老老实实的“士兵”汉子变成了“咬文嚼字的博士”,爱情的魔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宣称:“我不敢发誓爱情不会叫我变成一个牡蛎;可是我能赌咒,在这个爱情没有把我变成牡蛎以前,它别想叫我变成这样一个傻瓜。”(58)班尼迪通过有关牡蛎的比喻将愚蠢和想象结合起来,变成他形容爱情的不理智行为。他恐惧自己会因为爱情脱离自身,也担忧自己会像牡蛎那样被人“吃掉”(Kanelos, 2016:67)。正如克莱尔·麦克伊辰的注释写道:“牡蛎代表着一个男人在不忠的女性胃口面前的脆弱性。”(McEachern, 2016:244)而后面的场景更是证明了他的忧虑,即成为别人的猎物。我们看到克劳第召集同伙设计演戏来诓骗班尼迪,克劳第对彼得罗悄声说:“挨近一步,挨近一步;小鸟儿在打盹。” (62)他暗示着猎人偷偷行近,枝头的小鸟还安然自得,毫无戒备,那时就说。“小鸟儿在打盹”,根据舞台指示,克劳第说这话的时候,向班尼迪躲藏的地方窥视了一下班尼迪就跟小鸟一样,落入了克劳第的圈套之中。因此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霍布斯式的原子个体世界,杀戮或被杀,更野蛮的说法是吃或被吃(Kanelos, 2016:67)。
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到的食人指涉是让人恐怖的,有趣的是,其剧中的食人告诉观众更多的是发生在文明欧洲世界的传说。正如塞德里克·瓦茨指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中提到了异国的食人主义,但真实食人的上演就在家门口。”(Watts, 2000:198) 戈德斯坦也认为剧作家“关心食物”,是因为它们是“刺激了自我与他者边界的互相渗透”(Goldstein, 2013:30)。通过这些隐喻,莎士比亚描述了一个食人的社会,同样也展示出人与人之间吃与被吃的关系,所有的男女都是桌上的菜肴。
3 饮食与爱情、战争
人与食物的关系——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样吃等都构成了此人的关键以及此人所从属的社会经济或宗教群体。班科这样论断:“吃是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而食物的准备、食用、选择等都表达出个体在不同群体中所构建的身份。”(Back, 1977:31)进一步而言,“因为吃的价值远不止填饱肚子,它的本质是无意识层的、深深根植于情感中的有关自我与世界的关系”(Farb et al., 1980:97)。批评家彼得·帕洛林就写道:“食物承载着象征的权力,构建出一种表达文化与个体身份的语言。”(Parolin, 2005:217)罗伯特·阿佩尔鲍姆也同样赞同食物“是社会结构、宗教仪式、经济行为乃至身份结构的中心”(Appelbaum, 2000:33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剧中的饮食话语与战争、战场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贝特丽丝与班尼迪起初剑拔弩张的关系中,爱、战争、性都是一体的。第一幕第一场中,贝特丽丝特意询问使者班尼迪的讯息:“请问,那位‘摆花架式’大爷(Signor Mountanto)从战场上回来没有? ”(15)Mountanto来自于montanto 或montant,为剑术用语,指以剑“往上一刺”,同时也指性投机者(sexual opportunist),同时这一术语暗示着一种傲慢、流行的室内击剑格斗(类似于诙谐戏谑),而不是勇敢的军人职责,也具备吹牛士兵的意义,同时也有性暗示(Kanelos, 2010:23;McEachern, 2016:190)。显然贝特丽丝有意略去了本来战场上英勇战斗的班尼迪形象,嘲讽这位刚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吹牛士兵总是花架子、说大话摆谱,同时也本能地混合了爱与战争,从而一开始就制造出针锋相对冤家对头的喜剧效果。我们接着看到贝特丽丝说道:“从前他在这儿墨西拿,公开宣布,要和小爱神较量较量,说是那小爱神丘比特见了他就望风而逃,吓得箭都不敢放了。我家叔父的小丑听得了他说这些大话,还拿着钝箭头替小爱神打抱不平呢。”(15-17)一方面,贝特丽丝暗示出班尼迪是女性憎恨者,心房不会被爱情的利箭所袭击,同时也指出其对待爱情的态度:爱是一种竞争和较量,或者说是一种零和游戏,即一方得益另一方遭受相应损失,正如哈利·伯格(Harry Berger)指出那样:“爱的竞争让步于爱是竞争”(Berger, 1997:20);而另一方面,贝特丽丝是在说自己,赋予自己在叔父家中的角色,因为钝箭头是王工贵族家中所养小丑可以作耍的射鸟而不伤鸟儿羽毛的工具。接下来的对话,贝特丽丝直接采用了有关吃喝饮食的话语:
贝特丽丝:请问,他这次打仗,杀了多少人,吃掉了多少人?可是我只问:他杀了多少人?因为,可不,我早就答应过,他杀死多少人,都由我吃下去,我包办。
……
使者:这一次打仗,他也立了大功呢。
贝特丽丝:那大概是你们那些发霉的军粮多亏他帮忙“消灭”的吧。他是第一号大饭桶,吃饭的本领可真了不起啊。(He is a very valiant trencherman; he hath excellent stomach)
使者:他可也是了不起的军人呀,小姐。
贝特丽丝:在小姐面前,他倒是个了不起的军人(a good soldier to a lady);可是碰见了爷儿们呢?
使者:在爷儿们面前是大爷,男子汉中间是男子汉——他一身装满了各种美德。
贝特丽丝:说得对,他还塞满一肚子稻草;稻草之外,还有——唉,别提了吧,反正咱们都是要吃饭的人。(17)
在贝特丽丝的问题中“他这次打仗,杀了多少人,吃掉了多少人?”这一有关战争的场景中,班尼迪的“钝箭头”以及“快乐战争”(merry war)都一起崩塌了(Kanelos, 2016:65),从而被日常生活中饮食的隐喻所替代,揭示了战争和战斗者(士兵)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班尼迪是“大饭桶”,当时粗面包很多时候会放在盘子的底部,这些面包也被称为trencher。有时候上层阶级也用面包作为trencher,很多时候实际上他们自己不吃,而是把过滤酱汁的面包切下来给仆人或狗食用(Toussaint-Samat, 1999:229)。另一方面,她指出了战争的残酷性,胜利者不但征服同时也消耗乃至毁灭战败者。而“在小姐面前,他倒是个了不起的军人”有四重含义,一为将士兵和女人做比,二为侵略、进攻(特指性方面),三为男性将女人视为士兵而非求婚者,四为在女性面前吹牛的士兵(McEachern, 2016:191)。显然这是符合贝特丽丝对班尼迪的看法,因为对班尼迪而言爱就是竞赛,他对待他人专横霸道而自私,乃至于结交朋友也不认真,“每隔一个月要换一个把兄弟呢”(18)。正如贝特丽丝明确指出那样,将情感依恋当作游戏是不道德、应当受到谴责的。贝特丽丝暗示捕食者将被猎物所吃:“有班尼迪大爷那样丰盛的酒菜在供养她,‘傲慢小姐’(指贝特丽丝本人)能死得了吗?”(20) 可见“快乐战争”并非两个自由而平等对手之间的轻松巧辩,而是一场由班尼迪强加在贝特丽丝身上的消耗战,贝特丽丝不得不迫使自己放弃自己的意愿和判断来应对班尼迪(Kanelos, 2016:65)。
其次,爱情的变化也与饮食的变化一致。随着剧情的发展,班尼迪决定改变他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克劳第则站到了相反的一端,两人交换了最初的立场:对爱情蔑视的人变得相信爱情,而坚信爱情的人则变得蔑视爱情(Kanelos, 2016:68)。第三幕第二景中,彼得罗对克劳第说:“但等喝过了你的喜酒(your marriage be consummate),我就此动身,到阿拉贡去了。”(76)Consummate指具备性意味的庆祝仪式,暗示着克劳第将与喜萝同房,也可以说喜萝对他而言是可口的甜品,一个异国的、奢侈的物件。在卡内罗斯看来,这就是彼得罗这位海岛拥有者、剧中“荣耀”的男人的态度,他以女性为食物塑造出一副理想的哥们儿关系,因此莎士比亚隐藏了彼得罗的残酷无情和贪婪(Kanelos, 2016:69)。随从卜拉丘(Borachio)给唐·约翰出主意,让其去对彼得罗进言:“你只管去对王爷说,他让克劳第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你把他的身价拼命往高里抬——去跟一个臭婊子(contaminated stale),像喜萝这样的女人结婚,难道王爷不怕连累自己的名誉吗”(54-56),“contaminated stale”指堕落的娼妓,“stale”也是意味着引诱、圈套的术语,含有窃贼通过妓女诱骗受害者之意。同时也意味着放置过久的食物变得腐臭难闻让人作呕(McEachern, 2016:240)。对应剧中两对情侣感情的变化,我们看到班尼迪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从最开始不吃贝特丽丝这道“菜”,到后来改变了口味。而对克劳第而言,最初爱慕、珍贵的事物变得普通,喜萝从“最甜美的姑娘”变成了“烂橘子”,这是因为克劳第眼中的黄花闺女已经在“火热的枕席”(102)上领略风情,成了卜拉丘口中不检点的女人。同样彼得罗也自责自己落入了女人为男人设下的圈套:“叫我说什么好呢?我套进在里头,自己先没了光彩。我干了什么事?叫自己的好友去跟淫妇结合在一起。”(104)至此喜萝不再是可口的甜品,而成了“淫欲里打滚的畜生/纵欲的禽兽(savage sensuality)”(103),甚至其父亲廖那托深信不疑:“她如今落进了乌黑的墨缸里,就连汪洋大海也没有这么多清水能给她洗刷个干净,没有这么多盐好给她解除肉体上的腥臭。”(108)她成了一片腐烂变质的肉,就连水和盐都没有办法去除异味,因此可以说如果她是不贞的,那么就不能得以储存和保留。
再次,班尼迪与贝特丽丝在宣誓相互之间坦诚的爱情时也采用了饮食语言:
班尼迪:凭着这把刀起誓,贝特丽丝,你是爱我的。
贝特丽丝:快别发誓赌咒,免得这刀把子成了你的话柄子(do not swear it ,and eat it)。
班尼迪:我就是凭我的刀起誓:你爱我;谁要是说我不爱你,这把刀子就要叫他做我的活靶子(make him eat it)。
贝特丽丝:你不会嘴巴硬、心里虚吗?(Will you not eat your word?)
班尼迪:我嘴巴硬,心里甜;可再甜也不会把自己说过的话吃下去。我发誓,我爱你。 ( 114)
这一段对话非常有趣,有起誓、吞下自己的话等表述。凭刀剑起誓乃是骑士荣耀的体现,作为骑士的班尼迪自开始就以刀为参照物,将他对贝特丽丝的爱置于他与刀的关系之中,这恰好证实了贝特丽丝之前的嘲弄,即他并没有吹嘘的那么英勇。反而是贝特丽丝将誓言饮食化,揶揄着男性征服与消耗的癖好。同时贝特丽丝谴责克劳第婚礼上污蔑、抛弃喜萝时说道,“上帝啊,但愿我是个男子汉!我要在十字街头吃他的心”(115)。正如卡内罗斯指出那样,贝特丽丝实际上点明了这出戏的真相:男人是心的食用者。他们极度自私,以荣誉为名掩盖自己兽性的胃口,容纳的既不是同情,也不是爱。而贝特丽丝的话还可以反过来理解,即班尼迪对她要求的拒绝正是贝特丽丝一直以来所恐惧的——他在一点一点啃食贝特丽丝的心。然而在看到爱人的悲痛之后,班尼迪改变了。正如廖那托所言:“可是兄弟,这样的人世上不会有。不曾尝到痛苦的滋味,大家都能慰劝别把苦痛忍耐些;一旦自个儿遭遇了惨痛(tasting it),他的洞达变成了心摧肠裂。”(124)正是由于班尼迪经历过了,他才认识和体会到自己对贝特丽丝的感情,最终理解了激情和爱。当他说“够了,一言为定!(Enough, I am engag’d )”(116)时,不但说明他理解了克劳第,同时也表明他发现了自我(Kanelos, 2016:71)。于是面对克劳第,班尼迪不禁发声:“你已经害死了一位好姑娘(sweet lady),这深重的罪孽一定会落在你头上。”(131)他所采用的称呼正是克劳第反复称呼喜萝的。彼得罗要么误会了班尼迪挑战的严重性,要么认识到了重要性,因此试图以喝酒来搅浑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状态:“什么,请酒吗,是请酒吗?”(131)但克劳第这样回应:“我要是不施出全身本领,宰割得好好的,就算我这把刀子不中用。也许我还能吃到一只呆鸟吧。”(131)宴会彻底变质了,一场宴会的前提是狩猎和宰杀并提供新鲜的食物,但现在饮酒狂欢的人却做出了互相切割的姿态,作为和谐氛围象征的宴会则变成了争斗的场所。
4 结语
正如康奈尔(Patrick O’Connell)认为,“若了解食物也会了解历史、语言与文化”,食物不仅仅是我们生理需要的必需品,它同样指涉了社会身份、物质财富、多元农业、贸易、宗教信仰、价值观、同时代医学观念以及生活方式(Segan, 2003:13)。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食物是因为戏剧和食物是同时被享受的,“食物和饮料作为戏剧欣赏经历的一部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人们在欣赏戏剧的同时吃吃喝喝”(Fitzpatrick, 2007:5)。而莎士比亚通过食物探讨着舞台上人生的各个阶段:诞生、个人身份的形成,社会群体的定义,生理需要的满足,爱和性,死亡,他同样以作为生理基本需求的食物作为表达更加复杂的情感的手段。戈德斯坦指出,没有吃的伦理,只有作为吃的伦理,吃就是伦理(eating is as ethics)。吃不仅关乎我们怎样正确对待自己的身体、动物、植物和环境,也关乎我们认识自我的起点。吃塑造了我们的伦理自我(ethical selves)(Goldstein, 2013:209)。我们看到结尾处依旧是以饮食结束:
贝特丽丝:一半儿也是为了要救你一条命——我听人家说,你一天比一天的瘦了。
班尼迪:别闹!看我不堵住你的嘴。(152-3)
显然,莎士比亚通过剧中的饮食叙事,告诉我们食物及吃喝细节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剧情发展,乃至对整个故事有着统摄和暗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