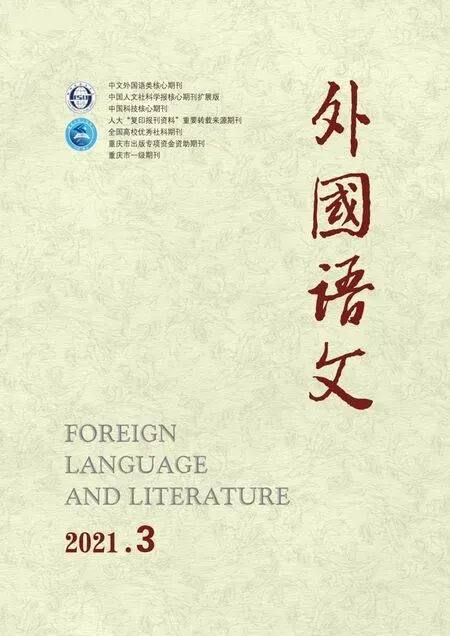海明威对梅勒的影响渊源考
许梅花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0 引言
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欧内斯特·海明威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一般而言,在谈及作家的影响力方面,人们倾向于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影响读者,另一类主要影响其他作家。海明威自然属于后者。作为一代文学之父,海明威以其独特的文风、典型的人物形象、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与态度影响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后辈,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能捕捉到海明威的影子,如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琼·狄迪恩(Joan Didion)、雷蒙德·卡弗(Raymond Carver)、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等。在以上作家中,诺曼·梅勒算是受海明威影响最为彻底的一个。梅勒长踞美国文坛达半个世纪之久,素有“海明威第二”“又一个海明威”“新海明威”的称号,对于这些标签,梅勒从未拒绝过,甚至在很多场合一再强调海明威对他及其他作家的影响。
1961年,海明威自杀身亡。梅勒在得知海明威的死讯后,悲痛不已,并评价海明威是“美国现代文学之父,至少对男作家来说是这样”(Solomon,1989: 145)。梅勒的评价的确是那一代男作家的心声,因为海明威的文风影响了几代人,用梅勒的话说,“就如一个漂亮女人穿过房间,一整屋子的男人都受到影响一样——无论好坏,他们都辗转反侧”(103)。自那以后多年,梅勒对海明威的总体评价从未变过。在1990年7月7日至11日于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海明威讨论会”上,梅勒致开幕词,依然称海明威是他们那一代的作家之父。他们对他怀有的特殊感情,就好比儿子对父亲:爱得甜甜蜜蜜酸溜溜,又惧怕又尊重。海明威去世时,他们大为懊恼,感觉像被自己父亲遗弃一样。
就梅勒个人而言,海明威对他的影响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在读大学之前,梅勒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大一时,他开始读沃尔夫(Thomas Clayton Wolfe)、海明威、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菲茨杰拉德(F.S.Fitzgerald)、法奈尔(James T.Farrell)、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作品。在阅读时,梅勒长期保持着喝酒的习惯,因为他了解到海明威也有此喜好。除此之外,对海明威的大男子主义竞技精神和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冒险经历,他也竭力模仿。羸弱的他开始积极参加各类运动,尤其酷爱拳击。在创作上,梅勒更是尝试着创作一些短篇,“而大多数故事都揭示了海明威对他的影响”(Lenon, 2013:37)。譬如,他曾和他的教友一起对海明威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和《永别了,武器》进行戏仿,题名《蛋蛋为谁而嚎:永别了,不安》(For Whom the Balls Squall: Farewell to Qualms)。在他另外一则短篇故事中,甚至还包含了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重写了60-70遍的选段。虽然在当时梅勒觉得帕索斯和法奈尔更让他感到兴奋,但对他来说,模仿海明威相对容易些,因为“像法奈尔或帕索斯那样写作需要更多经验”(Mailer,1992:27),而那种经验对当时只有18岁的梅勒而言是不可获得的。然而,梅勒未曾料到七年后当他那本以二战太平洋战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TheNakedandtheDead,1948)声名鹊起时,他的写作已经受到了多个作家的共同影响。小说发表时,他人在巴黎,当他回国时,发现自己早已被人冠以了“新海明威”“新多斯·帕索斯”和“新梅尔维尔”的头衔。
虽然梅勒身上可见多个作家的综合影响,但在谈到一个作家的影响力时,梅勒最重视的还是海明威带给他的影响。他对海明威的崇拜,自青年时期起就未停止过,除了海明威的自命不凡和反智主义他不敢苟同外,“他以老爹作为标杆评判自己持续了近70年”(Lennon, 2013:39)。这种崇拜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梅勒作品中人物塑造与主题选择、文体风格和女性观三方面。
1 人物塑造与主题选择
在人物塑造和主题选择上,梅勒继承了海明威的硬汉精神。众所周知,海明威擅长塑造保持“压力下的风度”的硬汉形象,从而彰显他的英雄主题。他作品中的硬汉形象包括拳击手、斗牛士、猎人、渔夫等,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拥有一种百折不挠、坚忍不屈的意志,在直面暴力和死亡、直面未知命运危机时,都能表现出一种从容、淡定的态度,从而表现出人的勇气,维护人的尊严。在他诸多作品中,最为经典的硬汉形象要数《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罗伯特·乔丹和《老人与海》里的桑提亚哥。乔丹从一名西班牙语讲师毅然变身为反法西斯战士,主动加入西班牙反法西斯战线,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不畏艰难险阻,显示出过人的勇敢和胆识,最后为了顾全大局,英勇地引爆手榴弹,圆满地完成炸桥的任务。老渔夫桑提亚哥更是将“硬汉”性格演绎到极致,在与大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他未被鲨鱼的强大所吓退,反而一直奋力与之搏斗,直到最后筋疲力尽。在这场不可避免的败局中,桑提亚哥真正表现出“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神,完美体现了勇气是“压力下的风度”。
诺曼·梅勒吸收了海明威的硬汉风格,推崇海明威式人物的勇气,即一种生存的勇气,直面死亡的勇气。从海明威那里,梅勒了解到,“在一个邪恶的社会里,除非一个人能保持勇气,否则就没有爱情、没有怜悯、没有仁慈、没有正义……”(Mailer,1992:340)。正是这股勇气使梅勒成为当代美国文坛中最具个性和反叛精神的作家之一。在他颇具代表性的文章《白色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7)发表之前,梅勒已经在《裸者与死者》《巴巴里海岸》(BarbaryShore, 1951)、《鹿苑》(TheDeerPark,1955)等作品中表现了嬉皮士般的勇气。在《裸者与死者》中,极权主义的代言人卡明斯少将和侦察分队的指挥官克洛夫特上校不允许部下保持他们的个性及反抗精神,如果有任何士兵违背他们的命令和意志,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动用自己手中的一切权力将他们彻底摧毁。小人物侯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作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代表,始终心怀个人信念,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哪怕顶头上司是一个具有极强权力控制欲的人,他也在所不惜地与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对抗,以致最后引火烧身,被克洛夫特暗算,死于日军埋伏的乱枪之下。侯恩的死证明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抗与勇气并不能成功地与极权主义的体制抗衡,最终会沦为权力的牺牲品。有学者指出当时的梅勒“完全不知如何对极权主义的侵蚀力进行有效的英勇抵抗”(Poirier, 1972:33)。事实的确如此,这从梅勒在作品中安排侯恩死亡的结局中可窥见其端倪。在接下来的作品《巴巴里海岸》和《鹿苑》中,梅勒继续表现海明威式的勇气,并找到了对抗极权体制的有效方式。这两部小说展现的都是美国当时的真实社会环境,即麦卡锡主义反共阴影笼罩下的美国。与《裸者与死者》相同,两部小说里的正面人物革命者麦克利奥德和理想主义者艾特尔最终都成为极权主义的牺牲品,不同的是两部小说的叙述者罗维特和瑟吉厄斯在目睹了牺牲者的遭遇后,依然能鼓足勇气面对未知的将来,不愿向极权主义低头。这时候的梅勒已经意识到“正在形成的勇气是至关重要的”(Wenke,1987:56)。
梅勒曾在一次访谈中谈道:“20世纪以来,海明威开始痴迷于暴力,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在战争中就被撕碎了。暴力对他来说是最主要的。我读海明威的时候,非常痴迷于他创造暴力的方式,但是还不满意。”(梅勒, 2017: 326)鉴于此,梅勒在塑造海明威式的硬汉形象时,将海明威对暴力和死亡的迷恋发挥到极致。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美国极权文化盛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消极、死气沉沉的气氛,人们要么没有勇气,要么勇气不够,行为和意识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勒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发表了《白色黑人》一文,阐述了他经多年探索形成的嬉皮士哲学。在这篇文章中,梅勒指出,要在极权主义环境与死亡威胁的夹缝中求生,并真正重获自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吸收黑人存在主义特质,做一个真正的美国存在主义者——嬉皮士(Mailer,1992:306)。嬉皮士的主要特征包括叛逆、放纵自我、勇敢、敢于冒险和崇尚暴力,在当时阴暗的政治文化环境下,这对自我回归显得尤其重要。在梅勒看来,嬉皮士精神不单单意味着海明威式的勇气和对未知领域的冒险,更是意味着任意宣泄都只受自我感觉支配的暴力倾向,以暴力“开辟成长道路”,达到“精神净化”(Mailer,1992:319)。在《一场美国梦》(AnAmericanDream,1965)中,罗雅克将梅勒所推崇的嬉皮士特质展露无余。为了实现他在财富和政治上的抱负,罗雅克娶了出身高贵的黛博拉为妻。但是,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妻子面前,他似乎扮演了一个软弱、“底气不足”“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角色。黛博拉性格傲慢、身份神秘,擅长对罗雅克进行各种冷嘲热讽,说他是“带着血腥味的哭啼者”,是“小贩的后代,可怜的物质至上的贪婪小人”(梅勒,2001:34)。面对魔鬼一样的黛博拉,备受控制的罗雅克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强烈的挫败感,因为他甚至不清楚自己“是不是有力量摆脱枷锁”(梅勒,2001:16)。最后,罗雅克在一次与黛博拉争吵的过程中,因再也不堪忍受她的嘲讽戏谑,与她扭打,并最终掐死了她,然后从楼上把尸体抛下,伪装成她自杀的假象。之后,为了逃避警察的盘问和岳父的挑衅,罗雅克通过一系列行动表现出海明威式的硬汉气概,努力挣脱主流社会强加给他的道德牵绊,采取梅勒心中“嬉皮士般的勇士”行为,从而实现了自我的回归,走向了自我成长的道路。梅勒在小说中对暴力和勇气的渲染曾遭到众多评论者的谴责,更有学者把罗雅克的杀妻行为与梅勒在一次宴会上因醉酒而刺伤妻子的行为等同起来,认为罗雅克是梅勒的“又一篇可怕的自我广告”(Glenday,1995: 88)。
或许,梅勒在现实中刺伤妻子的行为只是一种以身试险,试探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勇敢,恰如他在一则访谈录中回应是否海明威之死会影响他对勇气的评价时所作的回答那样:
我不愿意这样想。我有自己的假设:海明威很早就从生活中了解到,离死亡越近他就越有活力。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的灵丹妙药,所以才敢于不断地面对死亡,所以我想象海明威晚上经常在跟妻子玛丽说晚安之后,回到自己的卧室,就拿猎枪顶着自己的嘴,大拇指按在扳机上,慢慢地一点点按下去——同时紧张得颤抖起来——他就是想看看自己在不走火的情况下到底能靠死亡有多近。终于最后一天晚上他玩过火了。(梅勒, 2017:317)
从以上评论可以看出,梅勒把海明威的自杀理解成一种勇士行为,而不是很多评论者所认为的因内心敏感与脆弱导致的懦夫行为。
2 文体风格
在文体风格上,梅勒继承了海明威新新闻主义的写作方式,并尝试着模仿海明威的简洁语言。海明威一生致力于写作艺术,“他自认是在摸索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语言,是在与其他的现代主义先驱——如詹姆斯·乔伊斯、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坦因等——进行同样性质的探索”(休梅克,2019:13)。显然,海明威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是成功的,诺贝尔奖委员会于1954年因其“精湛有力、独树一格的现代叙事艺术”授予他文学最高奖项。
海明威成名之前,曾做过多年的报刊记者。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中,他突破传统的何时何地何人的新闻报道套路,用写小说的技巧写新闻,开创了写新闻的新形式,而且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虚构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影响了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诺曼·梅勒、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邹恩·狄迪恩等一批作家。60年代的美国社会混乱、文化变革、道德伦理观错位,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然而,传统的新闻报道依然以“客观事实”为衡量新闻的标准,无视重大的现实变革,更有记者凭着对客观事实的过分信任,充当政客和社会显要们的利益传声筒。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美国文坛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竭力寻求一种新的文学创作形式来记录当下的社会事件。
海明威早已开了新新闻写作的先河,之后又因社会形势所迫,新新闻写作便顺应时代而生,并逐渐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创作模式。该写作一反传统模式化的新闻报道形式,以积极主观的姿态介入到新闻报道中,并注入更多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以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让读者更真实、更深刻地了解社会现实。作为海明威最忠实的粉丝,诺曼·梅勒就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在他最具代表性的新新闻主义作品《夜幕下的大军》(TheArmiesoftheNight, 1968)中,他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反越战争的示威游行中,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进行报道,这部作品在风格上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手法,具有强烈的纪实文学特征。正如记者出身的海明威不允许把他的新闻作品归入他的小说和非小说一样,小说家出身的梅勒也拒绝新闻界授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称号。在《夜幕下的大军》中,他把文本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之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并将这种新新闻写作称之为“非虚构小说”。其实,两者并无太多不同之处,唯一不同在于前者是新闻记者执笔,后者是作家执笔。梅勒此后延续这种文风,创作了为他赢得第二次普利策奖的《刽子手之歌》(TheExecutioner’sSong, 1979),作品讲述了美国犹他州杀人犯加里·吉尔摩的故事。或许梅勒特别在意自己作家的身份,在这部作品出版时,他拒绝称之为“非虚构小说”,而是称作小说。尽管出版商都竭力反对,不过最终都选择妥协,认为应该礼让作者三分。在梅勒看来,小说与非小说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对此,他专门作过解释:
每个事件其实都是小说,因为,当人们试图再现发生的事情时,它已经杳无踪影了。这正是作家竭尽全力接近事实的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报纸上的每条报道其实都是小说,尽管不很精彩。报道的实质决定了记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件,在彻底弄清真相前,就给出一个小小的结论,从而引导人们用错位的符码看世界。而同是错位的符码,我更喜欢小说。小说的宗旨是要艺术地综合可能发生在人们身上的经历;非小说则力图涵盖故事发展所必需的创作元素,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你用拍照片的方法,那你就毁了整个故事。(梅勒,2016:24)
梅勒在创作《刽子手之歌》时,力图重现事实原貌,但他写完后,仔细校对文本中的人物,还是觉得有一两个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有差别。所以,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即便你小心翼翼地去写非小说类作品,你写出的仍是小说。”(梅勒,2016:24)其实,无论是非虚构小说还是小说,梅勒在融合两者时的成熟表现受到海明威的启蒙,这是无法否定的。就如梅勒自己所说,海明威“改变了我们看事物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写作的方式。那是两项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Lenon, 2013:716)。从梅勒两部获普利策奖的新新闻作品来看,他确实从海明威那里获益匪浅。
海明威的记者生涯,不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写新闻的方式,而且还锤炼了他的文字功夫,形成了一种“电报体风格”的简洁语言,在这一方面梅勒也尽力模仿。海明威简约的艺术在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极少用修饰词,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贝茨,1981: 319)。在一次访谈中,当梅勒被问及海明威对他的影响在何处时,他这样回答:“从海明威身上我学会了克制,同时,也领略了简洁英语的魅力。他向我们展示了把英语简约化,而不是尽可能多地使用拉丁词的时候,英语是多么摄人心魄。”(梅勒,2006:22)尽管他公开宣称崇拜海明威,但早期作品在语言上其实不怎么像海明威,而是一种“巴洛克风格”的文字,这源于他所称的“三角”影响,即海明威、福克纳、法奈尔的综合体。在他看来,“海明威力求中庸,惯用诗一样强烈的意象;福克纳富于超常规的狂热,整个人淹没在文字的海洋里;法奈尔带给你的真实使你除了尊重事实别无选择”(梅勒,2006:22)。基于此,梅勒最终认为自己的风格“既得益于超常规,又获益于最简约”(梅勒,2006:22),同时又尊重事实。在谈到小说的风格时,梅勒认为风格好,素材就会受限;素材好,风格或许就不那么好。他自认为在《一场美国梦》中他的“巴洛克风格”已经发挥到极限,所以在写《刽子手之歌》时,早期的“三角”影响不复存在,而是承袭了海明威的简约文风。在该作品获普利策文学奖时,评论家们提起最多的便是其朴素的文风。在此之前,梅勒的“巴洛克”风格备受批评家诟病。对此,梅勒自己也甚是苦恼,因为他觉得“巴洛克”风格并不好写,需要“得好多年的努力”(梅勒,2017:316)才能练就。最后,他还是决定找到最好的素材来证明自己可以写得很简洁。在《刽子手之歌》中,他便使用了最好的素材,形成了简练的风格。这部作品曾一度让他以为自己可以打败海明威,然而,要论简洁的话,他承认自己依然不是海明威的对手。在他看来,海明威“最为全面地展示了英语句子的潜力,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梅勒,2017:316)。尽管梅勒没有学到师父的精髓,但对于自己的弱项,一向狂妄的梅勒表现出难得的谦逊,这是比较罕见的。
3 女性观
在对待女性的矛盾态度上,梅勒与海明威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关于海明威的女性观,评论界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相当一部分评论者认为海明威作品中着重凸显“硬汉”形象,且海明威一生对强势的母亲都持敌视态度,所以认为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更有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根据海明威部分作品中所谓的“妖妇”形象,如《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安什利、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TheShortHappyLifeofFrancisMacomber,1936)中的玛格丽特、《乞力马扎罗的雪》(TheSnowsofKilimanjaro,1936)中的海伦等,故而定论海明威是一位有“厌女情结”的“男性沙文主义者”。然而,也有学者表示海明威并非彻头彻尾的大男子主义者,认为他是位女性主义作家,挑战男女的性别角色,塑造了强大的女性形象,她们有些仅凭自身便是女性版的“准则英雄”(休梅克,2019:14-15),例如《丧钟为谁而鸣》中的比拉尔就是这一类的“准则英雄”。她泼辣豪爽,坚强果敢,与胆小懦弱、瞻前顾后、只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丈夫巴勃罗形成鲜明的对比。比拉尔顾全大局,赞成炸掉决定战争成败的铁桥,而巴勃罗沉溺物欲,自私自利,阻止炸桥。他后来出尔反尔,在关键时刻私自出逃,而比拉尔则挺身而出,主动承担原本属于巴勃罗的任务。在比拉尔身上,海明威赋予她原本属于男人的传统品德:勇敢、坚强和责任心。所以,从这一点看,评价海明威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界定,并不为过。海明威渴望塑造新女性,但这一类形象对他来说还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纵观当时主流社会对女性的评判标准,并结合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不难看出,海明威的女性观反映了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矛盾。
综上所述,梅勒呈现出与海明威相似的痕迹。但与海明威不同的是,梅勒与母亲关系一直很好,母亲对他的宠溺成就了他自负狂妄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加上梅勒本身对海明威大男子气概的崇拜,导致外界一直对他有所误解,使他备受女权主义者的诟病。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梅勒有一种极度的厌女情结。如果单看他某些作品中的文字及其在公众场合的个别言论,似乎能得出这样的片面结论。他在《总统文件》(ThePresidentialPapers,1963)中公开表示“大多数彻底了解女人的男人都会对女性表示敌意……女人就是下垂的、松松垮垮的畜生”(Mailer, 1963:114)。在一次电视访谈中,他表示并不讨厌女人,只是认为“她们应该关在笼子里”(Dearborn, 1999: 286)。梅勒对两性的态度也趋于保守,他认为“女人首要的职责是在这个星球上存活足够多的年头并找到合适的最佳伴侣,生育出不断改良的孩子”(Mailer, 1971: 130)。如此过激的言论,连同他在生日宴会上刺伤妻子的事件,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7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的靶子。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1934-2017)在其专著《性的政治》(SexualPolitics,1969)中就专辟一章对梅勒的大男子主义进行抨击,称梅勒为“对男性气概顶礼膜拜的囚徒”(1999: 314),认为他在性别上的保守态度“连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和教会都望尘莫及”(323)。米利特的批评看似不无道理。梅勒作出回击,认为米利特在所选材料上缺乏忠实,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海明威一样,梅勒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也表现出对女性的欣赏与钦佩,在他看来此类女性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目的是拯救男人,如《鹿苑》中的埃琳娜、《一场美国梦》中的彻莉等。所以,梅勒也绝非那些评论者所认为的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他甚至在一些作品中同情很多身处困境的女性个体,如《鹿苑》中的露露和埃琳娜,《巴巴里海岸》中的古艾维尔夫人等。面对女权主义者的指责,梅勒曾公开进行辩护,表达自己的态度。对于女权主义运动所追求的权利,梅勒认同其中两点:一是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中遭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待遇;二是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他认为男女本质上是不同的。对女权主义者在堕胎、避孕和生育节制上激进的做法和非自然的观点,他表示坚决反对。
从梅勒对待女性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与海明威一样,呈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都渴望塑造新女性,但又都秉持传统的性别标准。正如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女性的秘密》所言:“当今的男人采取一种两面派态度。这很伤女人;他们从整体上接受女人是平等的人,但他仍旧要求她保持次要地位。”(1988:221)或许对海明威和梅勒来说,最能代表他们心目中理想女性形象的应该属玛丽莲·梦露无疑了。海明威曾撰写过《我心中的玛丽莲·梦露》一文,在文章中以惯常的简洁文风赞美了她的容貌,并高度评价了她的诸多品质和才华。在海明威的笔下,梦露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性感宝贝”,而是拥有鲜活饱满的多副面孔。梅勒也是如此,不仅在小说《鹿苑》中的女演员露露身上投射了梦露的影子,还在梦露死后,写了两部关于她的作品,分别为《玛丽莲的传记》(Marilyn:ABiography,1973)、《关于女人和她们的优雅》(OfWomenandTheirElegance, 1980)。和海明威一样,梅勒在书中对梦露的描绘和评价注入了一些理想化的成分。但与此同时,他们都对身处现代社会规约下的梦露寄予深切的同情。事实上,梦露最后的香消玉殒也证实了波伏娃的话“女人自主的胜利与女人气质相抵触”(1988:221),尽管不乏海明威、梅勒这样的大作家为之着迷,但作为全世界公认的女性气质最佳的梦露终其一生还是未能获得女人自主的胜利。
4 海明威与梅勒的互动
综上分析,可见海明威对梅勒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深远而持久。梅勒一直渴望能像海明威一样战斗,但总觉得与海明威相比,他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显得非常渺小。的确,梅勒同时代的或者后来的作家都想成为海明威式的人物,而海明威(1986:183)却认为,“人们模仿他的弱点,硬学他的节奏与韵律,还美其名曰海明威式风格,可是谁也不希望他好”。如果说海明威对他的同时代作家没有一句好话,那是不属实的。对于新晋作家,他时褒时贬。在他与梅勒之间,绝不是梅勒单方面对偶像的崇拜和痴迷,也有着海明威对他的鼓励和批评。
海明威(1986:170)如此评价梅勒:
梅勒可能是战后最优秀的作家,他是写心理的。可是他最吸引人的就是心理部分。说不定他再也写不出像《裸者与死者》这样的作品来。如果他写得出来,那我就得注意点了,又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较量,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干,谁也超不过三个回合。
能得到海明威的肯定,梅勒受到莫大的鼓舞。然而,在《鹿苑》的出版宣传期间,梅勒曾给素未谋面的海明威寄去样本,并未收到任何回复。在他送出去的样本中,他对海明威寄予最大的希望,因为他期待海明威的只言片语能为《鹿苑》带来好的销量。正如他之后回忆的那样,“我不能阻止自己去想从海明威嘴里说出来的20个词会在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之间带来差异。他会喜欢这本书,他必须喜欢这本书——他不可能看不见这本书蕴藏的巨大价值”(Mailer,1992:265-266)。在寄出样本之前,梅勒还随书附言,具体内容如下:
致海明威,——时隔多年,最终我还是急切地想知道你对这本书的看法。——不过,若是你不回答,或是你以你一贯对待那些业余作家、马屁精、谄媚者的批评方式对待我,那么不好意思,去你妈的。我也绝不会再和你有任何交流。——因为我怀疑你比我更狂妄,所以不管你喜欢与否,我都要警告你,在此书的353页,我参考了你。
诺曼·梅勒(1992:265-267)
从上述附言可以看出,梅勒渴望得到海明威的认同,不仅如此,他渴望与海明威有不同于一般作家的那种深度交流。但是,当时海明威远在古巴,梅勒的书寄出十天后,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为此,梅勒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性,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好在四年后,在《巴黎评论》(TheParisReview)主编乔治·普林顿(George Plimpton)的鼓动下,海明威写了一封信给梅勒,首先表达先前赠书的感谢之情,然后表示已经买了那本书,尽管恶评如潮,他依然喜欢。他鼓励和宽慰梅勒:“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担心那些评论。那些都是毒药。记住只有傻瓜才会担忧。当你写不下去,感到焦虑时,不妨去干架。那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思想。这是我所能告诉你的可能有用的东西。”(Hemingway, 1981:912)如果海明威的信件能早四年到达梅勒手里,那真算得上是一支强心剂,因为当时的他的确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
然而,在某些场合,海明威对梅勒的批评仿佛又毫不留情。在一次访谈中,他含沙射影嘲讽梅勒的狂妄,当提及一个写战争的作家时,他说到,“此人显然自以为有托尔斯泰之才,其实他只配在伯令·莫尔曲棍球队里当托尔斯泰”(海明威, 1986:198)。众所周知,梅勒写完《裸者与死者》后,曾宣称要写一部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伟大的巨著。显然海明威口中的这个作家非梅勒莫属了。另外,海明威(1986:125)在写给他的出版商查尔斯·斯克利布纳的一封信里也暗讽梅勒的狂妄:
我这人没有任何野心,除了想当世界冠军。我不会跟托尔斯泰博士来二十个回合,因为我知道他会把我耳朵打掉。这位博士力气可是足得可怕,可以老打下去,接得上去……
但是布洛克林那帮愣小子无知透顶,居然一开始就跟托尔斯泰先生交手。拳击还没开始,他们就宣布打败了托尔斯泰。
显然,“布洛克林那帮愣小子”包括诺曼·梅勒。梅勒宣称要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尔克斯、乔伊斯和弗洛伊德、司汤达、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施本格勒、福克纳,甚至还有正在腐朽的老海明威或许都会读,因为这部书承载着他们想要讲述的一切,飞完路程的另一部分。”(Mailer, 1992: 477)暂且不论梅勒是否能写出世界名作家都会读的作品,单就他对年老的海明威不屑一顾,就足以让同样狂妄的海明威气急败坏。
由此可见,梅勒对海明威的评价,也不是一以贯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刚出版时,梅勒表示喜欢老年渔夫为了捕到一条大鱼而做出的英雄般的搏斗情节,但他却无法忍受海明威的文风过于“忸怩作态”(Lennon, 2013:150)。最令他恼火的是海明威的自负,觉得他总是在暗示如下的信息:他是一个伟人,因机缘巧合成了一名作家。所有人都执迷于他作为伟人的历练所进行的高尚、勇猛和漂亮的尝试(Lennon, 2013:150)。这是梅勒自大学时代模仿海明威以来第一次直接表达对这位前辈作家的感情。他认为海明威早期作品都堪称经典,但对其后期作品持保留意见,同时对海明威的巨大公众表现力表示厌恶。然而,了解梅勒的人都知道,海明威身上让他讨厌的东西,如自负、巨大的公众表现力等,他都一并承袭了过来。在20世纪50年代末,梅勒又改变观点,认为海明威努力“用他的个性使作品更丰满”(Mailer,1992:21),并对海明威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当回首他重写《鹿苑》的日子,梅勒意识到他自己是他那一代为数不多受海明威文学影响的作家之一,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对海明威的二流模仿感兴趣,而是觉得他自己和“老爹”拥有了共同的思想,那就是“即便一个人才华耗尽,最终成了一个凡人,但比起成为一个好的作家,成为一个凡人更重要”(Mailer, 1992:265)。
5 结语
梅勒的写作老师纳尔逊·阿尔杰恩(Nelson Algren)曾对梅勒说:“重要的是你喜欢的作家能给你带来积极影响,你模仿他是因为他能快速教会你如何去创作,一旦你学会,你就应该立志和你的偶像保持适当距离,去开辟自己的创作风格。”(梅勒, 2016: 22)的确,“老爹”的离去,就像其他父亲的死亡那样,解放了梅勒。尽管他悲伤、愤恨、失望,但海明威的离去可以看作梅勒接下来10年伟大成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