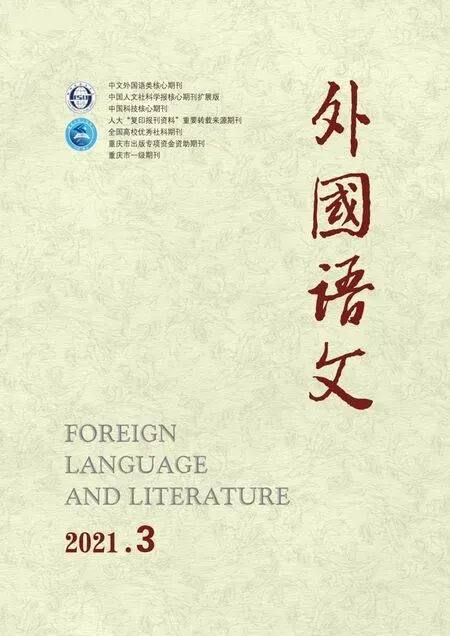空间·身份·共同体
——重读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的人》
简悦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0 引言
《晃来晃去的人》(DanglingMan,1944;以下简称《晃》)是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它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二战期间芝加哥犹太青年约瑟夫待入伍前的人生经历和内心生活,被誉为“美国最好的战争小说之一”(Bradbury,2010:36)。小说中,无论是主人公约瑟夫所处的宏观社会空间,还是他偶尔走访的亲朋好友的日常生活空间,均以前景方式活跃于文本之中,投射着以约瑟夫为代表的美国犹太移民的主体身份。学界相关研究倾向于对该小说进行存在主义式的解读,探讨其中的“选择”“异化”“自由”等问题,对于作品的空间之维则鲜有论及。哈桑(Ihab Hassan)指出,约瑟夫虽然有许多种选择,但他最后选择参军是为了逃避自由,日益加深的异化感让他忍无可忍(1982:190-198)。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论者将约瑟夫视为传统的反叛者,认为他最后在“存在主义与确实可以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的力量的妥协之中加入了军队”(埃里奥特,1994:956)。在布利吉特·什奇尔-什纳兹勒(Brigitte Scheer-Schäzler)看来,约瑟夫是个被异化的人物,只能“被迫在非渴望的抉择和渴望的抉择之间做出选择,约瑟夫为‘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乔国强,2014:101)。我国学者祝平认为异化状态并未让约瑟夫不作为,“他参军是他积极的‘自为’,是他对自己负责任的选择,他选择了群体,选择了社会”(2009:37)。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美国二战时期的社会空间以及犹太移民的家庭生活空间,揭示犹太移民的身份危机以及他们对共同体的强烈憧憬,深化对于该作品主题意义的理解。
1 反犹主义当道的社会空间
犹太青年约瑟夫生活在二战全面爆发之际的芝加哥。在《晃》中,这座大都市并非一个静止的背景、空洞的容器,而是一个由特定政治集团“加工、塑造”并被时代所镌刻的社会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表现”(列斐伏尔,2015:37),反映了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个社会空间生成后,便作为“一种控制、主宰和权力的手段”(Lefebvre,1991:26),影响着主人公约瑟夫的自我身份认同。
约瑟夫在第一篇日记中(1942年12月15日),开门见山地写道:“这好像是一种繁文缛节,一种打尽官腔的官僚主义喜剧。起初,我把这种想法藏在心里。今年五月,我被送回家,因为我的材料还未准备就绪。刚一开始,好像是假日来临,又像是暂缓处刑。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八个年头,但我仍然是一个加拿大人,一个不列颠臣民。虽然是个友邦的侨民,但未经调查,我还是不能入伍。……这样,我又被打发回来。肯定,这种倒霉事还没完。还会再气三四个月。”(贝娄,2002:4)在此,约瑟夫不仅以寥寥数语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更以自己的“倒霉事”勾勒出以芝加哥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空间内的政治图景,展现了犹太人二战时被美国官方敌视、排斥的遭际。尽管犹太人在美国享受了现代犹太历史上相对来说最为安定、繁荣的一段时光,“至少在以色列建国前,最幸运的犹太人是美国犹太人”(Raphael,2008:436),但反犹主义在美国并未销声匿迹,而总在经济危机、种族主义、仇外主义、甚至仇富心理等压力下,周期性回潮。二战时期,反犹主义愈演愈烈,在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新一波反犹浪潮。反犹主义者极力左右罗斯福政府与犹太人相关的战时决策,触发了一系列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一方面,犹太人合法的移民通道严重受阻。据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统计,“1943年时,只有11 737名犹太移民被获准入境,尚有142 142个移民配额虚位以待,这是自1862年以来,移民率最低的一年”(Bendersky,2000:332)。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对于吸纳犹太人入伍作战异常审慎,调查和审查机制极为繁复。因为,他们担心“苏联、纳粹、维希政权趁美国接收难民之机,向其安插情报人员。犹太移民或犹太难民在威逼利诱下,很有可能倒戈,成为间谍。”(Bendersky,2000:328)。美国海军情报局甚至认为“只要开价合理,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团体一定会出卖美国,他们是存心与纳粹勾结,迫害自己同胞的”(Bendersky,2000:331)。
在被反犹主义所操控的社会空间中,约瑟夫“被别人当一个可疑人物对待”,被“人用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贝娄,2002:143)。尽管已经在芝加哥生活了十八年,但是他仍旧迟迟不能归化入籍(naturalization)、参军入伍,就连在兑换支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他也因无法有效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接连碰壁。在偌大的芝加哥,反犹主义的膨胀严重挤压了他的生存空间。在一个“六面体的盒子”(贝娄,2002:71)似的租屋(rooming house)中,“自我在时间、历史的世界中不再是一个活跃的个体”(Frank,1978:278)。他的归属感、存在感、身份感被撼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份危机。
对于在欧洲饱受宗教歧视、种族迫害的犹太人而言,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啻“流着奶和蜜”的新迦南、一方全新的“应许之地”,甚至就是他们的“锡安”(Zion)。从19世纪末开始,归化的犹太移民打出了“在外是普通人”的口号(Alexander,2015:91),将美国性(Americanism)当作“外在的防护服”(Sarna,2019:198)。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随着美国犹太人口的急剧增加,“他们越来越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那些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过力的犹太人,在内心中生发出一种美国意识和身份认同(an American consciousness and identity)”(Sarna,2019:214)。二战全面爆发后,“犹太人更是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Sarna,2019:197),大量如约瑟夫一样的犹太移民踊跃报名参军,支援前线。“对于许多美国犹太人而言,他们之所以在1941年12月7日后,积极支持美国参战,其中既有其作为犹太人的良知,也饱含了其作为美国人的爱国热忱,他们油然而生了一种自己能够改变历史轨迹的感觉。”(Diner,2004:226)然而,反犹主义逆流无情地粉碎了犹太移民的“融入”之梦,吞噬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身份是人们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与构成这种主体性的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Gilroy,1997:301);是“一种被他人认同的、被解读的存在”(Sökefeld,2001:531);“确认个人身份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握人与空间的辩证关系”(李贵苍 等,2015:64)。在这个极端珍视自由、声称“不自由,毋宁死”的国家,约瑟夫们即便心甘情愿地让渡公民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自觉接受军队体制化的“精神监督”(贝娄,2002:156),也仍不足以表明忠心,为其悦纳。外部的敌意与排斥不断提醒约瑟夫们,他们不是美国人,之于这个国家,他们仍旧是局外人。因此,约瑟夫在历尽千辛万苦终被军队收编后,讽刺说:“我知道他(阿摩斯)要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说‘这是我要从军的弟弟’。从而以一个‘局内’的人而知名。”(贝娄,2002:153)
美国犹太移民一直在追问:“犹太人在美国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有种回家的感觉,可是美国是否也感到舒服、自在?”(Sarna,2019:215)可以说,贝娄以主人公约瑟夫的遭际对此做出了否定回答 。
2 退变的移民家庭空间
主人公约瑟夫辞职后,赋闲在家,等待入伍。他几乎终日困守于局促的租屋中,过着千篇一律、日复一日的生活,就算是偶尔外出,也不过是走亲访友。因此,《晃》所呈现的多是芝加哥犹太移民的家庭空间。空间的转换不仅缓解了约瑟夫所遭遇的时间停滞的危机,也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生产”出一层深意。对于这些约瑟夫细致描摹的家庭空间具象,我们不妨通过对文本外的“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文本内的“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来理解。
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中,“空间表征”属于强势集团的“构想空间”;“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包括“每一社会构成特有的生产、再生产的具体场所和空间体系”(1991:33),“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几乎囊括所有社会实践……常常体现为规约的空间行为,但不排除对规约的逾越”(赵莉华,2011:17);“表征空间”为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也是作家、艺术家们试图描绘的空间。在犹太教中,家庭被称作“小型圣殿”(little sanctuary)(Diamant et al.,2007:15),具有极为神圣的品格,起着承载犹太人民族身份的“空间表征”的作用,并进而规范着犹太人的“空间实践”,使其日常的居家生活统摄于这种特定的集体秩序之中,“从进入圣殿的一刻起,你便意识到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Diamant et al.,2007:14)。在“小型圣殿”中,洁净是第一要务,“每样东西都放在精心计划的地方……全都适得其所——整齐得如同女修道院的会客室”(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40),以表达对上帝的虔敬;家居摆设要体现犹太身份;能够“为家人及客人带来宁静、热情和美的幸福感受”(Diamant et al.,2007:15);“不以世俗成败论英雄,你从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为人”(Diamant et al.,2007:14)。然而,《晃》所表征出的犹太移民家庭则显示出对犹太教“空间表征”的背叛。在约瑟夫的岳父阿姆斯塔先生家,厨房一片狼藉,鸡血溅得到处都是,橘子汁里还漂着几根鸡毛。约瑟夫的朋友敏娜家充满异国情调:“时兴的瑞典式浅色家具,褐色的地毯,印制的夏加尔和格里斯的绘画,从壁炉上拖曳下来的蔓草,克哈塞水果鸡尾酒杯”(贝娄,2002:33),丝毫没有犹太印记。小说中,犹太移民在“空间实践”上也有违规范。比如,在约瑟夫哥哥阿摩斯家,金钱万能,出人头地高于一切,“贫穷与其说是丑恶,不如说是低贱”(贝娄,2002:45);就连约瑟夫尚未成年的侄女艾塔都嫌贫爱富,不把寒酸的叔叔放在眼里,甚至还敢对他出言不逊:“要饭的还想挑肥拣瘦!”(贝娄,2002:53)
那么,《晃》中的极为世俗化的、反犹太秩序的“挑战性‘表征空间’”(赵莉华,2011:17)和“空间实践”意味着什么呢?家是“人通过高超的手段创造出的东西,是人生的模拟”(贝娄,2002:15)。小说中“小型圣殿”的蜕变实际上再现、呼应了这样的现实:生存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美国犹太移民与其犹太性渐行渐远,逐步迷失了民族文化身份。那个“曾经塑造了其父辈(早期犹太移民)生活的共同体渐成追忆”(Raphael,2008:163)。
公元135年,由巴尔·科赫巴领导的犹太起义失败后,犹太人无法作为地缘共同体而存续,他们流离失所,进入了“大流散”时期,沦为典型的边际性客民。“对共同回忆的实践是集体归属感的基础,也是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出发点。”(Assmann,2006:50)在长期的散居生活中,犹太人流而不散,原因之一在于其对于犹太教的认同与持守,犹太教将其团结为极具辨识度的精神共同体。作为“犹太教的新中枢”(Diamant et al.,2007:15),家庭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空间,还与犹太人的宗教和礼仪生活密不可分,是犹太教“宏大叙事”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就是犹太人的根系、精神家园。“犹太教之所以在风雨之中绵延千载,部分归功于其对于家庭重要性与价值的强调。”(Kelley et al.,2018:707)在移居美国的初期,“家也是犹太移民身份的象征,要引导犹太儿童理解犹太性的内涵,无论这种犹太性所指的是一种正式的宗教信仰,抑或是无形却强烈的做犹太人很重要的感觉”(Diner,2004:306)。然而,随着犹太移民越来越卷入现代生活,他们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渐渐偏离了传统轨道,犹太文化身份对其日渐失去黏性,并成了他们极力想甩掉的负担。“现代性是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危机。现代国家、社会和经济不允许传统犹太生活继续下去。尤其在美国……”(Kaplan,2001:xii-xiii)。此外,美国周期性出现的反犹浪潮也迫使犹太移民不得不为求得自保而同化做美国人。在外部的政治高压下,“曾经恪守犹太教的移民,开始与其决裂、划清界限”(Sarna,2019:215)。《晃》借主人公约瑟夫之眼,展示了二战期间,美国犹太移民的日常家庭生活画面,以此揭示出犹太移民传统文化身份逐步被弱化的现实。“在家是犹太人”(Alexander,2015:91)的准则业已失效,“小型圣殿”成了其难以回还的一抹乡愁。
3 “晃来晃去的人”的共同体憧憬
孤独是主人公约瑟夫生活的底色:“我开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跃,我的行动便越迟钝。外界的喧嚣与狂乱和我的孤独以正比例增长。”(贝娄,2002:6)约瑟夫的孤独归根结底是主体身份迷失的“症候”。在美国国内反犹主义的打压下,他被排斥在国家这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之外,迟迟无法获得合法的美国公民身份。随着犹太传统文化的日渐疲软,它作为“一整套社会性的制度、习惯,失去了原有的对犹太族裔的影响力”(Sarna,2019:225),客观上难以为约瑟夫的身份建构提供强有力的支点。于是,约瑟夫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在身份上没有着落的“晃来晃去的人”。在如此窘境中,无根的他萌生出一种共同体想象,强烈憧憬着归属于某个“精神群体”(贝娄,2002:27)。
约瑟夫从画家朋友约翰·珀尔身上看到了艺术共同体的力量,因此,在他的共同体想象中,艺术共同体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有灾难,有谎言,有道德败坏,还有憎恨和洒落到每颗心灵的谬误及悲哀的屑粒,但他(约翰·珀尔)仍能洁身自好,我行我素。况且,这些运用想象力的工作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不单纯是个人的。通过这些行为,他跟人类最好的部分联系起来了。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就永远不会茕茕孑立,被弃置一旁。他拥有一个团体,而我只有这个六面体的盒子。善不是来自真空,而是从跟人交往中得来的,由爱伴随着的。”(贝娄,2002:71)所谓共同体,“并非指地理意义上的界限或疆域,而是一种乌托邦形式,是人们所寻求的以价值趋同为基础的共享家园和精神归属”(Rink,2008:207);共同体成员由此产生出“一种集体归属感、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或向心力。尽管这些成员或许未曾谋面,但他们怀有对共同体的共同想象,能够感觉到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员”(Anderson,2004:6-7)。无根的约瑟夫真切地希望自己能够像珀尔一样,心有所寄,在共同体中,与他人在精神上进行共振,并借助艺术想象力去挖掘生活中的善与爱,以此抵抗世间的丑恶堕落、孤独无助。贝娄曾说《晃》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Leader,2015:144)。小说中约瑟夫的这段内心独白又何尝不是犹太裔美国人贝娄踏上作家之路的“入职宣言”! 贝娄以此向那些认为他“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罗斯,2001:132)的哈佛白人精英们宣示着自己从事艺术创作的真正意图。
除了艺术共同体外,约瑟夫还借另一个自我——“替身精灵”之口,表达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火花:“他所向往的是一种‘精神群体’,或者是一群协同一致来制止怨恨、血流和残酷行为的人。杀人、破坏是信仰人生长久的人们所需求的。世界是残酷无情、危机四伏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活的确会变得像霍布斯所描写的那样‘龌龊、野蛮、短暂’。……如果另外一些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和恶势力做斗争,生活并不一定会那样糟糕。”(贝娄,2002:27)当时,二战狼烟四起,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即便“替身精灵”语焉不详,鉴于小说的日记体属性,上述引文中的“恶势力”在二战的语境下,自然可以被理解为法西斯主义、纳粹大屠杀。不难看出,“替身精灵”所构想的这个“精神群体”是超越种族、民族、国家界限的,它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下一步的行动是世界的行动”(贝娄,2002:155),共克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灾难。贝娄以此含蓄地驳斥了美国国内出现的将二战归结为犹太人自身问题的偏狭立场。贝娄的言外之意是,在这场战争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人都是犹太人”,世界人民命运与共,必须同仇敌忾。同时,贝娄也间接印证了自己参军的“更为‘严肃’的理由”:“我发现享受和平的红利而不为此做些什么,极为不妥。我意识到,作为艺术家,我完全有权要求免服兵役。这无可厚非。但是从良心上说,我不能这么做。而且你不认为这样很愚蠢吗?就像以必须有人活下来记录疫情为借口,申请免受其苦一样。不。”(Leader,2015:250-251)
身份是“一个建构、一个永远也没有完成的过程”(Hall, 1996:2),它“受到极端历史化的影响,总是处于变动和转化的过程中”(Hall, 1996:4)。处于身份危机中的约瑟夫通过对于共同体的憧憬,想象性地恢复了“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Gilroy,1997:301)。
4 结语
“贝娄认为作家的优势在于:忠于细节,用细节说话;透过细节看出真相,不论细节多么错综复杂。”(Leader,2015:172) 在小说《晃》中,贝娄通过对芝加哥社会空间以及犹太移民家庭空间的书写,再现了他们在反犹主义浪潮以及犹太教日渐式微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所遭受的身份危机,表达出“晃来晃去”的约瑟夫们对于共同体的强烈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