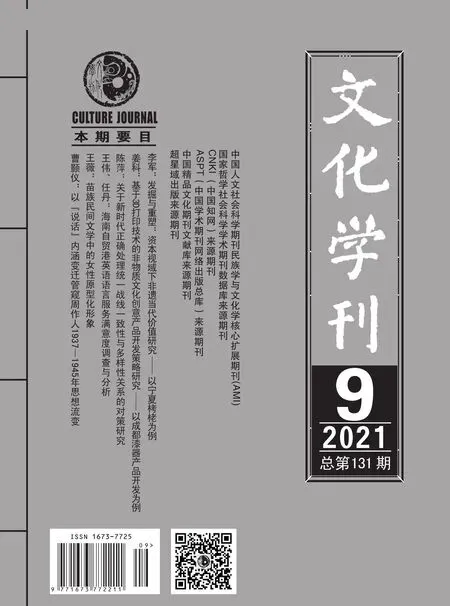以“说话”内涵变迁管窥周作人1937—1945年思想流变
曹颢仪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因政治局势不稳定且战局日益紧张,北平高校大规模南迁,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个人或家庭因素留在了北平,比如清华大学的俞平伯、刘文典、刘子高,北京师范大学的钱玄同、北京大学的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周作人等。这批知识分子大部分承担了保护校产的责任,也有一部分并未一直留在北平,比如刘文典等人后来就南下去了昆明。
周作人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北平。留守北平需面对诸多道德操守层面的问题,如何面对这种问题?周作人的答案并不新鲜。
20世纪20年代末,《雨丝》杂志被当局禁刊,这件事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他的很多言论与作品都发表在《雨丝》杂志上。当时,周作人不仅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于是便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躲避到一个日本朋友的家中,产生了“闭户读书”的思想,“宜趁现在不甚适宜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1]。”
如今留守北平面临着如同20年代末相似的境遇,周作人的选择便也与20年代末雷同,选择了“不说话”。
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说话”?“说话”的内涵又是什么?
若将“说话”定义为公开发表文章或者言论,未免有失偏颇,因1937年之后,周作人的文章曾多次公开发表,如《俞理初的诙谐》(1937年9月发表于《中国文艺》)、《谈关公》(1938年8月4日发表于《晨报·副刊》)、《关于范爱农》(1938年9月发表于《宇宙风》)等,便谈不上是“不说话”了。
实际上在沦陷初期,周作人又回到了30年代初的生活状态,常往广甸淘书购书,“一天十几个小时闲卧看书[2]”,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文章也多为文抄体,尤多见于《秉烛后谈》等集。因此,“不说话”并不等于不发表文章,而是指在特殊时期不对时事加以评点,同时也不谈及自己的私人事务,从而以“书斋”对抗外界。这也使得“书斋”成为兼具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场合。它的私密性在于将周作人个人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与他相关的私密事务与外界隔离,而公共性则在于它又是周作人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
一、“说话”即“声说”——从《玄同纪念》(1939)说起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先生去世,同年4月28日,周作人为他写下了纪念文章《最后的十七日——钱玄同先生纪念》。
自1939年1月17日至4月28日,历时百日周作人才为钱玄同写下纪念文章,以二人的交情来讲,在时间上实在显得有些不及时。周作人在挽联中写“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并自注曰:“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检、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类[3]。”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周作人的纪念文章何以发得如此晚,他自己说是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要写只好写长篇……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其二是“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发表也被认为是周作人开始“说话”的契机,他自己也称此文的发表“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
在《玄同纪念》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引用了《东山谈苑》中的一段内容,他说:“《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最后这句话也印证了上文周作人对于“不说话”标准的判断。这段故事在他作《玄同纪念》前已经被引用过,且在此文章发表之后也多次被引用。最早的一次是在1938年2月20日作《书<东山谈苑>后》,当时周作人尚未遭遇刺杀亦未下水,对“一说便俗”的说法还仅当作一句妙语,后来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又提及此语,说“其实最初我是主张沉默的……当时以为说多余的废话便是俗[4]”,这是他在特殊时期“不说话”的一种思想体现。
如前文所言,在不同的时期周作人对“说”的界定标准是不同的,同时外界对周作人“说话”标准的判断也是不同的。在《玄同纪念》(第二次引用)中,“说话”偏指“声说”,他终于开始提起与自己相关的事,书斋的私密性开始消解,但从本质上来说书斋的所谓“私密性”究竟是否存在还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因为实际上自北平沦陷后,这方书斋就处在了文化层面和政治层面的风口浪尖。
周氏的“落水”直观地与两件事有关。其一自然是发生在1939年元旦遇刺事件,其二就是钱玄同离世对他的影响。钱玄同在周氏落水前对其有堪称精神支柱的作用,而他的离世也对周作人的心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其著作《北京苦住庵记》中有所论述。木山根据周作人日记、文章,以及戴君仁(钱玄同的学生)的回忆推测周作人和钱玄同在1939年前已经就是否“出山”有过论争,而木山英雄认为二人之间的辩论使周作人思想中有关反抗名教的部分得到了凸显和加强。反抗名教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反抗中国传统的“名节”观念,钱玄同的“规戒”始终引导周作人接受这套名教框架的规训,周氏则在这个过程中越发产生了反抗的念头,并由此之后形成了一整套近乎顽强的自我辩解的逻辑架构。
这个说法得到了周氏行为的印证,他在1949年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就坦然承认了自己没有这套“名节”的观念,他认为这些名节上的印象都来自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的封建纲常伦理,本就应当抛弃,而一旦抛弃了这些东西,那么他的附逆也就不再是一种罪过。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可以印证一个说法,即周作人的所谓“落水”除了被迫的因素以外,也有一部分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这种自主性在本质上是抗争性的体现——当然,这种心理的产生也与周氏对时局判断有误相关(他认为日本的占领会像清军入关一样持久)。
二、“说话”即“辩解”——从《辩解》(1940)说起
在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后,周作人大部分时间依然还是在书斋中度过,并于1940年写下了《辩解》一文对自己的附逆行为进行解释。
他在文章开头时谈起对辩解一类文章的看法,说“记不起有一篇文章,能够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5]”,这印证了他的“不辩解主义”,说明他认为辩解本身是一件无意义且无效果的事。至于为何“辩解”无用,在周作人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看客冷漠。看客们认为辩解之人一经开口便是输了,其辩解自然也就成了闹剧,无法引起看客的丝毫同情,在此他引《水浒传》的一段情节为例证,林冲求董超饶命,董超却说“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这等求活命的话却被当作“闲话”,不可说不冷漠,周作人以此自比,自然知道求救无望,索性奉行起“不辩解主义”来了。
但在“不辩解主义”之外,周氏又实在进行了一些辩解性的行为,譬如他在元旦遇刺后不久即做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但思忍过事堪喜,回首冤亲一惘然。
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6]。
“忍过事堪喜”出自杜牧诗,“堪忍”为佛教用语,乃是梵文“婆娑”的音译,佛经中菩萨修行之地就叫做“堪忍地”,这里周作人实际上以修行者自比,将附逆期间面临的种种困境当成了“堪忍地”,“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思想脉络已经越发清晰了起来。在这种思想流变中,前一阶段的抗争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忍”的概念折射出周氏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了一种被动的态势,但他并没有完全地接受这种被动,而是依然试图对这种被动做出不一样的解释。他似乎依然存留着一些希望,认为只要以修行者的心态把附逆期间的困境当作历练,就可以辟出一条生路来。
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说服,这种自我说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伴随着周作人,这种自我说服为他的精神世界构筑了新的支撑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被捕后周作人依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汉奸。这种自我说服在形式上是有力而富有生机的,它为周作人提供了心态和精神上的新出路,但在客观上却也反映出他在心态和精神上的羸弱,这也是构成他悲剧性命运和精神困境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是,周作人“辩解”立足的基点是什么。日本学者木山英雄认为,周作人在沦陷时期坚持并用来支撑自身精神世界的信念,并非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实际上,这一观点正是周作人得以区别于其他“汉奸”的典型标志。
前文已经提及,周氏本身对于战争走向存在误判,他始终认为中国会在这场战争中落败。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类似于大后方的、行动上的抵抗是无意义的,也因此,他能始终面对大后方的口诛笔伐而岿然不动。在主观上否定了行动上的反抗之后,周作人实际上选择了一条“文化反抗”的道路。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指出,周作人的这种“文化反抗”有可能“是在仿效清末民族革命时代向他们教授国学的先生章炳麟的故伎:在反复批判传统儒学的‘致用’观念即学问政治化手段化的同时,却不惜把‘小学’这一最基本的文字训诂之学,作为激进的国粹民族主义的最高保障[7]”。
对“文化反抗”的解读可以是多向度的,其中一个典型的、也备受争议的例子是周氏的《中国的思想问题》。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的国民思想是儒家思想,而后提出“生存的道德”问题,即指出中国人民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以生存的道德为基点,周氏又恢复了一贯的悲观论,认为人民的这种求生意志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动乱。这篇文章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43年,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谷川彻三在南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就曾谈到周氏的这篇文章,他指出,中国思想问题即为生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安居乐业,那么所谓思想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谷川的这次引述和评论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1943年8月,日本文学报国会在东京召开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提出“扫荡反动老作家”的口号才从真正意义上将周氏和《中国的思想问题》推上风口浪尖。片冈铁兵尖锐地指出,周作人主张的生存道德实际上是对大东亚战争的一种消极抵抗,它为中国人的抵抗提供了传统道德层面的合法性支撑。传统的解读普遍认为片冈铁兵提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对抗战后期的周作人而言不但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个政治表演的道具,为他提供了某种自证清白、自我救赎的契机,乃至于“遇狼事件”中的沈启无也成为周作人反击片冈铁兵的一种政治牺牲品。本文不对这一观点做评述,而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假设:抛开对周氏自行制造“敌人之敌”的质疑,《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中国国民生存道德,是否具有构成其“文化反抗”内在机理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由奉行“不辩解主义”到生成一套自我说服的逻辑,再到充满自我矛盾性的“文化反抗”,周氏的“辩解”具有十分广大的意义内涵,且这种内涵在不同的时期也在发生着持续且微妙的变化。
三、“说话”即“理会”——从《文坛以外》(1944)说起
至1944年,周作人在政治上已经经历了起伏。1943年,以王辑唐为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全体辞职,其中就包括周作人,但后来旁人纷纷复职,只有周作人失去了官职,于他而言也不可谓不是政治上的一次挫败。
自1939年沾染政治以来,周作人的思想境况已经由单纯“文人学者”过渡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政治性的东西多了起来。譬如他在日记中写道:
1943年2月6日:下午,子鹤来,汪时璟来,述朱三爷(朱深)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手段仍乃冉公(王辑唐),思之良久不快[8]。
后得知朱深去世,又写道:“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
可见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受挫和遇狼事件的发生都对周作人的心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精神上的转变又相对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文坛以外》一文中。
周作人自言有“二不主义”,即“一不想做喽啰,二不想做头目”,他认为文化界中有一些奇怪之处,便是“有时不肯让你不怎么样”,譬如不肯让人不做喽啰,这在周作人的理解中尚且还算是合乎情理,真正令他困扰的是不肯让人不做头目,这个问题是1937年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所一直面对的问题,尽管他一直试图躲进书斋,却依然在北平文化界的真空中处在了核心地位,甚至逾越了文化的范畴而在政治上也被要求有所作为。
针对被迫成为“头目”的境况,周作人说:“假如彻底的退让,一个人完全离开了文化界,纯粹的经商或做官,那么这自然也就罢了,但是不容易这样办,结果便要招来种种的攻击。遇见过这种事情的人大约不很少,我也就是其一。平常应付的办法大概只是这两种,强者予以抵抗,弱者出于辩解。可是在我既不能强也不能弱,只好用第三种法子,即是不理会,这与二不主义都是道家的作风[9]。”
实际上,无论是所谓“强”的“抵抗”,还是所谓“弱”的“辩解”,周氏都有所尝试,只不过收效甚微罢了。于他而言,在1937—1939年间躲进书斋本就是一种抵抗,只是这番抵抗在其元旦遇刺之时受到了第一次剧烈的打击,而后生活的困窘又以“慢刀子”的方式瓦解着抵抗的决心,于是便就渐渐消弭了,这本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至于“辩解”,更是有许多,只是辩解之后也并无很大用处,非议仍然继续,周氏便也明白此路不通了,于是便只剩下一条“不理会”的路可走。
周作人认为“不理会”起码有两条好处,这些好处都是针对“抵抗”而言的。他将“抵抗”看作是 另一种“反攻”,“反攻”之所以不好,便在于“第一,人家攻击过来,你如慌忙应接,便显得攻击发生了效力,他们看了觉得高兴。其次,反攻时说许多话,未必句句有力,却都是对方的材料,可以断章取义或强辞夺理的拿去应用……只有不理会才可以没有这两种弊病。”这种“不理会”其实却是心态和精神上进一步退守的写照,周作人还是被逼到了墙角。
但被逼到墙角之后,有时反倒会多出一些坦然。譬如1945年12月6日,国民党军警至八道湾逮捕周氏时,他便从容道:“我是读书人,不用这样子。”这种从容是当抵抗与争取纷纷被证明无果之后,于无奈之中生发出来的。周氏在思想上也是如此,经历了“抵抗”与“辩解”,终于只能“不理会”,精神上的矛盾感每日愈发动荡,却又在另一个角度获得了某种平静。
纵观1937—1945年间周作人思想演变的脉络,可以观察到波动收缩的态势,即尽管其对应外界的方式夹杂有阶段性的反抗因素,但总体的态势还是渐趋退守,并在退守中体验痛苦的同时达成了某种平静。这种退守与平静从本质上说可以溯源至早期传统文化对周作人的思想影响。周氏本身对金圣叹的“蜉蝣世界之一逍遣法”有很强的认同感,他在总结自己南京求学时期的复合思想成分时还曾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到“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周氏对金圣叹思想的认同是可以预见的,因为金圣叹的思想本身就融合了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这与周作人思想谱系的底色是不谋而合的。
日本学者山田敬三在鲁迅研究中曾指出,存在主义在被命名之前就已经存在于各人的心理层面,因此他将鲁迅的人生哲学定义为“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这种说法后来也被学界接受。周作人研究领域的学者黄开发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周作人“最终选择的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生”,这种说法也解释了周作人“一说便俗”的思想根源。
周作人在南京时期阅读过大量传统的小说戏曲作品,也是在这一时期首先阅读了金圣叹点评的《西厢记》,周氏后来在《苦竹杂记》收录的《谈金圣叹》一文中说:“……我觉得他(指金圣叹)替东都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序》最好,此外《水浒》《西厢》卷头的大文向来有名。”这些阅读的文本包含了金圣叹鲜明的浮世消遣思想和虚无主义人生观,这与同样隶属于虚无主义哲学的存在主义有相当程度的共通之处。
金圣叹在自身的思想谱系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元素,其中重要的两个方面是隶属于道家的与世浮沉思想和同属于释道两家的超脱生死的观念。周作人曾在南京时期提出的“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显然呼应了金圣叹的“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在这里,周氏模糊了“生”“死”概念的边界,并以对生死和世界的虚无主义观念实现了对二者的某种超越。因为深刻意识到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个人之于外在世界的渺小,因而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对现世生活的重视又生发开来,正如他在《泽泻集》中收录的《死之默想》中所言:“或者舍不得人世的苦辛也足以叫人留恋这个尘世罢。”
从1937年到1945年,周作人的思想世界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由“不说话”转为“说话”是最重要的变动。这个转变的原因不应当仅仅被归为“元旦遇刺”事件的刺激,而应当从周氏的思想层面挖掘原因(比如反传统名教的思想、无意识存在主义思想等)。同时在1939年到1945这“说话”的六年期间,周作人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说话”的内涵不断变迁,经历了从“声说”“辩解”到“理会”的变化过程,这也是周作人原生的思想行为体系不断受到否定并不断在形式上消解的过程。这种种变化在使周氏陷入困境的同时,也使他收获了一种精神上的泰然与平静,而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来源于其本身的无意识存在主义思想及其对于世界的审美性观照。周氏在精神层面具有某种存在主义的特质,可这种对于存在主义的认同又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的存在主义背后实际上根植着他对于世界的、具有审美性的认识,这种审美性从他的“一说便俗”中就可以窥见端倪。“声说”“辩解”“理会”等行为都是周氏审美所抗拒的对象,现实的生存压力和政治压力可以让他暂时性地妥协,但在精神层面他却始终对辩解一类的行为怀有抗拒,“一说便俗”是审美的结果,也是他生存方式的体现。
其二,来源于周氏一贯的儒释道思想谱系。释家与道家思想无疑构成了周作人精神平静的底色,奇妙的是,儒家思想在周氏这里也实现了一种圆融。根据钱理群先生的研究,周氏一直认为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化合物”,他致力于将“酷儒”与“玄儒”从儒家思想中剥离出来,还原真正意义上的“纯儒”,并最终对“纯儒”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这种经过他本人改造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实际上成为了他进行“文化反抗”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成为了他打破僵局的一种可能性、为他突破精神困境提供了大方向,当这种尝试最终失败的时候,释家和道家思想又为他提供了一方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净土,三者的圆融使他实现了最终的平静。
其三,来源于传统文化,特别是金圣叹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于周氏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如传统名教)具有天然的反叛,另一方面又深受其影响,这一点与上文所说儒释道的思想谱系是一脉相承的。金圣叹的虚无主义思想与周氏的无意识存在主义达成了共鸣,在儒释道思想谱系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进而实现了对二者的超越,这种超越性是达成精神平静的又一重要力量。
总体而言,1937—1945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变化情况是细致而复杂的,由于本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具有特殊性,任何细微的外在条件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周氏思想的转折,但值得注意的是,引起这些转折的因素却不仅仅是时下所发生的具体的事件,而应当追溯到前期种种构成周氏知识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元素中去,如此才不至于将其思想解读得过于单一与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