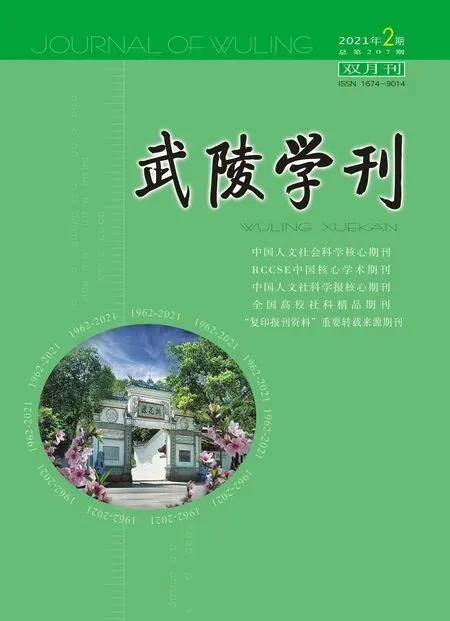侗族大歌与原始乐文化之源流考释
刘 崧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侗族是我国世居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黔、湘、桂三省(区)交界一带。据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侗族总人口约为288 万。侗族有自己的口头语言——侗语(俗称侗话),但没有自己的原生文字。侗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从语言渊源上看,侗族与壮族、水族关系密切,三者所处的地理区域多有接近或交叉。侗族大歌是侗族民间长久传承下来的多声部合唱歌的统称,参与人数从十数人到数百人不等。侗语称侗族大歌为“嘎老”(或“嘎玛”),“嘎”即歌的意思,“老”有大、众人及声音宏大之义。侗族大歌源远流长,据汉字文献记载,至迟在宋代时,侗族大歌即已存在①。
截至目前,关于侗族大歌起源的研究尚嫌薄弱。不少学者认为,侗族大歌源自汉代刘向《说苑》所载的《越人歌》,二者有渊源关系②。但《越人歌》不仅与侗族大歌近似,而且与壮、瑶等民族的民歌也近似,把《越人歌》视为侗族民歌的专有源头,似非公允。即便确认侗族大歌与《越人歌》存在关联,《越人歌》本身的起源仍是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侗族大歌来自侗族的耶歌,是由耶歌转化而形成的[1]。耶歌本是侗歌的一个种类。这个判断即便正确;也差不多等于同义反复。问题是,耶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究极而言,耶歌与大歌只是同一个文化生态的产物,用一个来说明另一个,好比用哥哥来说明弟弟,并不能满足理性寻根究底的渴望。我们应该追问的是这个文化生态本身是如何造就的。这又涉及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化。详细讨论文化的各种定义不是本文的任务。就本文的论述目标而言,我们只需要一个关于文化的启示性描述即可。有人类学家把文化比喻为“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2]5,颇有启发性。马克斯·韦伯认为人就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2]5。与此类似,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由人自己编织而成的意义之网”[2]5。显然,文化研究与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不同,它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本文讨论侗族大歌的起源,目的是给出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提供一种实证。
一、侗族族源与侗族大歌的文化渊源
探讨侗族大歌的起源,需要探讨侗族的族源,这是两个存在关联却又不能等同的问题。本文认同民族学界的一般结论,即侗族发源于百越的一支。《越人歌》与侗歌的相似恰可以说明这一点。不过壮族、水族、瑶族、布依族其支系也可以说发源于百越的一支,正如《越人歌》与这些民族的民歌也存在相似一样。因而,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发源”?为澄清问题,有必要区分一对概念:族源与文化渊源。有学者认为:“族源是就文化的整体面貌而言,是指某一人们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物质已与当今某一民族的文化整体面貌相同或相似。文化渊源则仅是就文化组成部分而言,具体地说,文化渊源不涉及该人民共同的文化整体面貌,而只是某些文化因子。”③就本文的论述目标而言,这一区分可资借用。族源是指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来源,而文化渊源则侧重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其因子)是如何发源的。就此而言,侗族的族源与侗族的文化渊源(如侗族大歌)具有不同的问题域,尽管二者存在一定的关联。当我们说侗族发源于百越的一支,实际上是在混淆这两层含义的意义上说的,并非严密的陈说方式。
基于族源与文化渊源的区分,我们可以大致描画一个轮廓性的线索,把侗族及其文化由以形成的历史分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汉藏民族的形成。这是汉藏系各类民族文化总渊源的出现。古汉藏民族的形成时间颇早,大概可以追溯到考古学所称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第二阶段是古百越民族的形成。古汉藏民族形成后,不断向周边扩散,逐步散布于中华大地的广大区域。大约在距今一万至一万五千年前左右,扩散到长江、珠江下游的古汉藏民族的一支与由南向北扩散而来的古南亚民族与古南岛民族相遇,在交流、互动和冲突中,形成古百越民族。第三阶段是古百越民族与古汉民族的融合。古汉民族形成后,由于使用畜力的农耕文明业已形成,开始向周边各民族的传统生境拓展,并与古百越民族发生融合[3]。这一融合同时伴随着族群的迁徙过程。侗族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④。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它列为第四阶段单独讨论。
第四阶段是侗族及侗族文化的形成时期。此间,有两个历史事件对侗族的形成甚关紧要,值得一提。其一是战国后期楚威王兴兵伐越。这次战争的结果是越人大败,越王被杀,越人由此而分散:或“服朝于楚”,或“滨于海上”,或逃进深山,或躲入溪洞[4]。侗族的祖先大概就是走的后两条路线,来到今天黔、湘、桂一带落脚定居。第二个重要事件是秦统一全国。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5]据考证,镡城在今天湖南省靖州县西南,所辖范围包括今天湖南省靖州、通道两县及贵州省黎平县东南区域,属沅江支脉渠水的源头。当时秦朝的五路大军分别沿赣江、湘江、沅江向南进伐。沿赣江南下的大军进展顺利,其中一军直达番禺(今广州),一军固守南野之界(今江西赣州),一军集结于余干之水(今江西大余)。不难推知,这些地区的南越人自秦代已经受到南下的中原文化影响。而沿湘江、沅江南下的秦国大军,进展不顺利。当他们进入今天湘南一线时,由于山高林密,遇到了西瓯、骆越人的顽强抵抗,“三年不解甲弛弩”。直到公元前214 年,秦始皇才最终征服漓江流域及南越地区,设立桂林、象、南海三郡,以统领百越之地[6]。而沿沅水南下的西线秦军,始终未能突破“镡城之领”,未能进入今天侗族的聚居之地——沅水上游和都柳江一带。这一历史结局,为古越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留存并焕发新机提供了可能。侗族与侗族大歌即缘此而生成⑤。
基于上述梳理,当我们说侗族发源于百越的一支,“发源”只是用以标识一个族群先民的来源之处,并不能说明这个族群之所以是这个族群的全部理由。侗族先民来自百越,但使侗族成其为侗族的文化元素却是在新的文化生境中形成的。当然,我们说侗族先民来自百越,这“来自”不可能是“空空如也”而来,而是携带着特定的文化信息而来;并且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融合与创生过程。这与文化作为“一幅地图”或“意义之网”的解释是完全相容的。据此,我们可以说侗族的先民是来自百越的一支,但我们不能说侗族的族源就是百越的一支,甚至也不能说侗族的文化就是百越的一支,而只能说侗族文化与百越文化有渊源关系。
侗族是古越先民来到新的文化生境后形成的;这一点可以从侗族的族名窥探一二。唐代以后的汉字文献多称侗族为“峒蛮”或“峒民”。唐元和六年(811),“黔州大水,坏城廓,观察使窦群发峒蛮治城,督促太急,于是辰、叙二州蛮张伯清等反,群讨之不能定。”(《唐书》)唐以后的汉字典籍把侗族记为“峒蛮”“峒丁”“洞人”“峝人”“峒家”等等[3]。这些称呼都有“峒”(“洞”“峝”)这个字眼。这正是黔、湘、桂交界一带非常显著的自然地理特征——南方喀斯特溶洞——的语言反映。直到今天,这一带仍有数以百计的村落以“洞”或“峒”来命名(比如侗族人口最多的黎平县有一个侗寨叫“岩洞”)。此外,侗族的自称也隐藏着特定的历史信息。侗族自称为“nyenc gaeml”,“nyenc”意思是人,“gaeml”在侗语中有掩藏、遮挡、藏匿之义。“nyenc gaeml”就是“躲藏之人”或“隐匿之人”[4]。可见,“洞”(“峒”)不仅是侗族聚居地的自然地理特征,也隐藏了侗族先民之所以来到此处的因由。
基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在特殊的自然与文化生境中形成的文化形态,其产生有特定的地缘生态条件(洞、峒)。同时,侗族大歌并非是由某一个人向壁虚构出来的,它与原始乐文化存在渊源关系,是原始乐文化在新的文化生境中发展出来的新型文化形态。原始乐文化是侗族大歌的发生学源头,地域文化生境则隐藏着侗族大歌的发生学机制(详见后文)。侗族大歌的形成与发展,既是特定文化生境催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反映,也是华夏民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不断融合创生的反映。
原始乐文化作为发生学源头如何影响了侗族大歌的形成呢?这里需要明确一个“中介”,即古越文化。如前所述,侗族先民来自百越,这“来自”并不是“空空如也”而来,而是携带着文化信息而来。这一文化信息就是古越文化所承袭下来的原始乐文化(详见后文)。原始乐文化通过影响古越文化,进而被侗族先民携带到如今侗族聚居的黔、湘、桂一带,并在新的文化生境中融入新元素而形成侗族大歌。
二、乐文化的源流及向百越地区的播迁
如前所述,文化可以比拟为“一幅地图”,一张“意义之网”。在地图上不可能存在孤立无缘的“孤岛”,也不可能存在孤立无缘的网结。把文化之“地图”整合起来的因素,或者把文化之“网”串接起来的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种力量:族群和地域。没有这两种力量,文化就成了断线风筝[7]。族群是文化的时间性传承因素,地域是文化的空间性建制因素。根据上文梳理,侗族是在古汉民族与古越民族的融合(迁徙)过程中形成的。侗族的形成不可能完全排除古汉文化因子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子就是原始乐文化作为原型对侗族大歌的型塑。为阐明此理,以下分为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其一,原始乐文化的源流以及向南播迁的大致线索。其二,原始乐文化与侗族大歌所共享的基本形态。第一点是历史因缘考察,第二点是文化生态考察。这种考察主要是解释性的,不是实证性的。
中国上古乐文化源远流长。对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⑥均可证实。乐文化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万年以前。据现存文献可知,尧舜禹时代是一个以乐文化为主导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事实是,帝舜家族的几代人都是乐文化的传承人,都是乐的精通者和重要乐器的发明者。舜本人发明了重要的管乐器——箫。《世本·作篇》记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舜的父亲瞽叟,虽常以愚顽的形象出现,却也是一位重要的乐器制作者,他曾在帝尧时代改作过上古时期非常重要的弦乐器——瑟。据《吕氏春秋·古乐》载,尧即位后,“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又《世本·作篇》载,瑟为传说中的庖牺氏所发明,后经黄帝改造:“庖牺氏作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此外,瞽叟还参与过尧乐《大章》的创作。《吕氏春秋·古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麇辂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可知《大章》之创作,质为主创者,瞽叟则改进乐器以奏之。舜的祖辈虞幕也是精通听风识乐的能手。《国语·郑语》载,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听风大概是乐产生的第一步,“听协风”与音律之发现有关。《吕氏春秋·音律》:“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庄子·齐物论》开篇讨论人籁、地籁、天籁,也是藉风而谈,殆非偶然。
舜家族是一个家世传承的音乐世系,这种家族氏的职业传承是上古时代的通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上古时期通过家族或氏族内部长期传承某种技艺,可以维持这种技艺处于很高的水平。《礼记·王制》:“凡执伎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伎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从舜本人及其父、远祖均通乐来看,有虞氏是原始社会末期及文明社会早期一个以乐为技能特长的著名族群[8]。舜的父亲在史书中被称为“瞽叟”,本身就是其职能的反映。瞽(盲人)因丧失视力,听觉能力转而特别发达,在乐的创制上多有贡献。先秦典籍有大量盲人从事音乐活动的记载。《国语·周语下》记载:“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韦昭注:“谓合中和声而度量之,以制乐者。”同书《周语上》云“瞽史教诲”,韦昭注:“瞽,乐师也。”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云:“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清人汪中认为“瞽”在唐虞时期其实是一种官称:“唐虞之际,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也。”[8]显然,舜父“瞽叟”实际上是以其官为称,其官职就是“瞽”(乐师)。汪中《瞽瞍说》认为:“瞽之掌乐,固世官而宿其业,若虞夏之后夔矣,不必其父子祖孙皆有废疾也。”[9]592-593
在今天看来,精通乐只是一种寻常的技艺;在古代则大为不同。乐是上古时代生活的重要支撑,建构着族群的日用生活,是凝聚族群、收摄人心的基本方式,发挥教育、政治、社会甚至宗教的一体化功能。乐在上古的重要性,不亚于电在今天的重要性。《尚书》记载,舜曾命夔作乐官,典乐以教化天下。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孔传云:“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抵庸孝友。”且不论“卿大夫”作为官职在舜时到底有没有,乐师掌管教事则可以定论。《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贵族子弟自幼学习乐舞,而教乐舞者,正是乐师。同书《文王世子》:“《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又同书《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青、大青、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可知乐官不仅负责教育,而且承担选举之责。同书《少仪》又记:“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这些记载,说明国之子弟受教于乐人的传统由来已久[9]592-593。所谓“正于乐人”,就是受教于乐师。上古时代,一切学问可以归于乐。俞正燮言:“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10]
上古之乐可以囊括“四教”:诗书礼乐,均可囊括于乐。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二“大司乐”条:“乐虽为六艺之一端,而此官掌治大学之政,其教以通陔三物(案“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不徒教乐也。”《礼记·王制》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四术”“四教”就是礼乐诗书,都是乐官的职责[10]。有学者认为,“儒”的渊源可能是承袭自上古时代的乐师。商周王朝中主管乐舞的官员与春秋时期的儒家都以诗书礼乐为教,这在文化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10]。这一推断显然并非无据。
在舜时,乐作为一切学问的总归宿,是建构整个族群生活的根本纽带,具有和谐伦理、沟通人天的作用。乐师在当时就是统合政治、教育、宗教等职能的职官。到春秋时期,孔子仍以礼乐作为根本的教学内容。《礼记·乐记》:“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本出一源,又相互建构。“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府总序》)若从发生学看,乐似比礼更为本源[11]。这从字源上可以寻出端倪。《说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聲。”裘锡圭先生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豐字应该分析为从壴从珏”,它“本是一种鼓的名称”[12]。林沄先生辨别豐、豊之异体,而礼之初字从豊,豊字则从珏从壴,“这是因为古代行礼时常用玉和鼓。孔子曾经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这至少反映古代礼仪活动正是以玉帛、钟鼓为代表物的。”[13]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诂林》认为:“豊当与乐有关。”[14]据字源可知,“礼”“乐”具有本源的同构关系。“礼”作为一种“礼节”“仪节”本身即包含在“乐”中。真实情形可能是,“礼”作为一种事态本然地包含在“乐”的活动中,但“礼”作为一种观念则未必与事态同步发生。“礼”作为一种观念,从与“乐”共享的事态中剥离(独立)出来,应当是后起之事。
总之,舜作为精通乐教的首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鉴于舜的地位及《舜典》所载,舜时的乐文化开始向周边播迁,并与南方百越文化发生融合,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逻辑。舜在位期间,曾亲自南巡。鉴于乐在当时的重要性,舜之南巡也就意味着乐文化随之南迁。舜在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湖南九嶷山。《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天湘南一带,已进入百越地区,与今天侗族聚集的地区接壤,也正是侗族先民的居住地之一。秦朝统一全国后设置南方三郡,乐文化南迁获得了政治性的支撑,汉乐文化与百越文化的互动融合遂达到历史上第一个高峰。这应当大致就是侗族与侗族文化形成的时期。
三、侗族大歌与原始乐文化的共享形态
我们把侗族大歌与原始乐文化建立起关联,除了上述关于民族与文化融合的历史梳理,还基于这样一个直觉判断,即侗族大歌与原始乐文化共享着“奏歌舞”(或曰“诗歌舞”)合一的文化形态。我们不能把这种共享形态理解为彼此独立发生的文化巧合,因为据上文梳理,这种“独立”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侗族大歌与古乐文化都是“文化地图”与“意义之网”上的一个环节,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分享着这张“文化地图”与“意义之网”的因缘整体性。
奏歌舞合一是中国古乐的基本形态。古乐与现代意义的“音乐”不是一回事。中国古乐一般称为乐舞,是一种融汇今天所谓音乐、诗歌、舞蹈乃至戏剧表演的萌芽形态于一体的综合文化行为⑦。奏歌舞合一的乐文化现象在古籍中不乏记载。《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有八子,是始为歌舞。”不独言“歌”或“舞”,而合称“歌舞”,二者实为一体。《吕氏春秋·古乐》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操牛尾投足”是舞,“歌八阕”是歌,也是歌舞不分。《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歌舞三者都是人类表情达意的方式。“在大多数的原始社会里并存着两种语言,一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15]歌是有声语言,舞是肢体语言,最原始的诗本身是通过歌舞来表达的。纯文字的诗是后起现象,它是在书写成为普遍的文化生活之后才出现的。《诗经》原本就是乐歌的总集,是诗歌舞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今天所见的一堆文字。《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朱光潜先生说:“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16]
奏歌舞合一是本源的文化现象。这里“本源”不仅是时间意义的本源,也是存在意义的本源。就后者而言,即便在今天,奏歌舞合一仍然是一种本源现象,广泛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生命冲动之中。
既然侗族大歌与原始乐文化都具有奏歌舞合一的形态,加之侗族与百越民族具有文化渊源关系,而百越民族与古汉民族曾发生长久的融合过程,因此,把侗族大歌与乐文化建立关联,并非突发奇想。这一过程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线索:原始乐文化→百越文化→侗族大歌。百越文化是乐文化与侗族大歌建立关联的“中介”。所谓“中介”并不是一个固定物,而是指一个漫长的文化融合与创生过程。侗族大歌一方面承袭了原始乐文化奏歌舞合一的文化原型,同时又融入了侗族生活环境的文化生境因素。本尼迪克特说:“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利用了所有潜在的人类意图和动机所形成的大弧形上的某个片断。”[17]218侗族大歌利用原始乐文化奏歌舞合一的原型,又融入了新的文化生境的一些元素;其间当然有所取舍,有所创造。“所有可能的人类行为都分布在其上的这个大弧形对于任何一个文化来说,都太大、太充满矛盾了,以至于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能利用的。首先需要的是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什么文化是可以理解的。”[17]219侗族大歌作出了什么“选择”呢?
侗族大歌可以分成若干歌种,比如:鼓楼大歌、叙事大歌、声音大歌、礼俗大歌、儿童大歌、戏曲大歌,等等[18]。但这一分类其实并不严谨,相互之间多有交叉。特别是礼俗大歌,几乎可以概括所有大歌的存在方式。礼俗大歌自然是在各种礼俗场合演唱的大歌,但哪种场合不是“礼俗”场合呢?比如拦路歌,是主客双方在村寨路口相互对唱。踩堂歌,是歌队在鼓楼坪或晒谷坪对唱,边歌边舞。酒礼歌是酒席上歌队向主客双方敬酒时演唱。大歌一般都会伴舞,是否伴舞,看场合是否允许。这些场合无一不是礼俗场合。上古礼乐同构,从侗族大歌可以窥见其遗韵。
无论什么种类,侗族大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形态,诸如复调性、多声部、拖长音、不和谐音、假嗓音,等等。从音乐类型看,侗族大歌可以归入复调音乐,但又与西方复调音乐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调式上,侗族乐歌的多声部和声以羽调式为主,多以领唱、合唱形式出现[7]。这种独特性可以从侗族所处的文化生境得到解释。侗族所处的生境有一个重要特征,即上文说到的“洞”(“峒”)。侗族在古籍中被称为“峒人”,这与侗族生活区域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溶洞、山洞有关。在学会建造木质房屋之前,这些“洞”是侗族先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居所。溶洞里面回声悠长,有多少原声就会发出多少回声、和声,而且溶洞越深、岔洞越多,回声、和声就越悠远绵长。这种天然的居住环境似可说明侗族大歌的复调性、拖长音、多声部等现象的生态缘起。侗族大歌大多从自然中取象,模仿各种鸟兽虫鸣而生成歌声,比如著名的《蝉之歌》就是模仿蝉鸣而成歌。文化的原始发生,说到底都是一个“人法地”的过程,与人在自然共生环境中的直觉创造有关。基于“人法地”而模仿自然、创生文化,在这方面侗族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民族。他们不仅基于峒中之声而创造了侗族大歌,还模仿杉树之形而创造了鼓楼艺术[19]。
四、余论:“礼失而求诸野”
本文大致勾勒了侗族大歌起源的可能线索,意在抛砖引玉,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以待学界贤达进而深入探究。因文献不足,本文之勾勒多为素描性质。文化现象,自有其精神脉络,并非一切均可诉诸可见“证据”,因而一定的推论是必要的。本文所论,建基于这一基本事实:文化现象既有族群的时间性传承因素,也有地域的空间性建制因素。两种因素同样制约着文化的承续和新生。一种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同时具备时间性传承因素与空间性建制因素。
准此以观,现代处境对各种文化生境造成了严重的疏离,各种地域文化正面临着危机与新生的可能。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力量,这一点即便在边远的民族地区也日益凸显。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化进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文化整合”。与此相随,现代科技及其所规定的生存方式、生活结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整合”各类族群文化,生活的同构化、同质化渐成大势所趋,少数族群的文化和语言正以超常的速度消失。值得关注的是,资本与科技的强势组合正在使文化的时间性传承因素失去传承力量,也正在使文化的空间性建制因素失去建制意义。手握一部手机,一个上海原住民与一个侗族原住民,在生存结构与交往逻辑上,并无实质区别。这是古代族群时代无法想象的现实。
《论语·先进》篇载孔子之言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表明,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野人文化深表认同。《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的另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在孔子看来,“野”才是礼乐的本源发生之处。上层社会的制礼作乐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对民间礼乐文化的采集和加工。如今,在资本化程度渐深的发达地区,原始乐文化日趋式微,而在边远的侗族地区(野),它仍以一种稍显变异的形态存在着。侗族大歌虽然不再是侗族人民的基本生活常态,不再作为一种组织机制参与建构侗民的日用生活,但它仍是原始乐文化的一块“活化石”。孔子“礼失而求诸野”的判断,对我们审视传统文化生态,不无借鉴意义。
注 释:
①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载:“辰、沅、靖州蛮有犵狑……。饮酒以鼻,一饮至数升,名钩藤酒,不知何物。醉则男女聚而踏歌。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辰、沅、靖州即今日湖南省西部的芷江、会同、靖州及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锦屏、天柱一带。犵狑为侗族自称“金”的双声音切,或说为仡佬族自称。“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与今日侗族大歌的形态符合。据此可推,侗族大歌至迟宋代已经存在。
②此方面研究可参见:林河著《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1985 年第4 期;张民著《试探〈越人歌〉与侗歌——兼证侗族族源》,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张民著《试探〈越人歌〉的诞生地兼证榜枻人与侗族的关系》,载《贵州民族研究》1986 年第4 期;朽木次郎著《侗族乎?壮族乎?——也谈〈越人歌〉的族属》,载《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4 期;邓敏文著《公正乎?科学乎?——与朽木次郎商榷》,载《贵州民族研究》1989 年第2 期;覃平著《也谈〈越人歌〉》,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 年第1 期。
③参见罗康隆著《论侗族的族源与文化渊源的关系》,载《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5 年第3、4 期。相关研究另可参见:汤宗悟著《考古发现与侗族族源》,载《贵州民族研究》1982 年第1 期;石若屏著《浅谈侗族的族源与迁徙》,载《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 期;洪寒松著《侗族族称、族源初探》,载《贵州民族研究》1985 年第3 期;邓敏文著《〈祖公上河〉的成因与侗族族源》,载《贵州民族研究》1987 年第4 期;吴忠军著《侗族源流考》,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 年第3 期。
④邓敏文先生考证指出,至晚在秦汉之际,已经有一支具有越民文化特征的古代居民在今黔、湘、桂边界地区活动。这些居民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今日侗族的祖先。参见邓敏文著《〈祖公上河〉的成因与侗族族源》,载《贵州民族研究》1987 年第4 期。
⑤由于文献资料不足,我们无法断定侗族大歌形成的确切时间。确定这样一个确切时间也不符合文化史的一般情形。另外,本文所说“侗族大歌”并非音乐学上严格界定的侗族大歌,而是作为一个弹性的文化概念来使用,在此意义上它可以包含侗族主要的奏歌舞形态。
⑥20 世纪80 年代,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发现20 余支鹤骨制成的骨笛,距今约有9 000 年至7 800 年之久,是“目前世界上出土的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出土个数最多、现在还能用以演奏的乐器实物”。经过专家测音,这些骨笛可以吹奏出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并且具备纯律、五度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因素。此外,在同一时期更早或更晚约1 000 多年的时间段内所制成的骨笛中,不论“型制、调高、音阶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每支骨笛上都发出C6 这样一个共同的音高”。(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第992、1012 页,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这说明早在距今上万年前,我国的乐器制作已具备相当水平。乐器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它与作为整体的乐文化密切相关。
⑦袁静芳认为:“古代原始乐舞乃是一种史、诗、歌、舞融为一体的混合艺术文化形式。”参见袁静芳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第65 页,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