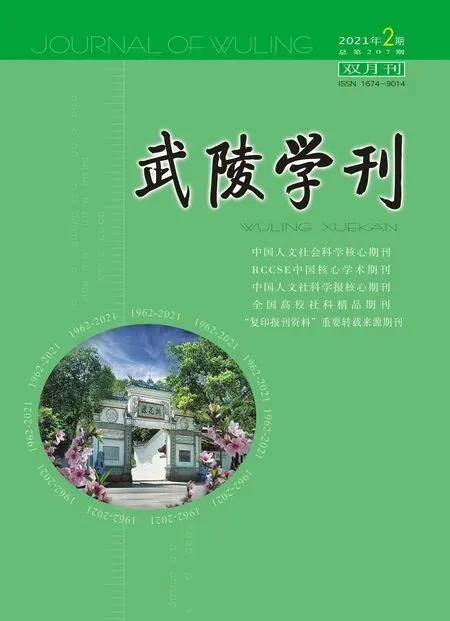功能对等视域下蒙学典籍翻译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
——以《三字经》英译为例
吴迪龙,宋玉露
(1.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2.黄河交通学院 基础部,河南 焦作 454002)
蒙学,国学之经典,泛指启蒙教育,特指童蒙读本,其中以《三字经》最具代表性,其所保存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对当今儿童乃至成人仍有很大教育和启迪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解文明冲突提供了“中国智慧”,因此《三字经》等蒙学典籍的对外译介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在蒙学典籍的英译进程中,关于“异化”与“归化”的取舍讨论从未停止,且纷争不断。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强调词汇、句法、文体和篇章四个方面的对等,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第一,信息传递;第二,原作精神及文体风格再现;第三,语言表达自然通畅,符合目的语的规范和习惯;第四,读者有类似反应。”[1]受这些原则和标准的启发,译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翻译需求和目的,灵活地将归化与异化相结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效果。
一、对立互补:基于功能对等的归化及异化辩证关系
在功能对等视角下,归化所实现的动态对等与异化实现的形式对等,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而归化和异化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但是互不排斥,它们对立互补。
(一)功能对等
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于1964 年提出的,他被誉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加上在美国圣经学会的长期供职,为他创立自己的一套翻译理论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其中“功能对等”成为他的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一理论是奈达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且在东西方翻译研究领域轰动一时。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翻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最贴切、自然的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风格而言。”[2]166形式对等要求忠实源语的词法规则及语法结构,动态对等则强调保留原文本的内容比保留其语法结构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为了确保内容对等,原文结构可能会被破坏。这种解释可能有些令人困惑,即内容与形式矛盾,这就是奈达为何用“功能”代替“动态”的原因之一。在实际翻译中,人们可能会坚持在翻译外交文件、商业文件等正式文件时采取形式对等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保留这些文件的语法结构就意味着准确,而在翻译小说等文学作品时,则经常呼吁动态对等,以确保可读性。形式对等关注形式和内容上的对等,这样的翻译往往涉及诗歌到诗歌,概念到概念的对应关系[2]159。功能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词汇对等是指在翻译词语时,要清楚该词在源语中的用法,然后找出目的语中对应的意思。由于英文中单复数及时态的表达与中文差别较大,因此句法对等比词汇对等更为复杂,译者不仅要知道目的语是否有这样的结构,还要知道它的使用频率。篇章对等则要求译者不仅要分析语言本身,还要注意该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和功能,脱离语境的翻译只会造成读者的认知困惑。文体对等是指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风格要无限接近,不同的语言风格蕴涵了不同的文化指涉,因此译者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且熟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
(二)归化与异化的定义及生成动因
归化和异化是1995 年由美国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于《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归化开始于17世纪的英国,指出这种消除差异的、透明的、流畅的翻译导致了译者的不可见性,造成他者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边缘地位,是一种文化自恋(cultural narcissism)。因此,为了弥补“归化”的罪恶,他主张用“异化”来解决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韦努蒂在该书中指出,归化是以目的语或目的语读者为服务对象,遵从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尽量使译文读起来熟悉亲切。归化要求译者尽量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尽可能用目的语母语者的口吻讲话。译者作为中间人,想要实现读者与源语作者的直接对话,就必须以母语的形式呈现译文。“采用归化方法就是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3]20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译文的可读性和亲切性,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译文并产生共鸣。它的优点是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高度再现源文本,缺点是忽略了语言层面上的特色和可能蕴含的文化内核。“异化是在翻译过程中使得读者向作者靠拢。”[3]20译文为了传递源语国家的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色,偏离目的语语言特点与文化气息。“异化翻译策略是源文化赢得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异化可以将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特征用另一种语言表现出来,为目的语文化注入全新内容,凸显源语文化的价值和地位。”[4]异化策略近年来受到很多译者的追捧,它能够满足他国读者对新鲜文字与文化的好奇,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不能超过读者的认知和接受能力,更不能打破语言规范为异化而异化。
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行为,归化和异化归根结底都是对文化的归化和异化处理,因此我们可以将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总结为文化差异。基于《三字经》的特色,影响归化和异化的动因可以从语言、诗学、意象和思维四个维度来谈。语言差异即英汉语言形式上的不同,例如英语重结构,汉语重语义;英文多被动,汉语多主动;英文多长句,汉语多短句;英语多采用前重心,汉语多采用后重心等等。归化与异化对文本的处理,最明显的就是语言层面的处理,为了保证译本的可读性,语言上的差异大多采用归化法。诗学差异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国典籍文章写作的技巧与规范,“诗学层面的归化或异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文体风格、叙事方式、篇章结构、段落组合、句子逻辑等。”[5]近代以来译者都喜欢采用归化策略翻译诗学作品,以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趣味,也有不少译者为了促进本国文化外传,偏好异化策略,以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借鉴。意象文化差异较容易理解,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图腾,意象蕴含着一个国家或民族自建立以来形成的文化渊源与审美趣味,如《三字经》中涉及的大量典故,短短三个字或六个字都可能蕴含特定的中国古代人物和历史事件,这就给译者带来了归化和异化的取舍问题,直接异化容易给读者带来困惑,直接归化又容易丧失原有的文化意蕴。中国人偏向于形象思维,而西方人则习惯逻辑或抽象思维;中国人强调整体性,偏好综合思维,追求“统一”和事物之间内部的联系,而西方人则重解析,关注细节和部分。中国古诗词强调赋、比、兴,赋和比都不难为西方人所理解,兴则不然,古代诗人睹物思情,即兴创作不在少数。《三字经》是体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典型著作之一,译者在翻译时也面临着对归化和异化的取舍问题。
(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关系
1.相互对立。从定义和作用来看,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打破目的语的常规,保留原文的异化性。它的作用是在源语中保留外文文化的异域性和价值,它比归化更忠实于源语的语言特征,保留了源语的韵味。异化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消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呈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异化是传播不同文化和促进文化交流的手段,有助于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其目标是发展一种自我重视的理论和实践,以抵抗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以促进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归化翻译的目的是顺应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因此作为两种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译法,文本翻译出来的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从此意义上讲,异化与归化是相互对立的。由此可见,归化与异化策略对翻译的形式与内容的侧重点刚好相反,对句子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对政治、文化、语言等问题也观点迥异,因此二者间的对立关系显而易见。
2.互为补充。任何一部译品的形成,都是“对源语文本的吸收与转换”[6]214,都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或国度的声音在我们面前演绎和解说,并等待我们与之对话,甚至碰撞出新的火花。尽管异化与归化实现的翻译效果大不相同,但是想要在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下,自然且准确地呈现源语信息,实现历史和文化的双重对话过程,就不能将归化和异化割裂开来,因为彻底的归化和彻底的异化都会使翻译陷入死角。翻译行为本质上是文化的交流而非单纯语言层面上的信息互换,因此掌握两种语言的文化比掌握语言本身更重要,单纯的归化只能传递信息,很难再现文化内涵,而单纯的异化容易造成读者认知和阅读困难,有时会丧失翻译的意义。世界上任何两种文化都有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将两种翻译方法相结合相统一,才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尤金·奈达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对动态对等的主张是:“动态对等的翻译是为了表达完全的自然……并试图将受体与他自己文化背景下相关的行为模式联系起来。”[3]159在意义和风格上都贴近原作,是功能对等的主要含义,将异化与归化有机结合,便可实现这样的翻译效果。
二、 殊途同归:归化、异化策略在《三字经》两种英译本中的应用
本文选取翟理斯与王宝童的《三字经》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两位译者如何辩证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来实现译文在词汇、句法、篇章和文体层面与原文的功能对等的。
1. 词汇对等。《三字经》内容简短凝练,却蕴含大量典故和经典名人,因此一些文化负载词翻译起来较为棘手,稍有不慎就会给目的语读者带来困惑,甚至引发歧义。
(1)三纲者,君臣义。
翟译:The Three Bonds are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7]97
王译: The king guides the Court,The dad guides the son.[8]85
在例(1)中,翟理斯将“三纲”翻译成“The Three Bonds”,而王宝童则翻译成“Three Guides”。“bond”一词蕴含一种美好的关系,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牵绊与联系,是平级的。而王宝童的“guide”则暗示一种上下级的关系,仿佛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硬性要求,下级不可违背。王宝童的翻译十分符合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但却与现代(不论中西方)的社会习俗相悖。由此可见,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了译者对归化异化策略的选择。王宝童对古代中国制度比较了解,因此在翻译时尽量忠实原文所传达的传统中国伦理,而翟理斯则受西方的伦理影响较深,因此将君臣之间的关系平等化了。翟理斯在处理这类文化特色词时,以归化为主,在保证原文特色的同时,也丰富了英文的词汇。相比之下王宝童则更倾向于异化,尽量保留原文中的等级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6]214由此可见,文化是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不同的文化环境塑造了译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他们的翻译理念。出于对本国文化更为深刻的认识,王宝童的译文在词汇层面上更符合原文语境,因此在翻译带有政治色彩的特色词汇时,使用异化策略更容易实现词汇层面的功能对等。
(2)如囊萤,如映雪。
翟译: Then we have one who put fireflies in a bag, and again another who used the white glare from snow.[7]128
王译: The fire-flies' light, And heavy snow white.[8]106
在例(2)中,“囊萤”和“映雪”是中国典故,用以激励年轻人要勇于打破环境限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翟理斯直接将该典故解释成“将萤火虫装进袋子里”以及“利用雪的反光”,没有进一步解释此种做法的原因或目的,因此读者不一定能够理解该句的寓意和逻辑。王宝童的翻译则侧重韵律,韵式明显,句尾的“light”和“white”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在背景故事上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说明。受相同的翻译目的驱使,在处理跨文化交流中的意象差异时,两位译者都倾向于异化翻译,通过直述“囊萤”和“映雪”两种行为,实现了词汇最初层面的对等。尽管实现更深层次的词汇对等,需要译者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而且对于这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两种译文都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困惑,但是由于缺乏解释,读者会产生进一步了解故事背景的意愿,这便间接激发了英语读者主动了解中国典故以及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推动了中华国学经典的对外传播。
(3)香九龄,能温席。
翟译: Hsiang, at nine years of age,could warm(his parents')bed.[7]76
王译: That Xiang at nine, Could warm his father's bed.[8]64
(4)孝于亲,所当执。
翟译:Filial piety towards parents is that to which we should hold fast.[7]76
王译:‘A dutiful son!'So is everybody said.[8]64
在例(3)中,原文只用了“能温席”,并未提及为谁温席,因此翟理斯和王宝童均采用增译的方法解释了主人公黄香为谁而温席,便于读者理解故事的原委,由此可见在文化词汇层面,两位译者都倾向于归化翻译。而在例(4)中,对于“孝”字,翟理斯将其译成“filial piety towards parents”,适当地增加一些词语能够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句子的意思,而“孝”这一概念在中国确实也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与感恩之情;而王宝童则将“孝”译成“dutiful”,但是“dutiful”一词几乎可以形容所有的责任关系,因此这种译法没有向外国读者解释“孝”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理念,这也是王宝童追求异化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文本类型以及诗学差异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为了呈现《三字经》作为诗歌的韵律感及其精炼的文体风格,王宝童倾向于运用异化策略,保留原文的诗歌体裁,而翟理斯则更多地采用归化策略,将“孝”这一概念中隐含的顺从父母的含义也译了出来。因此对于一些典型的文化特色词,尽管异化策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读者的理解,但却可以间接促进两种语言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这也是韦努蒂提出异化策略的初衷。
2. 句法对等。在翻译句子时,译者应当了解目的语中是否存在与源语结构相同的句式,若存在对等句式则尽量不改变原句结构,若不存在则改变原有句式,以获得最佳翻译效果。
(5)周辙东,王纲坠。
翟译: When the Chous made tracks eastwards,the feudal bond was slackened.[7]102
王译: Since Zhou moved east, The kingdom was failing.[8]99
从句法层面看来,在例(5)中两位译者的翻译都严格遵循了原句的句法结构,采用顺译的方法,对原句进行了异化处理,没有改变原句的成分顺序以及句型。对于一些在英文中可以找到相同句式的诗句,两位译者都尽量选择重复源语句式,通过异化策略,最大程度地保留原句句法,从而实现句法层面的对等。源语中的某个词在译成目的语时词性有可能要发生改变,两位译者都在必要时选择改变词性、变换句式、更换成分位置,以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
(6)父子恩,夫妇从。
翟译: Affection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7]79
王译:Paternal love,and nuptial bliss.[8]69
(7)人之初,性本善。
翟译: 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7]7
王译: 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8]5
(8)幼不学,老何为。
翟译: If he does not learn while young, What will he be when old.[7]12
王译: When weary of studies, The kids are to rue, When they are old, What can they do?[8]10
在例(6)中,“恩”“从”在原句中本来是动词用法,两位译者在翻译时都选择将动词翻译成名词,符合英语的句法习惯。在例(7)中,翟理斯将原本作为名词的“性”译成了副词“在本性上(naturally)”,使该词在原文中的成分变成状语,以修饰“good”。翟理斯将主语改为了状语,更加符合英文的行文习惯。而王宝童则选择用词组“at heart”来表示人的天性。从例(8)两位译者的翻译可以看出英语中状语从句和中文句式结构明显不同。“幼不学,老何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到了老年则会一事无成。翟理斯采用逆译法,将“幼(while young)”和“老(when old)”置于句尾,充当时间状语。王宝童同样也用两个时间状语从句来体现原文的逻辑关系。以上例子中翟理斯和王宝童均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在无法保留原文句式时,通过改变句式,以符合目的语句法习惯的方式再现原文,实现了目的语表达的自然流畅和句法层面上的功能对等。
3.篇章对等。对上下文的理解准确与否也是衡量翻译质量的根本标准之一,只有熟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理解文字背后的文化含义,才能成就合格的翻译作品。
(9)子不学,断机杼。
翟译: And when her child would not learn,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7]56
王译: And seeing him lax, She stopped her labour.[8]43
(10)融四岁,能让梨。
翟译: Jung, at four years of age, could yield the(bigger)pears.[7]78
王译: And Rong, only four picked the smaller pear,To leave his elders, The lion's share.[8]67
在例(9)中,翟理斯将“断机杼”译为“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直接再现原句表达的场景,虽没有对原文进行加工,直接异化处理,但无论按东方还是西方的思维方式理解此句,都没什么差别,大意是一致的。翟理斯这样翻译,也是基于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王宝童则译成“stopped her labour”,采用归化的策略,将原句译成“停止工作”,直接表达在中国古代文化背景下,“断机杼”意味着什么。王宝童的译法更加便利英文读者理解原文,但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中国特色文化因素,导致不能在解释原文的教化意义的同时,反映中国古时候家庭纺织的场景。两位译者的译法都明晰地反映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原文的隐含意义。在例(10)中,翟理斯采用增译法在“pears”前面加了一个“bigger”,补充解释了孔融让梨中的“让”字,偏向异化。即使典故的名称中未解释“让”是让什么样的梨,但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翟理斯成功地译出了“让梨”的隐含意义;而王宝童则继续采用归化法,用英语中常用的“lion's share”来表示最大的一份。在中国人谦让含蓄而西方人直接张扬的思维差异影响下,两种译法所传达的谦让精神都不难为外国读者所理解。从篇章对等的角度来看,在充分了解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归化翻译采用目的语中与原文相一致的概念,异化翻译则直接复述原文内容或再现原文场景。
4.文体对等。翻译作品不同,语言特征也各异,译者只有熟练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风格,并能够灵活运用两种语言,才能最大程度地再现源语风格,让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拥有相近的阅读体验。
“译出比前人更好的译本”[9]是翟理斯重译《三字经》所秉持的信念。由于翟理斯的译文阅读者均为西方人,且对汉语文化知之甚少,所以翟理斯在翻译原文时,优先考虑目的语读者,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尊重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翻译的地道性,令译文读起来连贯流畅。王宝童的译本则更简洁明了,从文体对等的角度来看,与翟理斯相比,风格更偏诗歌,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11)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翟译: If jade is not polished, cannot become a thing of use. If a man does not learn, he cannot know his duty towards his neighbour.[7]34
王译: Unless being carved, the jade is nothing more, Unless well-taught, your mind is raw.[8]26
(12)曰仁义,礼智信。
翟译: We speak of charity of heart, and of duty towards one's neighbour, of propriety,of wisdom,and of truth.[7]128
王译: Be righteous, kind, Faithful,polite.Use your mind,Good Virtues quite.[8]109
(13)谢道韫,能吟咏。
翟译: Hsieh Tao-yun was able to compose verses.[7]159
王译: Xie, the poet could chant amid cheer.[8]138
在例(11)中,翟理斯的翻译仍然偏叙事风,采用顺译的方法;王宝童则还是偏向诗歌体裁,“more”与“raw”体现了诗歌韵律。王宝童尽量不改变原句的风格,选词也十分巧妙。而在翻译方法上两位译者均采用了两个条件状语从句以表现源文本的逻辑关系和说理风格。例(12)中,与原文短小精炼的三字一句相比,尽管翟理斯的译文篇幅略长,不算明快,但对句子进行归化处理后,读者容易理解。翟理斯的归化译法主要优点一是在于内容充足,自然流畅,二是在于并列平行句式气势十足,实现了文体对等,但是没有押韵,读者难以准确地领略到原文的韵律美。与翟理斯相比,王宝童偏好与原文同韵,他在多处翻译中采用头韵和尾韵的策略,使译本同原文一样具有韵律感。从“kind”“polite”等元音入手,押韵上实现了极大的对等,与原文的诗歌文体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王宝童也关注一些不多见的押韵现象,尽力为源语文本找到对等的翻译,如在例(13)中,“吟咏”这个词在中文中以相同的元音[i]开头,因此王宝童翻译成“chant amid cheer”,以同样的辅音[tʃh]开头。归化表现在直接说理,忽略意义上的过渡,异化则表现在选词不仅要与原文同韵,而且要纯正地道。由此可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策略在诗歌或古文翻译中更能保留原文的文体风格,实现文体上的功能对等。
结 语
归化和异化作为处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差异的两种翻译方法,它们不是非此即彼, 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翟理斯和王宝童的《三字经》两种英译本,发现归化和异化都能在目的语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受文本类型、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不同的译者在翻译策略选择中偏向不同。在翻译《三字经》时,若想实现在词汇、句法、篇章以及文体层面的功能对等,需将二者辩证运用,假若异化更好则取异化,归化更好则取归化,二者结合效果更佳则一主一辅。“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国“蒙学”走出去提供了极大的战略机遇,全球化发展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与相互交流,因此新时代的译者要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结合时代新要求,巧妙合理地运用归化与异化策略,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