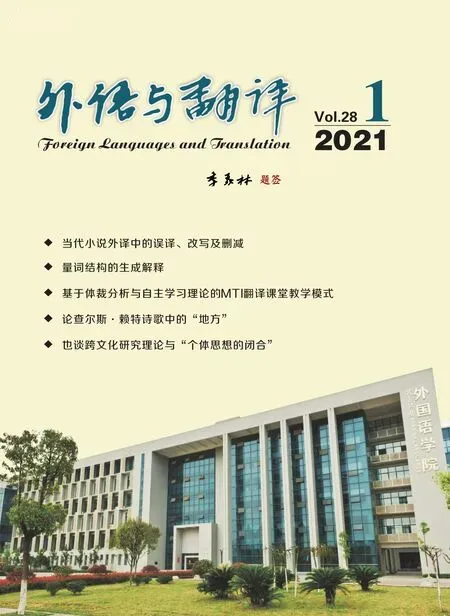《圣经》汉译过程父权叙事的女性主义诠释*
颜方明
秦 倩
暨南大学
【提 要】《圣经》因其父权叙事而受到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抨击,一些中国学者也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了《圣经》诠释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圣经》汉译这方面的研究却处于缺失状态。结合历史文化语境,本文以汉语《圣经·新约》中耶稣论“休妻(或离婚)”言论翻译的历时性变化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女性主义运动对《圣经》汉译的影响,指出女性主义价值观对翻译过程的介入是造成该变化的原因。
1.引言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波斯景教(即基督教分支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唐太宗时期进入中国并开始翻译《圣经》。因此,学界普遍认同《圣经》汉译活动始于唐朝。但严格意义上的《圣经》汉译“现存最早的是1700 年巴设的《新约》译本”(Wong 2017),之前的翻译只能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翻译行为,即部分内容的节译或藉《圣经》汉译之名的宗教著作。三百多年来《圣经》在中国经过了多次重译,译者包括了不同时期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和华人译者。以1919年为界,在此之前的译者群体大部分是教会委托的传教士。当代译者则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教会委托的华人译经团体,也有自发译经的信徒(如吕振中牧师)和纯粹出自兴趣的无神论者(如冯象)。学界对《圣经》汉译活动的历时性变化及其相关社会文化语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任东升(2007)从跨文化交流层面对《圣经》汉译的变化进行研究,傅敬民(2009)从社会学视角的文化资本和场域理论深入探讨这种历时性变化,颜方明(2015)从殖民语境切入分析不同时期的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但迄今为止,相关翻译研究很少将女性主义思潮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与《圣经》汉译有机地结合起来。廖七一(2002)和张景华(2004)等少数学者在论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时也仅仅提及与《圣经》相关的一些例子,并没有把《圣经》汉译实践作为研究对象。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与《圣经》文化及其女性主义诠释关联紧密,其早期标志可追溯到1895 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发表《女性圣经》(The Women’s Bible)一书。斯坦顿认为《圣经》是一部男权中心思想的著作,历史上妇女权利的匮乏根源在于“《圣经》对于妇女从属地位的宣扬,以及基督教会和教士的教导”(田海华2015)。随着女性主义和《圣经》诠释的发展,瓦莱丽·索茵·戈德斯坦(Valerie Sawing Goldstein)在《人类处境:一个女性的视角》(The Human’s Situation: A Feminine View)一文中明确指出当时的“神学教义主要是基于男性体验基础之上,有关人类处境的观点是站在男人立场出发的,因此对于女人的处境阐释不够”(Goldstein 1960)。后来,美国天主教会修女玛丽·戴利(Mary Daly)在《超越父神》(Beyond God The Father)一书中提出不应再称神为“父”,因为这种父权符号会使“压迫女性的社会机制看上去正当而且合适”(Daly 1973:13)。中国学者对这个视角的关注较晚,马月兰(2005)和梁工(2011)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西方《圣经》诠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对《圣经》汉译中国文化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没有涉及。为此,本文拟结合中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过程,以《圣经·新约》译文中有关“休妻(或离婚)”概念为具体考察对象,从不同时期译文变化尝试揭示女性主义社会思潮与《圣经》汉译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
2.“休妻”与《圣经》的父权叙事
“休妻”指“停止或终止某种关系和身份”的意思。而“妻”从属于动词“休”,处于被动的地位。“休”字本身就涵盖了“休妻”的意义,其本义指“停止;罢休(事情)”,“旧时指丈夫把妻子赶回娘家,断绝夫妻关系”(见《现代汉语词典》)。“休妻”概念的隐含行为主体是“丈夫”。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这个概念本身就有性别歧视内涵。“休妻”一词源于汉代《大戴礼记》所载的“七去”,即丈夫可以离弃妻子的七大理由:“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孔广森2013:246)。《唐律疏议》中称为“七出”,即“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长孙无忌等1983:267)。这两者大同小异,都是有关“休妻”的理由,因此在中国古代“休妻”也称为“去妻”或“出妻”。“七去”和“七出”的内容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歧视。但汉唐时期虽有“休妻”之实,却并无“休妻”之名。“休妻”作为正式书面概念的记载可追溯到宋朝的《东轩笔录》卷七中有关“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魏泰1983:77)的记载。“休妻”概念从汉唐的有实无名,至宋代的名副其实,反映出这种妇女地位低下的价值观模式在社会中呈现固化趋向,而且逐步渗透到社会语言中。这种父权社会模式沉淀在语言中的现象,“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表达,而且是一种政治化语言,一种文化定型”(杨永林2004:206)。在强调“三从四德”的父权社会,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在社会中处于男人的附属品地位。
这种类似的父权叙事同样也渗透在《圣经》中。《创世纪》所载夏娃是上帝从亚当身上取一根肋骨而造的故事本身就是典型的父权叙事,传递了“女人从属于男人”的社会价值观。《圣经》中记载在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被发现后,上帝对夏娃宣示“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更是典型的父权话语范式,而且是以宗教经典形式、经由上帝之口赋予的男性特权。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党派和宗教派别都宣扬这样一种源自《圣经》的价值理念,即“女人是造于男人之后,是藉男人身体制造出来的,是为男人而造的,女人比男人地位低并受男人支配”(Stanton 1993:7)。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对这种父权价值观予以了强烈的抨击。《圣经·新约》中与“休妻”译文有关的章节有四处,分别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以下简称马太5:31)和第十九章第九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至十二节和《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这些章节中与“休妻”概念对应的英文表达是“divorce his wife”, 与汉语中的“休妻”概念不同的是英文“divorce”的动作主体不分男女。“divorce”概念本身没有承载性别歧视的社会叙事功能,也不能反映出“休妻”概念的父权话语范式。在现存的多个《圣经》汉文译本中,有一些译本将“休妻”改成了“离婚”。这两个不同概念用于翻译《圣经》中的“divorce his wife”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看就是译者在父权叙事和中立叙事之间的抉择,反映了《圣经》在汉语世界传播过程跨文化的历时性诠释,但这个变化一直没有受到《圣经》汉译研究者的关注。这也是笔者专文探讨这个案例的直接原因。上述四处有关“休妻(或离婚)”的章节在内容上大同小异,都是耶稣就婚姻对信众的教导。因为“休妻(或离婚)”概念在《新约》中首先出现于马太5:31 中,所以下面的讨论焦点将放在不同时期译者对本节有关内容的翻译处理上。
3.《圣经》中“休妻”汉译的历史脉络
作为最早的比较忠实的《圣经》汉译本,传教士巴设在四川传教期间将《新约》绝大部分用文言译出,其翻译蓝本是拉丁语武加大译本。其后由马殊曼和马礼逊开启的《圣经》全译活动及后续的其他译者大都直接或间接受惠于此。所以,本文选择了从1700 年的巴设译本至当代不同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译本共10 本用于对比分析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决定性文化因素。这些译本按出版顺序列出如下:1700 年巴设(Bassett)译本,1822 年马殊曼(Marshman)译本,1823 年马礼逊(Morrison)译本,1839 年郭实腊(Gutzlaff)译本,1854年委办译本,1863 年裨治文(Bridgeman)、克陛存(Culbertson)译本,1919 年和合本,1949 年李山甫(G.Litvanyi)译本,1970 年吕振中译本,1984 年圣经新世界译本。
译文1:又有谓黜厥妻者必给之以休书。(1700 巴设译本)
译文2:昔有云凡休妻者宜給厥妻休書。(1822 马殊曼译本)
译文3:昔有云,凡休厥妻者则可交之以休书。(1823 马礼逊译本)
译文4:昔闻有言人出其妻可交休帖。(1839 郭实腊译本)
译文5:又言若人出其妻则以离书与之。(1854 委办譯本)
译文6:又言若人出其妻,当与之以休书。(1863 裨治文、克陛存译本)
译文7: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1919 和合本)
译文8:不许离婚“又有话说:‘凡休弃妻子的人,便应该给她休书’”。(1949 李山甫等人译本)
译文9:又有话说∶“无论谁离弃妻子,总要给她离婚书”。(1970 吕振中译本)
译文10:又有话说:“谁跟妻子离婚,就该给她离婚的文书。”(1984 圣经新世界译本)
比较上述不同时期的《圣经》汉译本可以看到,从1700 年巴设译本开始到1984 年的圣经新世界译本中与“divorce his wife”(希腊原文为) 对应的汉语译文分别为“黜妻”(1700),“休 妻”(1822、1823、1919、19491),“出 妻”(1839、1854、1863),和“离婚”(19702、1984)。有关“divorce his wife”的概念被译为“黜妻”是巴设的独创。巴设作为承上启下的《圣经》汉译传教士实际上在《圣经》汉译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从语义上不难理解,“黜”即废黜的意思,“黜妻”即妻子被免除与丈夫的关系。但“黜”主要用于罢免或免除官职和职务,“黜妻”这种创新式搭配则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所以从1822 年到1919 年间的《圣经》译本基本都使用“出妻”和“休妻”这两个在古代汉语中已经被中国社会广为接受的概念。即便是直接参考了巴设译本的马殊曼和马礼逊都没有沿用“黜妻”一说。从1949年李山甫等人的译本开始才陆续有译本在表达“休妻”概念的时候出现了“离婚”一词。1970 年的吕振中译本将与“divorce his wife”对应的译文改成“离弃妻子”,而本节最后的“a letter of divorce”则相应从之前的“休书”改成了“离婚书”。当代华人教会里使用的各类汉语《圣经》有一些译本存在“离婚”和“休妻”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如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中马太5:31前的小标题用“论离婚”,而在正文中又用“休妻”。下面不妨再结合西方的女性主义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分析造成这种历时性变化的翻译模式。
4.“休妻”到“离婚”——女性主义价值观的介入
“divorce his wife”对应的译文变化是不同时期社会价值观作用于翻译行为的结果。从上述不同时期马太5:31 的译文看,1949 年的汉译本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七个译本中巴设使用“黜妻”,马殊曼、马礼逊与和合本等三个译本使用“休妻”,郭实腊,委办译本和裨治文、克陛存等三个译本使用“出妻”。“出妻”和“休妻”是中国古代对丈夫离弃妻子的不同说法。相对而言,这两者中“休妻”一词在1919 年之前这个时间段更常用。“离婚”一词出现在《圣经》中较晚。1949 年出版的李山甫等四人合作的《新约》译本中最早出现“离婚”一词。而该译本也仅仅是在马太5:31 正文之前所加的小标题“不许离婚”中首先使用了“离婚”一词,而正文中仍然使用了“休妻”。1970年的吕振中译本在正文中用“离弃妻子”替代“休妻”,并用“离婚书”替代了“休书”。1984 年的圣经新世界译本则完全使用“离婚”来替代“休妻”,而且将“休书”改为“离婚的文书”。从时间顺序看,汉语《圣经》中对“休妻”的使用先于“离婚”。这一点与汉语文化中这两个词出现的先后秩序刚好相反。“离婚”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早于“休妻”。相对于“休妻”最早出现于宋朝典籍的时间点,“离婚”一词最早可见南北朝相关记载,如:南朝宋《世说新语》中有“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刘义庆2007:17)和“贾充前妇楚李丰女,丰被诛,离婚徙边”(同上:324)等两处;梁朝的《宋书》有“海盐公主先离婚,今应成服……”(沈约1974:399),“前废帝景和中,主谗之于废帝,藻坐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同上:1290),及“事上闻,有诏离婚”(同上:1390)等三处。从语言学视角分析,“离婚”一词并没有如“休妻”一样具有明显的父权烙印,属于无社会价值观附加性标记的中性词。“离婚”之所以没有普遍用于后来的封建社会是因为相对来说“休妻”更符合同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实,而“离婚”的弃用则是社会语言自然淘汰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与“休妻”并存的还有“和离”一词,即夫妻双方和气平等地终止婚姻关系,因此“休书”也可叫“离书”。但相对来说“休妻”和“休书”在父权社会中更多见。在巴设开始《圣经》汉译时,“休妻”是中国文化中有关夫妻关系终止的常见用法,而“离婚”则基本未见使用于该时期。
至二十世纪初叶,“离婚”一词在汉语中的复兴及其后在汉语《圣经》中的出现跟西方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冲击具有密切的关联。西方的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里程碑著作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一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792)。该时期前后西方女性对于男女平等地位的社会诉求拉开了序幕。至19 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大觉醒运动遍及美国,对西方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作用”(梁工2011)。1840 年一些基督教贵格教会女信徒首次召开了妇女大会并在1848 年的“赛尼卡瀑布”妇女大会上提出“男女生而平等”的宣言推动了女性主义《圣经》批评,进而直接促进了世俗社会的女权主义运动。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的《19 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女权观则主要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最早有关“女权”的言论始于1901 年4月,上海一位教会学校的学生吴孟班在《中外日报》刊出《拟上海女学会说》一文,并致信该报主编、维新人士汪康年,指出“中国之积弱由于女权之放失,女权之放失由于女学之式微。思之思之,痛之耻之!”(夏晓虹2007)清末时期中国女权主义运动的旗帜人物是秋瑾,她主张“女性要摆脱男性的压迫而独立”(须藤瑞代2005)。同时期另一女权主义代表何震,创立了“女子复权会”并创办《天义报》,他提出,“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首先必须打破男女之间的阶级”(同上)。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男女平等”思想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渐加深,“离婚”一词作为官方的法律用语出现于1911 年的《大清民法亲属篇》中,但随着清政府的崩溃而没有颁布实施。1915 年北洋军政府颁布了《民法亲属篇》正式将“离婚”概念写入了法律。而“休妻”这一具有明显父权主义特征的词汇则因社会结构和民众价值观的变革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离婚”一词实际上被时代赋予了新的社会学内涵,成为男女处于平等地位的一个标记性词汇。“离婚”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热词之一。“《申报》于1913 年1 月13 日报道,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者多’,北京、浙江、天津等地的离婚案也时见报章,而当时的离婚档案中,又以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居多”(郑琳2011)。“离婚”成为该时期的社会高频词以及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变化反映出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对中国传统父权价值观的冲击之巨。
从上述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到“离婚”一词在1949年之前从没有在汉语《圣经》中出现过。即便是在李山甫等人的译文中“离婚”也只出现在该节的小标题中。这种小标题模式的叙事策略最早出现于1874 年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圣经》相关内容而设置的阅读索引。因为原来的书籍以竖行方式排版,所以小标题最初是加在与经文相应章节的页眉上,这种叙事策略被和合本所采用并沿用至今。李山甫等人的译本也采用了这种小标题叙事策略并将其移到了正文中间,小标题的“离婚”和正文的“休妻”产生了社会叙事的矛盾阅读效果,反映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选词的犹豫。和合本及其当代修订版和其他一些译本在小标题和正文中并没有使用消解父权叙事色彩的“离婚”一词,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并不是译者们对社会价值观的变化缺乏敏锐的洞察力,而是因为他们追求对《圣经》原意的“忠实”以及社会新思想进入经典需要经历的时间差。毫无疑问,西方的女权主义从1901 年前后开始对中国社会(尤其是迅速接触新思想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笔者认为从这种初期的思想冲击到真正有机地融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需要时间的积淀。显然,“离婚”一词所反映的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发展到被社会各阶层广为接受的程度。和合本《新约》成书于1907 年,此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化模式并固化在社会语言中。1919 年和合本《新约》实质上是沿用1907 年版本,辛亥革命后社会巨大变革及其在语言文化中的反映没有表现在该译本中。当代《圣经》译文大多仍采用“休妻”一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翻译行为本身有“忠实”于源文本的语义与文化内涵的内在诉求。这一点在宗教文本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divorce his wife”在《圣经》中的语境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具有父权意识的“休妻”比“离婚”更接近原文。希腊语源文“”字面即“put away”的意思,与汉语中的“休”“去”“出”等动词的所指义相同。“”与其后的宾语“”构成的动宾词组与汉语的“休妻”概念比“离婚”更能建立微观语言语境和宏观文化语境上的对等关系。近现代历史上虽然多数译者采用英文译本作为《圣经》汉译的蓝本,但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参考了希腊语源语境。笔者认为这是汉语《圣经》在翻译过程中更多采用“休妻”来翻译“divorce his wife”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9 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开创了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1968 年玛丽·埃尔曼(Mary Ellman)的《想想妇女们》(Thinking about Women)和1969 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更加促成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大量涌现。从汉语《圣经》中“离婚”概念出现的时间节点与这些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高度吻合来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毫无疑问对彼时的《圣经》译者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其中吕振中全译本虽然是在1970 年出版,但其新约部分实际上早在1946 年就以《吕译新约初稿》的书名出版。初稿马太5:31 的译文是“无论谁休离他的妻子,当给他休书”。1952 年吕振中又对自己的译本进行了修改,出版了《新约新译修稿》,将相关译文改为“无论谁离弃他的妻子,要给他离婚书”。吕振中翻译的蓝本是牛津大学亚历山大·苏德尔(Alexander Souter)所编的希腊语《圣经》,译者本人笃信“经文本身亦蕴含神的存在”(颜方明2017),因此整体上采用直译的方法。与初版“休妻”相比,吕译《修改稿》使用“离弃”隐含了站在女性的立场对休妻行为的批判,具有明显的道德评价意义,这一过程译者的社会价值观主动介入了其翻译过程,并不是最“信”于原文的直译。可以看出,西方女性主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加深直接影响到《圣经》译者们选择更能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价值观构成和谐的“离婚”一词。但是,女性主义社会价值观在对《圣经》汉译话语传统形成挑战的同时,《圣经》构建的父权叙事认知框架及其原始语义也决定了一些译者更倾向于用“休妻”一词。这两种选择实质上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与《圣经》中传统的父权思想在翻译过程中动态博弈的反映。这种博弈长期的存在就是当代各类译本中“离婚”与“休妻”并行的原因。
4.结语
“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都是人类长期发展形成的,宗教语言也不例外”(傅敬民2009:3)。笔者认为,在《圣经》汉译的过程中,“divorce his wife”对应的汉语译文从“休妻”到“离婚”以及两者同时在译文中并立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圣经》的父权叙事模式在翻译中受到原文和译文社会文化语境的共同影响。1949 年之前的汉语《圣经》中大多采用了“休妻”这个具有典型旧社会父权思想的概念可以说是一个在多个层面上与希腊语原文更对等的汉语词。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在清末东渐的过程中“离婚”这个明显更中性的概念逐渐从中国传统文化废墟中被挖掘出来并在社会中替代了“休妻”一词。翻译作为受“社会因素调控的行为”(Hermans 1996),女性主义思潮及其对社会语言的影响在译者群体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一部分译者尝试用“离婚”这个更能代表现代社会男女平等价值观的概念来诠释“divorce his wife”就是这种影响的明证。
注释:
1 1949 年李山甫等人的译本虽然在马太5:31 小标题中用“离婚”一词,但在本节正文中使用“休弃妻子”,而且与“divorcement”对应的译文使用“休书”,因此实质上可以与“休妻”归为一类。但从小标题中使用“离婚”可以看出,李山甫等人注意到了“休妻”概念与新时期社会价值观存在的矛盾。
2 吕振中译本在马太5:31 中与“divorce his wife”对应的汉语译文是“离弃妻子”,与“divorcement”对应的译文是“离婚书”,而在马太19:8 中“divorce his wife”则使用了“离婚”一词。因而实质上可与“离婚”译文归为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