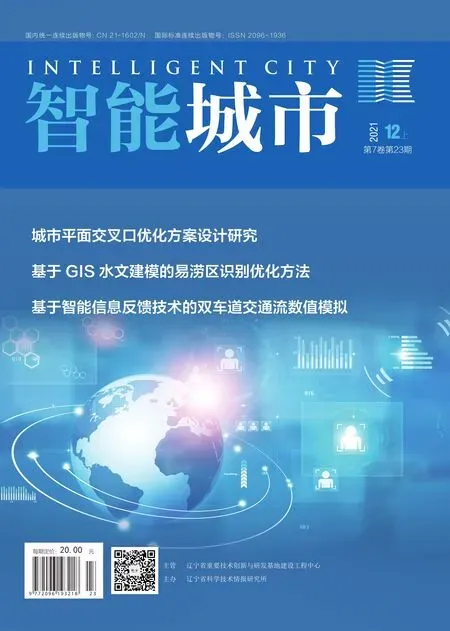“云”城市空间、符号与传播的互构
张琼心
(重庆移通学院,重庆 401520)
1 “云”城市:空间的再空间化
列斐伏尔眼中的“三元一体”空间本位论是将不同空间及其生成的样式统一到一种理论中,包括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事实上,空间本身的生产比空间的生产更应引人注意。伴随信息和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空间发展变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界限愈发模糊不清,且不断被重构,物理空间的限制已不再成为空间发展的关键要素,福柯提及的“监狱化社会”空间管制社会,在物理空间以及“云”空间中依旧发挥自动而匿名的权利作用。
城市生产空间作为一个由多种多样的城市事件构成资本场域,建立了一个不断自我生产和膨胀的社会复杂体系。城市空间与城市管理规划、城市经济相互交织、影响。
近年来,宅文化变得常态化,刺激了城市空间生产发展的速度。抖音短视频绘制的新空间在不断消解或转移社会焦虑情绪,且在一定限度上分解了平台的部分娱乐属性。随着用户参与平台不断拓展,从生产、围观到分享过程,均有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程度中加入“宅”文化行列,被深度挖掘的居家生活、广角呈现的居家场景、极致放大的居家方式使用户“生活圈”的景象迁移至“视频圈”,特色化空间内容私人生产成为公共领域生产的主力军。在各地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云课堂”“云招商”“云峰会”“云展览”等一系列“云”上活动衍生开来,城市文化的空间现实景象建构被迁移至虚拟空间中,实现在空间嵌入空间,“云”城市隔“空”而出,形成再空间化的“云”城市。
重庆率先敲开“云”城市的大门,学者们用各种理论解释“网红城市”,“云”城市传播研究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随着智慧城市兴起,城市空间从现实图景迁移至云上空间,完成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的再空间转换,城市再空间化与其他领域的互构也为其探索着新路径实施提供可能性和新的发展方向。传播与空间相互依存、相互构成,应最大化探索“云”城市空间发展可行的维度。
“云”城市的生产空间以文化内涵式发展为核心,形成以现代传播媒介方式编制成的对内与对外的城市空间生产传播网。在发展变化中,如何更深层重塑“云”城市发展的实质、内涵和规律,已经不局限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也是现阶段城市生产空间发展实践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2 “云”再现:空间城市的符号圈
马克·奥吉(Marc Auge)将城市空间区分为“场所性空间”(Place)与“非场所性空间”(Placelessness)。场所性空间不是简单的物理性空间,而是通过共同经历后的记忆符号交织重塑的物理环境,包括城市历史广场和博物馆等。非场所性空间指城市快速发展中形成的产物,包括商场、地铁站等带有现代符号性质的场所。我国城市空间中,非场所性空间数量较多,均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城市空间的符号大致可以分为城市建筑符号、城市自然环境符号、城市人文符号,对这些符号进行归类和运用,可以赋予其寓意性、价值性。没有一个符号机制能够孤立地在真空中起作用,符号的空间是其运行的必要条件。这个过程既是物质的文本符号,又是象征的视觉符号,也是寓意的阐释符号,在相互碰撞融合中形成循环,实现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圈。
“云”城市不同于传统的城市空间符号,以人类时间活动属性为基础,依托媒介衍生出“云”城市的符号圈,即文化圈、政府圈、环境圈、经济圈、人物圈,相互开放,相互连接,同时携带城市的地理、历史、民俗、建筑、艺术、人文等文化符号。
地方性符号场所被“推送”至大众面前,各个空间圈之间和不同规模场域的连接程度,构成了拟态环境实体化和虚拟化的符号生态圈,呈现城市的文化意象。城市内外的人依靠空间符号的读取,传递并参与城市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的生产建设中。
在“云”城市空间文化符号的形塑中,具有明显的象征符号特性。根据索绪尔的理论,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符号中显现的部分,是一种建构关系城市记忆成为符号价值的最终归宿。城市符号指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特征的、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并且让人引以为豪的标志性事物。例如重庆火锅、网红城市,上海外滩、东方明珠,北京故宫、长城等,在符号冗杂的网络空间中,云娱乐作为符号传输的重要出口,依托某种特定的、独立的又与城市相关联的表征符号,成为一个联结空间符号及其象征意蕴的结构性共情要素,在符号生产传播中达成城市印记的共识。
3 空间纹理:“云”城市的整合传播
3.1 “人与人与人”的实践:交织传播与认知印记
人们的相互作用会被感知到,是空间的填充。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生产。在融媒体时代,各类媒介的介入成为城市空间发展和品牌形象塑造的延伸口,城市特色、城市记忆等显性传播与城市形象和城市影响力等隐性传播,构建了物理空间内无法实现的新的符号地点和“云”城市新的拟态环境,沿着云空间形态形成的“纹理”不断进行整合传播。
媒介与空间必然相连,媒介内容的生产和阐释场所、文本投递的空间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跨越不同规模,交织在一起,成为“云”城市生产空间发展的路径之一。“云”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包括空间设计建构的现实人、虚拟空间中存在的人、被对象化的接收人,三者之间不断传递、模拟、转换中谋求“人-人-人”相统一的结合点。在算法推荐中搜索相关联的人,并与其产生对话,在“云”空间的内容生产中与传授双方达成共情,产生集体记忆。
在媒介技术中,城市生产伴随集体记忆的消解和重塑,不断警示“云”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记忆会在无意识中影响对某事的判断,大脑也可以无缝提取必要的信息进行调整,重新定位空间布局,会从大脑预存知识库中提取相似度高的事件相比较进行“合理猜测”,在其“意义吸收”的建构过程,记忆作为主体锁入大脑变为“印象”。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也不是某种神秘的思想,而是一个社会建构概念,是人们根据当下来对集体的过去进行理解与建构、回忆与再现。”共同话语环境中相似度的提高会引发共情力,在传播的实体记忆中感受自我的存在。社会性事件作为集体记忆的凝聚点,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中形成群体区分和群体认同。
风景知觉的意义是知觉得充实的,被知觉的对象在“于机体中”的方式上被意识,这种对象有其色、行等。认知共融在空间传播效果中占据绝对地位,且地域文化的差异依旧是“云”城市发展中的阻力,对传播的信息进行解码、译码,且同时不偏离“空间纹理”,成为整合传播的核心关键。
3.2 跨媒体叙事: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
空间的叙事化产生于人们对时间、事件和空间对场景的组织,是自然认知过程。从叙事中的多事件性空间进行解码、译码获取新的认知事件,延展个体对事件的识别程度,提升城市生产发展的空间。
媒介时代改变了现代人的习性,不断跳跃的注意力、不同空间中追求信息的流动,多媒体平台全方位的传播承载着受众的“期盼”,跨媒体叙事的出现,将日常生活推送到各种屏幕里,传播带来沉浸式感受的“云”娱乐。在虚拟中还原真实,在真实中建构虚拟,推动空间叙事的原生语境的消解和新的话语环境建立。
非虚构新闻话语因其叙事特征在公共性退场、消费性和文学性兴起、话语实践的参与性和对话性中日益凸显,最能符合新时代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经济格局的需要。媒介的渗透下,通过非虚构叙事的手法,“重访”和“再现”了“过去”,在虚实结合中完成故事的讲述。
3.3 场域“圈地”:碎片空间与领地扩张
“云”空间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通过媒介传播空间的领地扩张,形成空间撕裂,甚至同一空间内部的不同单元之间出现了各种形态的缝隙、边角和空挡,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碎片空间。碎片化的人类日常生活和精神思辨生产,在需求中演变为习惯,算法推荐下的碎片化信息宣示着空间的主权,不断探索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和人们拓展的接受度,“圈地”建构空间的元话语,以应对行业变化与机构需求。在位置确定、场景建构、领地扩张中完成“云”城市的生产常规路径。
重塑城市核心“角色”,宣传城市的文化形象,挖掘城市碎片文化,推出多元化旅游视频;传递城市共情印记,沉淀城市文化记忆。遵循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打造独特的城市品牌价值,追求形神合一的城市形象。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话语作为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共同的领地,任何东西与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相联系,就将形成空间、符号与传播三者之间的互构,其空间的生产、符号的维度、传播的物质,都是城市空间生产的探索的核心。在其发展中,如何赋予人们关于城市的清晰记忆和印象、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知名度和曝光率、依托何种平台和途径,依旧是每个城市永久探索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