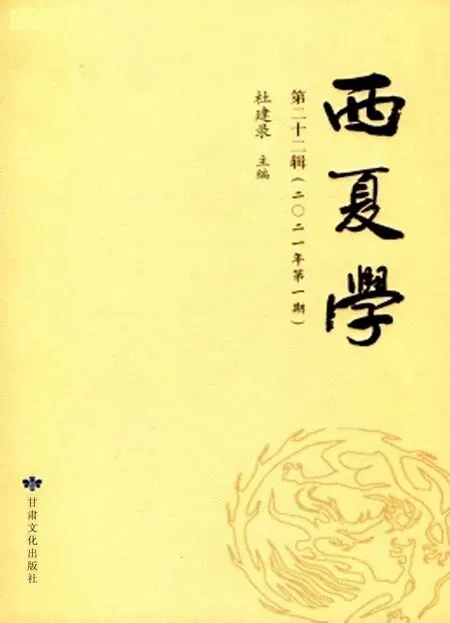辽朝佛教在西夏境内的流播与影响
程嘉静 杨富学
关于辽夏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书少有记载,学界熟知的资料仅有二则,其一为辽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1)[元]脱脱等:《辽史》卷二二道宗二,中华书局,1974 年,第267 页。从这一记载可知,西夏统治者曾将回鹘佛僧和金佛像、佛经一道作为贡品奉献辽朝。以佛像、佛经为贡品,是不足为怪的,但将回鹘的和尚当作贡品来奉献,以讨辽朝统治者的欢心,却是闻所未闻之举,诚辽国朝野对回鹘佛教推崇备至所致。(2)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447 页。其二为辽寿昌元年(1095)“十一月……夏国进贝多叶佛经。”(3)[元]脱脱等:《辽史》卷一○圣宗一,中华书局,1974 年,第108 页。舍此,不闻再有其他记载,唯黑水城、敦煌等地出土的文献文物和石窟艺术中含有一些相关信息,学界虽有关注,但大多未予详究,即使偶有探讨,也主要局限于文献方面。有鉴于此,特撰此文,以黑水城、敦煌石窟所见西夏文献文物与应县木塔、朝阳北塔等地发现的辽代实物进行比对,以探寻辽与西夏佛教历史文化关系的蛛丝马迹。
一、《契丹藏》在西夏境内的流播
辽朝佛教对西夏重要的影响之一即为辽代《契丹藏》在西夏的流传。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西夏李秉常在位时,接受了以宋《开宝藏》为底本的新印《契丹藏》,作为编校西夏佛经的补充材料。仁宗李仁孝之前,大藏经的主要部分已经陆续译成西夏文,但译文尚有不足,仁孝遂结合《开宝藏》和《契丹藏》对西夏文大藏经进行校勘。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所记即反映了此事:“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盛。”(1)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322 页。此处的“护城帝”即指西夏仁宗李仁孝,“南经”为《开宝藏》,“北经”当为辽代刻印的《契丹藏》。二者相较,《契丹藏》优于《开宝藏》,故而得到很广泛的传播,不惟西夏,甚至在更西的高昌回鹘王国,也都有《契丹藏》存在。20 世纪初,在高昌回鹘王国故都高昌故城出土的文献中即有《契丹藏》残片,庋藏于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编号为Ch.5555),内容为《增壹阿含经》卷三(图1)。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尾部余白部分有回鹘文题记,内容讲托里都统拜读了雕版的sang ir(a)ɣam(《增壹阿含》)。(2)[日]松井太:《契丹とウイグルの関係》,《アジア遊学》第160 号,2013 年,第65 页。

图1 吐鲁番出土契丹藏《増壹阿含经》残片
(原图采自:Kōgi Kudara-P.Zieme,Uigurische Āgama-Fragmente(1),Altorientalische Forshungen 10,1983,Taf.1)
印本残片的正面所书汉文佛经,尾书“增壹阿含经卷第三”等文字,内容是明确的。除此之外,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有一些回鹘语题铭,言及契丹版《大藏经》,庶几可证契丹版《大藏经》在西域的流通。
日本学者竺沙雅章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996—2000 年)为依据,甄别出属于《契丹藏》的文献残片数端:
TK274“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阿须伦品第六”;
Ф.123A“增一阿含经利养品第十三”;
Ф.204A“增一阿含经结禁品第四十六”;
TK273“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四”题签。
此外,诸如TK307“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下”、TK276“般若灯论释观圣谛品第二十四”、Ф317A“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五”也很有可能是辽刻《契丹藏》之残片。(1)[日]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 号,2003 年,第22—24 页。足见,如同高昌回鹘一样,在西夏国境内辽代《契丹藏》也是相当流行的。
辽与西夏各自为政,尽管常有敌对行为,但其间的佛教联系却不曾因战争而终止。关于辽与西夏佛教界之间的密切关系,学界已有论述,兹不复赘。(2)陈爱峰、杨富学:《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31—35 页;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年,第197—210 页;索罗宁:《辽与西夏之禅宗关系:以黑水城〈解行照心图〉为例》,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大象出版社,2012 年,第72—85 页。值得注意的是,据辽代石刻《法均大师遗行碑铭》载,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法均大师在燕京马鞍山开戒坛讲法,当时“来者如云,官莫可御。凡瘖聋伛,贪愎㤭顽,苟或求哀,无不蒙利。至有领邦父老,绝域羌浑,并越境冒刑,捐躯归命。”(3)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438 页。此处之“羌浑”主要指西夏统治下之部众。(4)古松崇志:《法均と燕京馬鞍山の菩薩戒壇——契丹(遼)におけtf大乘菩薩戒的流行》,《东洋史研究》第65 卷第3 号,2006 年,第21—22 页;姚义田译:《法均与燕京马鞍山的菩萨戒壇——大乘菩萨戒在契丹(辽)的流行》,《辽金历史与考古》第3 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258 页。自然包括西夏人,果若是,则西夏人越境到辽朝听戒说明辽朝佛教在西夏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种关系的存在,自然与《契丹藏》在西夏境内的流播息息相关。
二、辽朝佛教思想在西夏境内的流播与影响
辽朝佛教以华严学与密教最为盛行,同时也兼修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相关的多部佛教典籍均在黑水城得以发现,其中,尤以华严学为最,反映了辽朝佛典对西夏的影响。
(一)辽朝华严思想在西夏的传播与影响
黑水城出土编号TK88《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图2),竺沙章雅认为是辽朝大安十年(1094)单刻本。(5)[日]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 号,2003 年,第22 页。此时间节点刚好是辽代通理大师及其弟子善定等,在北京房山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续刻石经的时间,据大安九年所刻《菩萨善戒经》卷九题记载:

图2 俄藏黑水城TK88《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
添续成办石经功德主当寺通理大师赐紫沙门恒策、提点善慧大德沙门崇教、校勘沙门志妙……校勘沙门善定。(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442 页。
是见,TK88《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残片可能就是在这种活动的推动下刻印而成的本子,并且传播到西夏,而编号F14:W13《大方广佛花严经光明觉品第九》残片(图3)也应为辽代刻本。(2)[日]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 号,2003 年,第24 页。

图3 黑水城出土《八十华严》卷十三(F14:W13)
(原图采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 册)
(原图采自:《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图版57-1)
《俄藏黑水城文献》所收录编号TK252《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写本文献仅存《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部分,乃信徒参读《大方广佛华严经》过程中以原本《随函录》为参照,自行增订摘抄之产物。(1)赵阳:《黑水城出土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探微》,《吐鲁番学研究》2016 年第1 期,第36—37 页。辽朝《华严经》刻本在西夏的传播和西夏华严诸师密切关联,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法师辑录的《华严忏仪》,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遍)礼忏仪》,计有42 卷,收入明刻《嘉兴藏》,在末卷尾部记载了西夏华严诸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讲经律论重译诸经正趣净戒鲜卑真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经者救脱三藏鲁布智云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令观门增盛者真国妙觉寂照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传译开演自在 命口 咩海印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流传智辩无碍颇尊者觉国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西域东土依大方广佛华严经十种法行劝赞随喜一切法师;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兰山云岩慈恩寺流通忏法护国一行慧觉法师。(2)白滨:《元代西夏一行慧觉法师辑汉文〈华严忏仪〉补释》,《西夏学》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78 页。
其中,第四、五位分别是“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流传印造大疏钞者新圆真证帝师”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开演疏钞久远流传卧利华严国师”。借由“疏钞”二字,盖可观见二者对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书演义钞》在西夏的印造和讲读咸有所贡献。辽代鲜演大师《华严经玄谈决择记》是对澄观《华严经疏》的解释,因而也在西夏流布。俄藏黑水城出土编号为Инв. No.7211 的西夏文文献,克恰诺夫曾据尾题著录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注由义释补》,此编号的其中一叶实为辽代高僧鲜演大师所著之《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卷四的西夏文译本。(3)孙伯君:《鲜演大师〈华严经玄谈决择记〉的西夏文译本》,《西夏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27—34 页;孙伯君:《澄观“华严大疏钞”的西夏文译本》,《宁夏社会科学》2014 年第4 期,第95—99 页。
尤有进者,辽朝因受华严信仰影响而崇奉五台山,遂依宋境代州五台山之制而于立国之初在蔚州(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境内另建设五台山,清人厉鹗撰《辽史拾遗》卷十五引《山西通志》言:“金河十寺在蔚州东南八十里五台山下,河中碎石为金,故名金河寺,俱辽统和(983—1012)间所建。”有意思的是,西夏于1038年立国后,同样亦于贺兰山一带另建五台山,又称“北五台山”。(1)杨富学:《西夏五台山信仰斟议》,《西夏研究》2010 年第1 期,第14—22 页。这一现象纯属巧合还是依辽如法炮制,因缺乏证据,尚不得而知。
(二)西夏晚期显密圆通思想之辽朝溯源
西夏晚期流行显密圆通佛教思想,也与辽朝的华严思想存在着密切关联。密教经典《密咒圆因往生集》与《释摩诃衍论》较具代表性,前者为西夏桓宗天庆七年(1200)由西夏僧人智广、慧真辑录,金刚幢译定完成的一部诸经神验密咒的总集,在西夏广为流传。《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收录了《密咒圆因往生集》(TK271)残卷影印部分,刻本经折装,共10 折半,21 面,行10 字,上下双栏,有佚文,首缺。其辑录形式与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和辽代道敐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有很大相似性,其中《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的内容与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敐集《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次诵六字大明真言”的内容更为接近。《智炬如来心破地狱咒》根据《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下“供佛利生仪”内容辑录完成。《密咒圆因往生集》“教外之圆宗”之理论实则源于华严思想,与辽代华严之“华严一乘法界”为主的圆宗教义有共同的趋向。
与华严思想密切相关的《释摩诃衍论》在辽朝盛行,辽道宗耶律洪基“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2)法悟:《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卍续藏经》第45 册,No.772,第830C 页。。辽高僧法悟曾奉道宗之命,结合华严经为《释摩诃衍论》作注,从而在辽朝形成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 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2和TK80.2,原定名为《龙论》,即“龙树所造论”的简称。这两件实为同一残本,共计98 页。乃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二中的内容。除此之外,《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编号为F64:W1 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实则为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六,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3)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北方文物》2001 年第1 期,第95 页。可以肯定辽代佛教之华严思想及显密融合对西夏佛教之密教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三)辽朝禅宗对西夏的影响
辽朝的禅宗也对西夏产生了一定影响。黑水城出土文献TK254《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其内容与《禅源诸诠集都序》有相同之处,均为宗密作品。竺沙雅章根据版式及“明”“真”的避讳用法,确定TK254《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为辽道宗时期刊印。(4)[日]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 号,2003 年,第25 页。后者据大德七年(1303)贾汝舟“重刻禅源诠序”所述,刊刻者雪堂禅师曾从万寿寺方丈那里,得到辽清宁八年(1062)崇天皇太后主持印造,并颁行天下的定本。“崇天皇太后”之称呼,不见《辽史》本纪、传及表,据载辽兴宗之仁懿皇后,生道宗,于重熙二十三年(1054),被封为崇圣皇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被封为宗天皇太后,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皇太后崩,则此处之崇天皇太后应即此人,只是后世将皇后和皇太后的封号混乱所致错误。西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禅宗经典《六祖坛经》被译成西夏文。《俄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TK323 中的《往生净土偈》及TK132《慈觉禅师劝化集》中所收之《人生未悟歌》《未悟歌》皆出辽僧思孝之手。(1)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辽代高僧海山思孝著作考》,《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76—280 页。俄藏黑水城文献TK134《立志铭心戒》前部、A26《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全部与《立志铭心戒》后部、A6V《究竟一乘圆通心要》均为辽代通理大师恒策之作品。(2)冯国栋、李辉:《〈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理大师著作考》,《文献》2011 年第3 期,第162—169 页。而通理大师(1049—1099)是辽朝禅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究竟一乘圆通心要》与禅宗经典《少室六门》之《血脉论》《心经颂》同抄于编号为A6V 的卷子之上。
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写本研究所庋藏的一件西夏文佛教文献《镜》,从其禅宗内容分析,其或许为辽代道敐的《镜心录》的翻译本,(3)K.J.Solonin,Khitan Connection of Tangut Buddhism,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95 页。或可观见西夏僧修习禅宗的事实。西夏流行的对禅宗的理解不超越契丹法幢法师在《心镜录》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内所提供的“圆融”典范,是一种附属于华严宗的华严禅。(4)索罗宁:《禅宗在辽与西夏:以黑水城出土〈解行照心图〉和通理大师〈究竟一乘圆明心义〉为例》,怡学主编《辽金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2012 年,第297—298 页。彼时,辽和西夏禅学皆倡解行合一,如俄藏黑水城禅宗文献《解行照心图》所展示的思想即与辽朝道敐的修行论一致。(5)索罗宁:《辽与西夏之禅宗关系:以黑水城〈解行照心图〉为例》,黄夏年主编《辽金元佛教研究》,大象出版社,2012 年,第84—85 页。其禅学一致性跃然纸上。
(四)辽朝八塔信仰对西夏影响
辽朝八大灵塔信仰盛行,国内外学者已做过相关探讨。其对西夏也有影响,此前尚未引起关注。黑水城出土的《金刚座佛与五大塔》棉布唐卡(图4),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虽然其绘画风格有别于辽代八塔的密檐式,但其八塔名称与辽朝朝阳北塔一层塔身所刻基本一致,其中央大塔内为释迦牟尼佛及二菩萨,榜题为菩提树下成道场(笔者按:塔),其下方大塔左右各二个小塔,题记为:降服(笔者按:伏)外道名称塔,主尊右侧从上而下依次为:耆阇崛山大乘塔、菴罗林会维摩塔、佛从天下宝阶塔。主尊左侧从上而下分别为:尘园法轮初转塔、释迦如来生处塔、拘尸那城涅槃塔。(1)Mikhail Piotrovsky,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Ⅹ-XIIIth),Electa:Thyssen Bornemisze Foundation,1993,p.118,pl.6.

图4 黑水城出土金刚座佛与五大塔
辽代八大灵塔雕刻以朝阳北塔塔身一层为例,从塔身南面的“净饭王宫生处塔”开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净饭王宫生处塔、菩提树下成佛塔、鹿野园中法轮塔、给孤独园名称塔、曲女城边宝阶塔、耆阇崛山般若塔、庵罗卫林维摩塔及娑罗林中圆寂塔。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银塔上之八塔线描图也是是辽代八大灵塔的重要例证。(2)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71 页。(图5)

图5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银塔上之八塔线描
(原图采自:《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第71 页)观西夏八塔,和辽代八大灵塔图像在名称上何其似也,并且此种风格的八塔作品,科兹洛夫收藏有5 件,说明八塔信仰在西夏国时期的黑水城一带是非常流行的,与辽朝的八塔信仰存在着密切联系。而据《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卷末题记载:罗太后为西夏仁宗(1139—1193)三周年祭而祈福散施的77276 帧《八塔成道图》,其目的在于净除业障功德。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藏彩绘绢质八相塔图(图6),画面不全残存六塔,与此相类,佛塔侧有竖书榜题,书写塔名,仅有□□□涅槃塔、释□□□处塔可辨,为12 世纪末西夏八塔变。(3)雷润泽编:《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61 页,图版47。辽代八大灵塔流行早于西夏,如此足见辽朝八大灵塔的信仰对西夏的影响之深。

图6 宏佛塔天宫藏彩绘绢质八相塔图
(原图采自:《西夏佛塔》,图版47)
三、辽朝造像艺术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佛教艺术研究应置于10—13 世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研究,这对于研究辽夏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辽朝的佛画对西夏的影响是重要的一方面。黑水城出土西夏时代之《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纪经阿须伦品第六》(TK274)首题前后有格线,每行字17 个。(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365 页。其纸背书有“长阿含经卷第二十薄”,与《契丹藏》“薄”的帙号一致,因而竺沙雅章确定其为《契丹藏》本,其卷首附有“护法神王”扉画(图7),与山西应县木塔所出未完成的版画(图8)不无相近之处。(2)[日]竺沙雅章:《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汲古》第43 号,2003 年,第22 页;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19 页。应县木塔所出《妙法莲华经》卷一卷首画(图9)比较完整,其与TK274 相比,护法神王头饰相类,人物面部栩栩如生,两眼炯炯有神,有八字胡须,呈坐姿,一腿蹬地,一腿屈膝,腿部刻画几乎完全一致。推而论之,黑水城所出护法神王版画残片很可能属于辽国版画。(3)Shih-shan Susan Huang,Reassessing Printed Buddhist Frontispieces from Xi Xia,Zhejia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Art and Archaeology Vol.1,2014,pp.149-150.无独有偶,笔者发现俄藏敦煌文献Дx11472A.B.《佛说长阿含经》佛经版画残片(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221 页。、Дx11572 护法神王像以及Дx11576 护法神王像(图10)也与之相类,并且可以还原完整的护法神王像,画面左侧有武士装人物,头戴宝冠,右手横持剑。画面右侧,上部有一持宝棒的夜叉,下部是与右侧相类的武士形象,背景为祥云、山、水。因而辽朝的佛教版画题材同样影响到了敦煌地区。

图7 黑水城出土《长阿含经·阿须伦品》护法神王版画(TK274)

图8 应县木塔出土《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七卷首画

图9 应县木塔出土《妙法莲华经》卷一卷首画

图10 俄藏敦煌文献Дx11576护法神王版画
(原图采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 册)
(原图采自:《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9 页) (原图采自:《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第183 页)
山西应县木塔出土《契丹藏》之《中阿含经》卷三十六(图11)和《大法炬陀罗尼经》卷十三均为硬黄纸、卷轴装,二者卷首插图在构图方式上几无二致,图像正中为结智拳印的大日如来,其坐于大瓣的仰莲之上。左右为两大菩萨,其右侧为文殊,左侧为普贤,二大菩萨四周各围绕四大菩萨和四大天龙八部众。大日如来前方是一个供案,上置花卉及其他供物,供案两旁各一个仰头的举灯菩萨,供案前跪着五人,其中一人背对观者。据研究,此藏经为印刻于1003 年的《契丹藏》。(1)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 年第6 期,第2 页。其中八大菩萨的此种配置是辽朝构图的典型方式。(2)Laurence Sickman-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Puffin,1971,p.443.一个背对观者的僧人形象比较突出,此类图像较早发现于山西省博物院藏691 年雕刻的石碑上,碑正面底部涅槃佛陀右下侧有一身背对观者的跪姿僧人图像。(3)李琛妍:《幸存的涅槃:中国视觉文化中的佛陀之死》,香港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81—82 页。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背对观者的跪姿图像也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第12 窟、第61 窟华严经变壁画中,但这种作品在9、10 世纪的壁画中并不多见。西夏普贤菩萨行愿经TK142 版画(图12)根据榜题可知,主尊为“教主大毗卢遮那佛”,主尊右侧为文殊菩萨,被四大菩萨环绕,主尊左侧为普贤菩萨,同样在其周围配置四大菩萨,和辽朝时典型的构图方式一致。同时也有一个背对观者的人物,并且和敦煌莫高窟北区第B53 窟所发现的金代《华严经》残片(B53:1,图13)的构图方式极为相似,除了背对观者的人物,疑似主尊大日如来的宝冠、服饰、智拳印相似。而此种宝冠佛样式的大日如来和西夏《华严经》版画(TK243)中的构图方式相似,尤其主尊两侧仰头听法的胁侍菩萨神态特别相似,金代的这幅华严经版画时间大约在11 世纪末、12 世纪初,西夏和金共存了112 年,此间二者之间的影响从版画的构图看可见一斑,而其创作的粉本均是来源于辽朝,宋代的构图中也有华严经中背对观者的人物出现,表明这种版画方式在当时普遍存在。

图11 应县木塔出土《中阿含经》卷三十六

图12 西夏普贤菩萨行愿品TK142

图13 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金代华严经
(原图采自:《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 册) (原图采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 卷)
(原图采自:《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第73 页)
辽代的三珠火焰纹对西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火焰宝珠纹在辽墓壁画中比较流行,辽朝早期的宝山1 号辽墓壁画中就绘有多幅用云气托起的火焰宝珠图案,2 号墓石室门外正面还绘有四周以云气围绕的莲花宝珠火焰。(1)巫鸿、李清泉:《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 年,第166 页图5;第188 页图48。赤峰和库伦发现的晚期辽墓壁画中,宝珠火焰和莲花宝珠火焰仍然存在。宋金墓葬与辽代相比,宝珠火焰纹出现的次数明显较少。这和辽朝对摩羯的崇拜有一定关系。《杂宝藏经》中云:
此珠磨竭大鱼脑中出。鱼身长二十八万里,此珠名曰金刚坚也。有第一力耐,使一切被毒之人,见悉消灭,又见光触身,亦复消毒。第二力者,热病之人,见则除愈,光触其身,亦复得差。第三力者,人有无量百千怨家,捉此珠者,悉得亲善。(1)[北魏]吉迦夜、昙矅译《杂宝藏经》卷7,《大正藏》第4 册,No.203,页480c。
可见在辽人眼中宝珠有去病除怨之功能,随着辽朝摩羯图像的流行,从其脑中所出之宝珠也同样被膜拜。《大智度论》中亦云:
此宝珠名如意,无有定色,清澈轻妙,四天下物,皆悉照现。如意珠义,如先说。是宝常能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随意所欲,尽能与之,亦能除诸衰恼病苦等。(2)[印度]龙树造,[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59,《大正藏》第25 册,No.1509,页478a。
则宝珠不仅能光照万物,还能满足民众对衣食的需求。这些可能都和辽朝流行的摩尼宝珠有一定关系。西夏在与辽交往的过程中,宝珠火焰纹的艺术风格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会受其影响。西夏时期,多见莲花宝珠火焰及花砖,则辽代的火焰宝珠纹对西夏无疑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有人认为三珠火焰纹和阴阳珠火焰纹为西夏时期所独有,(3)岳键:《敦煌西夏石窟断代的新证据——三珠火焰纹和阴阳珠火焰纹》,《西夏学》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235—242 页。实不足取。
(原图采自:《大同华严寺及薄伽教藏殿建筑研究》,第190 页)
在佛教服饰上辽朝对西夏也产生了影响。如辽代石雕佛像中贴体裙裳以膝盖为中心,进而扩展到整个腿部的涡旋状衣纹就影响到西夏。其裙子涡纹式样可追溯到北魏时期,天水麦积山石窟第169 龛正壁交脚菩萨贴腿衣纹便是北魏时期这种衣纹的代表(图14)。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泥塑菩萨像膝盖部有此种衣纹(图15),或许是仿辽朝而制作(图16)。同时期的北宋也发现有此种纹样的裙裳,如麦积山石窟第43 窟主尊左、右侧胁侍腿部裙子皆是此种旋涡纹(图17),说明这种涡旋状衣褶也是辽、宋、西夏时期交互影响下形成的风格样式。

图14 麦积山石窟第169龛交脚菩萨(笔者拍摄)

图15 西夏绿城遗址出土泥塑菩萨残件

图16 薄伽教藏殿北次间主尊

图17 麦积山石窟第43窟主尊右侧胁侍(笔者拍摄)
辽、夏各自为政,但西夏人积极借鉴辽朝以华严思想为中心的佛教经典,包括大藏经及其他佛典,使西夏佛教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无论是显教还是密宗都表现出此种特点。同时在八塔信仰及佛教绘画、造像上又和辽朝佛教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从而使得辽朝与西夏在佛教思想及艺术上体现出相似性和紧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