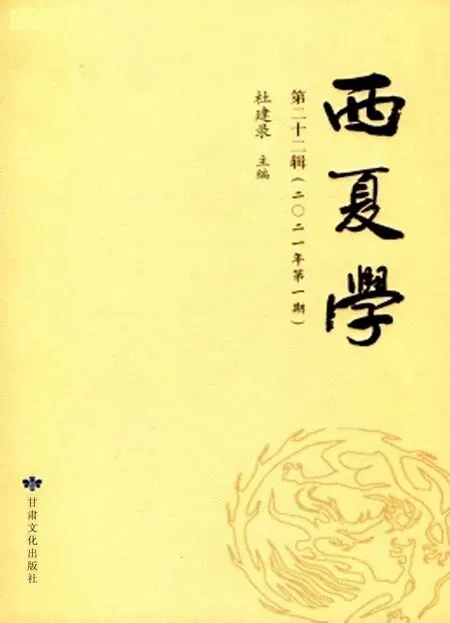西夏文篆书分类释名
赵生泉
篆书是西夏文的“存在”形式之一,可惜至今尚无写本形式发现,仅有碑铭、官印两种载体。(1)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29 页。数量方面,碑铭篆书存世有限,而自同治元年(1862)吴云《二百兰亭斋古铜印存》首次著录3 方西夏印章以来,西夏官印发现、著录日夥,20 余年前已有约150 多方。(2)白滨:《西夏官印、钱币、铜牌考》,载《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20 页。至于文字,则为西夏文篆书。因为载体的差别,碑铭篆书和官印篆书的形式特点有所不同。参照同期汉文篆书,前者可称为小篆,(3)[俄]捷连提耶夫一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82 页。后者可称九叠篆或叠篆。
一、西夏文小篆
西夏文小篆,目前共发现共3 种4 件。

图2

陵志文”(图3)。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敕感通塔之碑铭”夏汉对译例,“志文”之“文”应译为“铭”。(1)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3—5 页;韩小忙:《西夏王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69—70 页。考《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西夏五帝仁孝“谥曰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与碑铭正合,则此陵主为仁宗仁孝,此作可命名为《寿陵碑额》。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安市文物局各收藏一枚西夏文铜牌,俱圆形,有窍,由上、下两块铜板套合而成。国家博物馆所藏直径15 厘米,连窍18.2 厘米,一块正面阴刻双线四联忍冬纹,边缘近窍处有一镀金西夏文“敕”字(图4);下块正面阴刻双线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2)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73—74 页。西安市文物局所藏与国家博物馆宋藏形制相近,直径14.7 厘米,一块正面阴刻双线四联忍冬纹,边缘近窍处有一镀金西夏文“敕”字;下块正面阴刻双线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但字法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略异。(3)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75 页。

图4
这些作品中,《寿陵碑额》字数最多,但残缺太甚,《敕燃马牌》“敕”字迹清晰精美,可是仅有一字,所以讨论西夏文篆书,最合适的切入点其实是《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额。不过,此额只有八字,代表性有限,所以最恰当的途径是综合比较,特别是通过与楷体的比较,来探讨西夏文小篆的构形方法(表1)。

表1 西夏文小篆字形表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文小篆主要有省并笔画、拉长笔画、圆曲排叠等构形方法:
其一,拉长笔画。

此外,西夏陵M182 所谓“汉文篆书残碑”中,N42·020[P8:49](图5)、N42·020[P8:123]、N42·020[P8:132]、N42·020[P8:135]、N42·020[P8:M108H],也有可能是西夏文篆书,(1)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9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310—311 页。惟因过于残破,难以定论,姑存疑焉。

图5
二、西夏文九叠篆
所谓“九叠篆”,简称“叠篆”,主要指拉长笔画并刻意“叠曲”线条以求装饰、美化效果的一种工艺手法,是唐宋以来官印的重要构形方式和艺术特征。西夏文官印所用篆体在省并、拉长笔画的基础上,“叠曲”手段的应用极其突出,特别是“首领”印,虽然仅有区区二字,布局方式也只是简单的上下排列等分空间,但视觉效果却并不单一。之所以如此,显然离不开灵活多变的篆法与“叠曲”。

表2 西夏文楷、草、篆对比表

图1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至于所谓“倒体”印,即“由于铸印工人不懂西夏篆书,上下不分,故而倒铸”形成的西夏文官印,(1)李范文:《西夏官印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82 年第1 期,第75 页、图六。实际上是工匠把钮铭“上”字的方向因某种原因刻倒所致,本身绝非一种艺术手法。
又,《西夏官印汇考》10 号“首领”印(图13)右侧背款,李范文考为(乙亥六年)”,即天祐民安六年(1095),(2)罗福颐辑、李范文释文:《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12 页。其正面与内蒙古伊克昭盟文化工作站藏贞观甲申四年(1104)“首领”印(《中》M52·002,图14)(3)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20 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 年,第21 页。风格肖近,应属可信。与《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额相比,这两方印章更加繁复,但在100 多方官印中仍偏于简朴。更有意思的是,《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立于崇宗乾顺天祐民安五年(1094)正月,与《汇考》10 乙亥六年“首领”印仅差一年。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说明西夏文小篆、九叠篆出现的年代大致接近,都是西夏中期。当时正值乾顺之母梁太后专权后期,而“汉礼”的影响已逐渐扩大。在中原文化中,篆书不仅美观,富有装饰性,而且因其古老而具有一种“天生”的典范意义,经常被用于碑额、牌匾、诏敕的题写。西夏与中原文书往来颇多,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所以,西夏文篆书并非“自觉”的产物,而是受汉礼即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是模仿汉字篆书而来。

图13

图14
不能不说的是,作为目前所知年款最早的西夏官印,是《西夏官印汇考》11 号“首领”印(图15)制于贞观壬午二年(1102),比10 号印仅晚7 年,但风格已经明显趋于工细。倘若此印真实可靠,就说明西夏文九叠篆在天祐民安(1090—1097)之前确实有一个“准备”阶段。虽然这个准备阶段的详细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资料发现与发掘,但西夏文九叠篆与西夏文小篆一样,同样经历了由朴实到华美的发展历程,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图15
三、结语
与楷体原型相比,西夏文篆体字形尽管没有改变源自楷书的整体结构,但也确实改变了一些笔画、线条的组合关系,称之为楷体以外的一种“新”的书体是可行的。不过,西夏文小篆在《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阳作,在《敕燃马牌》作,右侧中间部件前者作侧倒之“∪”,后者作“工”。不仅如此,即使同在《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阳,意义相同,部件一致,仅左右颠倒的二字,分别作、,相同的部件,却有不同的篆体形式。凡此种种,均足以透露出西夏文“篆书化”的途径并不稳定,甚至有些过于随意。进一步引申,尽管在理论上所有西夏文都可以有篆书形式,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可能仅有极少数的字在用于碑额、印章、符牌时才被“篆书化”。也就是说,西夏文篆书是一种用于特定场合的,就特定文字内容进行装饰美化而形成的“新”书体。
关于西夏文篆书,还有一条极富韵味的材料。绍兴年间(1131—1162),(1)洪遵《泉志》第八页有绍兴十九年(1149)七月晦日洪遵自序,明万历刻《秘策汇函》本。鄱阳洪遵(1120—1174)著成《泉志》十五卷,在卷十一《外国品中》著录一枚“梵字钱”,其按语称:“右梵字钱。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2)[宋]洪遵:《泉志》卷一一·四下,明万历刻《秘策汇函》本。洪书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以致原图失落,至明万历癸卯(1603)毛晋、胡震亨据抄本刊刻时,才请钱塘徐象梅补入今图,(3)《泉志》末徐象梅《泉志跋》二上谓“缮本图篆失真,仅存形似”,明万历刻《秘策汇函》本。牛达生:《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中国钱币》1985 年第4 期,第13—15 页。即但未能定为西夏钱。此后直到清乾隆庚午(1750),梁诗正等奉敕修《钦定钱录》,历代泉谱皆袭徐氏之图。承此而下,刘青园据西夏碑将武威窖藏西夏钱币定为“西夏梵字钱”,(1)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一三“宋伪品·西夏”,转引自牛达生《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中国钱币》1985 年第4 期,第12 页。初尚龄更将刘说录入《吉金所见录》卷十三“宋伪品·西夏”。(2)牛达生:《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中国钱币》1985 年第4 期,第12 页。民国初,柯劭忞亦以“梵字”称西夏文。(3)柯劭忞:《戴锡章西夏纪序》亦称:“犹忆光绪辛巳(1881),予与福山王文敏公(懿荣)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属文敏购之,其人秘为鸿宝,不肯售。”转引自胡玉冰《清人著汉文西夏史籍亡佚者考略》,《宁夏社会科学》2001 年第2 期,第83 页。以上诸说,均以“梵字”指代西夏文。考《康熙字典》引《韵会》,释“梵”为“木得风貌”,即草木繁盛之态,用以形容笔画繁多,斜笔突出的西夏文楷书虽然可谓贴切,可是徐氏补刻之图尽管确实是西夏钱,其付梓年代却与原始著作年代相去逾400年。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推测明刊本《泉志》之图恐怕未必就是洪遵所见者。(4)牛达生:《西夏钱币中西夏文钱的发现与认识——兼论洪遵〈泉志〉的钱图问题》,《中国钱币》1985 年第4 期,第11 页。换句话说,把“梵字”作为西夏文的别称,其实是一个有来由的误会。至于所谓“梵字钱”得自“蕃”“梵”同音,(5)贺吉德:《中国藏西夏文献综述》十五《印章、符牌、钱币卷综述》,《西夏学》第2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78 页。就更是望文生义,大错特错了。
又,天津博物馆(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一西夏四字朱文印,5.5×5.5 厘米。1978 年,罗福颐、李范文释“有神圣位”,(6)罗福颐:《一方研究西夏历史的印章》,《光明日报》1978 年6 月9 日④。但1982 年出版的《西夏官印汇考》用其图(《汇考》95,图16)而未用此说,而1997 年出版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则仍沿用之。1988 年,史金波等将其翻转180°后,据背款“ (正首领嚩毘屈国成)”定为汉文阳刻《正首领印》(《西夏文物》183,图17),并推测印文可能是“□工之印”。(7)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183、305 页。1993 年,陈炳应比定为西夏文“ ”,汉语音译“成则为勒”,具体涵义不明,认为可能是蕃官名号,字法与西夏文“大安宝钱”类似,可能是在大安七年到九年秉常被囚禁期间,(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元丰四年四月壬申:先是,权鄜延路马军副都总管兼第一将种谔奏:“近谍报:西夏国母屡劝秉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其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之。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所激怒,欲谋杀叔母与梁相公,其言颇漏露。梁相公与叔母共谋,作燕会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于后园被害,其妻子及从者近百人皆实时继遭屠戮。臣窃谓贼杀君长,国人莫不嫌恶,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乱之变,诚天亡之时也。宜乘此时大兴王师,以问其罪。仍愿陛下假臣鄜延九将汉、蕃人马之外,量益正兵,选陛下左右亲信中贵人为监军同行,文武将佐,许臣自辟置,止裹十数日之粮,卷甲以趋,乘其君长未定,仓猝之间,大兵直捣兴、灵,覆其巢穴,则河南、河北可以传檄而定。”中华书局,2004 年,第7566 页。[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载元丰“四年四月,有李将军清者,本秦人,说秉常以河南地归宋,国母知之,遂诛清而夺秉常政”,中华书局,1985 年,第14010 页。西夏高层分裂,“在这两年左右的分裂对峙中,一方继续使用原来的官印、钱币;另一方则改造文字,新铸印、钱,以示区别,因而产生这种特殊的书体”。(9)陈炳应:《几件特殊的西夏文物试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82—86 页、92 页附录二。也就是说,它是“西夏早期官印印文”。若无误,当可藉以探讨西夏文篆书的发展历程。

图16

图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