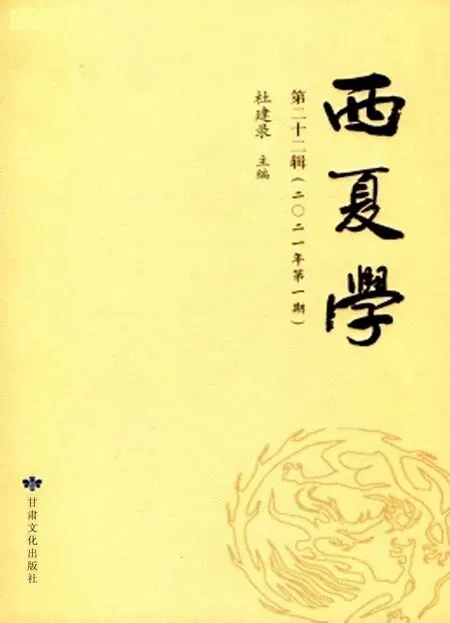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图像研究
易玲萍
俄藏黑水城《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图1)该画45×20.3 厘米,纸本彩画,现被界定于公元12 世纪至13 世纪期间的作品,图像大致描绘了皇帝与侍从于户外的场景性描写,其中还有很多生活用品、动物、以及钱财珠宝等陪衬物。(1)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96 页。
近年来,随着西夏文物的不断发现,关于西夏文化的各类研究正在逐渐深化,在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著中多有《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的论述,此图还较多地被作为其他论点的佐证材料。如:冬宫博物馆东方部西夏馆主任萨玛秀克博士在《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一书中对《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画面中每个物象进行了释文描述;陈育宁、汤晓芳在《西夏艺术史》著作中,主要提及了《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两位人物的服饰;王胜泽在《西夏佛教图像中的皇权意识》中举例《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皇帝着白衣形象,为说明西夏有崇尚白色的民族特征;任怀晟、魏亚丽发表的《图像中的西夏皇帝服饰》一文,论述了《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两位人物的着装样式、服饰纹样;此外,汤晓芳文章《对敦煌409 窟壁画人物“回鹘国王”的质疑》对《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皇帝服饰团龙纹样进行特征辨别,认为与莫高窟409 窟人物服饰团龙纹相同。
本文在各位前贤积累的成果基础上,回归本体的讨论,旨在重点研究画中丰富物象本身的意味、物象之间的关系。试图从这幅画的皇帝肖像图式、皇帝和侍从这两个人物的组合形式意味进行风格溯源,并结合与《听琴图》的比较,从而勾勒出《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的创作历史轨迹。
一、传统帝王肖像与西夏皇帝图像
中国古代有关帝王的绘画众多,要恰如其分表现出帝王的身份气质则离不开帝王服饰、帝王用具、帝王肖像的描写等。不同时期的帝王形象绘制也有所区别,有关帝王肖像图式的规律分析,学术界从宏观的角度认为元朝以前帝王图中皇帝的视觉形象特征是人物面部几乎均被描绘成四分之三侧面角度,元朝以后转为正面图式。(1)方闻,郭建平:《宋、元、明时代的帝王画像》,《东方收藏》2013 年第7 期,第3 页。居于此论点,也是在前人提供可藉以参考的资料上,笔者总结宋代以前这一图式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特征,直观地呈现出其规律性的变化,第一,能够帮助我们实际地、立体地洞悉中国传统帝王肖像图式所蕴含的审美特征。第二,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将《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的皇帝肖像绘制限定于特定的帝王图像视觉特征发展历史坐标中,对它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以求表明西夏皇帝肖像图式形成的生成动力。
通过图像资料的收集和对比,结合文献史料,对于历代帝王图像演变规律笔者作出了以下分析: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物画是战国时期的两幅墓葬帛画《人物龙凤图》和《人物御龙图》,两者肖像都为正侧面像,而关于帝王图肖像的绘制,检索文献,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衣,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2)李来源,林木:《中国画论发展史实》,《孔子家语·观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 年,第3 页。文献史料中记载的帝王肖像画部分随着实物载体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有一些图像却因载体材质的坚固特质被保留了下来,依据图像史料,当首推今存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梁祠画像石中所见三皇五帝排列的图像。(3)沈伟:《波士顿藏传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研究》,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 年,第73 页。其西壁共描绘十位古帝王,人物图像均为侧面角度。直至宋关于帝王肖像画的画作就有更多,如:魏晋时期《女史箴图》、唐朝《历代帝王图》、宋朝《晋文公复国图》等,详见表1,纵观帝王肖像画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其视觉特点以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是:第一,古人表现帝王形象惯以用线条的艺术语言描绘在各类建筑空间中以及绢本材料上。第二,帝王形象通常被安排设计于多人的故事情景中,唐以后出现了帝王单独个人的图制形式类别。第三,中国传统人物画喜用侧面肖像技法描绘人物,这一侧面人物图式的表现似乎已然成为民族绘画视觉习惯,汉代后续的朝代中帝王形象以四分之三侧面描写尤其多,但也出现了一些特例,例如在武则天亲政期间,武则天造卢舍那佛,大佛面首为女性化的武则天肖像,下身为转龙王身躯,武则天化身正面像佛陀,其目的很明显就是宣扬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很短,延续了唐朝形制,宋代宫廷绘画继承了唐五代时期的绘画传统,这一历史时期对于帝王的绘画继续保持了中国传统人物肖像四分之三侧面的描写,如:《宋太宗立像》《却坐图》《晋文公复国图》等。对比《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两宋帝王肖像图像资料,(如图2、图3、图4、图5)西夏皇帝与两宋皇帝的描写均为四分之三侧面像特征,事实上这样固定的肖像绘画视觉特征在同期的西夏作品中我们都有发现,如:《西夏译经图》《梁皇宝忏图》《注清凉图》、俄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国王像、敦煌莫高窟第409 窟西夏皇帝供养像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原绘制帝王肖像的比例图式深刻地影响了西夏绘画形式与创作。

表1

图2 《宋宣祖半身像》局部

图3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图

图4 《却坐图》局部

图5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局部
除了上文提及的以正侧面和四分之三侧面角度图式来表现帝王形象外,将帝王与陪衬者组合在一起的图式同样可以体现其身份意义。古代中国关于帝王图像描写的一般规律是皇帝作为主体重要人物,其在绘画构图中也是经过被精心安排的,并具有特定的指示意义。在众多关于帝王的绘画中,尤其是在与侍从或者臣子多人组合的场景绘画中,帝王往往被安排在绘画视觉中心位置,且他们的形象较之其他人更为高大,这种有意的对比构思往往就是在隐喻皇帝的主体地位。这种鲜明的主从格式,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人物的真实面貌和生活事实,但在视觉上却能迅速引起观者对帝王形象的关注和景仰,同时也切合了儒家尊王崇主的等级观念和名分贵贱意识,体现出了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职”的纲常礼教的政治秩序,故而成为帝王图像式样的典范之一,为后世所效法。(1)丁勤:《早期帝王图像的形态和特征》,《电影评价》2009 年第11 期,第2 页。《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各物象之间构成近“S”形的动态线,皇帝则位于“S”线的转折位置,是整幅画的视觉中心点,旁边的侍从身形体量明显小于皇帝。此外,在帝王题材绘画中,为了表现帝王的身份,还可以从侍从姿态表情体现主仆尊卑关系,画中侍从所行叉手礼,是我国古代生活中的一种礼仪,是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行的礼,以表达尊敬,并流行于唐宋。近年来,随着西夏历史遗迹的不断挖掘,也出现了与唐宋样式基本一致的叉手礼的人物图像。在《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皇帝平视前方,侍从则微微低头,眼睛略微注视下方,双手放在胸前行叉手礼,十分谦逊恭敬。通过侍从与西夏皇帝礼仪互动的细节着手,主从地位的对比更是加深了主体人物身份特征的意义。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皇帝的形象同样也延续了古代中国关于“帝王”肖像为画面中心点图像构成的样式规律。
党项人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政权——西夏,历时200 余年,与辽、北宋和金朝并立,在其政权的不断更迭过程当中,其文化与中原宋形成了广泛的交流,正如《西夏书事》卷七记载,李继迁以灵州为都,认为“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2)[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卷七,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88 页。如:仿制中原治国方略、社会政策汉化、艺术从题材和技法师承宋人。可见中原宋朝绘制帝王图式方法很大可能地影响到了西夏美术,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夏帝王肖像图式汲取了中原绘画文化。其次,这些图像均有背景情节的描绘,相比较于正面图像,人物侧面的表现更易融合于情景的表达。再则,《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原始是被放置在何种空间关系中,一定的空间也会影响人物形制的表现,由于目前缺少这方面的史料,还无法做出论述。

续表
二、《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
《听琴图》(图6)为故宫博物院所藏,据学术界考证为宋徽宗本人作品。画面中宋徽宗画押“天下一人”,正上方为蔡京题诗,题诗下千仞长松突秀,松下穿插几株修竹,作品主要内容为他与邀重臣抚琴论道的场景,画有四人居中端坐于绒垫石墩,着道士服抚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旁分别有两位着朝服人物端坐绒垫石墩上,纱帽红色朝服官员手中执扇,低头沉思。其与《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图1)两者主体人物皇帝面部五官特征非常地相似,其中丹凤眼、嘴唇、胡髭几乎一致。(如图7、图8)经笔者观察,两幅图主仆形式等多方面也产生了较多呼应,这种画面之间构成的强烈联系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将从以下三方面分析研究这两幅图之间的呼应关系。

图1 《西夏帝王与侍从图》

图6 《听琴图》

图7 《西夏皇帝与侍从》皇帝面部

图8 《听琴图》皇帝面部
第一,人物处理相似。首先,《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的皇帝与侍从这两个人物“一主一仆”的绘画图式显然是不同于中原宋帝王绘画题材的形式构成,中原宋皇室的帝王题材绘画多以单人朝服以及多人簇拥的情节性故事画较多,(见表1)反而宋代文人高士题材画中“一主一仆”的绘画图式相当多,在人物画中,早在南齐高士图中就已经出现“一主一仆”的表现方式,(1)龚美娟:《马麟〈静听松风图〉图像内容及图式研究》,浙江大学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6 页。在唐代图像遗迹中也有“一主一仆”的图式表现,如孙位《高逸图》、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长安王村唐墓壁画《树下仕女屏风》,很显然,唐代时期“一主一仆”两人性别分别有男性和男性组合、女性和女性组合、女性和男性的组合,发展到了五代宋时期,这种“一主一仆”图式模式更为普遍,到了南宋尤其流行,但是,这种图式对应的对象变为了为男性高士、男性文人与男性侍从的组合,如有著名画作五代时期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宋时期郭熙的《早春图》、南宋时期马远的《山水图》《携琴探梅图》《倚松图》《对月图》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的作者可能学习借鉴了流行于宋、易于被模仿的描写文人高士生活画作中“一主一仆”图式表达规律。在《听琴图》中戴纱帽着绿色朝服的官员为文人王黼,他拱手端坐,双手交合被衣袖遮盖,与坐在坐墩上的西夏皇帝坐姿相似,仔细观察王黼旁立一侍从,与《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的侍从人物造型极其相似,两位侍从分别位于主人身后,主仆距离较近,穿着衣服样式也很相像。其次同为双手合握呈叉手礼。(如图9、图10)

图9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主仆组合

图10 《听琴图》官员与侍从组合
第二,场景布置相似。首先,《听琴图》和《西夏皇帝与侍从图》描写的空间都为室外场景,《听琴图》的构成要素有松树、藤本植物、案几、桌子、琴、铜鼎花瓶、花、石墩、垫子、奇石。《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则由松树、藤本植物、案几、案几称布、铜鼎花瓶、花、坐墩、坐墩称布、一只动物、佛教吉祥物用品以及钱财等生活用品构成了人物活动场景,其中,铜鼎花瓶、花卉、案几、藤本植物、松树是两幅图共有重合的事物。(如图11、图12、图13、图14)其次,在构图上,宋徽宗与西夏皇帝都是作为画面视觉中心主体,《听琴图》中主体人物宋徽宗旁有一案几,《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端坐的皇帝旁也有一案几,而且很有趣的是这个案几上摆放的铜鼎花瓶与《听琴图》中最前景中立于奇石上的铜鼎花瓶形制上如出一辙,两个铜鼎花瓶都插有花卉。《听琴图》中铜鼎花瓶立于奇石之上,这一景观设置与两官员、宋徽宗共同形成了闭合的空间,使得画面开合有致,在《西夏帝王与侍从图》中,皇帝脚下佛教吉祥物和生活用品的组合正与《听琴图》中奇石上置铜鼎花瓶这一景观的空间意义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封闭画面下面部分的“气口”。

图11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花瓶局部

图12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案几

图13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松树图

图14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藤本植物
第三,立意相似。五代两宋时期,山水画皴染技法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使得画面效果产生了真实的空间质感。随着两宋宗教世俗化的发展,文人高士喜欢将自己的价值观、宗教感情抒发于大自然,这时出现了大量的人物画与山水画元素于一体的生活性场景性绘画。为表达绘画意图除去重要人物、山水花草外,最直观的载体就是象征性道具的出现,如此,帝王图像中的人物形象、配饰、道具等的位置并非任意填塞和罗列,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处理和安排,其最大的宗旨在于满足帝王希望自己永远处于国家乃至世界中心的野心和志向。(1)丁勤:《帝王图像的图式内涵研究》,《美术大观》2013 年第1 期,第1 页。有学者在文章中通过《听琴图》道具等的文化内涵的解读,论述了这幅画实则是着道士服“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以艺贯道,道法自然,不为外物所累,以天地自然之心,中和万物之儒道相糅的艺术观。(1)时玲玲、谢建明:《乐和,人和,天地和——《听琴图》新论及其作者再考释》《南京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2017 年第1 期,第3 页。不同于宋徽宗在《听琴图》对自己主权身份和政治理念的隐形表达,《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这位帝王从穿团龙纹服饰上看,他很明确自己的身份,画中充斥着生活用品、动物与佛教吉祥物,这些多样性的视觉符号不仅丰富了画面图式构成,它们的出现并非随意偶然,绘画者一番精心的布置安排则是表明西夏皇帝的身份、刻画西夏皇帝的生活风尚,同时还兼具物体特殊的隐喻和指向意义,动物与佛教礼器吉祥物被有意地挑选安排在画面上,一定具有特定含义,西夏笃信佛教,这幅图立意之一很可能就有佛教伦理意义的诉诸以及西夏皇帝得佛道之意。宗教世俗化的现象也出现在了西夏,并被绘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以上从《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宋代帝王肖像图式、“一主一仆”组合图式以及与《听琴图》对比之后,笔者进一步发现《西夏皇帝与侍从图》构图乃为宋时期特有的全景式构图,分别由前景、中景和远景分布而成,前景在地面上安排了一些物品、财宝以及佛教吉祥物。中景突出表现了主体人物西夏皇帝的中心地位,其旁有侍从一人和呈回首仰望姿态的动物,画面视线再进一步推远则是一个铺有称布的案几,上面陈列着一铜鼎花器,并插有一簇花卉。远景又是一片较为宽阔的水面,可见藤蔓缠绕着的两棵松树临水而出,松树枝叶部分超出了画幅并作垂落状直指主体人物西夏皇帝,整幅画面中各个陪衬物从面积大小,动态走向都旨在烘托西夏皇帝的中心位置,全局饱满,视野开阔。远景中两松树临水而出这一安排也十分符合宋时期的绘画风格,正如苏利文所说,画中“临水悬崖,丛树斜出,小舟飘摇——是一种12 世纪山水画的典型样式”。(2)SuLLivan,‘Notes on Early Chinese Screen Painting’,P.241 转引自巫鸿:《重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42 页。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西夏皇帝面容以单色墨线勾勒,面部不加渲染,衣纹处稍有墨色渲染。用笔以游丝描和少许钉头鼠尾描为主。钉头鼠尾描在皇帝衣袖部分集中运用,突出了皇帝拱手端坐衣纹密集的丰富效果,其余部分都为铁线描的刻画,笔锋中锋行笔,力度均匀,圆润饱满,皇帝膝盖结构处理准确,双肩流畅,使得整个人物形象与侍从形成了强有力的对比。那西夏皇帝形象绘制技法风格显然遵循了北宋中后期李公麟画风一派,其一是:画面整体为“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白描手法,画面主要以墨线勾勒,略施淡墨淡彩。其二是:在白描画风基础之上,两者表现物体形象的线条同为圆润劲挺又有起伏变化。(如图15)此外,宋代时期,插花艺术蔚然成风,各种造型、不同质地的类花瓶出现,其中就有铜瓶插花的审美趣味,宋人说到铜瓶,方才涉及折枝插瓶,便是插花和养花,而以北宋末年直至南宋为盛。(1)扬之水:《宋代花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年第1 期,第9 页。这一现象也被描绘到了画作中,如《瑶台步月图》《汉宫图》。《西夏皇帝与侍从图》案几上的铜鼎插花这一生活内容明显也是学习中原宋文化的又一反映。可见《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从绘画风格、绘画形式与内容等多方面的同宋代画风重合,由此,笔者推测绘制《西夏皇帝与侍从图》的作者很可能见过以及参考过《听琴图》以及其他大量画作。

图15 李公麟《西岳降灵图》局部与《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局部
三、总结
就绘画而言,图式是绘制者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里运用审美的原则,安排和处理形象或符号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规律的组合关系。(2)丁勤:《帝王图像的图式内涵研究》,《美术大观》2013 年第1 期,第1 页。西夏皇帝的肖像描写与中原帝王肖像图式是一脉相承的。另外,《听琴图》给《西夏皇帝与侍从图》提供了一种内容与形式上的图像参考,很有可能《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与《听琴图》两者是相近时期的作品,可以说众多的西夏美术作品显示西夏美术全方面多角度地吸纳了宋画的绘制形式,可见当时西夏对中原宋文化的热衷。同时,西夏绘画风格与宋相比较,在汲取中原绘画风格的基础上,也不乏“存异”的民族特色,比如在这幅《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中,西夏皇帝脚下有一些物品,有学者认为它们是珊瑚、火珠、乐用的犀牛角、一串钱、银锭和一些画卷(1)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俄藏黑水城艺术品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296 页。,这在同期中原宋绘画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关于它们的含义作者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