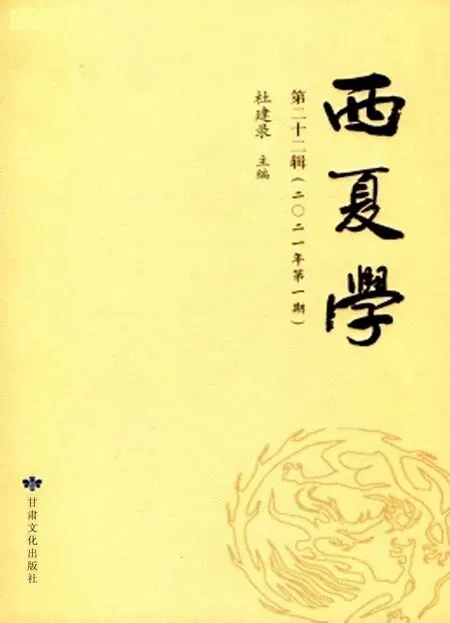西夏联珠纹初探
李玉峰
联珠纹,顾名思义是由大小相同的圆圈或圆珠连续排列而成的构图较为简单的装饰纹样。学界普遍认为此类装饰纹样是来源于波斯萨珊王朝(1)如陈熊俊、梁昭华:《“西”风东化——浅析联珠纹在敦煌服饰图案中的演变》,《美术大观》,2008 年第4 期;闫琰:《北朝联珠纹装饰纹样的组合》,《文物世界》,2010 年第2 期等均这样认为。。因为尽管其在中国出现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马家窑型和马厂型的典型纹彩陶罐上有形式简单的联珠纹,但是它并未形成自觉连续的传统,仅可看做是后来风靡流行的联珠纹的雏形。而在波斯的安息时代,这一纹样形式得到了延续,至萨珊王朝发展成熟,常被装饰于宫殿浮雕、钱币、丝绸、银器上。南北朝时期,随着各民族间的迁徙融合,西亚人的文化艺术,包括联珠纹这一纹样形式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中国在原有联珠纹雏形的基础上,很快接受了来自异域的联珠纹,并广泛推广应用。
笔者在整理西夏遗存相关资料时,发现联珠纹在西夏时期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并得以广泛应用,是当时较为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除织物和石窟壁画装饰外,其在建筑构件、佛教造像、金银饰品、实用器物中也较为多见。它通常作为辅助纹样,或与卷草纹相配,饰于带状装饰面的边沿,如石窟壁画中的边饰;或与莲花、兽面纹等独立纹样相配,饰于方形、圆形构件边沿,如瓦当、方砖;或出现在须弥座、束莲柱的束腰部位,坛城、华盖及实用生活器物的分界处,起着隔离不同图案的作用。
目前关于联珠纹的研究,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1)如闫琰《北朝联珠纹装饰纹样的组合》(《文物世界》,2010 年第2 期)、李晓卿《北齐徐显秀墓室壁画中的联珠纹艺术探析》(《山西档案》,2018 年第1 期)、李姃恩《北朝装饰纹样》(紫禁城出版社,2014 年)等文中主要以北朝时期的联珠纹为主要研究对象;吴巧仂《传承与创新——浅析唐朝“联珠纹”的时代特色与发展》(《艺术与设计》,2008 年第1 期)、刘昕璐《从唐朝织锦联珠纹的流变看唐朝对异域文化的吸收》(《艺术探索》,2014 年第6 期)、高山《从唐联珠猪头纹锦看联珠纹样发展过程中的装饰演变》(《四川丝绸》,2008 年第1 期)等文则主要以唐代联珠纹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包括西夏在内的其他时期的联珠纹讨论较少。,无人谈及西夏时期的联珠纹。而载体则多以织物为主,如涉及联珠纹的许多文章中均以新疆阿斯塔纳墓中出土的联珠鸾鸟纹锦、联珠对鸡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对马纹锦、“胡王”联珠纹锦等材料进行研究。对此之外的,如石窟装饰、器物构件等载体上的联珠纹则相对研究不多。在对联珠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时,多数侧重于联珠纹主题纹样的分析,而忽略了联珠纹本身,将联珠圈和它所环绕的主题纹样视为不可割裂的组合整体(2)尚刚:《从联珠圈纹到写实花鸟——隋唐五代丝绸装饰主题的演变》,2014 年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主办“岁寒三友——诗意的设计”——两岸三地中国传统图形与现代视觉设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此观点无疑更符合装饰的实际情况,对判断联珠纹装饰的文化来源也有较大裨益,但是却忽略了对联珠纹本身的形式、特征、流变等问题的归纳和探讨。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西夏遗存上联珠纹为研究对象,对其形式进行归纳分类,并总结其特征,探讨其流变等问题,以求了解西夏时期联珠纹在装饰纹样中的应用情况、文化内涵及重要地位。
一、联珠纹的类型
西夏时期联珠纹多见于各类遗存之上。根据联珠纹的特征,可将其分为三种“型”别。即A型:圆形联珠纹;B 型:椭圆形联珠纹;C 型:复合型联珠纹。此外,根据联珠的排列方式、大小差别及形态,又可将每“型”联珠纹划分若干“式”。
A 型:圆形联珠纹 此型联珠纹中的联珠是由圆圈状的联珠排列而成,根据圆珠的形态和排列方式,又可划分为4 式。
Ⅰ式 紧凑式联珠纹 由大小均匀的圆珠呈横向或纵向一字排开。此式联珠纹在西夏遗存中较为常见,多出现在石窟藻井、龛楣、边饰和壁画边框上。以敦煌莫高窟第400 窟窟顶藻井边饰中的联珠纹为例(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29。,浅色圆形联珠纹个个紧挨,整齐有序地排列在窟顶藻井边饰的第1、4、7 层,以及窟顶斜坡之间的交汇处。由于色彩较浅、构图简单整齐,使得装饰图案繁复的藻井层次分明,立体感增强,在视觉上加深了内部空间感,甚至可通过联珠纹寻觅到覆斗形石窟藻井内部简单的构造框架(图1)。榆林窟第10 窟藻井边饰第4 层(1)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07。,榆林窟第2 窟藻井边饰第2、4、7、9、11 层(2)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40。,莫高窟第87 窟藻井边饰第1、4 层(3)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15。,莫高窟第234 窟藻井边饰第1 层(4)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21。,莫高窟第130 窟窟顶斜坡四方交界处、藻井中心图案内层边沿、藻井边饰1、5 层(5)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22。,莫高窟第326 窟墙壁与窟顶斜坡交界处、藻井边饰第1、3、5 层(6)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23。等,均绘制此式联珠纹,唯一差别是联珠纹的颜色根据整体底色和周围装饰纹样色彩的不同有所变化。此外,此式联珠纹在造像装饰中也常见,如西夏陵3号陵北门出土红陶五角花冠迦陵频伽胸部残片T2310 ②:6、肩部残片T2311 ②:11及献殿出土釉陶五角花冠迦陵频伽肩部残片T1211 ②:7(7)宁夏文物考古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西夏3 号陵——地面遗迹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160、176、280 页。中,迦陵频伽胸前项圈边缘也整齐紧密地排列着联珠纹,与项圈内卷曲延伸的卷草纹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肆意的卷草纹束缚于两排联珠纹中间,有收有放,动静结合,达到和谐统一、变化自由的效果(图2)。这与莫高窟第409窟人字披顶部中脊卷草装饰带两侧边沿饰的纯色联珠纹(8)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33。如出一辙。
Ⅱ式 分散式联珠纹 其形态与Ⅰ式同,亦为大小均匀的圆圈,但Ⅱ式联珠纹相邻者间距相等,其排列方式自由多变,或呈一字排开,或呈各种形状围绕在其他单独纹样周围。
此式联珠纹在建筑构件、佛背光边沿、壁画及服饰纹样中较为多见。如西夏陵3 号陵、6 号陵出土的方砖和瓦当上,其中心为主题图案,在边沿处饰一周圆珠或圆圈形间距相等的联珠纹,此处联珠纹不仅有效地将中心主题图案与周边图案分隔开来,同时还将中心图案衬托得更加醒目,增强了装饰效果(图3)。与此相同的还有拜寺口西塔天宫藏童子戏花图印花绸(9)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255 页,图版一七六。,其上联珠纹亦呈圈状,围绕在内部被花叶以“十”字分为四等份且每份内装饰一枝侧视折枝莲花的纹样周围,此图样以四方连续的形式布满花绢,四个此类联珠圈中间饰一构图结构相仿、中间为折枝牡丹的菱形开光,菱形开光与联珠圈的间隙处饰一憨态可掬的小童子作飞天状,其余空白处均被花叶占据,花绢纹饰整体繁复稠密,但联珠圈内的莲花和菱形开光中的牡丹则更为醒目,使花绢纹饰繁而不乱,这便是联珠纹营造出来的一种秩序感(图4)。而莫高窟第245 窟西壁南侧供养人(1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 卷,文物出版社,1987 年,图版142。、榆林窟第29窟南壁西侧女供养人(11)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21。衣物上的联珠纹则为数个联珠围绕中间一颗简易的联珠组成花朵状,然后整个联珠花以四方连续的方式布满整件衣袍,精巧别致。此处联珠花构图形式与瓦当、方砖上的联珠纹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其仅作为装饰纹样增添纯色服饰的美感。
此外,Ⅱ式联珠纹还多见于佛像背光中,如东千佛洞2 窟前壁左侧顶髻尊胜佛母壁画中佛母背光边沿,同窟前室左壁救八难绿度母圆形身光边沿(1)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105、112 页,图版8、6。,东千佛洞7 窟前室右壁阿弥陀佛接引图中阿弥陀佛头光内层,同窟顶髻尊胜佛母塔龛边沿,八大菩萨中除盖障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的背光、头光边沿内层(2)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59、267、273、275 页,图版68、74(2-1)、76(8-1)、76(8-5)。均可见到等间距联珠纹,其根据背景色彩的不同变换自身的色彩,以整齐突兀的特征更加醒目地将背景与主题进行鲜明划分,同时仍表现出服帖融合感。藏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的3 件联珠纹铁壶(3)史金波主编,塔拉、李丽雅主编:《西夏文物》(内蒙古编)第三册,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901—906 页。颈与腹部交界处,榆林窟第29窟(4)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22。、东千佛洞2 窟(5)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124 页,图版10(3-3)。等窟壁画中多数尊者的莲花座外围边沿,以东千佛洞5 窟(6)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29 页,图版55(9-1)。、黑水城出土绢画和木板画(7)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图版125、126。为例的曼荼罗坛城城墙及金刚环边沿,东千佛洞7 窟八大菩萨之观音菩萨顶部华盖边沿(8)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73 页,图版76(8-1)。,拜寺口西塔天宫藏彩绘绢质上师图(9)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250 页,图版一七〇。边框等部位,均饰有Ⅱ式联珠纹。此时联珠纹亦起到了界限的作用,作为间隔纹样,其以活泼、跳跃的视觉感装饰和分隔了画面,这是弦纹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Ⅲ式 套叠式联珠纹 其特征为大圆圈内套叠一小圆圈,多呈一字型排开。此套叠联珠纹以榆林窟第3窟西壁南侧普贤变(10)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64。中罗汉衣服边沿处最为典型,联珠套叠、浑圆饱满、紧密相挨,呈带状排列,形成线性的装饰带,使袖端朴素整齐,严谨中略显别致(图5)。东千佛洞5 窟绿度母眷属坐的“亚”型须弥座(11)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04 页,图版45(2-2)。也饰有两列套叠联珠纹,使厚重的基座变得灵动精巧。此时的联珠纹在形态上已与最初传入中国的联珠纹产生差异,没有了象征意义,连分隔图案的作用也不那么明显了,仅保存了纹样符号作为装饰,发挥美化的作用。而东千佛洞5 窟八大夜叉坛城(12)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29 页,图版55(9-1)。中,从内至外,第一圈层上饰彩色套叠型联珠纹。其色彩饰于中心套叠的小圆圈上,以蓝靛为主,同时在彩色小圆圈中心涂以白点,表示物体在光线中的明暗和光点所在,将联珠纹的立体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联珠纹如宝石般镶嵌在坛城圈上(图6)。
Ⅳ式 叠晕式联珠纹 此式联珠纹排列方式与Ⅰ式相同,为紧密相挨排列。其主要特征是运用绘制建筑彩画的方法之一——叠晕来绘制。所谓“叠晕”,即利用同一种颜色调出二至四种色阶,再依次排列绘制的手法。此叠晕式联珠纹最典型的例证为榆林窟第10 窟藻井边饰(1)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 年,图版107。,黑底上用青、红、蓝、褐四色绘制联珠,叠晕联珠或浅色在外、深色次之,或深色在外、浅色次之,当中点白粉为宝珠心,最后形成不同叠晕色彩的联珠相间排列,精致华美(图7)。以叠晕方式绘制联珠纹,使联珠纹的立体效果更强,一排排叠晕联珠如珍珠镶嵌在藻井四周,既可以将平面的卷草花卉纹样规整地隔离,又以自身的饱满浑圆之感装饰藻井,使象征极乐天宫的藻井显得繁复华丽而又严谨典雅。此外,在黑水城出土的麻布彩绘唐卡金刚座佛(2)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艺术品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图版71。中,佛莲花座上层边沿也出现了这种叠晕式联珠纹。此式联珠纹还以“品”字型火焰珠形式出现,如榆林窟第10 窟藻井边饰中,但此时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联珠纹了。

?

续表
B 型:椭圆形联珠纹 此型联珠纹是由椭圆形联珠排列而成,在西夏遗存中不常出现,但根据联珠的形态,仍可划分为2 式。
Ⅰ式 由简单的实心(涂色)椭圆形联珠首尾相接,呈线性条带状排列。目前为止,仅东千佛洞7 窟甬道顶部卷草纹图案边沿处(1)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284 页,图版78。饰有此式联珠纹,其为浅色底纹上排列黑褐色椭圆形联珠纹,留白较少,整体厚重感较强(图8)。此类联珠纹标本,笔者收集到的材料中仅此一例。
Ⅱ式 此式联珠纹为套叠式椭圆形联珠纹,其主要特征为一个椭圆形圈内套叠一个小椭圆形,然后多个此种样式的套叠椭圆形紧密排列,组成条带状纹样。此式联珠纹在西夏遗存中也较为少见,目前仅见于拜寺口西塔天宫藏彩绘绢质上乐金刚图边沿(2)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251 页,图版一七一。和黑水城出土麻布彩绘唐卡金光明经变残片边沿(3)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艺术品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图版104。,金色底纹上饰套叠联珠纹,其内部小椭圆分别施以红、蓝二色,并相间排列,醒目华丽,如宝石镶嵌于绢画四周,体现出较强的神圣感与华贵感(图9)。与印度佛教装饰风格颇为相似。

?
C 型:组合型联珠纹 此型联珠纹由椭圆形和棱角并不分明的菱形(梭形)相间组成。在西夏遗存中有见,但仅存一种形态,故在此不做式别分类。以黑水城出土麻布彩绘唐卡《金光明经变》边框(4)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艺术品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图版104。和东千佛洞2 窟前室左壁救八难绿度母•牢狱难壁画上方边框上的组合型联珠纹(5)张宝玺:《瓜州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学苑出版社,2012 年,第117 页,图版8(7-6)。为例。黑水城出土唐卡边框上的组合型联珠纹椭圆为绿色,菱形为红色,其立体感强,装饰风格与B 型Ⅱ式同(图10)。此外,东千佛洞2 窟十一面观音•象难壁画左右边框处的联珠纹也为此装饰风格。而东千佛洞2 窟前室左壁救八难绿度母牢狱难壁画上方边框上的联珠纹立体感则较弱,施色因年代久远而漫漶不清,仅剩黑色单线勾画的轮廓尚存(图11)。

图10 黑水城出土12-13世纪麻布彩绘唐卡边框饰

图11 东千佛洞2窟前室左壁救八难绿度母•牢狱难壁画上方边框饰
二、联珠纹的特征
西夏时期的联珠纹是继丝绸之路开通后由波斯萨珊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联珠纹相融合,又经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不断改革和创新后形成的纹样。通过前述对联珠纹的分类梳理可知,它不仅普遍分布,而且样式不一,排列方式更是变化多端。经与前代联珠纹对比发现其有以下几点特征:
在西夏遗存上占比例较大的A 型Ⅰ式、A 型Ⅱ式、A 型Ⅲ式、B 型Ⅰ式四种联珠纹,均固守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直至宋时期已有的样式,并无太多创新。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表现西夏四种联珠纹与前代及同时代宋联珠纹之间的继承关系,现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图案卷》及笔者搜集相关纹样资料为例,列表如下:

表1 魏晋南北朝-宋时期联珠纹与西夏联珠纹样式对应表

续表

续表
由上表可知,A 型Ⅰ式、A 型Ⅱ式、A 型Ⅲ式、B 型Ⅰ式4 种联珠纹均继承自其他朝代已有的纹样。紧凑型联珠纹A 型Ⅰ式主要集中在盛唐至宋;分散型联珠纹A 型Ⅱ式主要集中在北魏至初唐时期;套叠联珠纹A 型Ⅲ式主要出现在北朝与唐宋时期,其他时期较少出现;B 型Ⅰ式椭圆形联珠纹则主要出现在隋代,宋也少量存在。上述4 式联珠纹均在前代已经出现,或一字排开,或组成联珠圈,亦或围成方框,形式相对自由,这与在西夏时期的组成方式也基本一致。
西夏时期部分遗存上的联珠纹通过设色来表现不同变化。由于联珠纹本身构造较为简单,故与其他纹样相比在应用的过程中装饰效果并不明显。西夏石窟壁画多以彩绘为主,为了在不同底色和装饰背景下较好地起到装饰和分隔画面作用,联珠纹通过设色来突出存在感,表现出不同变化。如榆林窟第10 窟藻井边饰的第2、7 层中装饰的A 型Ⅳ式叠晕联珠纹,其在紧凑型联珠纹A 型Ⅰ式的基础上,通过不同色彩的搭配和同一色彩明暗变化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将联珠纹的立体效果表现得十分到位。此外,东千佛洞2 窟前壁左侧顶髻尊胜佛母壁画中佛母背光及同窟前室左壁救八难绿度母圆形身光、东千佛洞7 窟前室右壁阿弥陀佛接引图中阿弥陀佛头光内层边沿饰的彩色A 型Ⅱ式联珠纹,东千佛洞2 窟十一面观音•象难左右边框饰的C 型组合联珠纹,东千佛洞5 窟八大夜叉坛城内层饰的A 型Ⅲ式彩色套叠型联珠纹等,均通过鲜明的色彩和联珠上表示光线明暗的白点来表现联珠的立体感。上述几例西夏石窟中联珠纹的设色手法在前期石窟中鲜有见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至宋时期石窟龛楣、佛像背光、头光、藻井以及出土纺织物中装饰的联珠纹,基本以纯白色和黑褐色为主,较少见到其他颜色。其着色也无明暗、深浅的变化,因此多以平面图案的形式呈现,几乎少有立体感可言。
除西夏时期石窟绘画中的联珠纹通过设色手法来表现立体感和变化外,出土的一些西夏时期织物中的联珠纹也通过同样的设色手法来体现纹样的立体感。如拜寺口西塔天宫藏彩绘绢质上师图和上乐金刚图边框上装饰的蓝、红联珠纹,黑水城出土西夏麻布彩绘唐卡边框上装饰的红、绿组合型联珠纹。虽然型、式不同,但不同色彩的联珠纹搭配在一起较好地表现出了纹样的华丽感。此外,同一色彩的联珠纹上饰以表示明暗的光点,立体感表现得比石窟之中更为逼真,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的一批联珠纹唐锦上则不见此立体感。
西夏组合型联珠纹中出现了棱角并不分明的菱形样式。就目前所见出土资料可知,波斯联珠纹中的联珠均为圆形,较少存在椭圆形,几乎未见其他形状。当其传入中国与本土的联珠纹雏形相结合后,在北朝时期出现了除圆形、椭圆形以外的组合型联珠纹。此时的组合型联珠纹主要见于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上层东起第二龛魏灵藏龛、南壁下层小龛边饰、杨大眼龛背光、北壁下层龛(183窟)龛楣边饰上(1)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第1 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图版159、160、173。,其以椭圆和圆形联珠相间组合排列的式样为主,变化中充满了秩序感。此后的隋、唐、宋多以圆形联珠纹为主,组合型联珠纹极为少见,而在西夏遗存上发现的组合型联珠纹则是由椭圆形和菱形(梭形)组成。看似较为自由的组合,却依旧遵循着颇有秩序的形式美。这种组合型联珠纹也多施以丰富的色彩,尤以黑水城出土唐卡边框上的最为艳丽有光泽,立体感较强,犹如镶嵌的宝石,这与藏传佛教艺术装饰风格极为相似。笔者认为这与西夏佛教后期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关系。这一造型和风格的联珠纹在之前其他时期较为罕见,现存西夏时期的相关资料中也不多见,笔者仅收集到2 例材料,不得不说这是西夏时期人们在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后对联珠纹的革新。
三、西夏联珠纹的作用
西夏时期的联珠纹与前代相比,其域外特征和宗教涵义并不明显,本土化程度相对更高,其更多是承担修饰边框和分割装饰平面的作用。很多学者认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联珠纹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联珠纹中连续的圆珠象征着太阳和月亮的光轮,圆珠圈代表宇宙中的圆环。”(1)王晓娟:《北朝联珠纹样探微》,暨南大学2010 年硕士论文。从其外形看,外围的一周小圆珠的确像抽象化的光芒,突显着联珠圈内主题纹饰的神圣性及其代表的无上权威。但当其传入中国,经过前人尤其是隋唐时期工匠的吸收、融合及改造后,逐渐在题材、造型、结构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纹样。此时其宗教涵义渐渐消退,装饰性作用逐渐增加,但尽管如此,隋唐时期的联珠纹依旧有着明显的域外特色。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出土的隋唐联珠纹锦,虽然主题纹饰已经变成了中国本土常见的龙、凤、鸳鸯、菩萨头像等,同时内置纹样也一改波斯时期喜欢单独纹样的风格,多以对称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内置纹样依旧遵循着简洁、粗犷的波斯特征,联珠大而醒目,相邻联珠圈之间也较少或简单饰有其他纹样。而在西夏遗存上的联珠纹,其域外特征和宗教涵义则几乎看不出来。如宁夏拜寺口双塔西塔天宫藏的童子戏花绢,虽然绢布上以四方连续的方式排列有联珠圈,但联珠较小,联珠圈内饰有多支繁复的花朵,相邻四个联珠圈中间饰有一大小等同的菱形开光,开光内也饰多支花朵,菱形开光与联珠圈平分秋色。此外,在菱形开光和联珠圈中间的缝隙处饰满了碎花和藤叶,憨态可掬的童子攀附在藤叶上做飞天状,此等繁花锦簇、装饰华丽的绢布与波斯织锦纹样追求单一的风格特征相去甚远。
另外,隋唐时期联珠纹锦的主题纹样以狮、象、鸭、鹿、翼马、羚羊、骆驼、野猪、高鼻深目的胡人为主,周围的联珠一方面使主题纹样更醒目,另一方面联珠可视为神光的体现,借以强调主题纹样的神圣或权利属性。而西夏时期的联珠圈则并不强调圈内主题纹饰的神圣属性,多体现为边框的修饰。如西夏陵3 号陵、6 号陵出土的莲花纹方砖,边棱上装饰A 型Ⅱ式联珠纹使整个方砖纹样别致活泼而富有秩序感。西夏石窟藻井边饰、龛楣、须弥座、坛城圈中的各式联珠纹也起着分层次修饰的作用,无域外特征,更无宗教象征涵义。甚至笔者发现西夏遗存上有联珠纹做主装饰纹样的案例,如榆林窟第29 窟南壁西侧女供养人和敦煌莫高窟第245 窟西壁南侧供养人衣服上饰满联珠纹花朵。此时的联珠纹一改过去的风格,联珠圈内不再饰其他纹样,而仅置一圆珠,简洁大方又不失精巧,与本土的点彩纹样颇为相似。
关于佛造像周围的联珠纹,笔者认为其作用亦不体现人物的神圣属性,因为尊者的神圣属性已被各种背光、头光纹饰强调,而处于边沿处的联珠圈似乎更多地承担着分割装饰面的作用,这与西夏石窟中许多壁画边沿的联珠纹作用相同,与边框处卷草纹的作用也大同小异。而兽面纹瓦当边缘的联珠纹,其是否带有宗教涵义,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一方面兽面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兴起而被广泛应用,由于各个宗教相继传入中国并相互融合,所以作为神兽其周围附有联珠来强调它的神圣属性是可以说得通的;另一方面,丝路开通后,东西方进行大规模交流,基于喜新尚奇的心理对外来粉本进行模仿借鉴,用于装饰并代代相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对某宗教的虔诚,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纹样符号在用。因此,关于兽面纹外围的联珠是否存在宗教含义,可以说有,亦可说无。综上可知,西夏时期的联珠纹基本承担着装饰和分割画面的作用,与前代相比其域外特征和宗教意蕴均不明显。
总而言之,西夏时期的联珠纹作为配饰广泛出现在各种装饰载体上,它是波斯萨珊式联珠纹与中国传统联珠纹结合后又经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演变而形成的纹样。其形制多为前代已有的圆形和椭圆形,但在装饰过程中已开始通过设色来表现变化。此外还出现了椭圆+菱形(梭形)组合成的新样式。虽然联珠纹由波斯萨珊王朝传来,但其域外特征和宗教含义在西夏时期表现得均不明显,仅发挥着美化和分隔画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