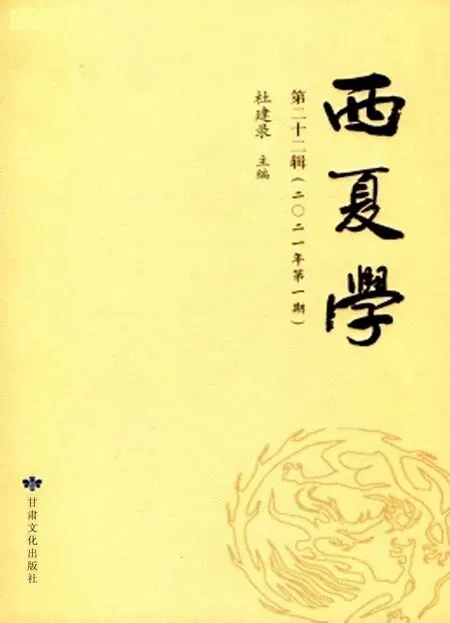教宗华严 行归净土
——莫高窟第365 窟西夏重修思想初探
李志军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在其统治的将近两个世纪中,由于地域关系、民族构成和历史渊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夏政权极其崇信佛教,并将佛教作为国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西夏境内僧人众多,塔寺林立,求经、赎经、译经、校经、施经等佛事活动空前繁盛。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西夏人同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瑰宝,而此方面的资料,“敦煌保存最为集中,最为丰富,最为珍贵”。(1)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分期研究之思考》,《西夏研究》2011 年第2 期,第23 页。在西夏统治的近200 年中,“西夏人在佛教文化已有很深积淀的敦煌地区,开凿洞窟和修缮前期洞窟达40 余窟,数量颇丰。”(2)张世奇、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研究综述》,《西夏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90—91 页。
西夏时期,敦煌人“在莫高窟的基本营建方式是重修前代洞窟”。(3)沙武田:《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构建》,《西夏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4 页。莫高窟第365 窟即其中一例。就目前365 窟的遗存情况看,西夏人在重修时保存了原西壁七佛塑像,而抹壁重绘了其他几面墙壁的壁画,这种取舍充分说明西夏人在重修前代洞窟时是有自己深层次的考量和重新构建洞窟的义理需求的。但学界关于第365窟的研究仍停留在中唐吐蕃时期,(1)相关学术成果整理可参考沙武田、梁红:《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辨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敦煌学集刊》2016 年第2 期,第70 页。对于西夏时期重修思想的研究尚属学术空白,后学于此不揣浅陋,略作考释,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七佛相关问题考释
莫高窟第365 窟最初开凿于中唐吐蕃时期。根据窟内现存塑像及佛坛下汉文与藏文题记判断,莫高窟第365 窟即敦煌写本P.4640(5)《吴僧统碑》记载,洪辩所开“七佛药师之堂”。换言之,该窟西壁七佛(图1)在初创之际是根据药师经典所塑造之药师七佛,这一点为学界共识,当无异议。然而,西夏人在重修第365 窟时于七佛头光北侧所留七方绿底白字榜题却揭示了西壁七佛身份的变迁,这一变迁对于我们了解西夏时期的佛教思潮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图1 莫高窟第365窟西壁七佛造像
(一)从药师七佛到过去七佛
就目前可辨识的西夏时期重修第365 窟时所留榜题来看,西壁七佛已由药师七佛改塑为过去七佛。七佛榜题内容如下:
西壁七佛南起第一身榜题为:
南无释迦牟尼佛
贤劫中有佛名释迦牟尼如来,寿命一百岁,于释家生,姓瞿昙,于阿说他树下得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闻其名,称赞敬礼者正,灭得七百万亿阿僧祇劫□之死重罪。
西壁七佛南起第二身榜题为:
南无迦叶佛
贤劫中有佛名迦叶如来,寿命二小劫,于婆罗门家生,姓迦叶,于尼拘律陀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闻正其名正,礼敬称赞者,灭除亿九十恒河沙劫生死之重罪。
西壁七佛南起第四身榜题为:
南无拘留正孙佛
贤劫中有佛名拘留孙如来,寿命十四小劫,婆罗家生,姓迦叶,优头跋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闻其名,称赞敬礼者,除得无数亿劫生死重罪。
西壁七佛南起第五身榜题为:
南无毗舍浮佛
过去世劫有佛毗舍浮如来,寿命二千劫,刹利家生,姓拘隣,于娑罗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闻其名,一心敬礼者,永破地狱业,不生三恶道。
西壁七佛南起第六身榜题为:
南无尸弃佛
过去世劫有佛名尸弃如来,寿命一千劫,刹利家生,姓拘隣,于分陀利树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闻其名,一心敬礼者,灭得九百亿劫生死之重罪。
西壁七佛南起第七身榜题为:


根据榜题所示,该窟西壁七佛名号自南起分别为:释迦牟尼佛、迦叶佛、□□□、拘留孙佛、毗舍浮佛、尸弃佛、毗婆尸佛。
从榜题的具体内容分析,不难看出其 “某佛信息+某佛功能”的基本模式。关于其中“某佛信息”部分,笔者通过与相关七佛经典对比发现,元魏菩提流支所译《佛说佛名经》内容可以与本窟榜题所示七佛信息相对应(表1)。

表1 《佛说佛名经》所载七佛相关信息(1)[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卷8,《大正藏》第14 册,第161 页上、中、下。
而“某佛功能”的部分,虽未见于《佛说佛名经》,但却屡见于七佛其他相关经典中,而灭罪及破地狱更是陀罗尼经典中所突出的七佛信仰的基本功能。(2)可参考占翀:《宋代七佛塔研究——以浙江地区为中心》,浙江大学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7—68 页。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在七佛信仰与大量陀罗尼神咒结合的时代背景下,(3)谷赟:《奉国寺过去七佛造像与护国思想》,《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3 期,第48 页。西夏人对于第365 窟西壁七佛的处理,以《佛说佛名经》所提供的过去七佛信息为基础,融入七佛与陀罗尼神咒结合所具备的灭罪功能,成功将原中唐药师七佛改塑为过去七佛。
(二)第365 窟七佛造像探源
“七佛”的概念最迟在两晋时期就已经进入中原地区的创作题材,(1)于博:《辽代七佛造像研究——以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七佛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2 页。就目前敦煌所保留下的材料来看,敦煌本地要晚至西魏才出现七佛造像,自此以后七佛造像一直在敦煌地区流行。然而,在莫高窟的造像传统中,过去七佛在洞窟的布局分配上始终扮演着陪衬的角色,绝大多数位于门顶部,个别也有位于洞窟南北壁的情况。
而西夏人对于第365 窟的重修,使过去七佛由敦煌造像传统中的次要位置一跃成为了洞窟主尊,这样的变化无疑反映了七佛在敦煌本地原有信仰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思想及功能上的重要突破。很显然,这种突破是受到了当时外来的一股强有力的七佛信仰新思潮的推动。
中唐以来,随着华严圆教的普及与密教修行的兴起,作为沟通显密经典重要题材的过去七佛信仰逐渐兴盛起来,辽代佛教上承唐代遗风尤为重视华严和密教,在辽朝佛教各宗派中,“最为盛行的是华严,其次是密教”,(2)陈爱峰、杨富学:《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西夏学》2006 年第1 辑,第32 页。因此,“过去七佛题材在辽代非常流行”。(3)谷赟:《奉国寺过去七佛造像与护国思想》,《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5 年第3 期,第48 页。庆州白塔像轮樘内有一百多座木雕法舍利塔上有过去七佛造像,辽中京地区的众多辽塔,其外部塑像也都有过去七佛。且据谷赟先生统计,目前发现的辽代七佛造像多数是在皇家寺院建筑里,(4)谷赟:《辽塔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3 页。由此可窥见辽代七佛信仰兴盛之一斑。
西夏佛教与辽代佛教关系极为密切。在辽代佛教的影响下,(5)索罗宁先生指出:“西夏官方的华严信仰起源可见在辽的佛教体系,而非宋代的中原佛教。”(详见氏著:《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4 期,第38 页)西夏同样盛行以“圆教”为标榜的华严信仰,大量翻译流传华严宗的根本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在目前“我国保存的西夏文佛经中,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最多”。(6)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56 页。正是在这样浓烈的华严学背景下形成了西夏官方佛教的基础。(7)“西夏流行的官方佛教的基础在于《华严经》以及其‘支流’。”(详见索罗宁:《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4 期,第37 页。)与此同时,在11—12 世纪西藏新译的密法思想传入西夏,并在民间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西夏“民间佛教”的主流信仰。(8)索罗宁:《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4 期,第25 页。两种思想交融激荡,逐渐成为西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论,由于华严和密教的兴盛,过去七佛题材在辽代非常流行,又考虑到西夏佛教与辽代佛教之间紧密的前后呈递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具有深厚华严与密教背景的西夏佛教,也会接受这一新思潮,并最终影响到敦煌传统的造像习惯。
有趣的是,在辽代现存的七佛遗迹中,我们发现其所用名号与莫高窟第365 窟榜题所辨识出的过去七佛名号是一致的:
其一,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七佛造像。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 年),初名“咸熙寺”,至迟在元大德七年(1303 年)改称“奉国寺”。该寺“大雄殿又名七佛殿,是寺内现存唯一的辽代建筑”。(1)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殿调查报告》,《文物》1961 年第2 期,第7 页。据于博实地考察辨识,“大雄殿七佛主尊,……自东向西为迦叶佛、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2)于博:《辽代七佛造像研究——以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七佛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9 页。
其二,朝阳北塔地宫出土辽代石经幢第二节八角座刻过去七佛造像。
朝阳北塔地宫出土辽代石经幢上雕刻的过去七佛造像保存完好,其榜题清晰可见,“从左往右绕依次是:南无释迦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拘那含牟尼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婆尸佛。”(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85 页。
莫高窟第365 窟过去七佛造像名号中,除一身由于漫漶严重无法识别外,其余六身与辽代所见七佛名号皆能对应,且从排列顺序上更是与朝阳北塔地宫所出辽代石经幢刻过去七佛造像一致。因此,可进一步据北塔石经幢七佛造像将莫高窟第365 窟西壁七佛造像名号补齐(从南向北):释迦牟尼佛、迦叶佛、拘那含牟尼佛、拘留孙佛、毗舍浮佛、尸弃佛、毗婆尸佛。
值得注意的是,殿开九间的奉国寺,作为辽代最著名的皇家寺院,前所未有地将七佛巨像供奉在大雄宝殿的主尊位置,为我们思考第365 窟过去七佛造像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奉国寺七佛与第365 窟七佛在排列顺序上却呈现出相当的差异,事实上,由于辽代七佛造像的多元性,导致其图像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七佛名号的排列顺序也因其分布的具体位置和作用不同而有所变化。奉国寺七佛造像的排列具有明显辽代“尊中尚左”的特征,是典型的辽代风格。很显然,敦煌并没有照搬这样的排序方式。
而考察敦煌本地的七佛造像,我们发现,在曹氏归义军时期重修的第309 窟东壁门顶部七佛造像和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北宋淳化二年(997)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相》顶部绘制的七佛造像,从各自所留榜题内容看,都与第365 窟过去七佛造像名号相同且排列顺序一致。(4)赵燕林、赵晓星:《莫高窟第365 窟七佛榜题校释》,《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辑),待刊。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受辽代七佛信仰的影响,西夏人重修的第365 窟将敦煌造像传统中处于次要位置的过去七佛提升到了洞窟主尊的位置,但在七佛造像的排列顺序上却保留了敦煌的传统习惯,并没有将辽代“尊中尚左”的排列方式一并引入。
二、洞窟主尊的次第境界
自唐代起,随着华严和密教信仰的兴盛,过去七佛便开始与陀罗尼神咒取得联系,而宋辽时期所新译的七佛经典也多与陀罗尼神咒有关,这样一来无疑使七佛的现世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从本窟所留七佛榜题内容来看,该窟的重修者似乎更侧重于表达七佛在除地狱业、灭生死之罪方面所具有的灭罪功能,西壁七佛造像便是以此功能为基础而顺利承担了本窟第一重主尊的任务。
然而,从敦煌的造像传统和石窟造像思想的角度考虑,所谓“主尊”,是指一尊能够代表全窟造像完整内涵的尊像。(1)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117 页。由此促使我们对能够代表本窟完整造像含义的单尊式主尊的探寻,考虑到西夏佛教与辽代佛教紧密的前后呈递关系及“绝大多数辽塔‘七加一’佛……即毗卢遮那佛与过去七佛的组合形式”。(2)谷赟:《辽塔研究》,中央美术学院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7 页。笔者推测,当年的设计者在引进七佛主尊的同时,遵循了敦煌石窟设计的传统并参考辽塔的造像特点,另外设置了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这位更深层次的单尊来从义学上统领整个洞窟的造像组合。
自南北朝末年以至唐代,华严完全取代涅槃而成为敦煌石窟造像的主流思潮,但曾经是涅槃学重要内容的“十方三世佛观”则被作为华严学和涅槃学的交汇点保留下来,而且在整个华严学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直至华严构成以“十方三世”为主题的相互含摄。本窟的设计者正是抓住了华严学的这一特色,通过在洞窟中构建“十方三世”结构的方法来凸显法身教主的存在。
(一)毗卢遮那佛义学主尊地位的确立
首先,西壁过去七佛造像为本窟塑造了第一重“十方三世”结构。
密教经典中常以过去七佛代表十方诸佛。在东晋失译杂密经典《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中,除经名的过去七佛之外,从经文的内容来看,在做礼佛仪轨时,实以“十方佛”为礼拜对象,乃至“依经行道时,亦以见‘十方佛’或‘千佛’为成就之验证。”(3)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版出版社,2009 年,第61 页。
如此一来,以密教七佛所代表的十方诸佛搭配过去七佛本身所传递的三世概念则构成完整的“十方三世”境界,这便是本窟的第一重“十方三世”结构。
其次,南北壁的弥勒经变与阿弥陀佛经变为本窟塑造了第二重“十方三世结构” 。
第365 窟南北壁中部主要位置各有一幅经变画。北壁经变画的主尊为倚坐佛像,故当为弥勒经变,与其相对应的南壁经变画中主尊为结跏趺坐佛,手中无药钵或者锡杖等可以表示药师佛的标志性持物,而“阿弥陀通常配置在窟内的南壁”,(1)[日]滨田瑞美著,马歌阳译:《敦煌石窟壁画的窟内配置与图像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辑),待刊。故当为西方净土变,亦即表示阿弥陀净土世界。关于这两类净土,吉藏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义疏》中讲到:
无量(寿)观辨十方佛化,《弥勒经》明三世佛化。
十方佛化即是横化,三世佛化即是竖化。(2)[隋]吉藏:《观无量寿经义疏》卷一,《大正藏》第37 册,第236 页下。
据此可知,阿弥陀佛净土代表“十方”境界,弥勒净土代表“三世”境界。所以,由南北壁的两幅经变画同样传达出了十方三世的概念,这是本窟的第二重“十方三世”结构。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翻阅由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整理而成的《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时发现,该忏仪的起始部分在礼请三身佛之后,紧接着礼请的却是药师佛与阿弥陀佛:
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
圆满报身卢舍那佛;
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十二上愿药师琉璃光佛;
四十八愿阿弥陀佛。(3)[元]慧觉:《华严海印道场忏仪》,(日)京都藏经书院,打印本(上),第26 页。
而且,在华严的多重结构中,“最常见的一重是一面侧壁为‘东方药师净土’,另一面侧壁为‘西方阿弥陀净土’。”(4)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206 页。当然,笔者并非要否定有其他华严结构的存在,事实上以弥勒和阿弥陀作为相对出现的华严结构也是敦煌常见的造像组合形式之一。于此笔者想说明的是,在现有的造像及洞窟空间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更为合理的搭配来彰显七佛背后设计师意欲凸显的义学主尊,这恰是本窟设计的着意所在。相较于皆表达“十方”境界的东方药师净土与西方阿弥陀净土,弥勒与阿弥陀的对置所诠释的“十方三世”概念在义理的表达上似乎更为充实饱满一些,如此也才有了本窟的第二重“十方三世”结构。
本窟正是在这样的设计中为修行者表达着华严的境界,同时也通过这重重的“十方三世”结构在西壁七佛的基础上为本窟塑造出一个可以含摄十方三世的法界主尊——毗卢遮那佛。以三面墙的组合关系来形成毗卢遮那佛的义学主尊地位,既是对原有洞窟的创造性利用,又暗合“法身慧体,究竟无相”(1)[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如来兴显经》卷1,《大正藏》第10 册,第592 页下。的佛教义理,由此彰显了华严教主的神秘存在。
(二)双层主尊设计方案的经典依据
如前所论,本窟在设计上,根据进窟者根行和修为的不同形成了七佛与毗卢遮那佛两个层次的主尊。关于两者的次第关系,辽代新出密教典籍《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则提供了相应的经典依据。此经由中印度来华僧人慈贤三藏译出。该经内容以弥勒菩萨的提问展开,弥勒向世尊询问秘要最上法门 “于何佛闻,师何佛学”(2)[宋]慈贤译:《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卷二,《大正藏》第20 册,第911 页上。,世尊回答说:
向于毗卢遮那如来所,闻如是法作如是观,秘密修行难得正觉。过去诸佛若不依此法门,无由得证于菩提。……乃有过去毗婆尸佛等,垂大慈悲敕大弟子遂告吾曰:“我是过去六佛大弟子也,奉佛敕故来相告,……太子速离宴座食于乳糜,经一月再诣本座必证菩提。”言讫忽然不见。……吾问说是已,依教奉行果证菩提。(3)[宋]慈贤译:《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卷二,《大正藏》第20 册,第911 页上。
由上引经文可知,释迦乃是在过去六佛的指点之下,方得闻听毗卢遮那如来如是妙法而成就菩提正觉的,过去诸佛亦是依此法门修行才得证于菩提,毗卢遮那佛作为法身慧体,过去七佛则代代相承传袭此法,这便是将过去七佛与毗卢遮那佛联系起来的经典依据。换言之,有过去七佛存在之处亦即暗示有毗卢遮那法体慧命的存在。
据杭侃先生研究,辽中京大明塔塔身八佛造像即依据此经典建造。(4)杭侃:《辽中京大明塔上的密宗图像》,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587—595 页。该塔的“第一层塔身每面居中为一身佛像,其中南面正中为大日如来,戴宝冠,结智拳印,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其余七面正中也都是一身坐佛。”(5)杭侃:《辽中京大明塔上的密宗图像》,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587 页。而且,大明塔八面佛造像除了南面的毗卢遮那佛可依穿着、手印做出辨识外,其余七尊表示过去七佛的造像在身型、手印方面几无差别,这一点,正与第365窟西壁禅定七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明塔以八面佛造像的形式向我们直观地呈现了《大教王经》中所传递出来的过去七佛与毗卢遮那佛之间的微妙关系,即由毗卢遮那佛统摄过去七佛,而过去七佛则世世相承传递法身教主的无上妙法。
因此,笔者推测,莫高窟第365 窟双层主尊的设计应当是在吸收了《妙吉祥平等秘密最上观门大教王经》部分经义的同时,参考了依据此经典所塑造的“七加一佛”模式的辽塔造像而来。
三、义学主尊法界性格的补充
按照《华严经》的描述,毗卢遮那佛是真正的世尊,唯一的如来,十方诸佛都围聚在他的周围,成为他的化身,他具有一切自渡渡人的智慧和善权方便的神足变化,“充斥于华严经典中的诸种神通构想和神话交织,在组织华严经学中起着重要作用”(1)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11 页。。本窟的设计者通过重重十方三世结构塑造了义学主尊的特殊存在,自然也会不失时机地去表达该主尊化现十方的境界和不可思议的神通。
(一)十方佛造像与华严教主含摄十方的境界
在西壁七佛顶部有一排佛造像,根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记载,该排佛造像被定名为千佛,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首先,从直观形式上看,上排造像确实符合千佛所谓“直成行,横成列”的空间排列关系,(2)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53 页。但是据赖鹏举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石窟造像的传统是千佛在四壁,十方佛在窟顶。(3)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 年,第55 页。宋以降,千佛图像大多占据四壁位置取代原经变画空间,(4)梁小鹏:《敦煌莫高窟千佛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 年,第18—19 页。洞窟的“东、南、北壁是此时期千佛图像首选位置”。(5)张世奇:《敦煌西夏石窟千佛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5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 页。
其次,笔者在仔细观察西壁绘画时发现,在禅定七佛的南北角除了各有一以赴会形式表现的说法图外,尚有两尊赴会形式的小佛造像(图2、图3),可以认为该赴会佛像即顶部一排佛像的动态化表示,建造者以独特的视角,用这两尊小小的赴会佛来沟通顶部的佛像和主尊,同时也通过赴会佛的动态形式来暗示顶部十方佛赴会的意义。

图2 莫高窟第365窟西壁北侧小赴会佛

图3 莫高窟第365窟西壁南侧小赴会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壁顶部实际是一排以千佛形式排列的赴会十方佛,如此巧妙地设计出来的十方佛造像,正是为再一次表达华严教主含摄十方的“不思议境界”。
(二)十地菩萨与华严修行
在整部《华严经》当中,《十地品》的位置非常特殊。“对华严单行本的研究始于东晋,……在诸种单行经中,最受重视的是‘十地’和‘十住’类”。(1)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43 页。所谓“十地”,是指入地菩萨即已经具有一定修行的菩萨最后修行的十个阶段,从初地起即“过凡夫地,入菩萨位”,(2)[东晋]佛驼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三,《大正藏》第9 册,第544 页下。到第十地“法云地”便可获得佛的一些功德。“十地”或“十住”(3)汤用彤先生指出:“晋宋间称‘十地’曰‘十住’。”(详见氏著:《隋唐佛教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30 页)。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乃是因为“十住”是对整个佛教修行过程从一个方面的总概括,它的地位与“六度”在般若类典籍中的位置相似。据说修行此“十住”之法,可以达到“自致成佛,度脱十方”(4)[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卷五,《大正藏》第10 册,第497 页上。“《渐备一切智德经》相当于晋本《华严经·十地品》,主要论述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详见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9 页)的不思议效果,且“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5)[三国吴]支谦译:《佛说菩萨本业经》卷一,《大正藏》第10 册,第450 页下。简言之,“‘十住’乃是佛的教法,认为过去、未来和现在诸佛由此而生,与把‘般若’作为诸佛之母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6)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283 页。从《华严经·十地品》内容看,该品系菩萨修行的最高阶段。
在第365 窟东壁门柱两侧对称分布五身菩萨,共十身菩萨。考虑到十地修行在《华严经》中的特殊地位及西壁佛坛下方与主尊之间紧密的呼应补充关系,笔者以为,在洪辨发愿文两侧对称分列的各十身菩萨即根据《华严经·十地品》内容绘制用以表达整部《华严经》的修行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修满十地的菩萨可以获得“光明普照十方世界”(7)[后秦]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卷四,《大正藏》第10 册,第528 页下。的神通:
是菩萨坐大莲花座上,即是足下出百万阿僧祇光明,照十方阿鼻地狱等,灭众生苦恼。双膝上放若干光明,悉照十方一切畜生,灭除苦恼。脐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一切饿鬼,灭除苦恼。左右胁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人身,安稳快乐,双手放若干光明,照十方诸阿修罗宫殿。双肩放若干光明,照十方声闻人。项放若干光明,照十方辟支佛。口放若干光明,照十方世界诸菩萨身,乃至住九地者。白毫放若干光明,照十方得位菩萨身,一切魔宫隐蔽不现。顶上放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光明,照十方诸佛大会。(8)[后秦]鸠摩罗什译:《十住经》卷四,《大正藏》第10 册,第528 页下。
这一神通力量与法身佛“放大光明身照十方,诸毛孔出化身,随众生器而开化,令得方便清净道”(1)[东晋]佛驼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大正藏》第9 册,第405 页中。的境界几乎无二无别。因此,将依据《十地品》所绘制的菩萨地修行的十个阶段放置于七佛坛下,既是表达整部华严经的修行过程,同时亦是为了配合整个洞窟来表现修行圆满之后的法身境界。
四、华严海会与莲花藏世界
与中晚唐时期在洞窟中大量绘制经变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夏人在重修洞窟时使用了较多的说法图。据笔者统计,在第365 窟中,共绘制各种不同形式的说法图达七幅之多。除去时代背景的影响,说法图作为洞窟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其与具体洞窟在设计理念上的协调性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第365 窟重修时七幅说法图的设计,理应是与整个洞窟浓厚的华严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七处说法与华严海会

图4 莫高窟第365窟7处说法图
《华严经》相传梵文全本有十万偈,中国大部《华严经》之传译,前有晋本六十卷,后有唐本八十卷。全经之组织,先有智俨大师和法藏大师,依据六十华严,言佛在七处八会讲说华严经,所谓七处指人间三处、天上四处,由于佛在普光法堂两度说法故此一处有两次法会,共为八会。唐本华严译出之后,澄观大师则据此提出七处九会之说,多一会者即佛在普光法堂三度说法。现将两本华严分别宣说之理论对比罗列于下:
第一会:佛在寂灭道场处,说毗卢遮那如来,依正因果法门,有世主妙言品已下六品。
第二会:佛在普光法堂处,说十信法门,有如来名号品已下六品。
第三会:佛在忉利天宫处,说十住法门,有升须弥山顶品已下六品。
第四会:佛在夜摩天宫处,说十行法门,有升夜摩天宫品已下四品。
第五会:佛在兜率天宫处,说十回向法门,有升兜率天宫品已下三品。
第六会:佛在他花自在天宫处,说十地法门,有十地品一品。
第七会:佛第二次重会普光法堂,说因果圆满法门,有十定品已下十一品,前六品明因圆,后五品明果满(此会六十华严没有,为八十华严所列)。
第八会:佛第三次重会普光法堂(在六十华严为第二次),说普贤十大行法,六法顿成,有离世间品一品。
第九会:佛在室罗伐城,逝多园林处,说入法界门,有入法界品一品,而第九会末,佛回归寂灭道场,则显十会圆明,顿彰玄旨。(1)刘果宗:《中国佛教各宗史略》,文津出版社,2001 年,第146—147 页。
然而,无论是六十华严的七处八会,亦或是八十华严的七处九会,其区别主要在于普光法堂讲法之次数,而不变者在七处讲法之地点,且同为人间三处,天上四处。以此为基础考察第365 窟的造像组合关系,笔者以为,本窟的七幅说法图正暗合华严大法的七处讲法之地,如此,本窟便呈现出了以华严教主毗卢遮那佛为主尊而提领《华严经》所载七处说法之地的完整华严结构。
(二)净土为归与莲花藏世界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诸宗竞起,在中国思想史及佛教发展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这一时期,“国家安定,华化渐张,而高僧之艰苦努力,不减于六朝,且教理昌明,组织渐完,玄奘,智顗,弘忍诸师人物伟巨”,(2)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272 页。故佛教义学被推进到了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也为佛教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过于精致的义理思辨使得佛教逐渐脱离一般信众。会昌法难及其后的五代动乱和周世宗灭佛,导致佛教典籍大量损毁流失,再加上隋唐之后僧才凋零,“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再也没有产生一个佛门大师”,(3)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371 页。义学寂寞,整个佛教处于颓势。
在义学诸宗盛极而衰之时,明心见性的禅宗和称名念佛的净土宗却迅速传播。与净土宗相比,禅宗虽受上层士大夫阶层追捧,但狂禅泛滥,亦属勉强维持。念佛修净土成为佛教发展的唯一出路。(1)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371 页。因此,自唐末五代永明延寿大师提倡禅净合流之后,“各宗对净土都提倡兼修,形成了各宗汇归净土的潮流。”(2)陈扬炯:《中国净土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371 页。在这一大趋势之下,浓厚的净土意味成为此后佛教发展的鲜明特色,西夏佛教的成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在这个基本认识下,我们来回观第365 窟的整体设计,除了南北壁中心位置直接表现净土世界的两幅经变画之外,东壁三幅说法图和南北壁上部的两幅说法图同样被渲染了浓厚的净土色彩,具有鲜明净土意味的莲花、化生童子及端坐在莲花上的听法天人等遍布其间。可以认为,整个洞窟的设计是在净土的基调下展开的。
设计者除布置了上述可以直观展现净土境界的经变画和说法图外,又根据净土的往生义在诸经变画和说法图周围绘制了众多端坐于莲花台上可以代表净土境界的听法天人,他们的存在实际起到了连贯整个洞窟的客观作用。诸莲花以一水相连最终交汇于西壁佛坛下部对称分布十身菩萨的中轴线上。
此处西夏重绘壁画因年代久远而脱落,所绘内容已无从辨识。考虑到整个洞窟的华严结构,笔者大胆推测西夏人在重绘时或仿照莫高窟第44 窟于中心塔柱前塑大莲花以表现华严莲花藏世界的方式于此位置绘制了具有同样含义的大莲花,有此含藏无量佛国世界的大莲华,方才构成圆满无碍的“华藏世界”。如经中所言:
彼香水海中有大莲华,名香幢光明庄严,持此莲花藏庄严世界海。(3)[东晋]佛驼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大正藏》第9 册,第412 页上。
整个洞窟在此大莲花的连贯下自然而然就“成了一种范围无限广大而又互相包容,互相贯通而无个别区分的大法界。”(4)吕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 年,第192 页。
莫高窟第365 窟在浓厚的净土基调下展开对华严教理的诠释,而最终又以华严的莲花藏净土作为修行的归宿,起于净土,归于净土。
五、余论
处在敦煌莫高窟艺术发展晚期的西夏,虽然顺承了整个时代趋于简约化的风潮,在艺术创作中直观地给人以建筑程式化、人物形象公式化的特点,但构图的简化丝毫不影响西夏人在洞窟的设计中对于精深佛理的追求与诠释。
正如巫鸿先生所言:“每次重修实际上都重新定义了一个石窟。”(1)[美]巫鸿:《美术史十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6 年,第60 页。西夏人在重修洞窟时,会选择性地保留下前代的部分设计,以配合新设计洞窟的义理表达。换言之,在重修洞窟过程中,凡是被选择性保留下来的前代造像,大多可以融入到重修时对洞窟所下新定义中。因此,对于洞窟重修思想的研究,无论是部分重修洞窟亦或是整体重修洞窟,都应从全局视角对整个洞窟的造像布局和设计理念进行思考。
在诸宗汇归净土的大潮中,西夏佛教的发展亦与净土思想密切相关,表现在洞窟的设计上,便是这一时期重修的洞窟多以净土色彩作为整个洞窟的基调。
(作者附记:本文使用图版版权归敦煌研究院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