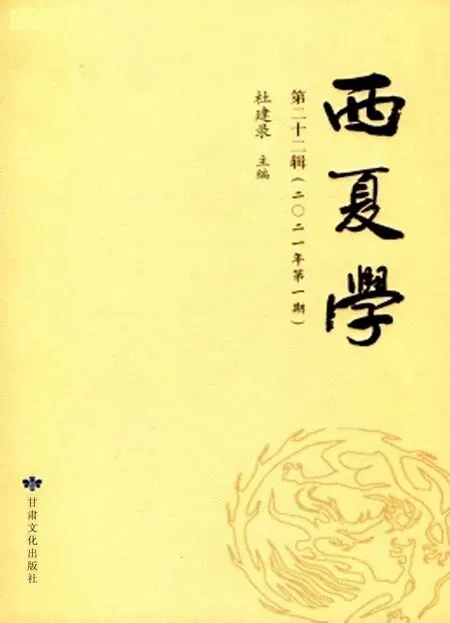莫高窟第464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
——莫高窟第464 窟研究之三
王慧慧
第464 窟后室壁画的内容相对单一:窟顶绘五佛,西、南、北壁绘观音现身,东壁门上绘六字真言、门两侧绘花卉装饰纹样(1)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 年,第170—171 页。(图1)。因题材简单,以往研究仅涉及观音现身,认为是依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以下简称《观音经》)绘制。

图1 464窟窟室内景
在历代观音的图像中,观音一般有两类化身:一类是为了救度众生,基于善巧方便示现各种形式的化身,这些化身见于《观音经》《首楞严经》和《大乘庄严宝王经》(以下称《宝王经》),其他佛经也有零星的记载。第二类出现于密教经典,观音在这些经典中通常现多首、多臂相,手中持有各种象征性的法器,宣说感应不可思议的神咒。本文试图从不同经典对观音现身描述的差异,结合第464 窟的图像,探讨此窟绘制的图像依据和洞窟的营建思想。
一、前贤对第464窟图像的辨识及存在的问题
据罗华庆统计,敦煌石窟有关观音现身内容的壁画有29 铺,绢画有7 幅,纸画有5 卷(1)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 年第3 期,第62—63 页,主要依据《观音经》绘制,莫高窟第464 窟亦是其中的一铺。
有关第464 窟观音现身的研究成果目前仅有《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一书对这些图像的辨识(2)敦煌研究院编,梁尉英主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年,第212—216 页。。根据梁先生的研究,按照正壁、北壁(右壁)、南壁(左壁)、自上而下、自左至右的顺序,观音现身的内容分别为:声闻、佛、佛、宰官、帝释、自在天、大自在天、不明,毗沙门天、人王、优婆塞、长者、居士、天,比丘比丘尼、妇女、四天王、比丘、童男童女、药叉(图2、3、4)。

图2 莫高窟第464窟-主室西壁

图3 莫高窟第464窟-主室北壁

图4 莫高窟第464窟-主室南壁
将以上定名与前述《观音经》和《首楞严经》中所记载的观音现身的名称做一对照,我们发现这些名称与《观音经》一致的有19 个,与《首楞严经》一致的有20 个,《首楞严经》中多了四天王身。对此,梁先生作如下解释:“此绘四天王,是据《首楞严经》卷六之说,《观音经》则只举出毗沙门天王,即北方多闻天王,本窟北壁即绘毗沙门天王身。此窟三十二应身变则取两经之说,显然是仰重毗沙门天王。”(1)敦煌研究院编,梁尉英主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年,第215 页。
这个解释稍显牵强,若此,在没有其他显著差别的前提下,不如说第464 窟观音现身依据《首楞严经》绘制的可能性更大,而不是《观音经》。
这就涉及到对这些观音现身的定名是否准确的问题。事实上,其内容被定为《观音经》更多地是承继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固有观念,没有考虑其特殊性,也缺少结合洞窟其他题材的综合研究。敦煌石窟有明确观音现身题记的洞窟有两个:莫高窟第45 窟和西千佛洞第15 窟(2)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 年第3 期,第60—61 页。,分别有21 条和12 条题记,其他洞窟的观音现身大都据此用图像对比、排除等方法定名的。而观音现身和观音救难内容的繁多又使得画面普遍存在与经文不能一一对应、不能完全列举,画面之间相互混淆、绘制内容没有统一严格规范和标准的问题,这给画面辨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第464 窟延续了以往的研究方法,辨别图像时首先将其纳入《观音经》的研究范畴,然后采用排除、对比等方法对图像进行断定。这样即使图像出现与经文无法对应、无法辨别甚至完全与以往的题材完全不同的情况,也会给出附会的解释,且笼统地将这些情况归为画面布局、空间限制、画师差异等原因造成。
我们列举几处有疑问的地方:一、如若定名无误,画面中出现两次毗沙门天王、两次比丘与以往图像不相符。二、画面解读标准不统一,宰官、自在天、大自在天、人王、居士的图像特征非常相似,却被判定为天人两种尊格。三、被判定为四天王身的图像中间一身明显不是天王,其服饰与前述宰官、自在天、大自在天、人王、居士的图像特征一致。
既然画面本身的辨识和所依据的经典都存疑,那么,从图像本身的藩篱中脱离出来,综合考虑整窟的营建思想及主题,考察图像之间的关系对于确立石窟的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第464窟观音现身图像的解读
《观音经》的图像自隋朝出现以来,一直遵循着两种模式,一种为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另一种为独立布局,由三部分组成:以观音菩萨为中心,左右分别绘制观音现身和观音救难的内容。无论哪种模式,观音作为一个具备无上神力的大菩萨,它的最大特性并不在于可以变化形象,而在于它的救难特征,观音救难永远是观音信仰的核心。敦煌石窟壁画和绢画中的观音图像充分说明了这一特征,即在第464 窟之前,石窟中普遍存在只绘制观音救难而不绘制观音现身的图像,而从未出现过只绘制观音现身而不绘制观音救难的图像。第464 窟的观音现身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唯一一铺完全抛开观音救难,而仅绘观音现身说法内容的图像。
除此以外,第464 窟画面还有如下特点:一、布局新颖,画面疏朗,构图简单,弱化主尊。二、画法有继承也有创新,出现明显的与之前人物构图和表现方式不一样的画面,如在装饰上添加云纹图样,人物坐具、手势较为特殊,出现“上师”像等。三、此窟后室南北长3.4 米,宽2.75 米(1)石璋如:《莫高窟形》(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 年,第206 页。,用如此大的壁面仅表现20 幅画面的内容,这是前所未有的,从整个墙面的大小和画面一气呵成的特点推知,绘制者在设计构图时就规划了20 幅画面,而不是32 幅。
《观音经》共记载观音有三十三现身(2)最早的《法华经》译本《正法华经》中观音的化身远少于三十三身,只有17 种,分别为佛、菩萨、缘觉、声闻、婆罗门、乾达婆、鬼神、富豪、提婆、转轮圣王、罗刹、将军、沙门梵志、金刚手、隐士、仙人和儒童。,分别有佛、辟支佛身、声闻身、梵王身、帝释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毗沙门身、小王身、长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罗门身、比丘身、比丘尼身、优婆塞、优婆夷身、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执金刚身。
观音化身也是《首楞严经》和《宝王经》中的重点。《首楞严经》以《观音经》为范本,提到观音有三十二种化身,大多效仿《观音经》的内容,数量、身形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首楞严经》将《观音经》中的辟支佛身细分为独觉身和缘觉身,毗沙门天王身改为四天王身,有四大王国太子身,无迦楼罗身和执金刚神身。此外,《观音经》《首楞严经》都保证信仰者能够通过念诵观音脱离各种危难、寻得各种解脱,经文中明确记有观音救难和十四种无畏力的内容。如《观音经》中观音救火难、鬼难、坠落难、被推悬崖难、贼难、枷锁难、毒药难、罗刹难、野兽难、蛇蝎难、雷雹难等,《首楞严经》描述观音有救火难、水难、贼难、枷锁难等十四无畏力。
而《宝王经》也描述了观音化现,分别为佛身、菩萨身、日天子、月天子、火天身、水天身、风天身、龙身等共计二十身。值得注意的是,与前述三十三身或三十二身化身相比,此经提及更多的是印度教神祗,这显然是试图表现出这位菩萨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世间的怙主。经中也特别强调观音能生出诸天这一特点:
观自在菩萨,于其眼中而出日月,额中出大自在天,肩出梵王天,心出那罗延天,牙出大辩才天,口出风天,脐出地天,腹出水天,观自在身出生如是诸天。
但此经中没有观音救难的内容。
前文已从整个墙面的大小和画面一气呵成的特点推知,绘制者在构图时就规划了20 幅画面,这在数量上与《宝王经》记录的观音现身数量最为接近。另外,此窟无观音救难的内容又与《宝王经》中只讲述观音现身、而无具体列举观音救难的内容相符。再联系到东壁门上的“六字真言”,笔者认为画面应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
《宝王经》是北宋天息灾于公元983 年翻译的经典(1)[清]徐崧:《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年,第7890—7892 页。。这部经讲述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应除盖障菩萨所问,说观自在菩萨如何入阿鼻地狱及饿鬼大城、救度受苦众生,如何化现种种不可思议威力,如何求得“六字大明咒”、诵写“六字大明咒”的种种不可思议无量功德以及观音菩萨的威力来源等。经中首次将观音提升到了至尊的地位,如经中描述观音创造日月并生成诸天,强调观音的光辉比任何其他菩萨或佛都要耀眼,她的无量福德,佛都不能尽数等。《宝王经》是以宣扬观音思想为主题的佛经,有观音现身,是“六字大明咒”的经文来源,这与第464窟的主题非常吻合。
同时经中还提到了观音现阿苏啰身、婆罗门身、蜂身、云马王身等,并特别指出“欲救度如是有情证菩提道,随有情类现身说法”,可见现身的种类很多。在其他涉及观音现身的经典里,此现象表现也尤为明显。如《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五记为: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一座中随诸听众,或见菩萨说法,或见佛说法,或见辟支佛说法,或见声闻说法,或见帝释,或见梵王,或见摩醯首罗,或见围纽天,或见四天王,或见转轮圣王,或见沙门,或见婆罗门,或见刹利,或见毗舍、首陀,或见居士,或见长者,或见坐宝台中,或见坐莲华上,或见行在地上,或见飞腾虚空,或见说法,或入三昧。大王,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度众生,无一形相及一威仪不示现者。
可见观音也可以化现摩醯首罗、围纽天、转轮圣王、刹利、毗舍、首陀等,这些形象与传统的《观音普门品》中的小王、长者、居士、比丘、比丘尼等显教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但也不违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为度众生,无一形相及一威仪不示现者”的初衷,随着显密教的并行发展与相互融合,形式上受到的冲击,显密图像融合是必然的。作为新出现的观音现身样式,在没有新版本参照的情况下,一方面难以摆脱旧有传统的羁绊,必然吸纳原有的一些元素,另一方面为了创新也会吸收当时流行的题材,这样就会出现图像难以识别或者各经典中的图像相互交叉的现象。
由此,根据《宝王经》,笔者依次对各壁面的内容进行了辨识,辨识结果如下(图5-1、图5-2):

图5 -2 根据《宝王经》辨识的观音现身图表

图5 -1 根据《观音经》辨识的观音现身图表图
正壁中心的位置有割痕,原绘制一幅“水月观音”图(1)王慧慧:《莫高窟第464 窟被盗史实及被盗壁画的学术价值——莫高窟第464 窟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132 页。,笔者认为,此画面一方面表现了窟内的主题思想为观音信仰,另一方面当表现的是《宝王经》中观音化现的菩萨身。
④、⑥、⑦画面相似,皆为头戴冠饰、身穿圆领长袍,结特殊手印,或盘在方毯之上,或坐于坐具之上的形象。同样的形象见于⑩、⑬和⑰的中心人物,值得注意的是⑬原定的居士身(图6),“此绘居士,眉目清秀,席地而坐,手执扇结印,儒雅清高”(2)敦煌研究院编,梁尉英主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 年,第214 页。,判别依据应该与维摩诘居士执扇有关,但仔细辨别人物手中的持物,笔者认为不是“扇”,应当是“圭”或者“笏”,这种持物在佛教壁画中多为天众或国王所持之物。此6 身画面原分别被判定为宰官、自在天、大自在天、人王、居士、四天王,其中自在天、大自在天、四天王属于天众,宰官、人王、居士属于世俗人物,同样的画面特征出现如此悬殊的差别有失合理。

图6 北壁原定居士身
事实上,这种人物形象和持物在西夏壁画中非常流行,在北宋以来形成的水陆画、寺观壁画中更频繁出现,多表现为国王或十二天、二十八星宿等天众形象。水陆法会传说起源于梁武帝时期,兴盛于唐宋,流行于明清,水陆画就是伴随水陆法会产生的宗教画。水陆画到两宋时,已经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规模和体系,如山西繁峙金代岩山寺正殿原本即水陆殿,里面曾绘制成套的水陆画图卷,可惜壁画已毁(1)[金]尹安祉:《建福院碑记》,李晶明:《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三晋出版社,2010 年,第19 页。。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水陆画壁画是元代山西青龙寺水陆壁画,最完整最全的水陆画为明代山西宝宁寺水陆画。这些水陆画中绘制的欲界十二天:大自在天、帝释天、火天、梵天、日天、毗沙门天、焰魔天、地天、月天、风天、水天、罗刹天等都是头戴冠饰,身穿袍服,足登云履,双手执圭(笏)的形象,且有题记(2)伪满皇宫博物院编著:《大明天顺皇家水陆画赏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6 年5 月。。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中也发现有题记的日天、水天等天神形象,虽不甚清晰,但也是头戴冠、身穿袍服的形象(3)陈爱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 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敦煌研究》2016 年第6 期,第84 页。。虽然目前没有保存下来元代以前的水陆画,但联系到水陆画与佛教画的密切性,敦煌文献中存有大量唐、五代有关施食,祈请神祗等与水陆仪文相似的文献(4)谢生保、谢静:《敦煌遗画与水陆画——敦煌唐五代时期水陆法会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6 年第4 期,第1—7 页。,说明水陆法会也很兴盛。再者,敦煌西夏石窟如莫高窟第61 窟炽盛光佛(图7)、榆林窟第3 窟水月观音图中也出现多幅执圭(笏)、头戴冠、身穿袍服的形象,说明西夏时期此类形象非常普遍且流行。如此,这6 幅具有相似形象的画面都应归入了一个体系,也就是说,被判定为人王、居士、宰官的形象应该与大自在天、自在天一样属于天众人物。因画面的高度相似性,笔者无法确认各尊格的名称,按照佛经顺序推测④、⑥、⑦分别为梵王、某天(《宝王经》无自在天)、大自在天,⑩、⑬为日天、月天,⑰为某天众。

图7 第61窟炽盛光佛中的星宿
⑧推测为那罗延天,根据经文顺序确定,不定,此画面与⑪左上角人物的冠饰、衣着皆相似,也应为天众。⑫画面特征不明显,原定为长者,也可能是宰官等世俗人物。⑮、⑯原判定为比丘、比丘尼、妇女身。此妇女身头冠华丽,坐于方具之上,与前述诸天神的卧具相似,也有可能表现的是水天,如若不是,这两幅应该是吸收传统绘画表现形式,比丘、比丘尼身后的人物可能为宰官。
⑲原判定为童男、童女身,当误,观音化现的人物是画面的主体,前面皆为跪拜者,不应把跪拜者作为观音的现身,此处当表现的现父母身。
⑱为一世俗人物形象,无头光,戴莲花帽,身后有三身侍从,一身双手持大伞盖,一身手持圆形团扇,还有一身为比丘,双手合十(图8),此画面原判定为比丘身,笔者认为可能是《宝王经》中讲的现“阿苏啰身”。经文在讲述完观音现身以后,紧接着有这样的描述:

图8 上师像
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随彼有情应可度者。如是现身而为说法,救诸有情皆令当证如来涅槃之地。是时宝手菩萨白世尊言,我未曾见闻如是不可思议希有,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实未曾有。
宝手菩萨对观音可以“随彼有情应可度者”现身表示怀疑,于是佛举了一个例子:
南赡部洲为金刚窟,彼有无数百千万俱胝那庾多阿苏啰止住其中。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现阿苏啰身,为是阿苏啰说此《大乘庄严宝王经》。阿苏啰众得闻是经,皆发慈善之心,而以手掌捧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足,听斯正法皆得安乐。若人得闻如是经王而能读诵,是人若有五无间业皆得消除,临命终时有十二如来,而来迎之告是人言。善男子,勿应恐怖,汝既闻是《大乘庄严宝王经》,示种种道往生极乐世界。有微妙盖,天冠珥珰,上妙衣服,现如是相,命终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宝手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最胜无比现阿苏啰身,令彼阿苏啰当得涅槃之地。
由上可知,观音化身“阿苏啰”,为其他百千万“阿苏啰”众宣讲《宝王经》,且现如是相时,有“有微妙盖,天冠珥珰,上妙衣服”。第464 窟南壁左下方的“上师”像头戴莲花帽,后有侍者执大伞盖,与经文“微妙盖,天冠”记录一致。推断“上师”的形象应该就是观音所变现的“阿苏啰”。
笔者没有查到有关“阿苏啰”的准确解释(1)阿苏啰的概念不明,出现的次数不多,有时跟“阿修罗”混同,根据此经上下文,此处当与阿修罗含义无关。,但根据佛经上下文阿苏啰住在“南赡部洲”,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就在“南赡部洲”。《宝王经》卷二又提到大力阿苏啰王在铁地,宫中有无数眷属,但多是背伛矬陋,因给佛施食垢黑不净被关此处。观音于是给大力阿苏啰讲施食如来的巨大功德,阿苏啰发无上菩提之心,观音授记其未来成佛,号吉祥如来,当证六字大明总持之门。
由以上两条得知,阿苏啰是普通圣众,观音授记将来会成佛,且证六字大明咒。观音现身“阿苏啰”为众“阿苏啰”讲授《宝王经》,应是讲经说法的形象,在绘制讲经说法像时很可能就借用了西夏流行的“上师”像,有关“上师”像的出现及流行可以参考谢继胜的相关文章(2)谢继胜:《莫高窟第465 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2 年第3 期,第69—79 页。,上师形象应该和西夏的国师、帝师、上师的制度有密切关系,是西夏帝师、国师、上师制度对佛教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之一。
这样,“阿苏啰”作为观音的现身,而且是“最胜无比”的现身,被绘制在画面就非常合理。联系到水月观音的救亡思想,此窟很可能是一个礼忏道场,亡者见如是相,将往生极乐世界。
综上,笔者认为第464 窟“观音现身”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较之前贤成果,其合理性在于:
第一,将相同画面的内容纳入同一个尊格体系中考量。
第二,《观音经》《楞严经》《宝王经》三经中,只有《宝王经》有现“父母身”,⑲明显是现“父母身”。
第三,对“上师像”的出现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总之,《宝王经》作为一种新的经典,经中观音所现诸身如水天、火天、风天、那罗延天等与传统观音现身的图像有很大的区别,可能因无可参照粉本,画家只好延续唐宋以来传统画法,并借鉴宋西夏时流行的元素及水陆法会的一些画法。
三、《大乘庄严宝王经》与整窟的营建思想
前文主要从构图和画面的特殊性来论证第464 窟观音现身图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下面分析一下窟室其他壁画与《宝王经》的关系。
窟顶绘制的是五方佛。五佛思想是直接依据《金光明经》《观佛三昧海经》所说的四佛思想发展而来(1)[日]松长有庆:《两部マンダffl(曼陀罗)的系谱》,日本种智院大学密教学会编,世界佛学名著译丛编委会译《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5:西藏密教研究》,华宇出版社,1988 年,第186—187 页。,四方佛图像出现于北朝,在初盛唐时期形成了窟顶四披绘千佛、中央绘四方佛说法、周围有十方佛赴会的构图(2)殷光明:《敦煌显密五方佛图像的转变与法身思想》,《敦煌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7—20 页。。吐蕃时期出现了金刚界五方佛的雏形,但还未有成熟的密教五方佛图像(3)郭佑孟:《敦煌吐蕃时期洞窟的图像结构——以莫高窟360 和361 窟为题》,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126—145 页。赵晓星:《莫高窟第361 窟待定名图像之考证——莫高窟第361 窟研究之一》,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183—190 页。。直至五代、宋时期经过显密五方佛图像的转变,才形成纯正的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密教五方佛(4)殷光明:《敦煌显密五方佛图像的转变与法身思想》,《敦煌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7—20 页。。从图像上看,此窟窟顶中央佛的手印为智拳印,四披佛的手印分别为触地印、与愿印、禅定印、无畏印,虽然各尊像没有身色变化,也没有台座,但是手印与大日如来、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的手印完全一致,故可判断其为金刚界五方佛。
此五方佛的显著特点是显密结合,中原艺术风格与藏传艺术风格相结合,中心大日如来有藏传绘画特征,其他四佛均为汉式风格。从特点上来看,它处于汉藏艺术结合、显密融合的时期,与莫高窟第465 窟窟顶,榆林窟第2 窟、第4 窟部分曼荼罗上部,东千佛洞第2 窟窟顶等五方佛,以及黑水城唐卡中出现在金刚、度母、明王甚至上师等最上方的五方佛略有不同,比较特殊。这与敦煌佛教一直是以汉传体系为主流的佛教,随着密教的发展,不少密教经典将显教的神祗及其功能移植到密教经典中,开始吸收或利用显教的图像内容和构图形式有关。考虑到此窟与第465 窟为同时代作品(1)谢继胜:《莫高窟第465 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中国藏学》2002 年第3 期,第69—79 页。,第465 窟的五方佛身色明显,有台座,已然是标准的成熟的金刚界五方佛。而第464 窟之所以没有完全绘制藏传艺术风格的五方佛,可能是与整窟的显教题材紧密相连,观音现身的内容虽然出自密教经典《宝王经》,但是毕竟观音现身更多表现的是显教内容。
东壁门上绘制的是六字真言(图9),六字真言最早即出自《宝王经》,此经是修行观音菩萨修行法门和六字大明咒所依的重要经典。《宝王经》形成于公元4 世纪末或5 世纪初(2)转引自张同标:《尼泊尔三乘物观音造像与成就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 年第5 期,第36 页。,在9 世纪成书的藏文佛经目录中已有记载,10 世纪末天息灾将其从梵文翻译成汉文,目前保存的写本有最早的7 世纪初期的吉尔吉特梵文写本、12 世纪末尼泊尔贝叶梵文写本、14 世纪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贝叶写本和15 世纪以尼泊尔写本为基础的改编本(3)张同标:《大乘庄严宝王经与观音图像》,《中国美术研究》2015 年第2 期,第91 页。,但真正对佛教信仰发生影响,经文特有的观音形象见诸图像,却是比较晚期的。据谢继胜研究,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图像构成固定对应关系当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的蒙元时期(4)谢继胜:《平措林六体碑与蒙元真言碑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九本,第四分,2019 年12 月,第672 页。。此窟的六字真言为兰札体梵字真言早期式样,也是目前发现比较早的兰札体六字真言。

图9 莫高窟第464窟主室东壁门上
从敦煌的情况看,同时期前后出现的六字真言有三幅,分别在第464 窟、第95 窟和榆林窟第29 窟。这三幅六字真言的表现样式不同,第95 窟和榆林窟第29 窟是以六字真言种子曼陀罗的形式出现,时间当比第464 窟晚,第464 窟六字真言非曼陀罗形式,还未从《宝王经》中脱胎出来,与《宝王经》仍然紧密相连。但三幅六字真言的共同特点是皆与水月观音对应出现:第464 窟东壁门上的六字观音与西壁正中的水月观音呼应(5)王慧慧:《莫高窟第464 窟被盗史实及被盗壁画的学术价值》,《敦煌研究》2020 年第4 期,第129—135 页。,第95 窟窟顶种子字曼荼罗前有水月观音,榆林窟第29 窟有两幅水月观音。五代宋时期,水月观音信仰兴盛,这反映在石窟中大量水月观音图像的出现,特别是在陕北及敦煌石窟。水月观音的经典及图像都具有浓郁的荐亡色彩(6)常红红:《西夏水月观音中荐亡图像考释——以东千佛洞第二窟壁画为中心》,《大足学刊》第三辑,2019 年,第312—313 页。,其信仰的流行与民间丧葬仪式有很大的关系,即与观音的度亡思想有关。这与《宝王经》中观音入阿鼻地狱及饿鬼大城、救度受苦众生,由现世救度功能转向地狱救度功能的思想完全一致,这或许是六字真言一开始就与水月观音呼应出现的原因。笔者推测,这几处水月观音与六字真言结合的洞窟很可能都是从事礼忏度亡等佛事活动的道场。
以上分析可知,六字真言与《宝王经》密切相关,而此窟窟顶的花卉图案又将五方佛与六字真言及门两侧的方框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说明了此处五方佛与六字真言融合的重要意义。
五方佛是密教仪式化的体现,仪式需要有空间和时间,五方佛绘在窟顶有统摄全局,强化空间和仪式的意义,此处五方佛与榆林窟窟顶第2 窟五方佛、东千佛洞第2 窟窟顶五方佛等意义是一样的。同时,也可能与六字真言本身密切相关,后期出现的经典《性命圭旨》或许可体现这一关系。《性命圭旨》是道教著名经典, 成书时间为宋至明朝,相传出自尹真人高弟之手。此书主张破除三教门户之见,宗罗三教历代精义,有明显的三教合一思想。有意思的是第464 窟出土的编号464:52 的残片一纸,墨写行书西夏文,存4 行,据研究此件为道教文献,且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件西夏文道教文献(1)《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三),《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第424 页。。《伯希和石窟笔记》曾对B159 号洞摆于祭坛上的诸多小物件进行了记录,其中有一件经文记为:“性命圭旨,被列于了尹喜的名下,扫叶山房版本。该书的式样相当古老。据我所知,它是用半口语化的语言写成的,如同宋代哲学家们的那样语言一样。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尚有待于对它进行研究(2)《伯希和石窟笔记》第361—362 页”。虽然我们不能追溯伯希和所记的这件文献的历史,但此记录说明了直到清末,敦煌地区仍在流行此道教经典。
此书中收录了佛教《观音密咒图》,将观音六字真言与气功修炼相结合,其文中有如下记载:
此咒是观音菩萨微妙心印。若人书写六字大明咒者,即同书写三藏法宝;若人得念六字大明咒者,则同讽诵七轴灵文。又能开智慧门,能救百难苦,三世业冤,悉皆清静,一切罪障,尽得消除,解脱生死,安乐法身。然而念咒亦有密诀。故第一声中叫唵之,乃以呼吾身毗卢遮那佛也。第二声东而嘛之,乃以呼吾身不动尊佛也。第三声南而呢之,乃以呼吾身宝生佛也。第四声西而叭之,乃以呼吾身无量寿佛也。第五声北而咪之,乃以呼吾身不空成就佛也。第六声复上返于喉而作吽者,乃以呼吾身大势至金刚也。久则五炁归元,即成就不思议功德而证圆通也。(3)尹真人密授:《性命圭旨》,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79 页。
此内容说明了六字真言 “唵嘛尼呗咪吽”的梵字分别与五方佛一一对应,可见他们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门两侧分别画一长条框,里面原绘有装饰花卉,后中下部的花卉已被一层薄薄的白灰粉刷掉,代以书写大量的回鹘文文字。据研究这些回鹘文题记是一首回鹘文佛教诗歌,整篇题记以押头韵诗写成(1)皮特·茨默著,王平先译:《解读敦煌文献B464:67 之回鹘文诗歌》,《敦煌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31—34 页。张铁山、彭金章、皮特·茨默:《莫高窟北区B464 窟回鹘文题记研究报告》,《敦煌研究》2018 年第3 期,第44—54 页。,回鹘文与花卉图样应该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在东壁门两侧这个位置仅绘制花卉而不表现任何主题在石窟中比较少见,或许是在某种礼忏仪式中起到经幡的作用也未可知。
四、《大乘庄严宝王经》流传及相关问题
中国佛教典籍的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译成《本生心地观经》之后就中断了,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才复兴,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是天竺三藏沙门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2)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 年,第384 页。。《瑜伽大教王经》《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佛说大乘八大曼拏罗经》等即是此时由天息灾等人奉诏翻译。
史书上载天息灾、施护到宋廷之前曾被敦煌当时的执政者曹延禄“固留敦煌不遣数月”(3)[清]徐崧:《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年,第7891—7892 页。“(雍熙)二年(985),帝览所译经,诏宰相曰,译经辞义圆好,天息灾等三人及此地数僧, 皆深通梵学,得翻传之体,遂诏天息灾、法天、施护并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又诏译经月给酥、酪、钱有差。法贤年十二依本国密林寺达声明学,从父兄施护亦出家,法贤语之曰,古圣贤师皆译梵从华而作佛事。即相与从北天竺国诣中国,至燉煌,其王固留不遣数月,因弃锡杖瓶盂,惟持梵夹以至,仍号明教大师……雍熙四年诏改名法贤,累加试光禄卿朝奉大夫。”,据郑炳林考证其滞留的时间当在980年(4)郑炳林、陈玉柱:《敦煌古藏文P.T.55<解梦书>研究》,《兰州学刊》2009 年第5 期,第1—2 页。。天息灾和施护在敦煌的短暂逗留,给敦煌的佛教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敦煌莫高窟窟顶“天王堂”的营建就与天息灾在敦煌的活动有关,天王堂穹隆体幻化网曼荼罗图像和窟内土坛上胎藏大日与八大菩萨图像粉本可能也是天息灾带来的(5)阮丽:《莫高窟天王堂图像辨识》,《敦煌研究》2013 年第5 期,第40—50 页。。
《宝王经》在敦煌地区的出现或许可追溯至此时,即10 世纪末。但第464 窟前室白壁残存有西夏文题记,这些西夏文书写在主室壁画绘制之前,那么主室的年代必然为西夏,则推测最早在11 世纪后期,随着汉文经典和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此经逐渐在敦煌传开。目前藏经洞出土文献、北区出土文献及整个河西地区,都没有发现有关《宝王经》的文献遗存,但第464 窟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出现说明了《宝王经》曾经在敦煌地区传播的史实,大概同时期吐鲁番地区也出现了这一题材。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9 窟券顶绘有多幅壁画,窟顶汉文题记的释读表明最少有6 幅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6)陈爱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 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考释》,《敦煌研究》,2016 年第6 期,第88 页。,这是在石窟壁画,乃至佛教绘画的其他作品中,首次、也是唯一发现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变。据研究,此幅经变是根据《宝王经》汉文本绘制,年代推断在11 世纪前后至13 世纪初。与敦煌相似,在吐鲁番地区也未发现与此经相关的文献资料。
加上第464 窟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目前能确认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变就有两幅了。柏孜克里克第17窟的表现方式是传统的佛说法图样式,而莫高窟第464窟是把握了经文的主旨和核心,绘制了观音现身和六字真言的内容,从现状看,似乎《宝王经》并未得到广泛的流行和传播,但从《宝王经》中脱胎出来的六字真言的发展来看,它的影响力应该是巨大的。
六字真言有莫高窟第464 窟横写的,有辽道宗九年(1093)张文藻墓中竖写的(1)沙武田、李晓风:《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时代探析》,《敦煌学辑刊》2019 年第4 期,第91 页。,更多的是种子字曼陀罗,如莫高窟第95 窟、榆林窟第29 窟窟顶。六字真言种子字曼陀罗的表现形式是六字真言从《宝王经》脱离的初期形态,是佛教密教真言化的见证(2)谢继胜:《平措林六体碑与蒙元真言碑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九本,第四分,2019 年12 月,第671 页。。到西夏中后期,随着六字真言经咒与流行的大乘佛教净土宗或禅宗等念诵仪轨的兼容,使得六字真言信仰蔓延开来,并从种子字曼荼罗的形式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纯的念诵真言。13 世纪末至14 世纪,六字真言与四臂观音图像才逐渐形成了固定对应关系,并产生了大量多体文字合并书写的现象,如莫高窟第464窟前室五体、金昌市永昌县圣容寺后山六体、北京居庸关云台六体等多语言文字合并书写的六字真言(3)谢继胜:《平措林六体碑与蒙元真言碑源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九本,第四分,2019 年12 月,第690—691 页。,发展到最后,六字真言成为藏区普遍的念诵经咒。
从现今所见文献看,西夏时期与六字真言相关的经典也有很多,有《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圣六字太明王心咒》《六字大明王功德略》等,大都是《宝王经》的节录或咒语的合集。其中《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是完全出自《宝王经》卷三、卷四的内容,不仅有单行本,还被西夏僧人收录在《密咒圆因往生集》(4)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198—199 页。,可见当时《宝王经》仍在通行。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知,六字真言从《宝王经》译出的10 世纪末到14 世纪近400 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被遗忘,甚至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六字真言所依据根本经典就是《宝王经》,六字真言的发展从侧面也反映了《宝王经》的流行。但是为什么除了六字真言,反映《宝王经》内容的经变和其他图像却比较少呢?笔者推测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宝王经》本身的内容有关系,《宝王经》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介绍观音救度的功能,另一部分是解释观音拥有这些能力的原因即六字真言的重要性。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六字真言长盛不衰的历史,而观音救度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和表现的原因可能与经中介绍此部分内容比较散乱有关,当然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与11—13 世纪观音信仰的极度流行有关,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水月观音、绿度母等观音思想占据主流,观音不仅具有现世救度功能,而且具备了地狱救度功能,其能量和地位甚至超越了佛。《宝王经》的思想与这些思想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契合性和融合度,所以独立的《宝王经》救世思想的内容就被主流的观音思想的内容所淹没,随着六字真言的独立发展,单独表现这部分内容显得没有必要,这也许是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绘制比较少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是与密教发展的趋势和佛教发展的阶段有关。虽然《大乘庄严宝王》也是一部密教经典,但是除了六字真言,其他的部分仍然是传统显教的内容,佛教发展到11 世纪以后,用经变的形式来宣扬一部佛经内容的表现形式逐渐减少,取之以密教的曼陀罗坛城,《宝王经》中显教的内容不被表现是一种必然。但在密教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六字真言仍保有一席之地,以坚强的韧性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实就说明了《宝王经》中密教内容的重要性和不可取代性,也说明了此经的影响力。
综上,通过分析莫高窟第464 窟观音现身图像的特殊性以及整窟壁画间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后室壁画是依据《宝王经》绘制的,是敦煌石窟首次出现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变。壁画风格以继承敦煌传统的汉传艺术风格为主,融合了藏传艺术风格,并结合了宋西夏上师、水陆画等的流行元素,从六字真言的发展来看,《宝王经》的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它没有被广泛流传和绘制有其自身经文内容的局限,也与时代发展的进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