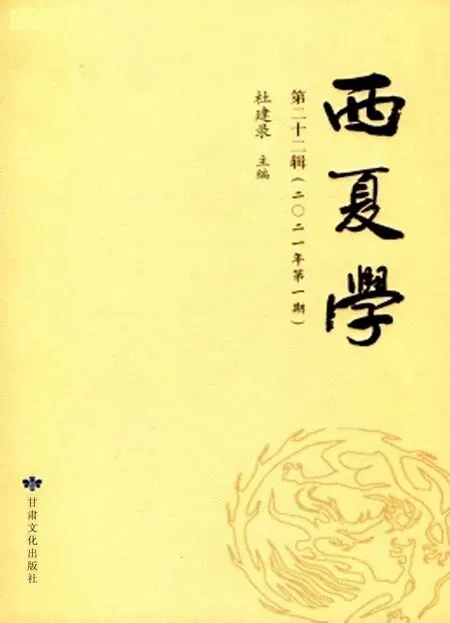宋金两朝沿边德靖寨汉蕃军民的精神家园(二)
——陕西志丹城台第2 窟洞窟营建与供养人身份考察
石建刚
城台石窟,位于陕西省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村西,共由6 窟(龛)组成,其中第2 窟是一座由宋金两朝沿边德靖寨汉蕃军民共同出资营建的佛教洞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019 年,我们发表了《宋金两朝沿边德靖寨汉蕃军民的精神家园(一)——陕西志丹城台第2 窟造像与碑刻题记内容调查》(1)石建刚、范建国:《宋金两朝沿边德靖寨汉蕃军民的精神家园(一)——陕西志丹城台第2 窟造像与碑刻题记内容调查》,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356—383 页。一文,就该窟的形制、造像和碑刻题记内容进行了详细刊布。笔者将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洞窟题记基本内容、洞窟营建与重修、洞窟供养人身份等相关内容进行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题记内容考释
城台第2 窟共保存各类题记64 条(图1、2)、碑刻2 通,这为深入考察石窟营建过程、造像题材、供养人身份、洞窟思想与功能等提供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然而由于题刻本身风化残损等原因,部分题记年代不明,给后续研究带来困扰。鉴于此,我们按时代和性质将洞窟题记分为“北宋造像题记”“金代造像题记”“重修题记”“游人题记”四类,结合造像内容,逐条对题记年代、供养人信息、对应造像、祈愿内容等基本信息进行详细考察。
(一)北宋造像题记

?
T48,据李静杰先生考证,华州保捷第□十一指挥都头为北宋禁军都之长官,(1)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 年第3 期,第109 页。且据笔者考证,与之对应的15-1 号降龙罗汉造像当是出自介用之手,主要依据有二:第一,降龙罗汉右侧下方有介用题记(即题记T47);第二,降龙罗汉,特别是龙和蘑菇形树形象的刻画,乃是典型的介氏工匠家族造像风格,类似造像还见于黄龙花石崖第2 窟、富县庙沟罗汉堂第1 窟、黄陵万安禅院第1 窟等洞窟。(2)有关介氏工匠家族造像风格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石建刚、袁继民《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 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255-268 页。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确定题记当为北宋题刻,时间在政和二年前后。
T59,题记末尾有工匠介子用题名,该窟所见介子用造像题记均不晚于北宋政和二年,据此可以断定题记年代当同样在北宋政和二年前后。
另有T32、T50,虽风化严重内容不可释读,但据题记对应造像及其他相关内容,可判断其仍为北宋题记。T32 对应造像疑为10-2 号罗汉,与之造像风格一致,且同龛雕刻的10-3 号罗汉有明确纪年“政和二年八月□日”,二者时间当相近。T50 对应造像疑为17-2 号罗汉,从造像风格来看17-2 号罗汉与两侧的15-1、16-1、18-1 号罗汉完全一致,16-1、18-1 造像分别镌刻于政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和政和二年九月,故T50 题刻时间当在政和二年八、九月间。
T47,并非造像题记,但其是工匠介子用留下的题刻,故一并考证。题记结尾处有介子用题名,该窟所见介子用造像均不晚于北宋政和二年,并结合相邻的K15、K16 龛造像年代,基本可以确定T50 为政和二年题刻。
(二)金代造像题记

?

续表

续表

续表
T3,该题记供养人“□□校尉卞移族巡检俄□成”当与T1 中的“进义校尉卞移族巡检俄□成”为同一人,且该题记所对应的K3 龛与T1 所对应的4-1 号罗汉造像相邻,故二者当为同时期镌刻完成的,也就是说T3 题记的镌刻时间也当在天德二年九月初五日左右。
T8—T18,对应造像为K5 龛内的11 尊菩萨像,从保存较为完好的T9、T11、T15—T18 内容来看,这组题记均为造像题记。其中有纪年者3 例,题记T9 天德二年□月十二日、题记T10 □□二□九月十一日、题记T18 岁次庚午中秋十五日,从T9、T18 纪年来看,这组造像当开凿于天德二年,在此年八、九月前后。
T20—T29,对应造像为K6 龛内的十方佛造像,其中有纪年者5 尊,题记T20、T21、T22 纪年均为天德二年九月十日,题记T24 为天德二□(年),题记T25 为天德二年九月初六日,其时间均在天德二年九月,故可以确定这组造像的开凿时间均在天德二年九月前后。
T36,李静杰先生认为保安军都巡应属北宋厢军,据此将该题记的年代定在北宋,刘振刚从之。(1)李静杰:《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 年第3 期,第109 页。然,保安军建制北宋及金均存在,故以此判断题记年代存在瑕疵。从题记末尾出现“化主”来看,该题记极有可能为金代题刻。“化主”当指化主僧,纵观该窟题记,宋代题记中均未出现僧人题名,而金代题记中普遍出现僧人题名,如T20、T21、T22、T54 中的“化主僧”题名,据此判断,该窟在宋代营建过程中并无僧人参与,而到了金代这里或已经形成寺院,有一定的僧众长居于此,并参与了石窟的营建和重修活动。另题记对应造像风格和题记发愿文程式亦可佐证这一判断。题记对应造像为K7 龛内小坐佛3 尊,K7 龛千佛造像与窟内其他有明确纪年的金代造像风格一致。该窟北宋题记的祈愿内容较具程式化,5 则发愿内容中,4 例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另1 例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及……民安乐”。而现存的22 例金代发愿文则是以祈愿“父母超生天界”“见存家眷平安”“禄位愿乞高迁”等个人切身需求为主,仅题记T53 中出现了北宋时期祈愿“皇帝万岁,臣宰千秋”的内容,但其落脚点同样是发愿文后半句的“各人见□□□□寿,亡过者生天见佛”。所以,笔者认为该题记当为金代题记。从前廊造像顺序来看,K7 龛内的小佛像当晚于同一壁面的罗汉、十方佛、11 尊大菩萨、4 尊天王等主要造像,故其时间应不早于天德二年。
T55,对应造像为22-3 号罗汉,造像风格与同龛的22-1、22-2 罗汉造像完全一致,而22-2造像题记有明确纪年皇统九年五月十六日,三尊造像时间应相近。
另有T2、T7、T30 三则题记,风化残损严重,题记内容不可辨识,但从其对应造像及石窟造像营建顺序等方面可以大致确定其题刻年代。T2,对应造像疑为K2 龛内涅槃造像,前廊东壁造像及与之对应的西壁K19 涅槃造像龛均开凿于金代,故T2 年代亦当在金代(贞元三年前后)。T7 对应造像疑为4-4 号罗汉左侧侍从造像,据T6 可知4-4 号罗汉像镌刻于皇统九年五月,故T7 当同样在皇统九年五月前后。T30 对应造像为9-1 号罗汉,而与之造像风格一致且同龛雕刻的9-2 号罗汉有明确纪年,镌刻于皇统九年五月十二日,二者时间应相近。
(三)重修题记(1)段双印、白宝荣:《宋金保安军小胡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第96 页。

?
T19,李静杰先生将其定为金皇统元年。刘振刚据“武功郎”和“将统制”均为北宋基层官制,不见于金代,而认为其年代应为北宋元丰四年。我们赞同李氏的判定,认为皇统元年为确。首先,该题记中的上石僧善妙同时出现于题记T10、T15、T16 中,T15、T16 没有纪年,T10 残损严重仅见“□□二□九月十一日,僧善妙”,但据前文考证,其年代当在天德二年。可见僧善妙当主要活动于天德二年前后,距元丰四年69 年之久。其次,题记T19 是杨仲妆銮石空寺大佛三尊而留下的发愿文,按常理此时距大佛完工当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皇统四年与此吻合。既然该题记确为金代题刻,何以出现金代所没有的“武功郎”和“将统制”这样的基层职官呢?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出现“第七将”字样的文书多达50 余件,建炎二年(1128)以前,有关第七将的文书使用的年款均缀宋朝年号,而至公元1131 年,“第七将”不使用南宋高宗的绍兴元年而使用伪齐的阜昌年号,只能说明至迟此年八月十五日鄜延路第七将已经由宋归齐。第七将降金伊始,金政权似乎并没有对它进行重新整编,依然沿用北宋编制。这或正是“武功郎”和“将统制”这样的职官名称出现于金代题记的原因。
T57,该题记中出现上石僧,据此判断,该题记题刻于金代的可能性最大。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历代题记来看,只有金代题记中出现“上石僧”题名。金代共有两个辛酉年,分别是1141 和1201 年,从窟内题记来看,1141 年前后杨仲及其家眷曾多次到城台石窟瞻礼佛像,并妆銮造像,而1201 年前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故此辛酉年为1141 年的可能性较大。
(四)游人题记

?
T61,题记中的“赵彦正”同时出现于T58 中,为杨仲的女婿,据此T61 题刻年代当是距T58 题刻时间1141 年较近的1127 年。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两则题记中的“赵彦正”非同一人的可能。
T42、T38、T40 三则题记均为游人题刻,且没有其他年代信息,具体题刻时间无法判断。
另有T43、T45,均被K6 龛打破,K6 龛造像镌刻于天德二年八、九月间,据这种打破关系可以确定题记镌刻年代应不晚于天德二年。从题记镌刻位置来看,这两则题记为游人题记的可能性较大。
二、洞窟营建及重修
关于城台第2 窟的年代问题,以往学者大多笼统地称开凿于宋金时期,然而,哪些造像是宋代开凿,哪些是金代续刻的,具体的营建过程又是怎样的,这些具体问题并不明晰。鉴于此,我们将结合题记和相关造像内容,对洞窟的营建和重修过程进行详细考察。
(一)洞窟营建
结合洞窟题记和造像分析,该窟的营建分为三期:
第一期(1108 年之前)
该窟所见最早题记为两则北宋大观年间游人题记,分别是“大观戊子年(1108)仲春十六日,张乐潜同行部张左臣、赵真,□人介用”(T41)和“同瞻佛像,大观庚寅(1110)十月,郭次公、刘子正、史致元、郭时中、贺机远、高及中、子冠□□同瞻”(T37)。这两则游人题记说明,大观二年洞窟造像已具备相当规模,否则“同瞻佛像”之说就无从谈起。而T41 中所见介用当与T47 中的“介子用”、T51 中的“鄜州作人介”、T59 中的“作人介子用”为同一人,正是北宋晚期延安一带著名的造像工匠介用。而前廊所见北宋造像题记均在政和二年,大观年间前廊尚未镌刻造像,故大观年间所瞻礼的造像当是洞窟主室造像。据此,大致可以确定主室造像在大观年间已经初具规模。
考察洞窟主室造像(图3),中央佛坛造像无存,现仅见台座和部分造像残件。后壁三佛六弟子造像、左壁中央的一佛二弟子和后部的自在坐观音造像、右壁中央的一佛二弟子和后部的自在坐观音造像、前壁窟口上方的七佛造像,造像风格一致,当为同一时期造像。与其他造像比较,这组造像显著的特点是台座高大、造像修长(以弟子立像尤为明显),佛像台座均为束腰须弥台承托的三重仰莲座,须弥台略呈“工”字形,上下台面正立面中间雕刻出明显的中线,中央佛坛残留的佛像台座和造像残件也表现出类似特点,应是同一时期雕凿。而主室左右壁前部的文殊与普贤造像则与主室其他造像差异较大,当非同一期造像(下文详述)。从造像细节来看,这组造像与相距不远的何家坬石窟造像存在一定共性,饶有兴趣的是两窟均是由宋金沿边党项熟户(或党项人与汉人共同)出资兴建的,(1)有关何家坬石窟的详细研究参见:石建刚、杨军:《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一)——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调查与初步研究》,《西夏研究》2018 年第1 期;石建刚:《北宋沿边党项熟户的净土殿堂(二)——陕西志丹县何家坬石窟的思想内涵与民族属性分析》,《西夏研究》2018 年第2 期。说明两窟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
第二期(1108—1112 年)
题记T41 内容说明大观年间的造像工匠正是介用,而在洞窟前廊还有两则题记提到工匠介用,分别是T47“东南西北顺,生活曾经进。同人若不识,便是介子用”(图4)和T59“(前略)作人介子用刊”。另外,在题记T51 中提到的“鄜州作人介”,也当是介用其人。介用是城台第2 窟中唯一留下姓名的工匠,足见他在该窟造像营建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曾对介用及其家族的开窟造像活动有过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介用,又称介子用,是北宋晚期至金代初期在鄜延一带极为活跃的石窟造像工匠。介用家族——鄜州介氏工匠家族——是一个长期以开窟造像为职业的石匠家族,他们在鄜延及周边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至少持续了100 年之久,不少于5 代人。介用是介氏工匠家族第4 代中最为重要的成员。就目前所知,以他为首开凿的洞窟有黄龙花石崖第2 窟、富县庙沟罗汉堂第1 窟、石佛堂第6 窟、安塞建华寺第3 窟、马渠寺罗汉堂第2 窟,另外,他还参与开凿了万安禅院第1 窟、阁子头第1 窟、十八罗汉洞第1 窟、贺家沟佛爷洞石窟。介用是介氏工匠家族中开窟最多的个人,其活动范围遍及鄜延地区。他全面继承了其父辈介端等人的造像特点,在长期的开窟造像实践过程中,又形成了鲜明的个性。(2)石建刚、袁继民:《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沙武田主编《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2 辑,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255—268 页。
据调查,城台第2 窟前廊共有北宋时期造像9 组,包括前廊后壁K10、K15、K16、K17、K18龛和左壁K21 龛的7 尊罗汉造像及其侍从人物,前廊东2 柱西向面K24 龛(现被毁)和西2 柱东向面K25 龛的日、月光菩萨造像,这些造像风格一致,均是出自介用之手。我们知道,十六罗汉和日、月光菩萨造像均是介氏家族成员偏爱的造像题材。由介端和其子介元、介用等人共同开凿的黄陵万安禅院第1 窟甬道两壁就镌刻了高大精美的日、月光菩萨造像,其风格与该窟的日、月光菩萨造像颇为一致。与该窟第三期的罗汉造像相比,介用所镌罗汉造像(图5)有3 个显著特点:第一,均雕刻于圆拱形山石龛内,或为单龛,或为两连龛;第二,罗汉均坐于“工”字型山石座上,台座雕刻精细,线条流畅;第三,蘑菇形树和龙虎形象的刻画独具介氏工匠家族风格。
这里需要特别探讨的是洞窟主室左右壁前部的文殊与普贤造像(图6)。比较容易确定的是,文殊、普贤造像雕刻时间晚于主室其他造像,依据有四:第一,文殊、普贤造像在体例上明显小于同一壁面的另两尊造像,左右壁造像的整体组合显得不甚协调;第二,文殊、普贤造像龛均打破了相邻的一佛二弟子造像龛,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左右壁佛像南侧一身弟子莲台下的云朵尾部均因文殊、普贤造像龛的开凿而被凿毁,存在打破关系;第三,在造像台座的处理上存在明显不同,以形制类似的束腰须弥台承托的仰莲座为例,主室第一期所见台座更加高大、修长,须弥台的束腰部更加纤细,上下台面正立面中间雕刻出明显的中线,这些都与文殊、普贤造像的台座显著不同;第四,造像风格不同,主室第一期造像更加修长,而文殊、普贤造像的衣饰则更加繁密。这样我们就明确了文殊普贤造像的雕凿时间晚于第一期造像。同时,从造像风格来看,文殊、普贤造像又与前廊的日月光菩萨造像一致,符合介用的造像特点,极有可能是出自介用之手。
第三期(1149—1155 年)
除第二期的9 组造像外,前廊其余造像均开凿于金代,风格一致,为第三期造像。该期造像大多有造像题记,纪年相对明确,详细考述如下。
前廊后壁金代造像。壁面东侧上部的K6 龛内为十方佛造像,每尊佛像旁均有造像题记,可辨识纪年者4 尊,6-1、6-2、6-3 号佛像均为天德二年九月十日,6-5 号佛像为天德二年,6-6号佛像纪年为天德二年九月初六日,从以上纪年题记大致可以确认这组佛像开凿于天德二年九月。西侧壁面上部K5 龛内有圆雕菩萨像11 尊,每尊菩萨像旁均有题记,现存纪年者3 尊,5-1号菩萨纪年为天德二年□月十二日,5-2 号菩萨为□□二□九月十一日,5-11 号菩萨天德二年中秋十五日,可以确认这组题记的镌刻时间在天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前后。后壁西侧下部4 尊罗汉像,现存纪年者2 尊,9-2 号罗汉纪年为皇统九年五月十二日。K9 龛内两尊罗汉造像风格一致,当为同时镌刻。后壁的四尊天王造像风格一致,其中11-1 号天王造像有明确纪年天德二年九月一日,说明四尊天王像当均镌刻于天德二年九月前后。
前廊左壁金代造像。K22 龛共三尊罗汉造像,其中22-2 号罗汉纪年为皇统九年五月十六日,说明这组罗汉的雕刻时间当在皇统九年五月前后。壁面上部K19 龛的佛塔造像纪年为□(贞)元三年三月十七日。
前廊右壁金代造像。壁面下部K4 龛的四尊罗汉旁均有纪年题记,4-1 号罗汉纪年为天德二年九月初五日,4-2 号罗汉纪年为皇统九年五月十六日,4-3 号罗汉纪年为皇统己巳五月十六日,4-4 号罗汉纪年仅可见“皇统□□五月”,可见,除4-1 号罗汉镌刻于天德二年九月外,其余3 尊罗汉均雕凿于皇统九年五月。前廊东右壁造像具有明显大的对应关系,右壁K1 龛和左壁K20 龛对应,均镌刻布袋和尚和小菩萨造像;右壁K2 龛和左壁K19 龛对应,造像均属涅槃造像内容;右壁K3 龛与左壁K23 龛对应。结合K19 龛纪年和造像风格等信息,可知这三组造像年代较晚,当在贞元三年前后。
(二)历代重修情况
从题记、碑刻内容来看,城台第2 窟在北宋造像结束之后至少经历了4 次重修,历次重修以妆彩活动为主。
第一次重修发生在金皇统元年(1141),距第二期造像完成的政和二年已有30 年之久,而第三期造像尚未镌刻。T19 是武功郎权鄜延路兵马钤辖兼第柒将统制西路军马杨仲妆銮三尊大佛时留下的,该题记位于前廊北壁中央窟口上方,位置颇为显要,其所妆銮的三尊大佛或正是主室中央佛坛上的三佛造像。T57 位于前廊西2 柱东向面K25 龛上方,据此推测该题记供养人所妆銮造像当为K25 龛的日(月)光菩萨。
第二次重修发生于金承安五年(1200)。从题记T56 内容来看,由于洛河泛涨,河水淹没石窟造像,致使城台石窟破败不堪。李怀远在瞻礼石窟寺造像之后,出资对其进行了重修,由于题记残损严重,我们无法从中得知更为详细的信息。
第三次重修在明弘治元年(1488)。根据残损严重的《弘治元年重修碑》内容分析,该年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大旱之后,有过一次较大的降水过程,河水泛涨,淹没了石窟,信士郭某等人对石窟进行了重修,从“岩洞妆颜焕然一……”一语来看,这次重修是以对造像的重新妆彩为主。
第四次重修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从嘉靖四十年残碑内容来看,此次重修同样是由于河水暴涨淹没石窟,对石窟造像造成了较大破坏。题记T34 和T46 分别是在此次重修过程中留下的。T34 是保安县静边里居住画工张润许和儿子张五十三妆彩罗汉留下的,从题记位置来看,他们妆彩的或正是K10 龛的伏虎罗汉造像。T46 同样是保安县静边里居住画工张礼同与儿子张守贤、张守能妆銮罗汉造像留下的,他们妆彩的罗汉应是K15 龛的降龙罗汉造像。这两则重修题记均是画工留下的,说明此次重修同样是以妆銮活动为主。
另据题记T64 记载,明天顺五年(1461),现住保安县德化里狄青城的同州府白水县务本里人氏,向石空寺献上石供桌两张。石窟主室中央佛坛前和前廊西侧各有一张石供桌,应正是题记中所述的两张石供桌。在石窟佛坛前设石供桌是明代石窟的显著特点,该窟主室中央佛坛前设石供桌或同样是受此时代洞窟营建特点的影响。主室石供桌现仅见底座、前挡板、上面板三部分,左右挡板已失,底座雕覆莲图案,前挡板正面分上下两排浮雕10 方花卉图案,上面板残损严重。前廊石供桌,上面板已失,现仅见前挡板和左右挡板,前挡板正面分上下两排浮雕9 方花卉图案,右挡板外侧面有题记T64。
三、供养人身份考察
城台第2 窟的营建经历了前后三期,第一期没有留下任何题记内容,我们无法从中得知供养人的具体信息。而第二期和第三期均留下了为数较多的题记,保存有大量供养人题名及其身份信息。特别是第三期出现的大量少数民族供养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城台第2 窟供养人的多民族属性提供了资料。
(一)北宋德靖寨军民供养人
北宋时期,城台第2 窟涉及供养人身份信息的题记仅有6 条。题记T59 明确说明供养人来源于“保安军德靖寨”。德靖寨,北宋天禧元年(1017)建城,初名建子城,天圣元年(1023)改为德靖寨,俗称“狄青城”,位于志丹县旦八镇城台村,西距城台石窟仅1500 米,城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题记T33、T49 中供养人均来自“本寨”,当同样是指德靖寨。就供养人身份来看,除德靖寨的普通民众之外,还出现了属于北宋禁军的华州保捷指挥都头,德靖寨属保安军治下的重要军事堡寨,延州西北方的军事屏障,军事地位非常重要,这支禁军应驻守在德靖寨。题记T51、T52 没有书写供养人来源,这些供养人当同样是来源于德靖寨及附近地区的民众。从供养人题名来看,这一时期的供养人似乎一律为北宋治下的汉族军民,且在T33、T52 中出现了大量女性供养人共同出资造像的现象。可见,城台石窟正是由临近的德靖寨军民共同出资建造的。这一时期的祈愿内容较具程式化,多为“皇帝万岁,重臣千秋”这样的套话。
城台第2 窟乃是陕北石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超大型洞窟之一,面阔达24.4 米,那么该窟何以具有如此规模呢?我们认为这与当时保安军德靖寨的政治军事地位、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直接相关。保安军本是延州永安镇,太平兴国二年(977)升为保安军,成为横山沿边中路的重镇,鄜延路的西北屏障。保安军所在临近西夏宥州,为蕃汉杂处地带,北宋一朝长期作为宋夏双方官方交涉的中心。《西夏地形图》标有宋夏之间的国信驿路,大体走向为:由兴庆府南下至永州,从吕渡过黄河,经谷雨、苦井、人头、百池(即白池)、乌池、万全寨、顺宁寨,最后到达保安军。宋人曾公亮著《武经总要》称这条道为长城岭路,并称“此路可行师”(1)[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八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同时,保安军也是延夏道路上的一个中转地,宋夏交易的榷场所在地。除了榷场之外,宋夏沿边地带还有不少和市、临时市场和未经政府许可的非法市场。(2)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182 页。延州及保安军大量的堡寨是北宋抗争西夏的依托,在这些处在沿边地带的堡寨中,由于军队的进驻和蕃部的活动而有了活力,所以这些堡寨就成了各类市场的所在地,德靖寨正是如此。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保安军旧(1041 年前后)商税点有在城及德靖寨2 务,岁3314 贯,熙宁十年商务有在城、德靖寨、顺宁寨和园林堡4 务,岁收商税3237.66 贯,其中军城1801.890 贯、顺宁寨489.261 贯、园林堡270.156 贯、德靖寨676.362 贯。酒务有在城和德靖寨2 务,熙宁十年前旧额酒税为69642 贯,熙宁十年酒税额为32511.334 贯。可见,保安军及德靖寨的市场贸易颇为发达,这就为城台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正是由于保安军德靖寨在宋夏沿边地带的特殊地位以及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为城台第2 窟的开凿提供了信众基础和经济来源。
(二)金代德靖寨蕃汉军民供养人
城台第2 窟所见金代供养人信息十分丰富。从T18 的“德靖寨兵马都监兼酒税”和T9、T20、T21、T22、T35 的“本寨”来看,这一时期的供养人同样以驻守在德靖寨的军民为主。但此时供养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量出现少数民族供养人。
从题名来看,金代题记中出现大量党项人题名,特别是T1、T3、T25 中提到“卞移族”,T35中提到“小胡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考古资料。有关小胡族的研究较多,孙继民先生以黑水城出“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见小胡族文献为核心,并结合该窟T35、T56 题记等相关资料,对小胡族的分布、兵员构成等问题做了分析,大致确定了小胡族主要分布于以德靖寨为中心的义正川、樊川和洛河一带。(1)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文献宋代小胡族文书试释》,《中华文史论丛》2007 年第2 期,第327—340 页。段双印、白宝荣先生以新出涉及小胡族的碑碣等资料为核心,对宋金时期小胡族胡公家族的世袭源流做了详细考证,并对小胡等族的族属进行了简要考察,认为城台石窟题记所见少数民族人名应是党项人或党项化了的回鹘人。(2)段双印、白宝荣:《宋金保安军小胡等族碑碣资料综合考察与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4 年第5 期,第91—99 页。有关卞移族的文献记载极少,仅《宋史·兵志》载:“鄜延路,肃戎军,卞移等八族,兵七百四十八、马一百二十三。”(3)[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85 年,第4753 页。目前,有关肃戎军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更无法从中得知有关卞移族的更多信息,有待更多资料的发现。题记T62 中还提到供养人折仲强,折氏是宋代陕北地区非常著名的大姓,有关折氏的族源学界有党项羌和鲜卑两种观点,但无论如何,两宋时期折氏被认为是党项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羌族有河西折氏,世居云中,为北蕃大姓。”(4)[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593 页。该书北宋政和年间始编,南宋绍兴年间完成,乃是当时之人对折氏族源的记载,颇具说服力。
从题记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延边地区的汉蕃民众之间虽然还存在着一定的民族区别,如题记中汉人和党项人题名大多是明显分开的,极少在同一条题记中同时出现汉族人名和少数民族人名,这说明汉蕃民族之间的交往依然受到限制。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党项人的汉化越来越深刻,民族融合趋势明显。这一时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蕃人用汉姓汉名、蕃汉通婚、接受儒家文化。如T31 中俄首领二子分别以永忠、永诚为名,T35 蕃人讹遇除长子外的三个儿子均为汉名,分别是家德、永德、永见,这些人名显然深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就发愿内容来看,这一时期蕃人的发愿内容主要有“报父母育养之恩”和祈愿“亡过父母超生天界”“见存家眷各保平安”,和同时期汉人的发愿内容一致,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石窟所见金代题记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T1、T4、T5、T10、T25、T31、T35、T53、T55、T56)及汉族平民(T9、T20、T21、T22、T54)供养人题记纪年一般采用金代年号,而汉族官吏很少出现纪年信息(T11、T36),个别有纪年信息者则采用了天干地支纪年(T18、T19、T57)。少数民族和汉族普通民众大量使用金朝年号的情况说明,金朝在延安一带的统治已成事实,普通民众已经接受了这一既定事实。北宋亡国以后,陕西境内义军继续抵抗金朝统治,希望能复国。德靖寨汉族官僚依然不用金朝年号,反映出他们依旧希望能够复国的心态,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时局动荡、朝代更迭年代汉族官吏的明哲之举。
四、结语
基于翔实的考古调查,本文对城台第2 窟所见题记的性质、年代、对应造像等基本内容进行了逐条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洞窟的营建和重修过程,将其营建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时间在1108 年之前的某个时段,开凿了主室除文殊、普贤之外的所有造像;第二期时间在1108 至1112 年之间,主要镌刻了主室的文殊普贤造像和前廊的7 尊罗汉像及日月光菩萨造像;第三期在1149 至1155 年前后,完成了前廊其余造像的雕刻。从现存碑刻题记来看,该窟自第二期造像完成之后,至少经历了4 次重修。至此,我们基本厘清了该窟的营建及重修过程,对不同造像的开凿年代有了清晰的界定。
城台第2 窟供养人均是来自邻近的保安军德靖寨的汉蕃军民。北宋时期所见供养人均为汉族军民,并未发现少数民族供养人。金代则汉蕃军民同时出现,蕃人汉化程度较高,但从石窟题记来看,汉蕃民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分。随着长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到明清以后,他们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个民族整体,除个别姓氏(如胡姓)还保留了少数民族的影子,其他供养人则已彻底无法区分其族源。该窟成为汉蕃民族融合的见证,也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