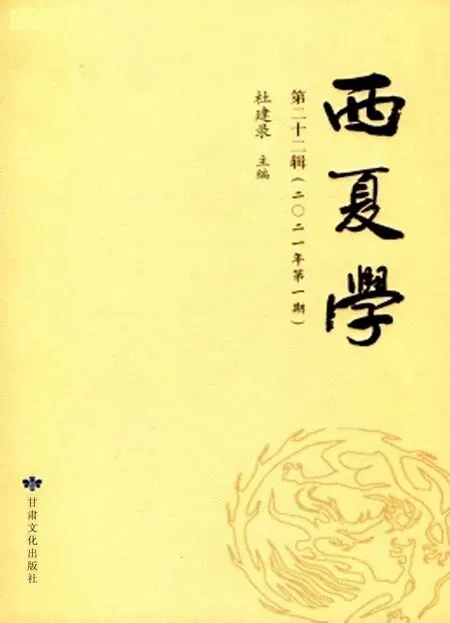西夏风俗概论
史金波 佟建荣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回鹘、吐蕃等族。其中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在政治上占有优势。汉族是西夏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人口众多、文化发达,在经济文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占有优势;藏族和回鹘在政治、经济上势力较弱,但在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特点。民族构成方面的这种特点,加上历史上西北诸民族的融入,使西夏社会呈现出番汉并蓄、多元杂糅的风俗习惯。番汉并蓄、多元杂揉既体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具体行为习惯上,更体现在番汉礼并用的风俗制度以及尊儒崇佛尚巫的意识形态上。(1)
一、多样杂糅的风俗习惯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党项族内迁发展,其实就是一个与内迁地原有民族及周边民族不断交汇交融的过程,在交汇交融的道路上,一个不同于早期党项族的新的党项族不断地形成。与此同时,不同文化、习俗也被不断地整合、揉进原有党项族习俗当中,加上境内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的共同存在,使西夏风俗习惯呈现出多样杂糅的特点。
在饮食上,出现以食肉为主和以食粮为主两类饮食习惯。其中食粮人群主要分布在适宜稼穑的农区,既包括接受了当地汉族传统生产技术的党项族人,也包括原本世代从事农耕的当地汉人。这些人群的饮食均有明显的西北传统,如喜食胡饼、烧饼、荞麦、包子等,辅之以当地出产的羊、牛及水果蔬菜、野菜。同时受吐蕃及回鹘影响,也食用一些青稞制品及回鹘瓜、大石瓜等。牧业地区以肉、奶及奶制品为主。西北的牧业生产使得党项族“烹牛羊,具酒食”的习惯得以延续,但农业区的同时存在,又让食牛肉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
在服饰上,西夏社会有皮、毛等游牧民族服饰,也有麻布、绢帛等汉地传统纺织品,还有中原地区刚刚开始使用的棉布。文职官员服饰中有“窄袍”“吊敦”“幞头”“鞾笏”“金冠”“金蹀躞”等,武职官员服饰中有“旋襕”“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金涂银束带”,配“蹀躞”“结锥”“短刀”“弓矢韣”等。其中的“窄袍”“吊敦”“旋襕”“金帖起云镂冠”等极具胡戎色彩,而幞头、鞾笏、蹀躞等则为唐宋装束。西夏法律明文规定,汉族臣僚必须戴汉式头巾。违律不戴汉式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1 页。幞头、裹巾、东坡帽等也见于百姓服饰中(2)魏亚丽:《西夏帽式研究》,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
在服饰制度上,西夏有着和汉文化中一样的等级限制,但具体的衣着颜色、图案、装饰又有明显的西夏习惯。元昊立国时规定“民庶青绿,以别贵贱”。(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2000 年,第13993 页成书于仁宗时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又规定“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鸟足黄(石黄)、鸟足赤(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的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282 页。
在建筑装饰方面,皇家宫殿喜用大型的琉璃装饰,装饰物既有汉族传统的鸱吻、四足兽,也有佛教色彩很浓的摩羯、迦陵频伽、覆钵形的莲花座等。
在婚姻嫁娶方面,西夏也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需征得女子本人的同意。彩礼是婚姻成立的条件,婚价由法律限定,家庭贫困者可以出劳力补偿。缔结婚姻除有汉地的说媒、纳礼、食价、婚价、嫁妆、迎媳等“六礼”程序外,还有族亲商议、饮酒食、设订婚宴等内容。从婚约成立至迎娶一般需要三年。同时,还有游牧民族抢婚习俗的痕迹。和中原汉族一样,婚后男子有“七出”的权力,但同时女子还有独特的“三不出”权力,反映出西夏从法律层面上对妇女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
召巫送鬼、礼佛消病、画符箓化病、求医服药针灸等多种治病方法在西夏社会同时存在。西夏巫、卜合一,诵咒驱鬼的是巫师也是卜算师;医学书籍既有中原的《孙真人千金方》,也有在中原基础上形成的《明堂灸经》《治热病法要论》《神仙方论》,还有众多用本土药材医治本土病的偏方、验方。
人去世后或土葬,或土葬与火葬相结合,墓地选择有请巫师占卜的,也有通过堪舆、龟筮等方法选择的。葬礼程序中有巫师作咒,也有亡灵超度,超度亡灵的法事上有僧人还有道士。亲属去世要服丧、哭泣、也要弹奏起舞。
早期党项族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内迁后四时耕作等皆用中原历法。建国后在采中原历法制度的基础上,自制历法。传世有汉文、有西夏文、有夏汉合璧历书。历书内容有干支年月,同时注入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二九曜星宿与该月时日的关系、六甲纳者和建除十二客,望日、沐浴、归忌、物候、神煞和选择宜忌等内容。
西夏多种文字并存,早期党项族有语言而无文字,内迁后,部分人逐渐接受汉语,使用汉文。西夏建国前夕,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被“尊为国字”。作为官方文字,西夏文(党项族文字)在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官私账目、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等方面被广泛使用,大量的汉文典籍、汉文佛经、藏文佛经被译成西夏文。与此同时,西夏社会还有汉语、汉文、藏语、藏文、回鹘文等其他文字。其中的汉文是和番文(西夏文)并行的官方文字,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被各个民族包括党项族广泛使用。为适应境内多民族多文化的国情,西夏不但有番汉对照的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还有大量的夏汉合璧书籍、夏藏合璧碑文、佛经等。在多语的影响下,传统的党项语言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其他语言尤其是汉语词汇及语法习惯走进了党项语言中。
西夏书籍装帧既有中原地区常见的卷轴装、蝴蝶装、经折装、缝缋装、粘叶装、包背装,也有源出印度贝叶装的梵夹装。还有蝴蝶装印刷经折装装订以及卷轴装改装经折装的习惯。
西夏有在洞窟佛寺墙壁、纸张、绢帛、雕板画、木板上绘制图画的习惯。绘制内容多为佛教题材,如佛像、说法图、经变图、菩萨像、佛教故事等;佛教故事有原生故事,也有如唐僧取经之类的民间传说故事;一些社会生产、生活场景有时也被绘入佛教图像中;图像的装饰图案有金刚杵等佛教法器,也有龙、凤、团花图案、宝相花图案、交枝卷草、波状卷云纹等,尤喜用龙、凤装饰藻井。除此外,西夏一些供养人、施主人物也被绘入壁画,并在旁边留下姓名。
在常规放射治疗中,脊髓、脑干、腮腺、颞颌关节、皮肤等组织器官,都会在高剂量射线下暴露,受到影响后,发生皮肤损伤、口干症等副反应,对患者的治疗安全造成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常规分割DT在10 Gy以上,在照射野当中的唾液腺,将会降低50%左右的分泌;如果分割DT在45 Gy以上,唾液腺将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而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利用了多野共面照射的方式,同时与动态多叶光栅相配合,能够优化调节正常组织受到的照射剂量,进而使放射治疗产生的毒副反应发生率最大限度的降低。
西夏盛行歌舞,上自宫廷贵族,下到寻常百姓,小至日常生产、婚、丧、嫁、娶,大到战时出征、使臣交聘、佛事法会都有歌舞音乐。西夏社会中有番乐和汉乐两种音乐,政府行政机构中设“番汉乐人院”,包括番乐人院、汉乐人院。(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372 页。西夏灭亡后,该地的音乐被统一称为“河西乐”,成为元朝音乐的组成部分。
西夏人亲属间以“ ”(音“则”)区分辈分高低和亲疏等次,一个基本家庭包括户主、配偶及未成年孩子。基本家庭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未出嫁的姑,平辈未成婚的兄弟、未出嫁的姐妹,儿子、儿媳、孙子、孙女等构成大家族,家族以父系为线。西夏家庭强调“孝”,子女孝顺父母,晚辈孝顺长辈,夫妻互敬,兄弟互助、姐妹互爱。
西夏有番姓、汉姓,同时杂以昭武九姓等其他姓氏。番姓即党项姓,早期有八大部族,以族为姓,分别为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破丑氏、野利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等,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至西夏建国后番姓多达300 余个,如此众多的番姓,除嵬名、妹轻、卧利、野利、破丑等沿袭早期八大部族外,多由唐五代以来部族繁衍融合形成。

西夏的汉姓有如李、梁、苏、刘、张、王、吴等传统的汉姓,也有党、浑、余等唐五代鲜卑、吐谷浑等民族曾使用过的姓氏。使用汉姓的有汉人,也有党项族人。使用汉姓的党项人一般会在姓后面缀个番名,如“梁乞埋”“梁乞逋”等,呈现独特的番汉合璧特征。
西夏的命名也是番汉并存,有的用“仁”“忠”“德”“荣”“茂”“昌”等名,与中原地区汉族人名用字没有区别;有的用狗、猪、驴等贱名,使用贱名是西北地区下层民众的普遍习俗;有的以山、月份、斤两为名,这是党项进入西北后民族融合的结果。另外,党项还有弥药、汉、羌等民族称谓和禅定、般若、佛塔、金刚等宗教词语的人名。在命名制度上,平辈中也有排行,如仁孝、仁友兄弟(1)[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有“泰和六年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废纯祐自立”。中华书局,1975 年,第2871 页。,吴名革、吴名山兄弟。(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五,哲宗元符二年正月甲子,中华书局,2004 年,第1281 页。这类人名中,除源自汉文化命名中的行辈制度外,许多是西夏的连名习惯所致。连名是普遍存在于西夏党项族命名中的一种现象,有父子(女)、母子(女)、兄弟等多种类型。如一户一家中父亲名字(麻藏达家茂)、母亲名字(梁氏小宝),儿子起名(达家宝),既包含父亲名字中的(达家),又包含母亲名字中的(宝)。女儿起名(达家舅),包含父亲名字中的;一户人家中兄弟可以分别命名(罗移达家山)、(罗移般若山),其中兄弟名中都含有(山),见于文中的“吴名革”与“吴名山”等类人名即属于此。
总之,党项内迁后对各民族的接纳吸收,建国后境内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的共同存在,使得西夏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样杂糅的特点。
二、同行并用的礼仪制度
多样杂糅尤其是番汉杂糅的背后是同行并用的番、汉礼仪制度。所谓“番礼”是指注重党项族自身固有习惯习俗的礼仪制度,用党项族的习惯协调处理各个部族之间的关系与利益。所谓“汉礼”,是指以汉文化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强调用中原汉族的礼仪规范调节统治秩序。
不同礼仪制度代表不同的文化倾向与不同的利益集团。西夏自立国之初就存在着番、汉礼之争,两种礼仪制度在斗争中相互融汇,最终形成了多样杂糅的西夏文化习俗。
景宗元昊为建立政权,强调蕃性,凸显党项部族特征,舍弃自唐以来的李姓、改姓嵬名,下令秃发、衣皮毛,制蕃字、立蕃学。毅宗谅祚亲政后,与宋修好,请求宋朝下嫁公主,派使臣上书表达仰慕中原衣冠之意,求复李姓,求赐书籍、废蕃礼,行汉仪。毅宗去世后梁太后掌控朝野大权,一改毅宗做法,提倡番礼,频繁侵宋。惠宗秉承喜习汉文化,对入夏汉人以礼相待,亲政后力主行汉礼,改善与宋关系。崇宗乾顺早期,大权由其母小梁太后把持。小梁太后紧步大梁太后后尘,继续推行番礼。梁太后去世后,崇宗亲政,开始着手发展汉文化。于贞观元年即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建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以廪食之。(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4019 页。仁宗即位后,进一步推进汉学教育。人庆元年即宋绍兴十四年(1144)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7 岁至15 岁都可以入学,专门请教授讲课,仁宗和皇后罔氏也常前往训导。令各州县立学校,弟子员增至三千人。第二年,又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夏人庆三年即宋绍兴十六年(1146)尊孔子为文宣帝,设孔庙,规格同帝王,孔子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经典成了西夏读书人的案头卷本,更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西夏名相斡道冲,年5 岁时以《尚书》中童子举,精通五经,译《论语注》,作《论语小义》20 卷,又作《周易卜筮断》。儒家思想更成为西夏制定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著名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即以儒家思想为依据。《论语》《孟子》《孝经》《礼记》等儒家经典被译成西夏文,《圣立义海》《西夏谚语》等西夏原创作品也处处贯穿着儒家的道德精神。甚至国师鲜卑宝源的著作《贤智集》也没有离开儒家的处事之道。儒家思想已成为王朝、政府、官员、百姓的主要行为依据。
三、兼收并蓄的多元信仰
西夏建国时,党项进入西北内地几百年,深受汉族文明的浸润,元昊建国时虽创制蕃文强调番礼,(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二月辛未,中华书局,2004 年,第2814 页。但在治国理念中儒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将《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及《四言杂字》等汉字蒙学书籍翻译成西夏文,番学成为推广儒家文化的工具(2)[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记载:“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中华书局,2004 年,第13995 页。;崇宗乾顺后期有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强调董仲舒的“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的养贤论(3)[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正》卷三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359 页。。乾顺纳其言,建国学,设弟子三百,立养贤务(4)[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4019 页。;仁宗时儒学在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秩序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彰显,皇权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开篇即规定:“欲谋逆官家(皇帝),触毁王座者,有同谋以及无同谋,肇始分明,行为已显明者,不论主从一样,皆以剑斩,家门子、兄弟节亲连坐。”(5)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谋逆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11 页。与维护皇权相伴的是不遗余力地推行孝义,以孝治天下,把对双亲的“孝”与对皇帝的“忠”紧密联系在一起,规范着上至百官下至百姓的日常行为。“失孝德礼”为十恶之一,位在谋逆之后,宣扬“上孝帝之行也,天下扬德名,地上集孝礼,孝德遍国内,此帝之孝也。次孝臣僚,持以德忠礼,不出恶名,以帝之赏,孝侍父母,则臣之孝也。出力干活,孝侍父母,国人孝也。”(6)[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译:《圣立义海研究》原译文为“扬天下德名,集地上孝礼”,今改译为“天下扬德名,地上集孝礼”。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74—75 页。
以儒治国的同时西夏王室大力推行佛教。党项族内迁的银夏地区早有佛教流传,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孔道,自凉、魏开始就寺窟林立,西夏北面的契丹、南面的宋朝、西面的回鹘早已接受佛教。西南的吐蕃在赞普朗达玛禁佛后,成为藏传佛教的中坚力量,处于汉族、契丹、回鹘、吐蕃几个信仰佛教的民族中间,党项人很快接受了佛教。太宗、景宗、毅宗、惠宗四朝曾6次向宋求赐佛经。在求赐佛经的同时,西夏开始了持续的大规模译经、校经活动,所译佛经包括汉传经藏、藏传经藏及梵文经藏。
在统治者的推动下,西夏境内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从寻常百姓到王室贵族的各个阶层都有佛教信徒。人去世后要有法事活动。统治者发起的佛事活动规模宏大,如仁宗“三七日”时,西正经略使在凉州护国塔作佛事上,“延请禅师、提举、副使、判使、住家、出家诸大众等三千余员”。(1)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手稿部藏黑水城文献Инв.No.117。仁宗去世二周年时,罗太后主持举行大型法会,期间“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散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2)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272—273 页。西夏中书相贺宗寿亡故后,其子法事活动上请僧众等七千余员;身体有恙,也会印施佛经,以求痊愈。天盛十九年即宋乾道三年(1167)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任得敬,因疾病缠绵,日月虽多,药石无效,而印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对皇帝的敬爱活动也要有僧侣参加。《圣立义海》“九月之名义”下“善月中会”条记有:“九月十五贤圣聚日,禅僧兴日,君德民孝,敬爱皇王”。时令节日也多与佛教有关。每年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需要全体官民礼佛,共同祈福(3)[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252 页。。元昊时专门规定四月三日为礼佛圣节,全国官民要礼佛。“善月”“金刚”“禅定”“般若”“塔”等佛教名词还见于西夏普通百姓的名字当中。
早期党项族“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4)[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六《党项族传》,中华书局,2003 年,第3192 页。后来,有了鬼神崇拜,“笃信机鬼,尚诅祝”。(5)[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中华书局,2004 年,第14029 页。“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闲,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旁。”(6)[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八,中华书局,2015 年,第8 页。生病“不用医药,召巫者送鬼”,“西夏语以‘巫’为‘厮’也;或迁他室,谓之‘闪病’”。(7)[元]脱脱等:《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中华书局,2003 年,第1524 页。人死后请巫者送葬,作咒。行军作战要占卜,战死要“杀鬼招魂”(8)[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252 页。。国遇大事要“祭地神大神”,夏乾祐七年(1176)仁宗在甘州镇夷郡立《黑水建桥碑》,敕告镇夷郡黑水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以求“诸多灵神,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重加神力,密运威灵,庶几水患永息,桥道久长。”(9)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第162 页。
西夏也有道教流行,元昊出征常携《太乙金鉴诀》,以推演敌情。(10)[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中华书局,2004 年,13993 页。其子宁明因“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正月辛未,中华书局,2004 年,第3901 页。民间常利用《六壬课秘诀》《六十四卦图歌》等书以占吉凶祸福,也有施刻《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绘制悬挂《玄武大帝图》等道家经典或图像以避凶求福。
总之,作为一个多民族政权,西夏在继承发展党项族自身固有文化习俗的同时,更多地吸收了境内外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与佛教,儒家思想是其治国的基本指导思想,规范着君臣、父子、夫妇等人群行为,维护着社会秩序。佛教为国家运行提供精神慰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儒佛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与鬼神信仰、巫术诅咒、迷信占卜等共同构成了西夏社会的精神家园。
四、小结
西夏境内多样杂糅的风俗习惯、同行并用的风俗制度、兼收并蓄的精神信仰不仅源于境内外多样的文化,而且得益于比较宽容的民族政策和相对融洽的民族关系。
西夏没有刻意采取民族压迫政策,各民族共同参与政治生活,西夏法律规定“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上”。(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司序行文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377 页。这里所说的“名事”“位”,系指职官的实际任职和品位。显然,西夏官员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名事”“位”,而不是民族,“名事”“位”相同时才强调番人的特殊地位。元昊立国前后,强调番人要衣皮毛、事畜牧,制番文,实行秃发,但并未对其他民族做出要求。仁孝时,倡导番汉民族互学对方语言,汉敬番人智者,番崇汉人贤士,编制番汉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2)《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指出:“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2 页。同时,法律中明确规定“汉臣僚当戴汉式头巾,违律不戴汉式(头巾)时,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二《内宫待命等头项门》,法律出版社,2000 年,第431 页。即用法律形式有意地保留多样尤其是汉族的风俗制度。总体上来说,西夏没有出现辽代那样的民族分别治理政策,也没有出现元代人分几等的民族等级制度,西夏境内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并不明显。
另外,对待周边外来的文化,西夏也基本上采取主动吸收和拿来的态度,毅宗谅祚多次派使臣求赐佛经及各类书籍。入夏的宋地文人多被以礼相待,有的甚至委以高官厚禄,诸如来自宋朝的谋臣学士,来自回鹘、吐蕃、印度的僧侣数量都比较大。所有的这些政策、态度为西夏境内非主体民族文化习俗的保留以及各种习俗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很好的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