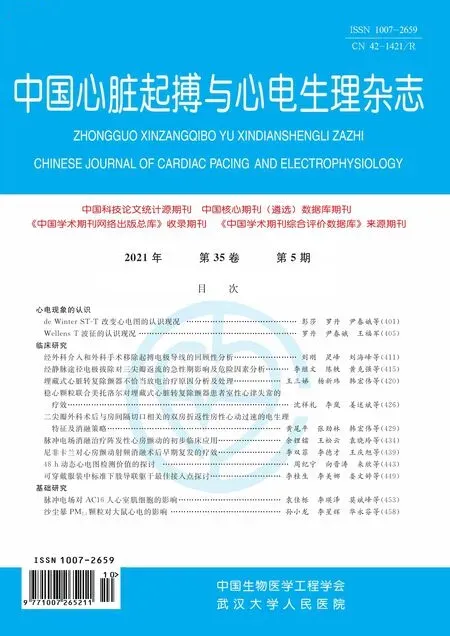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对三尖瓣返流的急性期影响及危险因素分析
李继文 陈轶 黄克强 蒋萍 苏晞
随着起搏适应证的拓展与人口老龄化,心血管植入性电子装置(cardiovascular implantable electronic device,CIED)的应用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但不幸的是CIED 感染的发生率却有不成比例的增加,成为目前CIED 患者临床诊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对于CIED 感染,国内外指南均推荐经静脉途径拔除电极导线[1-2]。国内开展的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手术也呈增加趋势。尽管使用了专门的电极拔除工具,包括机械旋切鞘、激光鞘等,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仍然存在较高的风险,严重并发症包括死亡、心肌及大血管撕裂、血气胸、室性心律失常、栓塞等[3]。其中急性重度三尖瓣返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TR)甚至右心功能不全是一种相对少见,但尚未受到临床重视的并发症。近年来国外的研究表明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与TR 加重存在相关性[4-6],但相关的研究数量较少且结论存在不一致性。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应的关注与研究。笔者通过观察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对TR 的急性期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入选2015年5月至2019年12月因CIED 感染就诊于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的患者共62例,其中男45例,女17例。记录病例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常规血生化检查、心电图资料以及CIED 及电极导线的类型、导线数量、植入时间等,入选患者植入的电极导线中至少包括1根以上的右室电极导线。患者术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美国心律学会«经静脉电极导线拔除专家共识»中的电极拔除适应证的定义[2],患者临床表现均符合Ⅰ类或Ⅱa类指征,包括起搏器囊袋局部感染(囊袋脓肿,皮肤粘连、破溃,窦道形成等)。有或无导线和/或装置受累的感染性心内膜炎,隐匿性革兰阳性菌血症或败血症。
1.2 术中TR 的测定与评估 术中患者取平卧位,超声检查采用美国Philip-CX50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全麻后将食管超声探头插入至食管中段,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全程监测术中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在电极导线拔除前及所有电极导线拔除后10 min左右测定TR 指标,包括TR 面积、返流最大速率、返流压差等。为便于定量分析TR 情况,根据TR 的严重程度分别从0到5的进行TR 评分(0=无反流,1=轻度,2=轻中度,3=中度,4=中重度,5=重度)。有临床意义的TR 加重被定义为电极导线拔除后至少增加2分或评分至少3分以上[7-8]。
1.3 手术方法及结果判定 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均在介入手术室进行。患者全麻,气管插管,术中桡动脉压及中心静脉压监测,常规放置经食管心脏超声探头。起搏依赖的患者放置临时起搏器,切开囊袋后,分离脉冲发生器及电极导线,对于植入时间较短的电极导线,先尝试使用普通钢丝或锁定钢丝(Locking Stylet)进行拔除,如电极导线与周围组织粘连较明显,则应用双层套叠式扩张鞘(Byrd Dilator Sheaths,COOK)或置入Evolution机械旋切鞘(LR-EVN-9/11.0,COOK),逐层分离导线与周围组织的粘连组织后拔除电极导线。如经上腔静脉途径拔除失败,则通过股静脉途径应用Snare 抓捕器或圈套器拔除电极导线。手术结果按照专家共识的建议判定:①完全成功:移除所有目标电极,无永久致残性并发症或死亡;②临床成功:移除所有目标电极,或残留小部分电极,但残留部分不增加穿孔、血栓等不良事件风险;③拔除失败:未能达到完全成功或临床成功,或出现永久致残性并发症或死亡[2]。
1.4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SPSS 22.0 统计软件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及治疗前后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根据情况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双侧检验危险因素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临床基线特征 共纳入62 例因CIED 感染行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的患者,其中男性45例,女性17例,年龄(64.2±9.5)岁,左室射血分数0.52±0.08。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中,冠心病12例(19.4%),高血压病13例(21.0%),慢性肾功能不全7例(11.3%),心房颤动15 例(24.2%)。而患者既往植入的起搏器类型包括普通起搏器55例(88.7%),埋藏式心脏自动转复除颤器(ICD)4例(6.5%),三腔起搏/除颤器3例(4.8%)。
2.2 电极导线特征及手术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总共拔除了125 根电极导线,电极植入的时间为(60.6±35.8)个月,包括心房起搏电极47 根(37.6%),心室起搏电极71根(56.8%),冠状窦起搏电极3根(2.4%),此外有4根(3.2%)ICD 除颤电极。按照电极的固定方式,其中螺旋电极为26 根(20.8%),翼状电极为96根(76.8%)。大部分电极导线使用了电极拔除专门工具,其中应用锁定钢丝配合Evolution机械旋切鞘拔除了82 根电极(65.6%),用锁定钢丝配合扩张鞘拔除了27根(21.6%)电极。少量电极导线(11根,9.6%)由于植入时间较短,而直接用普通钢丝+手工牵引拔除,另外5根(4.0%)残留在血管及心腔内的电极导线经下腔静脉途径拔除。分析手术结果,62例患者中,有61例完全成功拔除了电极导线,1例患者的冠状窦主动固定起搏电极(Medtronic,4195)术中未能完全拔除,残留小部分电极(<4 cm)在冠状窦静脉内,考虑手术临床成功。术中无死亡病例,但1例(1.6%)患者在使用Evolution机械鞘拔除一根植入时间15年以上的心房翼状电极时,出现上腔静脉与右锁骨下静脉交界处撕裂穿孔,导致右侧大量血胸,紧急行外科开胸修补后,患者恢复良好出院。
2.3 电极拔除前后经食管超声测定TR 的变化62例患者均进行了电极导线拔除前后TR 的测定及评估。患者电极导线拔除前后TR 评分的分布例数及百分率详见表1。对电极导线拔除前后的评分进行统计分析,拔除前评分为1.37±0.99,拔除后的评分为1.77±1.09。配对t检验结果提示电极拔除前后TR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t=-4.196,P<0.01)。

表1 电极拔除前后TR 评分的变化(n=62)
62例患者中,有6例(9.7%)患者的TR 评分相较电极拔除前显著增加(增加2分或术后评分至少3分以上),提示TR 显著恶化,考虑有临床意义。其中5 例术后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有1 例(1.6%)患者拔除一根7年的右室电极前,TR 为中度返流,电极拔除后TR 重度返流(图1)。该患者术后出现低血压、腹胀、双下肢水肿等右心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经予利尿等药物治疗后,临床症状好转,建议患者进一步评估外科三尖瓣置换指征,但患者拒绝出院。随访半年后,患者临床症状未见明显恶化,但经胸心脏超声(TTE)复查提示仍为三尖瓣重度返流。

图1 1例患者电极拔除前后TR 的变化
2.4 电极拔除后TR 显著恶化的危险因素分析对与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相关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0.021)、EF值(P=0.005)、电极数量(P=0.012)以及电极植入时间(P=0.003)与电极拔除术后是否出现有临床意义的TR 加重相关(表2),而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冠心病、房颤等基础疾病与术后是否出现TR 加重无相关性。

表2 影响电极拔除后TR 显著加重的单因素logistic分析
以术后三尖瓣是否出现有临床意义的TR 加重作为因变量(有=1,无=0),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有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方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电极植入时间(P=0.032)是经静脉途径电极导线拔除术中出现TR 恶化的独立危险因素(表3)。

表3 影响电极拔除后TR 显著加重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3 讨论
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的手术过程中可能因为损伤心脏与血管结构而出现严重甚至致命的并发症,其中三尖瓣装置(瓣环、瓣叶、乳头肌及腱索)损伤导致的严重TR 以及急性右心功能不全的发生虽早有相关的病例报道[9]。但直到近年来,少量的国外研究才报道了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对TR 的影响。但由于存在手术团队及使用器械、研究样本特征及数量、TR 测定技术、病例随访时间等差异性,手术导致的有临床意义的TR 的发生率范围从3.5% 到15%,且研究结论也有一定的矛盾之处[5-8,10-11]。尽管国内近年来经静脉途径电极导线拔除数量不断上升,但对此尚缺乏研究与报道[12]。本中心自2015年开始常规应用经食管心脏超声进行术中监测,由于经食管心脏超声的使用能够更灵敏地检测到三尖瓣装置损伤、及时测定TR 的情况,因此本研究的数据能够为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中TR 的急性期变化提供较为真实的评估。
本研究结果表明与电极导线拔除前相比,除了少数患者(6.5%)的TR 评分较电极导线拔除前略有降低外,更多患者的TR 评分相较电极导线拔除前增加,表明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可以导致急性期TR 增加。其中具有临床意义的TR 加重的发生率为9.7%,与近期国外的研究报道相近。同时本研究结果提示尽管9.7%的患者在术中发生了具有临床意义的TR 加重,但其中大部分患者术后并未出现明显右心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只有个别患者(1.6%)术后出现急性右心功能不全的症状与体征,需要积极药物治疗及评估外科瓣膜置换手术指征[13]。分析上述结果的原因及差异性,考虑与手术过程造成三尖瓣功能受损机制有关。既往研究中,根据尸检、心内直视手术的数据表明心室电极导线随着植入时间的延长,会逐渐形成纤维化粘连到三尖瓣装置上,包括瓣环、瓣叶及腱索等[14]。术中牵引电极导线及分离纤维结缔组织的过程中可能造成三尖瓣装置不同程度的损伤。轻者只是短暂影响三尖瓣的闭合,从而增加三尖瓣的返流;严重者可能导致腱索断裂、乳头肌甚至瓣叶的撕脱,从而对三尖瓣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另外在本研究中,也有少数患者在拔除心室电极导线后,TR 的情况反而有轻微的改善,这在既往的研究中也有类似报道,但机制尚未明确,考虑既往植入的心室导线对瓣叶有机械性损伤与阻碍、以及心尖部起搏导致心室激动顺序改变等[15]。因此推测对于植入时间较短,纤维化粘连较轻的患者,经静脉途径拔除心室电极导线反而有可能改善TR 的情况。
本研究在观察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对TR 的急性期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可能导致严重TR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多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只有心室电极导线植入的时间是电极导线拔除后是否导致TR 明显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一结果与最近Park等[8]报道的结果相似。因此结合既往研究结果,评估心室电极导线植入时间,而不是拔除的导线类型,似乎与术后TR 加重的风险更密切相关。另外有研究报道拔除3根以上的右室电极导线,有增加TR 恶化风险的趋势。但电极导线数量的增加与较长的导线植入时间常并存,且都与更广泛的纤维粘连及更高的三尖瓣损伤风险有关。因此在Park等的研究及本研究结果中,均显示心室电极导线数量虽然与术后TR 加重风险相关,但并非独立的危险因素[8]。
综上所述,通过本研究证实了在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后,少部分甚至个别患者可以出现TR 的严重恶化。术后严重TR 的发生率随心室电极导线植入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增加,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事件发生率较低,研究结论有待于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此外经静脉途径电极拔除术对TR 的远期影响及转归情况也需要进一步长期随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