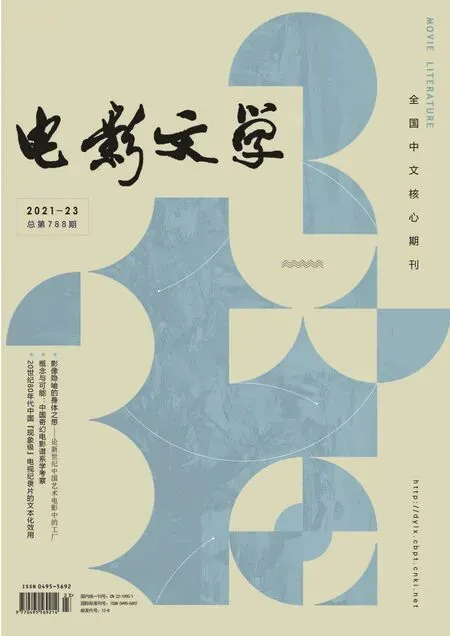新世纪谍战电影的人本主义空间分析
孟祥鹏 张 林
(1.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 济南 250002;2.山东文艺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002)
在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谍战”类型的作品不多,因而关于谍战电影艺术技法和价值呈现的探讨也较少,作为谍战叙事中以对立统一形式而存在的人本主义思想,则更是少有人关注。事实上,人本主义虽与谍战作品的形态追求有对立部分,却是该类题材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等环节不可或缺的一种创作思维,倘若舍弃人文主义的底色,那作品的意蕴空间和叙事张力将大大受损。所以,谍战电影的叙事不单要围绕“谍战”展开,更要关注其与人本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关系。可以说,人本主义思想在作品中的呈现程度,能够影响一部谍战电影的成功与否。
一、谍战叙事与人本主义的对立统一
间谍是随着社会阶级分化和战争等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史料中关于间谍的最早记载可在《左传·哀公元年》中觅到踪迹。“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说的是夏朝国君太康统治时期,太康的侄儿少康力图复国,派出女艾潜入寒浞内部刺探情报,女艾因此成为我国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的间谍,所以我国古代间谍活动有“用间始于夏之康”的说法。《说文解字》中“间”(后起字,古作“閒”)的释义为“隙也”,“谍”的解释为“军中反间也”,可以看出二者承担的原始指向功能有细微差别,但都与后来“间谍”一词的意义范畴有关。春秋后期《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对“间谍”的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了五种用间方法:“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战国后期的《六韬·龙韬》最早把“间”和“谍”连用,“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综上可见,“间谍”一词作为人物个体具有明确的身份识别性,即两军交战时,潜入敌方刺探军事情报或进行反间活动的特工,是为间谍。而间谍工作的核心是服务于己方军事利益而进行的谍报行为,在敌军内部侦察、获取、收集情报,并想方设法向己方进行传递,从而达到既定的战争目的。
人本主义(humanism),亦可称为人文主义或者人道主义,作为术语最早可追溯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提到“人文学”( the humanities) ,强调人的价值和地位,主张个体从宗教的控制下解脱,获得精神独立与自由;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则注重理性和思考,促进了现代主体意识的确立,标志着现代性的开端;18世纪末启蒙时期,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开始思考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的精神性冲突问题,于此基础上对人存在的本质意义做了深入分析。人本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外延随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截至目前,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已被纳入人本主义的范畴,尽管人本主义难以明确定义,但我们不难看出:人本主义不仅强调个体的独立、自由与存在价值,更涉及了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等。中国的人本主义思想产生较晚,以新文化运动为肇始,提出了“民主”“科学”等口号,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文学、艺术思想以求变革创新,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象征派诗歌等各种注重人作为活动个体的生存际遇描写和情感体验抒发的艺术形态。其后几十年战乱使“救亡”成为文学艺术界一以贯之的主题,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被迫弱化,这段时期倡导的是“小我”在“大我”、“自我”在“集体”中的融合,艺术一度成为统治阶层用来社会变革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当代艺术困境推动下的创新局面逐渐形成,现代派艺术成为大家的关注重点,人本主义思想才再次得到发展。“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打破封建枷锁、谋求变化发展的主要话语资源,在此基础上以世界艺术发展视境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特点与内容:反对英雄主义,倡导个性的凡夫俗子,反对阶级性,注重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回归人性本身。所以我们对“人本主义”探讨,并不简单地“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谍战叙事与人本主义思想存在着对立统一的特征。统一之处在于谍报活动的现代性内涵与人本主义思想中涉及集体诉求的部分相契合。新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如张艺谋的《悬崖之上》、高群书和陈国富的《风声》、柳云龙的《东风雨》等以抗战为故事背景,麦兆辉、庄文强的《听风者》和孙周的《秋喜》等则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这些谍战作品的叙事语境无一例外建置在为整体民族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无论作品以何种视角切入,以怎样的叙事方式展开,其中所有作为正面形象加以艺术表现的谍战特工,其行为动机都是以民族自由和独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理念,这是谍战叙事和人本主义思想的统一之处。但同时这部分内容又是题材所携有的自然属性,换句话说,谍战叙事的情节架构和人物塑造只能围绕以自由、独立等民族集体诉求作为价值理念的主人公来展开,因而这种贴合在叙事过程中不足以构成太多的戏剧冲突和情节推力,谍战叙事和人本思想的对立因素,才是类型电影在情节叙述和逻辑演绎上应开掘的重点。
《孙子兵法》指出,在战争中须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做好谍报活动,“欲所知敌情者,非间不可也”。间谍在战争中的根本任务就是获得敌方军事情报,为己方决策者及时、准确地提供有利信息,因此间谍具有行为活动上的保密性和身份特征上的伪装性,从事谍报工作的人一般在组织的安排下进行单线联络,甚至上下级之间只以约定的暗号或者接头方式进行信息交换,彼此之间素未谋面。比如《风声》中周迅饰演的“老鬼”和张涵予饰演的“老枪”几乎是在绝境中才知晓对方身份;《听风者》影片最后,沈静对何兵说:“七零一的墓碑就是这样,这里的人从生到死都是机密。”其次谍报活动本质上是军事活动,而军人的行为核心是“服从”,可见对间谍个体来说,其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作为谍报活动参与者的工具属性,他们的行动过程本质上其实是抹杀个体性的,所有任务的指派、实施与完成都以杜绝“非理性”为前提,与人的生物属性和欲望本能之间形成悖论,和人本主义思想所提倡的个体独立、自由相冲突。谍报的获取、传递过程中除了瞬息万变的现实情境,更受到间谍个体的情感思维干扰,当个体的利己需求与谍报任务的终极目的碰撞时,作品的内涵才有了向内、向深开拓的空间。所以谍战电影在以“谍战”为创作重点的同时,更应该深入挖掘“谍战”与“人本主义”结合的可能。
二、两种叙事策略之于人本主义的兼容
(一)“革命+恋爱”模式
“革命+恋爱”的叙事最早应用在小说创作领域,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写作模式,代表作家有蒋光慈、洪灵菲、丁玲等。茅盾曾将“革命+恋爱”叙事按照时间先后划分为三种类型——“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彼时“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产生是顺应时代潮流之势。五四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理念革新,性别意识和婚恋问题才逐渐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五四”落潮之后,“恋爱意识”作为思想遗产被保存了下来,与当时主流社会对革命性的强调共同形成了这一被大众乐于接受的“革命+爱情”的叙述模式。在电影方面,1949年时任中央电影局领导的原上海电影人史东山就明确提出:“我们也无妨来写写恋爱与革命相结合、两者互增热力的故事。”此后上海的电影工作者摄制了许多“革命产生了恋爱”式的影片。如《沙漠里的战斗》中的杨发与张珍;《为了和平》中的江思远与万方;《母亲》中的梁承文与颜佳;《护士日记》中的高昌平与简素华;《聂耳》中的聂耳与郑雷电等,他们都或在革命或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
新世纪以来的部分谍战电影对此类叙事模式有所继承,比较典型的是《听风者》和《东风雨》。“恋爱”作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感互动,是表达人本主义思想的优良介质,它和“谍战”在属性、目的上具备足够的矛盾冲突,如何通过这样的矛盾冲突去丰富、完整叙事的核心功能,拓展审美意蕴空间是影片最终呈现效果的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影片皆存在各自的弊病。
《听风者》中“谍战”和“爱情”两条线索交错进行,问题在于原本应该作为叙事核心的“谍战”部分形式割裂严重,“块状”情节以简单的逻辑进行贯通,“重庆”和“老鬼”的交锋在影片四分之三左右处才开始,最后“老鬼”被敌方特工刺杀的收场也略显草率。可以说,《听风者》中有关“谍”的叙事相对而言是被弱化的,完全围绕着“恋爱”叙事而展开,成为“恋爱”线索的附庸,因此剥开“谍战”这件质量并不上乘的外衣,影片的故事内核是一个爱情故事。张学宁与何兵从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到互相之间含蓄而克制的情感状态,以及张学宁与郭兴中之间被革命压抑的若有若无的情愫、好感,还有何兵和沈静的婚恋历程,这些情节都得到了有效的表现,展示出个体在革命战争中难以把控情感命运的无奈,然而这种方式没有触及谍战叙事的核心。因而从作品接受的角度来说,人本主义表达并非基于谍战叙事而进行,谍战只是作为叙事背景,作品本身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题材。《东风雨》的结构不存在上述问题,但其“恋爱”线索和“革命”线索同样没能有机融合,爱情故事成为主要的表现内容。“炉子和雪”“兽与鸟”等台词与主人公的动机、行为并无太大关系,只是给影片增加了一些文艺调性;且故事逻辑也存在漏洞,比如安明作为情报小组领袖在与欢颜谈恋爱之前没有摸清楚对方的底细,在难民营的寻人启事中挖出郝碧柔的藤木芳雄,抓捕欢颜后却对她公开的情郎不理不睬,欢颜也从前期一个承担爱情功能的角色忽然在影片后半部分成了操纵一切的间谍,而回望前面却找不到任何铺垫陈述,消除了观众参与情节的可能。虽然电影中关于个体层面的人本主义思想有浓墨重彩的表达,例如男女主人公在雨夜街头玩“跳房子”的游戏,犹太街巷对饮咖啡等,但整体来说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同样没有参与到谍战叙事中来,反而被拖沓的叙述节奏过多消解。
(二)“侦探”模式
《电影艺术词典》将侦探电影定义为:以侦破错综复杂的犯罪案件为题材的故事片。谍战叙事在本质上与侦探叙事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把侦探叙事放到了战争语境之中,不同阵营的角色围绕间谍活动展开搏斗,完成类似破案工作的最终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诸如情报如何传递、主人公命运走向、角色之间的敌友关系等悬疑因素都是维持观众对影片兴趣的重要因素。在悬疑推理中复原战争年代的历史场景,满足不同观影人群的“新奇”“怀旧”等各种情绪情感需求,这是此类叙事影片近年来持续受到追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里,这种叙事法表现得最好的当属2009年上映的《风声》。
《风声》开篇对背景和人物身份做了简单交代后,译电组长李宁玉、收发专员顾晓梦、剿匪大队长吴志国、司令侍从官白小年、军机处长金生火五人便被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裘庄接受盘查审问。在这个密闭空间中,充当“侦探”角色的是武田和王田香,“真凶”是老鬼。整部影片的情节模式围绕“罪案发生—侦探侦案—真相大白”展开,叙事核心聚焦在调查和破解案件上,目的指向谜案的解答,且涉及案件的五男两女互相之间是平等而对立的关系,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对方的敌人或盟友,没有暧昧不清的情感和人物关系作祟,线索只有抓住“真凶”这一条。这大大激发了观众参与推理的热情,因为清白的人物关系不会在关键时刻产生不为推理所控制的结果。整部片子推理路线明晰、节奏紧凑而周密,草蛇灰线的手法也使得出人意料的结果全在情理之中。
在人本主义思想表达方面,《风声》首先表现在对民族救亡意识的坚定,吴志国身受重刑却依然能保持气节不肯屈从;顾晓梦为修正自己传出的错误情报,不惜以自己的尸体作为信息载体;另外吴、顾二人在危急关头关于到底要牺牲谁的短短几句辩论,台词虽少,但演员的肢体动作和表情变化却也强有力地传达出在那个年代党的战士舍身为国的奉献精神。当然,如果只在民族、党国层面上做文章,《风声》的人本主义情怀算不上出众,如前所述,这一部分所表现出来的内容是题材所必有的属性,是任何谍战叙事中的主人公所应有的共性,在艺术感染力上不足以给观众惊喜。而《风声》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以来第一部在口碑和票房上都获得成功的谍战电影,与其给个人层面的人本主义思想所预留的表现空间较大是分不开的。第一,整部影片中出场的所有主要角色的形象立体饱满,例如曾是昆曲名伶的白小年,清高孤傲带着点尖酸刻薄,身为剿匪队长的吴志国则专横、暴躁,每个人物有明确的历史经历,同时在故事结束时也有清晰的结局或未来走向;第二,角色形象所涉及的情感种类丰富,例如顾晓梦和李宁玉之间近似亲人般的友情,王天香和武田、司令等人的职场纠葛与利用关系;第三,在维护正反派对立的基础上,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不回避其才干和个体性,比如武田在对五个人的拷问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谋略,以及别人侮辱自己亲人时的情绪反应。
总而言之,“革命+恋爱”叙事和“侦探”叙事这两种模式在关于人本主义思想的表达空间上都颇具弹性。总体来说,新世纪以来的谍战电影在这方面的佳作寥寥,这意味着谍战与人本主义冲突问题还未成为此类题材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关注重点。“革命+恋爱”在20世纪20年代末有其时代意义,如今再拿来套用,如何从旧艺术道路中走出新步伐,是值得继续深究的问题;起源于西方的“侦探”手法是商业片时代才被大量应用于国产电影的叙事当中,谍战虽然有题材上的侦探意味,但在表现过程中如何避免沦为“智力游戏”、与人本思想融合也应当引起创作者的重视。
三、《悬崖之上》:人本主义表达的新探索
张艺谋导演的谍战题材电影《悬崖之上》于2021年4月30日上映,与同期的影片相比,《悬崖之上》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张艺谋一贯的美学追求成为五一档的票房黑马,上映21天时间票房便突破10亿元大关,并取得了良好的口碑,这足以说明《悬崖之上》在谍战题材上的一些新尝试是非常成功的。
首先,《悬崖之上》把“谍战”作为绝对的叙事内核,影片中每一个场景都为“乌特拉”行动服务,没有节外生枝,故事节奏紧凑且环环相扣。张艺谋在访谈中表示:“我们一直坚持故事优先,故事是根本,故事中含有丰富的情节和人物,我最后的剪辑是完全跟着故事走,很多演员的戏都很好,但很多不得不剪掉,才能保证故事优先,用省略的方法、用减法让每个人物更为立体。”电影市场上商业片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导演在坚持“文艺片”的创作,对人的生存命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以此作为对抗金钱社会中理想和道德失落的依据。但这些“文艺片”非常容易陷入误区,创作者刻意淡化故事在影片中的作用,以大量的慢节奏、微观性的内容来代替,致使叙述失焦,作品散淡且空洞,因为没有牢靠的情节做支撑,抒情和思想便很容易失去根基。张艺谋向来具有自觉的市场意识,纵观他的电影作品,剧本都比较扎实,即便是当时语境中被部分评论者诟病的《英雄》,如今来看也难以否认其线索和主题的明晰。他的创作思路始终没有脱离市场和观众,一直在大家普遍的喜好中寻找、开拓新的表现场域,不失为一种令人钦佩的艺术心态。
其次,《悬崖之上》是部群像作品。“群像”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塑造方式,例如《左传》《史记》《论语》等都采用了这种方式,如今被广泛应用于各个艺术领域。在这部两小时的电影中没有绝对的主人公,各个角色的戏份没有过多偏颇,这也正呼应了我们前述的中国当代文化中集体层面的人本主义思想内涵——“反对英雄主义”,以表现“带有个性的凡夫俗子”为重——张宪臣、周乙、王郁、楚良、小兰以及作为反派的高彬、鲁明、金志德、谢子荣等人,都在整个叙事中占据份额相差无几的逻辑地位,他们各自在“乌特拉”行动的交锋中肩负着某个功能。正如间谍的工作性质一样,电影的叙述话语没有凌驾于角色之上,而是把角色的特性最大化,予以充分的发挥空间,避免了传统叙事中的典型化、突出化等问题。
最后,强戏剧化中的人本主义留白,是《悬崖之上》在类型影片中的新尝试。影片一开场就已经把人物关系和生离死别的处境交代清楚,“活着的去找孩子”是夫妻两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这句话就注定了要有人牺牲,“个体”和“集体”的冲突,也就是“谍战”与“人本主义”的矛盾在剧情展开之前就已经呈现给观众。于是接下来牵动人心的不仅是“乌特拉”行动成功与否,更隐含着对两种对立因素如何化解、个体命运走向和结局的担忧。影片上映后,有评论曾质疑张宪臣因为到马迭尔饭店门口寻找走失的孩子而导致任务失败这个情节的合理性,其实这并非为了剧本的逻辑自洽而做出的生硬推动,反而是谍战叙事中糅合了人本主义思想的魅力所在;父亲对子女的爱与挂念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再训练有素的特工也不会在血浓于水的亲情里成为意外,况且影片在这之前曾有多次铺垫,比如夫妻二人临行前的嘱托、张宪臣和小兰在阳台上的交谈等;不仅如此,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高光时刻”也是属于这对丢失的姐弟——张宪臣在赴死前突然折回,对周乙说“还真有一件小事”,短短的一两句话成为影片的几处“泪点”之一。导演有意把个人情感和家国存亡放在一起去制造悲情共鸣,不仅烘托出浓烈的情绪,同时也在对比之中突出共产党员牺牲精神的伟大,产生了非常好的戏剧效果。梳理整部影片可以看出,关于人本主义的表达在台词总量上没有占据多大篇幅,多数都是点到为止。小兰和楚良的爱情悲剧,张宪臣和周乙在千钧一发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战友情谊,甚至高彬和周乙、金志德的职场关系,任何个人层面的陈述都相对简短,这非但没有削弱表现力,反而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性韵味。当然不仅是台词上的留白,电影在整体的影像视觉上也费了一番心思。影片从头到尾几乎都在下雪,特工们身着黑衣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持枪战斗,雪成为美学层面的一种支撑,用冷酷与寒冷衬托热血和信仰。如果把这种视觉效果看作是集体层面的人本主义延伸,那寒夜里点缀的暖色调灯光则可以理解为对个体性的留白,用一种冷暖对立的视听语言提醒观众,他们既是英雄角色,也是血肉丰满的普通人。“留白”手法起源于我国古代,它和“意境”等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文学艺术史,《悬崖之上》在紧紧贴合谍战叙事的强戏剧化的同时,用“留白”手法把关于人本主义的表达融合在每个角色和情节之中,这对类型电影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也的确取得了优异的成果,既保留了谍战叙事的刺激、紧张氛围,又加强了内容的情感作用,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水准。
张艺谋说:“今天的岁月静好,是有许许多多的人负重前行。我在网上看到许多这样的议论,很感动。一部电影原来可以产生这样大的力量,尤其是让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感受,我很高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悬崖之上》的上映再一次引发了大家对谍战电影的热烈讨论,也势必让很多电影创作者燃起对该类题材的热情。谍战叙事中牵扯到的政治、文化、伦理和艺术等各方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研究、探索。怎样在精彩的谍战故事里融入人本主义思考,在持续紧张激烈的节奏氛围中塑造出成功的角色,这些都是摆在谍战电影面前需要关注的问题。“革命+恋爱”叙事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具有时代局限性,单纯的“侦探”叙事也容易罔顾题材的其他内涵,沦为通俗的“智力游戏”。与人本主义融合是谍战叙事的一个新方向,谍战电影不仅要包括家国大义、民族情怀,也应该给个体的情感、欲望提供充分的表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