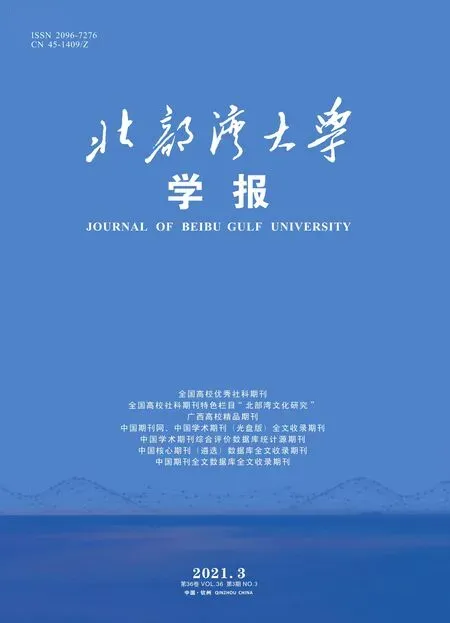枯树、梧桐与白鹭:美国杂志《中国文学》(CLEAR)的唐诗意象研究
,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430072)
引言
由于语言以及文化的差异,美国对于唐诗的研究始于译介,最初以引进欧洲(尤其是英国)的译本为主。 直到20 世纪初期,美国本土才出现唐诗译介(1)根据高超的观点,学界将1912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传奇与抒情诗》一书中译介的三首李白诗歌作为美国唐诗译介的开端。 详情参见天津师范大学高超于2012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及其诗学思想的建构》第一章第三节“美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第28 页。。 受二战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20 世纪的最后30 年逐渐出现了对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专门研究,此时的唐诗研究脱离了早期简单翻译的模式,更加系统化、专业化(2)此时美国汉学界不仅出现了大量选译唐诗的中国古典文学选本(如《中国文学选集》《含英咀华集》《哥伦比亚中国诗选》等),还出现了对李白、王维、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人的专门译介与研究,同时对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李贺、皮日休等中晚唐诗人的关注度也有所提升。 详情参见天津师范大学高超于2012 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及其诗学思想的建构》第一章第三节“美国的唐诗译介与研究”,第28-39 页。。 1981 年,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机构——“唐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唐代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逐渐在美国汉学界受到重视。 《唐学报》(T'angStudies)由唐学会于1982 年创办并发行至今,每年出版一期。 该刊对中国唐代进行全方位的批判性的考察,包括文学、历史、宗教和艺术史[1]。 《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andReviews. 简称CLEAR)作为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权威期刊,其发表的唐诗研究成果很有价值,作者群覆盖了西方唐诗研究领域的颇有建树的汉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的主流观点。 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可以拓展我们唐诗研究的视野,借鉴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找寻中国唐诗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解决当前中国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失语”问题。 唐诗意象是《中国文学》所载论文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中美学者对唐诗意象的考察在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均有较大差异,分析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唐诗意象在海外的研究进展和基本思路。
唐诗讲求“立象以尽意”,意象研究无疑在唐诗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中国文学》所载的唐诗意象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对枯树、梧桐、白鹭等意象的研究,涵盖了动物、植物的意象类型。 汉学家对这些意象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对唐诗意象问题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 《中国文学》的意象研究用“历史描述法”(3)历史描述法:在国际政治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是以历史分析为基础,通过演绎综合并加以类比以揭示其规律。 宇文所安将其运用于唐诗研究中,《中国文学》中的唐诗意象研究也运用了这一方法。梳理意象传统,区别于国内学者的定量研究法。
一、 枯树意象:悲情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于1979 年在《中国文学》发表了《枯树:从庾信到韩愈》一文,该文用大量的篇幅分析“枯树”这一诗歌意象的来源以及对唐代文学家创作的影响。 他认为,自庾信在《枯树赋》中第一次赋予“枯树”象征意义之后,“枯树”就正式成为见于文学作品的“意象”,并在此后漫长的文学创作史中形成了一种“枯树意象传统”[2]。 日本学者兴膳宏则认为,枯树意象虽说出自庾信的《枯树赋》,但其创作渊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枚乘的《七发》,甚至是《易》升卦的象辞[3]。 中国学者蒋寅也认为:“树木以枯病的形象进入文学,始于汉代枚乘《七发》中对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的描写。”[4]虽然对枯树意象的源头探讨仍有空间,但庾信所创立的枯树意象的传统,其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从唐代的卢照邻、骆宾王、王泠然、杜甫、张籍、韩愈和白居易等诗人的创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庾信的枯树意象的影子,他们或继承庾信笔下“枯树”的悲情传统,或“修正”传统的枯树意象,借“枯树”抒发唐代诗人特有的人生理解。 庾信的枯树意象创立于他羁留北朝之时,彼时南朝易主,庾信实际上成为无地可依的政治难民。 因此,他以枯树自况,将枯树看作自己孤苦心灵的投影。在众多诗歌创作中,《枯树赋》最能集中体现庾信的意象风格。 《枯树赋》中的枯树意象化用了《世说新语》中殷仲文的典故(4)殷仲文曾得桓玄宠信,一时风头无两。 但桓玄失败以后,他也受到牵连。 当殷仲文重新回到京都任大司马咨议,他看着院中的树感慨道:“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宇文所安认为庾信流寓北方时的心情与殷仲文一致,现实与典故交互重叠带来双重悲怆感,读来不禁令人感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2]日本学者兴膳宏也认为,庾信的《枯树赋》“将北征后失去活力的空虚的心灵与老树意象融为一体”[3]。 国内学者臧清的看法与上述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庾信的枯树意象更加侧重于内心层面的意指,“是庾信羁臣心态的外化”[5]。 可见庾信的枯树意象最初更加侧重于内心情感的一致性。
在唐代,赋体受到庾信的枯树意象的影响早于诗歌,在正式进入唐诗枯树意象之前,宇文所安先梳理了卢照邻的《病梨树赋》和庾信的《枯树赋》之间的承袭关系。 通过比对不难发现,《病梨树赋》中对“病梨树”意象的描写和所赋予的情感与庾信的枯树十分相似,并且卢照邻还在《病梨树赋·序》中直接引用了《枯树赋》的尾联,可见卢照邻的病树意象有意沿袭庾信的枯树意象传统。 日本学者兴膳宏则注意到二者之间细微的不同,他认为:“庾信将生活在空虚的心境中的自我形象同化于枯树意象,而卢照邻这里,则病树首先是直接象征自己生病的身体。”[3]卢照邻将枯树意象的意指扩大到物质层面的身体上。 在唐诗创作中,宇文所安首先关注到的是与卢照邻同处初唐时期的骆宾王、王泠然笔下的枯树意象。 宇文所安认为,骆宾王的《浮槎》既取材于庾信的同题创作,也取材自枯树意象传统[2]。 在《浮槎》中,庾信的“枯树”被骆宾王改造成一段漂泊无定的“浮木”,它同样是一个悲怆的、能引起读者同情的意象。 但是宇文所安认为,骆宾王“为这棵树的衰落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它的毁灭不是由于繁盛和衰败的自然过程,而是因为机遇,因为‘时代’”[2],待时过境迁后它仍可成为栋梁之材。 作为政治失败象征的“枯树”在骆宾王笔下重获希望与价值。 宇文所安认为,王泠然的《古木卧平沙》代表了初唐诗歌的另一种体系,即格律和内容都被严格限制的应试诗[2]。 除了枯树本身的表征,王泠然还增加了对枯树外部环境的描写以及外部环境对枯树的影响,宇文所安认为这种突破不同于《浮槎》,它来源于形式上的限制,《古木卧平沙》是标准化写作的产物。 即“在王泠然的诗中,枯树传统的主题被从更大的语境中移除,并成为子题的构成部分……应试诗的写作规定取代了任何形式上的创造性冲动,并且粉碎了枯树意象的强大传统。”[2]
宇文所安认为,初唐诗人大多延续了庾信笔下“枯树”的悲情传统,而对枯树意象的“修正”直到杜甫才得以开展。 宇文所安着重分析了《枯楠》和《古柏行》两首诗,认为杜甫对庾信枯树意象传统的修正“始于《枯楠》,在《古柏行》中得到完善……当杜甫(在《古柏行》中)以恰当的顺序列举主题的预期成分时,它们的意义就被打开、改变了”[2]。 在杜甫的笔下,“枯树”不再只是受人同情的悲惨形象,它虽然也经历风霜,遭人遗弃,但却不改本色。 日本学者兴膳宏则将考察范围扩大到《病柏》《枯棕》《病桔》《枯楠》这一组作品中的枯树意象[3]。 中国学者蒋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组作品中包含着诗人对个人、社会、王朝前所未有的深刻思索,涉及个人前途黯淡、民生凋敝、君主失德乃至王朝没落诸多重大主题,这些思索导致杜甫晚年思想的若干重要变化,也使这组作品成为他晚期创作中最具思想深度的开拓。”[4]三位学者都看到了杜甫对庾信枯树意象的改造:杜甫在诗歌中使用枯树意象,不仅是为了抒情言志,他的深层目的是引领社会的价值观。杜甫笔下的“枯树”不仅被注入了诗人自己的品格,也成为诗人心目中国家栋梁的象征,通过枯树意象传达出来的“为生民立命”的宏阔胸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宇文所安看来,在杜甫去世之后的几十年中,中晚唐诗人大多不重视杜甫其人其诗,所以杜甫的枯树意象对后来诗歌创作的启发不大。 只有韩愈、张籍、白居易三位诗人才认识到杜甫及其诗歌的重要性,他们沿着杜甫的枯树意象传统,完成了枯树意象之新变(5)这三位诗人都在相近的时间写出了有关“枯树”的诗歌作品。 韩愈《题木居士二首(其一)》《枯树》、张籍《古树》、白居易《枯桑》,而这些作品具体的关系已不可考。 宇文所安在《枯树:从庾信到韩愈》这篇文章中对这四首诗的关系序列作出一个有趣的假想:“其顺序是,韩愈的《木居士》(可能是在公元806 年创作),其次是张籍的《古树》,韩愈的《枯树》是对张籍《古树》的回应,而白居易的《枯桑》则是对韩愈《枯树》的戏谑。”。宇文所安认为,张籍和韩愈努力地在诗歌中淡化枯树意象的宗教意味,以便区别于杜甫笔下“枯树”的神圣性。 韩愈试图在纯粹道德的角度批判杜甫的“枯树”,他认为杜甫笔下的“枯树”高傲而自矜,空有高贵的自尊却不为此付出行动,“诸葛亮庙的古柏不一定拒绝被砍倒,但也不向往斧头”[2]。 因此韩愈笔下的“枯树”拥有了更加实际的行动意志,宁可完成“低一等”的使命,也不愿顾影自怜、郁郁而终。 而白居易作品中对杜甫枯树意象的超越在于对调侃的写作方式的运用,他用戏谑轻松的口吻讲述枯桑的故事,但是却饱含对“枯树”现状的忧虑,流露出对苦难诗人的同情与深切担忧。
纵观唐代诗人对枯树意象的使用,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意象并非单独出现的独立意象个体,而是对整个枯树意象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宇文所安认为:“诗歌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敏感的读者必须听到文学过去编织成诗并被它改变的各种线索。 但过去既不是传统评论的无实体短语,也不是现代评论的替代者——它是由完整的、互动的文本组成的复杂整体。”[2]我们在阅读这些诗歌的时候,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它们,而是要联系使用相同意象的其他作品,把诗歌中出现的意象放在前代的传统之下考察。 兴膳宏则由唐诗中的枯树意象联想到日本诗人三好达治诗歌中对樱花树枯死的叹惋,指出不论文化背景的差异如何,“枯树仍然是经常触发诗人心中对他自身遭际的深深哀伤的媒介”。
二、 梧桐意象:象征意义的场景化表达
麦大维(David R McCraw)的《沿着梧桐的足迹:中国诗歌中的桐树》梳理了“梧桐”这一意象在唐诗中的运用情况。 与上文梳理的枯树意象不同,“梧桐”不仅自成一套意象传统,并且还多与其他意象结合共同构成象征意义。 考察唐诗中的梧桐意象,实际上是考察梧桐及相关意象群的使用及其流变。 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都采用了分类的方式来研究不同背景下梧桐意象的不同内涵。 麦大维的分类是:梧桐与凤凰、梧桐与秋天、梧桐与爱情、梧桐成双、梧桐的象征义、梧桐的个别意义[6]。 中国学者俞香顺将这些意象分为:梧桐与音乐(此类中又分为孤桐、半死桐和焦桐)、梧桐与悲秋情结(此类中又分为井桐、疏桐、梧桐夜雨)、梧桐与爱情(此类中又分为双鸟与双桐、“梧桐”与“吾同”谐音双关、桐花鸟和桐叶题诗)[7]。 国内其他学者与俞香顺的观点类似,但分类不如俞氏完整,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麦大维将唐代诗人李峤笔下的“梧桐”作为唐诗中梧桐意象的开端。 他认为李峤在《桐》这首诗中塑造的梧桐树并不是一棵特定的树,而是崇高辉煌的理想,是一个“意象”[6]。 俞香顺认为:“李峤是第一位有意识、有计划创作咏物诗的作家。”[7]因此应将李峤笔下的“梧桐”视作唐代诗歌中梧桐意象的起点。 而李峤笔下的“孤秀峄阳岑,亭亭出众林”,明显化用了“峄阳孤桐”的典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 虽然俞香顺把“孤桐”放到“梧桐与音乐”这一分类下,但是他仍然单独梳理了“孤桐”人格化象征的来源与流变。 俞香顺认为六朝时“孤桐”才开始作为文学意象出现,他认为:“晋司马彪的《赠山涛》诗中有了孤桐意象之雏形……南朝宋鲍照的《山行见孤桐》中明确标举孤桐意象。”[7]李峤的“梧桐”实际上是沿着这个意象传统创作出来的。 而在李峤之后,“孤桐意象在陈子昂、张九龄的作品中有了突跃……对孤桐之刻画由‘直影’到‘虚心’,由表及里,体现了认识的深入,对孤桐内在品性的发现,已具人格象征之意味。 ……白居易则在充分认识梧桐生物属性的基础上,拈出其与士大夫处世立身相合的特质,即‘孤直’,从而赋予了梧桐以明确的人格象征意义”[7]。 同时,以麦大维和俞香顺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也都注意到“孤桐”与琴之间的联系。 梧桐的材质适宜制琴,名琴“号钟”“绕梁”“焦尾”“绿绮”均是由梧桐所作,因此,“孤桐”在后世成为琴的代称,在“孤直”的基础上增添了清雅高洁的意蕴。
麦大维发现,在李商隐的诗中,梧桐总是与凤凰一同出现,《圣女祠》《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书即事一章》《丹丘》《蜀桐》这四首诗都是如此[6]。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梧桐可以招来凤凰,是祥瑞之兆。 但李商隐却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注重发掘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它们拟人化,赋予了人的情感。 李商隐在《丹丘》中写道:“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凤凰飞走后,梧桐思念着凤凰,等待它的归来。 李商隐借梧桐与凤凰比喻君子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暗含了他对李德裕的同情与思念。 俞香顺则认为,“‘桐花凤’或者‘桐花鸟’的说法在唐朝开始流行”[7],意指美好的爱情。 这与麦大维从《丹丘》中解读出的君子之交有细微差别,但它们都是梧桐与凤凰意象所能代表的含义。 王昌龄的《段宥厅孤桐》着重描写秋天的梧桐,在秋天的背景下,梧桐意象更添萧瑟清冷之感。 对此,麦大维解释道:“它描写的梧桐,实际上是逆境中君子的写照。 梧桐孤独、寒冷、贫瘠、空洞、正直、痛苦,寻求着同情和理解。”[6]俞香顺也认为梧桐与秋天在梧桐意象群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梧桐叶落成为秋至的象征性景物,是悲秋主题的重要意象”[7]。除《段宥厅孤桐》外,在白居易的《早秋独夜诗》和王昌龄的《长信秋词》中都借助梧桐意象表达了悲秋主题。
而白居易笔下的“梧桐”,在麦大维看来则开创了“梧桐与爱情”的意象传统[6]。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分别用桃李和梧桐象征杨贵妃生时的灿烂和她死后唐玄宗的哀恸。 《长恨歌》中梧桐与浪漫爱情的联系就此延续,这种联系不仅为白朴的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提供了灵感,也在元末明初高启的《明皇秉烛夜游图》以及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中得以传承。 俞香顺则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角度分析,得出了“‘梧桐夜雨’是中唐特定的时代氛围中所产生的特定意象”[7]的结论,认为“梧桐夜雨”属于听觉意象,“黑夜的笼罩、空间的阻隔等都会导致视觉意象的遮蔽;而听觉意象可以洞穿黑夜、度越空间,让主体无所遁逃”[7]。 此外,麦大维还着重分析了《长恨歌》中“梧桐”(wutong)与“吾同”(we together)的谐音双关现象,并认为这一双关将杨贵妃与唐玄宗二人的爱情衬托得更加凄美,“斯人已逝,‘吾同’不可追,唯有‘梧桐’在眼前”[6]。 除了在杨贵妃与唐玄宗二人爱情故事中的运用,“梧桐”与“吾同”的双关还逐渐形成了“梧桐成双”的意象传统,陆龟蒙的《井上桐》和孟郊的《烈女操》都借用井边的梧桐来象征年轻的女子,通过“梧桐成双”来象征女子与伴侣二人的亲密关系。 俞香顺也注意到这一双关现象,并指出早在北朝的诗歌中,“梧子”就多与“吾子”双关,“双桐枝叶相交,象征着纠结、缠绵、至死不渝的爱情”[7]。
在麦大维看来,李贺与孟郊使用的梧桐意象与其他唐代诗人都不同,因此需要分别研究他们对梧桐意象的个别化处理。 李贺的《九月》《秋来》和《官不来,题皇甫湜先辈厅》通过对梧桐意象的运用和描写传达强烈的愁苦情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李贺创作风格所特有的场景与情感之间的戏剧性关系”[6]。 孟郊笔下的“梧桐”相较其他诗人,明显体现出粗犷的特征,如《秋怀(其二)》《秋怀十五首》,其中的《饥雪吟》甚至描写了梧桐在冬季的境况,在麦大维看来,这是孟郊诗歌创作的多样性与创造性的表现,因为“对于大多数中国诗人来说,冬天的梧桐是一个非常‘不合逻辑’的话题”[6]。 俞香顺则直接把孟郊的《烈女操》归入“梧桐与爱情”系列的“双鸟与双桐”类别中,未进行单独研究。
对于梧桐意象的研究,麦大维认为:“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它更像是一条小路,而不是主干道。它不像梅花或松树那样是一个关键的象征。 然而,对于那些想全面了解中国诗歌的人来说,探索它的诗性意义是至关重要的。”[6]王昌龄、杜甫等诗人的创作(如《长信秋词》和《宿府》)也会以梧桐为主要意象,借以抒发其他意象无法表达的愁苦思绪。 俞香顺总结道:“梧桐,尤其是孤桐,在后来成为人格象征的符号……梧桐又是琴材,文人操琴是雅人深致,借以寄托心声,琴声的含义投射于梧桐,丰富了梧桐的内涵。 悲秋是文学中亘古的主题,而梧桐及其相关意象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意象。 梧桐又是中国民间种植最广的树种之一,与日常生活,如爱情、乡情等都发生了联系。”[7]两位学者都指出了梧桐意象在唐诗乃至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梧桐意象的研究是唐诗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 白鹭意象:双重身份的隐喻和白描
《中国文学》对白鹭意象的分析,集中于柯睿(Paul W Kroll)的《中世纪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白鹭”》。 柯睿认为唐代诗人对白鹭的重视源于私人园林的兴盛,“唐代官吏贵族的私人园林的规模较前代有了很大的扩展,园中种植着各色植物,摆放着奇石珍宝,还饲养着各类珍禽异兽,其中白鹭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8]。 唐代诗人李德裕赞美园林景色的组诗中的一首——《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白鹭鹚》专门写到了白鹭,而李德裕的平泉庄恰好以精心布置和优雅而著称。 在李德裕眼中,园中景色美则美矣,但加上白鹭的流连栖息,便给静谧的园林增添了几分清洁灵动之美,二者一动一静共同构成了“清景”。 李德裕笔下的“白鹭”不仅是平泉庄中的一抹亮色,也是诗人隐逸理想的象征,诗的后两联写道:“碧沙常独立,清景自忘归。 所乐惟烟水,徘徊恋钓矶。”当时李德裕被贬在外,无法回到精心修筑的平泉庄。 赵建梅认为,此时李德裕笔下的“白鹭”“成了高洁不俗的隐士形象;园中钓石,令诗人想到汉代隐居不仕垂钓水边的严光……挥纶自适,是诗人怀慕的境界”[9]。 白居易也十分推崇白鹭在园林中的作用,把它们称为“雪客”。 五代诗人李昉在此基础上将白鹭在内的五种鸟唤作“禽中五客”,其中鸥为闲客,鹤为仙客,鹭为雪客,孔雀为南客,鹦鹉为西客(6)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载:“昉所畜五禽,名五客,仙客鹤,雪客鹭,闲客白鹇,陇客南客孔雀,西客鹦鹉,有诗云。”见《宋诗纪事》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9 页。。
但柯睿同时也指出,白鹭意象并不是一开始就与园林密切相关,而是高洁之士的象征:“白鹭从最早出现在书面文字中的时候起就被用作并被认为是一种象征纯洁和道德价值的动物群形象,可追溯到《诗经》。”[8]《陈风》《周颂》和《鲁颂》中常用一群排列整齐的白鹭象征参加祭祀的达官贵人,传达出人心像白鹭一样纯洁的象征意味。“因此,白鹭的文学谱系是正统的古典文学谱系,一些中世纪诗人在自己的诗句中将白鹭作为意象使用时,有意识地使用了古代赞美诗中的隐喻。”[8]白鹭是群居型候鸟,定期南北穿行,这与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员流动很相似。 另外,白鹭迁徙时按照长幼尊卑有序地飞行,这种对等级秩序的严格遵守与朝廷对官吏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晚唐诗人李频也认同白鹭意象的这一隐喻,在《省试振鹭》中用白鹭象征官吏,其中“君臣将比洁,朝野共相欢”“由来鸳鹭侣,济济列千官”两联明确将唐朝官吏比作白鹭,借以说明官吏有序自持,朝堂人才济济,一派清明景象。 刘长卿的《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白鹭》云:“如有长风吹,青云在俄顷。”以白鹭乘风振翅入云霄喻官场上得贵人相助可平步青云,同样也是将白鹭比作官吏。 刘象笔下的白鹭则“象征着清高的士人退隐或被逐出宫廷,在外省经过一段时期的修身生活后,重新回到自己应有的位置”[8]。
但唐代诗人对“白鹭”这一意象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古典文学的传统,也有诗人将白鹭放入咏物诗中,将它作为一种真正的鸟类来欣赏。 白鹭的羽毛呈白色,身形修长,因此白鹭总是和同样高洁清逸的事物一同比照着来写。 如杜牧和陆龟蒙用雪来刻画白鹭的洁白:“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鹭鸶》)“雪然飞下立苍苔,应伴江鸥拒我来”(《白鹭》);唐代诗僧贯休的《鹭鸶有怀》则是用霜来衬托白鹭的高洁:“粉魄霜华为尔枯,鸳鸯相伴更堪图。”在这些诗人的笔下,白鹭被比作雪和霜,白鹭是被当作审美对象(而非象征物)而描述和刻画的。 在众多咏白鹭的唐诗中,柯睿发现除了歌咏白鹭高洁的诗之外,也有以白鹭借喻容易招人嫉妒的有志之士的诗歌。 他认为罗隐的《鹭鸶》想表达的含义即为“白鹭的美丽高洁虽然令人向往,但也势必会招致灾祸”[8],故白鹭应当“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贾岛则设想一双白鹭中的一只被猎人射中,得以幸存的白鹭“失侣遇弦惊”,陷入孤寂恐惧和对前程的担忧之中。
除了将白鹭作为一种动物来描写外,中晚唐诗人也关注室内装饰物上的白鹭,“把白鹭的舞台由野外转移到了室内”[8]。 如张乔的《鹭鸶障子》就是描写屏风上的白鹭:“剪得机中如雪素,画为江上带丝禽”。 而在器物装饰上,白鹭最多的是作为鼓的装饰出现。 鼓的木质支架上,常雕刻有飞翔的白鹭,用作祭祀或战争,唐诗中描写的白鹭也有作为鼓架的木质雕刻。 柯睿认为:“这些出现在室内装饰品上的白鹭虽然美丽优雅,风度翩翩,但终究是被驯服了的,华美之下暗藏的致命危机也与唐朝气数将尽暗合。”[8]另外柯睿还注意到,白鹭意象的神化变形在诗歌中体现为“白鹭”转化为“朱鹭”,而“朱鹭”自楚威王时期开始就被认为是西王母的使者,是吉祥的象征,一旦成为“朱鹭”,白鹭意象就具有了神话意味[8]。南北朝诗人苏子卿笔下的“朱鹭”即为常人所不得见的神鸟。 但和前面分析的唐诗中的白鹭意象一样,唐代诗人笔下的“朱鹭”也有脱离神话和典籍赋予的神性传统的倾向,此时的朱鹭不再是神的代表,相关诗歌也鲜与神话或者政治题材相关联,诗人笔下的朱鹭只是一只活生生的鸟。 张籍的《朱鹭》展现了自由热烈的朱鹭被残酷地网住,以致母子分离的凄惨处境:“谁知豪家网尔躯,不如饮啄江海隅。”诗中传达的是对自然生灵的怜惜与喜爱。 但是柯睿发现,在唐朝的最后几十年中,“诗人们不再热衷创作这些暗含悲观情绪的诗,转而畅想白鹭挣脱牢笼后的自由生活”[8],这或许是作者出于冲破时局的渴望在诗中的表现。
具有基本的中国文学素养的人对唐诗中的白鹭意象并不陌生,杜甫“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名句脍炙人口,但关于唐诗中白鹭意象的专门研究鲜少。 国内学者多将白鹭意象归于“飞鸟”或“鸟”中进行笼统考察,而国外学者如柯睿也仅仅梳理了中世纪文学中白鹭意象的使用,没有进一步分析其在整个唐诗意象中所处的位置,抑或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些内容都有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四、 《中国文学》中唐诗意象研究的独特性
王德威在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概述之后,对研究现状进行了理性反思:“在审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成果时,我们可以有如下的论题:西方理论的洞见如何可以成为我们的不见——反之亦然? 传统理论大开大合的通论形式和目前理论的分门别类是否有相互通融的可能?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西古今的壁垒可以被重新界定,中国文学论述的重镇——从梁启超到陈寅恪,从王国维到王梦鸥——可以被有心的学者引领到比较文学的论坛上?”[10]他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从事海外汉学与中国学研究面临一个逐级推进的阶梯,那就是对海外成果从评介、消化、对话到建构的不断升级的过程。 王德威在此提出了中西比较的话题,启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中唐诗意象研究相对于中国学者的独特性。
(一) 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国内的唐诗意象研究成果丰硕,大多集中关注风、雨、月、花、草、舟船等普遍使用的意象,在相对固定的意象传统中考察,倾向于找寻众多诗人对某一意象的写作偏好,总结唐诗中出现的某些意象的共通之处,相对而言自成体系。 《中国文学》所载论文对唐诗意象的研究,则关注到枯树、梧桐、白鹭这些较少单独讨论的意象,它们或是使用较少的意象,或是主流意象中较少为人所关注的某一类别。 汉学家们也像国内学者一样重视研究意象传统研究的传承,但是他们似乎更加注重个体研究,通过唐代诗人内部的比较与参照,着重论述不同诗人对意象传统的改造和发展。 这种对冷门意象的关注,虽然受作者自身知识背景所限,但了解他们的成果应有助于国内学者寻找研究上的突破。
(二) 学科融合的独特性
从《中国文学》唐诗意象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汉学界的唐诗意象研究视野最大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 汉学家在分析唐诗意象的使用时,往往旁及历史、哲学、政治、生物、艺术等学科。 他们不仅重视诗歌对意象的描写,还将意象还原至历史语境,将其作为本身(而不是抽象的语汇)来考察,大大拓宽了论文的宽度和容量。 正如周勋初所说:“学问之道又贵触类旁通。 这也就是说,学者掌握的知识门类越多,那他通过交叉学科的渗透而酝酿出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11]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沿袭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从根源上剖析意蕴,既重视诗人群体的共性,同时也考虑到每位诗人意象使用的风格差异,就这一点而言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过国外的意象研究。 由于学术传统的承袭以及近代学科的划分,国内的研究对文学内部的互动与流变的关注占据绝大部分,汉学家具备的跨学科研究视野,正是国内学者需要继续加强的地方,同时也对国内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具有更深厚的知识储备。
(三) 研究方法的独特性
在唐诗意象的分析中,中西方学者倾向于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宇文所安曾就唐诗研究提出“历史描述法”,他尤其重视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历史语境,注重影响诗人创作的一切历史细节与文本细节,试图对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进行具体化、客观化的描述,从而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原貌,归纳出既合乎历史逻辑又符合诗学一般规律的正确结论。 这种“历史描述法”在《中国文学》的唐诗意象研究中也有所体现。 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汉学家们倾向于将某一意象的出现和使用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试图找出这一文化现象与当时其他议题的联系;非常注重诗歌和意象身处的历史背景,探讨某一意象的生成和意义时,从文化传统出发兼论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甚至是神话传说。 又因唐代采取科举选官,他们尤其重视科举制度、文官制度等对诗人创作的影响。 汉学家们的唐诗意象研究不再是对某一文化符号的探讨,而是尽可能接近文学史原貌,还原某意象的历史语境。 中国古代关于意象的研究混杂于文学作品的研究之中,并且多以诗性的话语进行概括和描述,仍然属于经验层面的分析,未成体系。 国内的当代唐诗意象研究因涉及诗歌数量极多,多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用数据和大量的诗句引用来直观地说明唐诗对某一意象的偏好,以此作为研究的支撑,同时在每一类中选取典型诗作进行分析论证。 而汉学家们则倾向于定性分析,受知识背景和可见文献的限制,他们多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某一意象的生成、传承与变化,将非著名诗人与著名诗人置于同等地位进行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梳理某一意象在唐诗中的使用。 综上可见,有必要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给出唐诗意象研究的总体分析,确定其在意象传统中的地位,再以定性研究的方法梳理某一意象在唐诗中的脉络。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在研究方法上拓宽了进一步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空间。
(四) 研究文献的独特性
汉学家对原始材料十分重视,这已经成为一种语文学(Philology)的学术传统。 1873 年,德国汉学家欧德里(Ernest J Eitel)在《业余汉学家》一文中批评业余汉学家对原始文献解读肤浅,言不及义。 首先,他提倡专精的研究:“我们在接触中国文献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未知领域还很广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掌握全部内容。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取一个分支,进行专门的研究。”[12]其次,他主张基于原始资料进行公正解读:“我们应该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当然也包括诸如注疏、传记和百科全书这样的二手材料,并利用哲学思维历史地、思辨地检验和批评这些材料。 不对任何东西想当然,也不依赖于潮流和传统的力量,而是严格地检验那些被称为确凿和古典的事物的真实性,公正地就事论事,就像我们坐在检验法庭的凳子上一样。”[12]欧德里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传统欧洲汉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与学术规范。 的确,近代以来,专业汉学家们由于语言、文献获取等方面的困难,在研究时非常重视原始材料,他们往往直接对原始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在文章中较少使用他人的整理成果。 因而其观点较少受到已有研究成果的束缚,提出的观点以及关注的角度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其中某些结论也许会因此有所偏差)。 国内对于唐诗意象的研究已有很多著述,学者在研究时不自觉地会依赖权威学者或经典论著,虽然这样可以快速地捕捉到意象研究的脉络,但也容易限制自己的思维。 如果重视原始材料,利用语言优势直接与原始材料对话,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限制与阻碍。
虽然以上从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文学》中唐诗意象的特色,但是这种中西比较而言的差异状况也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绝对的界限,而且国内外之间的互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因而不可过于夸大这种差异。 正如孙康宜所说:“国人(至少是中国大陆的读者们)对于美国汉学的新趋势似乎所知甚少。 他们仍然是以一种仰视‘洋人’的态度来评价美国的汉学家,以为美国汉学‘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结论’都与中国国内的研究‘不一样’,似乎二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其实,如上所述,今日的全球化已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同是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和历史,每个学者(不论在中国大陆、台湾,或是美国)都代表着各自不同的声音,中西之间固然还有区别,但同时也在出现新的融合。 对于西方的‘汉学家’,国人只需以平常心对待,不必特别抬高他们的身价,也不应出于自卫的排斥心理而妄加轻视。”[13]孙康宜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中西学者的互动和对话更加频繁,在思路和方法上不断走向融合,因此需要以平等的态度或者说平常心去理性看待西方学者的成果,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可夜郎自大。
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际,笔者还想补充介绍美国和日本在唐诗研究方面的一些历史状况,从而与《中国文学》的唐诗意象研究形成对话。 首先,美国汉学家对唐诗的研究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相融合。 宇文所安创立了“历史描述法”,即注重把握诗人创作的历史语境,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和诗作的内涵。 刘若愚致力于探索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古代诗歌及其理论。 高友工与梅祖麟则从现代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的新视角来观察唐诗的句法、用字与意象以及语意、隐喻与典故,探讨唐诗在音韵、节律、意蕴等语言学层面上的美学风格[14]。 其次,日本有许多学者在唐诗意象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老一辈学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论文,前野直彬的《风月无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 年)、松浦友久的《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研文社,1981 年)二书是比较集中地进行意象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5]津阪东阳的《夜航诗话》和《夜航余话》对中日两国诗歌意象风格的异同展开了深入比较;市川桃子长的《中唐诗在唐诗之流中的位置——由樱桃描写的方式来分析》《乐府诗采莲曲的诞生——荷花形象》对“樱桃”“荷花”意象进行了研究;兴膳宏的《枯木上开放的诗——诗歌意象谱系一考》则考察枯树意象在唐诗中的运用;有深泽一幸的《蜂与蝶——李商隐诗的性表象》得出“蜂”与“蝶”意象具有性意蕴这一独特新颖的结论;矢嫣美都子的《楼上的思女——试论闺怨诗题材的源流与发展》则围绕“高楼”“土垣”“高台”等意象作细致探究,阐述“登高致思”的特定内涵;埋田重夫的《白居易白发诗歌表现考》一文,探讨了白居易诗歌中频繁出现的“白发”意象;笕文生的《“绕床”考》则综合考察了唐诗的“床”意象[16]。 中国本土的唐诗或者唐诗意象研究应该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比较关系与交互关系,在世界视野中展开中国学术与国外学术的对话与交流,尊重他者的文化差异,在“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中创建本土的知识与思想,在跨文化的双向阐释中形成新的知识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