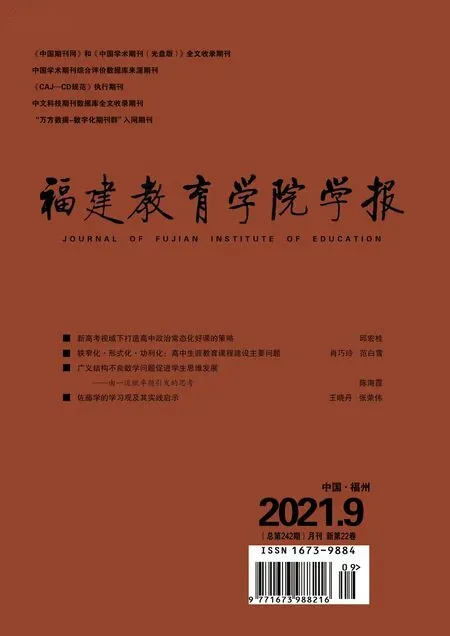整本书视域下的高中小说节选文阅读方略
陈君平
(泉州市第七中学,福建 泉州 362000)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对“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做出如下教学提示:“指定阅读的作品可以从教材课文节选的长篇作品中选择。”[1]这意味着小说节选文教学可以“篇”带“本”,延伸至整本小说的阅读与研习。整本书阅读,与节选文文本细读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倘若只掌握了小说整本书的故事梗概、人物关系等整体构架,无异于只是获取了名著的压缩风干物。正如叶圣陶强调,应“以精读选篇为例子与出发点,由此扩展开来,阅读其他文字,并整本的书,拓展认识。”[2]既要依据作品的全息性,把小说整本书的选篇放在整本书的视域下进行审视和设计;又应把行之有效的小说节选文解读方略运用到整本小说中那些能带动整体理解与鉴赏的相关篇章中。梳理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小说节选文,分布如下:1.必修下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变形记》,对应文学阅读与写作单元任务群;2.选择性必修上册,《大卫·科波菲尔》《复活》《老人与海》《百年孤独》,属于外国作家作品研习单元任务群;3.选择性必修中册,《小二黑结婚》,属中国革命传统作品研习任务群;4.选择性必修下册,《边城》对应的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
笔者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小说节选文为例,探究整本书视域下的小说节选文阅读方略,引导学生从课内延伸至课外,研习、研讨小说整本书阅读,以期为教师设置单元学习任务的下位问题提供参考。
一、关注文本统一处
(一)寻找与整本小说文本特色契合的节选文切入点
教材编者力求以“读书”为本,精挑细选教材选文,体现《课标》中“教材中的选文应具有典范性与时代性”[3]这一要求。统编教材中所选用的小说节选文,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现整本小说的无限精彩,指向整本小说的文本着迷点。若能在教学处理中寻找与整本小说文本特色契合的节选文切入点,则完全有可能实现“篇”与“本”之间的有机关联。
以选择性必修上册外国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为例,课文《大卫·科波菲尔》节选自小说第十一章“独自谋生”,成年大卫与童年大卫双重视角交叠,这也正是整本小说的特色。《复活》节选文中涅赫留朵夫内心的自我矛盾与斗争,正是典型的托尔斯泰式“心理活动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川流不息的变化之中”[3]的写法。《老人与海》节选文简洁客观的叙事风格与整本小说乃至海明威大多数作品的摄像机式的冷静叙述不谋而合。《百年孤独》节选文中马孔多人感染了“失眠症”严重至遗忘的程度,看似魔幻荒诞,但却有着真实的喻旨——历史遗忘症;文中丽贝卡吃土、乌苏拉看见丽贝卡梦境等魔幻细节,又是建立在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上。书中呈现出魔幻性与现实性兼具的特征正是《百年孤独》整本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这些节选文不仅是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还从言语形式上呼应着整本小说的艺术特色,指向整本小说的精神内核。
依乎整本小说之“天理”,因其文本特色之“固然”“批大郤,导大窾”,以“篇”带“本”,自是游刃有余。
(二)探寻节选文与其他章节指向文本精彩的呼应处
有些小说的节选文与其他章节之间,并不止步于小说内容的因果关联,还在内在逻辑上相互呼应,共同指向文本的精彩处。小说的重要篇章是构成全书的不可或缺部分,不仅关乎整本书的完整性,更是与小说的精神、骨髓息息相关。小说《小二黑结婚》情节连贯,环环相扣:第1-5 节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神仙”的故事引出了小芹、兴旺兄弟和小二黑的故事;第6 节“斗争会”到第8 节“拿双”展现了矛盾的激化。选择性必修中册节选了《小二黑结婚》第9-12节,其中的第9 节“二诸葛的神课”,二诸葛在二黑和小芹被抓走后,依然想依靠占卜算卦来寻求解决办法,赵树理在这一节中完成了矛盾激化前的最后准备。而紧接着的后三节,激化的矛盾得到了解决:外部矛盾方面,兴旺、金旺得到了惩治;内部矛盾方面,二诸葛和三仙姑封建迷信意识发生了转变,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到婚姻自由。小说其他章节与教材节选的相关章节,共同指向了整本小说情节连贯、环环相扣的特点,呈现了从矛盾的激化到矛盾的解决的过程,引人入胜。小说节选文与其他篇章形成互补关系,更为完整地呈现整本小说文本特色版图。
二、挖掘矛盾缝隙处
(一)品读节选文与其他章节的文本矛盾
小说节选文与整本小说中的其他篇章的文本内在矛盾,常常是文本费解处,倘若能就此“从作品内部的情感结构做深层次的分析,最后达到认识的和谐与统一”[4],最终将达成整本小说的深度解读。“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任务群中《边城》的相关单元研习任务为:“‘《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你是否有类似的阅读感受?循着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去思考探究,形成对作品的理性认识。”《边城》节选文尽显沈从文着力歌颂的“恰如其分的爱与美”——人性美。而节选文外的小说结局,天保罹难,傩送出走,白塔倒掉,祖父去世,翠翠在渡口孤寂地等待傩送的归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一任务立足于《边城》节选文部分与小说结局之间的矛盾,既指向整本小说的主题理解,又具有解读的多元性。在研讨中,有的学生认为,沈从文向我们展现的人性之美并非完美至善,翠翠的懵懂和忸怩、二老傩送对哥哥去世的愧疚与不安,这些纯真质朴的情感最终使翠翠的爱情无法继续。他们都太淳朴、善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伤害别人,于是产生了误会。有的学生则认为,美丽总是令人忧愁。《边城》展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指向整本书矛盾的课堂研讨激发了学生的言说欲,生成了精彩纷呈的个性化理解。在整本小说的视域下,于节选文与其他篇章的文本矛盾处设疑,让学生向整本小说更深处漫溯。
(二)比对小说节选文与其他篇章的人物行为矛盾处
深入比对小说整本书中人物自身行为前后不一致处,往往能探究出小说人物的性格着迷点。前后行为的矛盾,往往展现着人物性格动态的变化成长。“情节的曲折,脱不开性格的纵深层次,其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就随着这种层次而提高。”[5]性格的丰富与多样,塑造着立体化的人物,使之避免趋于扁平。
抓住教材节选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水浒传》第九回)林冲行为的变化,立足于整本小说视域下,可准确解读其性格转变。“酒葫芦”“被”和“钥匙”是林冲在外出沽酒和草厅雪塌时都随身携带的,而在出门投东时,他“再穿了白布衫,系了搭膊,把毡笠子带上……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前后行为的矛盾意味着什么?他丢掉了象征安寝与享受的被与葫芦,扔掉了和现实世界握手言和的钥匙;留下的白布衫和毡笠子是严冬御寒的用具,枪是闯荡另一个世界的武器。[6]这样的行为变化指向的是林冲性格由隐忍到血性的转变。
放眼到其他章节,能更全面感受其性格的转变。节选文中林冲手刃陆虞侯可谓血腥,“掇、挺、拽、搠、提、丢翻、踏住、扯、剜、割”一系列动作迅疾有力、狠辣准确,展示了其血性的一面。纵观七至十二回,出现“不敢”6 次、“怎敢”1 次、“如何敢”3 次、“哪里敢”2次、“岂敢”1 次、“敢道怎地”1 次。[6]从林教头到豹子头,从慈眉到怒目,从“忍”到“狠”的性格转变,指向了当时官府制度的黑暗,英雄也由此被迫诞生。
三、勾连篇章重复处
(一)捕捉小说节选文与其他篇章中反复出现的人物行为和心理
复现意味着聚焦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小说人物矛盾的累积。小说中复现的人物行为与心理,展示着人物的性格、心理、情感。在整本书视域下,节选文与其他篇章中重复的人物行为与心理,更能呈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托尔斯泰善于展示心理流动形态的丰富性。教材《复活》节选文第一部43 章集中刻画了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流动。当玛丝洛娃向聂赫留朵夫要钱时,聂赫留朵夫内心发生了动摇。“魔鬼的我”怂恿他用金钱来撇清和玛丝洛娃的关系,放弃对玛丝洛娃冤案的申诉、精神的救赎;“精神的我”一方面请求玛丝洛娃对自己的饶恕,另一方面希望玛丝洛娃能够觉醒。最终精神世界的天平倾向了“精神的我”。这样的心理流动多次在整本小说中重复呈现,教学过程中可由节选文的心理层次欣赏延伸至全书的相关章节。
在第1 部28 章中,当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玛丝洛娃后,他决定净化自己的灵魂。“内心的魔鬼”和“自由精神的我”展开了对话:“人人都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与“冲破束缚精神的虚伪罗网”两种声音撕扯;自我觉醒的好的泪水与自我感化的坏的泪水交织。第3 部第5 章在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聂赫留朵夫对玛丝洛娃的感情发生流动式的变化,这种感情不同于法院判决后他以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的心情,而是更为强烈、纯粹的怜悯与同情。第17 章中,当他得知西蒙松对玛丝洛娃的求婚后,作品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剖析了他的内心:他因独特的高尚行为无法实现而痛苦,因自我牺牲贬低了价值而沉重,因生活计划被打乱而复杂。
内心独白、对话以及全知视角的直接分析细微地拉开情感流动的卷轴,在徘徊中真实地展现了聂赫留朵夫在矛盾挣扎后的精神复活,从而达成内心世界的最终蜕变——而这复现的“心灵辩证法”也是整本小说的文本特色。
聚焦人物复现的行为可以窥见其心灵密码:《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在自疑与自勉中交织的内心独白贯穿节选文乃至全书;《边城》中节选文与其他篇章几次描写了翠翠想象爷爷离开或自己出走的场景,展现了翠翠内心对爷爷的依赖,指向人情美。
(二)留心节选文与其他篇章中复现的情节结局
复现的情节结局,暗示着小说的主题。重复叙事是小说中常见的情节安排手法。在不同篇章中重复叙事、但结局不同的整本小说,适合运用矛盾分析法;而对于节选文与其他篇章之间重复叙事且结果复现的整本小说,尤其需要关注其结局重复处。结局的重复是强化的一种,指向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变形记》格里高尔变形为甲虫,在整本小说中他曾三次走出房门。课文节选的是第一部分,格里高尔第一次开门,试图解说自己闭门不出的原因,却被父亲以手杖驱赶入卧室,一条腿受了重伤;跳出节选文,小说第二部分格里高尔第二次爬进客厅,想向母亲解释,结果被父亲误会并以苹果轰击,“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第三次爬进客厅则在小说第三部分,格里高尔企图向无心欣赏妹妹小提琴的房客表示不满,却被家人视作累赘,最终在房间中孤独死去。从格里高尔的角度看,他三次尝试与外界建立关联,正是他从虫回归为人的渴望;从行为结局看,三次分别被驱赶、伤害乃至遗弃,均以失败告终。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对人异化为工具的反抗,但变形之后的悲惨命运则揭示了反抗的虚无,而这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跨越教材节选文与整本小说的其他篇章,推敲重复出现的行为结果,揣摩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见出主题之深刻。
从节选文辐射小说整本书,从微观品读到宏观叩问,实现阅读的迁移与互补,精读“从困勉达到解悟”,略读时候“自会随机肆应”。当然,我们还可以立足任务群,进行整本书视域下的多篇小说节选文的组元联读。
如若没有方略指导,仅停留于学生自主阅读整本书的评点旁批,虽也能记录书中“越轨笔致”,但稍显分散零碎。构建整本书视域下的小说节选文阅读方略,将更为紧密地勾连节选文与其他篇章,引导学生把阅读方法迁移到整本书,“使所学的文学知识结构化”[1]。
——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常见问题及教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