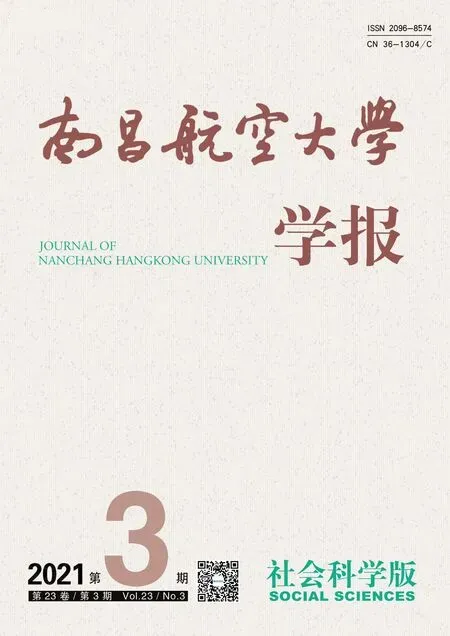改编电影和原小说之间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转换研究
——以《小妇人》(2019)为例
齐昂昆
(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63)
引 言
中国知网关于2019版电影《小妇人》的研究论文共36篇(截至2021年8月20日),多集中在女性主义探讨,共10篇,另有5篇关于电影的叙事策略解析,如叙事视角、跳跃性叙事技巧等,借此分析电影中的人物性格。综上,女性主义研究和叙事策略研究是该改编影片的研究中心,本文意在结合女性主义和叙事研究,以全新的双重视角来解读这部新版的女导演兼编剧的作品−从女性主义叙述声音转换的角度来解读电影的改编。在剧本改编中,《小妇人》编剧既保留了原小说的女性主义叙述声音,又切入了新时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电影叙述声音,并频繁切换于二者之间,使女性主义叙事有了1860年代和21世纪的两种时代特征,建构了传统和现代兼而有之的双重女性主义叙事观。
1981年,著名叙事学理论家苏珊•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中将叙事技巧−视角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对后期女性主义叙事研究起到了关键的铺垫作用[1]。1986年,她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中首次用到“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个名词,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叙事学相结合,成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起点。1992年,兰瑟的又一力作《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标、立场以及研究模式与方法做了更深入的探究;以理论建构和大量文本为基础论证了性别政治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文学作品中受女性性别意识影响而进行过修正的叙述视角;写作者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选择不同的叙事策略,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叙述声音,兰瑟将文本中虚构的叙述声音分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3种类型[2]。申丹教授作为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先行者,较早地将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相结合进行介绍和研究,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理论上有了更快的发展,在案例研究上也有了更多的理论支持。201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原著,并由北京大学黄必康教授导读,为中国研究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理论力作。本文是基于苏珊•兰瑟和申丹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研究,对新版的《小妇人》进行剖析研究,重在研究其女性主义叙述声音的转换。
2019版电影《小妇人》中的叙述声音在文学文本与电影剧本之间频繁切换,将叙述声音类型多样化,而自传性文学文本本身所具备的双重化叙述声音类型更将整部影片的叙述声音多重化;整个故事围绕着19世纪60年代的女性展开,从21世纪的女性剧本改编者、19世纪的女性小说作者、女性主角们3种不同的叙述声音中找到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改写方式,三重叙述声音震撼了奥斯卡的领奖台。
一、叙述声音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叙述声音” ( narrative voice)一词,指小说中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既可以来自虚构世界以外的全知叙述者,也可以来自作为故事内人物的限知叙述者。随着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发展,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独立的学科,30多年深入研究中,女性叙述声音的研究旨在研究女性作家的文学文本中的叙述声音,兰瑟将叙述声音细化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女性主义叙事。
在叙述声音中,第一种作者型叙述声音来自游离于文学文本之外的作者,虽然是虚构的存在,但具有评判、解释、总结的空间,在获得读者的信赖后增强了其叙事的权威性,并增强了文学文本的真实性[3]。第二种个人型叙述声音是由叙述者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较容易受到读者的质疑与抵制,叙事的权威性较弱[3]。第三种集体型叙述声音来自于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群体,从多角度独立的和相交互的声音中,反映长期受压制的女性群体的心声,叙事权威性较大[3]。三种叙述声音虽然独立存在,但随着文学叙事学的发展,在现代文学文本中,许多叙事声音以相交互的方式展现。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这些交互使用的女性叙述声音能从多种角度展现文学文本的女性叙事,从而体现出女性叙事的权威性,鉴证女性主义发展。
名著改编电影具有两重性,因为将名著文本改编为电影文本,其实是将叙述声音游离在两种文本之间,再加上两种文本内部的叙述声音,进而实现多重声音叙事。在后现代叙事的挑战下,为了满足现代多元化观众的需求,多重叙述声音更能增加现代叙事的复杂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逐渐拥有自己的叙述声音,这是对男性权威叙事的一种挑战,希望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获得女性的话语权。女性话语权在19世纪和21世纪的影响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2019版《小妇人》将一本19世纪的小说搬上银幕来面对21世纪的观众,其叙述声音的多重化是电影编剧不可避免的选择。《小妇人》 ( 2019)的电影编剧和《小妇人》(1868)的小说作者都是女性,但却生活在不同年代,所发出的女性叙述声音也不相同,因而多重化的女性叙述声音在电影中进行切换,丰富了电影叙事的研究角度。
“叙事是一种参与文化进程的文化现象。”[4]在电影剧本中,叙事的现代多元化既展现了女性主义的历史进程,也赋予了历史经典以现代文化元素,将历史经典和现代元素有机结合。这一结合需要依托于对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不同角度的叙事,从而实现叙事的多样性。叙事的多样性既体现在它展现的外部世界−社会生活与现象,也体现在它本身就着重描写的内在世界−人物的成长,因此,既让叙事有外在的广阔性,也有内在的丰富性。女性作者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内在心理,作者把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内在心理融入到自传性文学文本的创作中,通过故事中不同的女性叙述者表达,读者因而听到了不同的女性叙述声音。而自传性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双重叙述声音,分别来自于女性作者和女性人物。
改编的电影文本更多了一层时代特征的影响,即编剧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同是女性的当代剧本作者的时代特征和过去小说作者的时代特征的碰撞,多重女性的叙述声音在碰撞中交织,形成了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改写方式。正如姜麟博士所指出的: “苏珊•兰瑟的观点是不管是叙述视角还是叙述声音,它们都受意识形态的制约,而女性作家采用何种叙述视角也能够体现社会的权力关系。”[5]现代观众身处于现代社会,更加认同现代编剧的时代特征,而不是过去小说作者的时代特征。因此,基于原小说的叙述声音,电影剧本进行叙述声音的转换是编剧的必然选择,下文将详细分析这些转换。
二、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的转换
作者型叙述声音是由现代电影剧本作家发出的,在电影中与原小说作家发出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发生碰撞,在权威和非权威中徘徊,既有理性的思维,也有感性的知觉,观众在徘徊中产生情感冲突,从而更加肯定剧本作家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权威。
电影伊始,编剧就假借小说作者以全知叙事的方式告诉了观众,“我曾经历诸多烦难,所以我要写快乐的故事−路易莎•梅•奥尔科特”[6](107),小说作者希望在自己苦难生活中记录下欢声笑语,这是主观感性的叙事声音。但同时,编剧的叙述声音超越小说作者的叙述声音,逐渐将现代女性叙事的权威性体现出来。
电影的第一幕:站在出版社窗下的乔,在黑暗阴影之下被导演拉大身影,占据了整个屏幕,无疑是在告诉观众−这就是一个大女主的电影。但是,当她紧张而勇敢地穿过罗伯特兄弟火山出版社坐满了男人的办公室来见主编,却告诉主编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带来了一个故事,大赞这位朋友在写作界所获得的认同。明明是自己的作品,乔在主编面前却不敢直接承认,体现出大女主的不自信,大女主的形象因而受到了质疑,带有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观众一方面很容易去质疑这一叙述声音的权威性,从另一方面就会认同隐含的剧本叙述声音−要努力去打破过去女性被压制的事实。
然后,主编要求修改故事结局,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人们想被逗乐,而不是被说教,于是乔爽快地答应了。主编提出约稿,乔喜出望外,幸福地奔跑在大街上,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并直白地告诉观众她需要金钱来维持家庭,大女主的形象在观众的一片嘘声中摇曳−原来百年前的女性主义不过如此。事实上,小说本身并没有这一情节,剧本叙述声音对小说作者经历进行再加工,将其放入剧本中大女主的身上,体现出剧本叙述声音从现代女性角度重新阐释传统女性作者卑微的女性地位,对现代观众产生一种文化冲击。
总体上来看,电影《小妇人》(2019)是一个女性创作者剖析另一个女性创作者的故事,编剧、导演格蕾塔在描画小说作者奥尔科特。奥尔科特曾经在小说中给了乔那个时代完美的结局−写作、结婚样样不落,但在女性地位逐渐上升的现代社会里,这样的结局太过于平淡无味,如此完美的结局似乎存在于童话故事里,而不是现实中。于是,编剧格蕾塔的叙事最后游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给了乔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现代编剧的作者型叙事通过观众的认可而得到了确定,从而颠覆了原小说作者的叙事,把21世纪的女性叙事代入到了1860年代,一方面赋予了小说新的现代元素−多元叙事,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叙事立体解读原小说女性人物的女性主义诉求和剧本中小说作家的女性主义诉求,从而见证女性主义叙事的发展。
冯新平指出:“最新版的《小妇人》与前作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非时序性的叙事方法。影片并非像原著那样始于马奇家四姐妹的少年时代,而是从七年后她们作为20多岁的女性开始,然后再闪回到少时,并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回穿梭。”[7]尽管原小说是单线叙事,但电影却跳出传统,改编为双线叙事,即切换于乔的康科德家庭回忆(7年前)和纽约的写作事业追求(7年后的现在)之间,是现代编剧对于叙述声音的多元化、复杂化的体现。
电影编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方式进行,观众看不到她,也无法做出身份的判定,叙述声音是模糊的、隐藏的,不容易被观众所质疑,在情节的共鸣中会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叙述声音,增强剧本叙事的可信度。随着这种接受,女性话语权打破了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制、抛弃了他们所建构的女性气质,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话语权威。在小说文本中,并不存在乔7年后在出版社的那场辩论,在19世纪60年代的男性话语权威之下,大多数关于女性独立的宣言其实都是无法实现的。编剧格蕾塔借助原小说作者奥尔科特本人作为女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曾经经历过的质疑来发出这个声音,这也就成就了电影的双线叙事模式。这种叙述声音似乎是小说作者奥尔科特所发出来的,事实上是编剧格蕾塔本人的叙述声音,是格蕾塔借助于《小妇人》(2019)为现代女性主义发声,满足了现代观众对于女性独立的诉求。否则一部普普通通的传统叙事电影,尽管有古装剧的豪华,有庞大的演员阵容,有英格兰美景和巴黎欧洲风的吸引,也无法满足现代观众的女性主义价值观,也无法建立编剧导演本人格蕾塔的叙述声音权威性。
三、双重个人型叙述声音
传统叙事中,作者和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为同一个,全知叙事旨在增加作者的话语权威性,读者 “接受信息的作用纯粹是被动的,是限于原封不动地接受信息,是事后‘消受’一部他未曾参与、早已完成了的作品”[8]。然而,现代叙事强调叙述者与作者分离,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作品中形成双重的叙述声音。主要的叙述声音来自于小说中的某一个角色,使读者身临其境,如亲身经历一般,“任何阅读作品体验中都具有作者、叙述者、其他人物、读者之间的含蓄的对话”[9]。改编自传统经典小说的现代电影剧本需要迈出叙述声音双重化的一步,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剧情和单一的叙事不能满足现代读者或观众需求,双重化的叙事声音不仅能丰富叙事的多样性,而且也能让传统的剧情走出困境。
女作家在19世纪60年代是一种矛盾的产物,父权社会要求“她”保持缄默,而“她”拿起笔杆子就是为了发声,发出不同于父权社会权威下女性气质的声音,但同时却不得不展现男性社会权力下被压制的本质。女性写作是为了替自己发声,但是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家又必须在很大程度上附和男性权威,因此不得不采取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渴望,这种话语策略才能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接受,从而得以生存发展下来。《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为了赚钱养家,把自己关在了小木屋,将自己与姐妹们的亲密感情写成了小说。为了发表这些故事,她专门起了个男性化的笔名−巴纳德,好似乔治•桑。在那个年代,女性笔下只能有女主们的美满结局,正如《傲慢与偏见》《简•爱》《南方与北方》,这才是父权话语语境下的既定秩序。虽然奥尔科特想要反抗这样的话语权威,发出属于自己的叙述声音,但却要以符合男权社会权威的形式进行表达,女主需要婚姻、女主完美结局都是当时女作家发表小说的前提条件。
小说《小妇人》是奥尔科特出版于1868年的作品,故事从1861年圣诞讲起,正好是格蕾塔电影双线叙事中第二条线的起点。在这条叙事线中,奥尔科特作为主要的叙述声音权威贯穿于其中,将她的亲身经历以高于生活的方式写进了Little Women的四姐妹中,以弱小见伟大,让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开始关注新英格兰清教思想影响下的女性成长−自强自立、追求平等。“奥尔科特运用充满勇气与远见的笔触描述故事人物的同时,也向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束缚发起了挑战。”[10]
然而,21世纪的编剧格蕾塔并不囿于这样一个过去的故事,对有些情节和话语做了微调,让每一个女性都作为独立于男性而存在的个体,甚至让奥尔科特笔下的乔有了现代女性的特征,使其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因此,电影中的乔不仅仅是小说里的角色,写尽姐妹情深;还是编剧眼中的奥尔科特,追求事业独立的女性主义者。编剧格蕾塔将奥尔科特从原本小说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转换成了个人型叙述声音。比如,乔在最后和火山出版社老板商讨稿费时,她自信地预见自己的成功,坚持6.6%的净利润,而不是老板一次性付给她的500美元,这可不是19世纪60年代的女性作家敢去争取的利益,那时女作家的作品能出版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在活字印刷术和烫金装订本的油墨香中乔完成了自己的蜕变,从一个小女孩终于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女主,走出华丽的每一步,成功地建构了现代女性主义的叙事观。
因而,奥尔科特是电影剧本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乔则是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编剧格蕾塔将这两种个人型叙述声音合二为一,增强了两个时代女性的叙事声音力度,让小说叙述者和小说作者相互作用,从而体现出现代电影剧本的女性主义叙事多样性,使观众对电影的女性主义叙事形成一种信任感。
四、多元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整部影片将编剧、小说作者、小说人物3种叙述声音重叠在一起,为现代观众描绘了多元叙事与传统情节碰撞下的女性成长。不同时代的女性人物在一部21世纪的电影中演绎着各个时代的女性主义,以群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将叙事的权威性加大,即“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11]。前文分析了编剧与小说作者之间的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转换、自传体小说作者与小说主角之间的双重个人型叙述声音,这些叙事声音是集体型叙述声音的发出者之一,下面将从代表人物四姐妹、马奇姑妈的角度来分析小说人物的集体型叙述声音。
姐妹四人每一位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尽显女性的独立性,各自具有独立的叙述声音。大姐梅格在乎爱情而不在乎物质,在感情追求上其叙述声音是独立而有力的。二姐乔和隔壁的富三代劳里青梅竹马,但却拒绝了劳里,坚持以写作来养活家人;拿起笔杆子走世界,曾经孤独,但却坚持,其发出的叙述声音坚定有力,对全片女性主义叙事起到了主导作用。三妹贝思尽管身体最弱,但心细勇敢,面对难以抵御的猩红热,与之作斗争;尽管结局还是因病去世,但她勇敢地战斗过,在弱小中也可以听到其叙事声音的铿锵有力。四妹艾米对艺术有着不懈的追求,虽然她不是天才,但可以成就自己的爱好;虽然她不能依靠艺术而生存,但是她可以凭着艺术为自己找到另一半,用自己的独立爱好成就自己的人生。
此外,四姐妹的马奇姑妈,终身未婚,她的女权主义不仅仅表现在对男性的态度上,还体现在对侄女们的控制欲上。她需要的是安静顺从她的艾米,而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屈就于她的乔,所以跟着她去巴黎的是艾米。正如马奇姑妈对乔所言: “没有人能走自己的路,真正意义上地,尤其是女人。你需要嫁得好。”[6](124)但马奇姑妈有钱,能以女权主义的姿态做一辈子自由自在的老处女。在年华逝去时,还有侄女能陪在自己的身边,出没于欧洲上层社交场合。所以,乔觉得“当独身女性的唯一途径就是有钱”[6](125),于是她奋力写作,让自己变得有钱,这样才能实现独立。
那个时代追求女性独立的主人公们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同时在前进的过程中也是忧心忡忡,难以下定决心,以上这些叙述声音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犹豫,因而也符合19世纪60年代独立女性的叙事。小说中女性主义的时代特征明显,但是编剧赋予了她们更多的是21世纪女性主义的特征。正如陈叶知所评:“导演格蕾塔•葛韦格以女性的视角讲述女性的生活故事,将现代女性的喜怒哀乐融于150年前玛奇家的四姐妹中,呈现出了最真实的一群‘小妇人’。”[12]梅格因为购买昂贵的布匹与丈夫发生矛盾;乔剪了头发卖钱帮助父亲,但却暗自哭泣;乔向母亲哭诉:“我讨厌被人说爱情是女人的全部。但是我太孤独了。”[6](151)这些都能体现出追求女性独立所要付出的代价,女主们有犹豫,但却还是大步向前去追求自我。
导演编剧在处理这种集体型的女性叙述声音时,还特意弱化了男性的叙述声音。象征着男性话语权威的南北战争在电影中没有被展开描写。父亲在参战前是牧师,家庭自然受到清教思想的影响,这无疑也是男性话语权的展现,但电影几乎把原小说的宗教思想全部抛弃。父亲在小说中本是家庭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的声音一直回响在乔的耳边,但父亲角色在电影情节上的弱化也相应地弱化了他的权威性。隔壁爷爷在小说中是典型的老古董−“stern”(固执的),但在影片中他很少出场,一旦出场都是热情洋溢、亲切体贴、慷慨大方的,一个温柔的老爷爷形象。
小说人物集体叙事有着宏大的声音,每个角色在编剧格蕾塔、小说作者奥尔科特的双重叙事中体现出男权社会中女性拥有了话语权,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有现代视角下的;小说通过次要女性角色叙述声音的加入和男性叙述声音的弱化,实现了现代女性主义的集体叙事。诚如钟玲所评论:“《小妇人》150多年来曾多次被搬上大银幕……但格蕾塔•葛伟格开创性地改变了原著以时间为序的线性叙事手法,采用回忆与现实不断交叉叙事的方式,在双重时空的交错更迭中呈现女孩们的成长历程。”[13]格蕾塔改编电影的叙事手法有着独特性,将个人型与作者型叙述声音进行转换的同时,多元化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也掷地有声,将主要人物的叙事和次要人物的叙事有机结合,从而增强了女性主义叙事的权威性。
结 语
格蕾塔把经典之作的改编置于现代多元叙事和女性主义的双重视角之下,开启了女性导演大屏幕上的大女主之旅,是现代女性主义电影的叙事创新。编剧兼导演格蕾塔、小说作者奥尔科特之间实现了作者型和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切换,将观众沉浸在现代的权威和传统的非权威之中,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编剧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从而实现了现代女性主义叙事的华丽变身。奥尔科特和乔之间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双重化,加强了这一声音的张力,两种声音相交互,从而赋予个人型叙述声音以现代的权威诠释,传统女性主义叙事有了新的维度。电影剧本沿用小说中女性主人公们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在现代中见传统,进一步推进了女性主义叙事的深度。多重化的叙述声音鉴证了叙事学理论家兰瑟研究视角下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的相互作用。叙述声音在文学文本与电影剧本之间频繁切换、自传性文学文本使叙述声音双重化,让女性导演的电影发出了多元化的叙述声音,为新世纪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为当代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