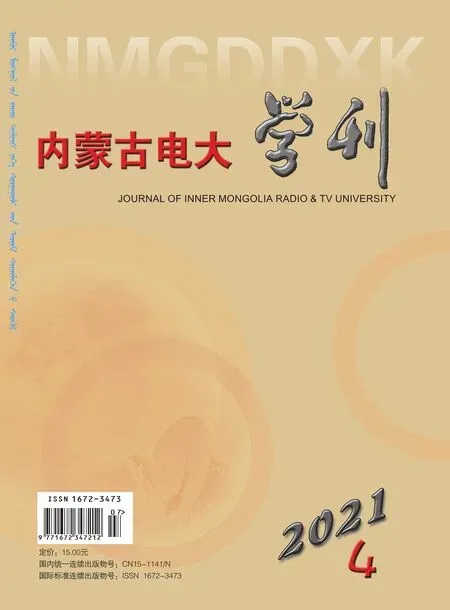松尾芭蕉“雅旨《庄》释”意味新探
杨 越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引 言
松尾芭蕉系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徘人、文坛一代宗师,其“高悟归俗”“以雅化俗”的思想源流隐含着深厚的庄子基因。然而,纵观国内学者就此领域的研究,大都偏向于诗文的引用、类比和美文揭示等层面,较少有整体关联下主体性视角的阐发及其以庄子思想本质为依托、展现“混溶”的独特文化形态与特色的成果。而要提升此领域的高度,不仅需要对芭蕉特性有所把握,更要对庄子思想的核心有一个正确且深度的认知,这样才能通过对照、比较找到彼此的契合点。
就庄子思想的核心而言,超越是主线,自由是目的。《庄子》思想所阐发的主旨,就是要通过不断地超越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至此,对蕉庄思想关联的把握也要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与目的去加以论述。鉴于此,本文特别选取了芭蕉《笈之小文》中,重点阐发“风雅观”的篇头首段为底本,在精准框定芭蕉涉《庄子》相关词句中“语意同源”“形异质同”的基础上,深入这些特定语句内部,通过文字训诂展开义理辨析,挖掘、剖析这些语意背后深层的庄子寓意,由此揭示其达成“风雅之道”的意义及源流。接下来就依照《笈文》首节的先后顺序,由上往下展开一一辨析。
一、雅旨“物有”中,涉庄心性思想的探究
先看《笈文》首行:“百骸九窍中物有。且自名为风罗坊。风罗者即形容其身犹如风吹即破的薄衣一般脆弱。”[1]中的“百骸九窍”一词,明显是芭蕉直引《庄子·齐物论》“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的部分,以此特释人骸。
紧接着,“物有”——“物”一词颇具隐意,值得推敲。如它在《芭蕉文集·日本文学大系》中就被直释为:“肉体间灵的居所。”[2]以明此“物”的“心”“形”二元特性,但并无明确此“物”与庄子的关联。而将“物”与庄子直接联系的是广田二郎先生。他将此“物”与《庄》典中最具核心价值的命题“心”相联系,并提出了“形者心之宾”[3]的物释法。
在笔者看来,得此诠释的依据首先在于前文“百骸九窍”作为“形骸”的代指物,明显引荐《庄子》句而来,而“物有”作为形骸中诠释“灵”之眹的部分,无疑就是指《庄》典中最有价值的命题“心”,因为在庄子看来心无形却真实存在。同样心作为支配形的君或宰,它才是真正引领庄子达成“逍遥”“齐物”的核心。而芭蕉“心由物代”的表述明显是为了更好地迎合《庄子》“虚心无形”以及“真宰”“ 真君”的价值特征,以便让自我拒绝并超越一切有形而与道同体。同时,得此推论的另一重要依据还在于,下文“且自名为风罗坊”中有关涉“无”的思想解读,恰好印证了此“物”的虚无属性。
不可否认,对“心”的发现是先秦哲学的特征标志,而庄子正是重要的推手之一。[4]如,“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齐物论》);“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人间世》);“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等等,强调虚心以及君宰的论述通篇皆是。而他如此重“心”还是为了要验心,即让体验成为可能的诸肉体器官,如何在心的统筹支配下来更好地感知外物。
从天和至贞享年间(1681年-1687年)芭蕉苦读《庄子》,在他《笈文》的篇头用“百骸九窍中物有”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灵肉成偶的形象。可以肯定,这是他借《庄子》,通过突出心的虚无与主导性,去带动诸肉体器官更好地落实体验的一种思路与尝试。鉴于此,“物有”不仅阐明了心在其羁旅体验中的虚无且真实存在,更彰显了它作为形的君、宰所具有的支配地位。同时,更需强调的是,用心去开启与达成“逍遥”的思辨,不仅是庄子的思路,更是芭蕉魂系老庄,“蓄风雅于肺腑之间”所要尝试的重要路径,毕竟无心的羁旅是脱离庄本的,而“物有”的隐逸与主导性恰好点明了他继承庄本的实质。
二、雅旨“且自名为风罗坊”中,涉庄“无”的思想探究
紧接上文,再看下句:“‘且自名为风罗坊’,风罗者即形容其身犹如风吹即破的薄衣一般脆弱。”其中“且自名为风罗坊”则是芭蕉继承庄子“无”之上,超越有待达成无待的阐发。
在日本持此观点的学者有今井文男等[5],他们将“且自名”与庄子众多寓言中最具哲理性的《南海之帝为倏·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串联起来加以论述。
如前所述,既然“物”是“心”的代名词,它具有隐逸和主导特征,那么“且自名为风罗坊”所表达的正是芭蕉寄望通过这一心的隐逸、主导性去超越一切有形、达成无形的一种诠释。之所以得此推断,除了芭蕉在移隐“深川”(1680年,37岁)前,在徘界已是青云得意、顺风顺水的事实外,还有“且自名”的寓意背后所隐含的他对名利(有)的刻意规避,与《庄子》“浑沌”——“中央之帝”的自然无识性在价值机理上有着深深的契合之处。因为从《庄子》对浑沌特性的寓意解读来看,显然,自然无识是确保浑沌与万物融通的基础,而一旦被南北两帝以“有”的方式凿出七窍后,“无”的自然特性便消失了,使得“我”被无情地隔离在了万物之外。
同样对芭蕉而言,鉴于他以上对有识的种种忌惮与畏怯,“且自名”恰好清晰地道出了身处徘坛“滑疑之耀”巅峰[6](1678年,35岁,获“俳圣”殊荣)的芭蕉,渴望通过套用浑沌的“无知性”去避免让自己不被凿成“有知”的一种刻意之举。究其原因还在于他看到了“有”之外“无”的价值。要是用更加哲理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无”意味着我仍停留在“未始有物”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万物纯粹且自然,也无任何“是非”“成亏”的欲求,万物的界限在彼此模糊中会成为一个被化通了的整体。而一旦被“有”所侵据,“有”的炫耀光芒会阻断芭蕉与万物的融通或并生,甚至会让他如浑沌般死去。芭蕉正是出此顾虑,才特用“且自名”来加以人为地遮蔽。
与此同时,芭蕉为了更深入地表达对“有”的忌惮,他甚至借用了“风罗坊”的庸常外表来反衬自己以提升对《庄子》“无”的内在超越性的认同。所谓“风罗者”,他本人将它形容为“其身犹如风吹即破的薄衣般的脆弱形象”。从这些字里行间恰好可以引申出,正是由于它“即破”“脆弱”的无用性,才是诗人芭蕉如此偏爱蕉树的缘由。至此,这一“无”就不是单纯的“没有”或“不要”的意思了,而变为一种刻意之无,是他超越“有”之后的“无”。一方面“且自名”表达的是他对“有”的极端排斥,预想人为遮蔽、隐逸的情态;而另一方面,他则希望通过“风罗坊”的庸常性去进一步让自己超越世俗的“有”,以衬托真实的“无”。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齐物论》)顾名思义,多数情形下所谓圣人就是因为有名才是圣人的,而有的圣人有了名后会把名看得很重,而有的圣人则超越名,成了真正的圣人。庄子对“无”的解读,恰恰在于“先有后无”的超越上。对此,同样芭蕉在《移芭蕉词》中也有相关类似的阐发。他说:“类山中不才之木,其性可尊。僧怀素以此走笔,张横渠观新叶而获修学之力。予不取其二,唯游于叶下,独爱其为风雨易破之质也。”[1]P264
文中的“山中不才之木,其性可尊”正是他对前句“其身犹如风吹即破的薄衣般的脆弱形象”的再补充、再诠释。其实质无不体现出芭蕉对《庄》“有用而不用”这一“无”的超越性的高度认同。例如,他举怀素(唐,725年-785年)、张横渠(北宋,1020年-1077年)二人“走笔”“修学”的有用性,与自己“唯游于叶下,独爱其风雨易破之质”的无用性展开对比来进一步阐明,人只有当超越了“有”之后的“无”才是真无。诚如他在《蓑虫之说》中所道明的“蓑虫无能不才,再现南华之心”,恰好印证了其“无”的庄子源头因素。
纵观以上“且自名为风罗坊”中,有芭蕉对庄子“无”思想价值的深层领悟与阐发。不得不说,庄子所倡导的“无”不是一个空洞概念,而是他超越了己、功、名之后的“无”;是从“有待”通往“无待”的境界之无。芭蕉正是继承了庄子这一“无”的基因,才为其达成风雅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雅旨“彼”等,涉庄“道”的思想阐发
有了上述认识后,接下来再看下文:“彼嗜好俳谐之狂句久亦,已成为毕生之事业。有时倦怠抛掷,有时奋进自励,企图夸耀于他人。是非存心而首鼠两端,不能按住。其间曾打算立身处世,但为此种事业所阻,有时又想学佛以晓晤自愚。然而亦为此种事业所破。终于无能无艺,只是专此一道。西行之于和歌,宗祇之于连歌,雪舟之于绘画,利休之于茶道,虽各有所能,其贯道之物一也。”其中“彼”“是非存心”“贯道之物一也”等,同样是芭蕉迫近庄本,雅旨庄释的要素。
首先,从芭蕉将“彼”作为人称指代的饰语手法就不难看出,这是他领悟了庄子“齐物”真谛后的一种释物表达法。纵观文序上下,要是细致阅读、对照《笈文》首页前后两段文字便可发现,从“前段的‘风罗者(吾)’”到“此段的‘彼(彼)’”,由于人称指代的错节所导致的达意的模糊不清,从条理上难免给人有种玄妙含糊之感,甚至不乏有人会将此既定为单纯的语误。而反观芭蕉文采斐然、才华横溢的天资,作为与万叶歌人柿本人麻吕(约662年-706年)的“歌圣”地位齐名,被江户徘坛冠以“徘圣”一绝的芭蕉而言,如此稚嫩的语误想必应该不会落在他的身上。不仅如此,依托典据则更可能是他模仿、套用“庄旨释雅”的又一刻意举措。因为通观《庄》典便不难发现,庄子本人就常用“彼”“吾”等玄语去代指其他,如“吾丧我”“非彼无我”“莫若以明”等等。表面上,模糊性指代似乎是庄文独特的一种文言定式,而透过表面观实质,则更应是庄子以此来诠释“齐物”的又一真实用意。依据是,只要你留意《齐物论》等代表篇目中的叙事方式便不难发现,庄子对“我”“他”等[7]表达“有己”“固定”性语言的使用是相当谨慎的,而对“彼”“汝”等表达“无己”“开放”性词语的使用是相当频繁的。究其原因,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所道明的“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显然,“有己”意味着“有”的特定实体的出现,而特定实体的出现所随之而来的“是非”“分别”等等,会让原本的真实被假象所笼罩,要是这样,庄子“逍遥而任化”的方外属性就会被彻底颠覆而偏离本质。
显然,芭蕉对上述庄子的刻意用心是不会浅尝辄止、视而不见的,相反,则是有透彻认知的。这从他“有时倦怠抛掷,有时奋进自励,企图夸耀于他人。是非存心而首鼠两端,不能按住。”的残喘叙事中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当他被这些固有的“我”“他”所包围、禁锢时,内心那种无以言表的苦楚与绝望!应当说“是非存心”所带来的算计、焦虑、争斗、冲突等等,都是在“夫随其成心而师之”(《齐物论》)的前提下,“以己度人”苛求他者去改变俳谐之道的做派,而这种“与物相刃相靡”(《齐物论》)忽视事物共性的有我之辩,肯定会让芭蕉陷入无休止的不安与痛苦中。对此,庄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而待彼也邪?”(《齐物论》)
辩无胜,尊重共性是庄子表达齐物的核心。对芭蕉而言,要是仍然忽视事物的整体性,仍然以我独尊,片面地处理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最终无疑会让他彻底偏离真实的俳谐之道,而走向“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齐物论》)的绝途。看看他“其间曾打算立身处世,但为此种事业所阻,有时又想学佛以晓晤自愚。然而亦为此种事业所破” 的“姚佚启态”,便已是“近死之心,莫使复阳”,在如此窘境之下他不得不再度问答庄子,因为这些在《庄子》看来都是小事罢了:“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齐物论》)
面对是非与分别,庄子要我们超越是非相对,进入绝对的境地并在此安住。他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非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与天,“亦因是也”。……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以明”即是要我们明白和尊重事物彼此的差异,“亦因是也”用道来加以关照。确切地说,彼此或是非是人的产物,是成心的变现。
对此,“终于无能无艺,只是专此一道”不正是芭蕉希望通过套用庄子之“道”去摆脱是非泥潭的禁锢,以达成“与道同体”的一种尝试吗?毕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应当说,这里的“无能无艺”,不是芭蕉要逃离现实,成为朱熹所谓“避世自说”的隐者。而是他要把自己从固有的我、他的争执中摆脱出来,上升到“天地之正”的高度,在道的关照下去拓展彼此无差别世界的一种尝试。更确切地说,就是要用羁旅这种非常人的方式,去与当下俳坛被无数个“我”“你”“他”笼罩、独占、包围下,充斥着各种假象、功利至上的风气进行殊死较量与抗争,并由此构建起真实意义上的俳谐艺术的一种尝试。为此,他得出的进入路径是:“西行之于和歌,宗祇之于连歌,——虽各有所能,其贯道之物一也。”艺术的真实不在“有我”之中,而在“无我”之下。当芭蕉参透了庄子“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的世界的无限性后,明确地告诉我们,不要在有我的是非争执中去寻求艺术的真实,而应将我从众多的“我”“他”中脱离出来,回归到物之初,即“道”的高度来寻求艺术的真实。
显然,作为雅旨的“贯道之物一也”正是芭蕉以庄子“道通为一”为源头的一种真实写照。“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橘怪,道通为一。”(《齐物论》) “多”只是显发是非的表象,而“一”才是实质。莛与楹;厉与西施,它们从物的角度是“自贵而相贱”的,但道则是“物无贵贱”。由此便可以明确,如果芭蕉期望将俳谐从以往的游戏、技巧、滑稽、低俗的是非(物)中彻底摆脱出来,建构起真实意义上的艺术载体,那就必须将它置于物之初,即“道”(未始有物)的高度进行整体思考才能化万物为一。
至此,“惯道之物一也”同样是芭蕉继承“道通为一”之上超越人的生死、是非、物我之后的思想写照。当芭蕉到达了道通为一的高度时,也就意味着他从“有待”进入了“无待”之境,进入了“无待”则象征着获得了真正高远的自由。
四、雅旨“顺造化”中,涉庄“万物一体”的思想阐发
最后再看,“此类风雅人物,顺应造化,以四时为友。所见者无处不花,所思者无处不月。若人所见者不是花,则若夷狄,若心所思者不似花之优雅,则类鸟兽。出夷狄而离鸟兽,顺造化而归于造化”。其中“顺造化,以四时为友”“顺造化而归于造化”两句可以极其鲜明地展现出,这是芭蕉通过不断超越,进入了“无待”之境后所获得的一种真正高远的自由的景象,这里的“顺造化”概念正是他对庄子“顺自然”(万物一体)思想的继承。
首先,芭蕉的“造化”一词是引自《庄子·大宗师》“今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的部分。文中庄子将“天地”比作大炉,“造化”比作冶师。依据《庄子·至乐》“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以及二程《二程遗书·卷十五》有关“造化生气”的解读,所谓“造化”:就是天地间通过“气”(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化生万物。这种依靠宇宙自身内部的力量化生万物的方式,作为从造化生化而来的人是无力对抗、只能顺从的。因此,庄子在诸如“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养生主》)、“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廖天一。”(《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齐物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秋水》)等等表达顺天、合天的论旨,自然成了《庄子》通篇的主旨。无疑,都是要我们融入造化之流中安之、顺之,应天而任化。
同样,根据楼宇烈先生对“顺自然”概念的当代解读:“在中国传统中,自然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指‘本然’,即万物原来的本性。所以顺自然不是顺自然界,而是顺从一切事物的本然状态,顺从它的本性”[8]。鉴于以上“顺自然”在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因素,作为远在扶桑的芭蕉,在认知上究竟到达了何种程度,将是衡量其领悟庄子思想高度的重要尺标。而从其“顺造化,以四时为友。”“顺造化而归于造化”的表述来看,无疑是达到此高度的明确证据。
其次,再观“顺造化”的内涵,鉴于楼先生所提“顺自然”就是要顺从一切事物的本然,顺从万物原来的本性,这就预示着“天地一体、万物共生”的自然主义大生命世界观,同样也是芭蕉“顺造化”所要达成的宗旨。而“天地一体、万物共生”作为人游于“方外”(道界)的标志性特征,人在这样一个反复终始、不知端倪的无极地域里,所有因人类中心所导致的是非、差别等等的执着与标尺,如同芭蕉笔下的“夷狄”“鸟兽”那样统统都会被给予极大的质疑和排斥。相反,这里万物普遍通连、物化流转成了一个花开花落的整体,鲲化鹏、蝶化庄、蛙化泉、月化虫,这一切的一切无不立足于顺应造化,立足于天、道来审视这个世界。在如此“自喻适志与”的大化流行下,“所见者无处不花,所思者无处不月”正是芭蕉达成“风雅之道”的绝对空间与不二圣地。由此可见,“顺造化”中深深地蕴含着庄子“天地一体、万物共生”的寓意,同样亦是芭蕉继承庄子的完美体现。
五、结 语
纵观以上,从“物有”知形成藕的佯狂体,到超越“是非存心”达成“且自名为风罗芳”的“无用是为大用”;再从“无用”出发,上达到“惯道之物一也”“顺造化”这一象征《庄子》“道通为一、万物一体”的自由无待。这层层的超越与升华无不体现出芭蕉血骨中太多的庄子基因。要是细品《庄子》即可得出,其思想的核心旨在不断超越的过程,而超越的根本目的是要获得鲲鹏般真实高远的自由。鉴于《庄子》的这种超越特性,芭蕉“以自身为目的,为艺术而艺术”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艺术载体。正是在此特性与目的的驱使下,才使得芭蕉能够突破“夷狄”“鸟兽”等的层层阻碍,并上达到了“似花”“似月”的天地高度,在这一“顺造化,与四时为友”无何之境中尽力拓展他的俳谐风雅化的道路。同时也不得不说,通过超越所到达的天地高度固然能让芭蕉获得绝对广域的视野以及对自然透彻的认知,但芭蕉达成这一境界的旅程背后所付出的切实的修炼功夫,更是他继承《庄子》的集中体现。鉴于此,芭蕉不仅有境界的高度,更有功夫的落实,是境界和功夫的统一,既是潇洒,更是超越,是超越后的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