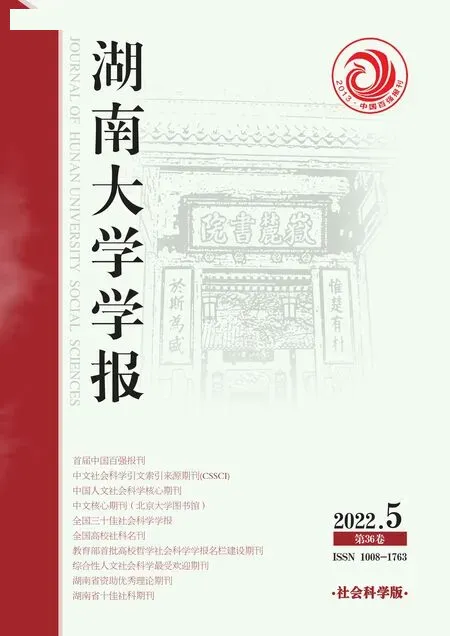“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
——程若庸《斛峰书院讲义》的道学旨趣及意义*
许家星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程若庸(生卒不详),字达原,号勿斋,又号徽庵,安徽休宁人,被誉为“休宁九贤”之一。从学于饶双峰、沈贵珤,为朱子三传。程若庸是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进士,毕生从事理学教育,是宋元之际享有盛誉的理学大家,长期执掌安定书院、临汝书院、武夷书院等著名书院,“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培养了范元奕、金若洙、吴锡畴、程钜夫、吴澄等杰出弟子。程若庸在《斛峰书院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中充分表达了对书院的看法。在他看来,书院的根本任务就在于“讲明圣贤之道”,故“学不闻道,犹不学也”。对道的学习最难者在把握道之全体妙用,主敬立本、穷理致知、反躬践实是学道的三种途径,针对把程朱理学章句议论化的为学弊病,提出杨时的默会自得之学习方法。他通过心与天地、道、理关系之论述,以全体妙用为核心,突出了心对于树立天地体用的优先性,对于道的统宗会元的主宰意义。他强调了心与理的相即无外、不可偏废的一体关系,体现了重视“心”的倾向,然其心并非所谓的抽象客观精神。程若庸最后提出立圣学之志,讲明圣贤之道是一切工夫之基始,认为“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
一 “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
《讲义》被视为程若庸的代表作品,关于程若庸写作《讲义》的背景,《新安文献志》卷39有所记载:
斛峰李尚书戊辰冬(度宗咸淳四年),寄所得《龟山先生全集》,立轩黄大夫己巳(1269)夏初寄所刊新书院讲篇,且有“地远不得屈至吾徽庵”之怅怏,若庸因述所闻,以酬盛心。(1)(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8页。
斛峰书院位于余干(今江西万年),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由当时万年籍尚书李伯玉建于万斛山之南。李伯玉在度宗为太子时曾兼任侍读,太子即位后曾任礼部尚书兼侍讲,颇受信用。李伯玉给程若庸寄来《龟山全集》。(2)李伯玉与若庸之师饶鲁皆师从余干柴中行(1175-1237),据《饶氏家谱》,李伯玉还曾应饶鲁弟子之邀为饶鲁写《行状》,而程若庸又被冯去疾聘请于临汝书院讲学,故李伯玉与程若庸时有往来。而黄立轩寄给其新刊讲义,表达了对徽庵的想念之情。(3)黄立轩其人不详,目前仅见萧立之《萧冰崖诗集拾遗》中和黄立轩诗三首。为此,徽庵写作《讲义》,以回复二位。
《讲义》因《龟山全集》而起,故徽庵首先引用《龟山语录》两段说法,作为自家论述的前提。第一条提出当以圣人作为求学之标的。
龟山先生杨文靖公曰:“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其学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见圣人之难为也,故凡学者以圣人为可至,则必以为狂而窃笑之。夫圣人固未易至,若舍圣人而学,是将何所取则乎?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后射者可视之而求中。其不中,则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为准?”(4)《讲义》被收入黄宗羲、全祖望所著《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双峰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7-2821页。另本文引文标点有不同原出处,下不再标出。
龟山此说强调为学当树立圣人必可至的自信和志向。古人之学皆以圣人为师,此学乃是德性之学。世俗之人缺乏自信,视成就圣人为不可能,反而以学圣人之学者为狂放之人而嘲笑之。但有志于圣学者并不因外人看法而改变,尽管现实中圣人的确很难达到,然成圣这一标准,是不应改变的,他用了射箭的譬喻,以圣为师好比学射一定要树立靶子,如此才有目标可求。至于中不中乃取决于个人,而树立准的则是普遍要求,无此则学无目标。故学为圣人之说规定了求学的性质、方向、工夫等,乃是求学第一义。
第二条告诫罗豫章语,则是具体论成为圣人的为学之方,提出学不闻道犹如未学。
又尝语罗公仲素云:“今之学者,只为不知为学之方,又不知学成要何用。此事大体须是曾著力来,方知不易。夫学者,学圣贤之所为也。欲为圣贤之所为,须是学圣贤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为文章,作忠信愿悫,不为非义之士而已,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然以为闻道则不可。且如东汉之衰,处士逸人与夫名节之士,有闻当世者多矣。观其作处,责以古圣贤之道,则略无毫发仿佛相似。何也?以彼于道,初无所闻故也。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古通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7-2818页。
龟山指出,今人为学最大问题在于不知为学之方与学成之用。只有切实用功者方知此学不易。为学之方就在于“学圣贤之所为”,但学圣贤之前提,是在学“圣贤所得之道”,即学道。龟山批评世人所追求的博闻之学、文章之学、忠信谨愿之学皆非圣贤之道,如东汉名节之学等,为此学者皆是未曾闻道,故平日只是空谈,临事束手无策。龟山彻底否认了此等之学,断定“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即只有闻道之学才是学。此显然是就子贡所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阐发。区分了两种学问,断定只有“性与天道之学”才是真正之学。此说意在表明何以为学,在正反对立中突出学者当志于圣人之学,闻乎圣贤之道,否则即是无学、白学。闻道之学其实即杨时所继承的二程“道学”,故为同样属于道学脉络的程若庸所服膺。程若庸所引龟山两段文字,阐明了当学圣学之学、闻圣人之道的求学宗旨,这也是书院的方向所在。
二 “学乎圣贤所知之道”
在引述龟山之说基础上,徽庵发表了对圣学(道学)的看法,其论述层层深入。
首先是学道之三层次:言道、知道、道之“全体妙用”。对道的论述,徽庵采用一个由“言道”至“知道之体用”进而“知道之全体妙用”的三层递进比较法。他说:“言道易,知道之体用难。言道之体用易,知道之全体妙用难。”(6)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8页。首先是关于道的言说与体知之难易比较。言道与知道存在难易之别,言道总是更易于知道,道不在于言说,而在于体知。其次是关于道之全体妙用与体用之难易比较。以全体妙用和体用相较,此一说法乃徽庵之新见,前人似未见提及。道之体用乃理学所习用,宋学开山胡瑗即提出“明体达用”之学,伊川“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是理学体用观的典范。朱子《大学章句》格物补传提出“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说,“全体大用”成为朱子体用观的一个标志用语。(7)朱子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等文本中使用此概念近20次。关于朱子“全体大用”的研究成果甚多,如:朱人求《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载《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杨儒宾《〈大学〉与“全体大用”之学》,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朱荣贵《全体大用之学:朱子学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而“全体妙用”朱子仅于《复卦赞》中使用一次,言“一动一静,於穆无疆,全体妙用,奚独于斯”。学者用之极少。而徽庵于此反复论及“全体妙用”,堪为其特色之表述。
第二层是何为道:“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理。” 在论述知道之全体妙用最难之后,徽庵接着正面阐明道之确切含义及对其认知上的偏差:
道者何?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理,初非有出于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外者。以形器为道,而不知其有冲漠无朕之体者,非也。以空虚为道,而不知其有阖辟无穷之用者,非也。②
提出“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理”即是道,道不在阴阳五行万物万事之外,道即在物中,物外无道。简言之,道即物之理,道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实在之用与超越之体。他进而基于体用观批评了对道两种对立的错误认识:一是体用道器不分,“以形器为道,而不知其有冲漠无朕之体者,非也。”②以器为道者,丧失了道的形上超越性,未能把握道之体冲漠无朕的向度,可谓以用为体或有用无体;二是批评佛老以空虚为道,“以空虚为道,而不知其有阖辟无穷之用者,非也。”忽视了道存于现实世界,忽视了道之作用无穷于存在事物的特点,可谓有体无用。此二者皆不知道之体用一源,不可偏废。徽庵在《增广字训》中对道的认识有助于理解《讲义》中的“道”。《增广字训》对道有两种定义,分别在造化门和情性门,情性门又分出天道与人道两种道。
(造化门)形而上者,无声无臭,是之谓道。(情性门)人伦事物,当然之理,公平广大,人所共由,是之谓道。元亨利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伦日用,当然之则,是曰人道。(8)朱升:《小四书·性理字训》,明嘉靖二十六年楚府武冈王朱显槐重刊本,第42、49、44页。
这种逐层分析字义的方法显然较程端蒙《性理字训》更为细腻深入,《性理字训》对“道”的解释是“人伦事物,当然之理”,只是同于《增广字训》“情性门”之道的前半部分,显得简略。徽庵首先将道分为两层:纯粹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道。纯粹形而上指的是不与具体事物相关联、只是作为造物者的道,其特点是超出一切具体实有之上、同时不为人所感知,可谓超越、普遍、造化之道。此正同于朱子对无极而太极之理的描述,是“净洁空阔、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者。形而下之道指的是道落实于具体事物之中,表现为人伦事物之中的当然之理,此说直接取自《性理字训》,其实本于《中庸章句》首章以道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但以日用常行的公平广大之理来论述道,则是徽庵的新解,《中庸章句》认为“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是道之用,徽庵以公平、广大来论述道,突出了道无偏无私、包容普遍的特点。情性门把此人所共有公平广大的人伦事物当然之理进而分为天道与人道两个概念,即元亨利贞四德所体现的自然之理和人伦事物中的当然之则,二者构成一种天与人、自然与当然的对应关系,分别是同一个道在天地与人类中的呈现。此正合乎此《讲义》以道为阴阳万物万事之理的定义,不过表述略有不同而已,体现了徽庵思想的一致性。
第三层是圣贤所知之道为何:道之全体妙用。徽庵接着论述“知道之全体妙用为难”说,此知代表了知之尽、知之至。
知其体之无朕,而不知其弥纶六合,无毫厘之空缺;知其用之无穷,而不知其贯通千古,无顷刻之间断,则其体之全,用之妙,亦有知之而未尽焉者矣。或闻而知之,或见而知之,其知之而尽焉者乎!生而知之,不思而得,安而行之,不勉而中者,圣人也;学而知之,思焉而无不得,利而行之,勉焉而无不中者,贤人也,皆知之而尽焉者也。学者之学无他,亦学乎圣贤所知之道而已。(9)中华书局点校者以问号标点“或闻而知之,或见而知之,其知之而尽焉者乎”,认为是疑问语气(实为否定),我们认为,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来自孟子之说,乃是表达肯定语气,故用感叹号。
如仅知道之体具有冲漠无朕、无声无臭的形上特点,却不知其用之周遍天地,四方上下,无有不尽,则亦不知道;反之,仅知道之用施展无穷,而不知其体乃贯通古今,超越时空、亘古不灭、永恒不息者,则对道之全体妙用属于略知一二而未尽全体者。那么何人属于对此道知之尽者?他认为孟子所言见知、闻知之圣贤属于知之尽者。《孟子》末章“由尧舜至于汤”提出三代至孔子的见知与闻知者,属于见知的有禹、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闻而知之者有汤、文王、孔子。(10)李景林师认为此两类道的承载者乃是圣、贤之别,即开创者与守成者。参李景林《孟子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325页。而《中庸》《论语》所言生知安行之圣人、学知利行之贤人皆属于知之尽者,即知道之全体妙用者,也是学圣人之道所应学习者。故学者为学之道别无他法,即在于“学圣贤所知之道”。
第四层落实为学圣贤之道之方:主敬立本,穷理致知,反躬践实。徽庵从此三方面具体论述学圣道之工夫。说:
学乎圣贤所知之道无他,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已矣。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大学明明德之工夫也。主敬以立其本,则又小学之工夫,而大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焉者也。程、朱子以来,谁不知由小学而进于大学?然少而习焉,壮而勉焉,老虽或知之,往往未能尽焉。何也?文靖之言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而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读书之法也。(1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8页。
徽庵从构成为学次第的小学、大学来分析,认为穷理致知、反躬践实即大学明明德工夫,主敬立本虽为小学工夫而贯穿大学始终。主敬说来自朱子,朱子认为主敬是用来补充学者小学工夫之不足而贯穿大学者。至于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为明明德工夫,是徽庵新论。徽庵指出自程朱倡导由小学而大学的为学工夫次第以来,学者皆知此工夫次第,自少而习、壮而勉,以至于老,然于此学却往往是有所知而未能尽。“知之未尽”是整篇《讲义》的核心思想,屡屡出现。徽庵剖析出现此等情况的原因在于读书不得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来自龟山,故引其体验默会的读书之法,强调要身体、心验、从容默会、超然自得于文字意象之外。朱子认可龟山身体心验之说,如朱子认为对于仁,“圣人都不说破,在学者以身体之而已矣”(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载《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但恐不满其“默会”之说,如朱子在讨论“致知”时言,“惟致知,则无一事之不尽,无一物之不知。以心验之,以身体之,逐一理会过,方坚实”(1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5,第482页。,把“默会”改成“逐一理会”。朱子更喜欢理会文本,与人讨论,而尤不满龟山“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说,因此说与其重视章句训诂之学的风格恰好相对,故从未引用。(14)此说为王柏《性理精义》所引。《性理大全》在读书法引之。当弟子有一次提起龟山此说时,朱子态度褒贬兼具:
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却不读书。”(1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3,第3592页。
此处所引龟山说未引“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句,“默会”改成“从容”,“从容”是朱子所喜用者。且弟子认为此乃延平所得于龟山者,是道南源流。朱子作为延平弟子,本来理当客气,但他在肯定龟山不废读书的同时,仍从“燕闲静一”四字读出龟山“要闲散”,意存不满。但徽庵坚持引用龟山原说表明他对龟山这一超然读书法的认可,据此以批评当时甚为流行的章句训诂之学:
不以此为法,而徒于章句训诂、文墨议论之是尚,则其于主敬也,不过曰“有整齐严肃而无怠惰纵肆,斯可矣”;其于穷理也,不过曰“有诵读记问而无疏脱遗忘,斯可矣”;其于反躬也,不过曰“有忠信愿悫而无私伪邪慝,斯可矣”。呜呼!是岂知圣贤之学,斯道之全体妙用,有不但如是而已者乎!(16)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8页。
朱子在《大学章句》序中批评“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所指乃经生之学与文辞之学,似并未泛泛地批评汉儒的章句训诂学。考虑到徽庵所处时代,朱子学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之学,徽庵从事书院教学多年,故其“章句训诂”当是指把程朱理学章句化、训诂化的学术倾向。还有一点就是使之流于“文墨议论”,即文辞化、议论化,流于空谈,华而无实,不切个人身心实践,无关国家治世安民。徽庵此说应该是感时而发,正中此后朱学发展之流弊。(17)朱子学的章句化训诂化是朱子弟子后学长期诠释朱子著作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朱子去世后,黄榦《论语通释》、陈淳《北溪字义》、真德秀《四书集编》等著作即开启了这一行程。至徽庵之后的元代朱学官学化后,愈演愈烈,形成了“纂疏体”“附录体”等形式的注朱文本。与此同时,理学本来具有的思辨性质及注重讲学的风气,使得此学难免沾染上“空谈”的意味,与注重现实实践的学风有所不同。此点遭到不少学者批评,尤其是徽庵弟子程钜夫更是直接驳斥此空谈之说乃误国之学。这种学风带来的问题使得主敬、穷理、反躬等工夫实践无法深入落实,而流于庸俗化、浅薄化、简单化。如缺乏对主敬的真正理解与践行,只是庸俗化主敬为外在仪表上的“整齐严肃”,没有怠惰放肆而已;浅薄化穷理,认为不过是精准诵读记忆文本,没有错漏遗忘而已;简单化反躬,认为不过是忠信愿慤,没有私心伪善邪恶而已。徽庵判此等为学之误为略知圣学之学、道之体用而未能真知、尽知圣贤之学、道之全体妙用者,此即其于《讲义》中屡屡标出的“知之未尽”。可见徽庵之论述善于以一正一反的方式,先正面引用龟山说作为圣贤读书法所在,继而反面批评三种违背此情况者,提出了自家新见,表现出了与朱子的不同。(18)龟山此说为徽庵所重视的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5所引,王柏《性理精义》亦引之,徽庵恐有受二者影响之成分。
三 “圣贤之学,斯道之全体妙用 ”
既然学者异化了朱子学,背离了圣贤之道,那么如何论述作为道之全体妙用的圣贤之学呢? 徽庵接着从心与道的关系入手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释:
圣贤之学,斯道之全体妙用,其何以言之?道为太极,造化之枢纽,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心为太极,品汇之根柢,一物各统体一太极也。万化之流行,由于元亨利贞之四德者,天地之全体妙用也。有人心之全体,而后天地之全体始于是而立焉。人心之全体少有或亏,则天地之全体不能以自立矣!有人心之妙用,而后天地之妙用始于是而行焉。人心之妙用少有或戾,则天地之妙用不能以自行矣!此参天地、赞化育所以不可一日而无圣贤之道。(19)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8-2819页。
较上文对道的论述不同,徽庵于此插入了“心”这一范畴,并且以太极来贯穿心与道,融合邵雍的道为太极和心为太极两种太极观及朱子太极为“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解。道为太极,内在于一切存在并作为其枢纽,即万物统体一太极;心为太极,构成各种存在的根本,即一物各自具有一太极。此即以理一分殊论太极与万物关系,既突出了道作为本原、实体的意义,也突出了心的创生、能动性。《增广字训》把太极定义为“至理浑然,冲漠无朕,造化枢纽,品汇根柢”。前两句突出太极无形无影的浑然超越层面,是对太极之体的描述,后两句更多注重作用层论,故用之于《讲义》。
徽庵在从太极层面分论心与道之后,又从全体妙用的层面分论心之全体妙用与天地之全体妙用的关系,把心与天地对比而论。如前所述,“全体妙用”是徽庵的核心概念,此把“道之全体妙用”分化为“天地之全体妙用”和“人心之全体妙用”,二者可谓分属道的两层——天道与人道。就具体生化而言,万化流行源于元亨利贞四德,体现了天地的全体妙用。在《增广字训》中,元亨利贞同属造化门,各以四个四字短语定义之:
万物之生,于时为春,气为少阳,天道之始,是之谓元。万物之长,于时为夏,气为老阳,天道之通,是之谓亨。万物之遂,于时为秋,气为少阴,天道之宜,是之谓利。万物之成,于时为冬,气为老阴,天道之固,是之谓贞。(20)朱升:《小四书·性理字训》,第41-42页。
四德之论就天道与万物的生成对应关系展开,而以气、时为具体的生化动力。元指天道开端,少阳之气,春天之时,万物之生;亨指天道之通,万物之长,老阳之气,夏天之时;利即天道之宜,万物之遂,少阴之气,秋天之时;贞即天道之固,万物之成,老阴之气,冬天之时。此四德完整体现了天地全体妙用。但此天地之全体妙用不能离开人心,有了人心之全体才能挺立天地之全体,若人心全体稍有亏缺,则天地全体不能自立;同样,天地之妙用亦不能离开人心之妙用而运行,人心妙用稍有乖戾,则天地妙用不能自行。徽庵以此强调人,准确地说是圣贤所践行之道,对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不可或缺性,突出人对于天地的主宰性和能动性。这个说法继承了传统上的人为天地之交、鬼神之会、万物之灵说,《增广字训》界定“人”为“天地之心,鬼神之会,灵于万物,能推所为”。(21)朱升:《小四书·性理字训》,第45-46页。这个说法本于《礼记》,是据人与天地、鬼神、万物之关系道出人之为人具有三个向度:于天地而言是心,于鬼神而言是会,于万物而言是灵。此三说皆在突出人的精神性、能动性与实践性,契合于横渠“为天地立心”的四为说。徽庵于此采用具有条件关系的强势语句来突出心对于天地的参赞化育之功,认为天地之全体妙用必须以心为前提条件,如离开人心之全体妙用,则其无法自立、无以自行,突出了人心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表明天地之全体妙用或道之全体妙用,归根结底,皆是由人道来实现,来彰显。此亦契合夫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说,道体无为,它要通过人来有为。故天道必然显发为人道,根本于能动、创造的人心。徽庵是结合道之全体妙用来对人的精神性、主体性作极大高扬,当然这种精神性又根源于圣贤之道。故人心若要发挥其参赞化育之功,“不可一日而无圣贤之道”。那么种种名相和论述,如心、天地、道、全体、妙用等,根本皆落脚于圣贤之道。
徽庵又从心与道的关系来突出心对于道的统摄性和根本性,言“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
学圣贤之道者,不以一身一家、一时一世之心为心,而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心为心;不以一身一家、一时一世之道为道,而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为道,则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浑乎大德之敦化,此道为此心之泛应曲当,脉乎小德之川流。(22)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9页。
正因圣贤之道不可或缺,而人心又是天地之全体妙用能够挺立作用的前提,故对圣贤之道的学习者而言,拥有一颗怎样的“心”就极为重要了。徽庵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来形容此心。此心须突破小我,超越时空,以天地宇宙、千秋万世之心为心,其实即是“大其心”,着眼于全体万世的超越之学。对道的理解也是如此,当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为道。“弥纶”来自《周易·系辞上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形容无所不包之统摄贯通义;“六合”来自《庄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指天地四方,故“弥纶六合”指统摄整个宇宙,“贯通千古”指通达往古来今,此说突出此心此道乃是超越具体时空的永恒无限者。以“弥纶六合、贯通千古”表述心与道,在理学家中甚为罕见,乃徽庵又一独特表述,实有以心为宇宙之意。
徽庵又进一步论述了心与道的关系,认为此心乃此道之统宗会元,此来自王弼《周易注》解“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说,表明心对道的统摄贯通作用。朱子在论述仁与义礼智的关系时,亦采用此说,认为此即太极与阴阳五行的理一分殊关系,“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2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第249页。又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真德秀《大学衍义》《四书集编》皆引之。此心相对此道,正如《中庸》“大德敦化”之浑然;此道对于此心则是“泛应曲当”,正如《中庸》“小德川流”之脉分。(按:“泛应曲当”来自朱注忠恕一贯解,朱子言“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增广字训》即以之作为“一贯”定义,言“心理浑然,泛应曲当”)徽庵把心与道的关系比作浑然一体与脉络分明,大德敦化与泛应曲当,显然视二者为理一分殊、大本达用的体用关系,其说当是来自朱子注《中庸》“诚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2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页。
“此心此道之全体妙用皆在其中”,徽庵进而从心、道、心道之全体妙用三方面来分别论述主敬、穷理、反躬三个工夫,指出在把握了此心对此道统宗会元关系上的主敬、穷理、反躬工夫,截然不同于此前“章句训诂文墨议论之学”。
其于主敬也,必将如对日星,如临渊谷,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而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心在其中矣。其于穷理也,必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究事物之准则,推造化之本原,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在其中矣。其于反躬也,必将以无欲为一,以无息为诚,以日新为德,以富有为业,以一民一物不被其泽为己任,以天下后世不传此道为己忧,而此心此道之全体妙用皆在其中矣。②
徽庵认为,此时之主敬必能做到意念纯一无适、小心敬畏,实现动静兼贯,达到俯仰无愧,意念真实自慊,此心自然成为“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心”。《增广字训》“敬”的字义即是“通乎动静,主一无适”,以“通乎动静”论“敬”颇具匠心,本乎《通书》“静而无静,动而无动”之意,显现敬贯心之动静的神妙作用。俯仰不愧怍来自孟子对三乐的论述,朱子引程子说认为此是克己工夫所带来的内心愉悦效果,“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54页。然而徽庵认为是主敬工夫之效用,可见徽庵对主敬之推崇。朱子还以“俯仰不愧怍便是浩然之气”表达内心的充实自得,徽庵用之于此,可见对敬之效用之推崇。(27)徽庵《增广字训》特重主敬工夫,以9页篇幅论之。他对主敬的定义在《性理字训》“主一无适”的基础上补充“通乎动静”,强调敬贯动静。在综合程子、谢良佐、尹焞、朱子诸前辈敬论的基础上,徽庵以愚按形式表达对敬的看法,提出敬之始、敬之成,敬与诚,敬与明,敬与初学、成德,敬与畏等关系。穷理则是探究复杂隐秘之事理,即《周易·系辞》所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穷尽事物运行之准则,最终推至造化本原所在,此穷理更注重宇宙客观事物之理。由此实现广大精微、高明中庸之学,则“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即在其中,此说渲染了穷理的深广之效用,可谓无处不到、无微不察。
反躬这一工夫,徽庵以“一”“诚”“德”“业”四个字的字义为中心。《增广字训》中“一”的定义是“贯乎始终,不息不杂”,突出“一”始终不变、持久不息、纯粹不杂的意义。《讲义》“无欲为一”则来自周子《通书》,《增广字训》引此说,“周子曰‘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云云。徽庵还在小注中引朱子解,言“无欲与敬一般”“一者其心湛然”,(28)程若庸:《增广字训》,国家图书馆元刻本,第14页。显示出对无欲工夫的重视,并将之与主敬、心之清明相结合。此处徽庵以无息为诚,二程主张“无妄之谓诚”,朱子则以诚为“真实无妄”。徐仲车主张“不息之谓诚”,(29)朱子在《杂学辨》中批评“至诚无息”说,“然遂以无息为诚,则亦误矣”。参《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2,载《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85页。程颐在《伊川易传》提出“健而无息之谓乾”说。徽庵在《增广字训》中言“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天之道也”,此解非常全面,涉及“诚”的多重意义,在朱子“真实无妄”说后,徽庵仍提出了“始终不息”,见出特别重视“诚”的无息持久意义。《讲义》对“德”的论述突出了“日新”,《增广字训》言“道得于心,日新不失,是之谓德”,兼顾了朱子“得于心而不失”,同时也突出了“日新”对于德的根本义。至于“业”,《讲义》以“富有”论之,此与《增广字训》“道著于事,富有无外,是之谓业”一致,此解兼顾道事、内外。(30)《小四书》本圈住“日新”二字,旁标“蕴而”以示替换;“富有无外”亦被圈住,旁标“积而有成”以示替换。朱升说,此篇言人之德业,当以“蕴而不失”易“日新”一句,“积而有成”易“富有”一句。参朱升《小四书·性理字训》卷二,第12页。徽庵认为,人在反躬之时,以民物被泽为己任,体现了入世担当之精神;以不传此道为己忧,体现了传承圣人之道的弘道追求。此心与道合一、体与用合一的反躬工夫所带来的效果是,“此心此道之全体妙用皆在其中”。此说把心与道、全体妙用皆融摄之,意味着主敬存心与穷理明道工夫皆最终落实于反躬这一工夫中。这一“此心此道”表述极似象山“此心之灵此理之明”说的简化,即“此心此理”。
接着徽庵引四位学者五句“所谓”来阐明主敬、穷理、反躬工夫之效验,显出了圣贤之道所在。
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子思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曾子所谓“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横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是皆吾分之所当为,而吾力之所能为者。文靖所谓“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者,此也;所谓“学圣贤之所为”,必欲闻圣贤所得之道者,此也。自非体之以身,从容默会而有深功;验之以心,超然自得而有余味者,能之乎?(3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9页。
张子、子思、曾子之“所谓”体现了极为宽广的宇宙意识,显示了此心此道的超越时空性与普遍永恒性。徽庵先引横渠四为说,又引《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章“建诸天地、质诸鬼神、百世俟圣”三句,再引《礼记》曾子论孝的“塞天地、横四海、无朝夕”句。在所引三句中,皆带有表示空间广大的“天地”“四海”和时间绵延的“来世”“百世”“朝夕”等词,此是颇有用心的。徽庵认为三者所论,虽看似广大高远,其实切合实际,乃人职分之所当为、能力之所能为,“当为”“能为”显示此即自家所应行之职责,所能行之事业,乃无可推托之人生使命所在。又回应开篇所引龟山以圣为师立学之说,即学圣贤之所为必先闻圣贤之道,可谓知在行先,闻道在践圣之先。又以龟山说强调对此领悟并非易事,必须能体之于身、从容默会功深;验之于心,超然自得有余者,方能闻道践圣。《讲义》至此,以“此心此道之全体妙用”为中心,完成了一个逐层深入、首尾相应的论证。
四 “言学便以道为志”
《讲义》接下来又补充了“立志”工夫,论述了“以道为志”的重要意义。徽庵首先引程子说论证此点:
程子曰:“莫说道‘将第一等逊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仁由义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32)此处中华书局版第2819页将“言学”一句置于引文外,据《二程遗书》卷十八来看,其实亦是程子之语,故将其置于引号内。是志也,坐春立雪之时,身体心验之旧矣。“道南”之教,宁不以是为先务乎?由龟山、豫章而延平,逮吾朱子,大成集焉,推其说以教天下后世,至明且备。(33)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19页。
程子认为志向并无大小之分,不应将成就第一等人之志向让给别人,而以成为第二等人为志向,此即犯下了自弃之病,自小志向。故为学当以道为志,为人当以圣为志,即志于圣贤之道。徽庵认为,此志即龟山受学于二程门下,如沐春风于大程,立雪于小程门之时,是龟山身心体验之学。故龟山所传的道南之教,即以志于道、学以圣为首要。此道南之传,由龟山而罗从彦、李侗而传至朱子,最终大成其学。朱子阐发此说,极为明白完备,使得道南之教遍布天下。徽庵由此将龟山与朱子关联之,其实朱子对龟山的道南之传并不太感兴趣。
徽庵进而提出四等之学,特别留意第二等之学,从立志角度具体论述人与道的关系。
若庸尝取其后集所答刘季章书,画为四等之图,其一等曰圣贤之学,其二等曰仁义名节之学,其三等曰辞章之学,其四等曰科举之学。有剽窃架漏而不入等者,有志于第二等而未能笃实者,有志于第一等而不能无过不及之偏者,有在二三四等中不安于小成而能勇进于一等者。大抵三四等识趣不高,夺其旧习,虽有甚难,而其不变,亦自不足为世轻重。惟第二等,资质稍高,一生谨畏,循规守矩,向仁慕义,不为不力,惜其不知向上更有圣贤之学,切于身心而为事业之根本者焉。今之收拾人才,推广圣贤学问血脉,正须著力救拔此一等人,而不可与其下二等概而视之也。若夫圣贤之学,无他,始由此以为士,终即此以为圣人;始由此以修身,终即此以平天下。即知此道是天地间自然之理,又知此学是吾人本分之事。既能真知而笃信之,则其趣向自然正当,其志气自然勇决,其工夫次第必能向上寻觅,不待他人劝率而自不能已矣。不幸而或不遇于世,亦必有以自乐,而无所怨悔焉。呜呼!所以为闻道之士也,此所谓圣贤之学也。(34)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20页。
徽庵据朱子答刘季章书信(今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似未见),以图画形式,将为学区分为四等:圣贤之学、仁义名节之学、辞章之学、科举之学。指出尚有低于第四等而以剽窃为学者,则不入于等。有立志仁义名节之学而不够笃实者,有志于圣贤之学而有偏差者,有不甘于所入之学而志于圣贤之学者,判定辞章、科举之学志向不高,改变其旧习很难,且其是否改变对于世道关系并不大。对志于仁义名节之学者,徽庵颇为重视,认为其资质高,行事谨畏,循规蹈矩,所不足在于安于小成而不知更有上一层的圣贤之学,实紧切于身心道德,为一切事业之根本。故人才培养工作,应重点针对此类人,通过对圣贤之学的推广,使此等人实现精神超越,转而立志圣贤之学。圣贤之学其实简单,即《荀子·劝学》所言“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大学》所言修身治国平天下。当由此领悟:此道既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此学又是吾人本分之事。如能对此道此学真知而笃信之,则其志向自然端正,志气自然勇猛坚决,自能奋发向上,而无须他人勉励表率。即便未能得到世人之欣赏,亦能做到自得其乐而无所怨尤悔恨,此即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人不知而不愠也。若能此,即是闻道之士,即是圣贤之学。可见圣贤之学关键在“真知笃信”,尤其是真知,然做到此绝非易事。
徽庵又继此提出“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说,点明书院之价值、意义完全建立在明道基础上。
文靖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立轩大夫宁不谓然?”②
此是回应开篇,再次引龟山学不闻道犹如未学说,突出道是学的灵魂、实质,道决定了学是否为学。由此推出如创办书院却不讲学发明此道,则书院等同于无,道同样决定了书院在价值存在上之有无,书院并非无生命价值的物质形式,而当以明道为根本。
五 心诚理中
在徽庵看来,此道乃“弥纶六合、贯通千古”者,只有圣贤能体知此道,以何者为工夫来实现此“弥纶六合,贯通千古”之道呢?徽庵以心之诚和理之中对此加以阐述,并再次提出心与理的关系。
或问:“弥纶六合、贯通千古者,道也,圣贤之体是道,而欲其弥纶六合、贯通千古,其可泛然言之,而无一定之义乎?”曰:“以此心言,莫若一‘诚’字,诚者,五常百行之根柢也。以此理言,莫若一‘中’字,中者,应事接物之准则也。对而言,则此心此理不可偏废;单而言,则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诚可以兼中,中亦可以兼诚。尧、舜、禹、汤言中,诚固在其中;《中庸》《通书》言诚,中亦不在其外。朱子谓‘理只是一个理,举著全无欠缺,且如说著诚则都在诚上,说著仁则都在仁上,说著忠恕则都在忠恕上,只是这个道理,血脉自然贯通’。其此之谓欤!”(3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2820-2821页。中华书局本标点亦有问题,未曾用引号标出朱子原文,据《朱子语类》卷六与此有所不同,如“说著诚”与“说著仁”次序颠倒,几个“说”皆是“言”,删了“言著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血脉自然”作“自然血脉”。
徽庵认为,就心而言,最要者在诚,盖诚乃“五常百行之根柢”(此本濂溪《通书》之言)。就理而言,则最要者在“中”,中乃“应事接物之准则”。此是分别就心与理两面而论,而诚与中又构成心与理的具体内涵。在分说二者之后,徽庵又统论之,言“此心此理”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心理互补;若单独言之,则“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即心理相互包涵,心不在理外,理亦不在心外,亦可说心外无理,理不外心。与前述“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突出心对于道的主宰运用不同,“此心此理”表明心与理是平行、相涵关系。故诚可兼容中,即心具理之义;中亦可兼诚,理存于心。《增广字训》对心的定义为,“主于吾身,统乎性情”,突出心对身的主宰意义,对心与理的关系,提出心具理、穷理、即理等说。徽庵由心理不外推出诚中互兼,意在强调心与理的互相包涵,一体不分。认为尧舜禹执中之中实内蕴乎诚,而《中庸》《通书》之诚亦内蕴乎中。《讲义》最后引朱子“理只是一个理”,举一则全体皆在说,表明诚、仁、忠、恕等范畴语义虽各有侧重,然皆是同一之理的体现,“举著全无欠缺”,可见此道理“血脉自然贯通”。如此理解,则诚、中、仁等皆是一理贯通。
六 结 语
《讲义》全文约2500字,文虽不长,却意义深刻丰富,乃宋元之际一篇重要理学文献。它浓缩了当时重要的理学教育家程若庸对理学弊病的反思及对治之方,体现了以下思想特色:第一,程若庸似乎表现了回归道南之祖杨时之思想以对治朱子理学弊病的倾向。《讲义》显然是以杨时的学圣贤之道为理论基础,在读书方法上,亦特别表彰杨时的身体心验、从容默会、超然自得书言象意之外方法,以矫正彼时朱子学所陷入的章句训诂、文墨议论之学。尽管杨时读书之法并不为朱子所完全认可,然程若庸坚持采用之,不惜与朱子不同,体现了他对于当时理学问题的理性认识,即认为理学重新落入了朱子所反对的理学化的章句训诂之学中,丧失了其躬行实践、身体心验的本来精神。第二,程若庸在主敬立本、穷理致知这两个朱子学基本工夫之外,特别提出了反躬践实这一工夫,并将其置于统摄二者之地位,体现了对此工夫的极度重视。这也是有见于现实中学者求道工夫流于空谈而无实践之功的考虑。理学虽然重视涵养存心、格物致知,但其根本还是要落实为道德实践。故程若庸提出反躬践实工夫,是非常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对其弟子吴澄等强调尊德性、主敬等实践工夫恐不无影响。第三,以全体妙用来论述圣贤之道,突出圣贤之道与世俗学问的分别,颇具新意。程若庸切实思考了如何凸显圣贤之学的终极性和完善性的问题,“知之未尽”构成其思想的一个焦点,故他有意论述了学问具有层次阶梯之分,程度深浅之别,目标导向之异,有言道者,有知道之体用者,有知道之全体妙用者,激励学人当“学乎圣贤所知之道”,即全体妙用之道,并将是否能学道明道作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所在,这在书院日益兴盛的形势下是极有针对性的。第四,凸显了心对于道(理)所具有的“统宗会元”之主导性。《讲义》对心之特点和能动性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它以心为“弥纶六合、贯通千古”者,有意识引用经典相关之说,用“天地”“百世”等宏大用语来渲染心之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和永恒性。此心可谓是超越了小我和世俗的宇宙之大心。不唯如此,在心与道的关系上,《讲义》认为就现实存在而言,突出心的能动性对于道的实现具有优先性和决定性意义。 在心与理的关系上,则认为心与理相互一体而不可偏废,相即不外,可谓心外无理、理外无心。若庸对心能动性与主导性的论述,使学者认为其心是脱离世界、比象山之心更为抽象悠远的客观精神。(36)学者认为,“程氏的‘心’……不只是超越了陆氏心学的主观精神,而是脱离了现实物质社会中活动主体的人和物质世界本身的客观精神了。”陆建猷:《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93页。此说未合若庸之意,若庸对心的意义的张扬,并非从本体论着眼,而是紧扣工夫实践。包括追求从容默会之心上工夫,皆是对当时学风陷入无关身心的章句训诂的救治,可谓以“主心”之学对治章句之学。这其实也是自勉斋以来至双峰的朱子学自我纠正调整的一条线索,若庸是勉斋、双峰这一学术脉络的继承者,同时又对弟子吴澄、程钜夫的和合朱陆思想有着重要影响,正好构成双峰思想发展演变至吴澄的必要中介,故对若庸思想的研究,对全面把握宋元朱子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37)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涉密,恕不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