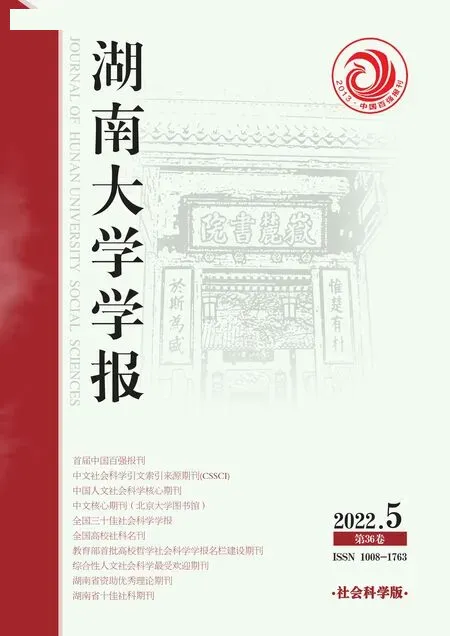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晋海学,张 璐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在清末的诸多“救世”策略中,“道德救世”是比较独特的一类,也是略显不合时宜的一类,吴趼人即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坚守先秦时期的儒家标准,既批判当下的现实社会,也批判宋代以来的儒学传统;既呼吁西方文化的引进,又时刻保持对它的警惕。作为小说家,他将这一“救世”思想积极运用到了小说的写作当中,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近十年之怪现状》中对现实社会“怪现状”的批判,《新石头记》中对理想社会“文明境界”的憧憬,等等。由于吴趼人将他的工作任务放在了文化的层面,所以,无论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还是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他的小说都是在文化的意义上展开的。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类小说在外表上虽不像那些以“立宪”“革命”等为主题的叙事显得即物,也不像那些以“疾病”“科学”等为主题的叙事显得峻急,但事实上,它们同样都是在面临国家危机的历史语境中,对如何拯救危机这一课题的主动回应,只不过由于大家对问题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所提的方案不一样罢了。从这层意义上看,方案的孰优孰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展示出了在国家危机面前的即物关怀,并因此呈现出了多种可能性。作为这些思考中的一部分,吴趼人小说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始终在探索一种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可能,并在这一文学尝试中,紧紧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立场,既批判传统文化之不足,也批判西方文化之偏狭。吴趼人这种既不认同西方,又不认同传统的做法,给他的小说注入了思想的力量。重新阅读这些小说,既是想发掘它们尝试建构文化主体性的经验和方法,也是想借此给当下文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资鉴和帮助。
一 “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主体性建构的文化言说
吴趼人小说中有两个标识性的文化主题,一个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怪现状”主题,另一个是基于理想社会想象的“文明境界”主题,这两个主题的产生与吴趼人所倡导的“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吴趼人思想的核心是先秦儒家文化,“恢复我固有之道德”则是基于这一思想而来进行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方法。有学者认为吴趼人的思想较为守旧,他的这一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绊脚石”。“‘固有道德’导致人们法制观念的淡漠模糊和法律制度的难以完善,这也是社会现代化的绊脚石。伦理型文化影响、左右了吴趼人的道德救世思想,他以为能用业已成为一盘散沙的没落的封建道德系统来重整芜杂紊乱的社会秩序,奢望着封建文化的枯树上能再发新芽,重盛鲜花。这也是与吴趼人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共同迷惘与困惑,明明看到了旧的伦理纲常的日趋没落,深刻意识到了变革的需要,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旧观念的阴霾。”[1]其实,这些都是对吴趼人思想的误读。吴趼人的本意一直都是在探索一种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可能,这是一种依靠自己而不是他者的建构方法。正是凭借此一方法中的“恢复”,他不去纠缠中学西学价值判断上的好与坏、是与非,而是将问题推进到去探索一种更有利于拯救国家危机的方法与策略这一层面之上,这种看起来显得保守的文化主张,其实恰恰是支持他“救世”行动的核心思想。吴趼人的大部分文化言说都是围绕这一主张展开的,他的大部分小说创作也都是以此为旨归的,尤其是“怪现状”与“文明境界”两个典型的小说主题,均是基于这一文化立场而来的小说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便离不开他的文化主张,所以,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怪现状”与“文明境界”的内涵,就不得不先从吴趼人的文化主张入手。
儒家文化自汉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就微观而言,它能解决个体生存的意义问题,就宏观而言,它能解决国家运行的正当性问题。儒家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清代之前没有受到域外文化的挑战,但是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无法在文化层面上给予“救世”以有效的思想资助,因此受到知识者空前的责难和质疑。陆世澧《中西学术异同得失策》云:“自上世中世以言学术,则中与西虽异而实同,互有所得,互有所失。就近世而言,则欧西以讲求学术而富强,中国以不究学术而贫弱,此则欧西之得,而中国之失也。虽谓中国近世无学术焉,不为过也。”[2]于是,知识者纷纷转向西学,以至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吴趼人对此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将视野放在知识者们的求学过程之上,想要看一下人们是否是在有主体性地学习西学。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知识者们大都满足于在知识的层面上把握西学,却很难做到真情实感有皮肤感觉地把它们引为“救世”的思想工具。他以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为例说道:“舍我之本有而取诸他人,不问精粗美恶,一律提倡。输进之精者美者庶犹可,奈之何并粗恶而进也?虽然,此犹曰失于审择耳。其尤甚者,则专为自私自利计。如谈自由而及于结婚,其语乃尽出于少年之辈,稍老成者必不肯言。其故果安在也?彼谈自由者,徒哓哓然曰‘自由’‘自由’,曾未闻有一研究自由之范围、自由之法律者。……是故讲自由者一及于范围、法律,则必有大不自由者在。……公等日以自由之声聒人耳,而曾不肯一讲范围、法律,公等谓非借此为自私自利计,虽苏、张来辩,吾不为屈也。”[3]273这显然不是吴趼人想看到的结果,他没有看到知识者在汲取西学思想时所呈现出来的主体性,换言之,清末知识者们是在缺乏主体性的前提下学习西学的。这不免引起他的担忧,就像久旱的禾苗无法一下子接纳大量的水分一样,中国的危机现状也不可能全部依靠西学知识来解决,“若不先在堤内修治备洫,以沟水有所归,贸然一决,必不免淹及田禾。”[4]552这是吴趼人对清末知识状况的观察,也是对这一知识状况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进行的预判,其目的就是提醒人们主体性之于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对那些志在西学的知识者来说,倘若不以主体性的姿态学习西学,那么,他不仅学不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反而最终会为其所害。
基于对清末知识状况的担忧,以及对文化主体性的思考,吴趼人开始对曾经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进行详细考察。他先从个体解放的视角考察了宋代理学的时代价值,认为宋代理学提供不出真正的精神资源,是束缚人们精神的罪魁祸首,“宋儒责人太甚,动不动要讲天理人欲。讲天理的,不准有一点人欲。”[4]556-557其次从致用的视角衡量了宋代理学之于当下社会的精神效用,认为宋代理学由于专注于功夫的培养,很少对现实表现出切实的关注,所以,它们距离现实越来越远,以至于在“救世”的当下显得空乏无用。譬如,在历史小说《痛史》中,程九畴和宗仁关于“正心”“诚意”有过一段精彩的讨论。程九畴认为宋代理学“徒托空言”“好陈高义”,“讲到正心、诚意,那些兵卒们,若不是人人都正心、诚意,也不能取胜呢。然而要教他正心、诚意,正不知从那里教起。还不如说些粗浅忠义之事,给他们听,养成他那忠义之气么?”[5]由于无法和现实保持动态关联,宋代理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很难认可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人们还有时间去研读“正心”“诚意”的义理这一行为,显然,宋代理学的不即物品质,不能为主体性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否定了宋代理学之后,吴趼人又考察了先秦的儒家文化,尝试建立中学与西学的融通之处。譬如,谈论民权,吴趼人认为《尚书》已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论述,《孟子》不仅多次出现类似论述,而且涉及民权思想的不同层面,因此,他认为:“民权之义,早见于三代,而大昌明于孟子。”[6]207再如,谈论公德,吴趼人认为《大学》中已有“与国人交,止于信”等类似的阐述,并以“泛爱众”“主忠信”等其他论述[4]548,表明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相通之处。王尔敏将此一思想归纳为“西学源出中国说”,“其意义实在于两种不同文化初接触时的文化心理反应,表达人们对于新事物寻求自圆其说”[7],但吴趼人思考的本意并不在此。因为对他而言,如何用新思想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才是最根本的,所以,他全心都在思考如何接受新思想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生成自己的文化主体的问题。当然,儒家原典中的相关论述与西方文化理论并不能如此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考虑吴趼人要探索的是建构主体性的方法,探索的是哪一种本土资源更有效于文化主体的生成时,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这一良苦用心只不过是想通过一种简单的比照来告诉人们,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才是建构中国文化主体的有效资源。
由此,他提出了“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4]559这里所说的“道德”是就先秦儒家文化而言的,其要有三:一是“孝”,《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8]5孔子认为孝是儒家文化对人要求的首要标准。在小说《恨海》中,陈仲蔼在京城动乱之际不远离父母,“别的事不敢令父亲动怒,这件事任凭大人责罚,孩儿也不敢行”[9]。陈仲蔼在双亲被害之后先把他们草草安葬,等时局缓和下来,又把他们迁葬广州,尽了作儿子的一片孝心。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8]19陈仲蔼的行为符合“孝”之道,这是吴趼人最看重的地方。二是“忠”,《论语》曰:“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8]38“忠”本身是双向的,它是君臣双方都应遵循的责任伦理。在小说《痛史》中,宋度宗整日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已经失去了对臣子和老百姓的忠信;贾似道则一味弄奸取巧,表面取悦于皇帝,暗地里却与蒙古国往来,更没有忠信可言。宋度宗、贾似道的行为均不符合“忠”之道,所以受到了吴趼人的强烈谴责。三是“义”,《论语》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8]178在小说《恨海》中,张棣华和母亲白氏住在张家店,店主人五哥夫妇待人厚道,他们不仅为白氏抓药、替她们张贴寻人启事,而且在住店客人过多时,还让张棣华母女二人搬进五姐儿的屋里。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张棣华母女的行为可谓是一种义举。
总之,吴趼人对“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倡导是一次积极的“救世”行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恢复固有之道德’的思想并不是消极厌世和思想倒退的标志,而是他尽自己的最大可能,努力探求济世之术、设计救国方案的积极用世思想的一种体现方式。”[10]只不过他的“救世”行为更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没有其他“救世”方案显豁、直接罢了。这也提醒我们,在理解“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内涵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去把握它才可能是最佳的切入点。
二 社会“怪现状”批判:主体性建构的文化起点
“怪现状”是吴趼人对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也是为其所下的文化判语。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趼人开篇就借助九死一生概论了清末现实,“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11]16。而在几年之后的《近十年之怪现状》,他再次明言:“此念才起,即觉魑魅魍魉,布满目前,牛鬼蛇神,纷扰脑际。”[12]吴趼人为何要不断地强调清末社会的“魑魅魍魉”性质?当时对清廷的批判并非没有,如医俗道人就直接说:“中国的社会,多也多极了。腐败也腐败极了。”[13]然而,由于吴趼人始终考虑的是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所以,他对社会性质的判断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思考的。至于“魑魅魍魉”,它本是古代传说中的鬼怪,属于“子不语怪、力、乱、神”[8]92的范围,如果考虑“‘子不语’的怪力乱神在中国并无太多市场”[14]这一文化事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吴趼人以“魑魅魍魉”为喻,实际上是在提示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以及清末社会失序的原因,清廷正是因为丢掉了儒家传统,才失去了它既有的文化主体性。显然,借助“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吴趼人在光怪陆离的“怪现状”现象之中,不仅看到了家庭伦理的颠倒与社会秩序的失范,而且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与社会整体诚信的缺乏,同时也看到了个体欲望的膨胀与社会公德的溃烂等,所以,他要完成对社会“怪现状”文化上的揭示和暴露,并将此作为以“恢复”文化主体性为终极目标的奠基和起点。
吴趼人从家庭失序现象中看到了儒家礼制文化的缺失。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小说通过“我”的社会阅历,看到许多人都没有遵守应有的职责,这些背离礼制文化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幸福,也给社会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譬如,长辈职责的变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石映芝,为人十分谨慎,懂事孝顺,但是他的母亲却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因为与媳妇不和,就不断责骂石映芝。她去街坊邻居家里“数说他儿子不孝”,也去石映芝朋友的家里“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后又去招商局“求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以致映芝最后丢掉了工作。[15]539-540正是由于她的存在,这个原本还算富足的家庭最终失去了幸福的庇佑。再如,子辈职责的丢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符弥轩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他向他的爷爷符最灵要钱花,一会儿说做生意没有本钱,一会儿又说给的本钱太少。符最灵没有办法,只得不断地拿出钱来给他,“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化了个一干二净”。[15]573-574更可恨的是,他把符弥轩抚养长大之后,符弥轩却把他看作“赘瘤”[15]575,经常虐待他,甚至不给其吃喝,以至于符最灵最终不得不向邻居“求乞”[15]579。又如,亲戚职责的偏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我”的伯父就是一个有失身份的长辈,他的所作所为早已偏离了作为亲戚的职责。“我”由于对伯父的为人处世知道得太少,所以,在父亲去世之际,“我”在第一时间里就采取相信伯父而不信任张鼎臣的策略,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的伯父拿到“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11]19之后,便一去没有了音信。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依靠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尽职尽责,《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食诸?’”[8]151儒家强调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伦理,所谓“父父,子子”,就是说当父亲的就应该像一个做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就应该像一个做儿子的样子,唯有当每个人都知道了自己的责任,并自觉地遵守这一伦理时,这个家庭才会有秩序地运转开来。由于家庭联系着社会,这些家庭中的各种“怪现状”其实也是清末社会礼制文化缺失的反映。
吴趼人从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现象看到了儒家忠信文化的缺失。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小说通过高升、南京祥珍珠宝店的掌柜等人的叙述,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欺骗行为,这些不符合忠信文化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人们自身的道德信誉,也给他们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失。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叙述了一个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惊天骗局,南京祥珍珠宝店的掌柜被设局骗去几万两现银。又如,名不符实的社会募捐。吴趼人看不上那些所谓的“大善士”,更不承认那些打着慈善名义所做的各种募捐活动。他以自己的父亲为例,讲述父亲的行善行为。父亲家庭富足,但是仅接济本家族人,而无法一一照应所有的亲戚与朋友,因此他的父亲虽然行善,却称不上是“善士”,以父亲为参照,那些所谓的“大善士”就显得名不符实。儒家文化曾提出“忠”的范畴,并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之上。“忠”就是诚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当中坦诚相待,反对各种瞒和骗的行为,社会秩序之所以能正常运行,依靠的就是每一位社会成员身上的诚实品德。但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再坦诚相待,这是儒家忠信文化丢失的表现。
吴趼人从个体私欲的膨胀现象看到了儒家义利文化的缺失。在“礼制”“忠信”之外,“义利”也是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文化保障之一。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是统一的,它尊重作为个体的私欲,但是在顺序上则强调以义为先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要求人们从社会“公义”的伦理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对社会积弊的积极预防。晚清的义利观有多维形态,有人主张实业富国,有人主张去利救世,有人主张变法维新,等等,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义利观,其实质都是围绕着当时最大的“义”,即民族、国家的富强而言的。但是到了清末,人们的逐利行为已达到偏至的地步,这些人不知道“义”的内涵是什么,更不知道“救世”为何物,只想着如何放纵个体的贪婪和私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此有很好的揭示。譬如,买官卖爵现象。一种是用钱捐官。这是纯粹的买官行为,买官人不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只需花费相关的银钱,就可买到一定品级的官职,如,钱庄的一个收账伙计竟然通过妓女“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11]28-29;钟雷溪在办了一段时间的钱庄之后,也用钱“捐上一个大花样的道员”[11]52。另一种是调剂私人候补。这些人或与督抚相识,或与藩台相交,或有“阔阔的八行书”[11]29,符合这三条之一的才能得到调剂。再如,营私舞弊现象。小说第十四回揭露了南洋兵船营私舞弊的种种内幕。据吴继之所说,这些管带根本无心公事,他们带领的兵船也根本无心迎战:“南洋兵船虽然不少,叵奈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那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那里还肯去打仗!”[11]98对于这些营私舞弊的情况,上级官员并非不知道,但是却不彻查追究,原因就是他们也是其中的受益者。由此,从督抚到管带,乃至到更下级的官吏,他们实际上都在维护着一种逐利思想。又如,技术贱卖现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赵小云所做的工艺品小轮船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做出来的小轮船不仅精美,而且价格低廉,其原因则是中国技术员未能受到足够的薪金待遇。赵小云已经在制造局当了十多年学生,他所制造的器物很精美,但是在待遇上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11]217,而外国工师的薪水却比他高得多,有了这些信息作为参照,我们也就不再惊奇他的小火轮为何精美却又价廉了。
综上所述,清末社会的各类“怪现状”在灭国亡种的危机面前显得尤其刺人,但小说家对它的揭示并非是最终目的,因为他要通过这一揭示来坚定其“恢复”和“重塑”“我固有之道德”的信心。从这层意义上说,吴趼人在揭示“怪现状”现象的同时,也在表达着对它们的否定。他不仅要将它们摈弃在理想社会的外面,而且要在克服它们之后走向未来。
三 “文明境界”想象:主体性建构的文化实践
“文明境界”是吴趼人关于理想社会的一次乌托邦畅想,但是,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狮子吼》等基于现实制度考量的政治小说相比,“文明境界”的思考似乎更为遥远,更像是对未来中国愿景的某种设想和规划。之所以是“设想”或“规划”,是因为在“文明境界”叙述中,吴趼人并没有将叙述重心放在对“文明境界”景象的格外关注上,而是很有节制地在每一次描绘之后,就及时展开对“这些器物为何会如此先进”,或者“这里的生活为何会如此美好”等问题的追问,如“老少年演说再造天”“研医道改良饮食”“验病所痛陈医理”“闲挑灯主宾谈政体”“论竞争闲谈党派”,等等,几乎都是老少年以当事人的身份,对这些问题的主动回答和释疑。所以,尽管“文明境界”里面的景象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小说家却一直在做着矫正读者目光的工作,期望他们多注意一下老少年的介绍和解说,去注意一下这个融合道德昌盛与科学发达于一体的现代寓言是如何实现的。而一旦将目光从那些奇谲的科幻叙事中移开,去专注于老少年的详细讲解时,我们就不得不直面当时中西学战的问题。这是小说家的有意为之,也是小说家的最终目的。他就是要在这里正面凸显儒家文化之于主体性建构的价值,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新的文化主体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并以理性的视野去估量西学的价值。由此,借助“文明境界”的想象与描绘,吴趼人对于未来文化主体的构思和探索便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了。
吴趼人认为中国自有其属己的文化,他将儒家文化视为是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由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文化。这在“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表述中说得非常明白,所谓的“我”即是指中国,是指在与他国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应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它反映的是“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扮演的是主体角色”[16]。正是缘于对中国主体位置的维护,吴趼人才在构建中国想象时,坚决强调儒家文化之“固有”于未来中国的重要性。在“文明境界”中,老少年将少年的修身学习看作是与未来“文明”关联的基本环节:
敝境的人,从小时家庭教育,做娘的就教他那伦常日用的道理;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课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贱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胸中。这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你不看见那牌坊上“孔道”两个字么?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内,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17]489
“孔子之道”就是儒家文化之道。对它的强调一方面包含了吴趼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以及它之于未来中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表明,吴趼人所期冀的文明之道是以“孔子之道”为主体,并由之发展而来的。基于这一考虑,“文明境界”对待儒家文化的做法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先让父母负责孩子们的学前教育,并向他们传授“伦常日用的道理”;在孩子进入学堂之后,再由先生们负责他们的在校教育,而在学堂之中,又以儒家文化的习读为基础,并将“修身”之课放在首位,把它作为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之课。
除了在基础教育的层面强调儒家文化的重要之外,吴趼人还将儒家文化作为主体的回心之点,西学只有在经过它的筛选和审择之后方才有效。对此,他说得很清楚:“以余观之,彼之文明,彼自以为文明耳,而认其为文明与否,其权在我。”[3]273这里所谓的“其权在我”,即是以儒家文化作为标准对西学的审读,如果所择之西学与中国的发展相适合,那么就值得学习;如果与中国的发展相背离,那么就必须加以否定。在“文明境界”中,老少年对于国家政体的讨论就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而是在深深结合中国的客观情况之下展开的。他认为不能在没有任何媒介的情况下,空洞地谈论西方的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种政体,尽管它们有着比专制政体更多的优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有主体性地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才是最佳策略。“文明境界”采用“文明专制”的事实表明,在全民实现了“道德普及”[17]473的情况下,那些“已经饱受了德育”[17]473的百姓,能够比较容易地成长为具有职业伦理的官员,而基于这一伦理办事的他们则因此避免了成为“暴官污吏”[17]473的可能,“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他做百姓的时候,已经饱受了德育,做了官,那里有不好之理。百姓们有了这个好政府,也就乐得安居乐业,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17]473所以,老少年才说,“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没有一害”[17]473。显然,“文明境界”因儒家文化而彰显出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性,儒家文化在“文明境界”之所以成为“文明境界”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吴趼人对于西学也十分重视,但这种“重视”是在把它们作为媒介的层面上成立的。众所周知,文化选择在清末已经成为知识者需要直接面对的历史课题。有些人或“以平等自由为邪说”[6]204,或“目民权之说是邪说”[6]208,或“攻新学为邪说,为异端,视之如水火”[6]209,甚至对于新政表现出反感姿态,“候补各员闻人谈新政,愚者掩耳疾走,黠者极口诋毁。”[6]209但是吴趼人不这么认为,他不仅因为“见人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我无此力量,坐看他人开眼界添阅历”[6]204而难过,而且以西学为媒介来审视社会现状,以查找其种种不足,如,能见到“每遇一显要到任,则衙门左近各客栈有人满为患”[6]204之景象,能听到“世人每以油嘴滑舌、巧于应对之辈为有阅历,有经济,有本事”[6]206之评价。所以,吴趼人并不低估西学的价值,而是赋予其显豁的媒介价值。譬如,在《新石头记》中,“文明境界”既是一个尊重科学的地方,也是一个科学昌盛的地方。这里出行便利,相比传统的马车,“文明境界”已拥有十分先进的飞车,这些飞车不仅有超强的安全性,而且有完善的与之配套的交通指挥系统,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停靠,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这里饮食卫生讲究,有完备的供餐系统,食物均是经医学家发明提取之后的食物精液,不仅卫生而且安全,食之不会有生病的可能。茶水也是如此,都是经过蒸汽处理之后的没有颜色的茶水。这种茶水“不过取一点香味,可以醒胃消食”[17]453-454,既保留其功效作用,又将可能对人体产生负担甚至危害的颜色加以处理了。更令人惊叹的是,“文明境界”里的家庭中没有厨房,而是实行统一供食、统一供水:“敝境人家,从来没有厨房。每一区地方,有一个总厨,四面分布送食管,按时由管送到,丰俭随人。这送食管就同那自来水管一般。非独是吃饭,便是喝的茶,也是由总厨里供应的。”[17]453这些都是“文明境界”最基本的设施,其他如“司时器”“助聪筒”“验性质房”“测验性质镜”“地火”等,也都可以被看做是“科学昌明”的日常表现。这里娱乐系统丰富。只需翻览一下《新石头记》的目录,看一眼“中非洲猎获大鹏”“捕鲲鱼快乘猎艇”“遇荒岛鸣枪击海马”“沉水底发电战鳅鱼”“慧神瑛戴冰获貂鼠”“探南极异景看漩涡”“走隧道纵游奇境”等题目,即能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毋庸置疑,这些皆是西学之所长,中学之所短的地方。它们之所以在这里被给予充分的展示,并不仅仅是为了格外凸显西学的价值,而是在尊重西学价值的同时,有意识地展示了它在怎样的层面上促进了中学的成长。这种对于不是“替代”,而是“促进”的分寸把握,是在媒介的意义上理解西学价值的典范,它不仅表明了有益于未来中国建设的西学内容是什么,而且展示了它们如何被儒家文化所吸收、所转化的可能性。
王德威曾评价“文明境界”说:“这些科技发明和神奇探险,不应只被视为商业噱头或者个人狂想。它促使我们分析小说中‘物质’的层面如何成为理解吴趼人的道德和哲学视野的关键。”[18]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文明境界”物质层面之外的“哲学视野”,并为我们的阅读做出了提醒,遗憾的是未能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关联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其实,这一“哲学视野”还应落实在吴趼人所提出的“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上。作为未来中国的理想形态,“文明境界”由于吸纳大量西学而不再可能是其最初的主体形态,但是它又没有呈现出与传统文化相悖的全盘西化的特征,所以,“文明境界”是道德昌盛与科学发达的完美融合。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关系不是毫无媒介地相互“掺和”。基于对自我的确信,儒家文化积极地以西学砥砺自己,并在不断的砥砺过程中涤荡和否定自己,最终使得被西学砥砺之后的自我,已不再是最初的自我,而是成长为包容了许多西学知识在内的新的自我。[19]
四 结 语
“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吴趼人小说当中最具标识性的两个主题。从表层看,一个批评现状,一个憧憬未来,其主旨似乎正好相反,但是,从内层看,无论是暴露还是想象,却又好像有殊途同归之意。冥飞评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时认为:“家庭怪状,几于无家不然,盖家族制度不良之故也。”[20]报癖谈及《新石头记》时指出:“大都与实际有密切之关系,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进,愈阐愈精,为极文明极进化之二十世纪所未有。其描摹社会之状态,则假设名词,以隐刺中国之缺点,冷嘲热骂,酣畅淋漓。”[21]可见,“怪现状”与“文明境界”实为吴趼人小说主旨的一体两面。吴趼人在文化上主张“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他对清末的现实思考都是以此为前提的,这就使得他的小说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意味,可以说,“怪现状”与“文明境界”都是基于“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积极实践。通过对社会“怪现状”的揭示,小说不仅呈现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趋势,而且彻底否定了宋代理学以来儒家文化之于主体性建构的价值;相反,凭借对未来“文明境界”的描绘,小说则不仅展示了涤荡之后新儒家文化的先进姿态,而且充分肯定了先秦儒家文化在构建现代文化主体中的意义。当然,吴趼人的文化认识也并非没有局限,譬如,在谈论政体时对于文明专制的偏爱,在观看军队演习时对于蒙汗药水的使用,等等,均可看到他对于自我的某种偏至或执拗,甚至呈现出非常保守的倾向,这也使得他的这一“救世”方案在当时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如果从文化主体构建的视野来看,这种“偏至或执拗”其实正好表明了他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坚守,考虑到自己的历史只能由自己来书写这一原理,以及当时新小说因“随声附和故”,而“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22]的创作现状,我们就不难发现,吴趼人小说里面所内含的那种依靠自我而不是他者来构建主体的决心和勇气,其实是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这恐怕正是小说家用心所在的根本原因,以及由此所呈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