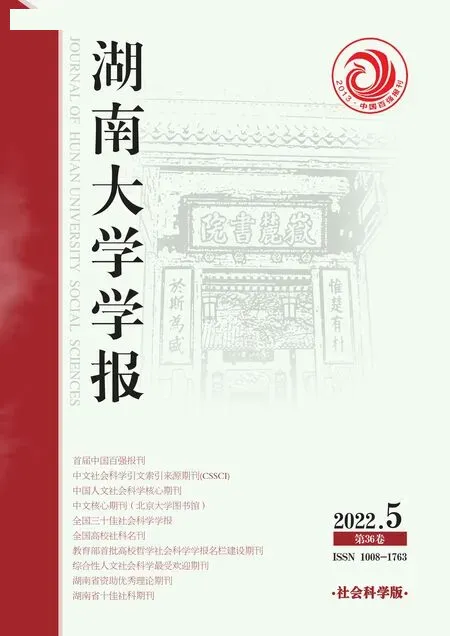回归孔子思想,避免过仁虚谈*
张 景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范式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无论思想还是行为,孔子都坚持“过犹不及”的中庸原则。然而自孔子之后,其思想就进入一个被后学不断拔高的过程,以至于出现“过”的倾向。这一现象也发生在道、墨等其他学派中。认真反思这一现象,不仅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古代学派的兴衰原因,而且对今天的思想建设也具有极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孔子对“过于取仁”的批判
在孔子思想中,“过犹不及”的中庸原则是一个极高的言行标准,以至于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91即使对仁这一核心思想,孔子也以中庸原则予以审视。孔子坚决反对不仁言行,但在中庸原则的支配下,他同样反对“过仁”言行: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如何?”子曰:“仁也。……夫子纠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于取仁,未足多也。”[2]16-17
常人认为召忽为公子纠而死是仁的表现,而管仲则相反。孔子在承认召忽的行为属于仁的基础上,批评他“过于取仁”,也即超过了仁的标准,过犹不及,因此其行为不值得赞赏。
孔子不仅反对召忽自杀式的“过仁”之举,而且也不强求大众做到他所赞美的“安仁”。孔子清醒地认识到人们行仁动机不同,《论语·里仁》把行仁动机分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1]69两个层次,《礼记·表记》则分为三个层次: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3]1301
最高的美德是发自天性、不求任何功利的仁行,即“安仁”;其次是认识到行仁对彼此有利而去行仁,即“利仁”;最低层次则是迫于畏罪心理而勉强自己去行仁,即“强仁”。“安仁”明显高于“利仁”“强仁”,但孔子并不宣扬“安仁”而赞成“利仁”,并以此要求弟子: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4]419
子贡出钱赎人拒绝回报,属于“安仁”,却受到孔子批评;子路救人接受酬劳,属于“利仁”,却得到孔子表扬。孔子批子贡、褒子路,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3]1301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3]1304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1]70
孔子认为“无欲而好仁”之人十分罕见,偌大天下只有一人能够做到。特别是后一段话,孔子反复感叹自己从未见过“好仁者”。既然只有一人能做到安仁,而自己还从未见过,那么提倡安仁,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岂不是徒劳?既是徒劳,就没有必要提倡。对待众生就只能宣讲层次低一些、带有互利性的仁义。
孔子倡仁,不是着眼于能够安仁的“天下一人”,而是考虑常人的接受能力。天下人都做不到安仁,那么如果用安仁去强制人们,就只能使人们既做不到安仁,同时也放弃利仁。孔子提倡互利性仁义,期盼世人接受,从而把人们的言行控制在一个较为宽松的道德范围之内,这是一种非常可行的合理举措。
孟子“利仁”思想更为明显,以至于有人认为孟子提倡“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1]207不过是“以《诗》《礼》发冢”而已:“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辩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阖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5]311此说乃亵渎圣贤,因为孟子“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主张建立在君民互利基础之上,而“发冢”则纯粹是损人利己。
在对待欲望问题上,孔孟也采取中庸态度。多数思想家都把欲望视为恶之源,荀子、韩非更把带有欲望的人性直接界定为恶。而孔孟对欲望采取相对宽容态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70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1]369孔孟都承认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只是要把“欲”控制在“道”的统辖之内,或者降低一些欲望:“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1]374孔孟主张的不是灭欲,而是控制在道义之内的寡欲。
孔孟面对现实,推行不“过”也不“不及”的道德原则,用“利仁”去引导普通民众,使社会维持一种互利和谐状态。然而到了后世,儒生则不断拔高仁义标准,从而走向“过”的偏颇之路。
二 后人不断拔高孔子思想的动因
《关尹子》说圣人讲话“如引锯然”[6]308,兼顾两端,取其中庸。而一些后人知进而不知退,对孔子思想进行不断拔高,这种“递高”动因源于学派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
造成学派思想“递高”的内部原因有二,一是真诚希望自己学派的思想体系变得更加完美,二是其后学在“相胜”心理支配下而有意拔高该学派的言行标准,目的是争夺该学派的嫡传地位。
早期儒家属于人类中心论者,他们在评价事物的价值与是非时,往往以人的价值观为准的,而道家则属于万物平等论者,《吕氏春秋·贵公》记载: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4]25
荆人爱所有荆人,孔子爱整个人类,老子泛爱万物。孔子的主张比老子现实得多,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但从抽象理论看,人类中心论者的思想境界要低于万物平等论者,不利于人们以更仁慈的胸怀去接纳万物,所以《吕氏春秋》说老子境界高于孔子,是“至公”。
孔子思想的这一“短板”,后儒竭力予以修补。《论语·乡党》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轻物爱人的表现,而后儒为此深感遗憾,于是就修改文意以拔高孔子思想。其修改方式有二,一是改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二是改为:“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修改后的意思是,孔子听说马棚失火,先问是否伤人,后问是否伤马。为何要殚精竭虑作此修改?因为后儒认为:“圣人岂仁于人,不仁于马。”[7]712这些后学真诚希望孔子的思想体系变得更加完美,以免输给孔子的老师老子,但这些修改毕竟不合孔子原意。
不少学派都有传人,这些传人为了证明自己是当之无愧的正统嫡系,于是就在本学派的思想方面表现得比自己的师辈、同辈更为激进。《韩非子·显学》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8]456-457
为证明自己“真孔、墨”身份,后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相互批判。《论语·子张》就记载子游批评子夏门人“本之则无”,而子夏则反驳“言游过矣”[1]190。荀氏之儒更是批评子思、孟氏之儒“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是则子思、孟轲之罪”[9]94-95。在墨家后学那里,这种相互批评更为激烈,他们“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为了成为巨子,“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相进而已”[10]289-290。后学就是在这种相互批评、彼此争胜的氛围之中有意无意地拔高了本学派的思想主张。
外部原因很复杂,除了学派间的相互刺激等因素之外,政治环境是导致儒学被拔高的主要动因。任何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学说为自己服务,一种学说一旦与帝王“联姻”,就会极大地改变这种学说的原始面貌。儒家思想被帝王相中,于是帝王的利己动机就凭借强权迫使儒家不断片面地拔高其中有利于自己的主张。
孔孟提倡忠君,但其忠君有前提。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6,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290。到了后世,孔孟忠君思想被片面拔高了。《史记·儒林列传》记载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反驳:“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以“冠虽弊,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来论证上下秩序不可颠倒,即使君主失道,臣下也应正言匡纠,不可乘机篡杀。辕固生反驳:“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史记》接着记载:
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11]2374
辕固生的主张更符合孔孟思想,但他的主张使景帝陷入两难窘境:如支持辕固生,就等于承认只要汉朝廷一有过失,他人就可合理合法地取而代之;如支持黄生,就等于承认高祖取秦属于篡杀,这实际就是否定汉朝存在的合理性。于是他只好要求学者回避这个问题,使这次争论不了了之。从“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这一记载看,这次争论给学者心理上留下的阴影是巨大的。朱元璋“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命儒臣修《孟子节文》”[12]2645。朱元璋就因为孟子强调忠君的前提条件,竟然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并删改了《孟子》。
孔孟忠君思想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应该说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删去前提的忠君就使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衡。这种改造,站在统治者立场看,也是一种“拔高”,是一种朝着“完善”方向的发展,但这种“拔高”却是对学派原有合理思想的严重破坏。
三 对孔子思想的拔高
《礼记·缁衣》记载了孔子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纟孛。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3]1324
帝王之言本来细微如丝,及其传到外面就粗大如纶了,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孔子批评那些“可言也不可行”的“过仁”言论是不可提倡的“游言”。孔子这段话不仅适合帝王,而且在他自己身上也得到验证,他这位“素王”的“如丝”言论被后儒夸大得“如纶”“如纟孛”。这种对孔子思想进行不断地、无限地拔高行为,极大地违背了孔子所主张的中庸原则,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使许多儒家思想原则成为“不可行”的“游言”。
先秦时孔子思想就已被拔高,孔子多次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1]153,而孟子则认为“管仲、晏子犹不足为”[1]228。到了汉儒时,“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3]1365。而宋明学者对孔子思想进行了一次全面提升,把孔子仁义上升到“天理”高度,进而提出存理灭欲的主张。先秦人虽然认为欲望是恶源,但他们知道欲望无法根除,也不可根除,所以孔子并不否认自己对富贵的渴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96,只是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孟子也只主张“寡欲”。而周敦颐《养心亭说》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14]52周敦颐认为孟子的“寡欲”主张不行,只有“无欲”才能成贤成圣。周敦颐在孔孟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而这必是踏空的一步,因为没有任何欲望的人根本无法生存。
对于这些随意拔高孔子思想的言论,儒家学者在相互审视时业已察觉。张栻与朱熹同为理学中人,且关系密切,两人之间的论学成为思想史上的佳话。然而朱熹就曾反复批评张栻的《论语解》“失之太高”:
(张栻)天资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逐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15]1922-1923
其立言造意,又似欲高出于圣言之上者。解中此类甚多,恐非小病也。[15]1359
今为此说,是又欲求高于圣人,而不知其言之过、心之病也。……今读此书,虽名为说《论语》者,然考其实,则几欲与《论语》竞矣。[15]1370
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15]1375
朱熹批评张栻解释《论语》时,立意比孔子还高,比圣人还要“圣人”,是在与“圣人竞矣”,甚至“视圣贤太轻”,以至于其主张变成了无法实践的“虚谈”,也即孔子所批评的“游言”。这种来自儒家内部的批评极具说服力。张栻《论语解》主要继承二程学说,二程曾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16]378张载同样认为:“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较。”[17]276这实际就是主张脱离儒家经书文字以发挥自己思想。从理论上看,这种做法并无不妥,而事实上,由此发挥出来的思想已经不是原始儒家思想,而是被拔高后的新儒家思想。如果这些学者能够沿着中庸、实用的路子前行,自是好事,可惜的是他们拔高了原本就难以企及的圣人境界,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极端。
朱熹对张栻的批评,就是对后儒“太高”思想的某种纠正。然而批评别人“失之太高”的朱熹又被别人批评为“为已甚之论”。所谓“为已甚之论”,同样是“失之太高”。王夫之说:
自荀孟有贵王贱伯之说,儒者遂为已甚之论,虽折衷以圣人之言而犹未定也。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既已以正许之矣,而朱子犹曰“心皆不正”。[18]409
孔子认为“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而朱熹对此却不认可:“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1]153朱熹对齐桓公的评价与孔子发生严重分歧,他拔高了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所以王夫之批评其说“为已甚之论”,而且王夫之认为这种“已甚之论”从“荀孟有贵王贱伯之说”时就已开始。
朱熹同张栻一样,拔高了孔子思想,而朱熹的弟子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序》批评朱熹弟子们犯了相胜毛病:
洙泗之传,至孟子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自后辩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19]240
王阳明认为朱熹思想已经偏离了孔子思想,而朱熹弟子与墨子弟子一样,“挟胜心以附己见”,以至于进一步拔高了朱熹思想。朱熹比孔子还要“孔子”,而朱熹弟子比朱熹还要“朱熹”,这种层层拔高现象,使原本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儒家思想变为看似美轮美奂却无实践意义、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我们顺便要提到的是,后儒不仅在道德层面上拔高孔子思想,在论证方式上也有所拔高,使后儒在天、理、心、性等概念及彼此关系方面纠结不清:“(孔孟)道理甚明、甚浅、甚易,只被后儒到今说底玄冥,只似真禅,如何使俗学不一切抵毁而尽叛之?”[20]74这是被誉为明万历年间天下儒家“三大贤”[12]3966之一的吕坤的深切感受。
四 对孔子形象的拔高
后儒不仅拔高孔子思想,也极力拔高孔子的形象。这种造神行为从孔子弟子时就已开始,《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1]234-235
孟子也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1]234这些或亲炙、或私淑的弟子们把孔子摆放到了孔子所要祖述、宪章的尧舜、文武之上(1)《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已有“附骥尾”者护骥崇师的虚夸之嫌(2)《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索隐]曰: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以譬颜回因孔子而名彰。”,而汉代的谶纬家更是把孔子打扮成一位无所不知的神汉。
如果说上述拔高还属于弹性很大的虚性评价和神学呓语,那么还有一些后儒则对孔子言行进行了具体的洗刷和修补。如王十朋《策问》说:
夫子之始末,莫详于《世家》。抑尝读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辩?夫子尝适周矣,及其施(疑为旋)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发,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岂足为圣人乎?此不免乎疑也。[21]
王十朋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在思想、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其观点具有代表性。王十朋的辩护逻辑是:圣人没有缺点,孔子为圣人,因此孔子没有缺点。王十朋至少忽略了两点:一是孔子的思想修养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因为孔子不是一位生而知之者——“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98二是圣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就会有欠缺,更何况“发人之恶”未必就是错误。《史记·孔子世家》载,当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时,孔子就唱着“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11]1546的怨歌离开鲁国。当“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时,孔子也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1]1548。这不是在“发人之恶”吗?
《论语·雍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见南子,东方朔《七谏·沉江》、王逸《楚辞章句》、《殷芸小说》卷二都记载孔子求爱桑女,《韩诗外传》卷一记载孔子戏挑阿谷漂女。这些事被写入典籍,不会全是空穴来风。而后儒为维护孔子形象,对此绝少提及或加以否认。《孔丛子·儒服》记载子高为孔子辩护的情况:
平原君问子高曰:“吾闻子之先君亲见卫夫人南子,又云南游遇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闻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卫,卫君问军旅焉,拒而不告。问不已,摄驾而去。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觌乎?……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类以行其心者之为也。”[22]339
子高不仅否认孔子的阿谷之事,而且连见南子的事也一并否认。后来洪迈对此也愤愤不平:“观此章(指《韩诗外传》孔子见阿谷漂女一章),乃谓孔子见处女而教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可乎?其缪戾甚矣,它亦无足言。”[23]205洪迈没有否认此事,只是批评韩婴不该拿此事解《诗》。
《论语·子张》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1]191同样的道理,圣人也不会“如是之完美也”,因为圣人有了美名,“天下之美皆归焉”,于是完美的圣人就出现了。对此孔子坚决反对:
孔子闻之曰:“……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11]2450
孔子认为连上天尚且无法做到完美无缺,更何况人?因此人们做事不求十全以上应天道。孔子进一步强调,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其“不全”。
捧杀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直接把他吹捧为完美、极致之人,让他蹲踞在远离世人的神坛之上。孔子为了保证自己思想的活力和实用性,反对“过仁”言行,始终着眼现实。而后人或出自善意,或源自私欲,把孔子塑造成了一位毫无瑕疵的完人,把儒家思想拔高到极致,从而斩断了孔子深扎于现实土壤中的思想根须,后人捧杀了孔子。
五 拔高孔子思想的弊端
《中庸》记载了孔子的一段极为精辟的话: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1]21-22
孔子明确指出:君子之道广博深邃,即使普通民众,也能懂得其中一些内容;但其最高境界,连圣人也难以企及。然而后儒偏偏要拿这些连圣人也难以企及的标准去苛求普通民众。韩非对此已有察觉:“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8]450-451拿“上智之所难知”的“微妙之言”去要求普通百姓理解、实践,其结果适得其反。无过不及的中庸原则是人类一切行为准则,思想发展也不例外。对思想进行无限拔高,看似完善了学派思想、圣人品质,然而却使这些学派和圣人一步步远离了普通民众,变为遥不可及的方外之物。思想“递高”的弊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派本身的伤害,二是对社会的伤害。
一个学派初期虽有许多不足,但毕竟是源自民众生活,植根于现实土壤,因此充满生机。后学的改造和拔高,逐步使这一学派的主张走向极端,从而失去了生命力。如墨家,后世弟子为争巨子地位,便以“苦”相胜,最后使这一学派因陈义太高、脱离现实而被世人遗弃。原始道家既讲治国,也讲养生,道教出现以后,世俗的“黄老”逐渐成为“修仙”的代称,忧国忧民的思想家老子被装扮成身着道袍、端坐神坛的太上老君。佛教发展到禅宗,本是件中国化的好事,可后来也慢慢走向极端,出现了生杀自由、无所忌惮的“狂禅”,连佛教内部对此也深感遗憾。儒家也没能摆脱这一宿命。
有些主张即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过度,照样使人生厌。仁爱是孔子思想核心,孔子主要讲爱人;后来发展为爱鸟兽,如孟子的易牲、远庖厨言论;再到后来,儒生把植物也列入所爱范围。博爱万物是正确的,但实践中的一些儒生走向极端:“哲宗皇帝尝因春筵讲罢,移坐小轩赐茶,自起折一柳枝。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正为此辈。’太后闻之,叹曰:‘怪鬼坏事。’吕晦叔亦不乐其言也,云不须如此。”[24]452-453连折一柳条都被视为有违仁爱而受到程颐批评,这种爱物思想达到极致。境界是被拔高了,却无法让人接受,就连同为儒家的司马光和吕公著都认为程颐行为令人生厌,甚至被太后视为“怪鬼”。
这种思想“递高”现象,使本来适中、有用的思想逐步走向僵化,更多地发挥出其负面作用。“递高”使人们塑造出一个完美但虚幻的孔子形象,也塑造出一个完美而难以实践的儒家道德体系,这一孔子形象和道德体系只能以理念形式存在,而无法真正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榜样与原则,甚至成了受人批评的口实。如李贽批评耿定向:“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25]29-30把自己宣扬的思想拔高到连自己都做不到的程度,其结果自己言行难以一致,从而被世人视为欺世盗名。朱熹对此也有深刻认识:“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有称述之者。此知之过而不择乎善,行之过而不用其中,不当强而强者也,圣人岂为之哉!”[1]21-22当一个学派集体宣扬自己无法做到的道德原则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学派的没落。
被拔高的道德标准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孔孟一方面提倡臣事君要忠,一方面又主张君待臣要仁,臣民对君主还可以表达不满与批评,甚至可以诛讨之。但后世君主凭借强权,片面强调君主权利和臣民义务,从而使身为大儒的朱熹也讲出“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26]287这样的话。后儒连批评君主的权利都放弃了,更遑论能像孟子那样理直气壮地去“诛一夫纣”!于是君主就可以任意地乾纲独断。孔子主孝,认为孝为万行之本,而后世却演绎出《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悲剧;原始儒家主张妇德,而后世却把它强化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6]301的极端原则。我们看看《孟子》和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中的相关记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284
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溢,自江西以下,沿江州县被灾……大水时,一女子避未及,水几没腰。有一人急援手救之,女子乃呼号大哭曰:“吾乃数十年贞节,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将同被灾者菜刀自断其臂,仍赴水而死。惜不知姓氏,恐天下穷而贞者似此湮没不少也。[27]152
孟子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但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对这一礼制进行变通。[28]而到了清代,女子宁死也不许其他男子触碰自己手臂。这“一女子”就是死于被拔高后的礼教,而旁观叫好的姚元之则兼备受害者与害人者两种身份。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之所谓理,强断行之……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29]187-188戴震认为后儒对孔孟之理进行拔高,拔高后的孔孟之理已不再是孔孟之理,而是后儒的个人“意见”。换言之,后儒用自己的“意见”置换了孔孟之理,然后以孔孟名义去判决世事的是非曲直,于是宽容温和的孔孟之理就变质为酷吏任心使用的“三尺法”。
孔子曾感叹:“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1]19受李贽批评的耿定向也在《与胡庐山书》中感叹:“六经、《语》《孟》具在,孔孟宗旨灿然,如日中天,第恨智者过之,愚者不及,致令二氏之学充塞流衍,许大豪杰亦自沉困颠迷于中而不自觉也。”[30]68“智者”过度拔高孔子仁义标准,无异于揠苗助长,费尽心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许多学派的“根”就是被后来那些能够“过之”的所谓智者拔离了它们依赖的土壤,从而掐断了它们的生命之源。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仔细清理那些“过仁”的游言虚辞,回归孔子思想——这种回归不是照搬其教条,而是“法其所以为法”[4]391,让孔子思想重新焕发出其指导现实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