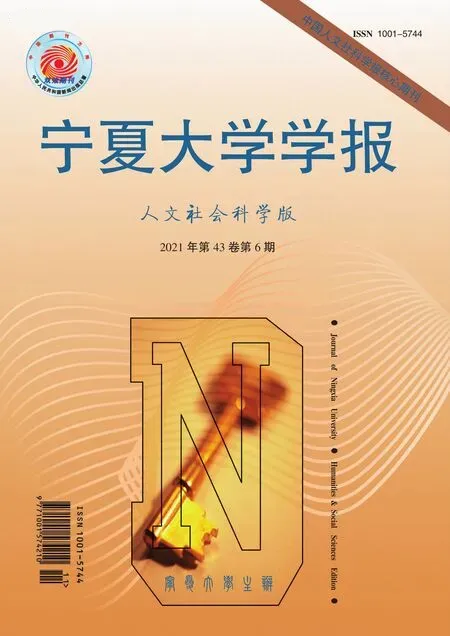王勃诗歌中的佛道思想探析
吴爱玲,梁祖萍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 王勃诗歌中的佛道思想体现
王勃现存诗歌中带有佛道色彩的诗歌共30首,这些诗歌多创作于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入蜀地漫游之后,按照其表现佛道思想的方法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诗题中直接表明与佛道两教有关,如《怀仙》《游梵宇三觉寺》《秋月仙游观赠道士》等,共10 首;第二类是在诗歌语句中运用明显带有佛道两教色彩的词语,或是诗句中蕴含了佛道意蕴,这一类共18 首,为更好论述,此处将具体篇目列入表1。

“兰气熏山酌……香度落花前”《林塘怀友》《圣泉宴》仙杼《春日还郊》 “还题平子赋”《九日》“若个是陶家”《杂曲》智琼神女《仲春郊外》 “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九重《伤裴录事丧子》《铜雀妓》“魄散珠胎没”《述怀拟古诗》神仙

表1 王勃诗歌中带有佛道意蕴的词语或诗句
从上表可以看出,王勃在表现佛教色彩时,多运用带有修心顿悟之意的词语,在表现道教色彩时多采用“仙人”之语,并且带有道家所提倡的跳脱红尘凡间的洒脱不羁意蕴。如“帝乡”便是道家认为天帝所居之所,《庄子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1]再如《咏风》“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便是化用《庄子知北游》“其来无迹,其往无崖”[2]之意,并且出现了佛道思想蕴于同一首诗歌中的情况,如“物外”一词,物外即超越世间事物的意思,而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拥有着这种超越性质,“物外”一词见于道教与佛教典籍之中,如《南华真经注疏》云公子牟:“体道清高,超然物外,识孙龙之浅辩,鉴庄子之深言”,又《楞伽师资记》谓神秀禅师:“迹远俗尘,神游物外。契无相之妙理,化有结之迷途。”[3]运用带有佛道意蕴词语是王勃诗歌中佛道思想的重要表现。
王勃另有两首在诗歌中运用道教典故的诗作,一为《出境游山》其一“化鹤千龄早,元龟六代春。浮云今可驾,沧海自成尘”[4]之句,便是运用的丁令威学道大成后,化鹤归辽之事,其本事于《搜神后记》中记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5]另一首为《散关晨度》,王勃在诗中运用了老子乘青牛车的典故:“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白马高谭去,青牛真气来。”[6]《高士传》中记载:老子好养精气,曾在东周作守藏史,后东周衰败,便辞官坐着青牛车离去,想要去大秦,经过西关时,其令尹喜看见有一股紫色,就事先知道要有圣人过关,便提前访查恭候,后果然老子来了,尹喜就热情地留下他并让他著书,老子便写了《道德经》[7]。王勃在诗中运用这两个典故不仅表明了对得道飞升的向往,展现了对于宗教典故的熟知,也委婉隐晦地表达了自己满腹才华不得重用的悲愤心情,并希望有一个如尹喜一般能够慧眼识才的人能够发现自己的才华与雄心。
如上所论,王勃在这30 首诗歌中或直接或隐晦地将佛道两家的意蕴融入其中,其佛道思想的体现与表达情感是具体而多样的,下面将对其进行详细论述。
二 佛道思想的体现及情感表达
探究王勃诗歌中体现的佛道思想,不能抛开儒家思想不提,作为我国古代几乎在历朝历代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在唐初仍是官方提倡的正统思想。早在隋朝,王勃的祖父王通对儒家思想极为推崇,但即使对于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不一,他仍觉得三者可以共存,因此提出了“三教可一”的命题。及至初唐,统治者汲取隋朝因实行暴政而亡的历史教训,开始复归儒道,提倡“尧舜周孔之道”,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加之家学渊源的影响,王勃早年的作品带有昂扬向上的意趣与积极入仕的态度。但当他经历一系列的打击,理想抱负得不到施展之后,这种积极向上便转变为流连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之外,开始求佛访道,并将佛道思想在诗歌中加以体现。
(一)佛教理念的体现
唐代是一个佛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汉明帝永平三年,经过历朝的发展演变,佛教在唐朝发展到了顶峰,且此时统治者对于佛教也是大力支持。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僧人受皇家尊敬,如唐太宗、高宗之敬玄奘三藏,武后之于神秀,明皇之于金刚智等等,我国佛教最有名之宗派均据此而兴起[8],尤其是主张“修心顿悟”的禅宗的发展更是空前活跃,深奥玄妙的佛理和佛家自我心理平衡的“悟”,不可避免地对文人士子们产生强大的诱惑力,加之残酷的现实使他们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于是便会自觉地向禅佛靠拢,以求佛问禅来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在入蜀地漫游之后,王勃接触了很多佛教典籍,求访了很多佛寺,这使得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禅佛意蕴,并将禅佛理念蕴于诗歌当中,借以一吐胸中郁气。
1.对佛寺佛像的求访
王勃在成年之后,其思想中的佛家理趣逐渐增多,尤其是被高宗怒斥逐府入蜀地漫游之后,王勃带着仕途失意的悲愤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其中不乏对佛寺的寻求与游览。此期王勃除了写下大量的佛碑碑文以及为佛寺和佛教典籍写序、写记之外,更是在诗歌中对佛教理念予以展现。王勃曾作有三首游览佛寺、拜访佛像的诗,即《游梵宇三觉寺》《观佛迹寺》和《寺中观卧像》,据聂文郁先生考证,此期诗歌约作于王勃被逐入蜀的前两年内(咸亨二年辛未前),即王勃二十二岁之前[9]。
在《游梵宇三觉寺》中,王勃通过记录在三觉寺的所见所感,写出了佛教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及作用。三觉寺位于汉州金堂县(今四川省成都金堂北三觉山),此寺建于隋唐时期,香火甚旺,信徒众多。在此诗中,他首先描写了三觉寺环境的清幽,接着描写通往三觉寺的道路是狭窄的,花坛中的花虽无人打理但是却蓬勃生长,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散发出一种野趣。随后笔锋一转,写自己在三觉寺的所见所感:“萝幌栖禅影,松门听梵音。遽忻陪妙躅,延赏涤烦襟。”[10]无论是“山路、花坛”,还是“禅影”“梵音”等,都渲染出了一种情境幽寂的氛围,在这种出尘幽静的氛围下,王勃便感到“延赏涤烦襟”。也只有在这种幽寂的环境之中,心中的烦恼才能够得到洗涤,而烦恼的出现正是因为空有满腔的热血与抱负,但是却“无路请缨”(《滕王阁序》),空有一身才华,声名在外,却不得重用,于是听到那空净清幽邈远的“梵音”能够暂时让自己忘记胸中的不快,这是他自我排解内心忧愁的一种方式。王勃在诗歌中展现的佛教“静”与“空”的思想以及他的崇佛、游寺行为,便成为一种自觉地为内心烦闷情绪求得解脱的手段。
在《观佛迹寺》中,王勃通过对寺庙的道路、环境以及佛像等的描写,表达自己体悟到的人生真谛:“莲座神容俨,松崖圣趾余。年长金迹浅,地久石文疏。颓华临曲磴,倾影赴前除。共嗟陵谷远,俄视化城虚。”[11]佛迹寺与三觉寺同在汉州金堂县,此诗应是与《游梵宇三觉寺》同时所作。当跪拜在巍峨庄严的佛祖雕像前,王勃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深深的无力感,他认识到没有什么是能够永垂不朽的,虽说陵谷沧桑,共同嗟叹世事巨变距离自身很遥远,但是时光飞逝,所有的一切都将如化城般归于虚空。所谓“化城”语出自《妙法连华经》,经中记载,释迦佛与弟子云游,一日大山阻路,众弟子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坐地不行,释迦便幻化了一座城池,激励弟子前行[12]。化城,即由幻化而来,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城,而是虚构的。王勃借此表现他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所体悟到的虚空感和幻灭感,是他在政治仕途中突遭横祸后对胸中不平的吐露。在《寺中观卧像》一诗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自应归寂灭,非是倦津梁。”[13]王勃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最终都应归于寂灭。“寂灭”即涅槃,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三世的观念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这一世过得太过凄苦不如意,便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或者是死后的彼岸世界。这种观念体现了佛家理念的精髓,佛家讲求“虚”与“无”,追求“空”与“静”,葛兆光《禅宗思想史》曾引《道德经》卷一《解诸法品第四》:“一切的本源是空,此法如是,犹如虚空。”[14]佛家理念认为这是自我追求理想人生境界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觉”是其终极目标,这是一种生而为人对自我心灵的拷问,是佛教众信徒走出自我困惑、救赎自我心灵的最高级方式。禅宗认为外在的东西都是心起妄念所致,六祖慧能也说,成佛的根本方法便是“无念为宗”,即没有妄念,“无我无欲心则休息,自然清净而得解脱,是名曰‘空’”[15]。
佛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空,一切也都要归于空,那么个体的喜怒哀乐在这种思想面前便显得无足轻重与渺小,这正是王勃仕途受挫后游佛寺、观佛像诗所表达的最主要的佛家理念与自身情感。
2.对修心净欲的参悟
王勃可谓是少年天才,《旧唐书》中记载:“勃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16]但在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唐高宗罢黜之后,王勃远离庙堂而流连山水,这使得他的人生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前后期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王勃十五岁之时曾作《上刘右相书》首,表现自己强烈的入仕愿望,即“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17]。但当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其创作观念由以前侧重儒家“经世致用”转变为侧重抒发自己情怀的表情达意。在《涧底寒松赋》中王勃以松树自喻,表达了自己不被重用的悲愤与自我宽慰的洒脱:“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物而有焉,余何为而悲者?”[18]即使仕途的打击对于王勃来说是致命的,但是在其作品中并不多见单是满腹牢骚的发泄。相反,他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旷达与超然,这与他受到佛教理念的影响关系密切。蜀地佛寺的兴盛与佛教的繁荣使得他主动地选择了讲究修心的禅宗,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解脱,为郁郁不平的心灵找到了一条出路。可以说,在入蜀漫游之后,王勃的诗歌带有更多的哲理意蕴与深厚的内容,表现出一种超然洒脱又带有丝丝感伤情味,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王勃对于佛教教义的醒悟与思考。
王勃在虢州任职期间因性情高傲与同僚难以相处,加之此时他对仕途已无太多渴求之心,于是在描绘自然山川之景的诗歌中难免带上了意欲归隐之趣味。他在《仲春郊外》中描绘了一幅安静优美的春日风景图:“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津。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19]置身于山中小院,安静非常,听到的只有飞鸟掠过与游鱼戏水的声音,雨过天晴,山里的庭院中不会有尘土与喧哗声,王勃用山中庭院比喻自己的内心,庭院无尘,意味自己心内无尘,在这里没有尘世间的喧嚣,有的只是幽静,这就是他所向往的佛学世界,是他一直坚守的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他渴望自己的内心能够不被俗世的“嚣尘”所侵染,能够有一个澄净的空灵心境,而这正是禅宗一直提倡的修心与妙悟。他在《春庄》中也曾说道“岂知人事静,不觉鸟声喧。”[20]正是这种对宁静自然环境的描写,更能体现出王勃渴望远离尘世,对“空”“静”生活状态的向往,这是一种在匆忙的人生中寻找到的片刻安静,表面的从容与洒脱的背后却隐藏着内心的波涛汹涌,曾经专于入仕的万丈豪情,只能压抑在内心深处,满腔的不甘不愿化作对禅佛思想的追寻。只有这样,那被麻痹的思维才能够与自己和解,才能够使自己得到片刻的宁静。
人们之所以招致烦恼是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欲望,而摆脱烦恼便意味着要净化欲望,借助的手段便是修心参悟。在《出境游山》其二中,王勃写道“宫阙云间近,江山物外临”[21]。物外,即超越世间一切事物之外,而达到一个绝对的境界。心游物外,神与理契,这便是佛家一直在讲的修心之法,只有远离俗尘,心游物外,才能到达一个绝对的境界,得到真正的佛家理趣,并且禅宗认为本心即佛,佛即本心,《六祖坛经》中说:“《菩萨戒经》云:戒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22]因此只要修心,便能“悟”,便能达到绝对的佛的境界。
王勃认为自己“本是江上客”,却无奈“牵迹在方内(《忽梦游仙》)”[23],被牵绊在茫茫尘世之中,而“尘间”却多“狭路”,所以只能寄情于他物来摆脱因纠缠于世俗逃脱不开而产生的痛苦心情,而“心外无佛,心即是佛”的禅宗思想,实质便是修心净欲,这为王勃救赎自我心灵指明了方向。佛家理念对于王勃思想影响巨大,在《释迦佛赋》结语中他甚至说:“嗟释迦之永法将尽,仰慈氏之何日调伏,我今回向菩提,一心归命圆寂。”[24]虽然王勃最后没有皈依佛门,但是佛教理念在他的思想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且在诗歌中予以表现。
总的来说,王勃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对于尘世的反感与渴望摆脱尘世羁绊的心情,对于禅佛思想的接受使得其诗歌在表达内心悲愤之余展现出了一丝超然与旷达。
(二)道家思想的展示
老庄思想在王勃诗歌中也带有深刻印记,初唐时期的道家思想承接魏晋时期的玄学而来,而玄学又是将传统的道家思想融入新的内容而成,历来的文人士子对于谈玄论道都非常热衷,尤其是道教中人远离尘世,淡泊高雅,他们的责任与任务便是谈论虚无缥缈的生命与宇宙哲理,这对于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文人们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这些带有老庄色彩的诗歌中,王勃所要展现的是一种寻求成仙,希望摆脱尘世的烦忧,渴望清净的心境。他在作品中进行了自我表白:“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25],表现在诗歌中便是对于得道飞升的向往与对闲适隐逸生活的渴望。
1.对得道成仙的向往
王勃渴望的是纵情山水、忘怀名利的闲云野鹤般的潇洒生活,在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之后,他的思想便由崇尚儒家转变成钦慕老庄,在《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中他明确道出自己思想上的转变:“早师周礼,偶爱儒宗;晚读老庄,动谐真性。”[26]在诗歌中也屡次表达对于神仙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在《忽梦游仙》这首诗中他畅想了自己遨游天际的情景:
仆本江上客,牵迹在方内。寤寐霄汉间,居然有灵对。
翕尔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龙光,烟途俨鸾态。
乘月披金帔,连星解琼珮。浮识俄易归,真游邈难再。
寥廓沉遐想,周遑奉遗诲。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
在此诗中,王勃描绘了一个自己期望已久的梦境:“翕尔登霞首,依然蹑云背。电策驱龙光,烟途俨鸾态。”王勃笔下梦中的自己腾云驾雾,好似已经飘然成仙。这种情态还反映在《怀仙》诗中:“常希披尘网,眇然登云车。鸾情极霄汉,凤想疲烟霞。”[27]这是他内心的一种向往,一种极度希望脱离尘世喧嚣的急迫心情。在见识到仙界生活的美好之后,他再一次慨叹“流俗非我乡,何当释尘昧”,渴望摆脱尘世羁绊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他又清晰地认识到这终究只是一个虽美好但永不会实现的愿望:“苍虬不可得,空望白云衢”(《寻道观》)[28],于是也只能“无为坐惆怅,虚此江上华”(《怀仙》)[29]。满心的欢喜过后,留下的是清醒的痛楚与无奈,徒有钦羡之情但愿望却不得实现,与梦境中逍遥洒脱的自己相比,现实中苦闷难过的自己内心所感受到的只能是深深的落寞与无力。
王勃诗歌中留有怀仙、游仙之作的原因,大抵以诗人自己所论为其要旨,即“仆本江上客,牵迹在方内”,他认为自己生来就应该是无拘无束、潇洒自由的,但是现在的自己却困于尘世中难以脱身,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于求仙得道的渴望和向往,而借助的手段便是寄情于山水之中。历来文人士子游山访仙,均少不了饮酒作诗,他们认为这是文人风采的展现,是风雅的外化特征,王勃亦不例外,他在《赠李十四四首》其二中便说:“小径偏宜草,空庭不厌花。平生诗与酒,自得会仙家。”[30]在平日生活中饮酒作诗,那么自然而然能够与仙人相会,即不被凡尘俗世所牵绊,纵情山水之中,将自己融于自然万物,在想象的仙界中遨游。这种思维方式展现在诗歌中便使诗歌带有洒脱不羁与淡然旷达的意味。
即使在“寤寐”间都憧憬自己遨游仙界,这种迫切向往得道成仙的心情从侧面说明王勃对现实生活并不满意。试想,如若现实中的自己所求所愿皆可实现,谁还会去奢求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呢?无论是“怀仙”或是“访仙”“游仙”,大抵不过是自己为历尽磨难后苦闷不堪的心灵寻求一个解脱的方式罢了,正好道家提倡的一种超越凡尘的生活情趣与超越时空的生存状态,与王勃遭受磨难后在现实世界中感到压抑与窒息,急需寻求一个精神寄托相契合。因此,道教中讲求享乐,肯定人的欲望的哲理学说,便被王勃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并且对于道家传说中的神仙,王勃也多有向往,希望自己也能够得道成仙,过上潇洒自在的生活。
王勃在入蜀以后,经常游历名山拜访道观,与道士交往酬唱,过游甚密,现存《山居晚眺赠王道士》《秋月仙游观赠道士》等诗歌可以为证。于道观借宿,与道士相谈,都使得王勃在无意识间接受了道家对于得道成仙、寻求长生的思想,并将其在诗歌中予以展现。
2.对隐逸生活的高歌
《庄子逍遥游》中有言:“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31]老庄哲学要求人们修心,追求无心无欲的至高境界,这种境界的外在表现便是超越荣辱,真正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讲求虚无寡欲。道家风骨,在外显为逍遥,于内化为心斋。其形可如槁木,其心亦可如死灰,然其风情却如神人之绰约,其骨又似浑沌之淡漠。逍遥是无牵无挂的精神,心斋是无羁无绊的态度。道家风骨建于二者之上,其形无所定而定无所形[32]。即使心如死灰痛苦不堪,但是表现在外的仍是逍遥洒脱,与其嗟叹命运不公,不如寄情山水,诗酒自乐,这种道家思想在王勃笔下便表现为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在任职虢州参军之时,他写下了《仲春郊外》《郊兴》《郊园即事》《春日还郊》四首赞美春日郊外风景的田园风格的诗,表达自己对于山野田园的喜爱之情,展现隐藏在优美闲适风景之中的那颗想要入山归田、渴望弃官归隐的心。在多首诗歌中,王勃都称自己为不愿为官、意欲归隐的“山人”,在《郊兴》中先写自己闲适的生活:独自饮酒放歌,赋诗作文,后以“山人不惜醉,唯畏绿尊虚”[33]收束全诗,再如“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琴尊唯待处,风月自相寻(《赠李十四四首》其一)”[34]。诗人寄情山水,将仲春的山区田野风光描绘得优美宁静,揭示出对于田园山野的喜爱与向往之情。在此之前,王勃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远离故乡的“宦游人”,但在这里,他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与定位却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对自我称谓的改变,也正标志着他思想情感的变化,聂文郁先生对其的解释是“自诗人被赶出沛王府后,悲苦、愤激而不满现实的思想情绪就在作者身上滋长发展起来”,并且在虢州任职期间“与同僚合不来,受到排斥厌恶,使这种思想情绪发展得更为严重,简直有时无法安置,只能以诗酒自遣、以山水自娱而自命为山人了[35]。若说在此,王勃弃官的愿望还不是很强烈,那么在《郊园即事》中,他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想要归隐的心情:“闲居饶酒赋,随兴欲抽簪。”[36]所谓“抽簪”,意即弃官,古代的士大夫为官,都必须束发整冠,用簪子将冠连到头发上,故抽簪散发,即弃官隐退。在这里,王勃的思想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人”思想,弃官隐居,诗酒自娱,究其根本,此种心态出现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仕不得意,是在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时的一种无奈选择。
在王勃看来,陶渊明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榜样,无论是他辞官隐居的行为,还是以诗酒自娱的精神,都是王勃为自己找到的一个精神层面的标榜。他在诗歌中屡次表达对于陶渊明的尊崇以及对其隐居生活的向往,如在《九日》中描绘了陶渊明在九月九日重阳节这一天,打开门便看到了菊花,正当他坐在菊花丛中找不到酒喝而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个来送酒的人问他哪一个是陶潜的家。再如《三月曲水宴得烟字》开头写道:“彭泽官初去,河阳赋始传。田园归旧国,诗酒间长筵。”[37]王勃对陶渊明的描写与塑造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他藐视官场、不进仕途而归隐田园的敬佩与向往之情。这种憧憬心理的显露正是王勃对世俗世界的无奈与厌恶,是现实的磨难逼迫内心去逃避苦难的一种自觉选择与追求。之所以选择陶渊明,是他在遍观了古往今来文人士子的整体状况后作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因为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对仕途不畅的王勃有着莫大的吸引,更是因为陶渊明思想“为周孔之儒术,为庄老之道家,抑或更兼有释迦之佛法”[38]。陶渊明率真自得的性情与返璞归真的诗文创作都是对道家听任自然、朴素不伪的贵真思想的接受与实践,《形影神》不仅是其创作思想与人生境界的追求,更是佛道思想的影响在诗歌中的反映。因此,对陶渊明的推崇,是王勃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寻找到的一个精神寄托,是其矛盾思想的外化,也是他能够寻找到的唯一的精神世界映照现实后的世人楷模。
总之,道教思维对王勃的影响可谓是巨大而深刻的,他在《述怀拟古诗》中深刻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仆生二十祀,有志十数年。下策图富贵,上策怀神仙。”[39]在经历一系列的不如意之后,王勃的入仕之心已经消歇,他认为荣华富贵非本愿,求仙问道当神仙才是最终目标,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实现的愿望,便退而求其次追求闲适隐居的生活。
王勃对于佛、道两教理念的选择与信奉,背后隐藏的是对于入仕的渴望,只不过在种种条件的限制下,这种愿望并不能够得到实现,便将其深埋于内心,用表面的旷达洒脱掩盖内心深处的郁躁不平,为备受煎熬的内心寻求一个暂时的宁静与解脱。
三 王勃诗歌中体现佛道思想的原因
王勃的一生是短暂的,《旧唐书》:“(勃)渡南海,坠水而卒,时年二十八。”[40]但是在他如昙花般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发生过巨大的转变,这转变也正是他的诗歌中佛、道色彩存在的最主要原因,加之家学渊源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并且在入蜀时期与南下探父路途中游览了大量佛寺、道观并与道士僧人交游,《六榕寺志》中载王勃前往交趾途经广州时,曾前往六榕寺礼佛,并且受到寺僧的热情接待,“寺僧素仰王勃大名,迎入方丈室,于时述说本寺史略及此次修葺因缘,并恳请撰写重修碑记,王勃慨然应允”[41],佛、道两教要旨不可避免地在王勃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自身经历与家学传统
王勃早年怀有积极强烈的入仕愿望,并且才思敏捷、博学多识,《旧唐书》:“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42]十五岁作《上刘右相书》指陈天下大事,十七岁拜为朝散郎,同年被沛王召为修撰,直至此期,王勃的思想都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要求个体服从封建帝王,将个体的行为与思想都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框架之中,以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早在隋朝时,王勃的祖父王通便极为推崇儒家学说,他将自己定位为圣人的后继者,退居龙门,一生都致力于研读和讲授儒家道义。仕途的顺畅与家学传统的影响,王勃早年的作品中洋溢着对生活的热情与磅礴的自信,坚信自己有所作为的他以凤凰自喻,借凤凰择木而栖自比良臣择主而佐,“凤兮凤兮,来何所图?出应明主,言栖高梧(《寒梧栖凤赋》)”[43],表达了自己想要积极入仕辅佐明君的愿望。但是在经历被逐入蜀、虢州任职、匿杀曹达等一系列事情之后,王勃的内心充斥着痛苦与无奈,强调个体社会价值的儒家思想已无法使其纾解心中的苦闷情绪,于是他便求禅问道、寄情山水,以佛老思想暂缓心中郁气。
王勃思想中道家色彩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便是他曾追随曹元学习《易》经,《新唐书》本传:“时长安曹元有秘术,勃从之游,尽得其要。尝读《易》,夜梦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极,子勉思之,’寤而作《易发挥》数篇。”[44]《周易》中的五行八卦、阴阳两极与回归自然等理念在王勃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且在诗文中予以表现。虽然佛家的修心求静与道家的旷达洒脱能够使王勃沉闷郁愤的心灵暂时找到精神寄托,但是士大夫传统观念中的家国情怀、入仕思想仍是他不能够得到彻底解脱的禁锢与枷锁,“名高位卑”的社会地位使他在入仕与归隐中苦苦挣扎,仕途的艰辛与自我理想相违背后产生的痛苦是他矛盾思想的根源,求取功名之心陨灭之后,也只能借助寄情他物予以慰藉。但即使寄情山水,在最初的欢喜之后,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悲慨与无奈仍会浮上心头“谁意山游好,屡伤人事侵(《出境游山》)”[45]。在《铜雀妓》中王勃借宫妓以自比,对宫妓凄惨生活的描写实际是对自己人生处境的反映与自怜:“妾本深宫妓,层城闭九重。君王欢爱尽,歌舞为谁容。锦衾不复襞,罗衣谁再缝。高台西北望,流涕向青松。”[46]独站高台,涕泗横流,却也无法改变现状,“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47],及至此时,王勃入仕之心已歇,只能无奈地转求内心的解脱,用寻佛、觅道的行为来减轻自己内心的苦难与愤懑,以达到自我的救赎。
(二)社会背景与初唐宗教政策
佛、道两教虽一为外来宗教,一为本土宗教,但二者都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及至隋唐可谓是到了鼎盛期。隋朝时,统治者便佛、道并重,“隋文帝振兴佛、道,隋炀帝从晋王时便经常参与法会,并且也常巡视道场,和尚、道士皆受到隋炀帝的礼遇”[48]。李唐王朝的建立,佛教徒与道教士都提供了资金与舆论上的支持,唐初统治者为稳定政权,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宗教,于是道教与佛教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经历了隋末战乱频发的社会,唐王朝的建立开创了一个相对开明稳定的社会氛围,这使得人们的文化心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四方来供、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初唐文人自信狂放的人格便被唤醒了,他们享受着这种肆意的生活,但在享受之余又不免带有一丝对盛景难长的忧虑与人生短暂的慨叹,这便使其思想上升到哲学层面,考虑的是人生宇宙等最基本的问题。恰逢其时,禅佛、老庄思想要义与此时的社会与文人的文化心理相契合,对于初唐文人来说便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生活在佛、道两教迅速发展的上升期的初唐文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在作品中加以体现。
初唐时期正值蜀地禅佛思想兴盛,入蜀漫游的王勃便于四川与佛教结缘,除了王勃,“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与杨炯等都曾到过四川,亦写下了带有禅佛思想的诗歌,如卢照邻《石镜寺》:“铢衣千古佛,宝月两重圆。隐隐香台夜,钟声彻九天。”[49]卢照邻更多地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新唐书》:“(照邻)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食之。”[50]为了治病,他不惜服食丹药,并且与道士交往密切。在《赤谷安禅师塔》中他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于佛、道思想的推崇:“高谈十二部,细核五千文。如如数冥味,生生理氛氲。”[51]所谓“十二部”“五千文”便是佛、道两教的代称,前者因佛教典籍共有十二部而得名,后者因为老子所作《道德经》约有五千字而著称。再如被誉为开唐代风气之先的陈子昂,其思想亦多受佛道的影响,甚至最后在其父归隐生活的影响与仕途受挫的情况下,选择了道家提倡的回归山野的隐逸生活,其作品亦带有鲜明的禅佛老庄思想。如《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钟梵经行罢,香床坐入禅。岩庭交杂树,石濑泻鸣泉。水月心方寂,云霞思独玄。宁知人世里,疲病苦攀缘。”[52]而在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中,陈子昂展现了自己渴望成仙的愿望:“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永随众仙逝,三山游玉京。”[53]也许,正是佛、道两教要义中存在着玄妙的宇宙生命哲理与思辨,能够让这些身心饱受折磨的文人们得到暂时的安宁与心灵的寄托。因此,佛、道两教在整个唐代都得到了大发展,并且一直影响着文人的人生观与创作观,如唐代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早年亦有用世之志,曾作《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以干谒。但在仕途困顿、痛苦失望之后,其思想便发生了变化,开始在寻佛觅道中寻求自我悒郁不得志的解脱,“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54],表现了对于佛教的向往。在《宿天台桐柏观》中他写道“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二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55]。明确表明自己远游在外,就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可以说,佛道思想对于初唐乃至整个唐代文人士子们的影响是深刻且具有广泛性的。因此王勃生活在此种社会思潮下,创作观念难免受到佛道思想的侵浸,并将其在诗文中予以反映。
总之,对王勃诗歌中所展现的佛、道思想进行分析,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王勃的平生遭际与思想变化。但同时也要看到,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内心仍存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建功立业的愿望,入仕思想是根深蒂固且无法彻底清除的。因此,即使王勃寄情山水之中、放浪形骸之外,但仍无法真正归于佛、道,只是借二者来获得心理上短暂的休憩与瞬时的宁静。王勃将深奥玄妙的禅佛、老庄哲学融入自己的身世经历中,使得其诗歌在悲怆之中蕴有超越时空的旷达与洒脱,历经千载,仍具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