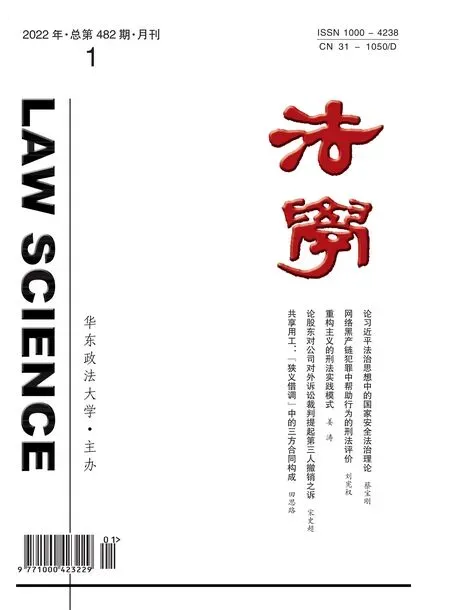重构主义的刑法实践模式
●姜 涛
重构主义是随着刑罚社会学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刑罚适用方式与哲学。在刑罚适用中,依据重构主义所主张的法益恢复,〔1〕我国亦有学者研究法益可恢复性犯罪,参见庄绪龙:《“法益可恢复性犯罪”概念之提倡》,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第969-999页。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关押,从根本上减少刑罚的“活的副作用”,并合理揭示刑法与行政法、民法关系上我们未注意到的理性方案。“迷途知返条款”是指行为人在犯罪后以自己的努力积极实现法益恢复,可以作为免罪事由(定罪上的迷途知返条款),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者损失或退赃的,可以作为从宽处罚事由(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立法发展是刑法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同时又反哺立法实践。立法已经走在刑法理论发展的前列,这集中体现为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发展中的一些新趋势、新特点:(1)刑法对部分犯罪设置入罪认定的行政前置性要件,如逃税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等,〔2〕国外也有类似规定,但也有不同,如《法国刑法典》第132-59条规定:“如表明罪犯已获重返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已予赔偿,由犯罪造成的危害已告停止,可予免除刑罚。”(2)司法解释对部分犯罪以法益被修复为由出罪,如受贿罪司法解释上的“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3)刑法部分条款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如《刑法》 第164条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法》第272条增加“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条款。(4)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了刑事和解、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3〕2018年10月26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面对刑事立法的新态势,本文从新的视角,强调需超越报应主义、预防主义和综合主义,提出与发展重构主义刑罚目的论,并以重构主义理论为指导,完善刑法中的“迷途知返条款”,以期促进刑罚目的多元论的建构,确保刑法立法的科学化发展。
一、传统刑法目的论不能解释我国刑事立法新发展
刑法是对犯罪的报应,还是对未来犯罪的预防?抑或是对被害损失的补偿?这是刑罚目的论的核心问题。这一看似已经解决的理论争议,仍需要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发展的创新予以再定位。
(一)我国晚近刑事立法的两大创新发展
1.刑法立法在个罪中设置消极的构成要件
就个罪构成要件设置而言,有无附加行为人的“迷途知返条款”,关系到犯罪圈的大小——附加条件越多,意味着犯罪圈越小,刑法就越谦抑。1997年《刑法》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有“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限制条件;《刑法》第196条“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有“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限制条件;《刑法》第296条“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有“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的限制条件。上述犯罪均涉及行为人与国家或组织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模型,如在实施某种行为之前或之后予以合作,则不构成该罪。
从属性上看,上述法律条文的规范属于关系性规范,即把行为人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主动权交由行为者本人,如果行为人采取合作,则不成立犯罪,否则属于犯罪。关系性规范是设计出符合一般条件的基本规范,然后由法规范主体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自主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分割问题。〔4〕参见姜涛:《劳动刑法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以正当防卫的规定为例,刑法即为不法侵害者与防卫者开辟了一个“较量”的关系网络,防卫者的防卫行为也被区分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事前或事后防卫等不同类型,且不同类型行为的法律后果不同。可以说,防卫者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他如何处理与不法侵害者之间的关系,法律把这种“命运”决定权交由防卫者,而不是刑法明文规定。
刑法修正案在关系性规范上有进一步创新。《刑法修正案(七)》有关“逃税罪”的修正,《刑法修正案(八)》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之构成要件设置,同样有入罪限制。其中,《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01条增加:“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它改变了逃税罪的构成要件,即强调积极要件(偷逃税款)与消极要件(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并存。《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罪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有“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消极要件,《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有“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消极要件。立法者尽管对两罪没有规定“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后支付,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从逻辑上已包含上述内容,故与逃税罪的构成要件限制并无区别,仅为立法表述差异。
上述立法创新体现在对刑法中“迷途知返条款”的先试先行,这值得刑法理论认真对待,如果说1997年《刑法》有关“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等个罪构成要件限制条款,即给行为人一个按照行政机关或银行的要求改正或纠错的机会,以恢复被破坏的法益,或避免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如果说这种犯罪认定的行政前置性要件还属于非典型的关系性规范的话,那么《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定,则是典型的关系性规范,它是把行为人犯罪后自行恢复法益侵害的努力及其状态,直接作为免罪处理的理由。
2.刑事诉讼法上的系列制度创新
对不法行为如何作出合理反应,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犯罪冲突在社会层面是犯罪人和被害者的利益冲突。对此,刑事诉讼法理论早期主张辩诉交易,后期主张刑事和解,当前重视认罪认罚从宽处罚。无论是辩诉交易、刑事和解,抑或认罪认罚从宽处罚,都是立足于被告人与国家、被害者之间的关系及被侵害法益的恢复所进行的理论建构,也都强调被告人自身的法益恢复努力争取从宽处罚的机会。
认罪协商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或其律师)通过某种形式的磋商,达成一致协议,不经审判程序而解决被告人之刑事追究的特别程序。认罪协商制度源于美国司法实务,历经百余年的发展,终获联邦最高法院肯认其合宪性,进而形诸于法律之明文规定中。认罪协商(Plea bargaining)与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Plea discussions”及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规定的“Plea Negotiation”的含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案件不经由审判程序而获致解决,可以提高司法效率,避免司法资源的虚耗,以便于将资源留给有重大争议的案件。
刑事和解是对辩诉交易的另类表达,也是一个来自德日成文法系的概念,〔5〕See Dieter Rössner, Mediation as a Basic Element of Crime Contro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mments, Buあ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3, No. 1(April 1999), p. 211-233.它以被害者的法益恢复为中心,因为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有效和解,尽可能地避免刑罚处罚。《刑事诉讼法》第288-290条,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审查与制作及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就刑事和解而言,其核心要义是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者谅解,从而正确从宽处罚。其中,积极赔偿被害者损失,就是一种犯罪后的法益恢复努力。重视犯罪后犯罪人对被害者的法益侵害的恢复,意味着刑法从“单纯处罚犯罪”到“弥补被害损失”的转变。
与刑事和解、认罪协商不同,认罪认罚从宽意味着犯罪嫌疑人与国家的合作模式,即主动投案、主动交代罪行、自愿接受刑罚处罚。认罪认罚从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犯罪后合作模式,其依据是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该司法解释第18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但没有退赃退赔、赔偿损失,未能与被害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从宽时应当予以酌减。”可见,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并行不悖,赔偿损失是认罪认罚从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赔偿损失意味着以被告人的努力弥补犯罪带来的法益侵害,在经济犯罪中,这是刑法所保护法益被恢复的直接体现。
上述刑事诉讼法的创新,首先具有诉讼制度变革意义,即从契约主义出发,赋予诉讼当事人某种程度的程序处分权,允许其在司法侦审程序中经由某种方式各自获得程序目的之全部或部分实现,追求最大制度绩效,进而营造出审、检、辩三方皆赢的局面,包括寄望通过消除定罪的障碍、摆脱或减轻刑事司法负荷过重的现实困境、积极应对诉讼社会“案多人少”的矛盾等。此外,上述创新与刑法立法创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强调犯罪后行为人积极的法益恢复,强化其对犯罪认定与量刑的影响,并且都是以刑罚处罚为后盾的法益修复,旨在重构为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或社会合作等。
(二)传统刑罚目的论解释上述立法创新的不足
“目的性的考虑是创造法的力量。”〔6〕[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宋英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8页。刑罚目的涉及国家刑罚权的界限及其合法性问题,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方向标,也是刑事政策的出发点。自中世纪至今,刑罚目的有因犯罪而处罚的报应主义、为不使其再犯而处罚的预防主义、兼顾报应与预防的综合主义等论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解释,一度成为刑罚目的论的终极问题。
报应主义强调对犯罪者施加(正当的)惩罚与他们犯下的(不合理的)错误相称,做到“罪有应得”,以抵御惩罚被当作“锋利的斧头”。报应主义与重刑主义具有天然联系,往往表达的是政治威权或道德义愤,会导致不符合目的性的刑法或强制措施。报应主义并不是不重视预防,而是强调基于威慑的预防理念,即理性、自我本位的个体通过计算利益得失而放弃犯罪动机,强调最有效的犯罪预防,包括施加足够的惩罚而不使犯罪成为吸引人的选择。正义理论(或正义模式)是报应主义的现代新生,它强调刑罚是正义的伸张,即以罪刑均衡方式实践均衡的正义,强调所有犯罪均应受到惩罚,而不是为防止再犯而去改变受刑人的人格,刑罚就是对犯罪的惩罚。当然,正义模式强调犯罪者应该受到适当的、相称的惩罚,这从限制刑罚适用角度具有意义,因为适度的惩罚本质上是好的。但是,它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刑罚目的是对罪犯造成伤害或痛苦,以免其再犯,或威慑潜在犯罪人实施犯罪。
预防主义从批判报应主义入手,强调报应本身不是刑罚适用的根据。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的恶害极其严重,即使对其进行报应也于事无补,无法弥补犯罪造成的恶害或恢复至犯罪前的状态,因此刑罚适用重在预防犯罪,即罗克辛所言的“刑罚的这个目的指向是防止性的(等于预防性的),针对的是个别的(特殊的)行为人”〔7〕[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预防主义深受功利主义影响,希望借助刑罚手段从而不仅能够预防一般大众犯罪,而且能够对行为人进行个别化预防,使刑罚成为达成预防目的的手段,因而在类别上有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之分。预防主义的贡献是,刑罚种类及其轻重程度取决于犯罪预防的目的,而不是犯罪造成的恶害,这有利于实现刑罚个别化。例如,李斯特提出个别预防理论(特别预防),强调受刑人的再社会化及其效果,犯罪人能否在特定时间与空间深刻反省,是检验刑罚的有用性的重要标准。
综合主义立足于报应主义、预防主义过于片面的缺陷,强调刑罚的双面性,即刑罚目的兼顾报应与预防,强调报应与预防是刑罚目的中系互为补充的一体两面,强调刑罚处罚的双重效果的原则,即在对犯罪之恶害进行报应的同时,尚有教育改造犯罪人以促进其再社会化之目的考虑。因此,报应主义中刑罚的适当性、确定性与经济性至今仍被保留,而预防主义的刑罚个别化、再社会化,也已经进入刑法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与此同时,报应主义下的重刑模式与预防主义下的医疗模式逐渐被淘汰。在大陆法系,综合主义大体上是旧派与新派握手言和的结果,而英美学者主张的报应主义因素与结果主义因素的综合性刑罚,〔8〕参见[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法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04页。与此并无本质区别。总体而言,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并非只强调贯彻绝对报应主义,亦非只强调实现教育改善效果,而是突出调和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正义与犯罪人社会复归等二律背反,朝着综合主义方向发展。我国刑法学通说也采取综合主义,强调预防犯罪是刑罚目的,预防包括一般预防(报应)与特殊预防(预防)。即使反对通说的学者,也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9〕张明楷:《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2期,第5页。。
当代不会再有学者主张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刑罚目的论固然存在争议,也只是综合主义内部的分歧。那么,综合主义是最终完美的理论吗?不难看出,综合主义仍是从国家、行为人或行为之间的思考,不仅会制造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对抗,而且没有把被害者纳入刑罚目的论的思考范围,更不会强调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合作,故导致对刑罚效果的高级迷信,也无法解释前述我国刑事立法的新发展。
第一,对行政犯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惩罚不是一种工具性的机制或至少不是主要原因,对犯罪的威慑或预防而言,刑罚惩罚类似于急诊室,不仅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往往是导致公众的“激情反应”,而且所付出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更主要是一种仪式化的表达。〔10〕See David Garl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 Crime and Justice, Vol. 14(1991), p. 123.正因如此,刑罚乐观主义在当代被刑罚怀疑主义取代,刑罚理论对现代刑罚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深刻的反思,比如福柯关于“惩罚的失灵”的论述、史东理(Lawrence Stone)提出的“退化的制度”等,〔11〕参见[美]大卫·葛兰:《惩罚与现代社会》,刘宗为、黄煜文译,商周出版2006年版,第8-9页。两者都强调刑罚仅专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的情绪和练习,比如怨恨、愤怒、责备和惩罚,是目光短浅的。〔12〕See Victor Tadros, The Scope and the Grounds of Responsibility,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1, No. 1(Winter 2008), p. 93.事实的确如此,对于新型经济犯而言,单纯的报应或预防是没有意义的,恢复被犯罪所打破的利益格局或平衡,需要以刑罚的威胁为后盾,激励行为人以自己的努力积极实现法益恢复。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固然犯罪人的行为值得刑罚处罚,且其犯罪所得数额也远高于通常的盗窃、诈骗等,但仅对其处罚并不能弥补被害者的物质损失,而被害者关注的往往不是行为人的处罚,而是参与集资的资金能否收回,这正是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被害者选择报警,而到法院阶段被害者又聚集在一起要求释放行为人的原因,因为行为人被定罪处罚后,被害者的资金更没有保障。也因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增加“在提起公诉前积极退赃,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条款。
第二,导致惩罚实践上的严重迷失。刑法哲学虽使人聪慧,但也受困于自我空洞之中。以往刑罚目的论更主要是一种刑法哲学视域的思考,对社会、司法的复杂性关注不够,其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性明显,如果对这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有效性检验,它总是漏洞百出:在理论上,综合主义属于抽象的理论,如报应、预防、二元等,这些理论在表述上是绝对的,它在哲学的伪装下,总是存在一种反现实主义现象,既不回避道德理论化,也存在“以虚拟正义对抗真实有效”这种并无多大意义的论述陷阱。或者说,传统刑罚目的理论强调不容置疑的真理,只有教条,没有方法,即没有明确的哲学参数阻止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多方位的滑脱,依此所建构的罪刑体系总会在复杂的世界里功能失调,因为它只强调对犯罪人的惩罚或预防,不重视对被害者利益损失的恢复,或者在报应、预防的天平两端严重失衡。在实践中,该理论与形式主义的抽象概念相一致,在运作中机械地产生司法上的答案,以至于为了惩罚犯罪而牺牲人权保障等现象频发,而与之相反社会越轨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矫正。
第三,背离“刑法是法益保护法”的性质。刑法是法益保护法,刑法保护法益不仅意味着行为人具有法益侵害或危险而惩罚行为人,而且也体现为在特定情况下激励行为人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法益。随着被害者学的兴起,被害正义不仅是报应正义,也包含矫正正义,在某些犯罪中,被害者的同意,也是阻却犯罪事由。毕竟,犯罪是对被害者利益的损害,被害者利益的恢复,当属于犯罪发生后最为着重之事,而不是借由国家对犯罪人施以处罚。报应是工具化的,预防是形式目的化的,而不是实质目的化,它们都是从“犯罪人与国家”的二元视角,而不是从“犯罪人—被害者—国家”的三元视角进行的理论建构,故会面临失却其法益保护的基础,从而沦为披着刑法外衣的控制工具。报应主义、预防主义均存在以偏概全问题,综合主义虽纠正了这一缺陷,但却在某些犯罪中存在主次颠倒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忽视法益保护原则。从法益保护原则出发,社会合作与和平的关键是避免法益侵害或恢复被侵害后的法益(刑罚目的的“主体结构”),其他的报应或预防等,则大多数属于附带现象(刑法目的的“附属结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最好的政策可能是,若行为人已经以自己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保护法益,则不必再受到惩罚。这种对法益恢复的关注与坚持,与刑罚社会学的论证联结,是对传统刑法目的理论忽视“刑法是法益保护法”的积极回应。
法律人必须走出刑法哲学的象牙塔,认真思考刑罚的有效性问题,才能发现刑罚的精神所在。当刑法哲学上报应或预防的梦想被刑罚社会学的结构所打破,一并带来了对刑罚目的的再认识。面对刑事立法的创新发展,我们需要接受更为务实的刑罚目的理论,从而在一个复杂社会网络中解决刑法的功能失调问题,重构主义就是这一思考的产物。
二、重构主义作为刑法目的论发展的新形态
刑法的核心功能是什么,这并没有固定答案,任何刑罚理论都会随着时空因素的概念而有所修正,刑罚目的理论也不例外。布兰迪斯大法官指出,“一个法律人如果没有研究过经济学和社会学,那么他就极容易成为社会的公敌。”〔13〕[美]大卫·葛兰:《惩罚与现代社会》,刘宗为、黄煜文译,商周出版2006年版,第Ⅳ页。重构主义就是从刑罚社会学观察的产物,也是刑罚目的论的重大突破。
(一)重构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在说刑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时,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理论而无须改造的,问题的焦点在于,对其进行合理改造的方向是什么?对此,大卫·葛兰指出,“对犯罪者施以惩罚(punishment)是社会生活中一个特别令人困惑与不安的面向。在社会政策方面,惩罚似乎总是无法达成它所夸言的目标而让人失望,同时危机与矛盾也不断削弱它的效果;在道德或政治议题上,惩罚也引发过度的激情、严重的利益冲突以及棘手的争论……惩罚之所以如此令人困惑与失望,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想将深层的社会议题转化为专门制度下的技术性工作。”〔14〕同上注,第2页。在葛兰看来,忽视惩罚的社会意义,导致惩罚工程根基不牢,而重构主义正是这一反思的产物,它是一种不同于报应主义、预防主义、综合主义的刑罚理论。
作为目前英美刑法的新理论,重构主义(Reconstructivism)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刑法作为特殊的法律,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结构,而刑罚处罚的任务在于恢复或缝合被破坏的社会结构,〔15〕See Kleinfeld, Joshua, Reconstructivism: The Place of Criminal Law in Ethical Lif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29, No. 6 (April 2016), p. 1485.强调重新建立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刑法在重新缝合社会结构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在维持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中能起到巨大作用,〔16〕See Chiao, Vincent,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Kleinfeld’s Reconstructivism: The Place of Criminal Law in Ethical Life,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129, 2015-2016, p. 259.刑法由此可能被贴上非惩罚性、非犯罪性的标签。〔17〕See Murray, Brian M, Retributivist Reform of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Connecticut Law Review, Vol. 52, No. 2(July 2020),p.873.重构主义对罪与罚的功能阐释依赖于至少两个前提:一是刑法对维持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二是刑法的核心功能仅在于维持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促进一些其他价值,因为刑法并不是一种促进任何特定价值的手段,相反却构成了对这种价值的尊重。〔18〕See Chiao, Vincent,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Kleinfeld’ s Reconstructivism: The Place of Criminal Law in Ethical Life,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129, 2015-2016, p. 260-261.我国学者指出,市场经济刑罚观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刑罚的社会效果,即刑事法律活动要达到的社会功能,只有坚持公正性与功利性,才能实现刑罚的最佳社会效果,如果从以刑制罪的立场出发,这需要正确对待犯罪的认定标准,包括生产力标准等。〔19〕参见赵秉志主编:《高铭暄刑法思想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7页。这其实就是一种重构主义的立场。德日刑法学主张的规范违反说,认为规范的有效性就是刑法法益,犯罪是破坏规范效力的行为,刑法所关心的是对受到有责行为威胁的规范有效性的维护,〔20〕参见[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宋英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即重建规范的效力,也是重构主义的另类表达。
重构主义是刑罚社会学的主张,强调刑法的目的与功能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社会学观点认为,惩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由社会和历史力量的综合作用形成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违法者本身。〔21〕See David Garl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 Crime and Justice, Vol. 14(1991), p. 115.法社会学侧重法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强调社会决定法律的特征和社会变迁引起法律的变化,而且重视法律规定的社会结构与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结构,从而追求社会生活中的“活法”。法社会学所建构的法律秩序,包括行为规范(判断标准)、强制力(惩罚)、正当性(惩罚的理由)与互动关系(关系性建构或法益恢复)。涂尔干、马克思、福柯等对此均有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与合作论,是重构主义理论的渊源,涂尔干认为国家有两种职能,对外表现为武力、扩张,对内表现为和平,它组织人民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承担着维护社会正义的职责,保护人民的权利,〔22〕参见渠敬东主编:《涂尔干:社会与国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导言第11页。而惩罚是维持社会“机械”团结的特权手段,〔23〕See Bronsther, Jacob, Two Theories of Deterrent Punishment,Tulsa Law Review, Vol. 53, No. 3(Spring 2018), p. 472.旨在实现社会连带。马克思主张的刑罚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惩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对犯罪的技术反应,而是一种社会阶层之间的斗争,是一种阶段问题。福柯强调刑罚的工具性与效用性,所谓工具性是指刑罚是加诸民众的权力与管制体系,〔24〕参见[美]大卫·葛兰:《惩罚与现代社会》,刘宗为、黄煜文译,商周出版2006年版,第213页。强调刑法对人的支配关系,从而使人成为刑法建构的“人”,此乃福柯在反讽意义上所言的效用性。福柯有关“监狱失灵”的重要论述,既是从刑罚社会学角度的观察,亦构成对刑罚目的之反思的强大思想动力。大卫·葛兰认为,“表面上看来,惩罚只是一种处置犯罪者的手段,好让其他人的生活不被罪犯骚扰,但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制度,有助于界定社会的本质、各种构成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中可行且可欲的生活方式。”〔25〕同上注,第463-464页。涂尔干、马克思、福柯、大卫·葛兰等人的理论强调惩罚与社会角色、效果之间的意义关联,改变了以往时代对刑法的认识,并提出了刑罚与制度实践的多重决定。
什么是刑法的核心本质?报应主义、预防主义或综合主义均把刑法视为纯粹的回顾性的、谴责的“机构”,指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工具主义学说只是提供了某种“目的—手段”型推理,一旦某种目的已经产生,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以任何方式利用刑法达成既定目的,〔26〕参见[美]布赖恩·Z·塔玛纳哈:《法律工具主义——对法治的危害》,陈虎、杨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8页。如为反恐而实施酷刑。其实,刑法更应指向未来,犯罪发生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无法挽回的结局,从未来角度看,如果行为人能够尽最大努力弥补犯罪给社会或他人带来的损失,这更加有利于国家、社会与民众,也更加需要激励行为人这么做,这恰恰是重构主义的逻辑起点。重构主义固然提供了一个规范的、有吸引力的评估刑罚目的的框架,但是,提出重构主义的英美学者把伦理生活秩序或社会生活方式作为目的,却是一种看不见也不易判断的目标,这种意义上的重构主义并不能提供给我们足够的理由,对任何人进行刑事处罚或不处罚,这限制了重构主义的功能发挥。笔者认为,重构主义需结合“刑法是法益保护法”的属性来思考才有生命力,刑法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确立了社会利益的分配法则,也保护利益被侵害后的恢复。具体而言,刑法通过奖励行为人自愿合作、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法益并严惩那些拒绝合作的行为,以改变刑法单一惩罚的刻板印象。这有助于促进民众的理性选择,毕竟,公众期待的惩罚不仅是保护他们不受犯罪之害,而且也要表达他们对法益恢复的需求。相比之下,传统的选择意义上的犯罪预防表达出一个更模糊的信号,而法益恢复则接近更真实的、有效的诉求,这种诉求与刑罚的社会意义吻合,有助于塑造合作、和平的社会。
在刑罚社会学看来,刑法是社会基本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社群主义有关,刑法作为维持合作的公民社会和公民保障自我的自由所依赖的制度,惩罚不是因为粗俗的道德或功利的原因,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基于此,重构主义把刑罚理解为社会现象,通过探讨刑罚在社会生活中能扮演什么角色,回答刑罚能够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在重构主义看来,维持一个和平、合作的公民社会,取决于可靠、有效、公正的刑法保护,是对刑法功能的直观而有吸引力的理解。毕竟,刑法是法治的组成部分,是保障所有人自由的源泉,应当追求最有利于保障民众自由的处理方式,这正是重构主义的优势所在。重构主义的理论贡献是,社会是一个密集的关系网络,刑法为这种关系网络提供保障,犯罪是对公民社会的和平、合作造成的暂时或永久破坏,如果行为人在犯罪后与国家合作,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法益,重建和平、合作的公民社会,使其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那么就基本上等同于公民社会没有被破坏。惩罚的作用是明确地重申犯罪所拒绝的价值观,同时,惩罚确保所讨论的价值是“真实的”和“具体的”,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和概念性的。〔27〕See Bronsther, Jacob, Two Theories of Deterrent Punishment, Tulsa Law Review, Vol. 53, No. 3(Spring 2018), p. 472.如果仅强调对犯罪的惩罚,可能就不只是福柯所言的监狱的失灵,而是包括刑法的失灵等。
正因如此,我们在思考刑罚目的时,需要从工具性标准向功能性标准转变,重构主义恰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视角:第一,构成重构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法益保护的概念,法益保护不是历史性分析,而是功能性分析,即把刑法视为社会合作、和平的维持与恢复系统。法益保护定义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反过来,法益恢复作为刑法逆向工程,在法益恢复的考虑下,刑罚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对刑罚适用与否的判断是真实的、具体的,也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这是因为重构主义是从“刑法是法益保护法”的前提所导出的,刑法的法益保护法属性应把法益保护及法益恢复作为任务去对待,既要向前看,预防保护法益被侵害或侵害危险;也要向后看,在法益被侵害后判断有无可能恢复被破坏的法益,如果只强调保护法益损害后的处罚,而不考虑被破坏法益的恢复,则会存在重大偏误。第二,在分析刑罚目的时,应警惕化约主义的陷阱,化约主义意味着以单一的因果关系或功能目的来解释刑罚,如果说刑罚是一种多元因素促成的结果,同时又是多元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当然就不是一种应当还原到最根本原因(报应)的存在,而是一种难以自我复制的复杂系统影响所致,刑罚目的不能被简单化约为单一目的,而是一种多元的存在。第三,惩罚的另一面是排斥,报应或预防扭曲了刑罚的真正目的,刑罚本身无法维护或创造刑法权威,相反,刑罚适用本身意味着刑法权威已经遭到破坏,故,它无法在维护刑法权威上扮演关键的角色,而只是一种符号或象征,追求报应或预防,反而削弱了原本可以加强的社会合作与和平。
刑罚社会学为重构主义提供了方向,但并不是其理论根据。重构主义的理论根据是罪责原则,罪责原则才是设定刑罚的标准,它主张“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消极的责任主义)的现代刑法的基本原理。〔28〕参见张明楷:《责任论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3期,第1页。从责任角度看待刑罚,而不是从犯罪角度看待刑罚,这不仅意味着刑罚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高于行为人的罪责,应当贯彻罪责刑适应原则,反对严厉程度与罪责程度不符合的刑罚,而且意味着不需要追责的情况下,无须动用刑罚,就像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因为不具有罪责基础,故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罗克辛指出:“通过将刑罚与罪责原则相联系,还可以消除一种道德性上的担忧,即在追求预防性目标时,人由于被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使人的尊严受到损害。”〔29〕[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罪责原则在于保障自由与限制权力,尽管它仍会出于预防的需要,但这种预防的需要必须在保障自由的范围内。责任刑与预防刑的讨论与此相关,正所谓“基于报应所裁量的刑罚是责任刑,基于预防犯罪目的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30〕张明楷:《论预防刑的裁量》,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第102页。如果某种处罚既能发挥预防作用,又能保障自由,则是两全其美之策,也是罪责原则实践的最佳方案。不难看出,重构主义主张的“迷途知返条款”就是这样一种最佳方案,因为它强调法益恢复的社会功能,注重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详细论证。
重构主义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处方吗?不难想象,重构主义最难以为法律人接受的原因,大概是认为重构主义抵牾刑法权威。殊不知,刑法权威并不是基于强制的权威,而是基于认同的权威,刑法只有真正能够给民众或被告人带来和平、合作的美好社会,才能形成基于认同的权威。相反,基于强制的权威仍是报应主义的立场,报应主义或综合主义主张的惩罚,并不是一种万能犯罪治理方式,预防主义已经对之进行过有力批判,惩罚不是对犯罪的道德反应,而是要追求某种特定的目的,预防主义把这种目的定义为罪犯的再社会化,重构主义把这种目的理解为通过合作而实现法益恢复,即恢复到犯罪之前的状态,能够增进基于认同的权威。这一定位有其时代背景,现代刑法已经进入法定犯时代,不少犯罪具有法定犯的本质,即违反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的犯罪,不会导致生命、健康、性自主等人身法益损害,在法定犯中,民众的报应情感明显减弱。重构主义认为现代刑法不是完全废除惩罚,而是减少惩罚或替代性惩罚,它依赖刑罚实现法益恢复,如果行为人能够以自我的努力缝合被自己撕裂的社会结构,就没有必要惩罚,这也并没有脱离国家控制的轨道:一方面,从目的论的观点来看,重新缝合被撕裂的社会结构是有价值的,也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有助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法益,也是一个非决定性的刑罚理由,〔31〕报应主义、预防主义与综合主义都是一种决定论的刑罚理由,报应主义取决于客观危害,预防主义取决于人身危险性,综合主义则兼顾考虑客观危害与人身危险性。而刑法的合法性是其为法益恢复提供了保障工具,而不是满足被害者的报应情感,这是一种有效性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将刑事处罚视为技术性措施或犯罪控制工具,从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项合理的选择,〔32〕See David Garl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nishment, Crime and Justice, Vol. 14(1991), p. 123.国家由此可以一举两得,既减少关押罪犯的改造成本,又可以避免因被害者贫困导致的其他治安问题。
就刑法与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的关系模式来说,传统观点把刑法理解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即其他法律设置的防线崩溃之后,由刑法来充当第二道防线,即把这种行为犯罪化,并予以刑罚处罚。笔者认为,这只是理解刑法与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关系模式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维度的存在。逃税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立法表明,刑法可以是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实施的后盾,即以刑罚宣示督促行为人在违反行政法、民法、经济法之后,积极按照这些法律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而不是让被害者等经过漫长的民事诉讼、劳动仲裁等去维权。如果行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即恢复自我行为所破坏的法益,那么就可以免除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可见,重构主义建构了一种刑法与行政法、民法与经济法的全新关系模式,即避免了刑民、刑行交叉等不法判断难题,也可以更好地保障民事救济、行政处罚等的顺利实施,是一种充分考虑刑法谦抑、刑法激励、刑法有效性的全新刑罚适用方式,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事实上,在德国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将赔偿作为刑罚、保安处分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将赔偿作为‘第三条道路’来减轻刑罚或代替刑罚时,赔偿与未减轻的刑罚相比,却能使刑罚目的和被害者的需求得到同样的或更好的实现与满足。”〔33〕[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一言以蔽之,现代刑罚适用的国有化、科层化与专业化,导致刑罚适用与被害者利益保护之间的鸿沟,被害者或被害者家属只能与惩罚过程间接沟通,刑罚成为道德中立而理性的工具。循此的刑罚适用,罪犯只是被起诉、被管理,而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重构主义力主改变这一格局,强调被害者的中心角色及与此相关的矫正正义。在重构主义的视野下,为惩罚而惩罚,就不是手段问题,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如果拒绝行为人的法益恢复努力,进而给予行为人刑罚处罚,就是非理性的。
(二)重构主义理论的五大优势
刑罚目的与社会变迁的演进有关,并随社会变迁的演进而变迁。重构主义从社会合作、和平的社会结构及其秩序(法益)出发,把犯罪视为对这一社会结构及其秩序的破坏,把法益恢复视为对被破坏的社会结构及秩序的恢复,法益恢复并非行政前置性要件或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淡化版本,它们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及不同的实践效果。
第一,符合法益保护实质化的要求。刑法是法益保护法,不是犯罪惩罚法,一部有效、可靠的刑法是维护公民社会的合作和人民放心的自由。〔34〕See Bronsther, Jacob, Two Theories of Deterrent Punishment, Tulsa Law Review, Vol. 53, No. 3(Spring 2018), p. 492.这是对刑法目的与功能的表达,涉及法益保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问题。法益保护的形式化是从国家视角的分析,它意味着刑罚是预防与控制法益被侵害的工具,或发生法益侵害后的报应工具;法益保护的实质化是从被害者视角的分析,它意味着法益被侵害后的恢复,即当属于被害者的法益被侵害后,行为人通过积极努力恢复被破坏的法益,把被害者的法益损失降到最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法益恢复可以作为一种“方便的替代物”,〔35〕James G. Stewart,A Pragmatic Critique of Corporate Criminal Theory: Lessons from the Extremity,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6, No. 2(Spring 2013), p. 297.从功能性视角回答“个人与社会秩序起初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原初秩序是因为什么行为被破坏”“在什么条件下被恢复”等社会安全问题。毕竟,最好的刑法适用方式是以代价最低且能恢复被破坏的合作与和平方式来表达谴责,那种以付出巨大成本而效果不佳的制裁方式,并不符合刑法文明的要求。
第二,实现刑罚适用的理性化。惩罚的理性化不仅是近现代出现的中央集权化、科层化与专业化,也包括最后手段原则,即只允许合理手段中那些最温和的手段,如果立法者在动用刑罚手段时,不曾事前确定其他法益保护的可能性效果已然不佳,便会违背最后手段原则,从而招致惩罚性立法的非难。〔36〕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页。笔者认为,因法益恢复等而拒绝处罚,拒绝刑罚处罚是为了更大的益处,也符合最后手段原则。比较而言,威慑是一种肆无忌惮的非法伤害,而不是最小手段,即使它是合法的,但也绝对不能是“王牌”。预防犯罪的设想效果是极为有限的,把报应与预防综合在一起,会导致刑事处罚的边际增长,而不是边际降低,因此,行为人接受刑罚处罚后,尚需根据特殊预防的需要而采取其他措施。重构主义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犯罪威胁到一个合作的、和平的公民社会的维持,如果行为人犯罪后能够以自己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公民社会,行为人值得刑法谴责的意义大为降低,没有必要再适用刑罚:一方面,这与公民社会破坏前的状态没有区别,如果行为人骗取贷款后予以返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予以赔偿,则如同法益本身没有被破坏;另一方面,刑法以无罪或从宽处罚方式,可以有效激励行为人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法益,而不是制造破窗效应或对抗,也一并减轻了国家惩治犯罪需要花费的巨大成本,可谓是“更大的益处”。
第三,改变以自然犯的不法、有责理论来套经济犯的偏误。直到19世纪中期,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几乎都是由自然犯所构成的,〔37〕参见[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法哲学》,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627页。刑罚理论自然依托自然犯所产生与发展,前述综合主义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刑法理论发展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刑法理论产生后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古典刑法理论形成之后至今,基本上是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自然犯为现象建构起来的。对于自然犯而言,鲜有法益恢复的空间,如故意杀人后不可能使被害者“起死回生”,以报应或预防为根据建构不法与有责理论,自然把刑罚惩罚作为主轴。经济犯多是一种非暴力的侵财案件,被形象地称为“白领犯罪”,其违法性意识不强,实施手段也为非暴力方式,但造成的经济损害极其严重,并且经济犯罪往往面临刑、民交叉问题,坚持自然犯持守的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立场,会存在不协调的困境。对于此类犯罪,报应或预防都并不具有解释力,报应代表国家或民众的立场,但并不符合市场规律,经济犯罪处理中的“政府”与“市场”两极,分别代表惩罚主义与协约自治,过度强调惩罚必然破坏协约自治,违背市场规律,会造成企业破产、劳动者失业、政府税收没保障等问题,故刑法需要为经济犯罪治理开辟一个“合作社区”,追寻“矫正正义”。以骗取贷款罪为例,什么是民事上的“欺诈”,什么是刑法上的“欺骗”,往往只是概念游戏,两者之间并无真正区别,把此类行为定义为犯罪,其实架空了民事法律,存在“以刑代民”的越权问题。同时,此类犯罪处理效果并不好,不仅存在“企业负责人坐牢导致企业经营困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无法被及时偿还”等问题,而且存在选择性司法、司法腐败、量刑不公、“拼凑判决”等反法治现象。相反,在重构主义看来,犯罪是对社会的伤害行为,从矫正正义和法益保护原则出发,强调行为人努力修复其对社会的破坏,如果行为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具有犯罪阻却事由或从宽处罚理由,这对激励行为人犯罪后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法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经济犯只能坚持弱报应主义,对它施加刑罚威胁,主要不是让行为人蒙羞,而在于激励其积极恢复法益。
第四,重构主义不会导致“破窗效应”。重构主义有一项令人误解之处,即导致刑法的破窗效应,导致刑法失灵。此一误解,当然来自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的立场,在原本报应主义或预防主义所依赖的刑罚目的理论中,从规范面向而言,法益恢复不能为报应或预防所包含。笔者认为,法益恢复并不表示起不到报应或预防效果,而是以替代责任方式,表达报应和预防。以逃税罪为例,是否存在“逃成功就大赚、不成功仅仅补缴加罚款”的破窗效应?固然,就预防犯罪而言,刑法如同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然而,替代责任并不是刑法上的最薄弱环节。笔者认为,矫正正义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不是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犯罪市场或犯罪黑数导致的惩罚概率低才是最为薄弱的环节。西方学者研究表明,从基本意义上说,立法者是在制造犯罪市场,所有形式的监管都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后果——地下行为,〔38〕See Jaros, David Michael, Perfecting Criminal Market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12, No. 8(December 2012), p. 1949.如毒品黑市、洗钱黑市或境外电信诈骗等。换言之,立法者最初试图消除犯罪,结果可能会加强犯罪市场,刑法上的犯罪化立法非但不能预防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等,反而促进了犯罪市场的完善。犯罪市场鼓励立法者更全面地评估运用刑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与收益,寻求以一种更充分促进的方式,避免以“简单化”思维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39〕同上注,第1990页。同时,不重视惩罚几率或惩罚概率低,也是预防犯罪的薄弱环节,如早期盗窃罪高发的原因是被抓概率低,如果司法机关把案件发现、惩罚概率提高,则上述破窗效应并不存在。不难发现,采取重构主义不仅避免了刑罚目的论中“国家与罪犯之间关系”相当迂回的论证,而且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比如,对白领犯罪而言,犯罪人的成本与效益计算理性更为明显,如果犯罪收益远低于犯罪成本,那么犯罪人一般就会停止犯罪,以范冰冰逃税案为例,因“首犯免罪”而附加的高额罚款(8.83亿补税及罚款),其预防犯罪效果并不比对其定罪处罚差。同时,因不存在面临严重刑罚适用的风险,行为人的对抗意识与行动相对减少,这反而有利于提高犯罪被发现的概率。
第五,充分关注被害者矫正正义。被害者的利益保护在哪里?当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前所述,报应主义、预防主义和综合主义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没有被害者,就没有严格的理由刑事定罪。〔40〕See Andrei Poama, Corrective Justice as A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A Prolegomenon, Crimin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12(2018), p. 608.近现代刑法理论缺乏对被害者利益的关注,它不是以现实的被害者诉求追诉犯罪人,而是以抽象的人民的诉求追诉犯罪人,整个侦查、起诉、审判到刑罚执行制度,都是为国家、社会和广大民众利益而设计出的对犯罪人的惩罚,是以国家惩罚代替私人报仇、家庭与家族的私斗,并通过法院借助中立法的规则处理犯罪,以确保和平。它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被害者把他们的道德权利捐给国家,而这事实上是一个尴尬解释,〔41〕See Bronsther, Jacob, Two Theories of Deterrent Punishment, Tulsa Law Review, Vol. 53, No. 3(Spring 2018), p. 491.因为刑法毫无根据地以国家利益取代了被害者的利益,把赎罪理论等同于报应,而不是法益恢复,类似于以弄湿溺水者为代价拯救溺水者衣服。其实,被害者不可能这么做,这就是被害者不断上访维权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不以被害者之法益恢复来证明刑罚权的正当性存在疑问,因为除了惩罚罪犯以防止未来的犯罪外,被害者更期待一种公平的法益恢复补救办法。被害者并不都是复仇主义者,对被害者的法益恢复或赔偿计划,有助于实现矫正正义。〔42〕See Michael Moore, Victims and Retribution: A Reply to Professor Fletcher, Buあ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3, No. 1(April 1999), p. 67.遗憾的是,在报应主义、预防主义与综合主义刑罚目的论中,被害者仅被作为一个逻辑问题,存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论中,〔43〕See Markus Dirk Dubber, The Victim in American Penal Law: A Systematic Overview, Buあ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3,No. 1(April 1999), p. 3.并且通常是一个象征性、情感性的角色,未真正走进刑法实践。
(三)小结
刑法的意义或功能是为了共同的合作与和平而对各种活动予以协调,惩罚与宽恕都是这种协调行动。刑法是国家控制行动,而不必然是惩罚,〔44〕See Dieter Rössner, Mediation as a Basic Element of Crime Contro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mments, Buあalo Criminal Law Review, Vol. 3, No. 1(April 1999), p. 219.通过法益恢复建立合作与和平,看似是一种宽恕,其实仍是一个国家控制犯罪的中心要素。相反,如果国家不能证明一项刑事意义上的处罚或量刑,是实现令人信服的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所必需的,〔45〕See Salil Dudani,Unconstitutional Incarceration: Applying Strict Scrutiny to Criminal Sentences,Yale Law Journal, Vol. 129,Issue 7(May 2020), p. 2112.那么这种刑罚适用就是不合理的。
刑罚需要在发展性视角与功能性视角下进行制度创新。重构主义意味着从刑罚的哲学基础到刑罚社会学基础的转变、从惩罚正义到矫正正义的转变、从理想化的一维刑罚形象到现实化的多维刑罚功能的转变,是关于刑罚目的论的第四种思考方式,亦为经济刑法之罪刑体系建构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矫正正义有望重振和丰富。而刑罚目的被重构主义再定义,需要重视制度与实践层面上“迷途知返条款”的建构,这是“以被害者为中心”的惩罚方案,应当引起立法者高度重视。
三、我国刑法中“迷途知返条款”的建构
从重构主义出发,刑法修正案应当重视出罪上“迷途知返条款”在经济犯、秩序犯中的积极运用,并重视量刑上“迷途知返条款”在其他犯罪中的扩展适用。
(一)“迷途知返条款”的适用范围
从规范属性上,“迷途知返条款”属于相对强制性规范,有别于一般刑法的绝对强制性规范,即以刑罚威胁保障法益恢复等的实现,若不具备这一实现,则需要兑现刑罚。
“迷途知返条款”是行为人恢复被破坏法益的“测试”,它强调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法、民法等途径,解决某些特殊的犯罪的责任承担问题,算是对保障民众不被轻易犯罪化的一次努力尝试。尽管刑罚是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特征,但是,犯罪带来的错误或伤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纠正的,这可能意味着立足于矫正正义而去罪化或轻刑化。而“迷途知返条款”就意味着去犯罪化、去刑罚化或轻刑化,会使刑法与其他法律的边界模糊,故其适用范围应当予以合理界定。本文把“迷途知返条款”分为定罪上的“迷途知返条款”与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鉴于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可以适用于所有犯罪,并且已经为司法解释所明确,故下文专门讨论定罪上“迷途知返条款”的适用范围。
众所周知,犯罪有自然犯与行政犯之分,行政犯包括经济犯、秩序犯等具体类型,不一而足。其中,经济犯即经济犯罪,而经济犯罪又可以细分:一是单一侵害财产法益与市场管理秩序的经济犯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罪”“逃税罪”等;二是侵犯财产法益与市场管理秩序,又侵害人身法益的经济犯罪,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秩序犯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专指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在秩序犯内部,亦有单纯妨害管理秩序法益的秩序犯与同时侵害人身法益的秩序犯之分,前者如“非法集会罪”,后者如“聚众斗殴罪”。
对于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原则上不宜建构“迷途知返条款”。〔46〕故意伤害罪(轻伤)属于自诉犯罪,可以由被害者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此外,97年《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本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免罪规定。《刑法修正案》将其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实现了定罪上的“迷途知返条款”到量刑上的 “迷途知返条款”之转变,体现了立法对侵犯人身法益设定迷途知返条款的慎重。如果经济犯或秩序犯同时侵害人身法益,自然也不适用“迷途知返条款”。对其他经济犯、秩序犯来说,则有建构“迷途知返条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如前所述,现有刑法对经济犯、秩序犯均有“迷途知返条款”,立法者已有先行先试。只是,刑法在秩序犯上多采取隐含性规定,如《刑法》第296条“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即“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本罪有“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的限制性要求。相反,若行为人实施非法聚会等行为之后,服从解散命令,则不构成本罪,这实质上是“迷途知返条款”。笔者认为,立法者在采用“迷途知返条款”时,当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对不涉及人身法益的经济犯当优先考虑“迷途知返条款”。对经济犯罪而言,有罪必罚的罪责模式,会制造一个适得其反的经济陷阱。刑法是法益保护法,不是大众感受宣泄法,刑罚系统不能只求迎合公众大致的感受,而是需要重视法益恢复。对于可以也能够恢复法益的情况,对行为人应当采取替代责任,还是应当一视同仁?传统刑法在定罪上采取一视同仁,只是在量刑上有所区别,以激励行为人积极悔过、积极赔偿等。要知道,这种激励效应的发挥对经济犯罪而言十分有限,经济犯罪人大都是理性人,如果让其退赃600万与从轻处罚1年进行交换,他会计算这种交换的成本,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愿意遭受轻微的惩罚而不是承担数额惊人的民事责任。”〔47〕Douglas Husak, Reservations About Overcriminalization,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4, No. 1(Winter 2011), p.102.《刑法修正案(十一)》加大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惩罚力度即是为了预防这一现象。再者,如果让其把骗取银行的600万贷款返还,以换取无罪的处理,行为人更多会选择“成交”;相反,如果把这种无罪处理,设计成一个赌场游戏中的“下注”,行为人更多是拒绝。忽视这种激励性评价的经济分析,会产生不理性的预测和不可靠的处方。〔48〕See Dan M. Kahan,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rim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 No. S2(June 1998), p. 610.就此而言,对经济犯罪完全可以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强化与行为人的“法益恢复”所密切关联的替代责任。替代责任看似是以罚款、民事赔偿为经济犯罪“定价”,但是,刑法形塑法益恢复比道德谴责更重要,这也是一种更便宜、更有效的犯罪处理机制。换言之,替代责任会产生一个复杂效应,包括有效的行为激励和充足的社会意义,这是单一的道德谴责无可比拟的。
第二,对不涉及人身法益的秩序犯可考虑“迷途知返条款”。作为前提,秩序法益本就属于刑法上争议比较大的领域,强化对秩序法益的保障,存在使刑法蜕变为社会管理法的重大风险,因此,秩序犯的罪刑体系建构需要“小心求证”。不涉及人身法益的秩序犯,之所以被定义为犯罪,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如果行为人在破坏社会秩序或造成社会秩序被破坏的危险后,随即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那么就有出罪的理由,也可以设置“迷途知返条款”。以《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为例,现有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有“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行为,且情节严重的,则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经过劝说后组织分散离去的,则属于事后的法益恢复行为,可以作为“迷途知返条款”,在立法者修改刑法之前,解释者可以把此类行为解释为“情节严重”的除外情况而出罪。即使是《刑法》第294条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有采取“迷途知返条款”的空间,比如,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后主动退出的,或参加时并不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了解真相后并没有立即退出,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后退出的,也可以按照无罪处理,以激励行为人积极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
第三,对涉及人身法益的经济犯、秩序犯等不可以设置“迷途知返条款”。侵害人身法益多属于自然犯,或属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组合形态。对于自然犯,正义模式强调的报应并没有过时,报应作为特定价值与信守进入刑罚过程,符合民众的文化心态与感受,具有工具性与象征性,也具有刑罚文化上的客观性,对于此类犯罪不宜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否则,这会彻底动摇刑法的根基。
在“迷途知返条款”建构中,必须强调的是,刑罚目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核心、外围和例外,正义层面的报应是核心,预防主义下的犯罪预防是外围,而重构主义主张的法益恢复是例外,只适用于特殊的犯罪类型。重构主义视野下的“迷途知返条款”所提供的是多元理论,而不是一元理论,因此,并不会构成破坏刑法体系的重大风险,相反,其成为我们观察刑法文明的重要窗口。
(二)“迷途知返条款”的类型建构
惩罚不应受到处罚的行为,就是刑罚的失灵,刑法上的“迷途知返条款”,就在于避免刑罚的失灵。同时,身处不断变动且日益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国家已经不可能管理所有的社会领域,“利维坦”号再也不能在惩罚罪犯上投入足够的资金。〔49〕See Carlos Gómez-Jara Díez, Corporate Culpability as a Limit to the Overcrimi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gulation,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Citizenship,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4, No. 1(Winter 2011), p. 96.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一个行为人犯罪后与国家、社会合作的机会,包括促进守法的行为与违法后的自我补救等,如果行为人能够在犯罪后自己恢复被破坏的法益或赔偿损失等,就可以给予他免罪或从宽处罚的机会,因此,刑法上的“迷途知返条款”成为时代必需,这涉及出罪与量刑两个维度。
1.出罪上的“迷途知返条款”
刑法上的“迷途知返条款”存在着延伸的重要性及累积的意义深度,有在经济犯、秩序犯中予以推广的必要。对此,大致有两种制度设计方案。
(1)事前合规建设与违法阻却事由
经济犯罪中单位犯罪增多趋势,意味着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性,企业合规建设是企业有效控制刑事犯罪风险的重要举措。如富国银行、通用汽车公司、Uber运输公司等,因未能妥善预防、发现、调查和纠正组织内部的不当行为,给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企业合规的重要性功能已经被不少公司所接受,并把企业合规的重心放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包括复杂的合规调查。〔50〕See Veronica Root Martinez, Complex Compliance Investigations,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20, No. 2(March 2020),p.249-250.试问,如果企业已经进行完善的合规建设,注重对社会或他人利益的保护,但个别企业员工仍故意或过失造成社会或他人法益侵害的,企业是否需为此负担刑事责任?对此,国外学者指出,在公司背景下,当他们通过、利用有效的公司合规计划时,这意味着公司不应该受到惩罚。〔51〕See Carlos Gómez-Jara Díez, Corporate Culpability as a Limit to the Overcriminaliza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gulation,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Corporate Citizenship,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4, No. 1(Winter 2011), p. 96.笔者赞同这一观点,首先,民众最宝贵的自由,是不被监禁的权利。在重视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公司过度犯罪化的迹象十分明显,这并不符合刑法文明,应对公司犯罪予以严格限制。其次,企业天然会存在不遵从的企业文化,如果公司员工违背企业规章制度行事,其代理行为固然与公司责任有关,但不能漫无边际,如果有证据证明公司提供尽职调查或企业合规,在努力培养一种守法的企业文化,则不能被认为是单位犯罪。再次,在法律上,合规计划的存在是确定公司是否应当对其雇员的行为负责。公司有严格的合规法案,其实是公司预防侵害社会、损害他人法益的积极努力,属于事前的“迷途知返条款”,也是免除公司责任的独立要素。事实上,刑法也存在类似条款,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如果行为人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地点与方法捕捞,则相当于行为人的合规建设,不成立犯罪。再次,单位民事责任可以避免公司刑事责任的不良特征,这些不良特征包括刑事诉讼拼凑现象与刑事制裁的污名效应,〔52〕See V. S. Khanna,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What Purpose Does It Serve?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9, No. 7(May,1996), p. 1477.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很少从威慑的角度支持对单位继续施加刑事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最后,在企业合规的情况下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与罪责原则不符,企业因无法预见而并不具有责任,只需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即可。相反,此种情况下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不仅不能反映公司真正罪责的行为,成为连带责任,而且必然会导致将不应受到足够责备的公司行为定为犯罪,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公司行为的过度犯罪化。
(2)事后法益恢复与附条件的出罪
英美学者胡萨克提出的“过度犯罪化”问题,〔53〕参见[美]道格拉斯·胡萨克:《过罪化及刑法的限制》,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引起全球学者的关注,在德国学界关于法律政策学的辩论中,人们也往往对过度的“惩罚主义”给予谴责,惩罚主义意指“刑法条文过多”或“刑罚过于严厉”。〔54〕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溯、黄笑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当刑法超出合理范围时,就会发生过度犯罪化问题。〔55〕See Andrew Ashworth, Conceptions of Overcriminalization,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Vol. 5(2008), p. 407.过度犯罪化令人担忧,它意味着对最后手段原则的背弃,可能对自由构成威胁。但如何限制过度犯罪化,仍有刑法制度创新的空间。
遗憾的是,刑法在讨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时,多适用模棱两可的概念,未找到确定犯罪化根据的概念。一直以来,学界认为刑法的特殊性是因为它使犯罪者受到国家惩罚,惩罚包括耻辱的痛苦或自由剥夺,是谴责和污名化,是吃苦受难蒙羞,受制于此,刑罚惩罚须符合更高的正当性标准,需“严格审查”来证明其合理性,法益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就是刑法的正当性标准。以这些标准衡量刑法,胡萨克所言的过度犯罪化担忧确实存在,也存在惩罚不成比例罪行现象。与此同时,法律必须发展,以满足随着社会秩序发展的需要,而社会秩序也在不断地变化,〔56〕See Joseph H. Drake,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aw,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16, No. 8(June, 1918), p. 601.这就导致刑法立法的活性化发展。〔57〕参见井田良:《刑事立法の活性化とそのゆくぇ》,载《法律时报》2003年第75卷第2号。在刑法立法积极、活跃的时代背景下,犯罪化态势是加剧而不是减少了,犯罪化攀比效应也不可避免,其中,尤其要注意的现象是行政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刑法化,如危险驾驶罪本系行政法调整的行为;骗取贷款罪本系民法、经济法调整的行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本系劳动法调整的行为;等等。这意味着刑法不再固守最后手段原则,而是成为前置手段或优先手段,导致警务民法、警务经济法等。为此,停止犯罪化立法也为不少学者所呼吁,而预防性刑法也被批判为不针对有正当理由的犯罪行为。〔58〕See Andrew Cornford, Preventive Criminalization,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Vol. 18, No. 1(Winter 2015), p. 1.我国刑法修正实践对这一呼吁并不理会,就原因而论,立法实践拒斥刑法理论有其必然性,现代刑法立法更加强调对民生问题的积极回应,当酒驾、恶意欠薪、冒名顶替、高空抛物、病毒肆虐、基因编辑、网络色情等成为民生问题时,加之在现代信息时代,激情立法主张等会如病毒般传播,极易形成社会舆论,此时,刑法介入就不可避免。但这恰恰又意味着,刑法的“钟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59〕See Greg Rustico, Overcoming Overcorrection: Towards Holistic Military Sexual Assault Reform,Virginia Law Review, Vol.102, No. 8(December 2016), p. 2072.因为刑法介入的副作用亦十分明显,危险驾驶罪每年产生10万以上犯罪人即为适例。
难道就不存在一条中间道路吗?作为前提,基于刑罚的标签效应与巨大的副作用,刑罚适用应不得已而为之。重构主义下的“迷途知返条款”是发明一种以犯罪化保障的“非犯罪化”,即行为人在造成法益损害后,刑法为行为人积极实施法益恢复开辟制度通道,这一制度通道是借助个罪之构成要件上的行政或民事前置性要件来体现的,它是为积极悔过的人设计法律,也意味着刑事追诉从对抗走向合作。以“骗取贷款罪”的修正为例,骗取贷款罪作为《刑法修正案(六)》新设罪名,在入罪标准上采取择一标准,即“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司法解释则扩张了该罪的入罪标准范围,〔60〕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7日《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27条之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刑法修正案(十一)》改变了择一标准,取消“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入罪标准,强调“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唯一入罪标准。〔61〕《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1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修改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笔者认为,骗取贷款罪也是观察刑、民交叉的重要窗口,它所带来的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之间模糊的界限,亦给刑法解释带来全新挑战。这一修正的目的在于限缩骗取贷款罪,但意义十分有限。笔者认为更好的选择方案是,对《刑法》第175条“骗取贷款罪”中增设“在经过银行或金融机构要求偿还贷款后,积极偿还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民事前置性要件,如果行为人能够积极履行偿还贷款的民事责任,则不构成犯罪。“迷途知返条款”作为一种混合型的关系性规范,其实是以犯罪追究保障民事责任的积极履行,其中,犯罪化的命令使民事责任的履行得到了加强,避免了民事诉讼上的诉累,保障了民事秩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解决方案”解决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对立的棘手问题,也是科学立法的应有之义。对此,要特别警惕的是,法学研究者不宜利用当前的公众注意力,以强化立法者动辄犯罪化的政治意愿,也不应在犯罪化立法上走捷径或“大跃进”。刑法立法的天平不应该朝着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倾斜,而是需要认真对待重构主义,扩大“迷途知返条款”在刑法中的适用范围,使重构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刑法立法创新的理论指南,也一并从话语体系上避免立法理论创新旁落。
2.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
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是指行为人犯罪后认罪认罚或积极赔偿被害者损失等而适用从宽处罚规定。相比于定罪上的“迷途知返条款”,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更为常见,也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对象。两高、三部2019年10月24日出台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包括基本原则、适用范围、适用条件、从宽的把握等,从而以司法解释方式明确了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有待补充的是,司法解释只是明确了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的一般性规定,并无关注具体个罪的特殊情况,且也存在不受法律拘束的疑问,因此,刑法修正案可以结合具体个罪分别明确量刑上的“迷途知返条款”。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提出两个需要遵循的原则:第一,区别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与非侵害人身法益的犯罪,对前者原则上否定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司法解释立足于实用主义立场,对所有犯罪均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这固然可以提高司法效率与节约司法成本,但严重忽视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对实体刑法的冲击。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传统自然犯而言,报应仍是正义的体现,对此类犯罪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处罚,与正义模式抵牾,并不可取。而就非侵犯人身法益的犯罪来说,民众的报应情感并不强烈,这种报应也没有预防的意义,因此,此类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具有合理性。第二,实现“迷途知返条款”的法定化。从法源角度看,以司法解释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存在法律的拘束力疑问,即存在司法解释立法化的疑问。对此,刑法修正案应当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实践经验,实现退赃、积极赔偿、法益恢复等从宽处罚的法定化,把原本属于酌定从宽处罚的情节,上升为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就刑法理论而言,“探索复杂度,并加以体系化”的方向标,一直是学术研究及其实践的核心。一直以来,压倒性的大多数文献对刑罚目的论的研究集中于报应主义、预防主义与综合主义,缺乏对重构主义的讨论,并且把产生于自然犯的刑罚目的论直接套用在经济犯等行政法上存在重大偏误。本文的努力在于提出与发展重构主义,对于刑法立法发展来说,当我们以更为广泛的刑罚社会学视角看待刑罚目的时,刑罚的悲剧才能转变为喜剧,犯罪后的惩罚也才有可能避免,也才可以消除国家对公民处罚之“内战性格”,而走向“和平之家”。尽管,重构主义的适用范围有限,按照本文的理解,它只适用于部分经济犯与秩序犯,并无普遍适用的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理论突破没有意义。刑法对社会是“功能性”的,其目的在于形成某种“功能”,引导或约束某种行为,包括引导行为人自觉、主动恢复被破坏的法益,如果能够达成这一目标,以惩罚为后盾的刑法的功能就已经得以发挥,就没有必要再施加刑罚或重罚。如果认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有序也需要合作的社会中,法益恢复就应当受到重视,由此才能种出“自由之树”,重构主义这种务实的理论就需要重视,这并不是一种符号性的荣耀概念,而是需要真正走入制度实践。对此,我们应意识到,在刑法的现代化过程中,刑罚既抚慰伤痛,又当激励重生,刑法在某种限度内可以作为营造美好生活的工具,重构主义符合犯罪的经典社会学分析,对经济犯、秩序犯的罪刑体系建构具有指导意义,两者均当重视“迷途知返条款”的适用,从而可以使刑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活法”。
——兼谈集体法益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