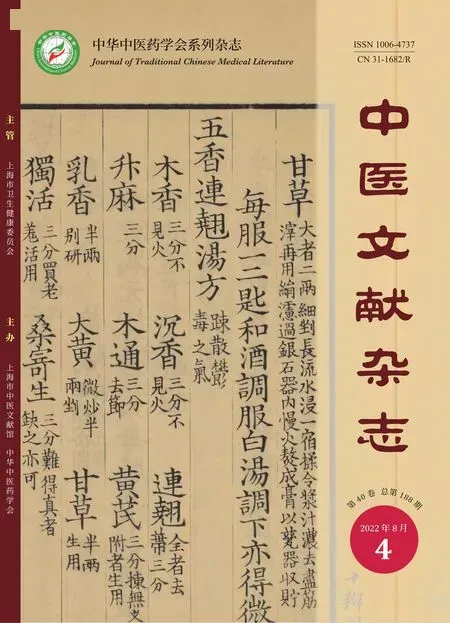中医儿科学发展源流简述*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蒋立卫 顾博丁 梁尚华
小儿具有脏腑娇嫩,发病易感易传,预后变化多端的特点,因幼儿不能自述病情,亦称“哑科”。中医儿科源于中医内科学,因其自身的独特性,后续独立成科。本文将中医儿科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3个阶段进行探讨。
萌芽时期
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入咸阳……为小儿医”[1]435,这是对儿科医生的最早称谓。该书亦载有儿科最早的病案:“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三日即病愈。”[1]436《五十二病方》亦载有治疗“婴儿索痉”“婴儿病间(痈)”的医方。
《黄帝内经》虽有关于小儿的论述,但未形成独立体系。《灵枢·卫气失常》中“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2]151,是对小儿年龄的最早分期。《黄帝内经》认为,生命活动源起于先天父母之精,如“人始生,先成精”[2]40,“夫精者,身之本也”[3]8,“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2]32,“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2]95。《黄帝内经》关于小儿的论述极具特色。如“人年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2]143,“女子七岁,肾气盛……丈夫八岁,肾气实”[3]2。书中关于小儿诊断的论述是后世儿科诊断发展的学术渊源,如钱乙将《素问·刺热》论面部区域对应五脏的内容用于儿科面部望诊,而小儿望指纹法实则源于《灵枢·经脉第十》的望鱼络法。
在疾病方面,《黄帝内经》注重先天禀赋的观点为临床提供了指导,指出小儿禀赋根于父母,“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循”[2]142。其首次提出“胎病”,并指出胎养疏忽是小儿先天致病因素。《素问·奇病论》言“生而有病癫疾者”属于“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3]77。诊疗上,《黄帝内经》将小儿与成人区别开来。如《素问·疏五过论》中诊病当“问年少长,勇怯之理”,《灵枢·逆顺肥瘦》云“肉脆血少气弱”[2]109,针刺时“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2]109,《素问·示从容论》“年少则求之于经”[3]158。《黄帝内经》对小儿病的预后也有论述。如“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大便青瓣飨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飨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2]187,“婴儿,热而腹满者死”[2]81。
南北朝时期有10 余部儿科专著问世,多已散佚,部分内容可从《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中窥得端倪。此外,葛洪、王叔和、陈延之等医家的著作中亦涉及儿科。此时的儿科多总结以往实践经验,儿科经典理论如变蒸学说等还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开拓了脉诊、外治法等新领域,小儿针灸和养护得到新的发展,为隋唐儿科走向专门化奠定了基础。
形成时期
隋唐至两宋是儿科学的形成时期。隋唐时期,中医儿科从理论到临床渐成体系,小儿生理病理、诊疗及护养均有发展。著名的儿科四大症麻、痘、惊、疮,在隋唐的医学著作中已有载录[4]。唐太医署把“少小”作为医学教育的独立分科,《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对小儿病分门别类进行论述。儿科作为独立的临床专科已初具规模。
《诸病源候论》全书6卷共计255候专论小儿诸病。巢氏的小儿养护思想更加完备,如“变蒸候”“易虚易实”“自非当病,不可下也”[5]等体现了小儿体质特点;小儿养护方法如“薄衣法”,基于对小儿外感病因的认识,又蕴含着预防医学的思想,影响了后世钱乙、陈文中、曾世荣等医家。《诸病源候论》开“婴病治母”之先河,元代《格致余论》及明代《证治准绳》《育婴家秘》等均有“婴病调治其母”的论述[6]。
《备急千金要方》云“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7],强调了儿科的重要性。孙思邈是历史上首位系统论述小儿护养的医家,其《备急千金要方》涉论106首,合方534首,集唐以前儿科之大成,首列儿科专篇,其中,新生儿拭口、断脐、裹脐、择乳母法等均具有科学性。《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少小婴孺方上》《少小婴孺方下》《小儿痢第十》《小儿丹附》《千金翼方·养小儿第一》,皆是儿科的专论,将小儿疾病分为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痈疽、杂病7种。孙思邈注重下法,对小儿急症、热病等擅用大黄祛邪攻下。卞国本[8]认为,孙思邈“但有微恶,则须下之,必无所损”“若不时下,则成大疾矣,成则难治”的驱邪攻下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后世采用截断疗法治疗温热性传染病及急性病的理论基础。
现存最早的儿科专书《颅囟经》系自《永乐大典》中辑录而成,书中提出“凡孩子三岁以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9]。“纯阳”之说阐明了小儿生机蓬勃、发育迅速的生理特点。该书还提出“分为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的“一指定三关”小儿脉诊法,首创烙脐法治疗小儿脐风。《太平圣惠方》《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制“烙脐饼子”以预防脐风,后世的火烧断脐法,均是在烙脐法基础上的发挥。
宋代重视儿科,儿科的医学教育较隋唐有所发展,官方设立慈幼局来收养被遗弃的幼婴。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承前人基础,提出新观点,创制新方剂,从辨证立法到处方用药论述详细,是我国现存最早集儿科系统理论与病证诊疗方法于一体的儿科专著,标志着中医儿科学正式形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10]
《小儿药证直诀》指出,小儿生理“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11],又生机蓬勃发展迅速,骨脉、五脏六腑、神智等逐渐“变蒸”,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补充了小儿纯阳之说。后世吴鞠通“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小儿体质学说,便是在此基础上的阐发与丰富。钱乙首次把五脏辨证应用于小儿临床,创立了较完整的五脏辨证系统。诊断方面重视望诊,提出“面上证”和“目内证”,根据面部和眼睛来判断脏腑气血变化和虚实盛衰的五脏归属。钱乙注重顾护小儿脾胃,以五脏辨证为依据,同时“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11],或化裁古方,或创制新方,用以五脏补泻。《小儿药证直诀》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同时代的董汲、阎季忠及后世的张元素,其方论、医案、方剂等几乎全部被《幼幼新书》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收载。受钱乙影响最大当属明代医家万全。他提出“小儿之病,胃最多也”,根据钱乙五脏辨证说,悟出小儿五脏中,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钱乙所制方剂,如泻白散、导赤散、泻黄散等至今仍为临床广泛使用。
南宋陈文中在儿科方面注重温阳,强调小儿调护以固护阳气为本,反对初生儿即服金石寒凉之品下胎毒,以致伤脾败阳。提出“慢惊属阴属脏,当治以温”治疗小儿惊风、痘疹[12];对于痘疹,若妄投寒凉之剂,恐冷气内攻而难治,临床常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用温补之法。
发展时期
金元明清是儿科学的发展时期。此期中医理论体系日臻成熟,为儿科的辨证体系注入了新的内容,丰富了儿科治疗学。
金元四大家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推动了儿科学术的成熟和发展。河间“火热论”认为,“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13],小儿所患热病多,用药偏寒凉。对表证而兼内热,自制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表里分消;用凉膈散主治疹痘斑疮诸疾。张子和主张儿科疾病要速祛邪,兼顾脾胃,慎用汗、吐、下三法。他把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概括为“六易一弱”及“四病二源”,提出小儿调护之法,若已病,则提倡祛邪而不伤正的外治法。受道家影响,张子和总结出一系列心理疗法治疗“拗哭不止”等疾病,他沿袭河间之旨,对斑疹等疾以疏表清解。李东垣认为,小儿脏腑柔嫩,脾常不足,若不能充养正气则易受外邪侵袭,这也是其脾胃失调所致疾病的内在原因,故在治疗小儿杂病中善用升阳健运之法[14]。他所创补土健脾方药如补中益气汤、黄芪汤等为儿科所常用。朱丹溪认为,“人生十六岁以前……惟阴长不足”[15],重视养阴、护阴,对于多阳证、热证、实证的儿科疾病尤为必要。
元代儿科医家曾世荣认为,小儿疾病应分清表里寒热虚实,重视望诊要观其形气。他在钱乙急慢惊风分类辨证的基础上,把惊风细化,详述“四证八候”,即“四证者,惊、风、痰、热是也,八候者,搐、搦、掣、颤、反、引、窜、视是也”[16]。受张子和影响,他主张“攻邪已病”,多以发散外邪为主,其《活幼心书》论治43个病证,多以发散表邪为先,论方230首,发表之剂约五分之一,且临床运用极为灵活[17]。
薛铠、薛己父子的《保婴撮要》广泛采撷自《黄帝内经》至明初方书、医论。俞景茂[18]认为,薛氏父子学术思想源于张元素的脏腑辨证,又承李东垣、王冰、钱乙等人之说。薛氏重视脾胃,同时注重滋补肾命,用药偏于温补,常见补中益气汤与地黄丸合用。《保婴撮要》专列一卷详论小儿外科及伤科病证70余种。对小儿外科辨证,“当分脏腑所属之因,病之虚实,调其血气,平其所胜”[19]。薛氏治疗儿科疾病首重脏腑,配合经络辨证,根据辨证结果,以清、消、补、托等内治为主。
张景岳反对“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莫治一小儿”之说,认为小儿诊断比成人容易,“辨之法,亦不过辨其表里寒热虚实”[20],诊断须四诊合参,提出“阳非有余,阴本不足”,治疗上重视温补,扶助“方生之气”,选方用药强调保护胃气,慎用攻伐。
清代医家夏禹铸《幼科铁镜》中否定小儿望指纹的意义,认为其“不足以反映脏腑病变”。提出“望形审窍,自知其病”,注重望神色和苗窍以及“宝色”的辨别。夏氏以方药与推拿并重为特色,《幼科铁镜》列推拿为首卷,论述了小儿推拿、灯火的常用穴位与操作方法,强调“用推即是用药,不明何可乱推”[21]。《中医大辞典》谓夏禹铸“长于小儿推拿术……后世小儿推拿医生,多宗其法”[22]。
叶天士丰富了小儿温病辨证论治体系,认为小儿脾胃未充,脏腑柔弱,体属纯阳,易患伏气外感化热。主张用药轻灵精简,热病当顾护胃津。吴鞠通继承并发展了叶氏经验,认为“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以“稚阳未充,稚阴未长”概括小儿生理特点。对于温病之学,吴鞠通认为,小儿外感多由六气所致,治疗上多推崇叶天士,主张存阴退热,酸甘化阴,“调小儿之味,宜甘多酸少”[23]。
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24]5,善以补气、活血治疗儿科疾病。他悟出疳证和血瘀有关,小儿偏风、惊风、痿证属于元气亏损。对于麻疹,他提出“辨明瘟毒轻重,血之通滞,气之虚实”[24]15,在解毒的基础上兼以活血化瘀和补气。
民国时期,出现了奚晓岚、奚伯初、钱同增、钱今阳、钱宝华、杨鹤龄、古绍尧、徐小圃、单养和、吴克潜、施光致等儿科名家。这一时期医家承袭古人观点,对儿科理论进行研究总结,且受西学的影响,融汇新知,对胎毒、变蒸等深入探研,在幼儿护养、常见疾病的诊断及推拿等方面有所论述,认识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5]。如徐小圃擅用温药“温阳抑阴”,奚泳裳善取寒凉药清解热毒,救治重证病危患儿。
纵观中医儿科发展史,历经萌芽、形成与发展时期,理论渐趋完善,病种日益细化,治疗不断丰富,为当代中医儿科学提供了理论与临床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