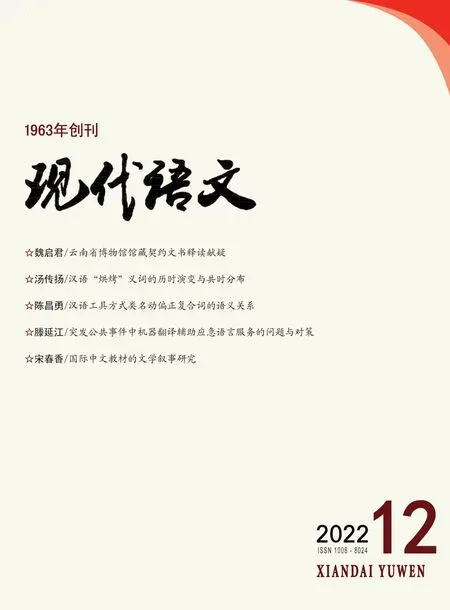“共衣”原始思维模式探析
——基于汉字构形角度
卢 艺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问题的提出
“共衣”,又称“同衣”,即穿同一件衣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共衣”是一个常见的文学主题,它是指有些人在某种特定情景或特殊心理下穿同一件衣服的行为,以表达一种亲密无间、同心同德的共情心理。中国人常说“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它是人们平时的必用之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衣”也是重要的表现媒介之一[1](P1)。而“共衣”不仅可以抒发情感,更是在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不禁令人深思:一件看似极为普通的“衣”,在文学作品中为何能够表达复杂的情感?为何“共衣”会产生“共情”之功效?本文拟从汉字构形角度,对“共衣”所体现出的原始思维模式表达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二、古典文献中的“共衣”
就目前的古典文献资料来看,“共衣”一词既出现在传世文献中,也出现在出土文献中。就相关内容而言,“共衣”共有两层内涵:一是可称为“同衣”,即两人或数人由于某种原因在特定场合穿同一件衣服;二是可称为“赠衣”,即两人或数人相互将自己的衣服赠与对方,以示关系匪浅。
(一)传世文献中的“共衣”
在传世文献中,“共衣”的文学主题应肇始于《诗经·秦风·无衣》。《诗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借衣抒情之诗,如《郑风·缁衣》《唐风·无衣》等。这些诗作大多囿于个人情感的抒发,缺乏一种能够引发“共情”的主题元素。而《诗经·秦风·无衣》的每章皆以“岂曰无衣”发问,以“与子同袍/同泽/同裳”来表达战友之间的深厚友谊,感情层层递进,体现出一种同甘共苦、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在物质匮乏、衣物珍贵的时代,有着“共衣”之情的战士,在战场上势必会齐心作战。朱熹《诗集传》云:“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2](P100)这无疑是《秦风·无衣》借“共衣”抒“共情”的现实缘起[1](P3)。
实际上,“共衣”在传世文献中并不鲜见,在春秋时期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3](P52)《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杜预注:“吴地贵缟,郑地贵纻,故各献己所贵,示损己而不为彼货利。”[4](P673)这里记载的是吴国公子季札和郑国公子子产之间惺惺相惜的赠衣故事,并留下了“缟纻之交”的千古佳话。可见,在这一时期,“共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
后代文学继承《诗经》,亦往往借助“共衣”来抒情或叙事。根据所共之衣的具体情形,可以大致将其主体情感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所共之衣为贴身之衣,这时大都是表达爱情之真挚。如三国魏曹植《种葛篇》:“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5](P81)西晋傅玄《秋兰篇》:“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回翔。君其历九秋,与妾同衣裳。”[6](P70)二是所共之衣为外袍或裘衣,则大多是表达同袍之情或同胞之谊。如明代陈子升《烛影摇红·与友人感旧》:“与子同衣,紫骝嘶入花丛里。”[7](P59)这里是化用了《秦风·无衣》的诗句,表达出词人和友人风雨与共、砥砺前行的思想情感。
(二)出土文献中的“共衣”
除了传世文献之外,我们在出土文献中也能见到“共衣”一词。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行》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凡且有大行、远行,若饮食、歌乐、聚畜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
关于这里的“衣”“同衣”应如何解释,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秦简牍合集(贰)》中的注释云:“衣,寝衣,即被子。《论语·乡党》:‘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集解引孔安国曰:‘今之被也。’”[8](P508)刘乐贤认为,此处的“同衣”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衣”为寝衣,即被子,夫妻同被可能指夫妻同房;二是亦可理解为夫妻二人穿同一件衣服,即妻穿夫之衣或夫穿妻之衣[9](P154)。吴小强认为,此处的“同衣”可有四解:因贫穷而同穿一件上衣;因男女私情而共用内衣;同被而眠,隐喻同房之事;按古汉语同声相训原则,同衣即同一,指夫妻身体合一[10](P93-94)。
沈祖春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衣’在此处非指‘被子’也,而是借指人的‘形体、身躯’。”[11](P116)作者还指出,《汉语大词典》“衣服”词条的第二个义项就是“借指形体、身躯”。他还从文化学角度找到了衣服代指身体的直接证据: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请求刺击赵襄子的衣服,以象征刺杀赵襄子本人。由于沈祖春的观点有理有据,因此,笔者赞同沈氏的解释,认为《日书》甲种《行》篇中的“衣”应是借指人的身体、身躯,“同衣”是指夫妻同房。而其他解释或过于牵强附会,或与“夫妻同房”之意相左,实不敢苟同。
事实上,衣服不仅与身体联系紧密,而且朝夕相伴。因此,用衣服代指身体,使其成为身体的象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人们共穿一件衣服,就代表着他们的身体发生了某种联系。而这种身体上的联系又象征着共衣之人的深厚情感(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这就是“共衣”能够产生共情效果的逻辑推导轨迹。因此,这种借指不仅在出土文献秦简《日书·行》中解释无碍,对传世文献中的“共衣”也同样适用。
三、从汉字构形角度看“共衣”之“衣”
众所周知,汉字具有表意性。早期汉字的构形和词义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汉字的构形以体现词义为目的,词义是汉字构形的主要依据,二者在汉字里是相互统一的[12](P76)。由此可见,汉字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总是侧重于从意义的角度与语言建立联系。早期的汉字构形,特别是甲骨文、金文字形,往往反映客观事物的形态。但这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复刻,它们是经由人脑加工过的,反映了造字者的认知信息。这就为我们利用汉字构形去探索先民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可能[13](P46)。《说文解字·衣部》:“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凡衣之属皆从衣。”后世多从许慎之说,认为“衣”在造字之初即表示衣服。值得注意的是,许慎主要是依据小篆形体来推测汉字的构形理据,而构意越是早期就越直接、越具体[14](P45)。因此,研究汉字造字构意,应将其最初形体作为研究对象。
甲骨文作为汉字的早期成体系的文字,其构意中蕴含着先民的思维特征,在构形上具有图画性、直观性的特点[15](P95)。就此而言,要想揣摩先民的思维方式,甲骨文构形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在甲骨文中,“衣”字可以写作“”“”“”“”“”等。其中,“”“”两种字形很难判断它们像“衣”之形。尤其是“”“”的下半部分“”“”,无论是向左勾还是向右勾,都已不再是“象襟衽左右掩盖之形”。因此,不少学者依据于“衣”的甲骨文字形,对其本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澱咸主张“衣”的本义是“围猎”,“象张网捕兽之形”[16](P87)。胡氏之说主要是基于“”等甲骨文字形所作出的推测。不过,“”“”“”“”“”“”等字形,却不似捕兽之网,又该如何解释呢?同时,“衣”的本义如果是“围猎”,也很难由此引申出常用义“衣服”。
华强则指出,“衣”的本义应是“胎盘”。作者认为,“衣”的甲骨文字形,展现的是远古时代人们剖腹产时剖开胎盘的具体方法:先横着剪一刀,然后垂直方向再剪第二刀,形成一个“T”形刀口,这样就可以很安全而且顺利地取出胎儿。当胎儿取出以后,胎盘的形状就是“衣”[17](P7)。对于这一解释,笔者不敢苟同。虽然古代典籍中有上古时期妇女剖腹取子的记载,但多为神话、传说,不可尽信。上古时期,医疗条件极其落后,一方面,剖腹取子对母体或胎儿来说,均风险极大;另一方面,由于工具的限制,剖腹取子的可操作性也较低。如果“衣”的确是剖腹之后的“胎盘”,它又在甲骨卜辞中屡次出现,说明在当时社会中剖腹产并不罕见,这却有悖逻辑与常理。
笔者认为,“衣”的本义应是“胎盘”“胎衣”。不过,我们的根据却与华强有所不同,理由主要有五条。第一,“衣”的甲骨文字形“”“”“”“”“”“”,确实是像胎衣之形。这些字形中所共有的奇怪的“尾巴”(无论是否有钩),应该就是指的将胎儿与母体相连的脐带。“”“”“”等上面的纹饰部分,可以看作是胎盘上的血管。至于“为何‘衣’这个胎盘有缺口”这一问题,华强认为是剖腹取子留下的“T”形刀口,笔者则认为这个“缺口”实为胎儿突破胎膜、脱离母体而留下的。这是女子生孩子时自然留下的痕迹,而不是刻意用刀切出的“T”形缺口。第二,根据甲骨文卜辞的相关内容,可以找到将“衣”释为“胎盘”的例证。如《甲骨文合集》14019:“贞:妇婐娩嘉,惟衣。二告。”其中的“衣”字为“胎盘”义,将其解释为“胎盘脱离”,也是符合该卜辞辞义的。第三,“衣”由“胎盘”“胎衣”义发展引申出“衣服”义,是符合语义发展顺序的。第四,在我国古代典籍中,特别是古代医书中,多处称“胎盘”为“衣”。明代江瓘所撰《名医类案》卷十一:“一产妇产后面赤,五心烦热,败血入胞,胞衣不下,热有冷汗。思但去其败血,其衣自下。”[18](P604)此处的“衣”即是“胎盘”。第五,在现代多地方言中,仍将“胎盘”称为“衣子”“衣包”等。如西南官话中,称“胎盘”为“衣子”“衣包”;中原官话中,称“胎盘”为“衣包”“衣胞得”“衣布袋”;晋语中,称“胎盘”为“衣衫衫”等。
将“衣”释为“胎衣”,也很好地展现了古人以“共衣”来“共情”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造字之初,“衣”的本义为胎衣;在它构意泛化之后,就可隐喻身体。胎衣本身即为身体的一部分,并且是生命之初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后来的使用中,以它来代指身体,自在情理之中。如此看来,“共衣”“同衣”是含有同胞之义的,“共一胎衣”也必然会用来表达亲密无间、深厚无比的情感。
需要指出的是,“共衣”“同衣”之“衣”并不需要释为“胎衣”,这里的“衣”仍是表示衣服,借指身体。笔者主要是从汉字构形的角度,分析为何“共衣”能够表达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厚情感。可以说,“衣”的本义为“胎衣”,折射出这样一种原始思维模式:即上古人们是选择共“衣”而不是“共”其他物品来表达情感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后世家族中仍存在“共衣”现象。《宋史·姚宗明传》:“河中姚氏,制成男女衣服各一架,由家众任意取用,不分彼此。”这里的“共衣”之“衣”虽然并不指代身体,但是其“共衣”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因为是一家人而‘共衣’”,依然包含着同族之亲的因素。也就是说,“共衣”亦可隐喻同族之亲。
上文曾提到最早表达“共衣”主题的《秦风·无衣》,以直白朴素的语言,颂扬了毫无血缘关系的战士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情怀。结合“衣”之本义为“胎衣”,更能说明为何此诗中的“同袍”可释为“同胞”。表面上来看,在气候酷寒的西北之地,“我”与“你”共穿一件衣服,足以表达同甘共苦之情。实际上,在秦人的原始思维中,共穿一件衣服,就将其视为同一胎衣而生的亲人,自然会亲如同胞兄弟。至于之后“共衣”“同衣”发展出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密之意,与上述原始思维模式在逻辑上并不矛盾。“共衣”所表达出的意义重在“感情深笃、关系匪浅”,是由“衣”字本义“胎衣”的隐喻投射而产生出来的。此处的“血缘”义是用来形容亲近的程度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将“衣”中的“血缘”义抹去,而适当扩大其“亲近”义的使用范围,亦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语义扩展路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古文字构形角度出发,通过对甲骨文字形的分析,认为“衣”的本义为“胎衣”。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中医古籍中,我们也找到了“衣”用作“胎衣”的例证。在如今的很多方言中,仍然保留着“衣”当“胎衣”讲的用法。也就是说,“衣”表“胎衣”“胎盘”义,古已有之,并且一直沿用至今。需要指出的是,“衣”的本义自身就蕴含着“同胞”之义,这也是“共衣”最为原始的文化内涵,为后世以“共衣”抒“共情”奠定了原型模式。随着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语义的不断扩展,“共衣”亦可用来表示其他亲密的关系。总之,古文字与原始先民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构形理据的背后更是蕴含着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这也为破译古代社会生活、阐明原始观念内涵、获取相关文化信息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