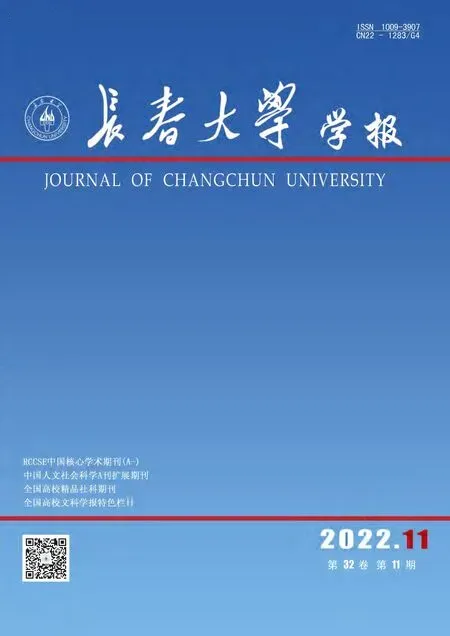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关于自然主义批评的道德话语探析
宋虎堂
(兰州财经大学 商务传媒学院,兰州 730101)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产生于法国的自然主义在英国得到了传播。综观自然主义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20余年的传播与接受,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的评价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大多数评论以道德为主导话语对自然主义进行价值评判。故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然主义在英国遭到抵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所呈现的创作观念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道德相悖。如英国学者弗斯特(Lilian R. Furst)等认为,自然主义之所以引起英国批评界的道德斥责,就在于其作品中运用的肮脏手法与表达的沮丧观点[1]。中国学者高建为则认为,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使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受阻[2]。诚然,道德对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进程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但问题的关键是,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的评判为何多以道德为切入点?其道德话语背后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就文学批评而言,话语通常是在思想传播和意义制造中的一种言说规则和范式,内含批评依凭的表达方式与范畴形态,且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若将研究仅仅停留在道德现象表层,实际难以揭示出道德话语的深层指向及其言说规则。鉴于此,本文拟从自然主义的“道德”指向入手,围绕英国批评传统、创作实践、思想文化与自然主义的关系展开论述,深入阐析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中道德话语的外在表征与内在症结。
一、自然主义的“道德”指向与英国文学批评传统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法国自然主义作品在英国的翻译出版,关于自然主义的批评接踵而来,自然主义倡导者左拉及其作品更是成为了被谴责的标靶。如英国批评家斯威布恩(Swinburne)尖锐地指出,英国人没有人会不顾道德地去印刷自然主义(左拉)的“恶心玩意儿”[3]。《环球》(TheGlobe)杂志上的文章宣称,左拉的书是“危险的润滑剂”,破坏了人性的天真,腐蚀了道德本性,而《伯明翰每日邮报》(TheBirminghamDailyMail)声称,左拉几乎就是在不道德中打滚[4]1145。国会议员史密斯(Samuel Smith)则指出,自然主义对青年的道德观念造成了可怕的影响[5]352。那时出现的嘲讽自然主义的漫画,甚至将左拉与猪猡、厕所等置于同一画面中[6]。类似的道德谴责可谓铺天盖地,不绝于耳。如此,在如何看待自然主义是否道德的问题上,有一个重要且容易误解的问题需要澄清,即自然主义所谓的“道德”具体指什么?
翻阅文献,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并未对道德问题进行过专门阐述,只是在阐述自然主义时有所涉及。例如,在《戏剧中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左拉指出,“对作品中的道德抱与个人无关的态度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7]。在《实验小说论》中,左拉又指出,若远离真实,就谈不上道德和高尚,只有“表达真理的作品才是伟大的和道德的作品”[8]。结合自然主义理论可看出,在作家身份方面,自然主义主张,作家不应是一位道德家,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自己的所见客观地描述并呈现在读者眼前就可,道德与否应留给读者去评说。在文本效果方面,自然主义主张,只有表达真理的作品才算得上是道德的,小说创作是否道德与其真实性紧密相关。概言之,自然主义的“道德”以真实为基点,侧重于客观再现,要求作家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不是制定一种社会性的价值标准,也不是标榜一种个体性的行为规范,更不是宣扬一种契约性的伦理观念。因此,随意地说自然主义道德或者不道德其实有失公允,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如何看待文学所具有的道德属性更为重要。就此追问,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与自然主义的道德有何关联?
针对自然主义的道德问题,英国学者怀特利(C.H. Whiteley)曾著文进行了阐述。在怀特利看来,道德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从心理学的角度,将道德当作个体信息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从社会学或政治的角度,道德主要描述如何将其应用到一个社区居民品德的所有方面。以这两方面为出发点,怀特利将心理学上的道德界定为“在个人意识和行为上的一种特定的品德”[9]23。在社会学或政治学方面,怀特利认为“道德依据来自于适应和接受的规则,……(道德)存在于品德中的自发行为惯性地与符合于来自任何动机与约定的习俗相一致”[9]23。结合批评不难发现,自然主义作品涉及的“道德”既与怀特利所阐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息息相关,也与怀特利阐述的心理学上的道德亦紧密相连。由此可推断,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道德将自然主义作品的艺术修辞、美学特征进行了意义同化与价值同构。或者说,自然主义作品的主题指向与英国当时的道德意识进行了机械捆绑。
笼统来讲,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或“真空式”的存在,而是承载着某种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符码。英国19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大力发展,在为英国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拜物主义、金钱崇拜等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衰落、社会分化以及宗教信仰动摇等问题。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巩固统治,维护其阶级利益,在政治、文化、生活中高举道德的旗帜。尤其是,“维多利亚主义”道德风尚的推行,使英国在精神信仰层面稳固现有秩序的同时,在思想行为上几乎“没有人能够逃出被道德审查的命运”[10]。因而,此种情形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英国批评界对文学的整体看法、认知维度和评判标准。那么,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的评价为何对“道德”情有独钟?
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曾指出:“道德传统理论总是欧洲文学批评传统中最为反理论的一种,在英国特别盛行。”[11]文学道德批评传统是否反理论姑且不论,但从道德角度审视文学却是英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方式。无论是18世纪英国小说兴起的时代,还是19世纪中后期英国小说成熟的时期,关于小说应承载道德意识的批评观念就贯穿其中,如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理查逊等皆主张将道德标准和美学标准相结合。19世纪中叶,《北不列颠评论》《爱丁堡评论》《民族评论》《都柏林评论》等一些英国的知名刊物刊载了大量的关于小说道德的文章,这些文章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注重小说的道德功能,将小说视为道德教诲的工具,小说构思应受到道德目的的支配[12]。这说明,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问题是英国文学批评关注较多的一个层面,小说的形式内涵似乎唯有统辖于道德才有价值,道德话语便成了当时英国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言说准则。这自然影响到对自然主义的价值评判。
二、自然主义与英国文学的“道德”向度
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强调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将社会道德标准与个体情感趣味统筹为一种体现审美价值的文学实践。故此,19世纪后期道德话语的主导倾向,使“发表作品的男男女女不可避免地总要起教育或陶冶公众思想的人所起的作用”[13],小说家担起的职责其实是教育家的职责。彼时的许多英国作家将小说创作与实际生活紧密结合,时常在道德层面对人与事进行评说,以艺术的方式展示英国社会的道德困境。其中的意图,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状况,劝导人们崇尚高尚的德行,一方面是为社会道德的发展需要服务,对读者的道德取向起到指导作用。
细细盘点那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家,艾略特、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等人的小说无不承担着道德训诫的功能。狄更斯的小说“履行了道德说教者的崇高职责”[14]。艾略特的小说“与其说是生活的图景,不如说是道德的寓言”[15]。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非常重视大众读者阅读趣味的培养,因为“阅读趣味承载的不仅仅是日益觉醒的中产阶级文化意识,更是合法化自身‘文化正确性’的有效手段”[16]。更重要的是,流动图书馆作为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重要传播媒介,在文学审查上强烈排斥“在主题或手法上逾越良好‘趣味’,而违反道德的任何作品”[17]。与此对应,丁尼生、卡莱尔、艾略特等一批作家在当时被视为一支强大的精神道德力量,在不经意之中成了读者崇拜坚信的对象。这些作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如丁尼生对家庭和爱情观念重要性的强调,卡莱尔为遵循上帝的旨意而努力工作的信念,狄更斯对慈善行为和同情心的提倡,艾略特对道德伦理的推崇等,成为英国广大读者身体力行的指南。
截然不同的是,自然主义文学借鉴自然科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理论,以实验方法对人的生物肉体进行科学解剖,其所传达的主题倾向会对英国的社会道德观有所冲击。这促使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社会性价值的关注,超过了对其文学性价值的关注。当自然主义被视为影响维多利亚晚期社会稳定的精神文化产品时,英国批评家“明确反对这种正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小说,一个反应特征是对性行为描写的厌恶”[18]。这从侧面反映出自然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污秽文学”的症结,其落脚点就在于自然主义作品中大胆具体的性爱描写。事实上,当时许多英国作家虽已意识到性爱在文学中的审美功能和文化价值,但是迫于社会意识的种种原因,对性的描写极为节制和含蓄,并使之符合道德说教目的。如萨克雷的《名利场》对蓓基所涉男女私情问题的隐晦处理,明显受到维多利亚时期道德风尚的影响和限制。与萨克雷不同,哈代虽然在《德伯家的苔丝》《卡斯特桥市长》等作品中对性问题(确切地说是情欲问题)有所书写,相比左拉来说也要含蓄保守很多,但依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相反,法国自然主义作品中的性描写:一方面注重描写具体的、可观察的性行为,专注于人的动物性,与英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实不相容。一方面,自然主义在性道德上的非个人化处理和纯理性倾向,与维多利亚文学呈现的艺术批判性不相兼容。尤其是,为塑造纯粹的民族灵魂,英国将16世纪以来的清教道德观发挥到了极致,即使以私通来弥补婚姻上的感情损失,也不能公开谈论被斥为不道德的性。这使自然主义作品所呈现的主题意义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取向形成错位对立态势。因而,在英国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话语系统中,英国批评家依据写实的范畴标准对自然主义的否定批判,使“自然主义”外化为一个用来否定道德的贬义词,其接受自然会受到干预。
譬如,1885年,英国国家治安协会(National Vigilang Association)因担心自然主义威胁社会稳定,发行了《有害的文学》(PerniciousLiterature)的小册子,将自然主义视为“有害的文学”[5]351,并采取措施进行压制。流动图书馆作为英国文学的“检察官”,不仅左右着当时的出版政策,还管控着英国小说情节主题等的呈现,对小说的出版进行严格审查。与英国本土文学相比,作为外来文学的自然主义在审查上则更为严格。典型的事实是,在英国翻译出版左拉小说的出版商亨利·维特泽勒(Henry Vizetelly),被视为传播有害文学的罪魁祸首,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较之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英国批评界普遍认为,在法国自然主义作品中几乎缺乏英国社会所需要的保守文化观念,更不用说道德文化的背离了,正如批评者克劳福德(Emily Crawford)所言,“左拉的物质主义是危险的,因为他所有好的方面都是以一种坏的方式呈现的”[19]。1888年,左拉的小说《土地》在伦敦出版时之所以引起了一阵抗议风暴,就在于小说中离奇古怪的暴虐行为令人恐怖,对农民残暴行径的赤裸裸描绘,触犯了资产阶级的道德尊严和精神诉求。说到底,在英国主流文化的主导下,自然主义小说作为一种影响客体,其所呈现的文本形态令英国批评界难以接受,被攻击的理由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不约而同地受到了道德层面的谴责,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进程也受到了阻碍。
三、自然主义“道德”的宗教浸染与功利致用
有学者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话语中心是宗教,它涉及所有的问题,以及精神指引的路径”[20],此言虽显绝对,但不无道理。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密不可分,宗教及其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诉求,成为道德话语的重要表征。
维多利亚后期,英国最重要的宗教事件无疑是福音主义宗教文化运动。宏观来看,批评界对福音主义的看法尽管存在一些纷争,但福音教派以独特的信仰体系影响着英国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内涵,且影响到当时英国作家的创作。维多利亚后期的小说:要么将人物塑造成与罪恶抗争的虔诚信徒,如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塑造了坚守个人信仰的福音派教徒布尔斯特罗德;要么重视女性的德行品格与个体修养,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的牧师克莱尔,因重视妇女而被称为真正的福音派教徒;要么对福音派提倡的人性美进行赞扬,如狄更斯《双城记》借《新约》对人性之美进行褒扬。
在福音派的文化浸染下,基督教在那一时代虽然暂且式微,但仍未失去作为一朝道德风尚和精神寄托的功能性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将宗教信仰(尤其是新教),纳入了国家的民族性”[21]。将宗教信仰纳入国民性,实际上意味着宗教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文学创作和世俗生活方式的影响,促使一种宗教意识扩展为社会道德形态。因此,英国学者安德鲁·朗(Andrew Lang)敏锐地注意到,与左拉在俄国等国相比,左拉在英国遭到阻碍、忽略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太走运的清教,哎呀!阻止我们去理解左拉和自然主义的乐趣”[4]1142。这表明,当某一时期社会的宗教倾向与某一文学观念产生“背离”或“间距”时,与此相关的作家作品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压制。
史实表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传播,使进化论观点成为英国知识生活的一种显性话语,而进化论科学的传播,促使人类在从精神蒙昧向科学实证迈进的同时,给根基深固的宗教信仰也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19世纪英国许多作家诸如萨克雷、狄更斯、哈代等人都在作品中对科学话语有所涉及。自然主义主张以实证的观念、科学的态度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其作品中或隐或现呈现的进化论思想及其观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流传,对传统的有关人与自然、宗教超自然等种种观念有所影响,这显然与宗教立足于虚幻想象的基本精神观念相抵牾,这也印证了英国文学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的抨击在所难免。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与宗教的亲缘关系,使得文学承担起一部分宗教行使的功能。问题在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为何要承担宗教的功能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小说何以成为小说的问题,其核心就在于小说有何用途。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曾谈到,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是“带给人自知之明”[22]。在布尔沃·利顿(Earl Lytton)看来,小说的成败在于它是否能“激发令人愉悦的情感”[23]。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则指出:“小说的目的应该是在使人愉悦的同时给人教益。”[24]从此类观点不难发现,不论小说的用途指向何方,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宣扬小说的道德训诫息息相关,由此注重小说的实用功能便成为了维多利亚晚期诸多英国作家所赞同的主张。况且,就民族性格而言,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辉煌使英国有些夜郎自大,而讲究实用的物质主义则使英国对外来文化保持谨慎态度。那么,维多利亚晚期为何尤为注重小说的实用功能呢?
细究历史,自然主义在英国传播的时期,正是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盛行的时期。功利主义主张任何事物的合理性取决于其用处,实用的才是合理的。在文学批评领域,功利主义在当时不仅成为确立小说体裁最有力的依据,而且为强调小说的实用功能提供了哲学的方法论支持。譬如,英国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就认为,“艺术的全部生命在于它是否符合真实,或者真正实用”[2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则从侧面指出,英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存在不足,就在于其“很少停留在纯粹智性的范畴内,很少与实用目的脱离”[26]。很明显,功利主义的文化氛围与着意强调小说用处的维多利亚文学十分合拍,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话语的折射反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遭遇阻隔,其主题思想被意识形态化,其审美艺术被道德误解、遮蔽,与功利主义不无关系。这意味着,与宗教的道德表征一致,“功利主义”同样是作为小说道德话语的重要表征而存在的。
就社会影响而言,英国国家治安协会将自然主义视为“有害的文学”,实际上指向的就是文学“有用”或“实用”的问题。自然主义文学是否“有用”,功利主义所提倡的“实用才合理”的观念,实际上成为了评判自然主义的潜在的重要标准。这样,维多利亚时代那些被主流文化认为具有实用性的文学,才有可能在文学类型、意识形态、审美接受的互动中形成和解关系,更好地传递出英国社会所需的精神观念。虽然我们不能随意地说,英国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对自然主义的批评具有主导性的影响,但在功利主义的思想语境中,英国批评界评判自然主义的道德话语,与强调小说实用的思想主张具有内在的共通性。
耐人寻味的是,自然主义作品在英国道德语境中的传播和接受,却没有完全削弱其本身的审美艺术价值,这一点正如英国学者阿尔玛·伯德(Alma W. Byrd)所言,“左拉的作品因为道德的原因被扔到一边,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位小说家的作品为他在文学中伟大道德的力量赢得了一个位置”[27]。对文学交流而言,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虽然受到英国社会道德话语的制约,但由英国功利主义而引致的急功近利心态,对外来文化文学的接受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一味地从实用或物质主义的角度来审视文学,并不利于英国文化异质性和文学多样性的形成。
四、结语
总而言之,维多利亚晚期以道德为主导的批评话语,影响着英国关于自然主义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言说,其背后的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更加值得关注。反思历史,检视英国自身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生态,英国批评界对自然主义的谴责批判,彰显出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对道德话语的坚守,凸显出以道德为价值导向,以宗教福音主义、功利主义为道德话语表征的文学接受机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自然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进程,制约了英国文学对新的艺术形式的吸收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