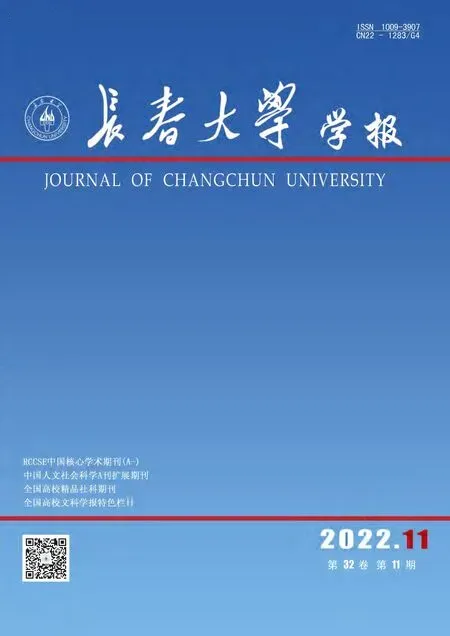苏童笔下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
——谈《河岸》与《黄雀记》
邢玉丹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
苏童是当代著名的先锋小说作家,他的作品也在新历史小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因此他的小说一直都具有容纳各种冲突、矛盾与悖论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他在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所完成的作品不仅显示了先锋小说特有的冷峻文风和深邃内涵,还更清晰地展现了新历史小说独到的读史眼光和观察角度。令人感兴趣的是,苏童90年代以来写作的长篇小说中,“历史”越来越成为一抹浅淡却无法擦掉的背景,作家似乎不再把重心放在对抗革命历史小说基本观念的一般新历史小说的另类历史观和新型叙事策略上,而是专注于在宏大的历史将要淡出人们的记忆之际,从现实中把它召唤回来。
一、对历史的追问方式:缺席的在场或徘徊不去的幽灵
无论是书写20世纪50—70年代生活样态的《河岸》,还是书写改革开放后社会状况的《黄雀记》,苏童都采用了相同的针对历史的追问方式,即把历史变成“缺席的在场”和“幽灵的复归”。在这里所谈的“历史”仍然是宏大叙事意义上的历史。苏童写的是当下的现实,但这样的现实始终与历史紧紧相连,它被历史决定,受历史影响,潜在的历史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抑或强大的保护伞,它是不在场的在场,不断地为现实背书。同时,历史中的死灰沉渣、流风余韵甚至是部分创伤记忆并未被彻底埋葬,也许人们未能与之很好地告别,致使它们像幽灵一般徘徊不去,时时复归。苏童用这种方式对历史进行追问,表面上刻画现实,实则是在为没有被妥善安放的历史喊魂,如此既增加了小说描绘现实时的历史纵深感,又饱含着对过去的反思和批判。
(一)历史遗产与债务的继承者们
《河岸》中作为背景的历史其实是主人公引以为傲的革命史,这段革命史以及成为烈士的母亲邓少香决定了主人公的父亲库文轩的干部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直到有一天,库文轩作为烈士遗孤的身份被怀疑和否定,他迫不得已将自己放逐到船上,远离了河岸。变故发生前,他是革命历史的切切实实的受益者,继承了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历史遗产,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它。但一场针对烈士遗孤的调查把他变成了河匪封老四的孩子,他的人生轨迹立刻陡转,他连带着自己的儿子库东亮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遗产顿时成了债务,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而在《黄雀记》里,最初求死不成的祖父本想“活一天赚一天”,稀里糊涂地生存下去,结果突然莫名其妙地“丢了魂”。为了找回自己的魂,他不得不求助于祖宗,要找回祖宗的尸骨。于是在寻找尸骨的过程中,陈旧的历史便被翻了出来,有关祖父的前史(父亲是汉奸,爷爷是军阀)自然地牵涉到了那段避不开的革命史,一段反帝反封建与土地改革的历史就以这种吊诡的方式呈现自身——“祖父挖掘手电筒的路线貌似紊乱,其实藏着逻辑,他无意中向香椿树街居民展现了祖宗的地产图。”[1]14革命之后,祖父只能继承历史的债务,由富家子弟变成普通人,而且子孙命途多舛,遭遇各种各样的不幸。
历史就这样在现实的人身上显形,每个人都是历史遗产或债务的继承者,而这样的继承是以先辈的消逝/死亡来决定的:邓少香的牺牲为库文轩带来了半世荣华,也给了他被众人抛弃的风险;祖父的祖宗们大概是为革命暴力所吞噬,让祖父丢了魂而无处寻觅。苏童的小说中,历史并不真实在场,它只属于过去,但它又时刻在场,决定着人物的前途命运,也构成了叙事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之一,这是苏童的新历史小说与其他同类小说的不同之处。一般认为,最典型的新历史小说为了抵抗革命历史小说中表现的强大的历史理性,会格外强调个人、偶然与无意识。在这些作家们的笔下,个人似乎成了历史的对立面,成了被历史强行影响的“受害者”,或者我行我素,完全无视滚滚向前的大历史车轮。但苏童的小说暗中承认了所谓的历史理性、历史逻辑对个体的塑造,历史在个体的身上打下的烙印不可忽视,个人始终被历史所裹挟。有评论者也曾质疑:“当面对社会结构中的历史时,个人的生命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去拥有自律性,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理性对话?”[2]苏童的小说表明,个人命运的自转律是在历史的公转律基础上运行的。既然人人都是历史遗产或债务的继承者,那么个体要理清自己的小历史(出身、家史等),也就必然触碰更宏大的作为时代主潮的大历史。
(二)关于历史追责的错位
问题的关键是,谁有资格享受历史遗产,谁应该偿还历史债务?这其中的责任由于历史进程的错综复杂而变得并不那么清晰明确、一目了然,常常存在着错位的情况。
《河岸》里的库文轩因为不再被认可为烈士邓少香的儿子,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干部沦落为船夫,他儿子库东亮也在一夜之间被抛出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变成了“空屁”——这个绰号生动而充分地说明他没有分量、不受待见,是迟早要被甩出正常秩序的杂质。河上的船员们都是有污点有问题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当时的弃民,被流放在河上,成为那个年代的“多余人”,而库文轩和库东亮也加入了这样的队伍。父子二人经历了命运之神的捉弄,想反抗却找不到出路,因为对邓少香后代的调查本身就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一切都悬置起来了。最后人们发现邓少香并无后代,当初她带着的孩子是从别处抱来的,寻找历史遗产的继承人变成了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也造就了库文轩父子的人生悲剧。“父亲坐在木盆里,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呜咽起来,想想我这辈子,我不甘心,我能甘心吗?他攥紧我的手,一边呜咽一边问我,我坚持了十三年了,等了十三年,我等到了什么好消息?我等到的都是坏消息啊,谣言、诽谤,还有阴谋!”[3]渺小的个体即使饱受责任错位的折磨也只能落一个“不甘心”,而血气方刚的库东亮在遭遇了种种不公之后被逼着喊出“秋后算账”这个历史任务。我们热衷于“秋后算账”,却从未彻底清理过中国20世纪的历史遗产与债务,有时甚至分不清是遗产还是债务,对于革命的看法也经常矫枉过正、对历史的叙述也颠来倒去,论争不休。
后革命时代,我们不宜再采用非黑即白的判断模式,不能因为厌恶革命暴力就不加思索地为地主翻案、否定革命,也不能因为革命的积极意义便盲目鼓吹革命的绝对正确性。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谁来继承遗产,谁来负责债务,谁有资格享受遗产,谁有责任偿还债务,这其中充满了混乱和错位。在错位处,历史的幽灵便会造访,迫使人们为它找魂,像《黄雀记》中的祖父执拗地寻找祖宗的尸骨那样。祖父追问“历史遗留问题”(到曾经是自家地界但如今已经是别人家的地界上挖掘遗骸)时,就有声音反对:“谁在翻旧社会的老黄历?现在是新社会……地皮房子都是政府的,政府给谁就归谁了!”[1]13祖父的追寻变成了一个笑话,一种由天翻地覆的历史所制造的黑色幽默。中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革命,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亏欠和债务根本追讨不清,遗产也分配得并不完全公正,这种错位在大历史中毫不起眼,但能够影响个体的短暂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到,苏童的小说里,“历史”变成了一个外在的庞然大物,“人民创造历史”的因果关系由此倒置成了无意识无逻辑的历史“怪兽”在支配着个体生命,个体只能顺从而不能反击。这里面隐含着神秘的宿命论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童有关历史追问的暧昧书写。
二、奇怪的书写效果:被消解的故事张力
读《河岸》《黄雀记》或者苏童触及历史的任何小说,都会油然而生一股不满足感,一股深深的压抑之感,总觉得他没有写透,在回避着什么,拒绝不顾一切地捅破最后那层隔膜。《河岸》与《黄雀记》这两部小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开端都极有戏剧张力,构思巧妙,立意不凡,对人性的洞察达到惊人的深度,对历史的反讽也深刻而富有意味。《河岸》讲述一个烈士后代忽然不再被认为是烈士后代的故事,将人为的革命和天然血缘的传承联系起来,也将蔑视血统、打破固定等级的革命与携带先天优势的血亲关系结合起来,如果深挖下去,这将会是一个多么有冲击力的故事。《黄雀记》开篇就以祖父丢魂、寻找祖先而拉开民国历史帷幕的一角来吸引读者,若进一步思考,也会诞生一部更好的小说。可是在这两部作品里,苏童偏偏更关心库东亮的性成熟和他对慧仙的单恋,偏偏关心保润、柳生与白小姐/仙女的三角恋情和犯罪始末,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这就使得一开始的故事张力在随后的叙述中慢慢消失。
苏童尤其喜欢表现个体与历史的纠缠不清,更喜欢将年老一代的这种撕扯和年轻一代的成长结合在一起。年老者坚持与历史残留物撕扯到死,如库文轩背负邓少香的纪念碑投河自尽;年轻人试图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却在上一代的牵绊下扭曲了心灵,个人的成长并没有顺利地达到目标,如库东亮遭遇性压抑,保润见识了人心的险恶残酷。苏童的这两部小说涉及了两代人乃至三代人,他更关注的是新一代的命运。在他的笔下,老一代已经找不到出口了,但新一代人仍然左冲右突,寻找出路,但碰来碰去都是壁。苏童自己也好像在两面石壁间狭窄的缝隙里写作,他没有足够的力量破壁而出。他的书写总是暧昧不明,刚刚有了一点强度又很快弱下来,他在文本的最关键处没有选择正面强攻,反而以其特有的非常抒情化的笔锋轻轻荡开。
王德威承认苏童这个作家十分擅长讲故事,但他也敏锐地察觉到,“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 ‘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淘空了的”[4]。《河岸》与《黄雀记》都有着沉甸甸的开头,却有着轻飘飘的结尾。小说的开端惊艳绝伦,令人眼前一亮,之后便愈发疲软,草草收场。例如《河岸》,“它总是在历史批判与青春成长的意义指向之间摇摆。对诗意的追求压倒了政治反思性,压抑了历史批判性”[5]。苏童果真宁可让诗意冲淡了思想的强度吗?或许,他追求的不仅仅是“诗意”,作家的写作一定还受制于另外的局限因素。我愿意把苏童的小说称为“半部经典”,它们总是有力地开启一个丰富的空间,却不带领读者遍览其全貌。于此,我更想分析苏童为什么要采用那样的暧昧书写,为什么要以那种方式消解掉作者苦心经营的难得的故事张力。在我看来,这与小说中主体的合法性危机有关。
三、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身份不明与心理崩溃
这里所讨论的“主体”是阿尔都塞提到的被询唤的主体,也可以看成黑格尔意义上的获得了承认的公民。主体一定要臣服于某种意识形态,将自己从游离的个体状态变为接受规训后的主体,而一个人要得到其他人的承认,才能不被抛出社会,他的存在才因此有了合法性。更多的时候,合法性来源于历史的认证——历史能够为主体的现实存在提供合法性,它不仅提供经验和教训,还在无形中证明主体“理所应当”“不言自明”地处于怎样的位置。所以,若一个人要确认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他就要从自己的历史中查找渊源。苏童笔下的人物正是由于其个人历史的不确定而遭遇了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河岸》里的库文轩不是邓少香的儿子,库东亮和他一同陷入身世的焦虑,这种焦虑始终飘荡在他们的生活中;《黄雀记》里的祖父因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的“罪恶”家族史也许已经被砸烂),如今该怎么安放自己,便呈现出“丢了魂”的状态。
(一)悬浮的主体
人生在世总要找寻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意义也是主体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若挪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念,意义的生成是由关系和位置决定的,那么主体生存的意义也由他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处的位置来决定。历史给人安全感,帮助确证主体的位置,而历史一旦失去了确定性,或者干脆被摒除、清空,主体便会感到危机。所以,“身份不明”“来历不明”是一件致命的大事,特别是在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人那里。《河岸》中库文轩不停地写信给上级,要找回自己作为烈士后代的身份,可以说,邓少香的个人史就是他的生命前史,当这个身份受到质疑,他的主体位置便岌岌可危。《黄雀记》中的祖父一心要找出祖宗的尸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他探寻家族发展史的过程,但是他的家族史早已被革命洪流冲垮、击碎,他只能保持着“丢魂”的样子。
祖父丢了魂,进而变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住进了精神病院;库文轩的精神也出了问题,整个人变得古怪又自闭。苏童总会把这样的人写成精神病,是他们的身份不明造成了心理崩溃。拉康认为,精神病的根源在于找不到所指的能指。这类患者的“症候……生成于心理内容(所指)与它的象征之物或符号之间的断裂”[6],因此精神病实际上是一种失语症。如果说主体存在的合法性是所指,是主体孜孜不倦的诉求,那么一个确定的身份就是恰当的能指,它的丢失会产生悬浮的主体,被搁置在半空中没有着落。找不到关系与位置,词汇就没有自己的意义,同样,在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之下,一个被剥夺了身份的人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历史,因为对他来说历史是一团迷雾,就像库东亮抬头看天,想从天上看出历史,却发现天上并没有,于是他认为历史是个谜。祖父想找的“魂”,或许就是一个主体位置的确认,找到了,他的精神病也就治好了。
(二)从失败到失败
苏童笔下的男性都是由血缘传承的几代人,但年老者被历史紧紧地缠绕,年轻者受到前辈阴影笼罩和现实成长压力的双重夹击。他们是忧郁的,既担负着上一代的遗留问题,又找不到合理的成长途径,其身心发展是畸形的,布满创伤的。库东亮、保润和柳生都是如此,忧郁又多情,却不知怎样以合适的办法表达,常常把好事变成坏事,最后真的坏了事。男性的主体位置承续着父辈的失败,同样有合法性危机。但女性在这方面更加特殊,苏童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来历不明的,她们都是被收养的孩子,与上一代并无血缘关系:慧仙和白小姐/仙女彻底不知其主体位置,她们在成长过程中就显示出乖戾、任性和随意性来。
两部小说里,年老者只顾着对付历史,年轻者还要面对当下,迎接未来,但他们的路注定要走得歪歪拧拧,甚至误入歧途。那么,合法性危机的主体如何坚定地走下去?书里的几名主要人物都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不能制定明确的成长计划,也无法笃定地按照自己设想的道路向前行进。他们都有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遇事就逃避问题,或用不当手段解决眼前的困难,处理突发情况总是显得惊慌失措、毫无理性。他们出于本能也挣扎过,可挣扎是无用的,他们只能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四处碰壁,结局惨淡。
这些人物的失败来源于其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也给苏童的小说染上了颓废和压抑的色彩,促成了他消解故事张力的暧昧书写——小说写到最后,什么都没改变,实质问题都被含混过去,既没有酣畅淋漓的大团圆也没有令人心痛的大悲哀,作家的文字在事件的惊险转弯处轻松地滑过。因为主人公们根本没有强力意志去解除危机,也不能强势地突入生活、拥抱生活,创造新的可能,找到可替代的方案。苏童给予了他们这种无路可走的围城困境,在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之下,身份不明造成了显性或隐性的心理崩溃,那些人物被卷入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复杂性里面,有什么更好的应对办法呢?
四、结语
90年代以来,苏童的长篇小说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追问,但总是潦草收尾,没有取得令人惊艳的突破。但至少他一直在探索,有学者这样评价:“‘历史’的异质性包括种种‘历史碎片’在写作主体意识中交替、更叠,不仅造成苏童小说特有的层次感、节奏感、构造感,而且衍生出不同凡响的叙事结构方式和叙事母题体系。”[7]的确,在苏童的构思与书写中,历史化为碎片,成为他不可能放弃的观照重点,这样的写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将历史的异质性释放出来。但即使有了独特的叙事结构方式和母题体系,苏童也应该更注意长篇小说的完整性和完成度,那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努力方向。在此,作家面临的其实是如何巧妙解决笔下主体位置的合法性危机的巨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