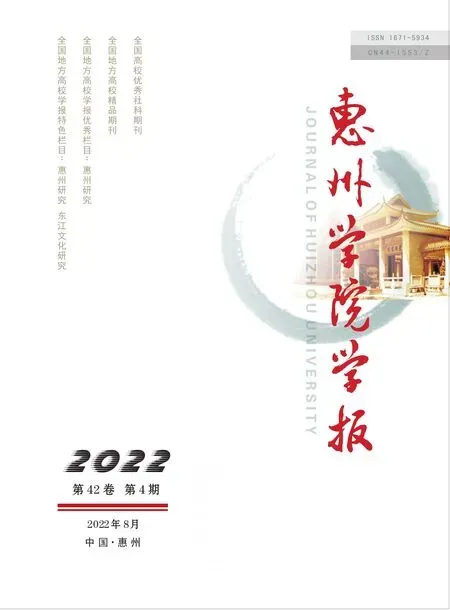从现代性反思视角看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1
唐慧丽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主要集中于辜氏英文著作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文名《清流传》)一书。该书出版于1910年,此时“戊戍变法”(1898年)已过去十二年,但辜氏批判的矛头仍然指向康有为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戊戍变法”对中国君主政体的破坏作用。至于后期康有为政治立场的转变,如康有为对复辟的支持,辜氏在著述中均未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因康有为支持复辟的言行晚于辜氏《清流传》的出版;另一方面,《清流传》一书的主角是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党,辜鸿铭将张之洞所倡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试图向西方介绍晚清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如何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受西方现代文明的侵袭,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现代文明的逼迫下,节节败退,从而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纳入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因此,《清流传》可以说是辜鸿铭为全世界的传统文明、文化保守主义唱的一曲“挽歌”。基于这两点,辜氏对康有为的批判也就集中于康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变革上——二者对于传统文化根基的破坏。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后来又有黄兴涛所译中文译本,名为《中国牛津运动故事》,载于黄兴涛所编《辜鸿铭文集》中。辜氏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并未引起学界注意。关于辜鸿铭与康有为的研究成果虽多,但鲜有学者留意到辜氏的这一批判,就笔者目力所及,尚无专论对此展开论证。将辜、康二人并举、对比研究的专论,只有一篇——何晓明著《破解“历史的怪圈”——康有为、严复、辜鸿铭合论》[1]1-7,但该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规律出发,剖析三人思想轨迹演化的根由,也未涉及辜氏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
辜鸿铭与康有为同为晚清文化名人,两人的文化思想分别代表着晚清两种不同的思想潮流。分析他们的文化分歧,至少具有以下三种意义:其一,以两人的文化分歧为个案,可从中管窥晚清思想史,中西文化互渗互融、既对抗又涵融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其二,探讨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是否有其合理性,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借鉴;其三,辜氏将康有为比喻为中国的“罗伯斯庇尔”,辜氏独特的“比附”手法素来为人所诟病,认为其有简单比附之嫌(如朱维铮等)[2]185-198,那么,辜氏的“比附”是否一无是处?笔者希望通过具体个案的探讨做出自己的判断,以期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提供参考。本文先概述辜、康二人的文化分歧,再分析二人文化分歧的原因,最后论证辜氏的批判是否具有学理上的依据,从而总结辜氏这一批判的价值与意义。
一、辜鸿铭与康有为的文化分歧
在辜鸿铭所臧否的同时代的政治文化人物中,他对康有为的批评尤为激烈,称康有为“庸俗粗鄙”“恶毒暴虐”[3]123“卖弄博学、怀有虚假的理想主义”[3]130(凡文中所引辜氏英语原文,皆为笔者所译,以下不再另作说明)。辜鸿铭评价人、事,皆从其道德视角出发。对于个人之评价,往往先对其行为动机作道德上的审查。凡出于高尚道德之目的,即使所作所为造成了一定的错误,在辜氏那儿也可以得到尊敬和谅解,如张之洞。尽管辜鸿铭反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但因服膺张之洞的个人品质之故,辜氏在其幕府供职达二十年之久。同样,对于康有为及其学说,辜鸿铭首先也是进行道德审察,认定康有为派“由那些聪明的、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自称是爱国者,其实虚荣、沽名钓誉,野心勃勃,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判断能力。他们要求挖根掘底的彻底改革和和像火车一般的飞速进步,丝毫不考虑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甚至不惜毁灭帝国。其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西方的财富、权力、和荣耀。他们无知的认为这一切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想以此满足自身的虚荣和野心”[4]5-6。如此,辜鸿铭首先从道德动机上就否定了康有为。
除了道德动机的否定,辜、康两人的文化立场、政治主张基本上背道而驰。其文化分歧主要有二:一是两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看法的分歧。辜鸿铭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深受阿诺德、卡莱尔等人的影响,对物质文明的痼疾深有体会,他将物质等同于道德的对立面,将二者置于两个相反的极端,对物质的追求便意味着对道德的背离。因此,整个欧洲现代文明,在辜鸿铭处等同于物质实利主义,他称之为“食肉怪兽”——不仅是“一战”的根源,还是一切道德文明的摧毁性力量。而康氏则对西方物质文明充满赞叹、艳羡。其二,两人对政治体制看法的分歧。辜鸿铭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康有为则提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他比较西方的三权分立与清政府三权合一的利弊:“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承责,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5]424,并得出结论:甲午前,国人认为“泰西之强”在于财富兵力,甲午之后,则认为“泰西之强”在于学校、知识,“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5]115”。因此,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把定三权以变政体作为变政的首要目标。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在辜鸿铭那儿则是寡头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在《西洋议院考略》中(该文收录于辜氏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辜氏以一种几乎戏谑的口吻考察欧洲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由来,称西方诸国的议会制起源于群酋之会。所谓酋长意即欧洲封建社会的诸侯、城邦领主。君主立宪制则是因为英国国王对各城邦征赋无度,诸侯们遂群起而攻之,逼国王订立盟约,是为英国之《自由大宪章》。上议院的成员多为世族,下议院的成员多为平民,英国国王集会,令下议院派捐,议会不允,乃引发战争。辜鸿铭把议会制定义为利益争夺的结果,又举法国为例,称法国仿效英国设议院、弑国君后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削弱君权的议会制俨然成了欧洲战乱的根源[6]。辜鸿铭写作此文的用意显然是针对康有为的改制说。
二、辜鸿铭、康有为文化分歧的原由
辜、康二人之所以有此分歧,在于二人对“文明”“进步”的理解不同:在辜鸿铭那里,衡量某一文明或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准,在于该文明、国家的道德教化程度;在康有为那里,则是以物质繁荣为准绳。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序言里,开篇即提出:评估某一文明的价值,不在于这一文明所创造的宏伟辉煌的城市,不在于其所建造的马路、高楼、家具、工具等物质产品,也不在于这一文明所具备的创造这些物质产品的能力,而在于它培养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这就把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指向道德人格的塑造,前面一大段的否定句式正是对现代文明以物质为标准的反驳。而康有为则相反——“文明之发达,皆视其时势之承平为比例,时愈平,民愈富,物质乃大发,文明乃愈进”[5]33。从不同的文明观出发,两人对英国的评价天壤之别:康有为赞叹英国的物质进步,“实为地球千万年来文明势力增长所未有也,则物质之为之也[5]73”,“同在欧人之中,其国之物质最进者,其国亦特出于欧洲群雄中而最强。夫论二三百[年]来,德、法之哲理新学何减于英?[5]73”而辜鸿铭却看到英国物质繁荣背后的道德沦丧。他抨击英国人只讲求实惠,把物质条件、生活水平当作衡量文明的标准,“生活水平”“物质水平”只是文明的“条件”,而非文明本身[4]178。
导致二人文化分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辜鸿铭在中西文化批判上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全盘肯定儒家文明,全盘否定欧洲现代文明。正是这种“一边倒”的方法论,使得辜鸿铭对公认的传统文化糟粕,如纳妾与缠足——也充满赞赏。同样,在这种方法论主导下,儒家的君主专制自然也成了他理想的政体形式。除此以外,辜氏对君主制的推崇还源于其老师托马斯·卡莱尔的影响。卡莱尔认为,秩序起源于人类对宇宙自然的敬畏,由敬畏而产生的尊崇是秩序得以形成的起点。卡莱尔将这种崇拜称之为“英雄崇拜”,认为这是人类的本能。由此出发而展开的人类历史实质就是一部“英雄传记”[7]1。卡氏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宗教起源的实质。人性的脆弱在面对神秘莫测的宇宙自然时,会产生恐惧、惊慌,由此想象出来的“神”或“上帝”,是脆弱的人性希求依靠时,在外部世界形成的投影。卡莱尔所谓的“英雄”,就如同上帝,是理想人格的神化,自身力量的外化。“英雄”即深谙宇宙秩序与法则之人,而宇宙秩序,在卡莱尔等浪漫主义者看来,即道德法则。故“英雄”亦是人类的道德榜样。“英雄”大致可分为六类,“君王英雄”则是各种英雄主义人物的总和,也是英雄主义的最后一种形式。故“君王英雄”既是道德秩序的缔造者,又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同时还是人类的道德榜样。在人类彼此能形成的关系中,最为道德的关系则是统治与服从。服从“君王英雄”的统治即忠诚的美德。这样一来,君主便成了德与智的化身,以君王为中心所建立的秩序,是符合宇宙之法则的道德秩序,由此,便论证了君主制的合法性[7]330。
辜鸿铭在儒家的圣君之治里看到了卡莱尔对“君王英雄”的憧憬,从而将儒家的君主专制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政体形式推向西方世界,并认为相较于西方的议会制——由各种利益集团形成联盟行使国家权力,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却能摆脱这种集团私利的羁绊,建立公平、公正的道德秩序。在尊崇君主权威的基础上,辜鸿铭又提出“文明国家”的观点,认为文明国家有其道德根源,是人类“出则孝,入则悌”的情感产物。从“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第十二章》)开始——即,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始于夫妻之爱,由爱自发的生成各种道德关系,从而构成整个道德秩序。因此,臣民对皇帝的尊崇也始于热爱,而非迫于利益关系的强制遵从。君主权威也就相应构成整个道德秩序的中心和基石。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正是由于君主权威的被破坏[8]51-54。在这种政治文明观的主导下,辜鸿铭对于康有为效法西方的维新变法自然会激烈反对。
三、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
因二人文化的分歧,辜鸿铭对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辜氏把康有为比作中国的雅各宾派:“马太·阿诺德说:‘对于过去的强烈不满,抽象的革新体制的一股脑作用,一种见诸文字、精心入微炮制出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的合理社会: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法。’也是李提摩太牧师和那些自称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极为赞赏的康有为的做法”[3]32-33。这段对雅各宾派的批评用来指责康有为,其要点有三:“对过去的强烈不满”,指责康有为摒弃传统;“抽象革新体制的一股脑作用”[3]32,指立宪体制的激进与草率;“一种见诸文字、精心入微炮制出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的合理社会[3]33”,指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辜氏对康有为的批评是否击中了康有为思想学说的软肋?康有为的激进学界多有共识,与康同时代的严复等人对康的做法也不表赞同。康有为在呈给光绪帝的奏稿中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9]224。欧美三百年所缔造的政治制度中国要在十年中完成,这是否可能?更遑论中国还没有与欧美政体相应的文化传统。这种一味追求速度的激进自然会导致革新体制的“抽象”——即,落不到实处。如当时康有为的地方自治民主改革,据领导了乡村运动的梁漱溟说,乡民投票,一致反对禁止缠足[10]196。正如学界所达成的共识──当时之中国,民智未开,千年封建统治之下未能有接受民主制的思想、心理条件,故革新体制只能是“抽象”的一纸空文。辜鸿铭斥其“抽象”可谓一语中的。
对比之下,还可以发现,康氏与雅各宾派的首脑人物罗伯斯庇尔确实有相似之处:两人在个性上一样以道德救世主自命,康氏的大同社会与罗氏依卢梭学说所要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也有相似之处,尤其是二人都表现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倾向。萧公权指出康有为认为“只要人主对其子民关顾,他可以用任何适当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更重视思想控制”[10]288。此论断一语中的。且看康有为对于王霸之辨的分析:“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己,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9]3,接着又区分“开塞之术”:“殛四凶,塞之术也;举十六相,开之术也。式商容闾,表比干墓,开之术也;诛飞廉,杀华士,塞之术也”,而“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9]3。显然,在康有为那里,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凡是“肫肫于为民者”就是王道,凡是“规规为私者”便是霸道[9]3。而为了实现王道,即便是“诛飞廉,杀华士”[9]3这类杀戮手段也可以采用,这是典型的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主张。这一主张还表现在康有为的政治实践中。例如,为了给自己的变法制造理论依据,他把孔子改装成“素王”,又把古文经学皆斥为伪经,并武断的说:“传经只有一公羊”[11]。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可以篡改历史事实甚至杜撰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把日本天皇于庆应四年颁布《五条誓文》一事说成是明治元年,并添加原文中没有的句子。为使光绪帝命自己设局编书,他又杜撰一个日本副岛种臣主持编书局并携带书局归野的故事[12]310、313。这些做法,用辜鸿铭的话说,就是“耶稣会教义卑鄙无耻的精神——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精神”[3]xxvii。所谓的“耶稣会教义”源于“耶稣会”。“耶稣会”亦称“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依纳爵·罗耀拉初创于巴黎,1540年获教宗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而成立……其产生背景是回应16世纪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即天主教会为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设立。不同于传统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取消了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以便容易融入现实生活。因此,其修会的宗教活动不是“遁世”而是“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对之施加影响……耶稣会成立后的一大使命,即积极参加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其重点是向亚洲和美洲传教[13]78。如在中国就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著名传教士。耶稣会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干预,招致了多方反对,树敌众多。辜鸿铭也是反对者之一。加之耶稣会的宗教工作又经常与世俗的商业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拉瓦莱特神父一案。拉瓦莱特神父自1742年起领导耶稣会在法属马提尼克岛的分部,因当地土地的收成和捐款满足不了传教的开支,拉瓦莱特神父借了高利贷,参与商贸活动。为了盈利,他与竞争对手一样开展种植业并使用奴隶。1752年拉瓦莱特神父因非法经营的罪名被告上法庭[13]83。对于一向反对欧洲物质主义文明的辜鸿铭来说,拉瓦莱特神父的行为,自然是“只要目的高尚(传教),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包括买卖黑奴)”的卑鄙行径。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批判主要见于其英文著作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中,其面对的读者是西方文化人士,因此,为了使西方人更理解中国的国情,辜氏采用其惯用的“类比”手法,将中国的文化现象、文化人物在西方文化中寻找对应物,从而消除文化隔阂,引西方人士共鸣。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另一方面,也将辜鸿铭针对中国近代文化问题的批判,纳入了世界反现代化思潮的视野中,从而使其文化批判具有了世界文化史的价值。在此处,辜鸿铭敏锐的发现了康有为、罗伯斯庇尔、耶稣会教士三者之间的相似性——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背离,为道德之目的采用不道德之手段。
在欧洲长大的辜鸿铭,亲身感受过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雅各宾派执政期的暴力与血腥更使其把法国大革命视为人类文明的“洪水猛兽”,对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犹有余悸。所以,一旦发现康有为与罗伯斯庇尔无论在个性上、思想上都有相似之处时,他自然对康氏痛恨犹切。他自然担心康有为的变法会在中国掀起一场与法国大革命一样的暴乱。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在其进入救国委员会,大权在握之后,进一步把卢梭的道德理想付诸政治实践——凡是阻挡他的道德救赎的,他一律施以“道德清洗”。作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在其演说中这样描绘其理想中的道德共和国:“共和国的政治是自由和平等;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和国所要维护和保全的是国家的生存。共和国的宗旨是道德;共和国的信仰是最高主宰;至于公民方面,彼此间的一般关系是博爱,他们的德行是诚实,是思想的纯正,社会活动的安分守己,是有利于国家而不是有利于个人”[14]232。然而,所有这些神圣的名词都可以用作“道义方面的罪行”来处罚异己党派:如“保王党和贵族的被控,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吉伦特党的被控,是以共和国不可分割的名义”[14]232。不仅如此,罗伯斯庇尔还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节日,这十个节日都是以某种道德品质命名,如最高主宰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等。在道德的名义下所采取的手段却是非道德的杀戮与血腥:1794年,在罗伯斯庇尔的支持下,“牧月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14]236,自“牧月法案”通过后,“成批的人被送上断头台,每天有将近五十人被处死,这种空前的恐怖局面延续了近两个月久[14]238”。可以想见,在欧洲见证过法国大革命的辜鸿铭自然会担心,如果康有为所依赖的光绪帝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如果康有为可以独操权柄,以他的刚愎自用,对自己学说坚定不移的信仰,对独裁统治的饰美,难免不会像罗伯斯庇尔一样用流血手段来完成他的改革。辜氏的担忧不能说毫无道理。
至此,不难理解自视甚高的辜鸿铭对同时代人向来多有贬词,连其上司张之洞也遭到他的讥嘲。但是,何以对康有为、袁世凯痛恨最切?原因正在于,他认为康、袁是彻底摧毁中国古老道德文明的罪魁祸首。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使中国知识阶层进一步意识到必须改革和学习西方。这为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提供了契机,维新派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也相应的由洋务派的“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这使得辜鸿铭对中国的前途更为担忧。在他看来,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要使“中国全盘欧化,中国的全盘欧化意味着输入粗鄙和丑陋”[3]34。康有为所推行的制度改革——君主立宪,动摇的不仅是满清王室,而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即,民众的道德信仰——对君王权威的尊崇。对中华文明而言,君王是秩序的中心,一旦这个中心被摧毁,则民众的驯良、自治等民族性都将被摧毁。一旦没有了对权威的尊崇,没有了道德信仰,西方物质文明的实利主义必将乘虚而入,从而使原本驯良、恪守道德准则的民众变为“群氓”。“群氓”一词是辜氏从马太·阿诺德处援引的概念,意即民众身上所潜伏的、为满足其膨胀的物质欲望,摧毁一切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力量。辜鸿铭痛心疾首的预言:“真正的灾难……不是这场革命(笔者按:指辛亥革命),而是革命以袁世凯当上共和国总统而告终,这就意味着群氓已将整个中国践踏在脚下。袁世凯……即群氓化身”[3]xxi。显然,在他看来,袁世凯的上台标志着中国古老道德文明彻底被西方物质实利主义摧毁。为此,辜鸿铭灰心之余才寄望日本,企望日本能发扬儒家道德文明。
既然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都遭到了辜鸿铭的否定,那么,辜氏解决中西文明冲突的方案究竟是什么?他的方案其实就是道德教化。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里,辜鸿铭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把西方物质文明对中国道德文明的侵蚀比喻成西方的有轨电车要进入上海。阻止电车的方法有四:一是站在马路中间,逼迫电车停车,如果不停,则以拳头和血肉之躯与电车对抗,哪怕被电车碾得粉身碎骨,这是端王及其义和团成员的做法;二是在上海创立一个对立的电车公司,与西方的电车竞争,这是张之洞等洋务派的做法;三是消极抵抗,洁身自好,不贪图电车的舒适享受,不乘坐电车,这是托尔斯泰解决中西文明冲突的方法。辜鸿铭认为这三种方法都不可取,最好的方法是第四种:找到一个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中都有德望的人,由于他的正直的品质赢得了民众的敬重,他可以激发民众的道德力量,号召民众都不去乘坐有轨电车,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第六十三章》)[3]134-141。辜鸿铭的方法实质是道德教化,通过道德人格的塑造来自觉抵制物质欲望的诱惑。因此,辜鸿铭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际,仍然要求中国放弃抵抗,作一个“君子民族”,以中国固有之文明的道德魅力折服西方蛮夷,使之自觉归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四、结语
从辜鸿铭对康有为的批评,以及辜鸿铭解决中西文明冲突的方法,不难看出他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视角的局限性。他分析任何问题都从道德视角出发,不顾具体历史情境,把所有具体的、政治的问题都依赖于抽象的道德予以解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天真的道德理想主义。道德固然是一种力量,固然是秩序得以维系的基石,然而,道德只能为人类言行提供最终的、形而上的价值判断,并不能取代具体历史情境中,各种不同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在分析中国近代文化问题方面,辜鸿铭的确表现出几分不通世务的天真,难怪张之洞说他“知经不知权”(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然而,在道德视角之外,辜鸿铭更多展现出来的则是对现代性、现代化批判的真知灼见。从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拉开现代化进程的序幕到今天,人类迈入二十一世纪已然又过去了二十年,现代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许多辜鸿铭当初的预言已成为今天的现实,如物质主义、信仰危机等。现代性引发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反思——中西文明,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将何去何从?又该何去何从?现代性危机,作为全球化背景下所滋生的共同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这种时代命题下,再回顾辜氏当年的思想主张,不得不感叹他的远见卓识。他对康有为的文化批判,集中于两点:一是物质主义;二是激进主义。这既是康有为思想的误区,也是现代性危机的表现。从“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激进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旋律。辜鸿铭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与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可谓“不谋而合”。王元化先生认为,对“五四”不能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起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15]131”,并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所流行的四种观念都值得反省,一是庸俗进化观点;二是激进主义;三是功利主义;四是意图伦理。所谓“激进主义,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15]127”,今天看来,正是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极端态度,使得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被激烈反对、彻底否定。即使“‘五四’对庄、墨、韩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利用庄子中的反孔观点),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实验主义)”[15]127。上述观点,都指出“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危害更应引起警惕。而早在晚清,康有为开始其“维新变法”之初,辜鸿铭已然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力量,其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尽管辜鸿铭没有提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成熟方案,但能够从儒学中寻找解决方案,说明辜氏已经看到了儒学之于现代文明的价值,指出了儒学现代化或“化”现代的方向,可以说,他是中国范围内最先反思现代文明之负面性的思想先驱,代表了中国文化语境中最初的现代性反思。他把康有为与罗伯斯庇尔进行对比,分析了两人个性人格、思想主张的相似性,不仅在批判方法上独树一帜,更将中国的现代性反思纳入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中,从而使其文化批判具有世界文化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