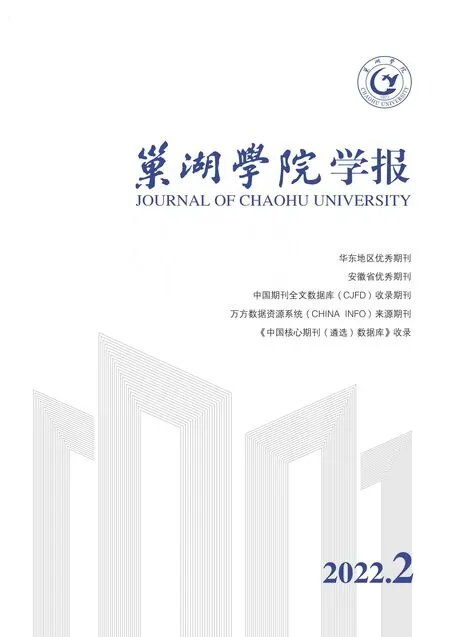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并称考论
周晓宇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引言
同一时期齐名并称的文人往往有交游酬唱的经历,如“竹林七贤”山林宴饮,“文章四友”应制赋咏,“元白”互寄诗作而成“通江唱和”,但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却非如此。四人两两间有好友同僚,亦有素昧平生,但绝非联系紧密的文人群体。因此,探究自唐以降四杰并称形成以及其作为文学群体地位变化的原因,相较于诗人行迹和情感关系,更要关注当时以及后世读者群的视角。当前学术界对四杰并称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诗文创作的角度寻找四杰的共通点[1-4],其二是从唐代文学的整体发展进程考察四杰的历史价值[5-6]。前辈学者的观点多聚焦于初唐这一时段,忽略了初唐四杰“王杨卢骆”之称并非一朝一夕间形成,而是经历了后世诗论家漫长的认识过程。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梳理“王杨卢骆”并称的形成过程,初步考察随着诗学理论的发展,这一文学群体如何逐步被确立为初唐文坛的代表。
一、唐时并称与负面评价
唐代已有并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现象,但是此时四人的排名次序还未固定。最早的记载见于中宗朝,郗云卿奉敕搜集骆宾王诗文汇成《骆宾王集》,他作集序云:“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7]景龙二年(708)杜审言离世,宋之问作《祭杜学士审言文》谓:“……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由运然也,莫以福寿自卫;将神忌也,不得华实斯俱。”[8]这两段文字虽重点不同,郗落脚于文辞才华,宋感叹身世坎坷,但都肯定了中宗时王、杨、卢、骆四人已获声名,并同为“四杰”“四才子”。郗、宋的记述离四人逝世不过数十年,或可推测四人在世时已有齐名并称之事。
进一步看,郗、宋提及四人的顺序并不相同,且均未明言排序依据。至开元年间,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提到了裴行俭评判四杰的标准:“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8]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标准,谓:“及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勮,曰:‘二公后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等四人,以示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勃等虽有才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者!杨稍似沉静,应至令长,并鲜克令终。’卒如其言。”[9]张、刘笔下的裴行俭重器识而轻文艺,将道德品性置于文辞才华之上,这是典型的选官标准。自《旧唐书》《新唐书》记载裴行俭评四杰后,史书的权威性使得“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影响甚广。尤其是在宋代,时人引用时毫不求证,深信不疑。但是细味上述两文对四杰人生终点的预判,颇有神化裴行俭识人之明的倾向,令人怀疑张、刘叙述的真实性。姚大荣在《跋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书》中亦有同感:“自张说徇裴氏之子请为作佳碑,妄许前知。新旧二书更增饰其词,滥加称誉,尤为失当。今考其实,行俭生前恐无轻蔑四子之语,后因四子盛名不获大用,斋志以殁,嫉才者乃饰为预料不终之言,归之行俭典选时评断。”[10]
关于裴行俭评鉴四杰之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王勃传》记:“初,吏部侍郎裴行俭典选,有知人之鉴……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必当显贵。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果如其言。 ”[11]《唐会要》卷七十五《藻鉴》记:“裴行俭为吏部侍郎,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为之延誉,引以示裴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余并鲜能令终。 ’”[12]《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记:“善知人,在吏部时……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嘿,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13]以上记载与张、刘所述基本无异,很可能取材于张、刘之文,都将此次人物品评系于裴行俭在吏部主持铨选考试之时。《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记:“(总章二年)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14]卷二百二记:“(调露元年十一月)癸末,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14]由此可知,裴行俭自总章二年(669)至调露元年(679)为吏部侍郎,接下来则要考察四杰在这一时段内的行迹。
总章二年(669),王勃因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南下入蜀;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在新都尉任上;骆宾王在东台详正学士任上。咸亨元年(670),王勃因病辞谢时选,在梓州、益州等地漫游;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秩满辞官;骆宾王罢东台详正学士任,随军出塞。咸亨二年(671),王勃仍在蜀地;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离开蜀地返回洛阳;骆宾王身处西域。咸亨三年(672),王勃返回长安,作《上吏部裴侍郎启》;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居太白山下;骆宾王从军西南,平定姚州之乱,还长安后又奉使巴蜀。咸亨四年(673),王勃求得虢州参军;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病情加重,淹留长安;骆宾王成都军中任职。上元元年(674),王勃匿罪奴曹达,事泄当诛,会赦除名;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居长安求医于孙思邈;骆宾王成都军中任职。上元二年(675),王勃不应朝廷官复原职,赴交阯省父;杨炯待制弘文馆;卢照邻病卧太白山;骆宾王年底离蜀返长安。仪凤元年(676),王勃南行渡海,溺水卒;杨炯应制举,补校书郎;卢照邻病卧太白山;骆宾王在武功主簿位上一年,不应裴行俭表荐。仪凤二年(677),杨炯任校书郎;卢照邻病卧太白山;骆宾王服母丧。仪凤三年(678),杨炯任校书郎;卢照邻移居东龙门山,后又于具茨山下买园舍;骆宾王服母丧。调露元年(679),杨炯任校书郎;卢照邻居具茨山,病痛缠身;骆宾王母丧服阙,调长安主簿,旋升御史台侍御史。由上述分析可见,总章二年(669)至调露元年(679)间四杰行迹几乎没有重合,实在没有一同参加铨选的可能①这部分内容参考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的张志烈《初唐四杰年谱》与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的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
为何文人、史官会选择相信这一虚构之事?裴行俭与四杰并不可视为孤立的个体,而应当看作宫廷和宫外两个群体的代表。四杰早年虽颇有仕途野心,但随着坎坷、失败接踵而至,少年锐气也消磨殆尽。王勃因斗鸡檄文被赶出沛王府,漫游山野间,时常“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15](王勃《春思赋》);杨炯弘文馆待制有十六年之久,中年又受从父弟叛乱牵连被贬,自嘲“二十年而一徒官,斯亦拙之效也”[16](杨炯《浑天赋并序》);卢照邻不仅仕途坎坷,中年染疾后病痛缠身,见病梨树犹引桓温语叹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16](卢照邻《病梨树赋并序》);骆宾王进取之心强烈,现实的碰壁使他选择了揭竿而起,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仕途坎坷的四杰与一路顺畅、身居高位的裴行俭有着截然不同的心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他们对生活、生命会有更深刻细腻的情感体验,而这些独特的生命意识反过来也促使四杰自觉地疏离政治中心。王勃自蜀地返回长安后,因文名多次被征召,但他屡次不应,并《上吏部裴侍郎启》开篇解释是担心由于不当言论招致灾祸,“诚恐下官冒轻进之讥,使君侯招过听之议,贵贱交失,恩爱两亏。所以战惧盈旬,迟回改朔,怀郑璞而增愧,捧燕珉而自耻。”[15]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已与九年前《上刘右相书》中的“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15]迥然不同,反映出王勃对当局朝政的失望与不信任。骆宾王亦是如此,《新唐书》卷二百一《骆宾王传》谓:“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13]四杰作为底层官员,始终未能触及正统政权的核心,而他们对儒家理想的坚持、对现实不公的愤懑则使自己彻底成为了高官显贵圈子的局外人。
这种宫廷与宫外的隔阂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亦体现在文学观念中。宇文所安在《文化唐朝》一文中提到:“专事庆祝颂扬的宫廷文学富赡华美,中国传统中一种持久的倾向是对华丽辞藻的怀疑,宫廷文学的修辞与这种倾向正相冲突。”[17]以虞世南、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创作进入高宗武后朝并未衰弱,依然引领着当时的文化风尚,但四杰对此种潮流望而却步。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述当时文坛之弊:“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16]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更是直言上谏,要求恢复雅正之道:“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15]卢照邻亦是王勃革新主张的支持者,杨炯记曰:“薛令公朝右文宗,讬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16](《王勃集序》)查阅四杰早期的干谒之文,或许会认同四杰革新主张“是从宫廷内部斗争的现实出发,并为宫廷政治服务的”[18]论点,但在占据四杰大半人生的京阙外生活中,曾经强烈的参政愿望逐渐被对“时、才、命”的思考取代,“迹均显晦,妙合虚无。同至人之体道,亦随时而不拘。……似君子之从容,常卷舒而不滞。……固自然以见体,托行潦以凝质。类达人之修身,故不欺于暗室。”[16](《浮沤赋》)对个体与宇宙、人生与历史的感悟使他们不再囿于当时当世,这是宫廷诗人难以感同身受和汇入笔端的,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注定了四杰与宫廷文化的易道殊途。因此,裴行俭评四杰实际上传递了两个讯息:其一,高宗武后时期主流的宫廷文学与宫外文学是彼此抵牾的,前者以高官贵族构成宫廷诗人群体,后者则由底层官员、普通文人等寒士平民组成,人生遭遇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时意象心境和艺术风格的差异,彼此都认为对方才是“华而不实”,本质原因不在于文风,而在于立场;其二,低官寒士往往位低名卑,泯没于历史,但四杰却因少年得名、声扬四海而有其独特性,即使身居下等官位,他们的号召力也远比普通寒士更大,自然被推到台前、视作宫外文化的代表,宫廷文化对宫外文化的排斥也就理所当然地通过对四杰的贬低来实现。
二、位次初定与两个组派
唐人将四杰视为一个文学群体的现象如上所述,但四人内部排名直到宋时才逐渐固定下来。有唐一代至少有四种并称方式,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述四人顺序为“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郗云卿《骆宾王集序》中谓:“卢骆杨王四才子”;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王杨卢骆当时体”;李商隐《漫成五章》中以小代大,谓“王杨落笔得良朋”。仔细考察以上四种并称方式,除郗云卿外,皆列王勃于杨炯前,这或许与杨炯自己的观点有关系。《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杨炯传》谓:
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11]
杨炯对王勃的尊崇实际上是当时一大批追随者的写照,“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择。近则面受而心服,远则言发而响应,教之者逾于激电,传之者速于置邮。”[16](杨炯《王勃集序》)同时崔融、张说之言也反映了时人认为杨炯文才略高于卢照邻的倾向。至于郗云卿的排序似乎与四人离世先后偶合,离世越早、离郗所处之时越远,则越排于后,但无确凿证据,只作一猜测。再来看卢照邻和骆宾王的先后关系问题,张鷟《朝野佥载》记:“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19]笔记小说所载不一定是事实,但至少不是空穴来风。王勃与卢照邻算得上忘年交,两人曾同游玄武山,王勃作《蜀中九日》,卢照邻作《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宿玄武二首》。无论是出于情谊或是对王勃才华的肯定,“喜居王后”都是可以理解的,相比之下,“耻在骆前”的情感便多了模棱两可的解释。因为王后骆前的杨炯被不着痕迹地抹去了,文中卢照邻的态度就不似杨炯那般准确,究竟是谦虚自贬不如骆宾王,还是自以为应当更进一步,在杨炯之前呢?考虑到卢骆两人关系,或许后者更为妥当。卢照邻在蜀地时与一市井女子交好,后又弃之而去,骆宾王奉使巴蜀时代此女作《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以“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7]的弃妇形象,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卢照邻的无情,后人或因此认为两人间产生了罅隙。两人展现的人生态度也迥然不同,卢照邻新都尉秩满后便远离官场,《唐才子传》卷一《卢照邻传》记述了他与政治大潮的背道而驰,谓:“自以高宗之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崧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20],而骆宾王始终未放弃政治理想,多次上言获罪,甚至投入李敬业麾下公然对抗武后政权,被置于伏诛之列,众人避之不及。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时政朝局,卢照邻都不大可能贬低自己拔高骆宾王。也就是说,王勃在杨炯之前、卢照邻在骆宾王之前的次序基本是得到认可的,而两两配对的“王杨”“卢骆”是最终“王杨卢骆”定式的雏形。闻一多曾从人的性格和诗的形式两个方面阐释两个组派的天然差异,称这种现象为“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21],虽未梳理四杰并称形成过程,但凭借着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深刻的历史意识,依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人深省。
自宋代以降,几乎只剩“王杨卢骆”和“卢骆王杨”两种并称方式,《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述四人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李弥逊《留题新安幕府聚秀轩》有“一时卢骆王杨辈”,李石《答田茂实解元启》则有“卢骆王杨名参四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中特别提出“王杨卢骆体”;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中谓“王杨卢骆因加美丽”;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则有“卢骆王杨,号称四杰”。李弥逊、李石两人很可能是出于平仄押韵的考量,选择使用“卢骆王杨”。而除却诗文对平仄的要求,在姓名并称中亦有音韵协调的习惯,余嘉锡在《世说新语·排调》“王葛、葛王之争”条下注:“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22]推诸四名同言的情况,亦是如此,譬如王扬枚马、尤杨范陆、崔卢李郑,皆以仄声落尾,如此说来,将“卢骆”置于“王杨”之后便水到渠成了。闻一多曾从文体的角度分析“王杨”排在“卢骆”之前的原因,他认为“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21],前者是刘希夷、张若虚的源头,后者是沈佺期、宋之问的前流,比较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可以发现“五律才是诗的正宗”[21],熟练创作五律的王、杨自然也就更被人推重。虽然四杰的诗歌创作以及唐人重五律的现象都不尽如闻一多所言,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颇具启发意义,即从律诗定型、发展的文体学史角度来看四杰,将四杰置于唐代诗歌发展脉络的发端。事实上,杜甫也有与之相似的感悟。
三、杜甫正名与诗评转向
因背离宫廷文学的“正道”,四杰身上始终都背负着“浮躁浅露”的骂名。到杜甫之时,对四杰的恶评由政治判断延伸到了诗文批评,杜甫通过《戏为六绝句》这一组诗精当凝练地叙述了当时文人批讽四杰之举,并表达了自己对此种情境的看法。杜甫虽题作“戏”字,但绝不可轻易将此六绝句视为调笑玩弄之作。
《戏为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杜甫已五十岁,诗中反映的是终其一生形成的论诗要义和诗学观念。历代笺释此诗者莫衷一是,郭绍虞梳理总结为以下三类:“其谓为寓言自况者,以为嫌于自许,故曰戏。其谓为告诫后生者,以为语多讽刺,故曰戏,亦有以为‘戏’字仅指第一首言者。其谓为自述论诗宗旨者,则又以为诗忌议论,故曰戏;或以为此辈不足论文,故曰戏。”[23]实际上,上述三者是可互通的,杜甫借庾信、四杰自比,以斥后生轻侮老成,并告诫后生习文作诗之道。其一述庾信文采卓然,时人却对其传世名篇嗤之以鼻,仇兆鳌《杜诗详注》谓:“当时庾信诗赋,与徐陵并称,盖齐、梁间特出者。”[24]吴瞻泰《杜诗提要》:“举一庾信以概六朝。”[25]末句中的“前贤”当是指以庾信为代表的六朝文人。其二以“江河万古流”反驳讥嘲四杰诗文的轻薄学人,杜甫在诗中提出了“当时体”这个重要的概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各有其特点,执一端而论未免狭隘。洪迈在《容斋四笔》中亦有此感,“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讥之。杜诗云云,正谓此耳。”[26]其三则是对四杰较为公正的评价,四杰诗文虽然不能与汉魏时近风骚之文比拟,但相较颇多唐人诗作亦有云泥之别。至于为何有“劣于汉魏近风骚”这一结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称:“卢、王之文,劣于汉、魏,而能江河万古者,以其近于风骚也。况且上薄风骚,而又不劣于汉魏者也。”[27]而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较为详细地阐释了这一问题:“风骚为韵语之祖。后来格调变移,造端于汉之苏、李,继轨于魏之建安。至唐初诸子初,而体裁又变。要之,皆同祖风骚也。故言‘纵使卢、王翰墨’,‘劣于汉、魏之近风骚’者,要亦国初之风骚也。”[28]杜甫从风骚一脉相承的传统入手,超越了体裁形式的局限,抓住了四杰不同于齐梁、与汉魏更为贴近的真正原因,即气骨、兴象。杜甫以“龙文虎脊”评四杰文风,仇兆鳌注言:“龙虎之骏,皆见重于汉庭,故曰‘君驭’”[24],古人常以品性优良的骏马指称雄健的文笔,韩愈《病中赠张十八》有“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四杰诗文中表现的力量、气势建立在贞观以降提倡的建功立业、匡扶济世思想之上,无论是求进之心还是不平之气都有着极其浓郁的情感,远非纤细华靡的六朝诗歌所能比拟。其四则总结前三首绝句所引庾信、四杰之例,贬抑时人轻薄之气。其五、其六是杜甫诗学观念的集中表达。根据前述三诗,可知杜甫所言古今之界当是以六朝为线,但划定界限并不意味着褒一贬一,而是追求兼顾古今,即“爱古人”也“不薄今人”。具体来看,齐梁以降的“清词丽句”不可废,追求音律协调、章句整饬是作出好诗的必要前提,但也不可全然仿效,落入浮靡轻艳的窠臼。可若是只模仿前人,恐会陷入后不如前、代代衰退的尴尬境地,也就是卢元昌《杜诗阐》中提到的“以其递相祖述,沿流失真,似此沿习,更复先谁耶?”[23]为打破这种僵局,杜甫提出要辨明并摒弃“伪体”,辗转受益于风雅、屈宋、汉魏、齐梁之间,由此方能摆脱亦步亦趋,卓然出群。
整体来看,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反映的诗学观念是调和兼容的,好古不遗今,务实不去华,而这与唐代始终存在的两种诗论派别暗合,钱志熙认为“唐一代诗论有两派,一派是源于齐梁声律讨论的格式派;一派是以汉魏诗歌为经典、上溯风雅传统的复古派。”[29]前者重视声律、偶对等形式美,主要依托于佛道玄禅,在杜甫诗学观念中表现为对“清词丽句”的雕琢;后者则主张学习汉魏并上溯风雅,深受儒家复古思想的影响,在杜甫诗学观念中表现为对气骨风神的重视。杜甫兼及此两种诗论,杨伦在《杜诗镜铨》中记张上若言,“趋今议古,世世相同,惟大家持论极平,着眼极正。”[30]故在考察四杰时不会一叶障目,一方面不因其在音律、句法等格式方面未能完全摆脱齐梁旧习便急切否定,认同恰当的雕琢辞藻、斟酌音律;另一方面发掘了四杰对雄壮刚健的追求,“取其雄伯,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16](《王勃集序》)如此一来,四杰不再只被视作下层文学、前朝文学的代表,而是承续汉魏以降风骨传统、开启后来盛唐文学内容和形式双重革新的桥梁。
四、“四唐说”形成与初唐四杰地位确立
杜甫虽早于诗文评论中为四杰正名,但一来受限于杜甫本人的处境,二来《戏为六绝句》往往被读者理解为自寓之作,并未改变主流对四杰的评价。钱谦益在《读杜二笺》引韩愈诗作论证,“韩退之之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然则当公之世,群儿之谤伤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发其意。”[23]甚至到宋代,注者仍聚焦于杜甫自况之说,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谓:“《戏为六绝句》诗,非为庾信、王、杨、卢、骆而作,乃子美自谓也。”[31]这也意味着终唐一代杜甫对四杰文学风格以及所处文学阶段的创见始终未能产生巨大影响,从唐末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所述便可见一斑,“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8]在宏观勾勒唐代文学发展历程时,对四杰以及初唐诗文无意识的忽略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而随着唐诗发展分期研究的逐步深入、“四唐”说的发展与定型,沈、宋以外的初唐文坛也慢慢浮出水面。
“四唐”说起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他分唐诗发展阶段为五: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严羽虽推崇盛唐,“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32]但是也以广参熟参唐诗为要,以时代为脉叙述诗道存续: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晩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32]
沈宋、四杰、陈子昂被列于南北朝与开元天宝间,这与历史进程基本一致。而从诗文发展上看,严羽以诗体为轴,按照时代和文人群体的不同进行了划分,“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 ”[32]再“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32]。对比可知,严羽所说的“一时体”范围更广,包含各类典型诗人,如“唐初体”内有“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而无论是时代体还是文人体,其依据都在于“分明别有一副言语”[32],至于各体的风格特点如何,严羽并未详说。但就四杰而言,严羽偏于感悟的主观划分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他们与沈宋、陈子昂风格的不同以及在初唐文坛的独特地位。
元初方回在《瀛奎律髄》中提出中唐,与严羽一齐为“四唐”说构建了雏形,但几乎未提及唐初,甚至常将盛唐向上延伸到唐初。此后,杨士弘作《唐音》,正式罗列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名目和时限,至此“四唐”说最后定型。杨士弘在书序中提出文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的观点,“先王之德盛而乐作,迹熄而诗亡,系于世道之升降也。风俗颓靡,愈趋愈下,则其声文之盛不得不随之,而然必有特起之才、卓然之见,不系于习俗之所同,则君子尚之,然亦鲜矣。”[33]但同时他也没有拘泥于历史分界,提出了另一种划分方式,“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33],纪昀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将两种划分方式进行了比较,“‘始音’惟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诗以体分,而以初唐、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诸家之作咸在。”[34]杨士弘以音律而非生活年代为标准,将“王杨卢骆”视作唐诗初起的萌芽,换言之,杨士弘肯定了四杰作为六朝诗歌向初唐诗歌过渡阶段的独特作用,但因为四杰理论上对齐梁文学的坚决否定并没有完全显现在诗歌文赋的创作实践中,所以不能跟同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陈子昂一起进入正音之列。杨士弘这一观点或取自杜甫,他深知杜甫广取各家所长:“子美所尊许者,则杨王卢骆;所推重者,则薛少保、贺知章;所赞咏者,则孟浩然、王摩诘;所友善者,则高适、岑参;所称道者,则王季友。……古之人不独自专其美,相与发明。”[33]
杨士弘虽为“四唐”说提出了具体名目,但是并未进一步阐释,直到明代高棅著《唐诗品汇》才使“四唐”说真正成为完整的体系。高棅认为终唐一代各类诗体“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35]基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高下有别,他将唐诗划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进一步来看高棅对初唐时期诗人、诗作的看法,“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远,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35]他将初唐分为始制与渐盛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虞世南、魏征开始,“稍离旧习”指的是贞观年间对绮丽文风的革除,譬如魏征主张融合江左的清绮和河朔的贞刚,“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36];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接续其后,他们在万国来朝的伟大功业中成长起来,极为认同此前政坛、文坛对匡时济世精神和典正富丽雅音的追求,并在此基础上以兴寄风骨丰盈了诗歌内容意境,这就是高棅所说的“因加美丽”;而刘希夷、上官仪则并不在虞、魏、四杰一脉之上,他们延续着齐梁诗歌的绮错婉媚,偶有清新流丽之作,尽管诗歌内容上并未有突破,但在声韵对偶领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高棅依靠自己对唐诗整体发展脉络的把握,简截了当地以三个文学群体勾勒出贞观永徽时错综复杂的文坛,突出了文学发展中的承与变。就四杰而言,他们作为初唐诗坛兴起的重要代表,高棅在论述各类诗体时皆有涉及,五言古诗中谓“永徽以还,四杰并秀于前,四友齐名于后”[35],五言绝句中有“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尤多,宋之问、韦承庆之流相与继出,可谓盛矣”[35],五言律诗中道“唐初工之者众,王杨卢骆四君子以俪句相尚,美丽相矜,终未脱陈隋之气习”[35],五言排律则有“永徽以下,王杨卢骆倡之于前,陈杜沈宋极之于后”[35],虽然叙目中论述七言诗时往往因唐初良者少而一笔略过,但在具体选诗时总是避不开王杨卢骆四家,足见四杰作为初唐诗坛承前启后力量的重要地位。
高棅《唐音》之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亦有此见,甚至将五言成为律诗正统的开端归自四杰,称“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37]此观点准确与否还有待考量,或有夸大四杰之嫌,但作为“初唐四杰”这一并称广为接受和认可的佐证,足矣。其后不久,胡应麟在《诗薮》中具体分析了四杰对七言诗发展的作用,他在论述七言古体中称“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歌行兆自大风、垓下、四愁、燕歌,而后六代寥寥。至唐大畅,王杨四子婉转流丽,李杜二家逸宕纵横,献吉专攻子美,仲默兼取卢王并自有旨 。”[38]在讨论七言近体时称,“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故体裁明密、声调高华而神情兴会、缛而未畅。”[38]在谈及七绝时谓:“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也。”[38]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强调四杰作为初唐之始的关键地位,“王杨卢骆以词胜,沈宋陈杜以格胜,高岑王孟以韵胜,词胜而后有格,格胜而后有韵,自然之理也。”[38]至此,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的并称已完全确定下来,此八字中不仅透露着四杰名次、后人褒贬的信息,同时昭示着他们承接六朝文学传统、开启盛唐恢弘气象的关键性地位。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在其当世已被视为一个文学群体,而四人排名顺序未成定式,终唐一代有王杨卢骆、杨王卢骆、骆卢杨王等叫法。他们以不同于宫廷诗文的风格独立于宫廷文学之外,其本质反映了作为下层文士代表的四杰与执笔“上官体”的宫廷文人处于对立的两方,张说、刘肃据此虚构了“裴行俭贬四杰”之事,虽是小说家言,却被记入了史册,这导致后世读者很长时间都对四杰戴有“浮躁浅露”的有色眼镜。即使杜甫以《戏为六绝句》斥诫后生不可轻薄四杰,但宋人深信史书所记,常以“先器识后文艺”为准,使得世俗伦理盖过了文学批评,甚至对四杰的名次排序产生了影响。自宋以降,随着古人对诗文发展历程的认识不断加深,对“王杨卢骆”文学主张、文体风格的分析不断深入,元、明两代评论家逐渐意识到:四杰是文学自六朝入唐、初唐转盛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在反对齐梁绮靡文风、重振风雅传统以及倡导兴寄风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足以成为初唐文坛的代表人物。在此基础上,“王杨卢骆”的并称最终确立。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并称形成的过程,本质上是古代学者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层累式深化的过程,这其中还蕴涵着文人个体和文学群体、当世评价与后人接受、文学传承与文学革新、文学批评的滞后性等诸多更为宏大、复杂的问题,尚有待于未来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