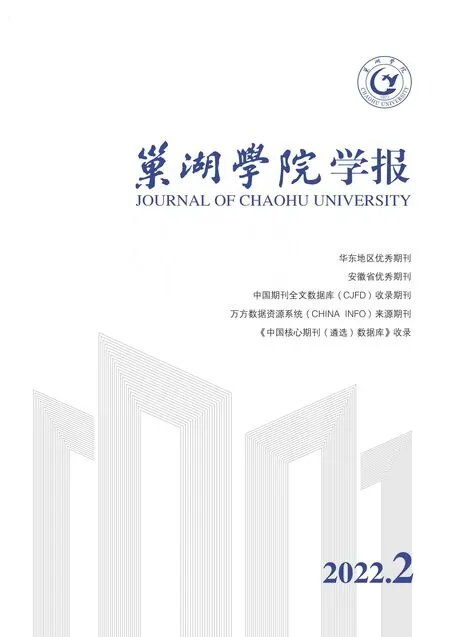跨媒介视域下艺术媒介之间的界限与相通
——以语词和图像为例
古 尚
(安徽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引言
“跨媒介”这一概念产生于二十世纪,但在古代东西方就已出现这种艺术现象,以及众多古典文献对这一现象的学理性描述。“诗舞乐一体”“诗画同源”等包含跨媒介艺术思维的观点在中国古典文论中随处可见,正如《毛诗序》这样描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诗歌、音乐和舞蹈采用不同的艺术媒介,但它们都是表达感情的艺术形式,所以在特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融通。苏轼认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亚里士多德从“摹仿”的角度指出诗歌与绘画的同等地位,即它们都是对社会生活的摹仿,只是摹仿的媒介不同。贺拉斯也将诗歌与绘画比作不可分割的“姊妹艺术”。应当指出的是,古代众多学者虽然意识到这种跨媒介艺术现象,但没有形成完善的跨媒介理论范式,也没有从媒介的角度深究其中的原因,其学理性的认识较为浅薄。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呈现出相互融合的现象,在跨媒介和跨学科的语境和艺术实践下,对跨媒介艺术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二次增长的态势。龙迪勇详细探讨了艺术中的跨媒介现象:“我们除了了解该作品本身的媒介特性之外,对于它‘跨’出自身媒介而追求的他种媒介的特性也必须有所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完整地欣赏其美学特色”[1]。周宪认为跨媒介性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将艺术交互关系分为五种研究范式,即姊妹艺术研究、历史考察模式、美学中的艺术类型学、美国比较文学的比较艺术或跨艺术研究以及最后的跨媒介研究。他还将艺术跨媒介性分为二分模态关系①单媒介的跨媒介性是在只存在一种单一媒介的艺术形式中模仿了其他艺术媒介的形态,如在元代文人画中感受到的诗歌效果;多媒介的跨媒介性是指包含不止一种媒介的艺术形式中存在的跨媒介性,如电影、戏剧、舞蹈。,即单媒介作品的跨媒介性和多媒介作品的跨媒介性[2]。对于跨媒介性的模态关系,延斯·施洛特创造性地提出四分模态关系②综合的跨媒介是指很多媒介融合为一种媒介的过程,好比电影艺术的媒介包含音乐、文学、绘画等等的结合;形式的或超媒介的跨媒介性的含义是指这种模态表现为某些超媒介的特征,例如虚构性、节奏性、写作策略、系列化等;转化的跨媒介,也就是一种媒介以另一种媒介的形式来呈现,如法国系列短视频《奇趣美术馆》就是以短视频的形式来介绍世界闻名的美术作品;而本体论的跨媒介性是认为无论每一种媒介的定义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性,都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媒介,也就是本体论的跨媒介性。,即综合的跨媒介性、超媒介的跨媒介性、转化的跨媒介性和本体论的跨媒介性[3]。拉耶夫斯基提出艺术跨媒介的三分模态关系③媒介转换意义的跨媒介性是犹如文学改编的电影、音乐等现象;媒介融合意义上的跨媒介性是指电影、戏剧、图画书等含有多媒介的艺术形式;跨媒介意义上的跨媒介性则是一种艺术作品的创作含有对另一媒介的参考,如电影参考文学、音乐参考绘画。,即媒介转换意义的跨媒介性、媒介融合意义上的跨媒介性和跨媒介意义上的跨媒介性[4]。
在讨论“跨媒介”这一概念之前,我们应有承认媒介特殊性的共识,即用以承载不同艺术形式的媒介材料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方式和特殊的艺术效果,这是保持艺术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前提,但这并不代表它们是互相排斥或者存在不可渗透的隔阂,每一种表达媒介之间从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艺术的跨媒介性在于鼓励各门类艺术的相互转换与融通,超越自身媒介的表达限制,追求他种媒介的艺术效果。而笔者旨在以具体的语词与图像媒介为例,对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特殊性以及跨媒介性现象进行分析探讨,这有利于打破传统艺术学理论中因为对于艺术特殊性的重视而对艺术交互性的忽视,从而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完善艺术学理论的崭新建构,也为如今艺术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语词媒介与图像媒介的界限
语词与图像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中具有表情达意功用的两种基本媒介。语词与图像的关系源远流长,它们不仅存在着一方向另一方艺术效果追求的渴望,甚至还包括两者的配合与融合,同时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也包含其中,米歇尔将此称之为一场“符号大战”,而这场大战双方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它们自认为对人类文明、真理、精神最有影响力的符号媒介。语词与图像作为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媒介,既有着不同的特性,也包含相互模仿的现象,可以作为讨论媒介特殊性与跨媒介性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媒介。它们在理论研究范畴中既是指叙事中的不同表述方式,也是指作为承载信息内容的两种符号在指代某物时的不同特征,其区分主要体现在叙事学和符号学中。
(一)语词与图像在叙事学中的差异
在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除了口语媒介,最重要的叙事媒介就是图像,如果没有相关图像在远古时期的创作,我们是无法对史前时期进行理解与认识的。对于图像的记叙作用,鲁迅这样说道:“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洞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悠闲,他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5]。而文字出现后,图像对于叙事的主宰地位明显受到了挑战,甚至受到了文字的抑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文字与图像在媒介特性中的区分。
语词与图像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写照的媒介,都承担着叙事的责任,罗兰·巴特认为用以承载叙事的媒介可以是一切物质材料,文字、口语、绘画、声音等媒介都是叙事的工具与手段。无法否认的是,文字与图像仍然是叙事中的两大主要媒介,但是自从文字产生之后,图像在叙事中的主宰地位逐渐消落,文字在叙事中的天然优势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这两类艺术形式在叙事中所采用的不同媒介的特性导致的。莱辛将诗歌(文学)与绘画分为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时间艺术适宜于叙述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情节,而空间艺术则适宜于描绘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叙事的本质说得通俗一些其实就是讲故事,而我们也无法反驳这是一件线性的时间性行为,而语词不论是作用于视觉还是作用于听觉,都必须在时间的流逝中完成,所以语词作为一种时间性媒介且具备极佳的表情达意的功能,故在叙述故事时就变得无比轻松和自然,这与在空间中并列的静态图像媒介正好相反,空间性媒介只能创造出某一瞬间的静态形象,无法像文字那般在时间的先后承续中去欣赏。他还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潘达洛斯把弓提起,调好弓弦,打开箭筒,挑选出一支没有用过的装好羽毛的箭,把它安在弦上,把弦带箭拉紧,拉到弦贴近胸膛,弓哗啦一声弹回去,弦嗡了一声箭就飞出去,很急速的飞向目标”[6]。潘达洛斯射箭的一连串动作是顺着时间的顺序一步步完成,所以这种持续的动作并不适合在空间艺术中表达,而是在时间艺术中去讲述。由于图像媒介材料的特性,它只能保持瞬间静止的形态,我们无法了解在这一瞬间的前后情节究竟是怎样的,当图像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它在叙事中是“失语”的,所以莱辛认为成功的绘画应该描述出某一瞬间的顶点,即“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只有在这一顷刻,观者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想象的自由性,填补原本在时间中失语的叙事关系,否则它就会沦为平淡和无趣。故在叙事的角度下,由于语词媒介的特性,可以自然而然的在时间的先后承续中去讲述一件事,而图像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媒介,只能在一定的空间中塑造在时间中凝结的形象,所以像绘画、建筑、雕塑这种空间艺术在时间性的叙事活动中具有天然的劣势。
(二)语词与图像在符号学中的差异
语词媒介与图像媒介不仅在叙事学中有着区分,在符号学的角度同样存在不同,其中最根本的区分就是任意性和相似性的差别。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或许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差异性。所谓“能指”是用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而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称为“所指”,“所指”也就是“能指”中语言符号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作为语言符号的“书籍”的词语是“能指”,而作为具体对象的书籍是“书籍”这个语言符号的“所指”。文字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其实就是皮尔斯所说的“象征”(一种任意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所以“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就使语言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其指向作用相当准确。而米歇尔等将图像定义为“某物的符号或象征,图像与它所代表的东西在感官上具有相似性”[7]。也就是一副图像的内容应该使观者的感官认为与某物相似。但是图像符号的意指作用并没有语言符号那么精准,而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任意一个单词或语句指代任意一件物品或者一个人,但是却不能随意的将一幅与某物相似的图像准确地指代某物。例如有人说这幅图像与太阳相似,又有人说它与向日葵相似,至于到底与什么相似,相似的程度有多少,一千个读者自然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在符号学的角度,文字与图像的差别就是任意、约定俗成的符号精准对应某个特定的具体事物与图像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具有相似性的差别,即任意性与相似性的差别。
二、跨媒介语境下的图像与文字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特定的表达媒介,它不仅是艺术外在呈现的物质载体,同样也是构成艺术形式本身的符号体系,不同的表达媒介呈现出的美学效果和艺术意蕴也不尽相同。前文分析了图像与文字在叙事学和符号学中的差异,更是证实了不同媒介在艺术表现中拥有不同的特性与优势。不可否认,不同的艺术种类很大程度上受到它所使用和承载的表达媒介的限制,这是承认不同艺术形式具有差异性的基本前提。但是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跨媒介艺术逐渐成为艺术的主要形式,与这种艺术实践相对应,跨媒介的艺术理论也应运而生。所以,一方面我们应对艺术媒介的特殊性与差异性有所认知;另一方面,打破学术之间的壁垒,以跨学科、跨媒介的视域重新看待传统艺术理论和对于艺术媒介性的认知,也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对于媒介多样性以及跨媒介的理论认知
莱辛认为:“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6]。他的目的就是反对当时“诗画相通”的主流美学观点,指出混淆文本与形象之间界限的严重弊端,并提出“诗画有别”的理论主张,也是从莱辛开始,诗画正式划分了边界。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说道:“在实践中,这种美学鼓励那些特殊的和一般的不诚实的艺术形式,它存在于这种企图之中通过躲藏在另一种艺术的效果之中来逃避一种艺术的媒介问题;绘画和雕塑在稍逊天赋的艺术家手中,不过成为文学的代笔和‘傀儡’。要还原一门艺术的身份就必须强调其媒介的不透明性”[8]。格林伯格是极力反对绘画中含有文学的诗意的,他认为要追求一门艺术不可还原的本质,就应该摒弃其他艺术门类所带来的艺术效果,避免其他表达媒介的参与,这种“不可还原的本质”是建立在媒介自身的特殊性与纯粹性上的。按照莱辛和格林伯格的观点,艺术中各个表达媒介之间可谓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艺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各个艺术门类之间产生一定的对抗性。我们相信,亚里士多德和莱辛以及格林伯格对已确立价值的媒介多样性的研究具有根本的意义,也必须在基于他们观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展开对跨媒介艺术理论的研究。但是各门类艺术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明显的区分过,它们非常容易就能够相互融合。如果将身体作为一种鉴赏艺术的媒介,那么各个感官媒介都是密切相关的。钱锺书认为:“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9]。正如米歇尔认为图像与它所代表的东西在感官上具有相似性,其定义并不是仅视觉感官能够满足,其他非视觉感官也同样满足其图像的基本定义,作用于视觉媒介的作品也同样作用于听觉和触觉甚至嗅觉,当感官互相渗透或者融为一体时,我们就很容易在各门类艺术中找出共通性,不仅是文学与图像,包括音乐、建筑,舞蹈等等艺术品类中,都能感受到这种艺术魅力。
“跨媒介”这一词语最早可追溯至1812年柯勒律治在文学实践中的运用,德国美学称其为“出位之思”,即一种表达媒介在保持自身媒介特殊性所展现出的美学特色的同时,试图跳出“本位”,不安分地追求另一种表达媒介的美学效果。另外,“跨媒介”并不是说转变成为其他媒介,也并不是两种或多种媒介的融合,这种情况并不在此次讨论范围内,而是一种表达媒介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追求另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特征,其媒介本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是在保持自身媒介特性的前提下,再“不知足”地去追求他种媒介的特有的艺术效果。中国书法作为我国独有的一种造型艺术,其中就包含着对音乐艺术的跨媒介现象,不仅仅是承载语言内容的符号形式,更是一种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象征,是艺术家情感的表现,是像中国画中“情景交融”的意境美。艺术家通过用笔的缓急、结构的疏密以及点墨的轻重来表达他对书法形象的感情以及意境的抒发,而这与音乐艺术的表达方式不谋而合,音乐就是用节奏、音调、旋律在时间的进程中表达艺术家丰满的情感,所以我们能够从书法艺术中感受到一种流动的音乐美,仿佛从书法形象里听到自然界发出的美妙乐音。所以,书法作为造型艺术门类中的一员,其形式美是在空间中来概括的,而其中又蕴含着作为时间性特征的音乐美,两者呈现出相通的现象,但是书法艺术的媒介并没有转换成音乐媒介,在同一种艺术形式中也没有出现这两种媒介的结合,而是书法艺术在保持自身媒介特征的同时,再来追求音乐美的艺术表现力。钱锺书提到对艺术的跨媒介现象:“一切艺术,要用材料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10]。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它可以与其他门类的艺术相互转换,而这种转换恰恰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所以,在保持媒介自身“本位”特征的同时,通过对艺术自身界限的突破,并与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融通,从而获得自身媒介所不具备的艺术力量,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创作和欣赏艺术,也正是出位之思的初衷所在。
(二)图像向文字的跨媒介
艺术的跨媒介倾向主要体现在时间艺术与时间艺术之间(文学与音乐)、空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雕塑与绘画)以及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语词与图像),而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间包含了最为重要的跨媒介艺术。首要探讨空间艺术向时间艺术的跨媒介倾向。这种特殊的美学现象在中外艺术史中自古有之,唐宋时期在诗歌与绘画之间的关系上就体现出跨媒介的思维倾向,苏轼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绘画属于造型艺术,是采用特定的物质媒介材料以美的规律和法则在一定的空间中塑造静态的美术形象,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由于其直观和形象的媒介特性,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再现艺术的典范,正如陆机所言:“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可中国的文人画家偏不以画写实,而是借助绘画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直抒胸臆,好比倪瓒所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可见,绘画作为一种再现写实的艺术形式,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却可以不受绘画媒介特性的影响,反而去追求文学中诗意的效果,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中的跨媒介。除此之外,绘画作为一种静态的空间艺术,也能够表达出像诗歌一样的表征时间性的艺术效果,米歇尔等对在图像中所显示的时间性有着深刻的论述:“我们与任何图像的相遇,某种形式的时间性都嵌入其中”[7]。这种图像中的时间性包含很多方面,例如图像的创作时期和产生日期、绘画中包含的历史性或者在欣赏图像时流逝的实际的时间和脑海中留存的记忆片段。图像是某物的符号或者象征,它与所代表的事物必须具有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与人脑中的记忆密切相关,一幅图像能否被认为与某物相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欣赏者以往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经历,图像包含的内容必须唤起他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龙迪勇强调:“记忆是一个心理学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架在时间与叙事之间的桥梁”[11]。所以图像存在于人脑记忆中的方式并不是定格的,而是“移动着的图像”,是在一定时间中流淌的片段,若将记忆当作一种媒介,那么图像与诗歌、音乐、文学一样构成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沃尔特·佩特对乔尔乔内“绘画诗”有着感人至深的描述:
它部分是戏剧诗的最高品类的理想状态,它向我们表达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意义和栩栩如生的片刻,它仅仅是一种姿势、一种表情、一个微笑,或许是一些短暂但绝对具体的瞬间,但是,一长段历史的所有动因、所有趣味和所有的结果,全将自己浓缩于其中了,而且它也似乎将过去和未来全都融入了强烈和可感的现在。[12]
从这段话中,我们竟然能在乔尔乔内笔下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体会到历史的变迁。乔尔乔内的高超之处来源于对主题对象的选择,其目的不是宗教之需,也不是教化之用,而是画一群男男女女的实际生活片段,他们或是谈话亦或是奏乐,仿佛在画中感受到了音乐的状态以及一种宁静恬美却激动人心的诗意,这也是为什么乔尔乔内的绘画能够成为戏剧诗所追求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绘画作为定格在瞬间的空间艺术形式,在一些美术家例如乔尔乔内笔下却能够体现出其中所包含时间的流逝,也就是绘画艺术向文学艺术的跨媒介。
(三)文字向图像的跨媒介
除了在作为空间艺术的图像中能够表现出文学诗歌般表征时间性的艺术效果之外,我们也经常能够感受到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字追求某种造型艺术的视觉效果。文学的表达媒介是语言和文字,实质上是在时间的进程中用来表情达意的,可诗人却能够突破语词媒介的局限给予读者一种独特的空间效果,跳出语词媒介的“本位”,转而去追求图像的美学效果,这同样也是另一种跨媒介的表现。语词媒介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以及读者基于文本所展开的无限自由的想象性,这种模糊和暗示正是文学馈赠给读者最好的礼物。而在二十世纪现代艺术中,却能够将语言视为听觉媒介甚至视觉媒介,几乎消除掉单词语义的暗示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达达主义的创始人特里斯坦·查拉擅长将单词和语句进行随意地“裁剪”“拼贴”,在他眼里,“拿份报纸,剪下单词,打乱顺序再重新拼贴,那便是超越粗俗的原创。”达达主义打破了语词固定在书本中的排版形式,主张无意义无规则地拼贴,并赋予单词物质形态和视觉效果。同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具象诗”运动认为诗歌的视觉元素与文本元素同等重要,“具象诗”又被称为“视觉诗”或“图案有形诗”,是指以语言作为对象,可以自由地组织与解读其中意义,并非一仍旧贯按照语言符号所代指的意义去理解,而是通过空间位置、图像、字体符号以及单词之间的感受来解读作品的意义。所以,通过对文字的排版使其具有既定的视觉效果,将文字变成诗歌本身的一部分,而非仅仅是承载语义内容的媒介形式,这正是“具象诗”的思想所在,也是文字向图像跨媒介的重要体现。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达达主义和“具象诗”以及类似的艺术现象是通过特定的方式清空语义内容,将传统文学中透明的语言赋予物质性,文字在其中不再是在时间维度上传达思想内容的媒介载体,而是将单词语句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处理给观者一种空间上的视觉形态,这是作为时间艺术的语言文学呈现出视觉图像效果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文字在不改变物质形态的前提下,既保持语词媒介的美学特征,又可以突破语词这种媒介材料的束缚,去追求空间性的视觉效果,这种视觉效果并不是通过作为肉体器官的眼睛,而是脑海中的“眼睛”来呈现。这种美学现象称为“艺格敷词”,即“以文述图”,是指对艺术作品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的写作手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一种修辞学传统,它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充分讲述”或“说出”,是古希腊城邦中法庭起诉和在议会大厅及其集会演讲时所使用的一种语言技巧,演讲者通过文字或者口语的方式使听众通过想象感受到一种逼真、形象的视觉图像效果。“艺格敷词”成为西方的一种文学体裁最早出现于《伊利亚特》中对阿喀琉斯的盾牌的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瓦萨里将其发扬光大,十九世纪初期诗人济慈的《希腊古瓮颂》被奉为“艺格敷词”的经典之作,直到现在依旧是当代文学理论以及艺术学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乔尔乔内的绘画具有一种浪漫的诗意,而诗歌和文学同样能够表现出视觉艺术的特征,诗人以画家的角度利用文字再现绘画的艺术特质如构图、色彩、韵律、动感,使读者虽处身外,却宛若置身其中并浮想联翩。这种奇妙的艺术现象正是来源于诗人和作家对于传统写作技巧和规律的突破和革新,使属于时间性媒介的语词呈现出属于空间性媒介的图像的美学效果,而这正是语词向图像的跨媒介。
三、结语
综上,诸多艺术媒介如语词与图像在跨媒介的独特视角下表现为在保持本质媒介不变的同时,追求异质媒介包含的美学特色或者与之结合,产生一种崭新的、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意蕴,表现出单一媒介无法表现出的艺术内涵,好比语词在一些创造性的作家笔下主动地去表现绘画甚至雕塑的空间效果,而在一些美术家笔下的绘画形象中也能感受到犹如诗歌般的时间性以及音乐般的状态。两种媒介的相互结合并不是对彼此的侵犯,而是对自身的突破与超越,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两种媒介杂交或交会的时刻,是发现真相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而产生的新的媒介形式”[13]。两种媒介结合时,能够孕育和产生巨大的能量和力量,在很多具有“出位之思”的独创性的作家或艺术家的手中,我们都能通过欣赏他们的艺术作品感受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