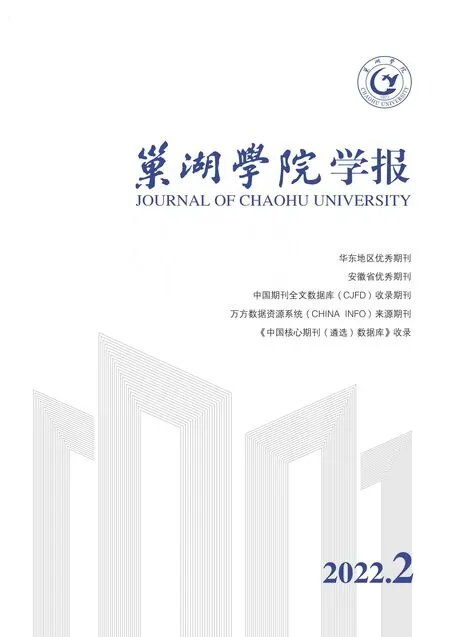建中之乱与韦应物宦滁诗
祁萍萍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引言
“建中之乱”是唐王朝中后期藩镇问题的缩影,也是安史之乱后对李唐王朝的又一次致命冲击。据吕思勉所言:“先是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各聚兵数万,连衡盘结以自固。”[1]然后建中二年(781),德宗拒绝了李惟岳承袭其父成德节度使的要求,坚持实行“以藩削藩”政策,以此为导火索引发了“四王二帝”、泾师之变、奉天之难、再逃梁州等一系列事件。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收复长安、七月德宗归,接着两年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被平定,至此结束,此即为建中之乱。
韦应物于建中三年(782)夏出守滁州,兴元元年(784)罢刺史,任职时段在建中之乱中。关于韦应物在滁州时期的写作,孙望和陶敏的诗集整理本均对韦应物宦滁诗作进行了校点、汇评与定年。较早的储仲君[2]将滁州诗作定义为“滁州的凄清”,这一基调是基本准确的。蒋寅[3]点出滁州时期的韦应物在“像春困一样难以抵抗”的厌倦仕宦心理下实则有顽强的责任感。景刚[4]认为滁州是“正式形成了他的吏隐思想”。在上述诸多学者研究之下,韦诗在滁州时期的生平考证、思想感情和艺术表现等内容已较为明晰。但是关于建中之乱与韦应物宦滁时期诗歌之关系,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是不可缺失的:“政治(事件)与古代现当代(文学史的复杂现象,某一时期作家的群体心态,乃至某一作家的创作历程)都有密切的关系。”[5]韦应物的诗作大多语气澹然、境界散淡、情感无大喜大悲,故历来以“高雅闲澹”(白居易《与元九书》)闻名于后世诗话评论,但这种“京师”的又一次覆灭、类似于安史之乱的政乱显著影响了韦应物在滁州时期的诗歌写作:对韦应物宦滁时期的吏隐诗歌创作产生了心灵冲击,刺激了其作为大历诗人走出天宝光圈后潜在的深刻不安之心理。《始建射侯》更是暴露了其情感鲜明外露的一面,而这种“金刚怒目”式创作在韦诗中是难得一见的。文章即就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期展现韦诗在历来诗话评价中的特殊一面,从而更全面地认识韦应物诗歌及其内心世界。
一、韦应物宦滁诗作对建中之乱的直接书写
韦应物任职滁州刺史时适逢建中之乱,这一大背景在其宦滁诗中多有反映。此5首与其直接相关。研究选诗标准有二:一是根据孙望、陶敏在其著作中对韦诗的系年考证,选取二人均一致认为作于滁州的诗作进行考察;二是选取对建中之乱有直接描写,或是韦应物本人于诗下自注之诗,抑或是经由孙、陶两位的笺评、注,参考两书对比得出。其中《寄畅当》和《始建射侯》主要书写战乱,而《答王郎中》《京师叛乱寄诸弟》和《西楼》则表现了建中之乱下韦应物直观的痛苦感受。
(一)战乱书写
寇贼起东山,英俊方未闲。
闻君新应募,籍籍动京关。
出身文翰场,高步不可攀。
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间。
昔为琼树枝,今有风霜颜。
秋郊细柳道,走马一夕还。
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
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
——《寄畅当》
题下自注:“闻以子弟被召从军。”时建中三年(782),因李希烈攻陷汝州,白志贞于京城招募从军:“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亦与其男官。是时豪家不肖子幸之,贫而有子者苦之。自是京师人心摇震,不保家室。 ”[6]《资治通鉴》亦载:“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师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资者甚苦之,人心始摇。”[7]可见官家子弟被强召从军实为苦差,京师人心惶惶以致于对当权者产生了怀疑。但是在韦应物看来,这是一次难得脱离“事州府”而建功立业的机会,因此更是深切勉励畅当为国从军,足可见韦应物对当时社会战乱四起的痛恨态度。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韦应物个人理想的展现:有立功之心,只是苦于没有“被召从军”的机会。尤其是末尾“何必事州府”、白白使得自己“鬓毛斑”一句就更为明显了。韦应物在赴任滁州前,均是“事州府”等州县小吏,这种“不平之音”隐隐暴露了韦应物的艳羡与不甘。
而《始建射侯》则是宦滁诗中难得一见的“金刚怒目”:
男子本悬弧,有志在四方。
虎竹忝明命,熊侯始张皇。
宾登时事毕,诸将备戎装。
星飞的屡破,鼓噪武更扬。
曾习邹鲁学,亦陪鸳鹭翔。
一朝愿投笔,世难激中肠。
——《始建射侯》
此诗刚健勇猛,并且带有张烈的荐己之志。此中武态,不同于韦应物年少时气势凶猛的“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逢杨开府》),更多是严峻环境渲染下的一种共鸣与唤醒。建中年间连年战乱,为防不时之需,州郡纷纷习武讲射,滁州也不例外。射侯,即张布而射的箭靶,自周朝便开始用虎豹熊麋各种毛皮来装饰射标,熊侯为王、诸侯所专用,有着“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8]的等级。孙望评曰:“此诗称熊侯,以刺史有专城之宠,有类诸侯,故云云也。”[9]这种“世难”,深深刺激了韦应物以往的“适越意”(《送崔叔清游越》)和专城刺史的责任感,紧张激愤的军事训练工作也一举激发了韦应物骨子里潜在的不平之志,甚至使其表达出了的卢飞马、投笔从戎的大丈夫之志,而这在韦应物宦滁诗中是极其少见的。
(二)心理感受
这并不代表韦应物就是盲目乐观的。在前期已显现出世乱苗头的阶段,韦应物就对此有着深重忧虑,不久后果然发生泾师之变等一系列事件。《答王郎中》作于建中三年(782)秋韦应物刚至滁州,韦应物在此诗中直言战乱带来的破坏:
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
赋繁属军兴,政拙愧斯人。
髦士久台阁,中路一漂沦。
归当列盛朝,岂念卧淮滨。
——《答王郎中》
此诗作于建中三年(782)秋,韦应物到滁不久,造成滁州“荒榛”的直接原因,即为赋税。从大历年间开始,中央和地方藩镇产生了大量的军事摩擦,加之德宗的削藩政策,中央开支极为巨大。而这种巨大的开支需要通过赋税来进行弥补。建中年间以来,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平卢节度使李纳、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幽州节度使朱滔、恒冀都团练观察使王武俊、魏博节度使田悦等人相继抱团举兵、叛乱,《旧唐书》载:“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6]因此这种四海多事的严峻情况致使税率提高,“(建中二年)五月丙寅,以军兴十一而税”[6]。为弥补不足,朝廷更是巧立各种名目敛财,甚至采取严酷手段,如建中三年(782)就对京城富商进行了大肆勒索,德宗“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6]。再如颁布两税盐榷法令,“五月丙戌,增两税、盐榷钱,两税每贯增二百,盐每斗增一百”[6]等等,不一而足。且江淮之地历来为税收大户,这种情势便顺势波及到了滁州。《新唐书》载德宗意欲聚敛,除了常赋外还有进奉,例如“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每缗二百,因诏天下皆增之”[10]。作为地方首任官吏,韦应物不可避免地要有所行动。但是这种军事耗费、严重赋税对于“氓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答崔都水》)的韦应物来说极其痛苦,对于本就经济凋敝的滁州更是雪上加霜。《月晦忆去年与亲友曲水游宴》亦反映了“凋氓积逋税,华鬓集新秋”的情况。“赋繁”和“军兴”对民生的冲击,虽为文学视角,也不难想象当时的滁州是如何的“荒榛”。
如果说《答王郎中》对于现实的直接书写还较为克制,那么《京师叛乱寄诸弟》所反映的“泾师之变”就很难压抑这种情感了,尤其它对韦应物的理想之地——“京师”进行了直接破坏。
建中四年(783)秋,在藩镇问题、西北边防失控、募兵制等多重因素作用和势力拉锯下,泾原军哗变了。八月丁末,哥舒曜被李希烈三万叛军围猎于襄城。九月,德宗调动在长安京西北即泾原藩镇的泾原兵救援哥舒曜,然而“丁末,泾原军出京城,至浐水,倒戈谋叛,姚令言不能禁。上令载缯彩二车,遣晋王往慰谕之,乱兵已阵于丹凤阙下,促神策军拒之,无一人至者。与太子诸王妃主百余人出苑北门。……戊申,至奉天”[6]。哗变的直接导火索,是京兆尹王翃带有德宗授意性质的“粝食菜啖”的吝啬犒赏,这种吝啬源于德宗过早的削藩决心。陈寅恪曾在《论李怀光之叛》中指出军晌不均对军队情绪之影响,加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唐纪》第四十四载泾原兵冬十月冒雨而行,长途跋涉,明显带有唐朝中后期兵力“拖家带口”的特点。因此泾原兵很快一怒而起,“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7],进而反戈京师将矛头对准皇帝。然而德宗在此危急关头却无兵将可用,手下白志贞“以神策军拒贼,无一人至者”[6],于是不得不狼狈出逃。这次事件直接反映在韦应物诗作中的就是这首:
弱冠遭世难,二纪犹未平。
羁离官远郡,虎豹满西京。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
归去在何时,流泪忽沾缨。
忧来上北楼,左右但军营。
函谷行人绝,淮南春草生。
鸟鸣野田间,思忆故园行。
何当四海晏,甘与齐民耕。
——《京师叛乱寄诸弟》
此诗作于兴元元年(784)春。“京师叛乱”即泾师之变,韦应物在其中表达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与愤慨情绪。一方面,因为一支区区数千人且职业素养较差的藩镇军就能将皇帝逼出京师,可见当时的藩镇力量亦或是德宗军事力量部署的隐患;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冲击了李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弱冠遭世难”复刻了诗人弱冠时对于安史之乱玄宗出逃的隐虑与惊伤。对于大历诗人,尤其是经历过承平日久“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燕李录事》)的韦应物来说,很难不“思旧日”,预感为“世难”再现的征兆。因此此次泾原兵于京师的叛乱使“远郡”的韦应物尤为心惊与愤怒。
“忧来上北楼,左右但军营。”北方叛乱,军事吃紧,地方必然也要驻扎备军。建中四年(783)春日,韦应物还是“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寒食后北楼作》)的乐观心态,但与此时相比,可以看出其情感色彩明显分化,痛苦于“行人绝”的民不聊生之景。袁宏道评“‘忧来’四句,写离乱之景,惨恻欲泪”(袁宏道《韦苏州集》参评本)。北楼,是滁州郡城北之楼,韦应物有《寄杨协律》诗云“簟卷北楼风”。与之相似,滁州西楼亦涉及战争描写:
高阁一长望,故园何日归。
烟尘拥函谷,秋雁过来稀。
——《西楼》
此诗情感较为和缓。函谷关的战争给韦应物带来的是雁少、音信缺的故园之思。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东都震骇……哥舒曜为东都畿汝节度使,率凤翔、邠宁、泾原等军,东讨李希烈”[6],二月哥舒曜攻汝州,八月李希烈攻哥舒曜于襄城,九月李勉的部将唐汉臣、刘德信在扈涧全军覆没,汴州军从此一蹶不振,东都危急。韦应物登楼远眺,“烟尘拥函谷”即谓此。而距长安二千五百六十四里、位于淮南道的滁州,与“行人绝”的函谷关相反,在兴元元年(784)春已经无情地“生春草”了,两下对比极为鲜明。末尾两句韦应物从眼前景希冀于国家重归海晏河清,作为士大夫,其展现的平民情怀尤为后世赞赏。唐人重仕宦门第,但韦应物却甘愿为民。纵观此诗,韦应物对于现实的态度是深切关怀甚至是干预的。虽然这种写作方式是“雅”的、隐晦的,怒而不露,哀而不伤,陆时雍《唐诗镜》评曰“忧而不悴。不必垂涕悲伤,意已至已。所谓雅者”,但相比较其他自守式宦滁诗作,已经有很大的情感外露。
从上述诗作可以看出,韦应物对建中之乱的态度复杂。一是“世难激中肠”,鲜明支持畅当参与朝廷军,积极参与地方军事备战。其苦于既往“陪鸳鹭翔”的无所作为,无法得之以“立功”,而建中之乱提供了契机。二是,正因为对现实的关怀与参与,韦应物并不是盲目乐观,其对滁州民生的凋敝和背后深切的原因存在着清醒的认识,有着士大夫尤为难得可贵的恤人之心和平等态度,“韦应物居官自愧,闵闵有恤人之心”(刘辰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太华书院刊韦江州集附录序》)。总之,反映建中之乱的诗歌在韦应物的宦滁诗中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对于全部的韦应物诗歌来说,也是不同的。
二、韦应物书写建中之乱的意义
事实上,韦应物是一个“俗人”。蒋寅说“韦应物诗在高雅的背后,骨子里有股俗气,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高雅的俗气”[3],对韦应物的定位极其准确。到滁之前,韦应物经历了二十余年稳定的京官生涯,历任高陵尉、大理评事、洛阳丞、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功曹参军、高陵令、鄠县令、栎阳县令、比部员外郎,逐步升迁,中间多次寓居精舍,不得不说这对他的仕宦心理和诗歌创作还是很有影响的。上述诗作不是追忆往昔、怀恋故园就是带有京师的相关因素。正因为如此,此次爆发于京师的战乱,以京官外放的审视视角迫使他展露出高洁背后激动且世俗的一面,迫使他走向“行动的文学”。
(一)展现退隐表象下的入世精神
退隐意识实则是韦诗创作的表象。
残花已落实,高笋半成筠。
守此幽栖地,自是忘机人。
——《园亭览物》
挥翰题苍峭,下马历嵌丘。
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
——《游西山》
如上述所示,韦应物在滁州期间的诗作,典型表现为在山水审美中捍卫独立的人格意志,崇尚虚静无为的自然法则,追求排斥情感与感官满足的贵族审美。在这之中,韦应物塑造着僧道交游、种药植树、山水游赏的尘外人形象,因此“向往自由舒适的田园生活,并向佛门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11]。在《答崔都水》中更是有着鲜明的逃避态度:“则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勿厌守穷辙,慎为名所牵。”
但事实上,韦应物做不到完全退隐。与“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李肇《国史补》)恰恰相反,建中之乱诗作暴露了韦应物内心相当“世俗”的一面,体现了其积极的入世色彩:《寄畅当》寄语畅当要“丈夫当为国”,这种英雄形象的塑造是韦应物内心渴望的表现;《京师叛乱寄诸弟》中谴责姚朱等人为“虎豹”,这种直抒胸臆、暗喻褒贬的用词与“忘机人”形成了鲜明对比,韦应物更是在结尾发出“甘与齐民耕”的行为表白;《始建射侯》诗题称“始”,韦应物兴元元年(784)有《答僴奴、重阳二甥》一诗说“西园休习射”,可见来滁三年后他仍有习射行为。而上述诸例与他之前的现实性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广德二年(764)的《经函谷关》总结安史之乱的经验教训,“豺虎起东北”与“虎豹满西京”形成呼应;宝应二年(763)的《广德中洛阳作》对洛阳的二次收复情况进行了批判,笔锋毒辣;大历十一年(776)的《使云阳寄府曹》更是表达了“贱子甘所役”的为民心态。可见韦应物早有入世精神,只是因后期官吏挫折、家庭变故、精舍生活等经历而沉寂,隐藏于后期以隐逸超脱为追求的写作模式中,而此次建中之乱成为了契机。关于这一点,李红霞把握地很准确:“韦应物志尚清虚,其郡斋之隐追慕隐逸的自由超脱,但内心始终萦绕着对功名利禄的留恋。”[12]这种功名利禄,其实是对现实的关怀,心中存有进取的幻想,因此在受到外界的冲击后内心不可避免地产生震动。尤其是发生于长安的白志贞召军、泾师之变等事件,对于有着“京师情结”,生长于天宝盛世光圈“以荫补右千牛”(丘丹《唐故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京兆韦君墓志铭并序》)然后经历安史动荡的韦应物来说,冲击尤其之大。
此外,韦应物也不曾真正归隐。韦应物一直尽力模拟陶渊明,有直接“效陶彭泽”等一系列拟作,写采菊见山之风韵,但终究与陶渊明迥然不同,只是模仿而不是效仿。葛立方评曰:“然渊明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应物乃因意凄而采菊,因见秋山而遗万事,其与陶所得异矣。”[13]不仅此诗如此,韦应物其他遗世之语也如此,只是借山水、郡斋作为退守之处以安慰自己,如“况将尘埃外,襟抱从此舒”(《再游西山》)。就连韦应物自己也不得不在《种瓜诗》中承认“信非吾侪事,且读古人书”,模仿或者是向往陶渊明的名士风流是可以的,但是当真正身体力行、劳作躬耕的时候,“田家笑枉费,日夕转空虚”(《种瓜诗》),韦应物其实是尴尬且不适于田园隐居避世生活的。更何况,“俭德”(丘丹《韦应物墓志铭》)的韦应物难以筹办“采山钱”,这也是他退隐困难之所在。
但这种退而不得的矛盾与尴尬却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正因为他不能完全超脱尘世,不能忘情世事,才心忧民瘼,身勤吏职,而不是像东晋南朝士人那样以放弃社会责任来求得超脱。”[14]这使得韦应物的忧患意识大大加强,对国家社会采取一种关心甚至是干预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在世俗地主真正取代门阀士族的中唐社会转型时期,他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天下亡”责任意识。相较于安史之乱的回忆性质诗歌,如《雎阳感怀》等,韦应物直接书写建中之乱之事,对于当时滁州民生凋敝、赋税严重、征召官兵等社会现实作了如实反映,如“数家砧杵秋山下,一郡荆榛寒雨中”(《登楼寄王卿》),滁州荒芜的描写在韦诗中更是屡屡可见。其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奋身折腰精神,使韦应物从士大夫精神田园走向广大社会,不会“清高到完全没有社会属性的程度”[15]。这种对世俗的奋斗和追求,有利于打破趋避心理,将世俗和“兼济”的儒家传统行为准则连在一起,避免个人主义。总之,建中之乱唤醒了韦应物早期即有的为官责任与热切热情,亦或者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的良心”。
(二)突破高雅闲澹的风格及其表达方式
建中之乱诗风与韦应物一贯诗风迥然不同。沈德潜曾评价韦应物得陶渊明真传,说“韦左司有其冲和”[16]。滁州诗风总体来说仍是韦应物“气象清华,词端闲雅”(徐献忠《唐诗品》)的典型创作风格,实践着自然含蓄的文学观念,如其《闲居寄诸弟》就写“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据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其滁州诗作共计129首,其中相当一部分即如此。韦应物在这种郡斋生活中构建了其亦官亦隐的吏隐空间,“对韦应物诗歌思想艺术风貌产生深刻影响的‘吏隐’思想是在滁州正式形成的”[4],进而形成了为白居易等人激赏的士大夫理想生活。诗风追求清丽空灵,文学观念崇尚自然含蓄,这种表达是雅的、贵族化的:
晦赏念前岁,京国结良俦。
骑出宣平里,饮对曲池流。
今朝隔天末,空园伤独游。
雨歇林光变,塘绿鸟声幽。
凋氓积逋税,华鬓集新秋。
谁言恋虎符,终当还旧丘。
——《月晦忆去年与亲友曲水游宴》
韦应物有《岁日寄京师诸弟端午等》《西涧即事寄卢陟》《寄杨协律》等多首诗亦如此,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写作主题:忆旧,写景,抒情。从“皇闱”到“古山郡”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韦应物经常产生忆旧之思,沉湎于过去“良俦”“曲池”的盛况而唏嘘感叹。在描绘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中,这种写景多为虚景,眼前之景经过提炼与加工,高度概括,点面略过,几无实处而“澄澹精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这种“有我之境”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绿”“幽”的观感色彩捕捉准确,同“沈沈水容绿,寂寂流莺歇(《月溪与幼遐君贶同游》)等相似,鲜明地追求凄清萧散、幽静细密的艺术风韵和审美意境。因此这种环境烘托更能抒写其情——带着隐逸的归宿与渴望,安贫守节,借之以获得尘世的解脱、表达澹然的世外之思。加之僧侣交游和《楞伽经》影响,“韦应物在滁州期间,是他仕历中接触僧人最多的时期”[17],这种明心见性、定慧双休的出世之意也使得韦应物诗作语言是“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馀”[18]:
一来非问讯,自是看山花。
——《偶入西斋院示释子恒璨》
独此高窗下,自然无世情。
——《览褒子卧病一绝,聊以题示》
与这些诗作相比,反映建中之乱的韦应物之诗,就明显展现出另一种姿态,不再是“萧散冲淡”(许学夷《诗源辨体》)的风韵,也不再是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三段论式写法。一方面,它深深冲击了韦应物自娱自乐、对景排遣的“清”诗风,情感显著外露,鲜明地表达出了痛苦而激昂的矛盾语言。韦应物直斥姚朱之流为“虎豹”,直言“军兴”是造成滁州荒榛的原因,不再是“数家砧杵秋山下”中优雅的旁观者姿态,而是记录地方上的凋敝与疾苦,拉近与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在谋篇布局上,韦应物也打破其固有写法。在“忆旧”上,更加关切现实而不是沉溺于追忆,《答王郎中》开篇即写滁州的荒芜。在“写景”上,景象也是具体的“春”草与“秋”雁,详细且沾有滁州气息。其中“军营”“虎竹”“熊侯”更是气势轩昂,语气旷然,与“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寄恒璨》)、“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寄全椒山中道士》)这种“无烟火气”(张谦宜《茧斋诗谈》)截然相反。在“抒情”上,上述建中诗作显著带有“警目”的意味,记录地方上的凋敝与痛苦,体现着韦诗的现实性。基调虽然是痛苦的、波动的、压抑的,但是积极渴望与现实进行交流、干预,并寄托了韦应物的“盛唐”式政治理想——“何当四海晏”。正如“甘与齐民耕”体现的韦应物有着突破门第之见的奉献仁爱精神,此类诗类似于“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是一种“仁者之言”“闵闵有恤人之心”[19]。
综上可知,韦应物在建中之乱诗作中体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态度和创作风格,在书写战乱情况、抒发心理感受的情境下,韦应物产生了相应的积极行为,并产生了在这种相应行为之下的文学作品。在德宗“幸”奉天的时候,韦应物“自郡遣使间道奔问行所在”[20],这是表明政治立场的真正行动。在兴元元年(784)的《寄诸弟》一诗下,韦应物自注:“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师兵乱,自滁州间道遣使,明年兴元甲子岁五月九日使还作。”[9]在诗中不仅批评他们是“兵戈乱京”,更是遣使询问生死存亡情况,可见韦应物对泾原兵变事件的关心与担心。尤其是此时已经是距离泾原兵乱京半年之久的兴元元年(784)五月了,能够接到回信,一个“忽”字、一个“泪”字,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韦应物在战乱形势下的惊喜、激动与感慨,可见韦应物从可有可无的态度变为关怀现实的思想。同时,在建中之乱中后期,韦应物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寄诸弟》外,另有《送中弟》《寄李儋元锡》等,亦是同样的现实性主题。《送中弟》是其在建中时期送弟北上还省归家之作,其中“山郡多风雨,西楼更萧条”,虽是现实描写,亦是山河飘摇的象征。当然对山河忧患表现更明显的是《寄李儋元锡》,写“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来黯黯独成眠”,韦应物因残酷的“世事”而思绪沉重、痛苦,可以看出建中之乱带给韦应物的创伤是难以泯灭的。
三、结语
仕宦滁州是韦应物一生创作极为重要的阶段,诗作数量多,吏隐思想浓重。但是建中之乱一系列事变冲击了韦应物的理想世界和实际生活,打破了其在吏隐思想下将隐逸的感叹、沉浸作为书写对象和创作主题的贵族化文学写作模式。大历之人的萧条逃避、安于一隅的心态在建中之乱诗作中消失殆尽,与其之前沣上诗作“清微简澹”“中唐雅语”(袁宏道《韦苏州集》参评本)的风格也明显相异。事实上,韦应物本远离建中之乱发生地,但是却完全没有回避现实,不仅直接书写建中之乱,同时在其他诗作中也展现了建中之乱的影子。这其中投笔从戎、慷慨激昂、赋税繁重、民生凋敝、故园之思等复杂情感,显示出韦应物在至澹至泊之外风骚的现实性一面。韦应物的宦滁诗不仅是高雅的、吏隐的,更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