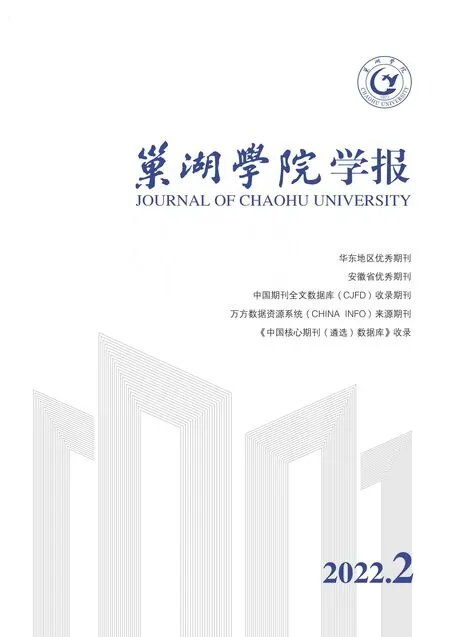从葛蕾特形象看《变形记》中父权秩序的消解与重构
基语馨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引言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文学代表作,正如其他的表现主义作品一样,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已被相当程度地抽象为象征的符号,其目的似乎在于表现文本表象下所蕴含的深刻内涵。正因如此,历来学者对《变形记》的阐释也就自然而然地安身于以符号表象与本质内涵所构成的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中,目标是探寻某一恒定的深度主题,如借变形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又如以威严父亲的表象寻找卡夫卡作品中潜藏的俄狄浦斯情结。放弃这一二元对立来对卡夫卡作品中的某一人物形象进行深入考察则被认为是舍本逐末。但随着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了追寻文本单一原意的信仰,而将目光聚焦于文本间的互文性,给予了表现主义文学更多阐释的可能。若对表现主义的“前见”进行解构,则不难发现在《变形记》中并非所有的人物形象都只是作为表现符号存在,人物性格的转变包孕了更多的意义可能性有待解读。
一、葛蕾特形象之变异
小说中主人公的妹妹葛蕾特在其性格发展中存在着由“情感本位”向“权力本位”的变异,而此变异的发生是以“葛蕾特喂养甲虫(格里高尔)”这一情节为界点的,在“喂养甲虫”的过程中葛蕾特从“失语的女性”逐步获得话语权,这使其变异过程带上了女性主义的色彩。
(一)“喂养”之前——以情感为本位的天使形象
葛蕾特在文本中的首次出场就表现出明显的“情感本位”的特征。小说开头,当一家人发现本应辛勤工作的格里高尔却仍在房间里之后,便想方设法试图将格里高尔从私人空间拉入“正常秩序”中。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葛蕾特的出场被叙述者紧紧地安排在父亲出场的前后,并巧妙地与其构成三组对立项。以下将就相关文本逐一分析。
第一组对立表现在二人对格里高尔的催促中,父亲用拳头叩击房门警示并以低沉的声音警告,而葛蕾特却以轻轻的悲哀的声音询问哥哥的身体情况,它构成了话语上的威胁与关爱间的对立;第二组对立表现在二人对秘书主任上门一事的行为回应中,在父亲殷勤地向秘书主任谄媚时,葛蕾特则用耳语向格里高尔通报消息,它构成了行为上的虚伪与单纯间的对立;第三组对立表现于二人在得知格里高尔得罪了秘书后的情绪态度中,“左边的房间里是一阵令人痛苦的寂静”而“右边的房间传来啜泣”[1],它构成了心智上成熟与稚气间的对立。由这三组对立中可以发现,葛蕾特的形象在一开始便展现出关爱、单纯、稚气等特性,而与父亲以利益为本位的性格截然相反,葛蕾特的原始性格中存在着更多的情感本位的要素。
这些要素反作用于葛蕾特并将其塑造为一个“天使”。吉尔伯特和古芭首次阐释了西方19世纪前期文学中由父权社会塑造出的两种虚假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她们作为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神话原型”,潜藏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尽管与现实中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并不相符,但由于顺从了男性作家与批评家的性别偏见和把女性置于从属地位的愿望,这种扭曲的形象模式在20世纪前的西方文学界中未能获得应有关注。在西方19世纪前期的文学中泛滥着由男性凝视所建构的理想女性形象,她们往往被描述为善良、温柔、顺从、无知,积极遵守着父权秩序的规定,成为男性审美下的“天使”。而葛蕾特在父亲的对比之下,在对哥哥格里高尔无私的关爱、单纯的帮助与幼稚的情感表露中完成了天使形象的自我塑造。
文本中的葛蕾特不仅存在于叙述者所叙述的空间里,而且被笼罩在哥哥格里高尔的凝视下,格里高尔视角下对葛蕾特的书写为人物塑造提供了另一个特殊的侧面。首先,妹妹的啜泣在格里高尔的凝视下被置换为“天使的惩罚”。文中格里高尔因为妹妹的哭泣而陷入自我怀疑:“他妹妹为什么不和别的人在一起呢?她也许是刚刚起床,还有没穿衣服吧。那么,她为什么哭呢?是因为他有丢掉差事的危险吗?”[1]在格里高尔的凝视下,葛蕾特被塑造为过惯了舒适生活的幼女形象,而这个一直以来无忧无虑的天使的哭泣声则被格里高尔视为对自己因变形而被逐出集体的惩罚。其次,妹妹的离场在格里高尔的凝视下被置换为“天使的出走”。在这里,格里高尔又将葛蕾特塑造成符合男性理想的圣女形象,他期望妹妹以“女性”的身份在场从而挽救当前的异常形势,相信“总是那么偏袒女性的秘书主任会乖乖听她的话”[1]好让自己重返集体。而妹妹的理想在格里高尔的凝视下最终被置换为“天使的职责”,葛蕾特在格里高尔的话语中被彻底地剥夺了挣钱养家的义务,与“挣面包”的世俗不同,葛蕾特被格里高尔赋予了更加“诗意”的职责——拉小提琴,进而被塑造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艺术性的存在而非俗世中生存的个人。
综上所述,在葛蕾特发现格里高尔的异常直至开始喂养甲虫的这一段叙事时间中,葛蕾特的人物形象基本被塑造为一个以情感为本位的天使形象,这种塑造不仅见于叙述者对情节的描述,而且同时潜伏于格里高尔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下,使葛蕾特丧失了个体性特征,正如吉尔伯特所认为的那样,“不管她们变成了男人眼中的艺术对象还是圣徒,她们都回避了她们自我”[2]。
(二)“喂养”之后——以权力为本位的妖妇形象
葛蕾特在困境之中主动承担起了喂养甲虫格里高尔的责任,然而,正是在“喂养”的过程中葛蕾特的人物形象发生了由“天使”向“妖妇”的变异。“妖妇”处于天平的另一端,往往被描述为风骚、凶狠、多嘴、自私,是“不肯顺从、不愿放弃、自私、不恪守妇道的女人”[3]。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三类:男性化的女人、悍妇形象与欲望化身的妇女形象,而在变异后的葛蕾特的身上则不难发现这三种形象气质的踪迹。以下将就葛蕾特人物形象与性格变异的过程做具体分析。
首先,葛蕾特的形象由单纯无知的“幼女”蜕变为具有男性智慧的“男性化的女人”,主要表现在人物行动力的增强上。在小说第一章的叙述中不难辨认,此时的葛蕾特是缺乏行动力的,如面对混乱场面,葛蕾特自始至终除了哀求之外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即使被父亲命令去为格里高尔求医,后文也没有对她求医的结果做出任何的补充叙述。可见,身为一个以情感为本位的“天使”,葛蕾特在行动上却是萎弱无能的。然而,在承担喂养甲虫的职责后,葛蕾特却展现出了强于任何人的行动力:她给格里高尔带来甲虫爱吃的腐食,将椅子推到窗前供他眺望窗外,甚至为方便他自由爬行而把挡路的家具都搬了出去。葛蕾特行动力的增强成功动摇了原先被建构的“天使形象”,她从女性化天使变成了一个男性化主权者,将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划归为一种“例外状态”,即“在该状态下,生命不再具有‘公民’身份,被排除在它本应受到保护的空间外,缩减为赤裸生命”[4]。在决断例外状态的过程中,葛蕾特作为主权者以强大的行动力将格里高尔彻底从“人的社会空间”中剔除,使其作为一条赤裸的“虫的生命”存在。
其次,葛蕾特的形象由远离俗世的“圣女”变异为泼辣凶狠的“悍妇”,主要表现在人物话语权的获得上。葛蕾特在承担喂养甲虫的职责前几乎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她被迫置身于这场闹剧之外。然而,当她从喂养甲虫的职责中建构出一套权威性的话语系统之后,权力通过话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影响着这个家庭中每个人的命运。一开始,葛蕾特的言语是由叙述者代为叙述的:“葛蕾特夸大了哥哥环境的可怕,这样……除了葛蕾特是不会有别人敢于进去的。”[1]获得话语权的葛蕾特号召母亲将房间内的一切搬空,并通过话语塑造了格里高尔所处环境的可怖,得以彻底地将格里高尔建立为他者,而他者的建构目的恰恰在于确证自我,葛蕾特通过话语权的获得不仅剥夺了格里高尔重返主体的权力,而且确证了自身话语的真理性。之后,葛蕾特的言语便以更直接的形式即间接引语表达出来。在三个房客因格里高尔的突然出现而愤然退租后,相比于父母的沉默,葛蕾特显然掌握了话语权:“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点不是了。”[1]经此,所有人便在葛蕾特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达成了共识——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赶走格里高尔。
最后,葛蕾特的形象由高雅的“艺术性对象”堕落为“欲望化身的妇女”,主要表现在人物身体活动上。葛蕾特的爱好是拉小提琴,变形前的格里高尔也曾把送妹妹进音乐学院作为自己奋斗目标。但是,自家庭发生了变故之后,葛蕾特不仅承担起看护格里高尔的职责,而且为了帮扶家庭同时做着售货员的工作。直到在小说第三章,“小提琴”再度出现。但此时它对于葛蕾特而言并非艺术的追求而变成了讨好房客的手段,是父母为了吸引房客留租而举办的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在他们的凝视下是这已不是艺术的表演而是一次“献身”。更加讽刺的是,这次献身并没能让这些男人满意,房客“对原以为是优美悦耳的小提琴演奏已经失望,他们已经听够了”[1]。如果说在这个为了欲望的献身行为中,葛蕾特的眼睛仍是“专注而悲哀的”,那么小说最后写道在搬家的旅途上,葛蕾特“仿佛为了印证父母为她找到个好女婿的打算”,而“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就意味着葛蕾特正式从欲望的羞耻中解脱,而利用身体使自己于男性凝视下如鱼得水地生存。梅洛-庞蒂认为人通过身体与世界联结,“身体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种手段,一种组织”[5],葛蕾特对自己身体的展示恰恰隐喻了她存在的方式。
综上所述,在葛蕾特承担起喂养甲虫的责任直至甲虫死后一家人开始踏上搬迁旅途之间的这一段叙事时间中,随着人物行动力的增强、话语权的获得以及对身体活动的描写,葛蕾特的人物形象逐渐由男性视域下的“天使”变异为“妖妇”。这类女性形象对男性而言是一种威胁和挑战,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形象恰恰是女性创造力对男性压抑的反抗形式。
通过对变异过程的对比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在葛蕾特身上存在着一种跨越式的“生成”,“生成”是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德勒兹提出的文论概念,所谓“生成”就是一种生命持续增强的力量,并永远在创造“可能性”。“这种生命知道如何依据所遭遇的力量转换自身、使自己变形,并总是与这些力量组合成一种更大的力量”[6]。葛蕾特正是在承担喂养职责的过程中以权力和欲望生成了自己,她的行动是其从美梦中清醒而面对残酷现实的必然,她的话语拥有着远比哭泣更强的威力,而她去音乐学院的理想与其琴技平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葛蕾特对于自身完美形象的一种揭穿,这些最终将葛蕾特由一个梦幻中生命萎弱的、懵懂无知的少女,生成为现实里行动果断的、善于掌控的领导者。
二、传统父权秩序的消解
葛蕾特形象由“天使”向“妖妇”的变异发展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它必然体现于角色所处的人物关系网络中,甚至打破原有系统的平衡以触发整个人际系统内部秩序的变异。葛蕾特形象的变异性使她既不单纯地作为父权秩序的受害者而与“反抗者”格里高尔处于完全相同的阵营,同时也不作为父权秩序的顺从者而能够与身为“维护者”的父母和睦相处。由此可见,《变形记》中的人物关系绝非处于一个静止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它们构成了一个不断解构又重构的多义性的动态系统,而具体演变的过程就是通过人物间的矛盾对抗而呈现的。正是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由非理性的传统父权秩序出演的悲剧终于落下帷幕。
(一)葛蕾特与格里高尔——父权秩序下个体的融入与逃避
传统卡夫卡批评认为,格里高尔是作为父权秩序下被异化的个体而存在的,正如上文所谈到的,即使受尽畸形的家庭与社会秩序剥削,格里高尔却仍对重返集体充满渴望,这正是“异化”的表征。然而不难发现,变异前的葛蕾特同样也是父权秩序下的受迫害的个体,虽然叙述者与格里高尔在一开始有意将葛蕾特塑造为受人宠爱的“天使形象”,但在建构出一个“天使”的同时葛蕾特的个体性也消弭了,于是在父权秩序捏造的镜像中,葛蕾特只是一个无用的女儿和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然而当葛蕾特形象发生变异后,她与格里高尔便发生了分歧。格里高尔变形为没有利用价值的甲虫,使他在父权秩序之中彻底丧失了话语权,此时在他的心中呈现出两种矛盾的“暗语”:一种宣布其仍向往回到原先的秩序中,而另一种却诅咒着“人类世界”的一切异化并越发渴望像虫子般活着。不难发现,随着叙事的进程,后一种“暗语”最终压制了对重返秩序的渴望而占据上风。“暗语”的出现恰恰表明格里高尔自我意识的增强,而“虫化”的行为正是它逃脱原有父权秩序,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但是,变异后的葛蕾特却选择了与格里高尔相反的道路。在格里高尔失语后,她通过承担看护甲虫的职责而逐渐在父权秩序中建构了新的话语。
话语,在福柯的理论范畴中是一种陈述,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限制和约束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或建构有关知识的方式”[7]。从挑选食物到挪动家具的位置到最终彻底将房间搬空,葛蕾特一步一步将原本在“人与虫”之间游移的格里高尔浸透在了“虫”的话语之中,以新的知识型分裂传统父权所一直维系的“集体”。葛蕾特既不像变形前格里高尔那样对传统父权五体投地,又不如变形后的甲虫那样逃避集体以实现个体自由,而是将自己建构为话语权力的新主体,如变形后格里高尔“常常听到父母对妹妹的行为表示感激……在妹妹替他收拾房间的时候,老两口往往在门外等着”[1],这恰恰证明了新主体不仅获得了原有秩序的认同,而且顺利地融入其中。同是父权秩序下艰难生存的个体,格里高尔选择了以逃避集体而保存个体的方式反抗父权,而葛蕾特则以“同流合污”的方式融入集体、更新集体,最终演变成话语权主导者对失语者的全面控制。
(二)葛蕾特与母亲——父权秩序下女性的叛逆与顺从
在卡夫卡的众多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往往被塑造为父权秩序的维护者。然而,《变形记》中的母亲对于父权秩序的维护却被书写得更加隐蔽。首先,母亲的存在方式即是“离场”。相对于格里高尔在小说中引发的三次骚乱:阻截秘书离去、阻止葛蕾特搬走画像和出现在房客面前,文本中三次写到母亲的受惊昏厥,而昏厥实则意味着“离场”,意味着在父权秩序中的示弱。然而,“离场”同样是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离场同时是一种“介入”,每当父亲与葛蕾特做出行动以惩罚骚乱的“罪魁祸首”格里高尔时,母亲总是以“昏厥”的方式提前离场,这恰恰保证了父权秩序的运行无碍。而且,母亲还是格里高尔逃离集体而确立自我的最大阻碍。小说中母亲对儿子的“真情呼唤”无异于塞壬的歌声,正如海妖以美妙的歌喉使本想逃离大海的奥德修斯在其幻觉中沉醉于塞壬的诱惑,母亲嚷着要进去瞧瞧儿子、坚称要为他保留原来的家具实则是为了将“已经濒于忘记一切”的格里高尔从寻求自我的道路上重新拉回至毁灭自我的父权秩序中。
前期的葛蕾特与母亲同作为父权秩序下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父权秩序的融入。然而,当葛蕾特通过看护格里高尔的方式获得了话语权,成为了权力中心的一员后,她与母亲二人的身份于同一中开始分裂,对原有父权秩序的叛逆是她与母亲之间存在的最大矛盾。小说中,葛蕾特因母亲私自打扫了格里高尔的房间而与她发生了争执,因为“她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格里高尔事务的专家了”[1]。由此可见,掌握了话语权的葛蕾特意图建构一个由话语构成的“真理的体系”,她赋予了自己“专家”的身份,作为一个新的中心对传统父权的中心进行反叛。所以,尽管葛蕾特试图将自己与父母纳入同一个主体,然而她绝不满足于此,葛蕾特敏锐地感知到母亲以及其效忠的父权秩序实际上有悖于她建构一个新的权力主体的目标,而后文葛蕾特在精神崩溃的父亲面前做出的一番激烈演说正是她在摇摇欲坠的父权大厦前摆出的一种挑战姿态。如此,母亲对父权的软弱顺从和葛蕾特与之争权夺利的反抗构成了另一个矛盾,看似爱护儿子的母亲实质上只是父权操纵的傀儡,而葛蕾特的叛逆形象在女性主义批评的透视下最终却呈现出女性在父权秩序下与之周旋并伺机而动的崛起意识。
(三)葛蕾特与父亲——父权秩序内部的对抗
传统卡夫卡批评将“反父权”作为卡夫卡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他们认为“父权”在卡夫卡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至上权威,它往往以“蛮横”与“荒诞”的形式对异化个体进行压迫与控制。的确,在卡夫卡的众多作品中的父亲都呈现出父权秩序中的主导者的形象,他们善于以无端的狂怒与理所应当的残暴恫吓妻子与儿子,使其对自己臣服。《变形记》中的父亲形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典型。在知道格里高尔失去赚钱养家的功能后,父亲为了保证父权秩序的合理运行,以主导者的姿态对格里高尔展开了一系列“去主体化”的暴行,如追赶私自逃出房间的格里高尔,为阻止其逃脱而用苹果将他打伤。
值得注意的是,父亲在对格里高尔施以暴行后总是伴随着某种“补偿”,如被苹果打伤的格里高尔之后发现“每到晚上……起居室的门总是被大大地打开,这样他就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这大概是他们完全同意的”[1],他被父亲再次给予了重返家庭、重返集体的机会。除此之外,父亲日渐疲乏衰弱的身体与精神也预示着父权秩序的外强中干和难以为继:“他总想在桌子旁边再坐上一会儿,可是又总是重新睡着”[1]。另外,小说后半部分家人间因格里高尔而爆发的争吵越发频繁,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变异后的葛蕾特使得原本统一的父权秩序产生了分裂,同时也代表着父权秩序内部的权力对抗带来的混乱。
葛蕾特在对传统父权秩序的融入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对抗性,而这对抗性来源于与传统父权秩序运作形式之间的矛盾。与传统父权的非理性、外显性相对,葛蕾特的权力运作形式朝着更加理性化、隐蔽化的方向演变,其主要表现为以渗透代替压迫、以话语代替暴行。首先,葛蕾特能够抑制格里高尔重返集体的欲望并将他建构为一个作为他者的“它”,靠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对其进行“虫化”即个体化的渗透式规训。比起父亲的“拳脚交加”的惩罚模式,葛蕾特为格里高尔塑造了符合虫性的日常生存环境,令他在个体肉身的舒适中主动放弃对集体的幻想。这就是福柯所提出的“现代社会隐形的规训机制”,即规训方式由作为公共景观式的惩罚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规定与计划,规训的对象也逐渐从肉体转向灵魂。非理性的暴行是权力作用最低级的形式,而话语作为另一种压迫的形式更具理性与隐蔽性。在小说第二章,格里高尔因母亲昏厥而前来帮忙,这一行为却经由葛蕾特之口被“过于简单地解释”成“格里高尔逃了出来”,直接导致了父亲对格里高尔又一次的暴行。葛蕾特不仅通过话语的魔力操纵了愤怒中的父亲,还抓住机会在“父权”示弱之时以话语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权威,以“甲虫专家”的身份阐述了赶走格里高尔的必要性,令之前鄙夷她为“不听话的女人”的父亲不由转变了态度称:“她说的对极了!”至此,随着父权中心的臣服,传统父权秩序已然瓦解。
综上所述,葛蕾特通过将自我纳入集体,并在融入过程中与之对抗,最终建构自我为新的权力主体,并消解了原有秩序。
三、父权秩序的重构及文化反思
通过自身话语权的获得、行动力的增强以及身体活动的表现,葛蕾特展示了其人物形象的变异过程,而个体的变异则以一种反抗的姿态在人物关系网络中动摇了传统父权秩序的稳定性,具体表现为格里高尔的分裂与父亲母亲的示弱,完成了父权秩序的消解。然而,解构的目的始终指向重构。葛蕾特的“胜利”不仅意味着由父亲所代表的“父权本位”的式微,更意味着一种与非理性父权秩序对立的理性权力秩序的诞生。而理性权力秩序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葛蕾特就此凭借女性的身份崛起而改变了传统父权制下的异化状况,相反,个人权力的膨胀之下隐藏的只有危局。
(一)父权秩序的重构
葛蕾特所建构的一种新兴的权力秩序与传统父权秩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具有理性的特质。传统父权通过暴力和公开惩罚的方式来维护其秩序,而新兴的理性权威则通过非暴力、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得以扭转羸弱的传统秩序以建立新秩序。这种渗透主要依赖于权力主体葛蕾特的话语和行为的力量,二者背后皆隐藏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
1.将个体唤为主体——隔绝父母与甲虫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取消了人在行动中包含任何思想的可能性,它以信仰和行为将没有主体性的个体唤为主体,从而达到欺骗个体的作用。在原先父权意识形态构成的秩序中,葛蕾特作为“无用的女儿”与格里高尔同作为个体被动纳入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主体中。而在重构新的权威秩序时,葛蕾特通过喂养甲虫、搬空家具等行为将父母与格里高尔隔离,主动建构了“动物—人”的对立,她向父母宣称:“如果这就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和动物是不能一起生活的”[1]。这不仅将父亲与母亲召唤为由自己建立的主体——“人”,更是将“格里高尔”与“人”彻底地对立起来,通过话语权构建了“常”与“非常”的等级结构,使个体主动从旧的父权秩序中脱离,从而被召唤进入以葛蕾特为权力主体所建立的新秩序中。
2.个体对主体臣服——建立新的知识权威
在意识形态将个体召唤为主体后,下一步就必然要使个体对主体绝对臣服,即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而深信不疑。在小说中,葛蕾特在掌握了有关格里高尔一切事务的话语权后,建立了新的知识权威,潜移默化中使原有权力秩序主体向新主体臣服,如“在她收拾房间的时候,老两口往往门外等着”。而当母亲私自打扫了格里高尔的房间时,父亲却站在葛蕾特一边训斥妻子多管闲事。可见,即使父亲在表面上似乎仍在行使他作为主体的权力去恫吓不服管教的个体,但“葛蕾特负责格里高尔的一切”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父亲深信不疑的“准则”,理性权力秩序正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消解非理性的父权秩序并且重构自身。
3.主体与主体相认——形成命运共同体
阿尔都塞认为,当一个虚幻的主体被建构出来之后,人便不断地通过各种意识形态仪式,使自己与主体相认,即维护主体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小说前半部分,原有秩序的运行是以父亲为主导,即使父亲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葛蕾特在格里高尔方面的权威,但他还是通过训斥妻女与暴力对待儿子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父权秩序的正常运作。然而在小说最后,以葛蕾特为主导而建立起的新权威赢得了父母二人的“膜拜”,最终成功重塑了意识形态主体并且完成了主体与主体的相认。之后格里高尔再次向三人爬来时,父亲已无力再次通过暴力驱赶,而是“张开双臂仿佛要保护葛蕾特似的”[1]挡在她的前面,这种种便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仪式的表现,这种仪式在父亲与葛蕾特之间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联结,维护葛蕾特就是维护新秩序的合法性。就此,葛蕾特重构父权秩序的任务完成了。
(二)葛蕾特权力获得之文化反思
葛蕾特突破了男性凝视下天使形象的枷锁而对传统父权秩序进行解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加隐蔽也更有威力的新型权力秩序的诞生,葛蕾特通过这一秩序代替父亲成为了新的压迫者。在当代女性主义的文化语境之下,似乎很难将其定性,葛蕾特身上女权与反女权表征的共同存在恰恰暗示着当代女权文化的暧昧性。“女权”首先是以权力的形式存在的,因此通过葛蕾特权力之获得对女权文化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
1.以福柯话语理论看权力归属性问题
葛蕾特所建立的新型权力秩序形式主要以话语为导向。“话语”是福柯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认为“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6],从而形成理论构架。小说《变形记》中,在以葛蕾特为统治意识形态的话语领域的建立过程中,实际包含着多种话语的争锋。
每个人物形象都在其发展过程中塑造着自己的话语。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处于“失语”状态,但他在内心建构了属于个体性的“暗语”,从而将自己与整个父权秩序剥离复归自我意识,“人变成甲虫,丧失语言能力,这是从隐喻的层面,也是从本质的层面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8],他的失语恰恰是对整个父权秩序下“他人即地狱”的否定;而父亲自始至终处于“疯语”的状态,他对儿女的谩骂既无法恢复格里高尔的主体性又不能阻止葛蕾特最终的“篡权”行为,在父权话语的尖锐铠甲之后隐藏的却是非理性的虚无与软弱;母亲则在小说中处于“弃语”的状态,父权秩序的规训使她放弃任何演说的机会,而总以“惊叫”和“祈祷”来为父权话语作“伴唱”,母亲的“弃语”表现出对父权话语的绝对忠诚。而这些话语最终在葛蕾特面前隐退,原因在于她的话语背后有着不断上升的权力作为强力支撑。
葛蕾特之所以能够代替格里高尔说话,归根结底在于她在喂养格里高尔的过程中获得了看护权。而权力能够被真正地“获得”吗?福柯认为权力不是单向运作的:“监狱的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了一起”[9]。权力并不是被固定在某一端的,“而是在运用过程中得以传播、扩散;权力不仅是集中于某些机构或阶级,而是有无数的作用点”[10]。卡夫卡显然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小说末尾,由格里高尔所引发的骚乱已经随着他的死亡彻底销声匿迹,而在这时“老两口几乎突然发现……女儿已经成长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了……该给她找到一个好女婿了”[1]。如此,当葛蕾特以话语建立的知识领域失去效用之后,权力又从她的手中回到了父母那里,预示着新型的权力秩序也将在原有父权秩序的卷土重来中瓦解。
2.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权神话
葛蕾特的形象成功地由男性凝视下的“天使”转变为反抗父权中心主义的“妖妇”,直接导致了传统父权秩序的变异与消解。这样的解读似乎颇具女性主义批评的色彩,然而实际上福柯的权力理论已经使这个“女权的神话”不攻自破。女权主义旨在男女平等的实现,而并不是解构父权中心主义后再建构另一个中心主义,如葛蕾特照看格里高尔的目的从一开始的出于亲情到最后只为证明自己比父母更高明,她在解构父权秩序之后建构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压榨个体的集权秩序。“妹妹葛蕾特权力意识的觉醒代替了格里高尔在家庭中的地位,所以在小说最后,格里高尔的死不仅没有让家人感到悲伤,反而如释重负”[11]。
权力的流动永远是跨阶级的,但不论是在父权中心主义还是女权中心主义下,个体的权益都是无法保障的,在集权之下“底层的人民”将永远无法获得话语权。当权力的齿轮由葛蕾特再一次转向父母之时,她那“青春活力”的身体也必将再次成为男性凝视下的“拍卖品”,新主体的泡影之下永远是被异化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葛蕾特的崛起仍然是父权主义的崛起,由女性建构权力秩序也许仍然是另一种集权秩序的延续。
四、结语
卡夫卡的《变形记》不仅为文学批评实践提供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而且还在文本之外激发了对社会文化思潮的辩证思考。通过对葛蕾特形象横纵两方面的考察,福柯笔下隐形的现代权力机制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呈现了自身,葛蕾特与父权秩序的争权夺利实则是权力在两极之间的游戏。正因如此,葛蕾特的获胜不能代表女性的获胜,对《变形记》的女性主义阐释也不能将其圈禁在“性别问题”之中,恰如德勒兹所认为,卡夫卡极力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欲望的幻觉。他在以文学告诫耽于权力的“沉迷者”勿要受其操控的同时,也提醒着摆脱幻觉的“清醒者”小心跌入另一种幻觉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