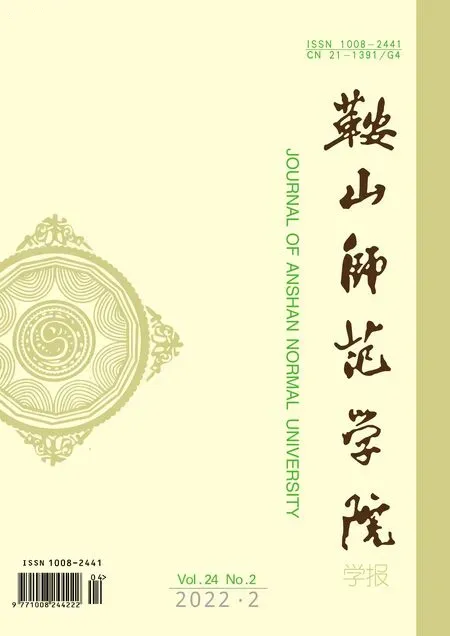汉代“鼓吹”与先秦“恺乐”的关系辨析
谢 芳
(莆田学院 音乐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鼓吹”一词自汉代出现后,历代文献中常见与之相关的其他称谓,如“恺乐”“短箫铙歌”“黄门鼓吹”“骑吹”“横吹”“军乐”“吹打合奏”等.关于上述相近称谓的界说与辨析,曾引发一场隔空争论.最早是南朝宋沈约《宋书·乐志》“鼓吹”条从时间角度对“鼓吹”与“短箫铙歌”“恺乐”“箫鼓合奏”“骑吹”“黄门鼓吹”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论说了自己的观点;时隔五百载,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题解,征引沈氏未曾提及的文献对沈说予以驳斥并做出了自己的概念判定.这场辩论汇集了汉魏“鼓吹”概念的诸多早期散佚文献,今人讨论汉代鼓吹乐,征引文献也大多出自其中.沈、郭二人的考述与论说涉及“鼓吹”概念的诸多议题,如区辨“鼓吹”与其他称谓的标准、“鼓吹”所指范畴的历史演变,等等.
《宋书·乐志》“鼓吹”条与《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关于“鼓吹”概念的论述与区辨,可归纳为如下两个议题:一,先秦有无“鼓吹”;二,“鼓吹”的“通名”与“专名”说.
关于议题一,两文本的观点一致,均不认同先秦已有“鼓吹”的说法.沈约认为,其一,作为乐种概念的“鼓吹”,与先秦指称演奏方式的“鼓吹”语词有本质区别;其二,“鼓吹”是“非八音”属性的乐种,与先秦“八音”范畴的“箫鼓合奏”也不可同一而语.郭茂倩认为,与后世“鼓吹”性质一致的“鼓吹”概念,应始于汉初班壹雄朔野之“鼓吹”.
关于议题二,两文本的说法略有不同.沈约认为,汉代“鼓吹”是乐种专名,仅指用于殿廷宴乐的“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骑吹”因使用场合、用途与“黄门鼓吹”不同,尚未称作“鼓吹”,故作为乐种专名的汉代“鼓吹”并不包含“短箫铙歌”与“骑吹”.“鼓吹”作为通名的用法,始于魏晋.郭茂倩则认为,从使用场合与用途的角度看,汉代“鼓吹”不仅用于殿廷宴享,也用于出行仪仗与军事,因此,汉代“鼓吹”已是乐种通名,包括“黄门鼓吹”“短箫铙歌”“横吹”等名目,只是“黄门鼓吹”“短箫铙歌”“横吹”作为“鼓吹”的不同形式,各自侧重的使用场合与用途有所不同,即“所用异尔”.
基于以上认识,今人关于汉代“鼓吹”源于先秦的说法(视汉代鼓吹为军乐,与先秦“恺乐”一脉相承)有待商榷.本文从以下两方面对此展开进一步讨论,一是分析“军乐”说的文献依据,二是考察秦末汉初进入宫廷之前的边地“鼓吹”的性质与功能,论证边地“鼓吹”与先秦“恺乐”的本质区别.
1 汉代鼓吹“军乐”说的文献依据
学界至今较为普遍的论断是:先秦军乐乃汉代鼓吹乐的前身.黎国韬[1]认为,鼓吹乐原出中国之军乐,后受胡乐之影响而逐渐形成,中原乐与胡乐之比较中,前者稍占优势.张芳梅等[2]有“鼓吹,为马上演奏的军乐”之说.宋新[3]也持相同观点:“由西周军乐所开创的新型器乐合奏形式,正是汉代鼓吹乐的重要渊源.”于雨琴[4]强调汉代鼓吹乐与先秦恺乐的渊源关系,“先秦时期的鼓吹乐原先并不称之为鼓吹,而为‘恺乐’”,“西周、春秋时期鼓吹乐是一种军乐用乐,其功能就是振武扬威,只是当时并未称之为鼓吹,而是叫作‘恺乐’罢了.”
以上代表性观点的文献依据主要有三:《后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东汉蔡邕“汉乐四品”说、南朝宋沈约撰《宋书·乐志》、晋人孙毓撰《东宫鼓吹议》.为方便讨论,将此三段文献材料抄录如下:
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师)大(捷)(献)则令凯乐,军大献则令凯歌”也[5].
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哥.”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6].
鼓吹者,盖古之军乐,振旅献捷之乐也[7].
上述三段引文中,东汉蔡邕最早提出“军乐”说.但蔡邕“军乐”说仅针对短箫铙歌而言,与鼓吹无涉.在“汉乐四品”说中,蔡邕采取了分别论述黄门鼓吹与短箫铙歌的方式,因为,在蔡氏看来,此二类音乐明显不同.蔡氏从两方面对黄门鼓吹与短箫铙歌进行区辨:一方面是音乐用途,黄门鼓吹是“天子宴乐群臣”之用,短箫铙歌是“军乐”之用.另一方面就是渊源,就黄门鼓吹而言,蔡邕将其与先秦的君臣宴乐场景相联系,“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意思是说,用于天子宴乐群臣的黄门鼓吹乐,应上溯至先秦宫廷宴乐;就短箫铙歌而言,则应上溯至黄帝时期,“黄帝、岐伯所作”,后经历周代振旅献捷之“凯乐”“凯歌”阶段,最终发展成为短箫铙歌.由此可知,蔡邕“军乐”溯源说的对象与内容很清晰,仅指短箫铙歌,无关黄门鼓吹.
蔡邕“军乐”说是否适用于汉代鼓吹乐的溯源,还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黄门鼓吹之类的汉代鼓吹乐与短箫铙歌是什么关系?笔者以为,在汉代,二者间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短箫铙歌与黄门鼓吹并列,皆隶属汉代鼓吹乐的范畴;其二,短箫铙歌不是汉代鼓吹乐.若是前者,蔡邕“军乐”溯源说也可用于汉代鼓吹乐的溯源,“先秦军乐乃汉代鼓吹乐的前身”的论断可成立;若是后者,则情况相反.对此,沈约《宋书·乐志》中有明确回答,“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此时”即汉代.沈约述及鼓吹乐时,首先是对鼓吹乐的界定,“鼓吹,盖短箫铙哥”.从时间上看,这一界定应视为沈约所处年代时人对鼓吹乐所持有的一种普遍认识与观念.此番界定之后,是沈约对短箫铙歌的源头以及鼓吹乐发展的梳理.
关于短箫铙歌(鼓吹乐)的历史发展与演变,沈约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黄帝时期.沈约直接引用蔡邕对短箫铙歌的注解,将短箫铙歌上溯至黄帝时期的军乐.
第二阶段是先秦.沈约仍然沿用蔡邕对短箫铙歌的说法,将西周恺乐视为短箫铙歌的前阶段.此外,沈约还辨析了战国雍门周与孟尝君对话中提及的“鼓吹”一语,认为此语并非后世汉代“鼓吹”之类的“乐名”.史料记载,雍门周乃鼓琴名家,“尝于孟尝君,引琴而鼓之”[8],据此推测,沈约所言“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句中的“鼓”与“吹”应理解为演奏方式,“鼓”指鼓琴,“吹”指吹奏竽、籁之类的丝竹乐器.
第三阶段是汉代.述及短箫铙歌在汉代的情况时,沈约仍然将短箫铙歌与黄门鼓吹分而论之.首先,沈约论述短箫铙歌,“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沈约此论断的依据是汉代应劭《卤簿图》,“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箛.箛即笳,不云鼓吹”.箛、笳与角相同,都是吹奏乐器,“笳、箛一物,今人亦谓之角,或吹鞭,或卷木皮、芦叶而吹之.笳、箛、角,一声之转,凡吹笳者,皆为角声,且以其卷皮叶如角,故谓之角”[9].魏晋之后多用于军旅,成为军乐乐器.沈约作为南朝时人,依据笳、箛、角等军乐乐器的性质,将汉应劭《卤簿图》所述“骑执箛”的演奏视为军乐,是有可能的.再联系沈约一再强调短箫铙歌的前身是军乐的论断,可作出如下判断:沈约将汉应劭《卤簿图》中的“骑执箛”之类的军乐等同于短箫铙歌,据此得出结论,作为军乐的短箫铙歌,在汉代并未称之为鼓吹.之后,沈约又述及黄门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结合沈约的表述,“短箫铙歌,此时未名鼓吹”与“而汉世有黄门鼓吹”两句,采用“而”字连接,我们可作如是理解:沈约指出了鼓吹乐在汉代的发展状况,此时只有黄门鼓吹乐,而短箫铙歌尚不属于鼓吹乐的范畴.
第四阶段是魏晋时期.沈约首先叙述了魏晋时期骑吹与鼓吹的关系演变,后又叙述了魏晋时期鼓吹乐的使用情况.
此外,汉代文献中“鼓吹”与“短箫、铙歌”的概念使用情况,也能证实两汉期间的“鼓吹”与“短箫铙歌”并无交集.“鼓吹”最早出现于班固《汉书·叙传》,而“短箫铙歌”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注引蔡邕《礼乐志》.从时间上看,班固是东汉前期和帝年间的人物,蔡邕则是东汉晚期时人.这意味着,鼓吹与短箫铙歌,直到东汉末期也未曾交集,二者混用是汉以后的事情.南朝沈约将鼓吹乐释为“盖短箫铙歌”之后,人们述及鼓吹乐的渊源以及黄门鼓吹与短箫铙歌的关系时,不再区辨鼓吹与短箫铙歌.如晋人崔豹将短箫铙歌视为“鼓吹之一章”;晋人孙毓直接采用军乐释鼓吹,“鼓吹者,盖古之军乐,振旅献捷之乐也”;宋人郭茂倩将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统统视为鼓吹,“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铙歌与横吹曲,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
综上可知,将汉代鼓吹乐追溯至先秦军乐的认识并不准确,这一认识源于忽略了汉代鼓吹乐与短箫铙歌的区别.
2 先秦“恺乐”与汉初班壹“鼓吹”的异同
据文献记载,“鼓吹”作为音乐品类的概念被使用,最初是指西汉初年班壹用于楼烦边地的鼓吹乐.“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10].值得注意的是,边地班壹所用“鼓吹”乐,并不具备先秦“恺乐”的军乐属性,而是被赋予了新的象征内涵.
2.1 先秦“恺乐”的军乐属性
先秦“恺乐”属军礼用乐,但两周“恺乐”的仪式场域与功能已有变化.西周,“恺乐”是献俘礼的仪节之一.《周礼》“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若师有功……恺乐献于社”.“大献”,即献俘礼,包括庙社告祭、献俘、作乐、宴饮、大赏等一系列庆功仪节.可知,“恺乐”是周王行献俘礼时使用的仪式乐,是战争获胜后向上帝、社神、先祖的献俘祭祀,在社庙内举行,其所奏之“恺乐”属人神交流之乐,旨在禀告神明并答谢其庇护.至东周,晋楚争霸的“城濮之战”,晋师克楚后“振旅,恺以入于晋”,师旅获捷归来,于郊外振旅治兵,高奏“恺乐”进入国门,以“示喜”也.可知,两周时期“恺乐”尽管都属军礼用乐,但仪式场域已发生变化,西周“恺乐”作于庙内,面向神明;东周“恺乐”奏于入国门之途,面向国人.
2.2 秦末汉初班壹“鼓吹”的财势象征
班壹,《汉书·叙传》载:“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10]可知班壹是楚国令尹之后.“令尹”,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执政官,“令尹,官名.春秋战国时楚国设置.”[11]位高权重,相当于宰相.昔日楚国,令尹“执一国之柄”[8],对内掌理国政,对外领兵作战,总揽大权于一身.因官高位重,令尹人选一般只从王族中选任,故有世袭的传统.班壹身为楚国王室后裔,因袭了王族血统与威重职权的双重形塑,即使面临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境遇与局势,仍有称雄一方的气势与决心.因此,班壹趁秦末汉初四处战乱之际,远避至清净地楼烦,在此安顿修整,大力加强物资储备,“致马牛羊数千群”,至西汉初,班壹成功积聚大量财富.纯粹的财富积聚并非班壹的最终目的,身为楚国令尹之后,班壹称霸一方的雄心壮志从未消失,于他而言,财富积聚只是实现此最终目的的手段,故班壹“以财雄边”,试图利用财富成为“边地之雄豪”.
2.3 班壹“鼓吹”与先秦“恺乐”的关联
秦末汉初边民班壹的“旌旗鼓吹”部分沿袭了东周“恺乐”的内涵与属性,而与西周“恺乐”无涉.就场所而言,班壹“鼓吹”与东周“恺乐”同,用于行进途中,有别于西周“恺乐”的社庙之所;就意图而言,班壹藉“鼓吹”夸耀财势的方式与东周以“恺乐”庆贺战功、建威造势的方式一脉相承,有别于西周答谢神明庇佑的奏乐宗旨.
尽管如此,班壹“鼓吹”与东周“恺乐”仍有不同.东周“恺乐”乃班师凯旋后庆祝战功用乐,面向军队与征战之师,也有炫耀“权力”之意,但此种“权力”主要在敌我双方之间得以彰显.作为军礼用乐,其仪式场域凸显的是敌我之分,面对敌人,君臣是一个整体.而班壹“鼓吹”用于边地雄豪的“出入弋猎”之途,其社会面向不再局限于军队,财势炫耀的对象与用意也悄然发生了转向.班壹在“出入弋猎”之途设置鼓吹,表面上是借用鼓吹制造声响,向朔野之人宣布自己的弋猎之事,吸引众人的注意力;实则是借此场合,向众人宣告自己的财势与“权力”.
“弋猎”作为一种武力展演,本就象征着“权力”.“弋”,原初义指木桩,也指带丝绳的箭,后引申为狩猎、取代、俘获之义[12].“猎”,有“逐禽”“取兽”“捷取”等义[12].“取”“俘”“获”等字眼,形塑出“弋猎”之人的强者、胜者、征服者的鲜活形象.虽然“弋猎”的具体内容是猎取禽兽,但在古代社会,“弋猎”活动仍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图与军事意图,即炫耀武力与整训军队.班壹借由“鼓吹”,大张旗鼓地举行此类活动,诏告朔野众人,其用意昭然若揭:夸耀个人的权力.在此过程中,“鼓吹”与班壹的个人“权势”得以连接:班壹此举之所以未招致汉王朝的禁令,《汉书·叙传》颜师古注有云:“国家不设衣服车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也就是说,西汉初年,孝慧、高后之际,朝廷并未出台严格、完整的车服制度,班壹才能趁此空档配备“旌旗鼓吹”.
班壹所用“鼓吹”的社会面向是“朔野”而非军队;“鼓吹”炫耀的“权势”在班壹个人与朔野众人之间彰显,而非战事中的敌军我军;“鼓吹”凸显的是“边地雄豪”与朔野众人之间的“上”“下”之别,而非敌我之分.由此可知,自班壹“鼓吹”始,汉代鼓吹乐的内涵与社会性质因使用场合而产生了有别于先秦“恺乐”的社会意义.班壹用于构建与炫耀个人权力的“鼓吹”后被汉代宫廷充分利用,“鼓吹乐”被视为构建“王权”尊威之象的核心要件.
总而言之,今人将汉代鼓吹追溯至先秦恺乐并笼统界定为军乐的认识并不恰当.“鼓吹”作为乐种名称始见于汉代.尽管其表演形式可上溯至先秦,但其功能与性质奠定于汉.鼓吹与短箫铙歌、骑吹、横吹等相关概念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之间的区别或体现在乐器组合、或体现在使用场合.魏晋以降,随着鼓吹乐的用途越来越繁杂,短箫铙歌、骑吹与横吹通称鼓吹的情况更为普遍.但,秦末汉初班壹“鼓吹”与先秦“恺乐”已有明显不同.
3 结语
“鼓吹”概念历来争议颇多,早在南朝宋时期,此一现象就引起了沈约的关注,其《宋书·乐志》“鼓吹”条目从历史角度梳理了“鼓吹”所指范畴的演变:先秦文献中的“鼓吹”是指“鼓自一物”“吹自一物”的两种演奏方式,至汉代才成为乐种专称,仅指黄门鼓吹乐,魏晋以降,横吹、短箫铙歌也通称“鼓吹”.北宋郭茂倩对沈约之说发起驳斥,争议焦点在于汉代“鼓吹”是否指称短箫铙歌、骑吹、横吹等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汉代鼓吹是否始于先秦,二人意见一致,都持否定观点.但,这一点并未引起今人关注.
通过相关文献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以为,无论先秦“恺乐”还是汉代“鼓吹”,其内涵、属性与功能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现象值得关注.西周“恺乐”到东周“恺乐”、东周“恺乐”到班壹“鼓吹”,或许有着相似的乐器组合,但各自被赋予的性质、内涵与功能已随使用场合的变化而有不同.如,虽同属军礼用乐,但西周“恺乐”的祭祀功能至东周已不再鲜明;而东周“恺乐”的军乐属性至班壹“鼓吹”已消失殆尽.因此,将汉代鼓吹笼统界定为“军乐”,有悖于“鼓吹”乐种处于发展演变之中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