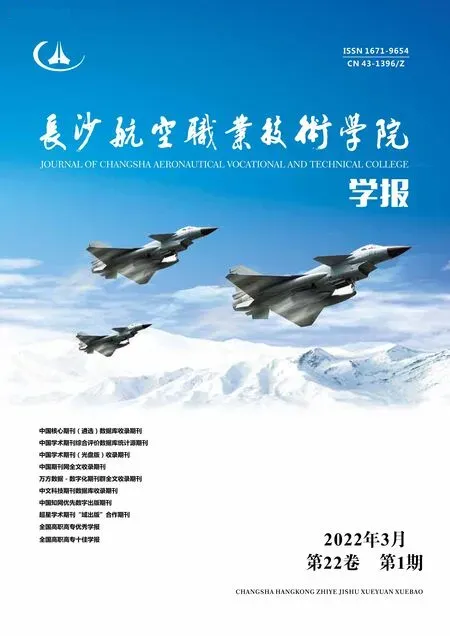译者主体性与山水诗歌英译研究
——以《次北固山下》多个英译本为例
王 齐,王玥颖,李昌银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王湾现存诗作十一首,其中《次北固山下》为王湾的传世之作,此诗创作于开元年间,诗人往来于吴楚山水之间,秀丽的江南风光使之陶醉,于是在旅途中创作了这首诗风清雅的诗作。篇中第三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被当时的宰相张说题于政事堂,以抒发其仕途抱负,而这也恰好引领了当时的文学潮流。《河岳英灵集》中殷璠以《次北固山下》的创作时间为选诗起点,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又称该诗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为划分盛唐与初唐、中唐诗歌的界线[1]。历经各路理论家的推崇,最终《次北固山下》一诗的诗史地位就由此确立起来。
该诗目前英译研究一片空白,似乎也未能引起翻译学界的重视,而该诗却在多位知名译者的诗集中得以寻见踪迹,各位知名译者对该诗的处理方式、译文特色各有千秋,不禁让笔者感慨“山水诗歌”的英译可谓难以捉摸,尤其是其中的“意境”如何再现、如何保持原作“诗画结合”的美感。由此笔者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口,从“诗歌意义未定点”和“再现意境之美”两个维度探讨《次北固山下》四个英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译文特色,以期为山水诗歌英译研究作出有益贡献。
一、汉诗英译情况概述
过去,在“欧美中心主义”的制约下,各路中外译者仍然坚持汉诗英译这一方园地,为此付出大量精力,当然他们的努力也让汉语诗歌英译本在西方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甚至成为意象派诗歌灵感之源。自1920年开始,江亢虎和维特·宾纳就开始了他们的合作译诗之路,由于宾纳不懂汉语,江亢虎就将原诗直译成英文,由宾纳加工成英语中的“诗”,两人的这种合作方式颇似美国版“林纾译诗”[2]。两人合作的译本最终合订在《群玉山头》(Jade Mountain)一书之中,该书的意义不容小觑,它预示着从唯一的欧洲中心的文学模式重新寻找方向,让中国作品成为诗歌创作灵感的来源[3]。先有1958年美国青年诗人加里·斯耐德(Gary Snyder)在垮掉派作家的宣传阵地《常春藤评论》(Evergreen Review)秋季刊第2卷第6期上发表唐代禅诗诗人寒山子的24首“创意英译”的译诗[4],后有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的《汉诗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等翻译佳作的助推,这使得在中国“边缘化”的寒山诗歌能在西方文化中走上“经典化之路”。
在本世纪,海内外译者仍然埋头于汉诗英译这一领域,各类著作层出不穷,汉诗研究的门类细分也更加具体,巴恩斯通父子醉心于王维山水诗歌英译研究,翻译并出版了译本《空山拾笑语——王维诗选》(Laughing Lost in the Mountains: Selected Poems of Wang Wei)等,巴恩斯通和美籍华人学者周平还合译了《安克诗集:中国诗歌选》(The Anchor Book of Chinese Poetry: From Ancient to Contemporary, the Full 3000-year Tradition),该书译介了上至周代下至中国当代的诗歌,其内容磅礴,气质不凡。另外,当代知名汉学家比尔·波特译介并出版了众多诗集,包括《寒山诗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千家诗:中国古代唐宋诗词选》(Poems of the Master: China’s Classic Anthology of Tang and Sung Dynasty Verse)、《值此时艰:韦应物诗集》(In Such Hard Times: The Poetry of Wei Ying-wu)等,此外还有大卫·辛顿(David Hinton)、许渊冲、叶维廉(Wai-lim Yip)、傅君勤(Michael A Fuller)、杰罗姆·西顿(Jerome Porter Seaton)等学者对汉诗英译、中国诗学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拓宽了汉诗在海外的研究深度。
二、王湾和《次北固山下》
唐代诗人王湾,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即713—756年。据考,王湾于公元712年中进士,次年游历吴楚,从洛阳经运河南赴瓜州,后乘船东渡大江抵京口,即北固山所在地,随后东赴苏州。此诗于旅途中写成[5]。该诗首联从水路和陆路两个角度描绘北固山的地势特征,随后描写潮水、船帆、日出,字里行间蕴含写实的况味。本诗采用白描手法,不过多着墨于色彩变幻,径自描绘事物轮廓,读罢仿佛在画中游。该诗不难理解,所用辞藻并不华丽美艳,而是清新隽永,通篇气质悠远,将唐代北固山与海相接的壮美江南景致和游子的乡愁融在这短小的诗篇之中。
三、译者主体性与山水诗歌翻译
随着“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兴起,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是一种对原文本的改写,译者作为源语文本的操控者,无疑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此外,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翻译四步骤理论也指出,理解即阐释,阐释即翻译[6]。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居于中心位置,也就是起着主体性作用,在“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翻译步骤中,译者的主体性逐渐渗透到翻译整个流程之中,起着连接原作者与读者、原文与译文的核心作用。
事实上,多位中国学者也曾撰文论述过“译者主体性”的相关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武能先生便开始探讨“译者的定位”,他认为,文学翻译的完成是由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不过,译者在这三者中处于核心地位;查明建则将译者主体性定义为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条件下,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许钧则通过阐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旁征博引,巧妙分析,最终得出翻译活动是由理解、阐释、再创造构成的循环,译者、原作者、读者在这个循环中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活动场,而译者在这个活动场中位居核心位置,起着最积极的作用,由此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综上,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是一种主体性活动,译者的主体性应该得到重视,不应强迫译者隐身。
那么对于山水诗歌翻译而言,如何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这种有益的主观能动性来助力呢?首先,我们要看到山水诗的特质,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对于山水诗有这样的精彩评论:诗歌中的山水描写要解脱其衬托的次要作用而成为诗歌中美学的主体对象,本存自然,这才能叫作山水诗[7]。其次,哪些情况下,山水诗歌翻译更需要译者凸显主体性呢?据徐玉娟和束金星所言,汉语古诗具有天生的简约之美,诗人有意留白让读者去想象,如果译者将留白之处全部填补,无疑背叛了作者本意,又可能欺骗了读者,由此“诗歌意义未定点”(通俗来说就是“留白”)需要恰当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8]。此外,有研究者强调通过形象化思维来表现山水诗歌的“意境”之美,遗憾的是他们未提及译者主体性相关内容,但却可在其文章中找到译者主体性之于山水诗歌英译的重要性之体现。
四、译本分析
(一)译者主体性与“诗歌意义未定点”
文学表达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是文学语言的特有之处,从阐释学角度来说,这种模糊与不确定叫文本空白与未定点。中国古诗先天就具有简约之美,诗人有意留下意义空白让读者肆意想象。然而,如果译者将所有留白之处都填补殆尽,这无疑违背作者本意又欺骗了读者,让原诗的精华变成了糟粕[9]。“留白”(或称“诗歌意义未定点”)在文学作品中始终存在,尤其是中国古诗,这种文学现象值得学界细细琢磨。而“诗歌意义未定点”与译者主体性的交织错杂的关系,下文拟以《次北固山下》多个英译本为例予以说明。
原诗文本如下:

次北固山下 (唐)王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本文所涉及的四个英译本如下:
比尔·波特译本[10]:
Stopping at Peiku Mountain
My route goes past blue peaks
Where riverboats ply green water
The current is smooth the shores are wide
The wind is perfect for hoisting a sail
The ocean sun rises in the traces of night
The river spring starts inside the old year
How shall I send a letter home
tied to a goose bound for Loyang?
维特·宾纳和江亢虎译本[11]:
A Mooring Under North Fort Hill
Under blue mountains we wound our way
My boat and I, along green water
Until the banks at low tide widened
With no wind stirring my lone sail.
Night now yields to a sea of sun
And the old year melts in freshets
At last I can send my messengers
wild-geese, homing to Lo-yang.
许渊冲译本[12]:
Passing by the Northern Mountains
My boat goes by greenmountains high
And passes through the river blue
The banks seem wide at the full tide
A sail with ease hangs in soft breeze.
The sun brings light born of last night.
New spring invades old year which fades
Where can I send my word to my end?
Homing wild geese, fly westward, please!
托尼·巴恩斯通和周平译本[13]:
Stopping at Beigu Mountain
Man on a road through green mountains.
A boat sails the green water.
The banks grow when the tide stills.
One sail taut in the wind.
The ocean sun emerges from broken night.
Spring flows in rivers as the year ages.
How can my letter find its way home
to Luoyang where the geese fly?
在《次北固山下》一诗中,所谓的意义未定点,为“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其意义其实是“夜幕还没有褪尽,旭日已经在江上冉冉升起;还在旧年时分,江南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此句感叹光阴无情,岁月又匆匆逝去,抚今追昔,徒增游子无限乡愁,为后一联“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的“游子意”的抒发奠定了氛围基调。而这种“游子意”能否在四个知名译本中得以体现呢?这个“游子思乡之意”和“南国年末春至”的两层意义是否能为各个译者所体现?
首先,就诗歌的内容层面来说,四个译本对于“海日生残夜”的表述都完整传达了原诗的含义,至于对后半联“江春入旧年”的理解,各个译本则相去甚远,笔者以为对 “江春”和“旧年”两个词的拿捏是本句的核心。首先,何为“江春”,江春意指“江南的春光”,而“旧年”则意指“年末之冬”,时至旧年的冬天,江上已有了春天的气息。对于此句,比尔·波特采用直译法,译作“The river spring starts inside the old year”,字字对应,留存原诗的内容。不过译作是否能彰显原诗的韵味,只能由读者评论。至于宾纳的译本则是“And the old year melts in freshets”,“江春”之意已经从文中省去,换来一番带有诗歌气质的译文,毕竟江亢虎和宾纳的合作模式就是,江先直译诗歌成英文,再由宾纳加工成有诗歌气质的英文译本。而许渊冲的译本则是“New spring invades old year which fades”,结合前文来看,许先生是为了满足前文的质感,满足后两联隔行押尾韵的模式将行文翻译如此状。不过该译本未体现“江春”之意,忠实性得打上问号。至于巴恩斯通和周平的译本,“Spring flows in rivers as the year ages”则和宾纳译本有几分类似,都舍弃了译文的忠实度,而创意英译以谋求更好的诗学效果。
由此,可以看出在“诗歌意义未定点”的英译上,《次北固山下》的四个译本都有各自的译者主体性,托尼·巴恩斯通和维特·宾纳的译本均舍弃了原诗的忠实性,转而谋求富有英语诗歌中诗意审美倾向的译文,许渊冲先生则是在部分忠实的原则下,追求自身“三美原作”指引下的诗歌标准,比尔·波特的译本则最为忠实于原文。
(二)译者主体性与“再现意境之美”
意境,这一概念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伟大发明。在中国传统山水诗中,纷繁的景色被分解浓缩成一个个意象,并与诗人倾注的所思所想相结合,随后在诗人的语言中循序渐进勾勒出一幅情景交融的画卷。山水诗不是简单地咏叹山水之美,往往寥寥数语描绘一番山川景色之后,笔锋一转婉转地抒发诗人的情愫,山水诗的“意境之美”往往需要意象的层层烘托,才能营造出诗歌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意境”。山水诗歌英译,尤其需要注意如何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意境”,这需要译者深厚的双语能力和惊人的创造力,纵观海内外英译山水诗的各种佳作,无论是在海外被奉为汉诗英译之圭臬的《群玉山头》(Jade Mountain)还是在西方掀起寒山诗热潮的由加里·斯耐德创意英译的24首寒山诗,译者创造力的张扬在翻译实践中不难找到明证,而这种创造力、创造性的发挥,也就是本文所强调的“译者主体性”。
《次北固山下》一诗,前三联都在描写周围的景色变化,以奠定全诗的调性,尾联直抒胸臆,畅谈“游子思乡”之意,层层烘托,最后得以表现全文之境。在译本中直接写景的前两联内容已经比较确定,各位译者对此的处理大同小异。至于最能体现该诗“思乡之情”的尾联,四位译者的译本则差异较大,各自译本的译者创造性凸显。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意指家信不知如何才能传递到家人手中,希望北归的大雁帮我捎回到洛阳的家中。其实这里王湾借鉴了“飞雁传家书”的典故,真实的情况是北归大雁并不能帮诗人传递家信,只能借用北归大雁来遥寄思乡之情。因此,此处诗歌英译本各自差异较大,也可以理解。
笔者认为,尾联部分仅巴恩斯通的译本最能体现“意境再现”和“思乡之情”,巴恩斯通的译本为“How can my letter find its way home to Luoyang where the geese fly?”,该译本保持原诗语言特色,并且表达了一种不知如何传家信的无奈感,更贴合王湾想要借用大雁来遥寄思乡之情的意图。而另外三位译者都是默认了“飞雁传书”这一可能性。首先,比尔·波特的译本为“How shall I send a letter home tied to a goose bound for Loyang?”该译本默认“飞雁传书”是可行的,由此发挥译者创造性,描绘出了“将书信绑在大雁身上,以传家讯”的画面,这体现了理想主义色彩。许先生的译本为“Where can I send my word to my end? Homing wild geese, fly westward, please!” 许先生的译本结构完整,句式对仗工整,但是该译本意思则比较模糊,未直接说明“飞雁传书”的可能性,也未表述传家信的途径,文本偏向模糊。宾纳和江亢虎的合作译本为“At last I can send my messengers wild-geese, homing to Lo-yang.”该译本以“雁群”为“邮差”,以传递“家书”,行文比较浪漫,默许了“飞雁传书”的可能性,同时也违背了原诗“苦于无法传递家信而遥寄相思”的本意,算作是创造英译。
五、结束语
山水诗歌的英译向来不易,但是一些成功的译本不但将汉诗英译经典化,同样也使得中国山水诗成为了西方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通过对比分析《次北固山下》一诗的多个英译本,可见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在处理“诗歌意义未定点”上能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基于译者不同的审美体验和意义分析,能为译本带来独特的诗学气质。此外对于诗歌“再现意境之美”这方面,译者主体性同样渗透进了译本的每个毛孔,不同的译者对于处理“意境再现”有各自的独门秘法,但终究得把握住原诗的“深层意义”才能使得主体性的发挥起到“画龙点睛”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