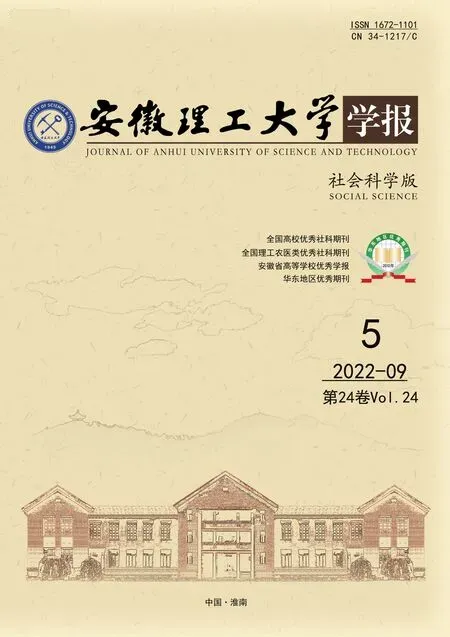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阙下《初秋》汉译本的翻译倾向
张白桦,金 港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51)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地位低下。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众多学者开始为女性发声,批判文学作品中忽视女性的畸形现象,希望重写女性独特的个性、权力诉求以及审美观念,利用特定的翻译技巧,突破时代性束缚,使女性重获社会地位以及话语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发轫于此时,体现了女性群体对于话语权的渴求,以及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
加拿大翻译理论家路易斯·梵·弗罗托(Louis Van Flotto)在《翻译与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TranslationandGender:Translatinginthe‘EraofFeminism’)一书中提出,女性主义译者主要是采取增补、加写前言与脚注、劫持3种方式干涉文本。本文欲借助弗罗托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选取美国最杰出的黑人作家之一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的微型小说代表作《初秋》(EarlyAutumn)汉译本进行文本分析,具体探讨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是如何通过这3种文本干涉方式,再现原作中的女性形象,体现女性主义翻译倾向,旨在为当代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提供个案参考。
一、弗罗托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权运动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女权运动催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翻译理论家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在《翻译中的性别》(GenderinTranslation)一书中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都坚持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为其性别身份构建创造条件[1]。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女性的翻译观念,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其政治诉求。翻译并不是简单机械式的工作,女性译者在翻译的同时也流露着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认知,对于女性话语的追求。受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性译者开始以翻译为手段反对男性话语体系。“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切人点,突破一系列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妇女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向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提出挑战,以达到发掘女性话语、重建文化研究新理论的目标。”[2]
女性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罗托重新对“忠实”进行了解读。她坦言,“作为女性主义译者,大可凭借自己对原著的剖释进行改写”[3]34。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女性“创造性叛逆”同样突显了她们对于女性话语权的追求。她们对于女性身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能够感同身受;她们将女性社会地位的诉求延伸到文化领域,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文化角度干涉翻译,不仅激活了女性在男性为主导的话语权体系中的意识觉醒,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具体践行到翻译实践层面,弗罗托提出:“女性时代的翻译也是对先前女性主人公的重塑,是对以往给与女性的那些性别特征和态度的改写”[3]50。她认为,女性译者最常见的3种干涉文本的方法分别为:增补、加写前言与脚注、劫持[3]50。
“增补”是指女性译者从女性角度积极介入翻译,在译文中补充源语和目的语由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差异而导致的缺失。“补充是指译者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做法,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4],译者通过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为读者填充背景知识。“增补”手段的意图主要为:背景知识补缺和辅助信息理解[5]47。
“加写前言和脚注”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和表达译者主观意图判断的策略之一,是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中的非常规操作。译者在译文风格重写与微调中难免遇到文化缺失,因此,必须以显性修改和强势介入的方式加以解释[5]47。译者会通过阅读相关平行文本,掌握作者的写作特点和风格,解析原作中的词语和句子的隐喻内涵,并考虑读者的文化底蕴,尽力还原作者的语调,提高作品信息呈现的有效性,并利用脚注的补偿效应为女性“发声”,加深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从而达到突出和还原原作女性形象的目的。
“劫持”,又称“挪用”或“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策略中最激进、最具欲望的策略,目的是引导读者自发地探寻女性角色在作品中的境遇,为作品基调与情节铺垫留有余地。译者对原文中的文化隐喻进行解码,增加其主观逻辑判断,对女性角色进行赞美,修改或删减作品中因对女性歧视或偏见而使用的词语,帮助女性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争取平等话语权。女性主义译者用这种富有活力的、创新的翻译方式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使读者对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处境产生了探索欲望,为作品的基调和情节创造了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初秋》汉译本翻译实践
作为“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中坚人物,美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在美国文坛,尤其是黑人文学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他写过小说、戏剧、散文、历史、传记等各种文体的作品,主要以诗歌著称,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于将爵士乐与黑人民歌引入诗歌,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美国黑人诗歌”,被誉为“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他的微型小说代表作《初秋》1950年9月30日发表在《芝加哥卫报》上,短短434字,讲述了一对旧情人街头相遇的典型爱情故事。作者用诗歌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人类情感的无限复杂性,原作也反映出浓郁的女性主义倾向。
张白桦的《初秋》汉译本原载于《百花园》(2001年,总185期)、《中学生必读的爱情小说100篇:给爱一条回家的路》(2013年,湖南少儿出版社);《趣味英汉互译教程》(2015年,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基础指津》(2017年,中译出版社)与《时光不会辜负有爱的人》(2017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时光不会辜负有爱的人》很受读者青睐,迄今已重印3次,且根据知网统计数据,现有与此书相关的学位论文4篇,期刊学术论文13篇,图书4部。
《初秋》汉译本的译者张白桦(1963-)为当代女性译者,现已出版译著编著40余部,累计约1 200万字。在微型小说翻译领域,出版有中国首部微型小说自选集英译本《凌鼎年微型小说自选集》(2016年,美国时代科发集团出版社)、中国首部微型小说译文集“译趣坊”系列全11册(2017年、2018年、2019年、2021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张白桦多次获国内国际各类奖项,如微型小说《爱旅无涯》获“1997年度《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最受读者喜爱的译作”,得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英文版中国日报、中国作家网等媒体广泛介绍。其文学翻译实践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女性主义倾向,在当代女性译者中颇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其作品为研究文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下文从文化翻译层面,以《初秋》(EarlyAutumn)汉译本为研究文本,具体探索译者张白桦如何根据弗罗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3种干涉文本方式,展现其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一)增补
增补是指译者在翻译中使用补偿手段,在不改变原文意义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增译。文化差异会导致语义偏差,增译能够使译文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尤其是增加有利于女性话语权及其地位的描述,更能体现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思想的觉醒。
例1:He stopped.At first he did not recognize her, to him she looked so old[6]136.
译文:他驻足,开始没有认出她来,觉得她看起来显得那么老[6]133。
这句话发生在男女主人公玛丽和比尔分手多年之后的重逢之时。“显得”的意思是表现出某种情形,原文没有相关表达,该词是译者加上去的。这句话以两人的外貌差异描写起笔,深化到两人内心的情感差异。译文凸显了男性和女性在情感地位上的差异:男性是主导地位,女性是从属地位;同时也强调了双方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男主人公比尔对待感情的态度如过眼云烟,而女主人公玛丽却十分念旧。翻译实践中通过显化女性群体的弱势地位,容易引起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共情,体现译者对于提高女性地位的希冀。
例2:“We live on Central Park West,” she said.“Come and see us sometime.”[6]137
译文:“我们住在中央公园西大道,”她说,“有空过来我们家坐坐。”[6]134
这句话是男女主人公谈论家庭状况时女主人公玛丽向比尔说的一句话。译者采取了增补方法,将原文中的地名译为“中央公园西大道”,符合“名从主人,物从中国”的翻译原则;同时,增译之后还渗入了一种隐喻意义,即女主人公玛丽为自己的生活状态作出了解释:“中央公园西大道”说明玛丽的日子过得很好,用于还击上文比尔的炫耀心理和步步紧逼的问题。译文使男女主人公鲜明的性格差异跃然纸上,体现了译者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良好把握;同时,这种增译也是译者努力为女性角色争取足够话语权的体现,显示出其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
例3:“When...” she wanted to say, but the bus was ready to pull off[6]138.
译文:“什么时候……”她想把话说完,但车就要开了[6]134。
这句话发生在男女主人公分别时。“说完”一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的,原文中没有关于“完”的表述。尽管只是增补一个“完”字,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多层需要读者细细品位的多层含义:首先是字面上的含义,“完”表示男女主人公即将分别;其次是体现女主人公玛丽对于男主人公比尔的不舍,她还希望能够继续与比尔交谈,不想就这样和比尔分别;更深层次是隐藏着玛丽复杂的心理状态:车就要开了,比尔的缘分也将要结束,即便有再多的不舍和留恋,最终这段感情也将无法挽回。通过一个“完”字的增补,译者不仅刻画出女主人公玛丽在爱情中的地位、状态和心理,还展现出女性对于爱情和社会地位的诉求。
(二)加写前言与脚注
前言和脚注也可以用于普通的翻译,但是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加写前言和脚注来解释原文的背景,却是一个有意为之的翻译策略。译者使用这类副文本,旨在唤醒女性读者的女性身份意识,并试图展现出女性译者的差异性翻译。《初秋》一文编入“译趣坊”系列第一辑《时光不会辜负有爱的人》时,由于篇幅较短,脚注使用得较少,但该书的译者自序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倾向,特别是女性主义倾向,体现出译者对于原作主题内容的精准把握。因此,通过研究译者所加的前言和脚注等副文本,可以更好地理解女性译者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过程中对于翻译策略的取舍。
首先,自序体现了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倾向,特别是女性主义倾向。如,“我翻译时的期待视野定位在年轻人身上,目的是做文化,文学的‘媒’,因此更愿意贴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觉得‘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在翻译方法上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在翻译方式上,以全译为主,节译为辅;在翻译风格上以时代性为特色,笃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之说。”[6]2通过这段自序,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读者,尤其是对青年女性读者的充分考虑。译者在翻译方法上使用更加贴近读者的归化法和直译法,不仅体现了她对青少年群体,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关怀,也为青少年读者、女性读者学习翻译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译者站在青少年读者和女性读者角度进行翻译实践,可以探究到普通译者和读者触及不到的角度和深度,使译文更具特色和风采。译者这样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倾向,以及她对于女性读者的关注,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相契合的,也为女性主义翻译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自序体现了译者对原作主题内容的把握,以及对女性形象的认识和干涉。如,“对于原作的主题,我更喜欢以人性探索为立足点的人文视角来选择、诠释。妇女、儿童和草根阶层等弱势群体始终是我关注的焦点。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治愈系、成长系、幽默系三个板块。”[6]2
译者对于原作主题的选择首选妇女题材。作为女性译者,她对女性有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而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同情反过来又会激发译者对于女性地位和话语权的呼吁,这种呼吁就体现在译者翻译过程中对策略的选择上。译者之所以理解并践行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一方面是因为她身为女性,对有关女性的描写更为敏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时代的进步。相比过去,在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世界上很多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话语权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女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译者所处的时代和大环境更有利于她践行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为女性争取权利和地位。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了解到,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的女性仍处于受屈辱、被压迫的状态中,甚至很多女性基本没有任何权利和社会地位,唯命是从成为她们理所当然的宿命,女性主义译者应为此作出应有的努力。译者张白桦对于原作主题的选择体现了译者对于女性形象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干预。
译者的这则自序不但阐释了译者的女性主义思想,也表达了译者本身的女性观,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7]的知行合一。
(三)劫持
弗罗托认为翻译应从女性主义视角进行重写,从而对文本进行灵活性的干涉和改写[8]。“劫持”是指女性主义译者对原作的挪用,赋予不具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劫持作为笔译活动秉持女性视角译者最常用的手段,既保留了原作的风格与基调,又体现了译者在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
例4:Then somethingnot very importanthad come between them, and they didn’t speak[6]136.
译文:接着,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于是他们不再说话[6]133。
这句话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产生隔阂的原因。原文“not very important”可直译为“不是很重要”,但译者采用了归化翻译策略和反译的翻译方法,译为四字成语“鸡毛蒜皮”,化虚为实,化静为动,符合汉语直观形象、生动活泼的特点。同时,“鸡毛蒜皮”一词也表达出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生活中女性的地位都不如男性,因为在汉语文化中,女性往往处于被发现和被创造的从属地位[9];相应地,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所承担的角色也是“鸡毛蒜皮”的小角色。译者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对原作进行了干涉,目的是寄希望于读者关注女性群体,呼应女性提升社会地位与话语权的诉求。
例5:Unconsciously, sheliftedher face as though wanting a kiss, but he held out his hand.Shetookit[6]136.
译文:她下意识地扬起脸,好像在等待吻,而他却伸出了手,她握了[6]134。
这是男女主人公在文中的第一次对话。译者采用了换序和省译的策略,将原作的词序进行了适当调整,遣词造句别出心裁。“lifted” 和 “took” 两个词在英文中的语义范围较大,译者从女性内心出发,将二者分别译为“扬”和“握”。“下意识”“扬脸”是肢体语言的细致描写,却反映了玛丽的内心活动,她依旧对爱情抱有幻想。随后一个“握”字,简短有力,却体现出了玛丽的无奈和卑微,面对冷落时只能被动接受。译者关注到了女主人公玛丽在爱情中的弱势地位,通过上述对原作的干涉,希望能够引导读者产生共情,呼应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诉求。
例6:Shelostsight of Bill.Then she remembered she had forgotten to give him her address—or to ask him for his—or tell him that her youngest boy was named Bill, too[6]138.
译文:她看不见比尔了。接着,她想起来,她忘了给比尔地址,忘了要他的地址,也忘了告诉他自己最小的儿子也叫比尔[6]134。
这句话是全文的结语。原文的“lost”有多重含义,本意是“失去”,译者将其译为“看不见”,有一语双关的修辞效果,表示玛丽在最后终将失去比尔,暗示了玛丽在爱情中的悲剧结局。原文的谓语动词“forget”统领了3个宾语,用破折号隔开。译者翻译时使用了删减法,去掉了英文常用而汉语不常用的破折号;同时,又使用了增加法,在两个宾语前增加并重复了该谓语动词“忘了”,使译文形成了排山倒海式的排比句,不仅符合汉语喜欢重复的习惯,而且取得了重复修辞的强调功效,将全文的情节推向高潮,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感:玛丽一直深爱着比尔,比尔对玛丽的爱情却已是冷冷的秋[10]。该句译文,再一次凸显出女性在爱情中缺失话语权。
三、结语
《初秋》的原作者用诗化语言描述了一对情侣的爱情悲剧。译者张白桦站在文化翻译的高度,运用女性主义的3种翻译策略,还原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特别是对女主人公玛丽的描写强调了她在故事中的卑微地位,表现出了译者对于提升女性地位的呼吁,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玛丽的血泪心酸。张白桦在女性主义视阙下,倾向于采取增译法补充原作女性角色话语权与社会地位缺失的描述,重塑了一位鲜活的女性形象,突出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张白桦还采取了补充自序副文本、换序加增减的“创造性叛逆”干涉文本手法,重现了原作中的女性形象,呼吁读者关注女性对其社会地位及其性别身份、话语权的诉求。本文只是当代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的个案,在当代中国,女性地位和话语权正在不断提高,相信当代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研究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