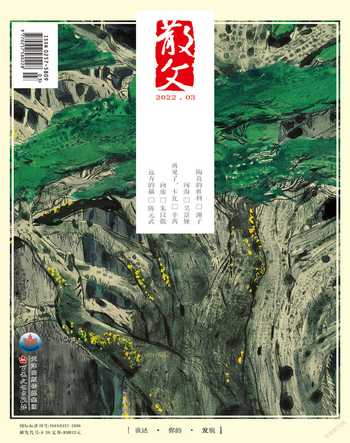原点
王威廉
因为疫情以及工作的原因,居然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父母。原本计划6月份去西安看望他们,可那时广州出现了一波新冠疫情,不让出省。等到8月份,再次启动休假事项,可南京又来了一波,蔓延多地,于是,广东也再次不让随便出省。签批好的休假单放在桌面上,眼睁睁看着它失效。
熬到10月份,到北京做完小说集的活动之后,就赶紧踏上了前往西安的旅程。但就在这一天,新闻报道说西安出现了病例,防控政策开始收紧。没办法了,硬着头皮也要闯进去。
乘高铁约下午五点到达西安,这才发现两天前做的核酸检测,刚刚超过四十八小时。前方排着拥挤的队伍,不知会如何处理?好在只是让排队做核酸检测,做完之后就可离开。
坐地铁到航天城站,父母开车来接。父母的状态跟去年见面时差不多,健康状况较佳,心下稍安。父母带我到小区后门吃菠菜面,陕西人以面食为主,一日不吃面条,就觉得没吃好。面店里挂着一道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要不是手工面,朝我脸上泼。”陕西人的这种愣娃性格,让人哑然失笑。
不过,此行不住市区,要回祖屋去。因为疫情,我有两年没见外公了,他是我祖辈中唯一在世的了,马上就要接近百岁。
回到终南山下的柿园村(自户县成为西安市鄠邑区后,官方名稱已经改成柿园社区),祖屋一侧的墙上刻着祖父写的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章草体,一般人不认识,每每需要祖父给解释一番。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幸听祖父多讲了几遍。但是这字迹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也就是二十一年的光阴。
空气清新,但极冷。这波冷空气,让中国北方提前入冬了。蜷缩在祖屋的二楼房间里,很晚才睡着。深深体会到寂静与安静是两回事:一声鸟叫在安静中是和谐的,但是寂静中的一声鸟叫,不亚于一声枪响。
去祖坟抚碑。祭拜了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然后才提着礼物去看望外公。外公跟小舅住在邻村。他的记忆大部分都模糊了,看着我认不出,但依然用亲切的笑容看着我,不时向一旁的小舅询问:“这是谁?”
外公的皮肤都快变得透明了,里边的骨头像是玉一般光滑。他的耳朵早在好多好多年前就老化了,给他配了助听器,他却不乐意戴,所以跟他的交谈是困难的。扯着嗓子喊几声,他也许只能听清十分之一的内容。于是,只能我对他笑一下,他对我笑一下,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认出我来了,因此很开心。我看到他炕边的瓷片掉了几个,询问之下,才知道有一次他偷着抽烟,结果不小心把被褥点燃了,然后他用拐杖使劲抽打,把瓷片都给打掉了,幸好家人发现得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听完这个事情,我看着面前这个挂着孩子笑容的老人,悲欣交集。人越老就越返回童年,这真是一个闭环。
中午在小舅家吃扯面,地道正宗。饭后走去给外婆上坟。那一年,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突然收到外婆过世的消息,很震惊,因为她身体尚好,只是得了一场感冒,谁也没有料想感冒也能如此凶残。那一年外婆八十五岁。
我还想跟外公再多待一会儿,但外公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此时他又陷入了昏睡。父母带我驱车上山,访新兴寺。因前几天有泥石流,寺中仅有一人留守。今年天气异常,整个北方一直大雨不断。寺门口有塔,上刻有创立者女尼的碑记。女尼是本地高僧,她的丈夫早亡,她独自将孩子拉扯长大后遁入佛门,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建造了这座新兴寺。其中故事,让人不能不为之触动。
寺庙建在山腰上,四周都是原生态的山野。父母自幼在乡野长大,看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柿子成熟,便给我摘野柿子吃。放入嘴里还是有些生涩,但毕竟让口齿生津。这时有个公众号要对我进行一个访谈,是关于小说集的,在这荒郊野外吃着野柿子,谈论小说集,似乎是一个极错位又极恰当的地方。
晚上铺了电褥子,这才感觉好多了。一夜冷雨,早上方停,白色的雾气在周围弥漫,湿度极大。西北有如此大湿度的天气比较罕见,堪比我常年居住的广州。我的鼻子发痒,喷嚏连天。父亲提议去翠华山看看。祖父曾经在国共合作时期上翠华山受过抗日游击训练,那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在翠华山受训后,便前往山西前线。在一次侦察任务中遇见日本敌机,他匍匐在地,纹丝不动,另外两人惊慌失措,乱跑起来。敌机发现后,用机枪扫射,两人皆牺牲。因此,祖父是一个幸存者。可这只是个开端,然后,他也一直是一个幸存者,一次又一次从人生的巨大危机中逃脱出来。
外公跟祖父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因此就在几年前,他们同时获得了有关部门赠予的牌匾,上面写着“抗战英雄”四个大字。随着时间流逝,那场战争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亲身经历过的人也越来越少,终究会有一天这世上再也没有人是亲历者。而那场惨烈的战争,也将再无血肉之躯的见证者。
我曾经无数次跟祖父谈起他的战争经历,但是我从未问过祖父内心的细微感受。我跟祖父的感情非常深,在他临终前,我从广州匆匆赶到,他已陷入弥留。他听到我的呼喊,眼睛不能睁开,但是流下了泪水。那年,我的孩子尚在妻子腹中,祖父在清醒时一再询问。如果我能更早一些赶到,能够等在他清醒的时候,跟他再说说话,那该多好。这成了我心底很深的遗憾。
那就去翠华山。可是,等车开到了山脚下,才发现峪口被拦着,还有执勤人员驻守,因为西安出现疫情,现在不能上山。那就徒步在近山流连,没想到竟然看到了被拆除的秦岭别墅的残迹。这是前几年的大事,惊动了中央,村里面也议论纷纷,说此地岂是能随便乱建的。实际上,不远处还矗立着一片符合规定的别墅,证明并不是建了就要拆除,而是要符合相关的土地法规。那几栋别墅确实很漂亮,让人不免心生艳羡。住在这里,也许真的能得到天地灵气的眷顾?
终南山下,人杰地灵,柿园村的西边数公里是楼观台,是老子写《道德经》出关的地方;东边数公里是草堂寺,是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地方。
翠华山在东边,离草堂寺不远,便去草堂寺吧。走过那座冒着烟雾的千年水井,第二次看到了鸠摩罗什的舍利塔。想到他说自己因为译有真经而在涅槃之后舌头不化,浑身涌起一阵感动。这个从西域来的异乡人,在这里成就了他一生最大的事业与功德。
晚餐后再去看外公,他又睡着了。妗妗把他叫醒了。他睁开眼睛,微亮的眼神茫然望着我们。他再次认不出我们了。妗妗说我们来看他,他忽然大声说:“有啥好看的,就跟死了一样。”他的这句话犹如当头棒喝,我的心脏被刺痛,然后又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安慰。他的意识已经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但对于死亡已经无所畏惧。
第二日中午,我跟父母去看大姑。大姑独自在家,亲自下厨,还是地道的陕西扯面。她今年已快八十岁,身上却全无暮气。大姑父跟三个孩子,全是教师,而且小学、中学、大学皆有。祖父对此深感骄傲。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聊天。大姑讲了一个村民的事情。那个人得了晚期胃癌,到了医院准备做手术,但是切开之后发现已经无力回天,又给缝回去,家人就骗那人手术很成功,于是就很开心,出院后又是跳舞又是打羽毛球,可后来病情一下子恶化,人就走了。大姑说这个故事时的语气很平淡,生死的事情在这片土地上天天都在上演。不远处的一家人,就将祖坟安置在自己的后院里。生与死在同一个空间,也不觉得忌讳。只有现代城市,才会想尽办法处理干净死亡的痕迹。
下午又去看三姑,她在家附近的葡萄园里帮忙。那里种植的是“阳光玫瑰”这个很流行的品种,她专门采摘了新鲜的葡萄请我们品尝。葡萄汁液饱满,香甜可口,确实非常好。她前几年有些病痛,现在身体倒是越来越好,人的生命里充满了神奇的力量。
从她家出来,没想到与鸠摩罗什大师再一次相遇。
通过导航看到不远处有村叫罗什村,不知道跟鸠摩罗什有没有关系。但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们前往罗什村一探究竟。原来,那里还真是因为鸠摩罗什而得名。村里有一座寺,就叫鸠摩罗什寺。进寺后发现里面并无僧人,只有一位管理者。据此人说,这里就是晋逍遥园遗址,是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地方,草堂寺是后来才建,建好之后,鸠摩罗什这才搬迁过去。历史的细节早已湮灭在时间的尘埃中,正如这寺中那两个巨大的唐代莲花石座。这至少证明这座寺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即便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也依然相信鸠摩罗什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因为在这片历史极为丰富的土地上,一个命名往往已經蕴含了太多的历史信息。
返回的时候,夜幕已经笼罩了关中平原。
短短几日,白驹过隙,又到了离别的时候。在这几天里,只有我自己跟父母在一起,我便也重新变成了一个孩子。
第二天清晨,父母开车送我到西安北站,走高速仅用一个小时。很多年前,我的祖父为了报考西北革命大学,背负行囊,从凌晨出发,步行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时,方才走到西安市区。那一年关中大旱,祖父走在将近一尺深的浮土里,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扬起漫天的尘埃,像是曾经在丝绸之路上走过沙漠的僧侣。而他怀里揣着的三块银圆,是解放军在祖屋里借住之后,硬塞给家里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笔巨款来自革命,他决定把这笔巨款重新用回革命。
我坐在高铁的座位上,准备给手机充电。这几天,我的手机快充线在家里一直充不上电,不得不花了四十元买了一条普通的数据线,我知道肯定是买贵了,但似乎在心理上也愿意买贵一些。路途上还有大把时间,我便掏出那个坏的数据线,试着插进了高铁上的插座,结果立刻显示充电已连接。这根数据线是完好无损的。难道是村里的电压不稳定?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这表明,太过精细的电器,在乡村的粗犷中可能会变得没有用武之地。这是一个现实,当然也是个隐喻,而且,还是一个准确的隐喻。
中午时分,我问父母回到家了没,他们说没有回家,又去泾河县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点”。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真有“原点”这样的地方。大地有原点,就像我们的人生也有原点——我们的原点就是我们的父母。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