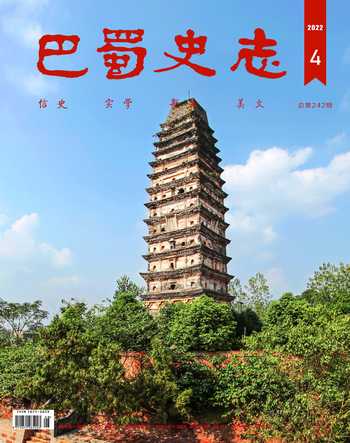从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看方志述体的发展
刘德元
广义上说,非虚构文学就是方志文学的延伸。非虚构文学创作(写作)与中国学界惯常认为的“纪实文学”有着类同属性,与地方志书中的“述”脱不了干系。《上海地方志》2021年第2期刊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地方志研究室齐迎春的理论文章《地方志述体的发展: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这是笔者在地方志系统内第一次看到把“文学”与“方志”联系起来的理论文章。关于这样的命题,笔者联想起四川最近很火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是阿来的《瞻对》,二是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看过之后,忽然明白了“方志”与“文学”的渊源竟如此之深。
一、文学与述
关于文学,辞书上的定义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述,行业内,我们一般是指地方志书中的述体。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的体例包括结构、体裁和章法;其中,体裁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形式,述列第一。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述在地方志书中的作用和意义。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命题,即述是文学,是方志文学。这是因为,在志书中,只有述是叙述,其余是记述。
新方志中的述,大致分为总述、综述、概述、无题述几种类别,述体的类型又分鸟瞰式、浓缩式、轴心式、横展式、纵贯式、简介式、提要式、策论式等。在新方志中,一般是总述(概述)居于志首,篇章下设无题述,有的志书还在节下根据内容设有一段引言,这种情况也是述。
述的作用和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总述(概述)是宏观提要。因方志的基本结构是横排纵述,故一部志书如没有总述(概述),读者就难以从总体上把握全书内容,就会只见微观,不见宏观。第二,述贯全志。把志书篇章节各不相通的类别联系起来,使得百科之业得以相互贯通,增强志书的整体性。第三,彰明因果关系,反映事物规律。第四,引领阅读。人们阅读总述(概述)可以首先对志书有一个总体认识,从而综览全书,全局在胸,达到事半功倍,增强阅读效果的目的。
述是文学。纵向看,中国古代的文言文即是述,也称记叙体,但往往是语录对话体居多,《论语》《国语》都是这样。再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是直接记事,用叙述体的不多,如《史记》《汉书》等。后来小说的出现,对人物、情节、环境做具体描摹,这是述的升华。我们通常见到的小说,大多属于叙述体小说。叙述体小说在语言上分两种:一种是叙述人语言,就是作者本人的语言,不管用什么风格、什么形态表现自己的语言,作者必须首先要用文字来记录内心世界,透过文字,读者才能了解作者创作的一个社会状态,这就是叙述人语言,它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是述体。第二种是人物语言,就是作品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的语言,包括人物心理动态、人物对话等。放眼看,西方国家使用述较早,它是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创建。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①说:“非虚构写作就是叙述体(述),它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它不能编故事。看起来这比虚构写作缺少更多的创作自由和创造性,但它逼着作者不得不卖力地发掘事实,搜集信息,非虚构写作的创造性正蕴含在此间。”
根据上述,“述”在志书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对述是文学的判断,由此得出结论:地方志书的述体,既是文学范畴,又是方志范畴。在目前方志学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之前,将方志述体称为方志文学,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有利于方志文化的发展建设。特别是第三轮修志即将启动之际,正确处理方志文化与述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述体的应用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四川两位作家的非虚构小说很有代表性
(一)《瞻对》
2014年1月,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阿来出版了他继《尘埃落定》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瞻对》(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瞻对是一个地方,因行政区划调整,具体位置只能说是四川西部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明朝时即授印归附中央朝廷。在阿来的这部非虚构新作中,他以瞻对200余年的历史为载体,将一个民风强悍、号称铁疙瘩的部落“融化史”钩沉出来,通过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运用,讲述了一段独特而神秘的藏地传奇,同时也展现了汉藏交汇之地的藏民独特的生存境况,并借此传达作者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其中设置的章节内容,蕴含了方志文化的诸多元素,如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人口地理、经济状况、军事设施、牧耕文化、草原文化,以及藏医、藏药、藏文化等。
(二)《昨日的边城》
《昨日的边城》作者龚静染,2017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昨日的边城》直接应用志书体纪实,断限是1589—1950年。边城即今日马边县。马边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小凉山区,位于乐山市、宜宾市、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合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另一个就是以马边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马边在历史上彝汉杂处,近代以来则经历了由边疆变为内地的过程。龚静染的《昨日的邊城》截取马边400余年以来若干大事件,钩沉在时代中被尘封的人物,以疾缓有度的笔调,从明万历十七年(1589)马边建城写到1950年,通过将马边的历史文化、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穿插其中,一幅边疆小城数百年历史的立体画面栩栩如生地展开在读者面前。其中有大量的叙述、故事、历史细节,文笔质朴淡然,时而有诗意的语言,散发深谷鲜花的清香,活脱脱一部方志文化成果。
上述两部作品各领风骚、各擅所长,为中国的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贡献了难得的范本,呈现出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特征。方志界常讲,地方志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地方志讲的故事必须是以“真实、客观”为前提条件,而真实、客观亦是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诞生的前提条件,也是二者存在的最大价值。
三、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
方志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熔铸一体,方志文学即非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离不开方志文学。述既是志书体裁之一,也是非虚构小说的表达形式。
其一,方志文学中,述体的运用非常重要。一部志书的分量,不在文字的多寡,而在志书的质量。如果述写好了,其总体质量也就自然提高。志书中,除总述(概述)、综述和篇章述外,还包括卷首的序言(前言)、图片说明、前志述略、特载、凡例,以及作为志后铺垫的编后记,等等。
其二,以“地方”和“微观”为书写对象。志书、非虚构小说都是以某个特定地方为书写对象,如一市(州)、一县(市、区)、一乡(镇)、一村,甚至是一条老街、一家老店、一泓溪流、一口古井或一棵树,非虚构作品更是细微到某一个群体,刻画某一个人物。从上述四川两部非虚构作品来看,《瞻对》是关注一地(川西的一块藏族聚居地),《昨日的边城》是关注一城(马边)。二者的相同点是,将对“面”的观察细化为“点”,将大量微观事物和细节带入读者视野,这是对方志文学中述的升华的具体表征。
其三,以“述而不论,揭示规律”为书写准则。方志小说是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其本质是小说,是小说就有虚构的成分。但与传统小说不同在于,方志小说将自己置于观察者的角度,用方志体裁(述)不动声色地进行写作,叙述的过程中尽量不做主观评判,力求忠于现实,还原真相。其实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种旁观者的写作方式并不少见,例如清代纪昀撰写的《阅微草堂笔记》、20世纪70年代沈凯撰写的《古玛河春晓》等。相对于最近阿来的《瞻对》和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非虚构写作更是追求做一个记录者,记录和呈现一切现实元素。这些特点与地方志“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的编纂原则一脉相承,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客观呈现。此外,与传统的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不同,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十分注重结构设计,热衷于对叙述内容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将表面似乎不相关的事物,通过结构设置与文字技巧,暗隐逻辑,把他们内在的逻辑与因果规律揭示出来。用事实说话,用细节支撑,是地方志、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共同遵循的一个准则。
其四,非虚构写作关注民生。如2017年9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喜迎党的十九大·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上①,《高腔》《通江水暖》《山盟》三部作品作为脱贫攻坚文学的“四川样本”得到与会各位文学评论大家一致肯定和点赞。其中,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刊载于《人民文学》,刘裕国和郑赤鹰的长篇报告文学《通江水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明春的中篇小说《山盟》刊载于《中国作家》。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会联想到地方志中一些事物记述:第二轮修志中党委、政府的扶贫工作,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等。再如阎连科的《炸裂志》,除了小说的标题直接叫作“志”,全书的谋篇布局也参照志体,如书中所设章节包括舆地沿革、人物、政权、传统习俗、综合经济、自然生态等。
其五,我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并无一定范式,但起码有四条线索或路径,是绕不过去的。也可以说,它们是非虚构写作者手中的四大利器:一是田野考察,二是方志文献征引,三是对地方志工作机构编撰的地情资料的直接引用,四是“口述”资料。离开这四者,非虚构写作很难成立。就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所采用的方法来看,更多的是以田野考察中所获得的大量耳闻目睹的口述资料,辅之以文献或地情资料的印证来达成非虚构写作目的。
如上述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就是一部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它不仅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而且对地情资料的遴选和采用也用尽了心思,下了一番苦功夫。据作者自述,他在写作之前,曾将清嘉庆版《马边厅志略》、清光绪版《雷波厅志》和清乾隆版《屏山县志》进行细致对比,从而发现这三个互为邻县之地,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的大事件,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
作者发现了隐藏其间的微妙差异,并从这些差异的呈现中,展现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就此,作者不仅在较大的历史叙述中力求全景式地呈现,在很多细枝末节上,也给予了认真关注。他写道:
“这座古镇(荍坝)虽饱经沧桑,但清、民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保留了古香古色的风貌,在苍翠的山峦中呈现出一道独特的景观。走在小镇上,吊脚楼静静地诉说着悠远时空的美学,光亮的石板路仿佛还倒映着过去的影子,若是小雨迷离之时,整个小镇也有一点前世的惆怅。而一到赶场日,镇上人头攒动,彝族、苗族的绚烂服饰穿插其间,格外引人注目,充满了异域风情。从附近山上背来的菌子、竹笋、木耳、茶叶等山货一路摆开,新鲜而价廉,这是内地乡镇少有的。当然,在人群中还有那朴素而美丽的小阿依,她们的眼睛比山涧溪水还要清澈,仿佛藏着一个隐秘而古老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边地小镇流连忘返的原因。”
这样一幅古风与异族风扑面而来的风俗画,既是方志述的一种延伸,也是非虚构小说的一种表达形式,述的影子若隐若现。
以上论及的关于地方志与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共同特征,有人认为是出自对地方志的借鉴,这种借鉴既包括书写内容上的,也包括书写形式上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新文体”的出现与迅速传播并非偶然,与地方志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借鉴”,事实上,二者是地方志“述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2019年4月,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冀祥德在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培训班讲话中指出:“地方志已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成果群所蕴藏的“矿藏”包罗万象,不仅是关于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人文等方面静态的记述,在世代绵延不断的記载之中,这些资料和数据还按照他们自身的属性与发展,自发地产生联结、融合,生发出不可预计的变体和变量。这就是说,地方志资源不只是地方志工作机构所独享的一种资源,而是逐渐被社会所认识、所掌握的一种共有、共享的资源;从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看方志述体的发展,方志文化更加波澜壮阔。
(作者系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退休干部)
〔参考文献〕
①向以鲜:《从〈昨日的边城〉说最近很火的非虚构文学》,艺评圈,2017年11月15日。
②齐迎春:《地方志述体的发展:方志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上海地方志方志》,2021年第2期。
①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知名非虚构作家,生于美国,牛津大学硕士,曾任《纽约客》驻华记者,出版多部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如《江城》《寻路中国》等。
①四川新闻网,2017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