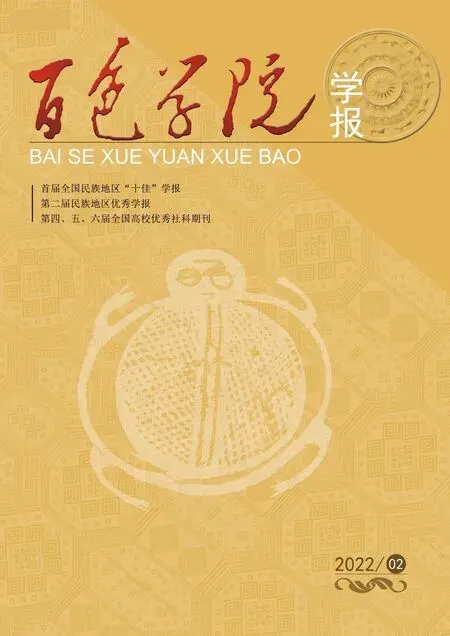壮傣民族史诗的始祖叙事传统与传承机制比较
——以布洛陀和布桑嘎西为中心
李斯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壮族和傣族有着深厚的百越文化渊源。根据语言学、考古学、分子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两个民族曾有共同的族群起源,在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都延续着共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民族在独立发展中逐步接受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内容,形成了看似异常迥异的始祖叙事传统。其中,壮族的“布洛陀”和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①由于两部史诗文本较多,内容存在差异,在此使用引号来表示史诗的集合概念。分别是这两个民族中以创世内容为主的史诗代表作。以两部史诗叙事为中心来探索其中的始祖叙事与传承机制的异同之处,将可再现壮傣两个民族叙事中的深层骆越文化基因。
一、引言:以史诗“布洛陀”与“巴塔麻嘎捧尚罗”为中心的始祖叙事
壮族史诗“布洛陀”和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分别以布洛陀和布桑嘎西为民族始祖。两位神祇的角色设定、叙事内容等较为相似,其创世、造万物、制文化的历程既有共性,又别具民族文化个性。
壮族史诗“布洛陀”主要流传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右江、红水河流域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族分布区。它主要讲述始祖布洛陀和配偶姆洛甲(麽渌甲)开天辟地、造万物、制文化、定秩序的历程。史诗里说,在天地形成初期,布洛陀顶天撑地,给人们开辟了生存的空间。他造出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他还指导其他天神来完成造人,又围绕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帮助人们找到谷种,造牛、羊、狗等动物。在此基础上,他又创制出各类生产工具,教人们炼制铜器铁器,开辟新生活。如:
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主要流传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周边的傣族傣泐支系分布区。它主要讲述始祖布桑嘎西和配偶雅桑嘎赛创世、造万物、定四州的内容。天神英叭派布桑嘎西夫妻来到地面来修补世界,并创造人类。[2]144-252布桑嘎西用泥垢来修补天地,并拔下自己的七颗牙齿固定地盘。夫妻二人在四大洲埋下四颗宝石,以此代表四个方向,区分四洲的颜色。他们把仙葫芦里万物的种子洒向四方,于是世间有了各种动植物。种子不够用了,布桑嘎西便拔苗去种树栽花,雅桑嘎赛用海底的黄泥巴捏出多达九亿种的动物。他们拉犁种树形成了大山小山、谷盆山菁。他们流下的汗汇成了江河湖海,滋润了大地。夫妻二人用天上找来的人类果揉成药泥,做出了人类的祖先——神面人。经过数代的发展和更迭,葫芦中的兄妹约相和宛纳结为夫妻,繁衍人类。
作为壮族与傣族的始祖神祇,布洛陀和布桑嘎西的神迹既有重合又有不同。民间流传的口述散体神话对布洛陀和布桑嘎西创世造物的神迹又有所补充。例如布洛陀教人们造房子、布桑嘎西夫妻制婚姻等。
除了布桑嘎西,傣族另外一位名气很大的首领——桑木底的神迹也与布洛陀有所交集。其神迹主要是与诸神分家、分谷种、制婚姻、划分耕地、造犁、饲养动物、烧制瓷器、炼制铜器铁器及造房子等。笔者曾采录到的分家母题里说,桑木底、帕雅恬、那伽三兄弟都是天神的孩子。他们志向各异,帕雅恬喜欢天空,就住到天上去了。桑木底喜欢人间,就留在人间。另外一个兄弟那伽,喜欢水,就跑到水里去生活了。①采录时间:2014 年10 月25 日;采录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龙镇曼栋村;采录对象:傣族章哈岩拉(男,50 岁);采录人:李斯颖。桑木底受天神变成的凤凰启发,最终做成了以凤凰坐姿为基础的干栏房屋。在制造陶器时,他教人们用黑土、黄泥等来做成碗、锅的形状,并烧制成形。他又教人们烧铜炼铁,制作出刀、斧、锄、犁、耙、弓、箭等。[2]366-425
笔者综合了布洛陀、布桑嘎西与桑木底在史诗与神话叙事中的主要母题(表1),以表格的形式来进行比较。通过对比,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布洛陀神迹与布桑嘎西、桑木底神迹的相似与差异之处。

表1 布洛陀、布桑嘎西与桑木底叙事的主要母题
从表中可以看到,布洛陀的神迹呈现出从创世到造物、文化创造、秩序规定的过渡,侧重于文化方面的发明创造。布桑嘎西的神迹更侧重于创世和造万物,桑木底的神迹侧重于傣族社会的规则制定与文明创造。对比之下,在壮族史诗与神话叙事中的布洛陀合并了布桑嘎西和桑木底神迹对应的母题,使得他融合了创世神和文化创造神的双重角色身份。
除此之外,壮傣两个民族的始祖神话在细节上也有相互呼应之处。如壮族人民认为布洛陀寄生在树下,以树为形象,而傣族布桑嘎西是负责种树的神祇。无论布洛陀的配偶姆洛甲还是布桑嘎西的配偶雅桑嘎赛,都蕴藏并延续着花崇拜的传统。姆洛甲从花中生长而出,并以“花婆”的形象掌管为人间送花(子)事宜,而雅桑嘎赛以花为食。作为女性,姆洛甲和雅桑嘎赛常常是创造各类动物或生育人类的伟大母亲。她们直接生人的母题主要以散体的形式在民间口耳相传,少有进入典籍记载之中。这些细节之处,都使得两个民族的始祖在文化内涵上有了更多的共性。
综上考察,布洛陀显示出神迹涵盖更为多样、形象和职能融合更为宽泛的倾向。布桑嘎西、桑木底的神迹范围则较为清晰,侧重各有不同,在神祇性质方面存在一种前后延续的关系。这与壮、傣两个民族独立的文化与审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二、以史诗为中心的始祖形象比较
壮族史诗“布洛陀”和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分别对布洛陀和布桑嘎西两位始祖及配偶等形象进行了生动细致的精彩刻画。以史诗叙事为中心,辅以民间散体神话,可对两个民族始祖的形象塑造进行集中比较。其中,两个民族的始祖都延续着以“智慧”“坚韧”为主导的共性,但在具体内容上又各有侧重。
(一)始祖形象的“智慧”特征
壮傣两个民族的始祖形象各有特色,但依然可以清晰找到二者始祖形象的“智慧”共性,这是他们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创世、造人造物等过程,充满了艰辛复杂,并不是一蹴而就。其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需要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
壮族的布洛陀被壮人誉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祖先。布洛陀的名字本身就带有这层含义,“洛”为壮语“知道”的意思,“陀”为壮语“全部”的意思。他和配偶姆洛甲不但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创世,解决造物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更帮助人们解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人们遇到各种麻烦事,都要去祈请他们,“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姆洛甲)”。在这种情形之下,“布洛陀就讲,麽渌甲就说”[3]276,他和姆洛甲无穷的智慧指导着众人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并顺利地恢复生活的常态。例如,在“造谷种”的篇章中,就多次提及了布洛陀的指点。在谷物被洪水冲上山巅之时,他指导人们让老鼠和鸟去帮助寻找。在老鼠和鸟不肯把谷种带回时,他或指导人们捕捉它们,或自己亲自去捕捉它们,找到谷种带回栽种。他又嘱咐人们具体的耕作方法。在种出的谷物十分巨大而难以被食用和运输时,教人们把谷种击碎,这就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谷种。此后,他又教人们如何收割、定下招谷魂的仪式,让耕作之事代代相传。[3]260-277
用木槌来捶,用舂杵来擂。谷粒散得远,谷粒飞沙沙。拿去田中播,拿去田峒撒。一粒落坡边,成了芒芭谷。一粒落院子,变成粳谷丛。一粒落寨脚,变成了玉米。一粒落在墙角,变成了稗谷。一粒落在畲地,它变成了小米。一粒落在田峒,变成了籼稻。变成红糯谷,变成大糯谷……[3]271-273
布洛陀的智慧还体现在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上。他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麽仪式与经文,帮助人们维系日常生活的宁静:“起粮仓与建干栏,也是您的书中提。如何安葬选坟地,也是您的书中提。架桥拦水坝的事,也是您的书中提。”[4]949凭借自身的智慧维系着人类世界的秩序与规范。
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中多次提到布桑嘎西、雅桑嘎赛“聪明”“有智慧”。“智慧的桑嘎西/聪明的桑嘎赛/是英叭派下来/叫老夫妇二神/专下来补天/补天又补地/开创新人类/做人类始祖/当人类父母”。尤其是丈夫桑嘎西,“智慧更浩广”“主意办法多”。[2]149-153与其他可以为所欲为、靠咒语或者一个想法就能实现计划的天神不一样,布桑嘎西、雅桑嘎赛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尽一切办法来完成修补天地、创世造物的任务。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他们根据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结合现有的材料不断解决难题而实现的。
一来到大地上,两位始祖就面临如何修补天地的难题:“老夫妇二神/携带仙葫芦/走到天下层/仔细作观察/边看边思考/怎样来补天/怎样来补地”,雅桑嘎赛提议用自己身上的泥垢来补天地,得到了布桑嘎西的认可,他“称赞妻聪明”,便开始用泥垢做大地。“智慧老神仙/补地办法好”,做了很大的地盘。地盘在水中不稳,怎么办呢?雅桑嘎赛就想着找来大神树稳住大地,他上天入地都找不到这棵神树,着急万分。这时,“善良又聪明”的雅桑嘎赛冥思苦想,找到了好办法。她建议布桑嘎西用嘴里的神牙来固定大地,大地这才安稳了。他们用四颗宝石定四洲,“有智慧的”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给四大洲都定下了名称,修补天地的工作这才结束。[2]153
接着,他们将仙葫芦里的种子撒到四方,诞生了万种动物、万种草木,然而种子不够用了,还有半个大地没有种子撒,还光秃秃的。二位始祖神又开始商量该怎么办,雅桑嘎赛建议布桑嘎西去种树种花,她比较心细,则来造动物。雅桑嘎赛“聪明手巧”,捏出了世界上的各种动物。而桑嘎西“有的是智慧”,他想出用石块、石犁来刨坑、翻地,才把树苗种好了。[2]192-194
天地万物造好,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便商量如何造人。经过仔细商议,确定了人的样子、造人的方式、造人的材料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二位始祖“有的是神力/有的是办法/有的是主意”,捏出了一对神面“药果人”召诺阿和萨丽捧。后来,布桑嘎西、雅桑嘎赛把隐语的答案告诉召诺阿,他才能和萨丽捧结为夫妻。[2]153-228当葫芦人宛纳和约相想要造人时,约相说“要创建人类/事情不容易/你得有智慧/还得有眼力”,经过考验二人才结为夫妻。可见,人类对智慧的推崇,是生存的需要。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智慧来源于始祖,并不断受到他们的指点。
记录在贝叶经中的散体神话也多次强调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的聪明才智。例如说布桑嘎西“智慧非凡”“有智慧”“智慧超群”。他“懂得全部世规礼仪”,“知晓一切,主意和办法很多”。对应的,雅桑嘎赛则是“聪明的”“聪明绝顶的”。[5]29-58
人类首领桑木底也延续了布桑嘎西的智慧和能力,他不但是天神嘎古纳转世,还同样是以“智慧”特质取胜的首领:“他满脑有智慧/说话有道理/做事有办法”,故此被选为领袖,成为“帕雅桑木底腊扎”。[2]366-367
在早期百越先民的生活之中,生存与发展的艰辛使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更集中于自身智慧的运用。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拓了水稻的人工栽培,开创了稻作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创造了蔚为壮观的稻作文化。这种积淀在基因之中的以崇尚“智慧”为重的传统,扬长避短,不强调单纯以力量或神力取胜,而强调了发挥自身优长之处、以智慧破解难题的思维模式。
以“智慧”为根基,壮傣民族的始祖形象塑造又各有侧重。从内容上看,傣族始祖布桑嘎西、雅桑嘎赛注重于创世、造物和造人,他们依靠自己的亲身行动,佐以天神及神葫芦等的帮助,完成了人类物质世界的创造。在文化创造方面,他们主要完成了四大洲的方向、属性的确定,为万物和人类案名定性,主导人类的繁衍兴旺。相较而言,壮族始祖布洛陀、姆洛甲创世的内容则显得没有这么详尽,主要集中于布洛陀和姆洛甲顶天立地方面。史诗叙述的重点主要放在造物造人、创制文化、安排秩序等内容上,突出了始祖在社会形成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创制文化、安排秩序等方面,与桑木底的内容多有重合与相似之处。例如兄弟分家、造房子、祭祀寨(心)、开创定居的农耕生活、教人们饲养家畜,制作器皿等。这些异同之处,反映了壮傣民族在传统社会中的不同精神需求。
(二)始祖形象的“坚韧”特征
无论是壮族还是傣族的始祖,都以“坚韧”见长。虽然他们身材伟岸、神力超群,但相关叙事更注重强调他们在创世造人等历程中的百折不回、细致耐心精神。这种精神,蕴藏着百越早期稻作生产生活对民族品格的凝铸。
壮族始祖布洛陀在对待创世、造物等事宜时全心全力,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并没有因为偶然的失败而放弃努力,而是通过多种方式,以坚韧细致的精神完成创世造物的过程。例如在造牛时,他耐心地完成有关过程的每一个细节。用黄泥、黑泥做出牛的身体后,还需要“用杨乌木做大腿,用酸枣果做乳头,用紫檀木做牛骨,用野蕉叶做牛肠,用鹅卵石做牛肝,用红泥来做牛肉,用马蜂巢做牛肚,用鹅卵石做牛蹄,用刀尖来做牛角,用枫树叶做牛舌,用树叶来做牛耳,用苏木来做牛血”[3]281造出了牛模型,放到土坑壅埋,九天后才长成活牛。布洛陀又指点人们用麻绳穿牛鼻,把牛牵回家饲养,牛繁殖很快。此后,遇到牛生病时,还要举行“赎牛魂”仪式,使牛魂回归附体,才能继续繁衍。
傣族的始祖布桑嘎西、雅桑嘎赛亦拥有坚韧不拔的品格特征。他们在面对各种困难时,锲而不舍地寻求解决方案,并历经千辛万苦去解决问题,肯于作出牺牲。在二位始祖来到大地上时,地便薄了,神柱也倾倒了,天垮地塌,只有茫茫水一片。在这种恶劣的情境之下,布桑嘎西、雅桑嘎赛没有气馁,他们想尽办法,先做泥垢盘,捏出大地,抛入水中做成了大地“罗宗补”。布桑嘎西又上天去寻找固定大地的神柱,他飞到天上神山没有找到,又飞到更高层的神王山去寻找,此后,又到河里、海里去找,“寻遍茫茫水域/不见树影子”,还是没有找到。雅桑嘎赛让布桑嘎西用嘴里的神牙固定大地。布桑嘎西心里犹豫:“这可不能够/这主意不好/我把牙拔了/嘴里就无牙/我两腮凹陷/岂不变难看啦”,后经雅桑嘎赛劝说,他毅然拔下了自己的一颗犬牙和六颗门牙,把大地固定好了。此后,他们还不厌其烦地在四大洲埋下宝石、为它们确定性质、取了名字,创世才算完成。[2]153-228
在造万物的时候,两位始祖神面临了更大的问题。葫芦里仙籽数量不够,只撒了半个大地。于是,他们只能自己捏制动植物,自己栽种树苗把大地填满。地上的树苗树种多,“叶嫩杆又细”,但就算是如此繁琐,布桑嘎西依然耐心细致地“拔了又拔/从东栽到西/从南栽到北”,把树苗全都栽满,“所种的植物/种类多达九万亿”。他们认真地地挖沟犁地栽种树种,不顾自己疲惫不堪:“他俩累极了/鼻尖流下汗”,汗水汇成了大地上的江河湖海。[2]153-228
在造人的时候,始祖更是极具耐心,付出万千的艰辛来制作人种,呵护人类的成长。布桑嘎西更是费尽力气才找来孕育人类的仙果:“到了神王山/仔细来找寻/看过亿棵树/找了万处山/好不容易才找到/孕育人种的仙果”。他们耐心地把仙果碾碎,揉捏搓得像黄泥一样有黏性,捏出形状,还要对药果人吹仙气、做祷告,药果人这才成活。此后,他们还要让召诺阿和萨丽捧结为夫妻,帮召诺阿解答隐语。都是有了始祖的细心呵护,人类才最终繁衍起来。[2]153-231
壮傣民族性格中坚韧不拔、耐心细致的特点在始祖形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强调神祇无限扩大的神力、征战英雄无穷的力量和速度等不同,史诗更注重展示的是始祖这种基于生产生活实际而养成的民族习性。
三、始祖形象的日月信仰本源
壮傣民族的布洛陀和姆洛甲、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两对始祖在名字与内涵上都呈现出对应关系,这是侗台语民族常见的对偶始祖崇拜的特征再现。对偶始祖的名字相互呼应,具有同源属性。从始祖名字与内涵上分析,他们都与早期的日月崇拜有关。
(一)壮族始祖形象的日月信仰本源
布洛陀、姆洛甲的名称来源于日月。无论是“洛”“陀”还是“甲”都是壮族“日”“月”的语音演变。其中,“洛”最初源自早期侗台语“月”的发音,李方桂构拟的原始侗台语“月”为[ʔbl/rɯen],梁敏则拟为[ʔmblɯen]。[6]134这个词还与“日”“眼”有关。后来由于语音演变而与“鸟”相同或相近,便产生了其为鸟的相关传说。而“陀”则来源于ta,“甲”来源于kjaŋ,都具有“眼睛”“日月”的含义。布洛陀和姆洛甲的名字具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根据史诗内容的重叠等特点,他们的名字及神格具有内部的一致性,为同一神祇分化的结果。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布洛陀和姆洛甲的含义又不断丰富,内涵逐渐增多,但其根源依然是侗台语早期的日月(眼)崇拜。[7]
具体来看,布洛陀带有早期“日—鸟”崇拜的特征。在神话《布洛陀四兄弟分家》中,布洛陀有四兄弟,老大是雷王,老二是蛟龙,老三是老虎,布洛陀自己是老四。[1]49布洛陀和以“鸟”形象著称的雷王是兄弟,亦带有鸟图腾的基因。他和雷王针锋相对的斗争,体现出“日—雷(雨)”的对应关系。布洛陀史诗中说世界由三黄蛋分裂而成,天上由雷王管,人间由布洛陀管,水界由图额管。卵生的叙述是早期壮族先民鸟崇拜留下的痕迹。
姆洛甲形象亦体现出“月—乌”崇拜的浓厚色彩。与姆洛甲一脉相承的“达汪”形象,在壮族民间广为人知。她被视为“月神娘”,传说因为被土司陷害含冤而死,鸟雀把她的尸体葬在月亮上。[14]196西林等地的壮人说娅王是造物之神,造出了世界万物。娅王每年农历七月十七就开始生病,七月十八病重,七月十九去世,七月二十出殡安葬,七月二十一重又生还,年年如此。这与月亮的阴晴圆缺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起死回生特点,与月亮的性质是一致的,月亮因为围绕地球转,并被地球带着围绕太阳公转,所以每月都会出现圆缺的变化,古代人们对此现象不理解,便以为月亮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由月亮衍生而出的西王母才拥有不死药,可以起死回生。”[7]壮族先民对月亮的崇拜凝聚在姆洛甲的形象之中,并延续于此后的相关角色。
与此同时,姆洛甲还保留着早期的日崇拜痕迹。如云南文山州西畴县的壮族人民将太阳称为“汤温”,在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过“太阳节”。节日当天正午,村中18 岁以上的女性要到河里沐浴更衣,着盛装到当地太阳落下的太阳山祭祀太阳神树,并由年长者领唱《祭太阳歌》。“汤温”与“达汪”在发音上相接近。“在人类的早期,太阳与月亮往往是同一名称,都被视为人的眼睛”,日月从根本上是统一的。[7]有关“太阳节”起源的另外一个神话异文《乜星与太阳》则说太阳是男性。他化身为壮族小伙子躲在歌场,壮族首领鸟母乜星找到他后,托着他飞到空中,从此只要雄鸡一叫,她就托着太阳准时地在空中翱翔。乜星的女儿,则变成月亮,追随着她的情人——太阳。[8]由此,姆洛甲形象中所带有的日崇拜基因也是十分鲜明的。
(二)傣族始祖形象的日月信仰本源
从语音上探讨,布桑嘎西(pu:35saŋ55ka33si:55)、雅桑嘎赛(ja:33saŋ55ka33sai13)的名字带有日月的痕迹。西双版纳傣泐语中,“光”“线”称为“sai55”,无论是“日光”“月光”,使用的都是这个词。比如“日光”为“sai55dεt35”。①由于名字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存在音转、音变的可能,故暂时不将音调列入考察范围。因此雅桑嘎赛的“赛”虽然有所音变,但仍可回溯其所具有的“日光”这一含义。
从名字上看,布桑嘎西和雅桑嘎赛呈现对称关系。除去性别词头尊称、表示神祇身份的“桑”,二人的名字则是相似的。无论是“布桑嘎西”与“雅桑嘎赛”,还是“布桑嘎”与“雅桑赛”、“莱桑西”与“婻桑赛”、“布桑嘎洒”与“雅桑嘎西”等叫法,“西”“洒”与“赛”都具有语音上对应、演化的可能。②受个人学识限制,在此只能使用汉语音译名称来进行比较,但由于记音的变化不大,不影响此处的研究分析。更不用说其他的始祖名称如“布桑嘎”与“雅桑嘎”、“布桑该”与“雅桑该”等始祖名字中,“嘎”“该”都是完全相似的简化用字。根据泰国清迈皇家大学兰纳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万瑞媛(Wannida)的介绍,在泰北相关民族中还有“布桑赛”与“雅桑赛”的叫法。基由于二位始祖神祇名字呈现对应关系,雅桑嘎赛名称中“光线”的含义可被布桑嘎西所共享。
从两位始祖的形象来看,他们与“日”“月”的关系愈发明显。例如布桑嘎西“在亿万天神中/数他神力大/英叭神恩赐/赋予他火型/所以他性情/贪婪又急躁/心刚烈似火”,他“两眼像太阳/望穿万座山”,更不用说身宽体大,听力发达,嘴边长着大犬牙,两腮长的胡须又重又长,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2]151还有神话说他“周身长满黄毛”“终日以热浪和空气为食”。[5]29又如雅桑嘎赛的形象,“肉色像银花/夜间身发光/笑脸像明月/不打扮也美/在所有的女神中/要数她第一/英叭神恩赐/赋予她土型/做万物的母亲”。[2]151她的肤色“洁白娇嫩”,宛如“一朵银色的缅桂花,夜里也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她“椭圆形的脸庞”犹如月亮一般,“就是在夜晚,她的肤色也会闪烁金光”。[5]29从内容来看,雅桑嘎赛对应的是月亮的形态,并和代表阴性的“土”是相对应的。可见,布桑嘎西的形象来源于太阳(火),而雅桑嘎赛的形象则来源于月亮(土),特征十分鲜明。
(三)日月信仰的骆越之源
根据相关研究,壮族和傣族的主体均源自百越中的骆越先民。江应樑在《傣族史》中就明确指出,壮、傣等民族均源出早期的百越族群,无论是“越”还是“瓯”“骆”,“是同一族的不同称谓”。[9]24-26他们底层文化中的日月崇拜根源,是理解两个民族文化同中存异的基础。
壮族先民的主体来源于骆越。[10]47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壮族来源的看法都较为一致,认为他们主要来源于百越中西瓯、骆越两大部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徐松石曾认为,“僮”或称为“西瓯”“骆越”。[11]73《壮族简史》中曾指出“分布于广东西部和广西境内的西瓯、骆越等支系,则同壮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壮族主要来源于土著的西瓯、骆越”。[12]7-8《壮族通史》认为:“在众多的越人种属之中,壮族乃渊源于西瓯、骆越人。”[13]288大致在邕江、右江界限以南,沿玉林到南宁一线延伸至文山地区,都是骆越人生活的主要区域。如今这些地域大部分仍为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且从古到今,骆越人虽然有部分发生迁徙,但综合历史记载、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历史文献资料,其主体部分仍是当地的土著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形成了今日的壮族。
傣族先民中的主体部分也来源于骆越。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壮傣族群的大规模西迁肯定是汉朝时南越国灭亡之后,傣族进入元①笔者认为“元”字为笔误,应为‘云’字。南和泰国据证也只是唐朝的事情。而从云南的勐卯国西迁至印度则是公元1215 年。所以西部越族发源于广东的历史是清晰的。”[14]从广东省广州市之南、高州市、茂名市等地直至海南省,都属于古骆越国的东部疆域。后晋时的《旧唐书·地理志》、清代的《康熙字典》都记录了广东骆越人的活动。至今,在广东西部仍有少量骆越后裔——壮族分布。故此可推测,傣族的主源是广东的骆越先民。
“骆越”一词同样具有日月崇拜的内涵。根据吴晓东的研究,“骆”的上古音构拟为[ɡ·raːɡ],到了中古才演变为[lak]。这个字与月神女娲的“娲”可能同源,“呙”可念kuo。“骆越”的“越”字,目前与“月”同音,而其上古音构拟为[ɢWaːd],与女娲的“娲”读音几乎一样。“骆越”一词很可能与日月有关,骆越民族一开始便可能是因为崇拜日月而以日月命名。[7]由此可见,作为骆越后裔的壮、傣民族人民的日月崇拜原有出处,一脉相承。
由日月崇拜而衍生出的乌、鸟信仰在骆越文化中根深蒂固。骆越典型的铜鼓上亦多有羽人、鹭鸟、渡船的纹饰。《越绝书·记地传》《交州外域记》等典籍中都有对骆越耕作鸟田等的记载。可见,骆越对鸟类的崇拜来源于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对象。在天空层面的天体(日月)到鸟类都是影响骆越先民生存之道的传统延续。
壮傣两个民族始祖叙事也继承了骆越文化中的鸟崇拜传统。例如,布洛陀、姆洛甲中隐藏的鸟图腾信仰和骆越文化所体现的鸟崇拜相一致。布洛陀史诗里曾写“天下十二个种族”“二六个部族”,其中就包括了鸟部落、鸡部落(禽类)。[1]47-48从语音上来考察,原始侗台语构拟的“鸟”,发音为*mrok 或*mlok,文本中“鸟”的发音多为 l(r)ok8,与布洛陀之“洛”lu(o/ɔ/ə)k 的发音也较为一致。[15]32傣族文化虽受佛教文化影响深厚,但依然隐藏着早期鸟类崇拜的一些内容。与布桑嘎西似有血缘联系、带有太阳属性的英叭就驾驶着一辆凤凰鸟(或大鸟)驱使的飞车。[16]24
壮傣民族的始祖叙事还突出展现了人类日月神话的共同特征。无论是布洛陀还是布桑嘎西始祖均是创世、造物、制文化的大神。“纵观世界上诸如希腊神话、印度神话等神话圈,这类大神多源于对人类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日月神话,换言之,这样的大神多是由日月拟人化之后演变过来的。在汉族神话中,伏羲女娲、后羿嫦娥、黄帝嫘祖这些创世夫妻神或文化英雄夫妻神,也都是从日月神演变发展过来的”。[7]综上所述,壮傣民族的始祖神信仰之源可上溯至骆越先民的日月崇拜。
四、史诗传承机制的比较
(一)源于“越巫”的壮族布麽与傣族章哈
壮傣民族先民的巫信仰可上溯至骆越先民的“越巫”(mo)传统。骆越先民早期的思维观念崇尚各类巫术。明朝邝露《赤雅》记载了汉代京师的越巫活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 年)平越,得越巫,适有祠祷之事,令祠上帝,祭百鬼,用鸡卜。斯时方士如云,儒臣如雨,天子有事,不昆命于元龟,降用夷礼,廷臣莫敢致诤,意其术大有可观者矣。”[17]52越巫被视为通达天际与人间、鬼界与人界之使者,行鸡卜之术,在社会中有威望,受人尊重。越巫的行为和观念也在壮族和傣族文化中有着无形的深远影响。壮族和傣族先民传承并发展了“巫”(mo)信仰的内容,如今,壮语里仍称巫师为“麽”(mo),傣语里“巫师、算命师”也被称为“mo”,男巫为“bo mo”,女巫为“me mo(mot)”。两个民族的这类共同词汇发音十分相似,其涵义和相关仪式也较为一致。
壮傣民族先民在巫信仰的基础上分别培育出了作为史诗演述人的布麽和章哈。作为史诗“布洛陀”演述者的布麽,其“麽”字即来源于“巫”。布麽在自成体系的麽信仰里操持相关仪式,完成史诗的演述。其身份珍贵而受人敬重。他们有独特的麽信仰神灵系统,具有诸多自我约束的条规。在仪式之外,他们还进行鸡卜、解卦、选日子、查看风水地理等具有巫术源头的活动。
章哈是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专业演述者。“章”是专业人士的意思,“哈”有多种意思,包括“韵文诗歌”“赶走”等含义,亦有学者写作“赞哈”等。章哈脱胎于傣族社会早期的巫师,正如屈永仙的研究指出:“傣族文化还处于诗、歌、舞尚未分工的阶段,会唱歌的人(章哈)和会祭祀的人(摩赞)仍然合二为一,歌手即巫师。随着傣族社会的发展,章哈与摩赞出现了新的分工,章哈不再兼管祭祀,只管为村民生活仪式中唱歌;而摩赞则放弃了唱歌的职能,专管祭祀。这样,章哈便从摩赞中脱胎而出,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职业……”[16]61-62随着时代的发展,章哈逐步脱离仪式,成为以“娱人”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演述人,演述内容在史诗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民众喜闻乐见的成分。如今的章哈,其主要功能在于“助兴娱人”。[18]
章哈中的“章哈丢拉”与壮族“布麽”的身份、职能高度相似。“章哈丢拉”曾经是西双版纳傣族傣泐支系中主持祭祀、驱邪、祈福等仪式并吟诵相关史诗内容的章哈。“丢拉”在傣语中就是“神”的意思,或源于佛经里的巴利文“Devānām”(泛指天神)的简称。在早期傣族社会,还有女章哈在祭祀仪式上献唱的传统。如祭祀寨神和勐神时对章哈身份有特殊的要求——必须是未婚处女。[19]101随着时代的变迁,西双版纳地区的“章哈丢拉”逐渐消失,相关演述由一般的章哈来主持完成。
(二)承载仪式及其功能
壮傣民族中与始祖叙事相关的仪式活动都有大、小之分,既有集体性的祭仪场合,又有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小仪式。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演诵场合有大有小。大的如红水河中上游地区的祭祖、右江流域的扫寨、广西田阳敢壮山的“春祭布洛陀”、玉凤镇祭祀布洛陀岩像以及云南文山村寨祭祀布洛陀树等仪式活动。届时,布麽会吟诵所知布洛陀史诗的全部内容,讲述布洛陀开天辟地、造物、创文化直至定秩序的丰富内容,向人们传递传统的民族知识。在补粮、招生魂、赎亡魂、为新房安龙、招谷魂、赎牛魂、祭灶、缓和人际关系等小型仪式上,布麽根据实际需求而选取相关篇章来念诵。例如,在四月初八“牛魂节”或牛突然生病时,布麽就会选择“赎牛魂”的篇章来演述,赎回牛魂。同样,傣族章哈演述始祖史诗的情形亦包括大型和小型两种仪式。大型仪式如以集体形式组织的祭祀寨心、勐神等,一般两到三年举行一次。在这类仪式上,章哈演述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了创世、造人等篇幅较长的史诗篇章,讲述世界的来源和今日要遵守仪式规章的各种缘由。小型仪式主要是以家庭或个人为主导的入新房、婚庆及丧葬仪式等,所演述的史诗内容篇幅较为有限,而且可以根据听众的需要选择相关内容。例如,入新房时偏重讲述傣族先民首领桑木底教人们造房的内容,但章哈也根据需要演述布桑嘎西、雅桑嘎赛创世、造人的篇章。在傣族人的观念之中,两位始祖也是各类仪式规范的制定者之一。
壮傣族始祖史诗所依托的仪式步骤亦具有相似性。仪式既要驱走邪祟,又要传递祝福。壮族演述“布洛陀”史诗的仪式亦包含了驱邪、祈福两大内容。在仪式一开始,要先请始祖神等入座,然后根据所举行的仪式挑选史诗中相关的篇章进行演述,以此陈述与仪式起源、传统相关的内容,让民众理解史诗与仪式之间的关系,感受始祖伟力的神圣不凡,增长始祖的威望。在吟诵结束后,要驱邪扫晦,并请始祖等神祇返回自己的居所。
傣族演述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仪式步骤大致也是如此。屈永仙观摩的傣族入新房仪式中,人们要先做出各种邪祟之物的塑像,并在波占念经后将之送走。与此同时,僧人也来屋中念经并用犁、锄等工具驱邪,并挥洒圣水洁屋。驱邪结束之后,则要进行祈福环节,波占、僧人为屋主诵经,亲朋好友也跟着祈福,并给将要居住在新屋里的一家人拴白线。唱诵有关始祖叙事的章哈前来表演,要请寨长代为敬告寨神,才能开始自己的演诵。按照传统而言,他们是不能边演唱边看手抄本的,必须完全脱稿。[16]147-148章哈所演唱的内容,则要讲述始祖造人、桑木底盖房等内容。
总之,壮族和傣族有关始祖的史诗演述都来源于早期民间信仰仪式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需要,它们逐步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途径,形成了面貌迥异的表现形式。历史上壮傣民族的史诗演述仪式分别受到道教和佛教的深刻影响,这是其表现差异的主要原因。
(三)差异日益扩大的传承模式
如今,壮族“布洛陀”和傣族“巴塔麻嘎捧尚罗”史诗传承模式的差异日益扩大。这既反映了两个民族人民不同的精神需求,又与社会诸多力量的作用有关。
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演述依然以仪式传承为主,布麽对仪式和史诗进行改变与创新空间极其有限,依然以唱诵手抄本、按照既定仪式规则来操持为主。因受传统观念限制,仪式上演述的史诗则很少会在日常场合中出现。这就极大地阻碍了史诗的传承。与此同时,仪式之外的散体始祖神话传承缺乏革新动力,逐步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淡化,年轻传承人较少。
傣族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的演述日益世俗化,不但可以在传统仪式中演述,还可以在各类节庆表演中出现。如在西双版纳泼水节庆典上,章哈可以随着游行队伍,在旱船上为大家进行表演。[20]164章哈演唱的内容形式更为灵活,可根据不同场合而进行创编和调整。章哈的伴奏乐器也有所革新,如杨民康在调查中就曾看到章哈歌手以吉他来进行伴奏,因为演述人觉得这种乐器更为时髦、更受年轻人欢迎。[19]129
除此之外,随着章哈的日益职业化,傣族史诗演述人与文本撰写者之间日益分离。这种现象的出现,为史诗文本的丰富提供了创作的活力。受自身学识的限制,章哈会请学识丰富的“康朗”帮助他们创作韵文体的演述文本。“康朗”是傣语的记音,指的是那些“出家修行到大佛爷僧阶然后还俗的男子”。[16]46康朗熟读佛经,掌握多种文字,能够将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等按照傣族传统的韵律,结合佛经的内容与形式完成史诗文本的创作。不同的康朗根据自己丰富的经历和独特的领悟力,会创作出精彩纷呈的史诗文本。“巴塔麻嘎捧尚罗”就有不少文本是他们创作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文本的大量涌现为史诗传承提供了活力,以精英加工的方式实现了对民间的反哺,在词句、韵律、情节等方面都有着美学上的提升。如根据屈永仙的调查,勐海县勐遮镇的女章哈玉旺叫就曾请当地的康朗洪为她创作过不少演述文本。这些文本内容丰富,既包括了各类民众喜闻乐见的神话内容,还包括各类传说、反映现实内容的题材等。[16]46康朗洪为玉旺叫所创作的文本中就有一首短歌,反映了勐遮镇的历史变迁。歌中融入了民间有关青鸟栖榕树的传说,把青鸟的来去和勐遮的兴衰进行了勾连。歌中歌颂了新时代下勐遮经济的恢复,游人如织,令人充满了期待。与此同时,有的学识渊博的章哈依然可以自己完成演述文本的创作。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种章哈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也使章哈这个职业所传承的内容日益偏离传统的叙事,与时代的需求相结合,根据听众的需要来撰写文本。
由此,不同的传承模式影响了始祖叙事传承的生命力。壮族的始祖叙事传承人——布麽,本身就是仪式操持者和民间信仰的坚持者。他们对于传统的坚持,对于信条的坚守和信仰的执着,使得始祖叙事内容较少会被改变。布麽奉祖传的手抄本为经典,新的文本尽量按照传统来抄写,也基本不示外人,很难突破既有的框架去创新。此外,布麽所述的始祖叙事内容逐步变成以“娱神”为主,以向神陈述祈祷为主,较少去考虑听众的感受,也就没有那么急迫的需要去进行符合时代的革新。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的发展,难以跟上社会的进步,不易受到年轻人的接受和喜爱。相较而言,傣族的始祖叙事的文本创编与演述者之间日益分离,这既有演述者方面对傣文、傣族文化掌握情况不佳的情况,但也使得文本生命力增强,依靠更为适合的创编人不断获得新鲜血液,融入新的叙事内容和个人色彩,逐步走向仪式之外。创编人可以根据时代和听众的需要,不断调整书写内容,使之更为适应当下的需要。
五、结 语
立足于壮族和傣族的经典史诗“布洛陀”和“巴塔麻嘎捧尚罗”,通过比较布洛陀、布桑嘎西和桑木底等始祖神祇的形象与内涵,我们可以对目前形态呈现差异较大的壮族、傣族文化传统有新的认识。两个民族的始祖形象虽然看着面目迥异,实际上在叙事母题、形象塑造与文化内涵上有着突出的共性与渊源:(1)两部史诗都强调始祖的“智慧”“坚韧”的特征,突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超强能力;(2)史诗母题传承着诸多源自早期的共同叙事,包括创世、造人、造物等内容;(3)两个民族的始祖名称与文化内涵均指向日月崇拜,共享骆越族群早期的天体信仰内容。
随着壮族和傣族社会与文化的独立发展,两个民族史诗的传承机制各有不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傣族史诗与仪式的分离使史诗具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活力增强。历史上,壮傣民族及其先民也有不断南迁的历史,这使得他们的始祖史诗叙事广为传播。越南的侬族(Nung)依然有布洛陀史诗的传承。分布在东南亚的傣族傣泐、以清迈为中心的泰阮(Yuan)族群中,都能找到“巴塔麻嘎捧尚罗”的传承与发展。史诗演述语境的多样化是今日史诗创新发展的有利条件,相关研究工作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的民心相通都大有裨益。同时,对史诗传承机制的考察和规律总结,将有助于这一口头传统精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找到最优的传承创新途径,激发其生命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