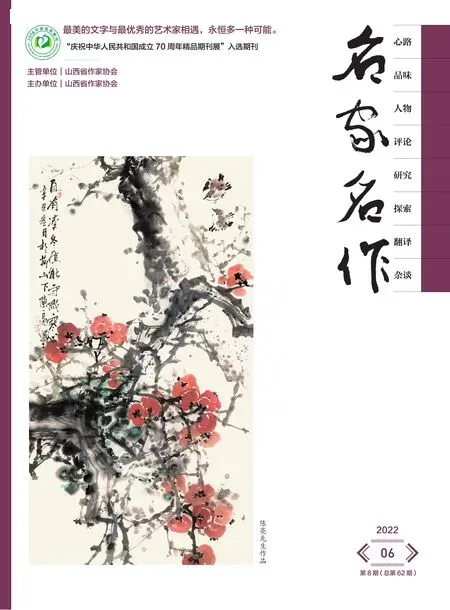“肉夹馍”结构方式探究
黄若琦
“肉夹馍”是汉语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单从外观来看,“肉夹馍”的真正意义是把肉夹在馍里,本就应该叫“馍夹肉”,而非“肉夹馍”,但现在虽然偶尔也有“馍夹肉”这种说法,但并不常见。有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笔者将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寻找出更有说服力的说法。
一、民俗文化说
“民俗文化说”大多源自民间,往往是由人们口耳相传而得,流传得较广的要数“读音说”和“消费者心理说”。虽然“民俗文化说”大多数没有具体的证据,但在文化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读音说
“读音说”源自陕西民间。根据陕西当地人的口耳相传,陕西本地对于该问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在过去这样的民间小吃大多是靠吆喝售卖的,这种“吆喝”都是平仄协律、平上去入、阴阳浊清严格分明的,而因为地方方言的语音限制,“馍夹肉”用陕西当地的方言讲起来像“没加肉”,完全不适合吆喝,更不利于售卖。吆喝中的“肉夹馍”名称的出现很可能是某个商贩为了迎合吆喝所需的协律而形成的,从此以后人们便将这个名称流传下来。该说法虽然流传甚广,但依旧要对其提出疑问:根据陕西方言,“肉夹馍”中的“馍”字读音是四声偏轻声(关中话是轻声),而“没加肉”的“没”字读音是二声偏轻声,就算在读音上会有一些混淆或者歧义,在现实中也基本不会有什么使用上的困难。更何况“肉夹馍”这种食物不仅陕西地区有,山西地区也有,那么“读音说”又如何让山西地区的人信服呢?甚至陕西和山西某些地区还卖“菜夹饼”,词语结构与“肉夹馍”相同,但却没有上述说法的存在,这也说明了读音说较难成立。这样的民俗文化说我们很难去考证是否完全准确,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馍夹肉”谐音的存在,因为往往正是这种“口耳相传”才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
(二)消费者心理说
另一种民间说法是认为把“肉”字置于最前面更能体现出这种食物的特点,因为肉夹馍中的“肉”才是整个小吃的主要部分,将“肉”字置于最前面能够起到吸引顾客的作用。无论是售卖者还是销售者,主观上都希望这种食物的“肉”的含量看起来更大,所以将“肉”字置于前面。但这种民间说法更像是为了迎合“肉夹馍”的名称和食物特点所创造出的一种“美丽的说法”,具有文化上的参考价值,而在其名称考证上的价值还有待商榷,这里便不加赘述。
二、缩略说
有许多学者提出了“缩略说”这一观点,他们认为陕西方言中保留了古语的说法,“肉夹馍”应该是古代汉语中“肉夹于馍”的缩略形式。古代汉语中省略句十分常见,因此这种说法的出现也不无道理,因为“于”在古代汉语中常用的用法是作表被动的介词,若把“肉夹馍”认作是“肉夹于馍”的省略形式,那么就表示最初这个食物的名称应该叫“肉夹于馍”。但这个说法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若把这种食物的名称叫做“肉夹于馍”,那么它便不再是词,而变成了一个句子,这样的命名方式更像在叙述一件事情,不符合名称语言的简洁性,说服力不强。第二,若把“于”字省略了就模糊了原来被动的含义,可能让人产生误解,认为它不是被动而变成了主动,而事实上强调被动的这个“于”字是不应该省略的。付佩在《关于“肉夹馍”的几点思考》中也提道:“肉夹馍是一个具有特殊指称的合成词,其指称的事物是语素相合之外的一种特殊含义,如果分开就不能表示这个食物的整个特征,它是根据本质属性划分的类别,属于词。”根据以上几点阐述,许多学者提出的“缩略说”还有待商榷。
雁红在《也谈“肉夹馍”》一文中认为:“肉夹馍”这个名词并非一般的合成词,而是短语(或句子)缩略而成的凝固形式,是“肉夹在馍里”的缩略形式。她认为“肉夹在馍里”根据韵律的句法规则,以“留下重读词、去掉轻读词”为原则,去掉轻读的“在”和“里”,自然缩略成了“肉夹馍”,这样是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律的。然而这种说法虽有其道理,却缺乏佐证的历史材料和语言材料,因此也是有待商榷的。
三、外来词直译说
语言是多样的,语言接触的现象时有发生,上面的两种观点都是基于本国语言进行分析的,那么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肉夹馍”一词其实是由外来词直译,或者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接触而造成的特殊语法现象。该猜测虽然是根据陕西关中当地的饮食文化背景等条件合理提出的,但据历史材料显示,这种食品的制作工艺早在唐朝就已出现。根据贾志刚所阐述的资料显示,最早记载与“肉夹馍”制作工艺相关的资料是唐人刘悚撰的《隋唐嘉话》:“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拭手。帝屡目焉,士及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这里的“饼夹食用法”便是“肉夹馍”的前身。在此之后的唐人和宋人都对此事有所记载。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历史文献都记载了这种食物的制作工艺,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食物的雏形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是属于中国地域的美食,因此“外来词直译说”是不成立的。
四、词语结构分析
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虽然有其道理,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民俗文化说”缺乏佐证的历史材料;而“缩略说”则模糊了语法意义;“外来词直译说”更是由相关的历史材料证明出其不合理之处。想要进一步探究有关“肉夹馍”的语言现象,需要对词语结构进行分析。提出“肉夹馍”为什么不叫“馍夹肉”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把这个食物名称拆成了三个语素:“肉”“夹”和“馍”。这里的“肉”和“馍”都是名词,而“夹”则是动词。通过排列组合,我们知道这三个语素一共可以有六种排列,分别是肉夹馍、肉馍夹、夹肉馍、夹馍肉、馍肉夹、馍夹肉。“肉馍夹”和“馍肉夹”这两种排列的意义不大,因为 “肉”和“馍”为两个名词,将两个名词并列放至“夹”的前面并不能表现“肉”和“馍”的主动与被动的情况,因此这两种并列结构的命名对该食品文化的发扬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因此才没有流传至今。王都蔚对其余四种结构做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将它们分为两组进行说明。
(一)动宾结构:“夹肉馍”与“夹馍肉”
首先,我们可以将这两个词看作动宾结构:“夹—肉馍”和“夹—馍肉”。与“炒鸡蛋”相似,这里的动宾结构是做名词使用,但在平常的使用中人们可能会将其认为是一种“夹”的行为动作。王都蔚教授将“夹肉馍”和“夹馍肉”看作偏正结构。他认为,“夹肉馍”指的是一种馍,意为“夹着肉的馍”;而“夹馍肉”指的是一种肉,意为“夹着馍的肉”。这样看来,“夹肉馍”这种说法是合乎道理的,而“夹馍肉”主要指的是其中的肉,与食物特点并不匹配。根据王都蔚的阐述来看,“夹肉馍”的结构似乎更合乎道理。
(二)主谓结构:“肉夹馍”与“馍夹肉”
这两个词语结构的说法将重心落在了“夹”字上。首先,“肉夹馍”这个词可以看作是主谓结构,表示“肉夹住馍”,“馍夹肉”也能看成主谓结构,表示成“馍夹住肉”的意思,这同样也是很多人的看法。然而,将其理解成“肉夹住馍”或者“馍夹住肉”,有将其作为动作行为的嫌疑。王都蔚也将这两种结构理解为偏正结构,即“肉夹的馍”和“馍夹的肉”。但这都只强调该事物的其中一部分,即“肉夹的馍”强调了“馍”,而“馍夹的肉”强调了“肉”,不能代替整体,因此这两种结构似乎都不太符合食物的特点。
从这些观点来看,似乎是第一点提到的“夹肉馍”更符合食物的特点,但为什么流传下来的是“肉夹馍”而不是“夹肉馍”呢?王都蔚认为这是“约定俗成”的。首先,“夹肉馍”这个名称并不适合该食物的流传,因为“夹肉”并没有固化成一个独立的词,那么“夹”字在这里会被许多人理解成为动词,整个词组就会被看作是“1+2 式”。在汉语的结构中,“1+2 式”以动宾结构居多,例如“租汽车”等。所以在这个词组中,人们便会顺理成章地将其理解成“夹起一个肉馍”,而不是理解成上面所阐述的偏正结构——“夹着肉的馍”,在造成一定误解的同时也对食品文化的流传带来一定的阻碍。王都蔚认为最终流传下来的是“肉夹馍”这个名称不仅仅与词语结构有关,可能还与当时人们的消费心理有关,这个说法可以参考前文的“消费者心理说”。
(三)偏正结构:肉—夹馍
这种说法不把“肉夹馍”看成主谓结构,而把它看成是除“肉夹的馍”外的另一种偏正结构,认为“夹馍”是一个偏正词语,而“肉”在这里是修饰“夹馍”的成分,是说明“夹馍”的材料。这样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如杨锡彭曾这样解释“夹馍”:“所谓夹馍,或将一块馍掰开形成一个夹层,或将两块馍上下叠放,中间加上肉、蔬菜什么的,就成‘夹馍’。”杨锡彭对“夹馍”的解释也说明了“夹馍”这个词的凝固性很强,所以“夹馍”可以暂且定义为“夹着东西的馍”,这样“肉”和“夹馍”都变成了名词,“肉夹馍”便可以认为是偏正结构(或者说是定中结构,定语+中心语)。从杨锡彭的解释中不难看出这里的“夹馍”同样也是一层定中结构,由“夹”修饰“馍”,最后再由“肉”修饰“夹馍”。在关中地区,“夹馍”是当地人常用的词汇,那里不仅仅只有“肉夹馍”这一种小吃,还有菜夹馍、大油夹馍、辣子夹馍等一类的“夹馍”。这样分析下来,“肉夹馍”这个食品名称便相当符合食物的特点,这个说法也是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的。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夹”这样解释:“夹,持也。从大侠二人。”段玉裁注:“持者、握也。握者、搤也。搤者、捉也。捉物必以两手。故凡持曰夹。”对于“夹馍”凝固化的探究,笔者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夹”字下面的词条。由于“夹”字是多音字,有[jiā]和[jiá]两个读音,所以“夹馍”中的“夹”究竟读一声还是二声也是有争议的,且“夹”字字条下两个不同的读音所表达的意义也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夹[jiā]”,该读音下包含了如“夹板”“夹棍”等与“夹馍”所表达的语义结构相似的词条。比如我们拿“夹板”这个词条来说,词典里是这么解释的:用来夹住物体的板子,多用木头或金属制成。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夹[jiā]”这个读音更多是具有动词性质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为“从两个相对的方向加压力,使物体固定不动”,那么当“夹馍”的“夹”读为[jiā]时,它的词义可以解释为“中间被切开的能够使夹住的东西固定住的馍”,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食物特征的。我们再看另一个读音“夹[jiá]”,该读音下收录了“夹被”“夹衣”等词语,这里的“夹[jiá]”与前面提到的“夹[jiā]”有所不同,它不是具有动词性的,反而是形容词性的意味更大些,意为“双层的”。那么当“夹馍”的“夹”读为[jiá]时,它的词义便可以解释为“双层的馍”,这样的解释也是行得通的。所以理论上,这两个读音都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大多数将“夹”字读[jiá],这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习惯和约定俗成的结果。
或许会有人提出既然食物的主要部分是肉和馍,为何不直接命名为“肉馍”,类似于“肉包”的命名方法?其实“肉夹馍”的“夹”字就像“肉包”的“包”,体现了该食物的特点,若将“夹”字省略了,该食物的形态特点便变得不够突出了。
五、结语
通过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和结构的分析,笔者更赞同将“夹馍”认为是一个偏正式词语,里面包含两层定中结构:由“夹”修饰“馍”,再由“肉”修饰“夹馍”。这个说法既符合关中地区人们长久以来的说法,也符合词语的凝固性,将“夹馍”看成当地特有的食物,对弘扬当地的食品文化也有一定的意义。然而,与“肉夹馍”的名称结构类似的、具有相同争议的食品名称在中国其他地区仍有不少,如何看待并研究这类特殊的语言现象,仍然是当代语言文字工作者重要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