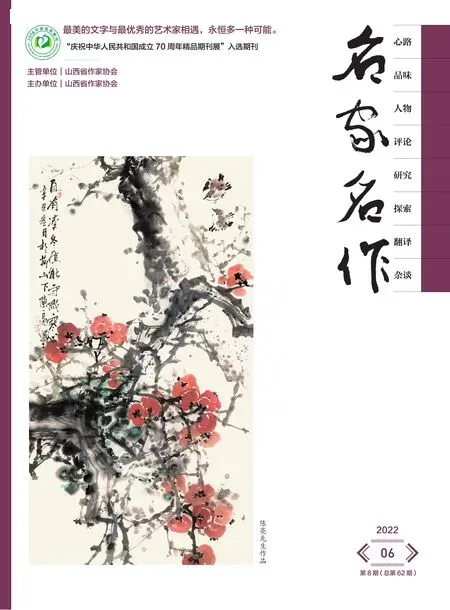从语言效果看话剧翻译—兼评《茶馆》英译
朱 娜
一、戏剧翻译与语言效果
在西方,戏剧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在西方戏剧的影响下,我国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更诞生了一批精品话剧。从本质上讲,戏剧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演员面对观众表演而且还要引起共鸣的艺术。
目前,戏剧翻译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较多。因为戏剧的本质决定了戏剧具有文学性和表演性这一双重特质,同时也决定了在翻译戏剧的时候必须能够兼顾这两方面,而这对于译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 指出服务于舞台演出应是戏剧翻译的主要目的。译入语要简洁、口语化且能反映戏剧的言外之意。此外,苏珊·巴斯耐特也指出译者要考虑到要用于舞台演出的,因而译本的语言必须容易上口,易于朗读且利于观众理解。综上所述,国外译者指出在戏剧翻译中必须考虑到语言效果。
我国学术界对于戏剧翻译的关注相当有限,其中对于戏剧翻译研究最深的应属英若诚先生。英若诚先生对戏剧翻译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思索,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独特的戏剧翻译理论和方法。在英若诚先生看来,戏剧翻译中首先必须考虑语言的简洁性和口语化,要考虑舞台上的“直接效果”,力求保证译者观众能够获得与源语言观众类似的心灵共鸣。在翻译的过程中,英若诚主张多方合作。
戏剧是语言和舞台的艺术,戏剧效果要最大限度地展现给观众,除了演员本身的表演之外,戏剧语言效果的展现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留原剧的语言艺术成了翻译家应该注重的问题。结合先前翻译理论家对戏剧翻译的建议,我们总结如下:要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原剧的语言艺术,翻译的时候必须注意戏剧语言的动作性,戏剧语言要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对于文化词语的翻译,在保留其语言效果的同时应方便译入语观众理解,戏剧的语言要简练且具有口语化的特质。
二、《茶馆》分析
《茶馆》是老舍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最负盛名的保留剧目,也是一直以来盛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在西方,《茶馆》被誉为“远东戏剧的奇迹”,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甚至特别为《茶馆》的演出升起了五星红旗。在美国,《茶馆》被誉为是中国的《推销员之死》。由此看出,《茶馆》在西方的演出获得了他们的极大认可,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这一话剧的反应是相近的。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对《茶馆》译本语言效果的研究便有了基础。
(一)语言的动作性
话剧是一种集文学性和表演性于一体的特殊的文学样式。戏剧必须要在舞台上演出才能称之为戏剧。同时,话剧语言还被用于表现故事冲突、人物性格,其具有动作性,将人物的内心状态用外部动作表现出来,更是和人物的形体动作融合在一起,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情感、思维上的变化等,推动剧情发展。
例1 常四爷:二哥!你好哇?
FORTH ELDER CHANG: Second Elder. My, my!How are you?(霍华译)
Chang: Master Song, my brother! How’ve you been?(英若诚译)
该对话发生在多年之后常四爷和松二爷再次在王利发的茶馆相遇时。常四爷和松二爷相交多年,但之前因为常四爷一句“大清国要完”而被捕入狱,两人因此多年不见。此次不经意间的相遇对二人而言实属意外。在对该句的翻译中,霍译和英译都将二人问好寒暄的功能翻译出来,但相比而言,霍译比原文多译了“My,my!”这个词语的重复充分展现了松二爷多年后乍遇老友的惊喜心情,也能使观众体会到这一惊喜。
除此之外,《茶馆》的语言动作性多次通过任务对话表现出来,而对于语言动作的表现,英若诚和霍华的处理也各不相同,译文的效果也就有所差异。如话剧中,有一段幕是在康六和人贩子刘麻子之间展开的。康六因生活所迫,被迫将女儿卖给太监做老婆,于心不忍,认为自己对不起女儿,因而想跟女儿商量一下。人贩子刘麻子则心狠手辣,在看出康六有些动摇的时候则给康六施加压力,要其尽快决定。两人在对话时,康六先是分别叹了两声“唉”,这两个字充分体现了康六刚开始犹豫和后来不得不卖女的无可奈何的心理。在霍译中,两声叹气被译成了“Ah”和“Ai”,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出康六的这一心情变化,仅仅凭借这两个语气词,英语观众可能很难理解康六此时的矛盾及无可奈何,而在英若诚先生的译文中,这两声感叹则被译为“well”和“Yes”,展现了人物最开始的犹豫不定及后来的无可奈何,其语言效果与原文接近。而后来,康六在感慨自己 “怎么对得起人”的时候,英译中加了“please”一词,使康六祈求的口吻更加明显,并带有一种绝望悲凉的感觉,同时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二)语言的性格化
话剧不同于小说等文学样式,其主要组成部分便是对话,其人物的性格、个性以及心理变化都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现的。因而话剧的语言还具有明显的性格化特征。所谓性格化,就是话如其人,人物角色的语言可以体现出他的角色性格。老舍的《茶馆》中,整部戏中的人物有七十多个,但是如此众多的人物并没有给听众紊乱的感觉,而是各个形象鲜明。这一人物形象的展现来自老舍的语言艺术,《茶馆》更是一句台词勾画一个人物。
例2 庞太监:我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EUNUCH PANG: I want something living—not a corpse.(霍译)
Eunuch Pang: I ordered something alive. I won’t take it dead!(英译)
庞太监是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为人阴险毒辣。该对话发生在庞太监第一次见到康顺子时,此时他仍然有权有势,当顺子知道自己要被卖给太监做老婆而晕倒时,庞太监的第一反应不是要救助康顺子,而是说出了自己只要活的不要死的,充分显示了庞太监的毒辣性格。在霍译中,“want”和“something”能够表现出庞太监毒辣的性格,而相比之下,英译则更能生动地表现出来庞太监阴险毒辣的性格。“ordered something”与“take it dead”二句说明,对于庞太监而言,康顺子只是其预定的一个货物,在他心底里并没有认为自己买的妻子是个人,他对买来的妻子的要求是要活的,而此刻结合其具体的语境,康顺子已经昏倒,庞太监所关心的是自己的货物是否符合自己预定的要求,更表现出了庞太监的毒辣性格。
例3 老林: 还有个娘们!
OLD LIN: Our bride.(霍译)
Lao Lin: Us and a woman.(英译)
此处“娘们”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而这样粗俗的词语却恰恰适合老林这样没有文化,从战场上逃命回来的老大粗的形象。他希望和自己的“兄弟”共用一个老婆来节省开支。因而在比较两种译文时,霍译的“bride”较为文雅,这样文雅且偏褒义的词语并不适合老林的性格,也不能表现出老林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情况。
(三)语言的简洁性和口语性
从艺术的传播方式来看,戏剧艺术是不可完全重复的一次性艺术。观众在观看话剧的过程中,如果不理解某句话,就再也没有机会“听”懂它。所以话剧的语言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口语,这样观众才不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而且考虑到戏剧语言的演出效果,语言更是要简洁有力,切忌拖沓重复。在戏剧演出时,观众听到的应该是一种干脆、工整的语言, 要有双方的对手戏,有来有回。因而在戏剧翻译中,口语化和简练变成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而《茶馆》在这方面表现更为明显,因《茶馆》描写的是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其中的语言更是以口语居多。
如《茶馆》中,有一段对话是关于秦仲义和王利发的。在对话中,秦仲义解释了自己回收房子的原因。在秦仲义的话语中,“买卖”是汉语中的口语词汇,表示一个人的商店和自己的生意。在霍译中,“establishment”是一个较文雅、正式的词语,表示机构以及大型机关,相较之下,英译中的“shop”则更加口语化。秦仲义的最后一句话中的“拢”也是一个口语化的词语,意为“把……和在一起”,相比较两个译本,同样也是英译本中的语言较为口语化。另外,从句子的角度看,对于秦仲义的第一句话,霍译将其译为了一个偏长且较为复杂的句子,而英译的处理则是分成了两个短句。虽然第一个句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但是这种简单、不完整的句型却恰恰突出了口语化的非正式的语言风格。
在《茶馆》中,每一个角色的语言都干净利落。如特务吴祥子在抓住逃兵时,与逃兵老陈有过一段对话。在该对话中,吴祥子的话是一些简短有力的话,且每句话都以 “是吧”结束,这充分勾勒出了吴祥子认为自己抓住了老陈的把柄,洋洋得意。在对它进行翻译时,霍译将其处理为整句,用If 从句表示,虽然也正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是却比英译略逊一筹。在英译中,译文用不完整的、简短的句子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这一口语化语言的使用如“Deserters, right”等更形象地刻画出了特务当时得意的嘴脸。英译中的另一优势便是语言的简练性,删繁就简。如,在本段对话中出现了两次有钱就想在北京藏起来的说法,如果两次都完整地译出,语言便显得多余、累赘。因此,英若诚先生将第二次的省略不译,不仅不会影响观众的理解,更增加了语言的简练程度。
(四)语言的文化性
话剧的语言除了具有动作性、性格化等特点之外,还具有文化性。因话剧是作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创作的,其语言势必会有当时社会文化的痕迹,而对于并不熟悉这一时期的观众来说,这样的语言便难懂了。《茶馆》横跨了半个世纪,其历史时间跨越极广,从封建社会末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描绘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因而如何将半个世纪中特有的文化传达给观众成了翻译家的主要任务。
《茶馆》中,有一段是康有为被抓之后的秦仲义和庞太监的对话。在庞太监的话中提到了中国古谚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两种译文中,译者都成功地阐释了这一谚语的含义。而霍译中“Like the eight immortals crossing the sea.”不仅将原文的字面意思翻译了出来,其随后也解释了这句谚语的意思,这样一来,便将八仙过海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传递给了听众,相对而言,翻译得较好。
而在刘麻子将康六女儿卖出之后,松二爷问刘麻子是不是又赚了不少,刘麻子回答说弄好了也就是赚个元宝而已。“元宝”是旧中国货币的一种,在清朝,“元宝”的价值是很高的,刘麻子说自己“赚个元宝”,其实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但是对于不懂这一历史情形的人来说,这一信息其实很模糊。在霍译中,元宝被直接翻为“a silver ingot”,对于不懂这段历史的外国观众来说,这样的翻译译犹未译,仍不能明白刘麻子到底赚了多少。而在英译中,这一数目被具体地翻为“twenty taels of silver”,听众再结合之前刘麻子给康六的价格便可以显而易见地明白了刘麻子获得的巨大利润,此处的文化区别便被攻克了。
三、结论
话剧是一种语言与表演艺术相结合的演出艺术。为了让观众体会到话剧的魅力,在翻译中语言效果如动作性、性格化、简练性以及文化性等方面的处理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一研究仍具有其局限性。因为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其最终的目的是舞台演出,语言效果的阐释与演员演出时的语气、语调等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音响等舞台效果也在舞台演出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而这些则是译者所无法控制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