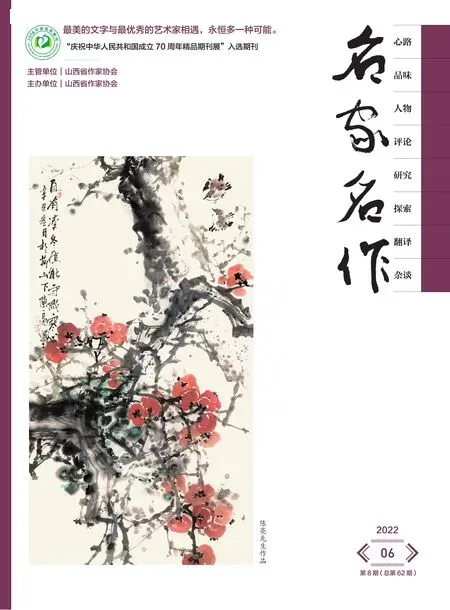由《新唐志》三级类目窥见唐代学术新变
张竞颐
一、《新唐志》三级类目的增设
汉代班固编纂的《汉书·艺文志》成为史志目录的开端。历代朝廷格外重视史志目录。唐贞观年间,官方修订的《隋书·经籍志》在《汉志》基础上,改“六分法”为“四分法”,开创了“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的四部分类法,并在其下继续划分小类,小类下不再细分。《旧唐志》延续《隋志》做法。这种分类方式属于二级分类。北宋《新唐志》对此做了突破,在部分二级类目下进一步细分,设立三级类目。其具体分类如下表。

《新唐志》中增设的“三级类目”
由表可见,《新唐志》增设的三级类目共有七个。每类三级类目前有子目小序,以“凡”字开头,与二级类目区分开来,小序统计该三级类目所收书目数量及卷数。如史部“杂传记”下“女训”类小序:“凡女训十七家,二十四部,三百八十三卷。失姓名一家,王方庆以下不著录五家,八十三卷。”正如郑樵所言:“学术既分,类例自明。”史志目录作为一朝目录书的权威代表,其中分类的聚散离合实际是各朝代学术发展情况的缩影。《新唐志》增设的三级类目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学术的演变。
二、《新唐志》三级类目溯源
(一)“实录”与“诏令”
“实录”主要记录统治者发布的政令及政治行动,是“起居注”发展演变的产物。其名称最早见于《汉书》:“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脱胎于“起居注”,但又与“起居注”不同,它属于后人撰写前朝的历史,且主记政治活动,并非像“起居注”一样实时记载帝王言行。起初实录数量较少,在史志目录中并不被重视。《隋志》仅有一部《梁皇帝实录》,且记录在“杂史”下,说明“实录”文献尚处于萌芽期。到了《旧唐志》,“实录”被挪入史部起居注下,这是符合其史书性质的。《旧唐志》“实录”著录书目包括唐前《梁皇帝实录》《梁太清实录》以及唐高宗到中宗编纂的七部,共九部。虽然《旧唐志》并未将“实录”单独分类,但与《隋志》相比,这种分类方式已经说明“实录”在当时史书编撰中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新唐志》,“实录”正式成为三级类目,且有二十八部,与《隋志》共四十四部“起居注”,仅有一部收在杂史的“实录”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诏令”作为帝王朝廷发布的政治命令及纲领在先秦时代已萌芽,较早出现并流传于世的“诏令”有《尚书》《逸周书》。《尚书》中出自古代圣贤之手的“训、命、誓、诰”等具有示范命令性的文献是“诏令”的雏形。两汉至隋代“诏令”文献数量增加。起初,“诏令”的划分方式较为复杂。《隋志》将《魏朝杂诏》《晋咸康诏》等大部分“诏令”文献归入集部总集,只有《后周太祖号令》被归入史部起居注。《旧唐志》对诏令类书籍依时代进行分类:将《晋书杂诏书》《晋杂诏书》《晋诏书黄素制》《宋永初诏》《宋元嘉诏》等晋宋诏书与《汉武故事》《汉魏吴蜀旧事》等记录朝廷政令的“故事”类书籍一同归入史部“故事”类;将宋干《诏集区别》、李德林《霸朝杂集》、温彦博《古今诏集》等后周及隋唐时期诏书归入集部“总集”类。与《隋志》相比,《旧唐志》的划分方式实际上已标志着“诏令”文献脱离集部,逐渐向史部演变的趋势。
(二)集史
《新唐志》“集史”共六部,分别为《通史》《南史》《北史》《小史》《洞史》《统史》。考其内容,《通史》与其作者梁武帝共佚。《南史》《北史》分别记述南朝宋、齐、梁、陈以及北朝魏、北齐、北周政权的兴亡,《隋志》《旧唐志》将二者收入正史。《小史》记远古至唐高宗时期史录。有人认为此书是记述轶闻琐事的著作,据学者考证,其内容取自历代正史和唐实录。章学诚对此评论道:“《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推测《统史》也属此类。因此收入正史是合理的。但在“正史”下单独设立“集史”的举措实显多余,若因这些史书都裁录自正史,那么《南史》《北史》则并不符合其标准,其划分似乎并无统一尺度。因此并未被后世目录学著作继承。
(三)女训
“女训”是对女性的教导与规范,先秦时期《诗》《书》《礼》等儒家经典蕴含着对女性礼仪规范的教育。西汉刘向作《列女传》,由此产生了第一部女训书,东汉班昭撰《女诫》成为后世宫廷教导女子之书。《隋志》《旧唐志》将该类书籍收入记录正史所不收的人物“杂传记”中。《新唐志》将《隋志》《旧唐志》“杂传记”中有关女子教导的典籍单独析出,并增加开元时期后的“女训”类典籍,体现了唐代对女子教育的重视。
(四)“神仙”与“释氏”
“神仙”为道教分支,“释氏”为佛教典籍。佛道二教斗争由来已久,历代目录书对二者如何收录一直成为焦点。“神仙”本质上与传统阐释道教教义的经典不同,属于讲求方术炼丹之类。《隋志》子部道家只记老庄等经典,道经和佛教典籍附于书尾。《旧唐志》将道经归入子部道教,并将《十门辩惑论》《通惑决疑录》等佛典一并收入,已初具三级类目模式。宋仁宗景祐年间编修的《崇文总目》则在子部设立“道家”类与“道书”类,“道家”类典籍收录《老子道德经》《庄子疏》《贺子》等阐释道家学术观点、治政理念的道家经典;“道书”类则专收仙传、仙道、灵丹、服饵等讲述求仙得道之路、长生不老之法的具有浓郁宗教性质的典籍。这一分类方式使道教典籍有了更加明确的区分,对《新唐志》子部道家小类的划分颇有启发。
(五)文史
“文史”即品评诗文的著作。该类书籍在魏晋南北朝萌芽,到唐代有一定规模的发展。起初,文史典籍在史志目录中与合“众家之作”的总集著录于集部总集类。唐人吴兢《西斋书目》始设“文史”类,主要收诗文评与史评著作。《崇文总目》《新唐志》沿用该名称,收录有关文学批评、文学旨归、文学技巧的著作。《新唐志》所收录的“文史”著作包括《翰林论》《文心雕龙》等魏晋文学批评著作及《诗例》《文格》等唐代文学理论论著。
三、由三级类目窥见唐代学术新变
(一)史书类别的革新
《新唐志》中新设的七个三级类目,有四个属于史部,体现了宋代对唐代史学的解读以及唐代史书新情形的出现。
在统治清明、国富力强的唐代,帝王十分重视从历代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重视修史。在唐初便组织修订了《晋书》《梁书》《齐书》等多部前朝国史。此外,唐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自身言行的规范及影响,唐太宗励精图治,“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这就迫切需要一种可以记载政令的史书以求统治者自身关照。记载帝王言行的起居注虽在魏晋南北朝流行,但其主要与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都希望通过编订专属起居注为标榜自身统治有关,并不能反映唐朝大一统的政治面貌,也不能达到唐帝王对以史为镜、审视自身的目的。而从实录这种既可记录君主政令,又可为君主提供参照加以约束的史书便取代起居注受到唐统治者关注。唐代将“实录”视作“帝王之书”,认为实录所记载的内容关系着一朝统治者及臣子形象,是判定帝王统治能力及群臣贤能与否的重要标准。遂把编纂实录定为一种制度,每位皇帝都必须修一部实录,记载其生平及其在位时统治情况。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受诏撰写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唐玄宗时期修《开元实录》四十七卷;武后时修《高宗实录》一百卷。“实录”数量的增加与地位的提高,致使《新唐志》编纂时将其单独列为一类,且《新唐志》“起居注”类只在《旧唐志》的基础上新增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其余所收范围均未超过《隋志》。这也说明了“起居注”的没落,实录的兴起,反映了史学发展的新要求。
此外,“诏令”的增设也反映了唐代史学的演变。与唐中期“中书门下”体制有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权加强。中书门下这一新体制正式建立。在这种体制下,宰相将地方各级上奏的奏议进行裁决处理,再向皇帝申奏,最后由皇帝下旨批准实行,由于这些步骤,皇帝控制国家政令的权力增加,也就使“诏令”在唐代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渐成为唐中后期国史编撰的主要形式,“诏令”书籍数量增加,体现在目录学分类上便是“诏令”单独成为“起居注”下的一个子目。“实录”与“诏令”三级类目的设立正是宋代史官对唐代史学的深刻理解。
(二)女子教育的兴盛
《新唐志》史部将《隋志》《旧唐志》“杂传记”中有关女子教导的典籍单独析出,并增加开元时期后的“女训”类典籍。说明唐代女训类书籍盛行,这与唐代风气较为开放、文化兼容并蓄、女子地位提高有关。社会对女子的束缚减少,人们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增加,有条件的家庭都支持女儿读书学习,名流贵族还会专门请女老师教导女儿。皇室中还有专门教导公主、后妃的专门机构,唐设内文学馆,隶属中书省“以儒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内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唐代女子教育的风靡使“女训”书应时而生,与之相对应的,《新唐志》“杂传记”下新设“女训”三级类目,也体现了唐代社会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但这种分类方式并未被后世目录书继承。
(三)佛道二教的交融
《新唐志》增设“神仙”“释氏”,正反映了佛道二教在唐朝的发展情形。唐代初年到武则天时期,历代帝王普遍认为梁武帝佞佛导致其统治败落,认为佛教无法治理天下,因而对道教加以扶持,唐太宗将同姓氏的道家鼻祖老子视为李唐先祖,甚至有意将道教改为符合统治发展的学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道家经典与论述神仙、丸药等求道之书必然数目大增。道家学说的兴盛让后代学者修订唐代史志目录时重新考虑图书分类问题。《旧唐志》在子部道家下设“道释诸说”,将佛道二教典籍收入其中。受《旧唐志》《崇文总目》影响,《新唐志》子部道家先收录道家老庄哲学经典,再设“神仙”与“释氏”小类。而佛教典籍之所以在《新唐志》《旧唐志》中一同被收入子部道家,是因为佛道二教之间的深刻渊源。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起初为立足本土,佛教主动与道教中的神仙方术思想相结合,为自身寻找合理保护层。而道教面对佛教传入对自身地位的挑战,也模仿佛教科义编制道教科义。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在争夺正统地位中不断压制对方,以求自身发展。唐代虽重道教,但统治者实际采取“三教并立”的政策,儒释道并行发展,释道二教间既有依存性又有斗争性,其依存性体现在《新唐志》中便是佛道典籍书目位置相近,斗争性则通过《新唐志》中先道后佛的收录方式反映出来。需要说明的是,《新唐志》下以“释氏”名称收录佛教文献,是以“释”家强调对佛教学说的统领,反映了融会贯通儒学与佛学要义的“释门”学者在佛教门派中的重要地位。
《新唐志》子部道家“神仙”与“释氏”两个三级类目的设置,实际反映了对道家哲学、道教仙传典籍和佛教典籍的正确认识。有学者认为这种归类方式混淆了佛道界限,笔者认为,目录书中佛道二教位置的相近,紧密联系正体现了它们之间既依存又斗争的复杂关系,是唐代佛道并行史实的典型例子。
(四)文学批评观的发展
《新唐志》“文史”类的增设与唐代更重视文史理论发展、相关著作数量增加有关。由于唐代科举制设“杂文”科,发展到唐后期成为“作诗以代帖经”,这就要求科举士子具备较高的诗歌创作水平,许多诗歌批评理论著作应科举需求问世。同时,由科举制成就的文人,不问出身,在诗歌创作上的态度尤为认真,普遍具有文学史观,“要求在文学理论上的创造与探寻”,注重研究文学理论,对魏晋南北朝诗风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力求摒弃南北朝浮夸奢靡诗风,转向对诗歌内容、格律的重视,崇尚风骨。提倡“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文学为政治和社会服务。许多学者既是诗人,也是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如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中倡导的“情绪为先”及以“质”“气”相辅的理念,实际上是对钟嵘《诗品》“直寻”与“文质并重”思想的继承。
《新唐志》“文史”类的增设影响着后世史志目录的分类方式。宋代晁公武顺应史学评论著作增多的情况,在《郡斋读书志》中将文史书中论及历史的书籍划出,设为“史评”类。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又分化为“史评”类和“诗文史”类,其划分更趋于合理。由目录学领域对文史理论典籍划分方式可见,中国传统文学文艺理论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
综合来看,尽管《新唐志》中的三级类目存在着数量较少、某些分类标准模糊等不足,但三级类目的设置是对四部分类法新的突破与发展,是书籍分类史上的重大进步,于细微之处体现了唐代学术的过渡及目录学分类精细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