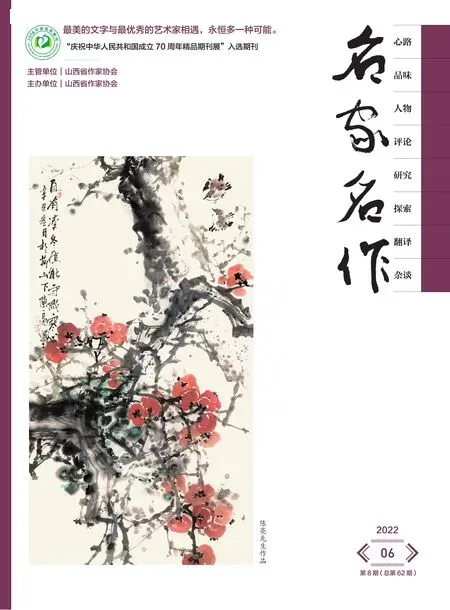辩证的乌托邦: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
李卓阳
一、莫尔式“辩证综合”乌托邦
在《未来考古学》中,莫尔的《乌托邦》是詹姆逊讨论的起点。詹姆逊的乌托邦观的辩证性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为理论基础。在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中,S1 和S2 是对立的两个项,~S1 与S1 互为矛盾,~S2 与S2 互为矛盾,四个项以及各项之间的关系是其基本展现形式。在这四项的基础之上,综合项(complex term)是同时包含S1 和S2 的项,中和项(neutral term)是同时包含~S1 和~S2 的项(如图1)。

图1 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
就“综合”与“中和”的关系,詹姆逊增加了自己的辩证法思考。在詹姆逊看来,“综合项实际上是寻求着兼得鱼和熊掌的方式,它希望通过利用对对立的两极来说被认为是积极的所有东西来定义自己”。两个对立的项是综合项形成的前提,也是辩证法的前提,综合项实则是调和对立的一种方式。综合项将对立项中积极的因素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结合,统一了各项中肯定的因素,形成了对S1 和S2 状态的超越。因此,在詹姆逊的意义上,综合项形成了辩证综合。
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介入莫尔的乌托邦,可以发现莫尔式乌托邦意象的根本特征在詹姆逊的意义上展现为“辩证综合”。莫尔式乌托邦首先是乌托邦科学与乌托邦意识形态的辩证综合。乌托邦的科学性表现为科学理性的规划,涉及城市建设、制度体制以及社会结构等。如詹姆逊所言,“莫尔的文本满有信心地给了我们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社会宪法的东西”。乌托邦意识形态在莫尔式乌托邦中则呈现为两方面,分别是莫尔的社会情境性的显现以及其个人愿望的满足。所谓情境性,是指个体“所面对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国家、历史的情境性”。乌托邦的形成在詹姆逊看来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莫尔对乌托邦的创造源于对特定环境的回应。透过乌托邦的表面,可以发现他性和差异源于对詹姆逊所谓的“乌托邦原素材”的拼凑,莫尔假想岛屿的结构正是由来自英国社会的乌托邦原素材经改造和重组后搭建起来的。因此莫尔式乌托邦实则是对其社会情境性的间接呈现,这种呈现旨在改进社会环境,是一种由乌托邦冲动驱动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下的呈现。詹姆逊指出这种拼凑和被拼凑在一起的乌托邦原素材本身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信息。莫尔个人愿望的满足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呈现的另一方面。在詹姆逊看来,“愿望的满足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莫尔对乌托邦细节的设计以及解释即为例证之一。乌托邦中的教堂光线昏暗,莫尔解释“微弱的光能使精神集中,虔诚得到促进”。这种特别的说明作为个人愿望满足的表征,反映了莫尔本人的意识形态偏见。乌托邦意识形态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乌托邦科学的理性,形成了对乌托邦科学的否定。乌托邦科学与乌托邦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两极,但在詹姆逊看来,莫尔实际上对两者进行了调和。不论乌托邦科学还是乌托邦意识形态,对莫尔本人来说积极的因素都得到了保留和结合,于是乌托邦架构起了一个乌托邦科学和乌托邦意识形态得以共存的空间。由此,莫尔式乌托邦形成了兼得鱼和熊掌的辩证综合。
此外,詹姆逊视角下的莫尔式乌托邦也呈现为乌托邦体裁与反乌托邦体裁的辩证综合。达科·苏文指出,乌托邦体裁“是对根本不同的另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的描述;这个社会中的组织关系要比作者所处的社会更完美;相对于通常的抽象的乌托邦计划而言独特的赋予个性特征的任何建构”。苏文对乌托邦体裁的定义主要包含两个要素。首先,乌托邦体裁应是对乌托邦的具体建构。其次,乌托邦文本中的社会环境体制相比于作者所处社会要更加完善。不同于抽象的乌托邦计划,莫尔完整而具体地构建了乌托邦,同时与英国社会彼时状况形成对比。显然,莫尔的文本汇集了乌托邦体裁所需的积极因素。反乌托邦体裁是对乌托邦体裁的否定性回应。詹姆逊认为,“真正的反乌托邦总是被一种反驳乌托邦的强烈的欲望所驱使的”。其次,库玛(Kumar)指出反乌托邦的产生要“从乌托邦中撷取原材料,并以一种否定乌托邦所肯定的事物的方式重组这些材料”。综合来看,乌托邦的存在是反乌托邦产生的前提,反乌托邦作为乌托邦的对立面表现出对乌托邦的不信任,这种质疑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就有所体现。乌托邦中的同一性被认为是反乌托邦焦虑产生的根源。正如詹姆逊所言,“莫尔在同一性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反面的乌托邦”。因此,莫尔的乌托邦除了包含乌托邦因素之外,“也包含了反乌托邦和对它自身进行模仿或讽刺的全部组成部分”,乌托邦中的反乌托邦因素形成了对自身的否定。显然,两种元素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同时存在,乌托邦被反乌托邦的部分质疑,但乌托邦却并未因此消除。这种结合对应于符号学矩形中的综合项,也就是乌托邦在书中的辩证呈现。
莫尔式“辩证综合”乌托邦在詹姆逊的视角下是乌托邦传统的起点和内核,综合项展现的辩证结合也向来被很多人视为就是乌托邦,而詹姆逊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好的乌托邦主义,因为它“建立在表现论和肯定性内容的幻象基础上”。但詹姆逊并未否定综合项的意义,作为调和对立面的一种方式,综合项给乌托邦带来了空间,提供给我们同时思考对立面的机会。然而,莫尔对乌托邦的静态想象被反乌托邦主义质疑是脱离现实、出离历史语境的,反乌托邦主义认为乌托邦会引发历史的停滞和终结。就此,詹姆逊转向科幻小说,试图在其中发掘出可能的回应。
二、科幻小说式“辩证中和”乌托邦
詹姆逊认同达科·苏文的思路,“相信乌托邦是科幻小说这一更宽泛的文学形式中的一个社会经济的子类型”。他由此出发,把发挥了乌托邦功能的科幻小说纳入了乌托邦的讨论范围。詹姆逊意义上的“辩证中和”乌托邦是以符号学矩形中的中和项为理论基础的。詹姆逊指出中和项并不希望同时拥有两种肯定性,相反,“它希望保留两种否定性或缺乏性特征,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否定”。两个否定项不会在中和的状态中被消除,相反,否定项会被一并保留并加强。因此,辩证中和的乌托邦意味着否定项相互作用的状态,各乌托邦可能性相互否定却又不相互削弱。在《未来考古学》中,科幻小说式“辩证中和”乌托邦被进一步划分为两个维度,即辩证复调乌托邦与辩证无力乌托邦。在詹姆逊的视角下,罗宾逊的科幻小说包含的乌托邦属于辩证复调乌托邦,奥尔迪斯的科幻小说中展现的局部乌托邦属于辩证无力乌托邦。
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在詹姆逊的意义上展现了辩证复调乌托邦。詹姆逊沿用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复调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复调的否定性意涵。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观,意在突出“众多各自独立的意识在相互交锋”,并不能被归结成一个完整的独白。詹姆逊对复调概念的使用就是建立在复调小说对“交锋”强调的基础之上,交锋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冲突碰撞。在复调式乌托邦中,彼此独立各异的乌托邦可能性之间相互否定,不断地展开交锋,形成不稳定的共存,与符号学矩形中的中和项相呼应。乌托邦的未来由此充满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开辟出了乌托邦得以被想象而成的空间。
在詹姆逊看来,火星作为乌托邦之所以呈现为辩证的复调,是因为火星所展现出的各类乌托邦选择间的冲突及共存。小说中“最初的一百人”本就是多元化的集体,人物的多元化带来了立场的多元化,各人物间的冲突形成了各立场间的张力,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更高层面的发展重组,不仅为多元决定论提供了抽象的代表,也为复调中各部分的辩证运作提供了象征性说明。各立场象征着独立各异的乌托邦可能性,它们之间不断辩争,甚至不可调和,但詹姆逊相信“这正是当代乌托邦的优点和成就”。由此,在詹姆逊的意义上,火星作为乌托邦呈现为辩证的复调。同时,詹姆逊挖掘了火星作为辩证复调乌托邦所具备的现实主义特点,作为对反乌托邦主义的抵抗。一方面,小说以大量现实科学事实作为解决问题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小说并未试图掩盖乌托邦形成的复杂性。詹姆逊认为可以用多元决定论概括火星上问题解决的结构。也就是说,在火星形成乌托邦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共存,无法被单独离析。通过多元决定论,罗宾逊展现了乌托邦形成的复杂性,由此乌托邦表现为动态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
除了辩证复调式乌托邦,辩证无力式乌托邦是辩证中和乌托邦的另外一个子类型。“无力”在詹姆逊的意义上特指想象未来的无力。科幻小说代表着对差异和未知的想象与描摹,但在詹姆逊看来,科幻小说并不能使未来具有生命力,也不能使极端他性得以被呈现和理解,“相反,它最深层的功能是一再地证明和渲染,尽管我们具有表面上看起来很充分的表现,但实际上对于想象和象征化地描述未来我们还是无能为力”。但这种无力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的想象只能以失败告终。无力让我们得以发现围困想象力的壁垒,触发对想象边界的思考,进而指向了对壁垒和边界的突破。因此无力呈现为既未成功又未失败的中和项状态,意味着对未来的想象始终是辩证运作的过程,无力由此在凝固的对立中开辟了未知的空间。如果说遥远的未来表现为乌托邦的样态,那么詹姆逊强调的便是当下的矛盾冲突如何经过辩证的运作和关联指向乌托邦式的未来。
奥尔迪斯的科幻小说中展现的局部乌托邦可以被主题化为辩证无力的乌托邦。奥尔迪斯的《星河战队》在詹姆逊看来是一部通过描写“未来历史”来发挥疏离作用的科幻小说。《星河战队》企图在与现实隔离的飞船上重新发明历史,描绘一个不同于经验世界的宇宙,在此意义上飞船空间发挥了乌托邦的作用。在飞船的未来形式下,奥尔迪斯试图在与现实隔离的巨大空间内想象设计不同的制度与文化,但“不管小说家具有怎样的才华,他的创作总是必须来自对真实的推断或与真实的类比”。通过将未来形式与类比真实历史的内容拼接到一起,奥尔迪斯创造了呈现为“未来历史”的飞船世界。奥尔迪斯采用了未来的形式,看起来是要描绘未来,但呈现的实际上是装在未来形式下的人造性历史。因此小说并没有真正描述出未来的样态,想象力的局限使我们更加确定“作者在创造另一个真正不同的宇宙时所表现出来的终极的无力”。在《星河战队》中,对未来的想象没有达成,但这种努力已经将我们带离了现实的原点,无力的辩证性在想象的过程中得到确认。詹姆逊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他称之为拼贴画的组织机制,未来的元素同历史的元素结合,来自不同文学样式的元素相结合,发挥了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最重要的作用,即与现实之间的疏离。疏离将我们同自身的处境拉开距离,也是在这段距离中想象的困境得以明晰。相比于对未来的想象,无力带来的对现实的冲击成为聚焦点,指向了未知的可能性。
詹姆逊坚持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启动历史感,让它再次开始传递微弱的时间、差异性、变化、乌托邦的信号”。科幻小说则为此提供了一种迂回的解决策略,通过站在科幻小说中的未来视角,我们的当下得以被当作历史来理解,现实和未来由此建立起联系。科幻小说虽然并不能真正展现一个绝对差异化的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幻小说所做的努力是失效的。科幻小说想象未来的无力唤醒了我们对于失去未来的担忧,提醒我们认识到当下的禁锢,由此我们的注意力得以集中在对当下的突破上,集中在对不可能的思考之上。因此,对未来想象的无力包含了詹姆逊败中求胜的辩证逻辑。直面自己想象乌托邦的无力,这看起来似乎有些悲观,但“如果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坚定地被锁在一个没有未来的现在,并意识到所有限制我们对未来想象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取得一些成就”。
三、结语
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当代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中呈现的乌托邦观以辩证性为核心特点。这种乌托邦观包含“辩证综合”和“辩证中和”两种样态,二者构成了乌托邦矩形的两级。莫尔“辩证综合”式乌托邦是乌托邦传统的内核,由此发展出可划分为辩证复调的和辩证无力的“辩证中和”式乌托邦。詹姆逊以否定性的期望辩证地看待乌托邦,强调乌托邦对当下治疗性的干预,强调对当下的批判和否定以及这种否定带来的生产性。通过辩证的乌托邦,詹姆逊试图打破反乌托邦对乌托邦传统的围困,并重建乌托邦在后现代当下的核心意涵。辩证的乌托邦并非脱离现实,而是提供给我们挣脱现实、审视现实的机会。辩证的乌托邦也并未出离历史,而是试图带领我们重回历史,重建历史感的努力,而这正是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坚持。通过辩证的乌托邦,詹姆逊想要实现的是对现实的不屈从,是对想象力的释放,是在辩证的过程中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