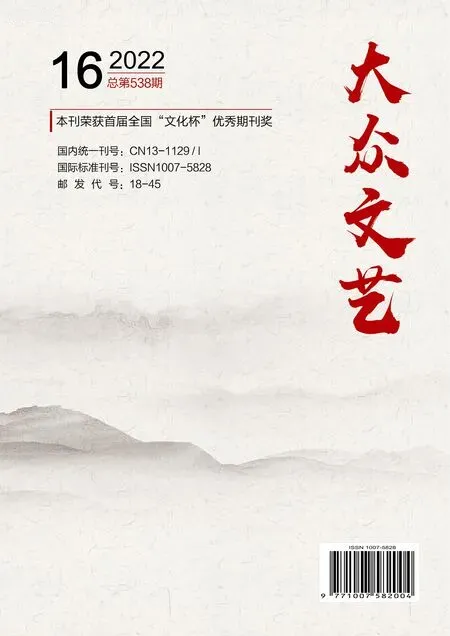浅析第五代导演电影的文学性
王继国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山东聊城 252000)
电影学术界通常认为第五代导演电影的影像美学是对传统中国电影叙事美学的一次冲击,认为第五代导演在电影美学上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文学性”。然而,因为第五代导演对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以及对当时社会和民族集体命运的思考与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使得第五代电影在整体风格呈现上仍具有十分强烈的文学性,尤其是将把第五代导演和第四代导演、第六代导演相比较,这种文学性更加凸显。正是这种文学性,使得《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活着》等一批风格鲜明、意蕴深厚的电影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经典和巅峰之作。
从叙事角度看,“美国电影之父”格里菲斯在谈道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电影是小说化了的或讲故事的形式;从电影语言的呈现层面,罗曼•雅各布森则认为“文学语言是通过强化、凝聚、扭曲、缩短、拉长、颠倒等手段,使得日常语言陌生化”。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无论是在电影语言、电影叙事还是思想内核上,都颇具文学性。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可以说是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完成了一次对话,互相凸显了各自艺术形式的特色,被改编的文学作品被赋予更多层次的阐释,电影因其文学性也更加厚重而意蕴深刻。
一、创作来源——文学作品的改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蓬勃发展、创作井喷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电影与文学有着高度密切的融合与交融。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吴子牛等,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了大量养分,把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一大批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搬上大荧幕,形成了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线。
第五代导演对文学作品的青睐,源自其与作家相似的成长背景、学习经历和文化根脉。80年代,新时期思想的活跃,文学艺术界也试图在废墟中开辟一番新天地,亟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培育一批生力军迫在眉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82届的这批电影导演,组成了第五代电影人的主流,宣告中国电影新纪元的到来;1988年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培育了一批日后成长为国内外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文坛。思想活跃、创作力旺盛,是他们的共同的精神面貌;反思时代、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内核。彼时,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的强烈冲击下面临转型,而中国文学也百废待兴,这又赋予他们相同的文化担当和民族责任感。因此,第五代导演很容易在这批当代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共鸣。北大教授陈平原在访谈中曾谈道:“八十年代的文学、学术、艺术等,是一个整体。包括寻根文学啊,第五代导演呀,还有文化热什么的,在精神上有共通性。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但互相呼应,同气相求”。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中先锋的写作风格和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成了第五代导演有了最合适的创作来源。
1987年,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问世,电影由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其后续的电影《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根据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改编,21世纪以来的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陈凯歌的《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分别改编自阿城、史铁生和李碧华的同名小说。还有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周晓文的《二嫫》、黄建新的《黑炮事件》等。这些当代中国电影史上响当当的名字,都来源于当时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像张艺谋所说“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他从两个方面阐释了文学带给他的电影创作灵感,一个是风格,一个是内涵。
二、电影语言的文学性
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风格在第五代电影中得到一种影像化的延伸和彰显。从第五代电影的台词来看,通常带有一种站在大众文化对立面的精英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有别于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表达,相较通俗、浅近的生活化语言,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表现力、感染力,注重诗意呈现和个性化表达。以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为例,梨园行的关师傅训诫徒弟“自古人生一世,需有一技之长,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全在年轻”;程蝶衣揭发段小楼“我也揭发!揭发姹紫嫣红,揭发断壁颓垣!”四爷赏识程蝶衣发出的惊叹“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此貌非你莫有”。人物语言不仅十分贴合人物形象和身份,且含蓄并具有隐喻性,更有大量戏曲语言的加持,使得整部电影的台词极富文学性。
众所周知,莫言的作品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强烈的主观感觉、绚丽诡谲的语言著称,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红高粱家族》在1987年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用镜头语言完美还原了莫言小说的叙事语言,描写红高粱地时莫言在小说中这样写道:“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而在《红高粱》电影中,张艺谋将大面积的红色调铺满整个银幕,红色的高粱地、红色的天空、红色的酒水,红色的刺眼日光,红色的衣服和皮肤,再到一个个长镜头的运用、祭酒剥皮的仪式化展现,诠释了小说中高密乡人们的自然、热烈和故事的戏剧性,视听语言使原有的文学语言更加的具象化。在这里,张艺谋用色彩和构图赋予画面以文学艺术性。
另一个电影语言的文学性表现便是“意象”的塑造,“意象”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融合,用客观物象来表达哲理观念和思想内涵。而第五代导演通常会让视觉意象化,“意象”作为一种导演传递思想的载体随处可见。比如田壮壮的《盗马贼》中,反复出现的祈福转经筒和天葬仪式中的神鹰就是一种代表藏族人民信仰的意象,让观众联想到“人与宗教”“人与天命”之间的神秘关联。《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灯笼和脚锤是一种象征“一夫多妻制”封建礼教的意象,高高的青灰色院墙则是代表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黄健中的《良家妇女》结尾“生育”的浮雕、“裹足”的浮雕、“踩碓”的浮雕、“嫁女”的浮雕、“沉塘”的浮出、“哭丧”的浮雕……更是传统妇女一生具象化的陈述”。
三、电影叙事的文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道文学的六个要素时,把情节应居于首位,认为情节就是叙事之事。通过研究第五代电影,我们能发现本时期的电影叙事已较中国以往电影有了极大的改革和突破,在着重凸显影像叙事的基础上,把文学叙事的技巧加入影片中,赋予作品以浓烈的先锋色彩。
像小说一样,第五代电影擅长灵活变换叙事视点,不再是统一运用上帝视角。比如《红高粱》,采用九儿和余占鳌的孙子视角来讲述他爷爷奶奶的故事,同时加入了旁白,这种远离中心人物视角的讲述方式给故事带来了一定的疏离感和主观性,尤其是影片结束的时候又用镜头切入了豆官的视角,他看什么都是红色的,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燃烧的高粱地、人们的鲜血、天空和太阳,红的耀眼。
张艺谋的《英雄》的叙事方式更为独特,显然是借鉴了日本电影《罗生门》,影片在无名与秦王二人的对话中产生,虚实交替、真假参半、扑朔迷离,几位刺客的形象逐渐丰满,刺秦的故事逐渐清晰。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进行不同视角和不同立场的叙述,使叙事有一种更广角的摄取故事内容的角度,能够更加立体的呈现故事的全貌。通过几个“非全貌”故事,一点点引导观众自己去重构整个故事脉络。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第五代电影的叙事不再简单以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讲故事,而是把更多的主导权交给了观众,麦克卢汉认为在电影中人人都可以大量插入自己的解读。田壮壮的《盗马贼》以艰涩难懂著称,不仅拍出了散文的诗意,更拍出了意识流的感觉,而电影最为重要的情节叙事却被忽略,观众很难去定义这是一个什么故事,故事的起承转合表达也是极不明显的,或者说,导演隐藏了情节,让观众在他诸多的镜头中自己去拼凑情节,去还原故事。大量的藏民念经祈福的场景、触目惊心的天葬仪式、草原辽阔的长镜头,都不是故事情节的展现,也无助于情节发展,但这些镜头语言传达了藏民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能让观众在心中勾勒出盗马贼罗尔布复杂的心路历程。
从时空角度来看,第五代电影叙事具有某种“史诗性”,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反映出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命运,表现出对宏大命题的思考。具体表现就是叙事时间跨度较大,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通过讲述主人公富贵通过男主人公福贵一生的坎坷经历,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影片通过富贵的回忆讲述,一个平凡家庭在简化的历史背景下,在大时代的裹挟下,历经苦难,展现时代的荒谬。《霸王别姬》从1924年的北平,到1977年结束“文革”动荡,从程蝶衣小时候被母亲送入戏班子,到最后在北京戏院的台子上自刎,通过讲述程蝶衣和段小楼二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对于人性的思考,对于时代变迁的感慨。
四、电影内核的反思性与批判性
“电影的文学性,不仅体现在电影剧本上,更体现在一种以文载道的人文关怀、思想传递的功能上,体现在一种深邃的思想内涵和恢宏的史诗般的文学韵味上”。第五代导演,同“寻根文学”一样,都有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怀,在面对本土的发展和西方的冲击时,有很明确的社会关切和责任意识。用他们镜头语言独有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传达这种反思和情怀。
“即便到今天,我们看陈凯歌的电影,都有这种状态。使命感,英雄主义、浪漫激情,还有一点‘时不我待’,或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挺悲壮的”。陈凯歌的电影,总是充满对文化和历史的忧思,因此“隐喻性”是陈电影的一大特色。最典型的就是短片《百花深处》,冯疯子央求搬家公司进行了一场并不存在的搬家仪式,紫檀衣橱、堂屋条案、前清灯座等代表着老北京的传统,而断壁颓垣上的“拆”字、高楼大厦、立交桥则象征着现代对传统的冲击与破坏,围剿与涤荡,导演最终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的消逝,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反思了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种文化的缺失和文化信仰的坍塌现象。《黄土地》作为第五代电影的奠基之作,阐释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人对于土地那种原始而复杂的情感,折射出了新时期中国人誓要变革的决心。《孩子王》里孤独的乡村教师老杆那句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反思了文化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制约和束缚,从深层次上是在探索新时期中国文化如何破旧立新,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这种对民族文化和国人集体命运的关怀是陈凯歌电影乃至第五代影人最鲜明的特色。
张艺谋擅长把个人命运放在时代波澜壮阔的大背景下,营造一种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力感,表现出对个体命运的深厚关怀。电影《活着》通过富家少爷福贵跌宕起伏的一生,刻画了小人物在特定时代下被各种历史事件所裹挟而产生的现实悲苦,流露出个人命运在历史巨轮的碾压下的一种荒诞感。《归来》同样是阐述被社会和历史的变动所扭曲的人生,以及由此带来的衍生,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时代的错误将陆焉识和妻子强制分离20多年,女儿也因为父亲的经历而屡屡碰壁,一个原本平凡而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此时不知该将这种悲剧性归因于何处,反而更使这种悲剧性找不到出口,深刻地揭露了动荡的时代曾带给国人的伤痛。
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人用自己独特的影像语言孜孜探索中国文化的根脉和未来,反思民族命运的何去何从,探求人性最深处的幽微光芒,不仅有着与文学家一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将电影这门艺术的文学批判性发挥到极致,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学范式,塑造了第五代电影的魂魄和精神。
电影艺术,不仅局限于视听与影像,它本身承载着更多的文学性,而第五代电影就是电影“文学性”的典型代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电影受到好莱坞电影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巨大冲击,使得电影无论是从视听语言、镜头美学还是思想韵味上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退步,电影的文学性面临极大的消解,如何在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下重拾电影的文学性,是当下电影人创作面临的严肃问题。
①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76.
②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36.
③李尔葳.当红巨星——巩俐、张艺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58.
④莫言.红高粱家族[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45.
⑤朱斌峰.文化的符码 审美的意象——论第五代导演电影视觉意象的运用[J].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9(03):31-34.
⑥钟菁,黎风.电影的文学性与“文学电影”[J].当代文坛,2015(03):97-100.
⑦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23.